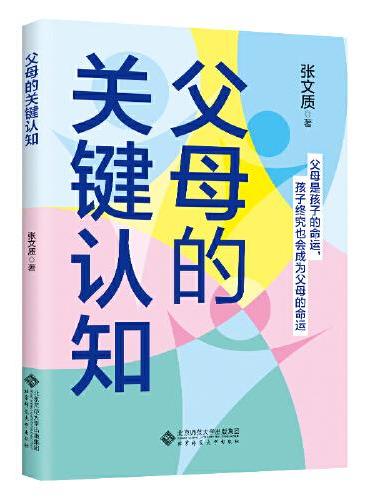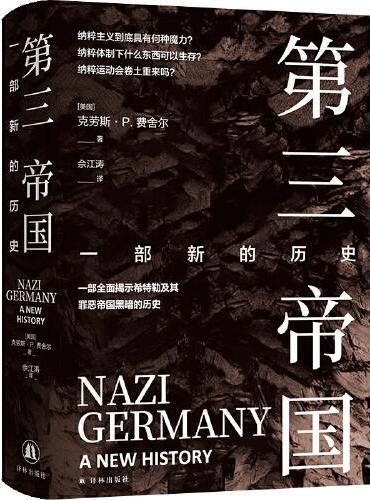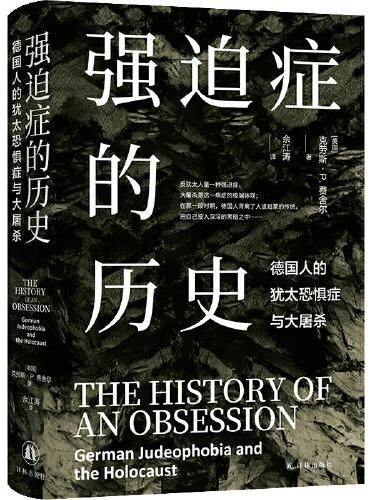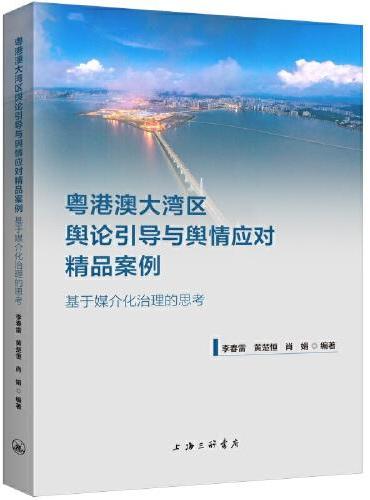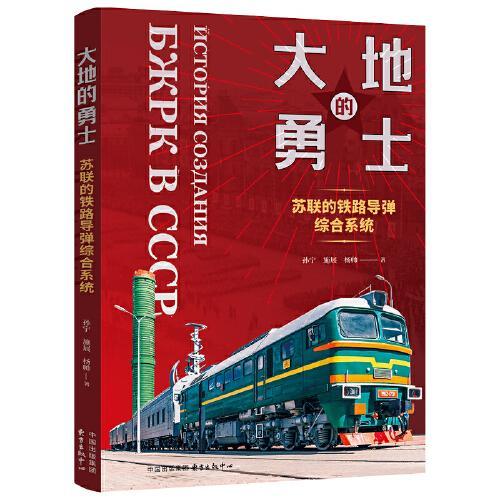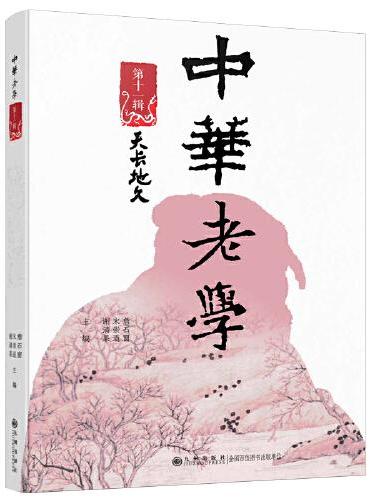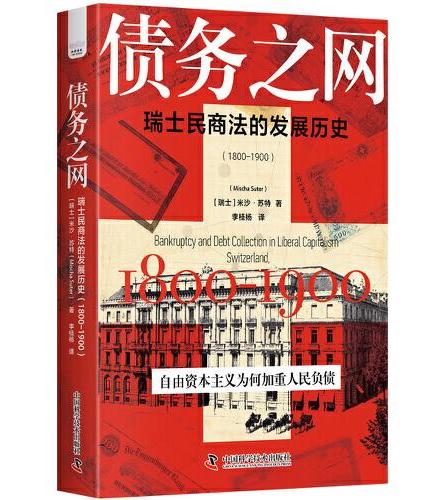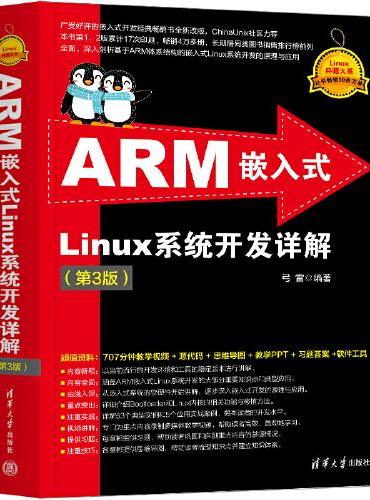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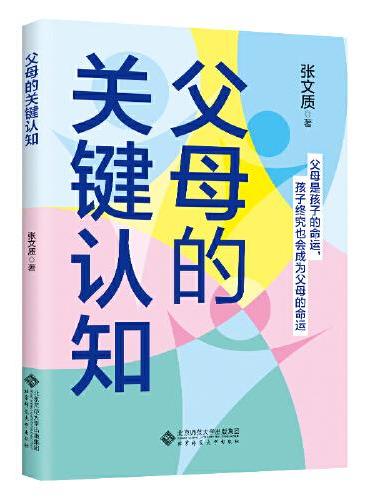
《
父母的关键认知
》
售價:NT$
2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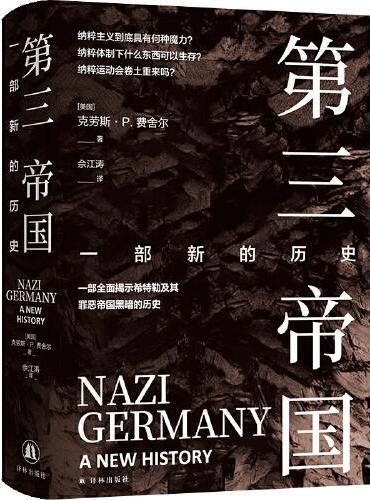
《
第三帝国:一部新的历史(纳粹主义具有何种魔力?纳粹运动会卷土重来吗?一部全面揭示希特勒及其罪恶帝国黑暗的历史)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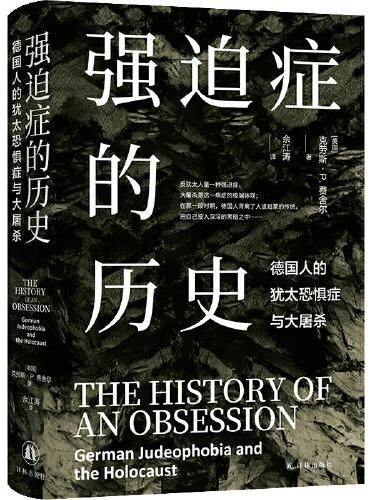
《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德国历史上的反犹文化源自哪里?如何演化为战争对犹太人灭绝性的种族杀戮?德国历史研究专家克劳斯·费舍尔叙述德国反犹史及其极端形态的典范之作)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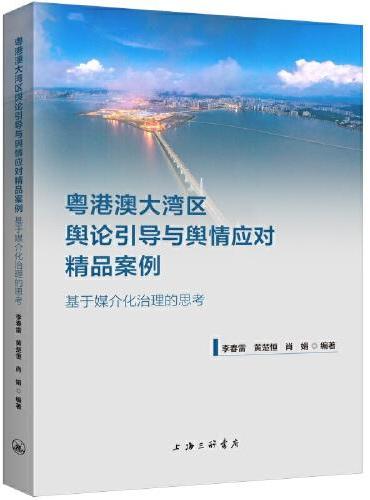
《
粤港澳大湾区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精品案例:基于媒介化治理的思考
》
售價:NT$
4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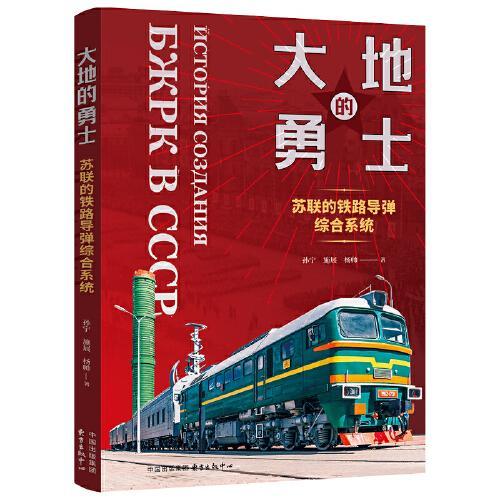
《
大地的勇士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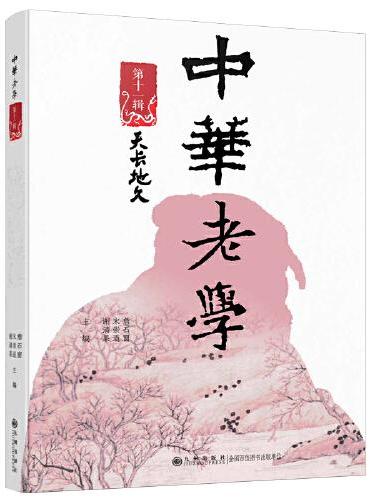
《
中华老学·第十一辑
》
售價:NT$
3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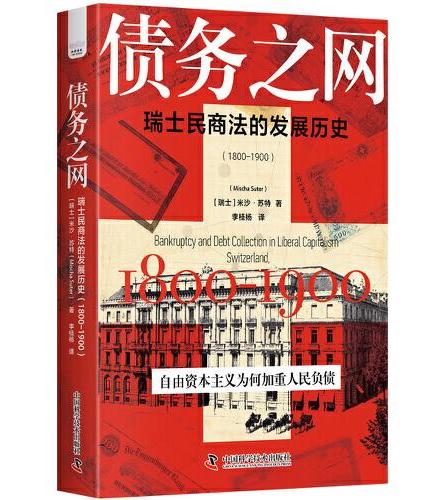
《
债务之网:瑞士民商法的发展历史(1800-1900)
》
售價:NT$
3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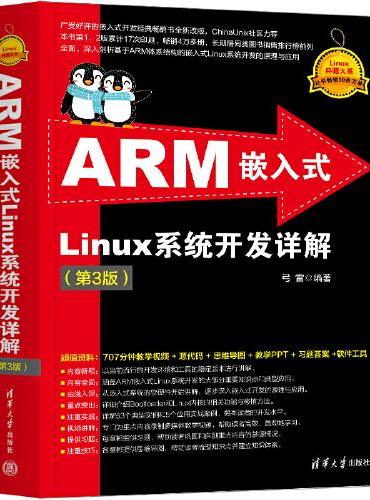
《
ARM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详解(第3版)
》
售價:NT$
595.0
|
| 編輯推薦: |
|
在近三十年的创作中,毕飞宇不以高产著称,但他的每一部作品从创作伊始,就被赋予了坚实的质地,都折射出毕飞宇文字的一个独特品质,那就是他始终如一的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坚持和维护。他的文字始终关注人,关注人和他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关注人的疼痛,关注这个社会的病痛,这个几乎可以说从五四以来的一个经典命题,毕飞宇在他的创作中,给予了新时期的承担和回应。这正是毕飞宇创作可以一直保持较高水准的原点所在,也是他赢得广泛而经久的尊重和热爱的内因。他的作品值得大家经久阅读。
|
| 內容簡介: |
内容简介: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以记叙性非虚构文体为孩子讲述作者在兴化街头长大的童年生活,红领巾泳裤,奶奶的蚕豆等情节感人至深。全文庄重与诙谐并具,情感与记忆交织,不可多得。书中具体收录了《补丁》《游泳裤》《九月的云》《水利工地》《盲人老大朱》等作品。
|
| 關於作者: |
|
毕飞宇,出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南京大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毕飞宇文集》四卷(2003),《毕飞宇作品集》七卷(2009),《毕飞宇作品集》九卷(2015),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散文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写满字的空间》;文学讲稿《小说课》;文学对话录《小说生活——毕飞宇、张莉对话录》。《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Three Sisters》(《玉米》《玉秀》《玉秧》)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7年获法国文化部“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作品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在海外发行。
|
| 目錄:
|
目录
楔子
章衣食住行
补丁
游泳裤
口袋
袜子
玉米秆
汤圆
蚕豆
庙
草房子
家具手电筒
家具热水瓶
水上行路
第二章玩过的东西
桑树
鸟窝
九月的云
蒲苇棒
蚂蟥
红蜻蜓
第三章我和动物们
猪
马
牛
羊
第四章手艺人
木匠
瓦匠
弹棉花的
锡匠
篾匠
皮匠
剃头匠
第五章大地
麦地
稻田
棉花地
自留地
荒地
第六章童年情境
磨坊
水利工地
打孩子
葬礼
现场大会
父亲的姓名(1)
父亲的姓名(2)
池塘
床
第七章几个人
盲人老大朱
哑巴
黄俊祥
陈德荣
|
| 內容試閱:
|
楔子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叫“杨家庄”,我的父母亲则是杨家庄小学的乡村教师。1969年,父母亲的工作调动了,我们一家要去一个叫“陆王”的村子。这一调,生活的谜底揭开了,五岁的孩子知道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我们不是“杨家庄”的,我们家和“杨家庄”没有任何关系,这里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子、舅舅、舅妈全是假的。去“陆王”也没有什么不好,可五岁的孩子感受到了一件事,他的生活被连根拔起了,一敲,所有的泥土都掉光了,光秃秃的。
我们家在“陆王”一直生活到1975 年。1975 年,一切都好好的,父母的工作又调动了,我们要去一个叫“中堡”的镇子了——去“中堡”镇同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可十一岁的少年知道了,他的生活将再一次被连根拔起,他所有的玩伴将杳无踪影。
比起我的二姐来,我要幸运一些,我少颠簸了一次,我的二姐还在“东方红村”待过的呢。
比起我的大姐来,我的二姐又要幸运一些,我的大姐还在“棒徐村”待过的呢。
咳,这么多的地名,有些乱了,还是重点说一说我的“陆王村”吧。
就在“陆王村”,我知道了一件大事:我不只是和“杨家庄”“陆王村”没有关系,我甚至和我周边的农田也没有关系,我的户口是“国家”的。告诉我这个秘密的是我的一个邻居,他比我大七八岁——他的依据是我们家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本。一个孩子哪里能弄得懂“户口”“国家”这样尖端的科技话题呢?我真实的感受是这样的:我背叛了自己的故乡,和“汉奸”也差不多——你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呢?答不上来的。“国家”不可企及。等我知道“国家户口”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是一个青年了。
当然了,我不会为此伤神,更不会去问我的父母。孩子的直觉是惊人的——我们来到这里,不会是一件光彩的事;孩子的世故也是惊人的——父母亲一直不说的事,你就永远也不要去问。
漂。漂啊漂。漂过来漂过去,有一样东西在我的血液里反而根深蒂固了:远方。我知道我来自远方,我也隐隐约约地知道,我的将来也在远方。我不属于的仅仅是“这里”。
1979年,我们家离开中堡镇,去了一个叫“兴化”的县城。作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我的生活又一次被连根拔起了。老实说,这一次是我向往的,一个崭新的“远方”在等着我呢。但十五岁的少年犯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容易犯的错,我过于乐观了。在兴化,我们一无所有,连一个平米的住房都没有。我们一家就待在一个叫“人民旅社”的旅店里,所有的旅客经过“我们家”门口的时候,瞳孔里都有狐疑的目光。我也很狐疑。父亲说过的,我们“回老家”了,而我的生活为什么如此破碎?一切都是临时的,敷衍的。我的家居然还有代号:201 、203 ,每一床被子和每一个枕头上都有鲜红的“人民旅社”。到了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拿起碗,穿越大街,去一家机关食堂——我至今不喜欢酒店的生活,多么豪华的酒店我都不喜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