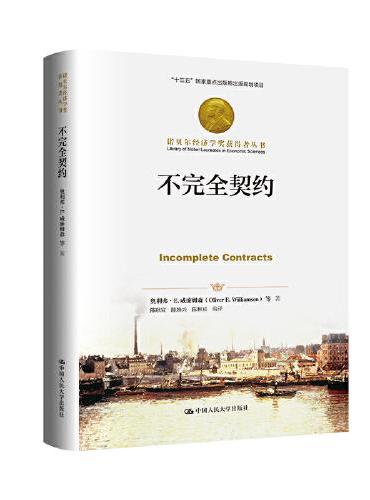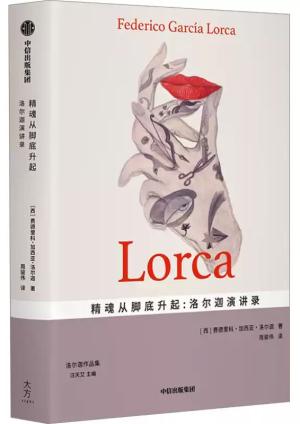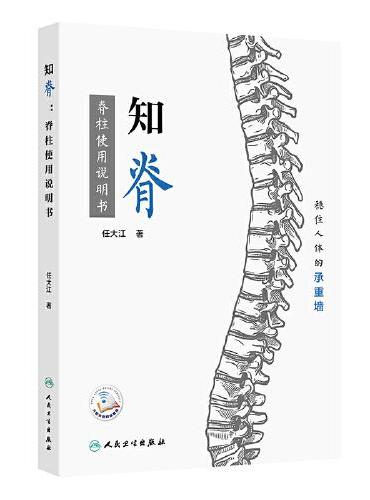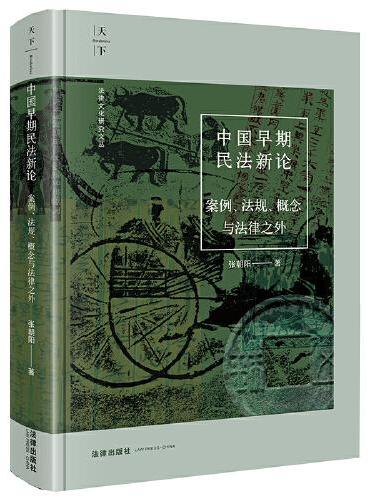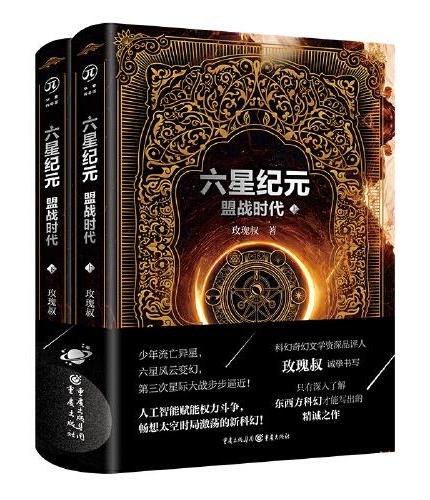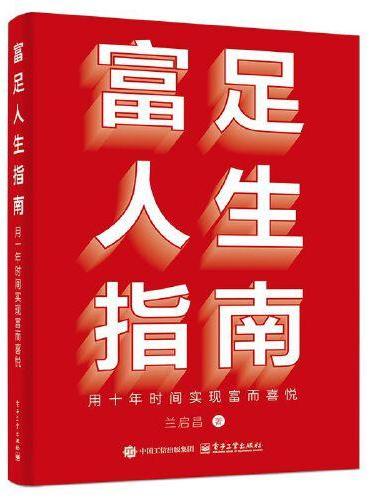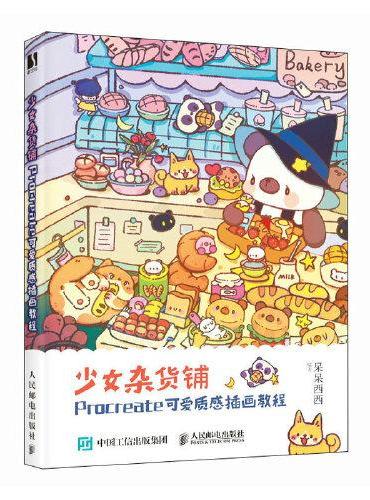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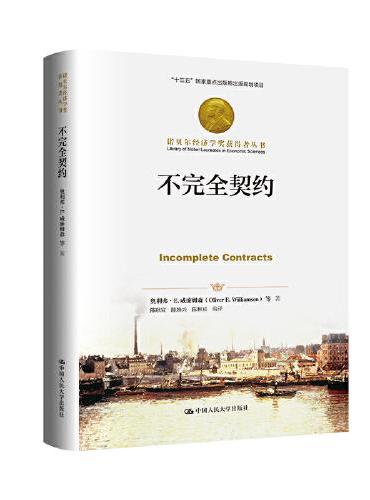
《
不完全契约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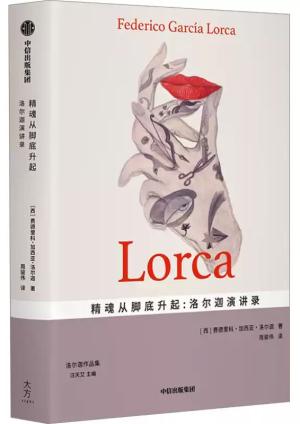
《
精魂从脚底升起:洛尔迦演讲录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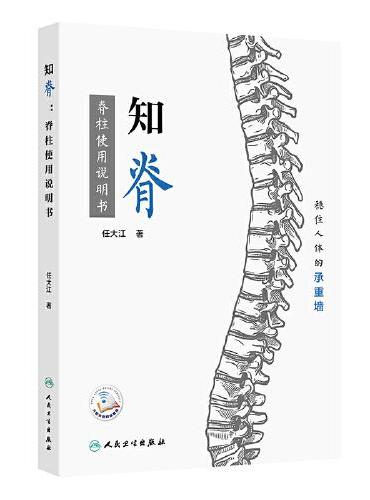
《
知脊:脊柱使用说明书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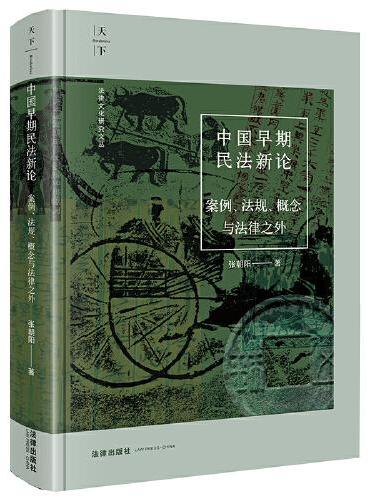
《
中国早期民法新论:案例、法规、概念与法律之外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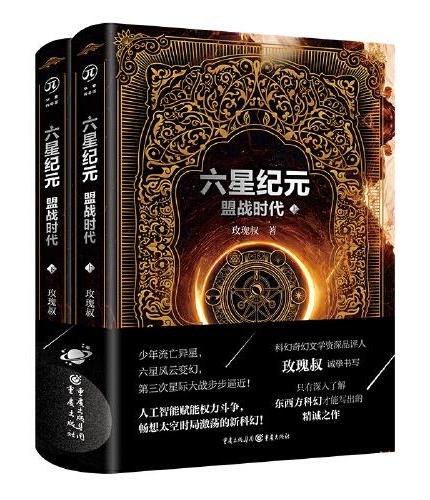
《
六星纪元:盟战时代
》
售價:NT$
398.0

《
明代女真史
》
售價:NT$
4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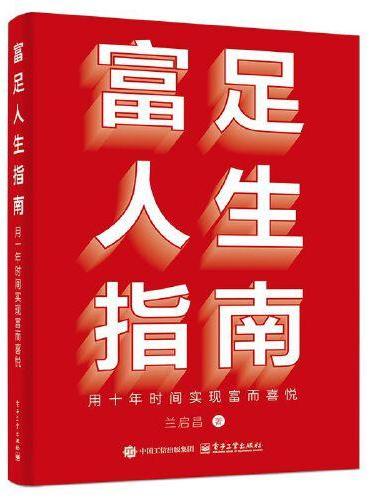
《
富足人生指南:用十年时间实现富而喜悦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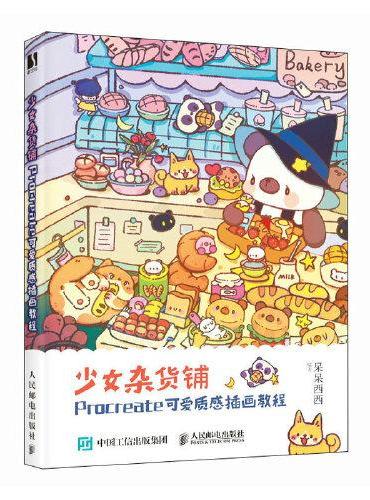
《
少女杂货铺 Procreate可爱质感插画教程
》
售價:NT$
356.0
|
| 編輯推薦: |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12)——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徐贲专文导读,从对战争性质的思考和国家认同出发,解释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巨大差异。
★《罪孽的报应》借由作者的个人游历观察、访谈,以及对文学作品、电影、博物馆、教科书、纪念碑等文化产物的挖掘认知,回溯了战后五十年间德日两国政府和民众面对战争罪孽的思考与作为,追寻隐藏在反思与忏悔、否定与歪曲、麻木与逃避背后的民族心理与集体记忆。
★《罪孽的报应》超越常见的罪文化与耻文化分析,指出德国与日本在历史记忆上的差异更多源自政治,而非文化。政体的改变和国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义的影响、加害者和受害者定位、天皇制与纳粹极权的不同,决定了两国对过去罪孽的不同记忆与悔悟。
★《纽约时报书评》《芝加哥论坛报》《纽约书评》《经济学人》等媒体齐声推荐;时隔两年,中译本再版修订。
|
| 內容簡介: |
倘若说人类史上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战后德国人曾经“无力哀悼”,然而如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对比拒绝忏悔的国家,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
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抹去。
二战结束七十余年来,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危险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的?表面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关于奥斯维辛、广岛、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以及为了实现“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
在《罪孽的报应》一书中,布鲁玛精确剖析了德日两国的战争记忆,通过深入调查和实地走访,作者敏锐地指出:“没有危险的民族,只有危险的情境。”实际的政治安排,往往比所谓的历史规律和民族性格,更能影响一个国家在面对自身历史遗留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过去深入骨髓,历史从未清零。布鲁玛带领读者进行一次深刻的人性探究:关于在我们这个时代,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何在各个方面影响了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
|
| 關於作者: |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生于荷兰海牙,先后在荷兰和日本就学,曾于莱登大学攻读中国文学与历史,后专注于日本研究。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和《旁观者》杂志记者,为包括《纽约时报》《纽约书评》《新闻周刊》在内的多家西方报刊撰写关于亚洲的政治和文化评论,并曾任教于牛津、哈佛、普林斯顿、格罗宁根等大学。现为《纽约书评》主编、纽约巴德学院保罗·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出版的著作有《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创造日本:1853—1964》《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伏尔泰的椰子》《残忍的剧场》等。2008年被授予“伊拉斯谟奖”以表彰他“在欧洲对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同年以其卓越的著作帮助美国读者理解亚洲的复杂性而获得“肖伦斯特新闻奖”。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全球*思想家”。回溯了战后五十年间德日两国政府和民众面对战争罪孽的思考与作为,追寻隐藏在反思与忏悔、否定与歪曲、麻木与逃避背后的民族心理与集体记忆。
倪韬,1985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学士,现从事新闻工作,任英文报纸Shanghai Daily评论员。
|
| 目錄:
|
导读 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徐贲)
前言
序:敌人们
部分
章 反对西方之战
第二章 废墟中的浪漫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奥斯维辛
第四章 广岛
第五章 南京
第三部分
第六章 历史站上审判席
第七章 教科书风波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第四部分
第九章 一个正常国家
第十章 两座普通小城
第十一章 告别废墟
注释
鸣谢
索引
|
| 內容試閱:
|
前言(选摘)
足球,特别是欧陆足球,是检视各国国情一个很有用的风向标。2006年,德国举办了世界杯。除开决赛中齐内丁·齐达内的“铁头功”让人大跌眼镜外,这届世界杯还因为德国人迸发出的毫不做作、欢天喜地的爱国热情而显得与众不同。在过去,德国人有充分理由对在全世界面前挥舞民族标志物感到犹豫。这一次,他们这么做了,过程中流露出的友善让人无法将其误认为是什么邪恶的事。尽管德国队在2006年未能杀入决赛,但德国人似乎很骄傲于自己是德国人。
那届世界杯的另一大非凡之处在于,德国队赢球时,似乎没人会太往心里去。在过去可不是这样。比方说你是荷兰人、法国人、捷克人或波兰人的话,输给德国就好像又被侵略了一样。因此,难得战胜德国队时就会大肆庆祝,仿佛甜蜜复仇。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这种情绪似乎终于消散了。对了,德国好的两位球员都是波兰裔。
随着记忆淡去,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尽管有些历史记忆挥之不去,很是要命。但我相信,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当我在1994年写作《罪孽的报应》一书时,世人仍很畏惧德国,也不信任这个欧洲经济强国。就在前不久,德国人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街头欢庆两德统一,震天响地高喊“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口号。这在那些记忆尚未淡去的人听起来有一丝不祥的意味,某些德国人尤其如此。但到2006年时,君特·格拉斯(GünterGrass) 的那句名言——“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听着比 1989 年时更像是在自抽耳光,荒谬得无以复加。作为欧洲一分子的德国做得十分出色,几十年来一直规规矩矩参与欧洲机构和北约的事务,因此若再对新一代德国人心怀戒备,会显得心胸狭隘。毕竟二战时,他们可尚未降临人间。不过,德国人之所以获得邻国更多信任,是由于他们正一点点学着信任自己,尽管这一过程缓慢而痛苦,且有时并不彻底。
总而言之,在西德,小说家、史学家、记者、教师、政客和电影导演都已经反思过德国近的一段残暴历史,有时会执念于此,但态度往往相当开放和坦诚。很少有德国学童会不知道自己国家过去的滔天罪行。如果说有杂音的话,那么也确实有部分人开始对这种不间断、填鸭式的教育感到厌烦。直到21世纪,依然有公众人物就战争发表不甚光彩或不成体统的言论,但这些人随即会遭到其他德国人的口诛笔伐。
对于德国人,二战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说笑的事,也不应该是。但在2008年,一位犹太裔瑞士导演拍摄的电影《我的元首》(Mein Führer)票房大热。这或许是个好现象。拿自己的国家开涮总比自抽耳光要好。倘若说人类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
同样的话,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用来形容日本呢?日本人在2002年同韩国联袂举办了一届世界杯。日本国家队的球员年轻而时髦,在他们意外获胜时,日本年轻人也会怀着同四年后德国人一样兴高采烈的劲儿,为国家队欢呼叫好。然而,韩国等亚洲邻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却并未消失。因为尽管那些挥舞旗帜的日本青年看着没有什么好勇斗狠的念头(或者对历史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也成问题),但他们一部分供职于政府和大众传媒的前辈,却仍在就战争发表起码是让人不安的看法。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对战争罪行的辩解和否认之声依然不绝于耳。很明显,太多有头有脸的日本人并未“应对”过战争。
按理说日本人对此应感到更自如才对。亚洲的战争很血腥,既发生过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浩劫,也见证过劳工被迫修建泰缅铁路、后活活累死的血泪史;从新加坡到苏门答腊,遍布着惨无人道的战俘营;中国在战时死亡上千万人。凡此种种,都在亚洲的历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伤疤。但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系统性灭绝一个民族男女老幼的计划——这个民族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被认为不配有生存权。
反常的是,这一切也许使日本人更难正视历史。第三帝国倒台后,除了部分精神失常的边缘群体外,鲜有德国人会容忍犹太人大屠杀,更别提以此为荣了。“我们并不知情”在1950年代是一种普遍反应,但到了1960年代,这句话在年轻一代眼里已经变得令人不齿,因而羞于提起了。这场蓄意的种族灭绝罪恶滔天,昭然天下,因此根本不容辩驳。
日本人从没取得像德国人那样的共识。右翼民族主义者喜欢借日本没有屠犹这点做文章,以此证明日本人根本没必要对这场战争感到愧疚。在他们眼中,这场战争跟其他战争一样。残酷么?没错,但历史上所有大国参与的战争都是残酷的。事实上,鉴于太平洋战争的对手是西方帝国主义者,这就是一场可以被正名的——甚至是神圣的——亚洲解放战争。
从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鲜有日本人会采纳这一观点,反观这一时期的多数德国人,却还在竭力忘却历史。战后初几年,日本小说家和导演在面对军国主义罪行时都十分坦诚,这点实属罕见。这份坦诚在2009年反倒失色了。目标读者为年轻人的流行漫画书赞美日本军人和神风队员的英勇事迹,而中国人和他们的西方盟友则被描绘成一群奸诈好战之徒。2008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参谋长宣称日本是被中美两国“拖入”战争的。
怎么会这样呢?人们往往认为这一定能在文化上得到解释。在东方人的观念中,耻感必须靠沉默、抵赖等做法来加以掩饰。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对这一说法予以了大力驳斥,如今我依旧这么看。德国人在道德上并不比日本人更高尚,罪感和耻感也不比后者更强。曾几何时,他们的普遍态度也是逃避。
事实情况是,日本依然为历史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应得到解决。之所以没有,更多是出于政治而非文化原因。这不光同1946年美国法学家起草的《和平宪法》有关,也同天皇体制扮演的角色有关。战后,麦克阿瑟将军出于权宜之计,豁免了日本皇族的战争罪行。
在德国,第三帝国走向覆灭是历史的一次彻底扭转。但即便处在盟军占领下,在天皇被迫放弃神圣地位后,统治日本的大抵还是同一批官僚和政治精英,不过凌驾在他们头上的是一部全新且更民主的宪法。因为在日本不存在类似纳粹党的组织,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日本军国主义就被归咎为“封建”文化和武士道精神的恶果。正如人们难以信任一个洗心革面的酒鬼会对烈酒点滴不沾一样,日本宪法禁止日本使用武力或保留武装力量。自此,美国就要肩负起保卫日本的责任。
纵然多数日本人对不用再上阵打仗由衷感到高兴,纵然为了便于成立自卫队,宪法很快被敷衍了事,但部分保守派对他们眼中这一践踏国家主权的做法感到甚是屈辱。对他们而言,从盟军主持的东京战争罪审判,到左翼教师和知识分子谴责日本的战争行径,所有这一切从今往后都将被视为民族耻辱。较为“进步”的日本人越是搬出战时暴行的历史来警告人们切勿背离和平主义,右翼政客和评论家就越会为日本的对外战争进行辩护。
换言之,历史观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化和两极分化的。宪法和平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1950年代曾导致政治动荡,为了拔掉这枚“肉中钉”,主流保守派尝试通过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战争和政治上转移开。
这一策略很成功。日本日渐富强,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建立了某种压制的稳定秩序。但历史拒绝远去。自民党内的民族主义右翼对战后协议的怨气持续发酵,并以一种粗鄙的形式呈现出来。凶神恶煞的青年穿着卡其军装,站在旗帜飘扬的卡车上,伴着高亢的战时军队进行曲喊出他们的反对之声——这跟2002年时球迷的欢腾气氛可不太合拍。
几十年来,奉行沙文主义的右翼无论对高中教育,还是对天皇地位等问题,观点都很反动,他们能得到约束,要拜有时同样教条的日本左翼所赐。马克思主义曾是教师工会和学界奉为圭臬的意识形态。然而,同世界各地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1990年代初苏联帝国解体以及波尔布特一手酿成的惨剧广为人知后,已经日渐式微了。
这一思想体系的崩塌导致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崛起——或许只是昙花一现。在日本,后果更为严重。由于自民党实际上一党专权,边缘化的日本左翼又因为自身的教条主义颜面扫地,不只是走向衰落,而是彻底瓦解了。这等于帮了为战争唱赞歌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一个大忙,他们甚至在东京大学这样的进步思想堡垒里壮大力量。形形色色的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宗旨是“改革”历史课程内容,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也许是因为对纯粹物质追求的厌倦,也许是因为对身不由己背负罪恶感到懊丧,也许只是因为无知——或者更有可能是以上三种情况兼而有之——日本年轻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套爱国主义的甜言蜜语。中国惯于以日本的历史罪行作为把柄,进行政治施压,因此日本人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催生了一种好斗的爱国心理,甚至不惜以无视历史事实为代价。
鉴于德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些区别,也许读者会以为我的书在德国更受好评。其实不然。该书在日本不仅销量更大,而且获得了更为积极的反馈。对此,我只能猜测个中原因。日本人乐见自己的国家被拿来和德国作比较,它们都有高效、干净、勤奋、守秩序等优点。而战后的德国人坚定不移地想成为自由、进步的西方社会的模范成员,他们可并不热衷于被人拿来同日本人作对比,因为这太像是对战前“东方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一种肯定和赞许。
然而,如若我的看法是对的,即两国之间在历史记忆上的差异更多源自政治,而非文化,那么德国人这种神经过敏就毫无必要。不过,认为文化无关紧要、世界各国的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想法很天真——在过去也被证明很危险。但文化差异论——学界的理论家喜欢管这叫“抓住本质”——同样大谬不然,而且也很危险。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部分是想检验这些想法,探求类似的心理创伤何以影响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这项冒险之前,我的直觉是——您愿意的话也可以管这叫偏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似局面下反应大致相同。总而言之,德日两国人的行为并不一致——但在东德、西德和日本,无论战时还是战后,局势也都迥异,今天亦是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