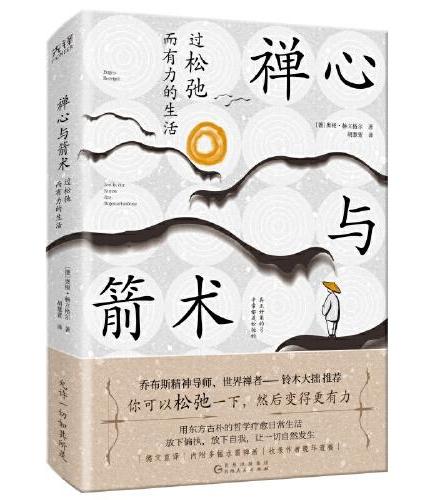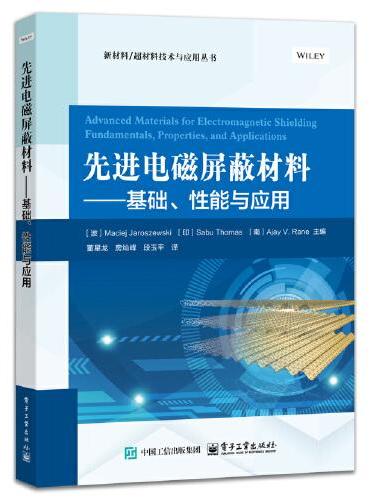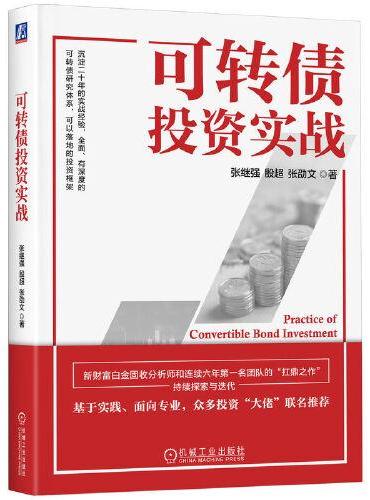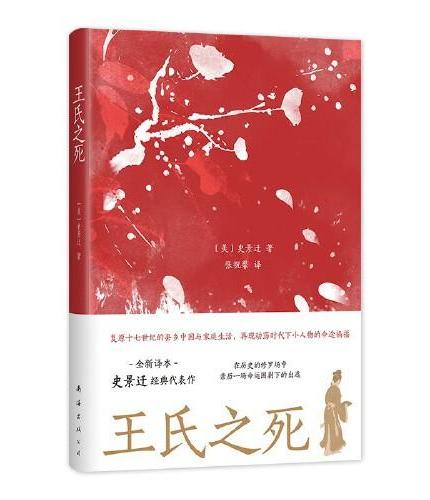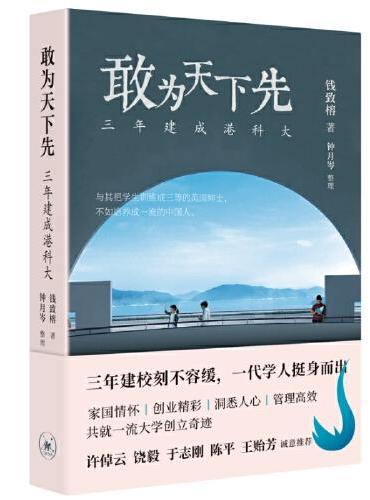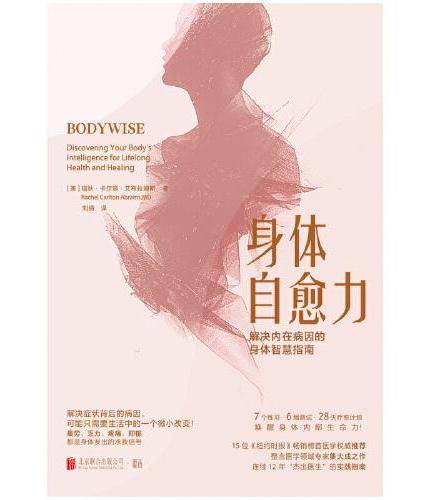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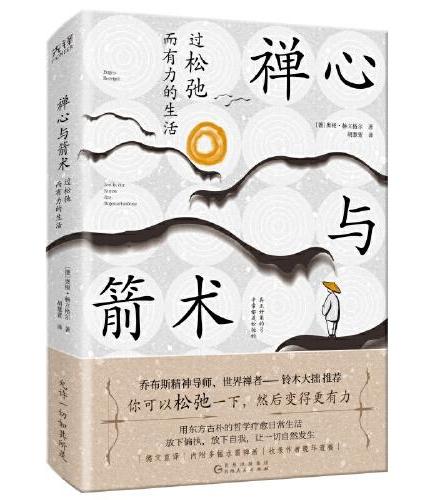
《
禅心与箭术:过松弛而有力的生活(乔布斯精神导师、世界禅者——铃木大拙荐)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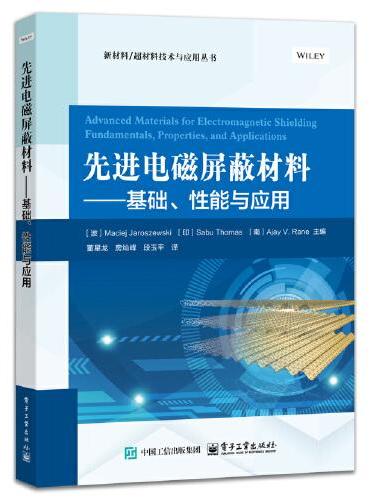
《
先进电磁屏蔽材料——基础、性能与应用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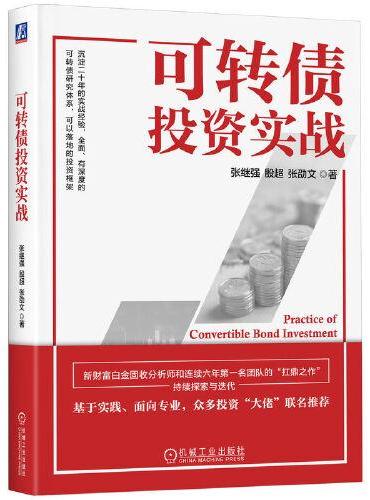
《
可转债投资实战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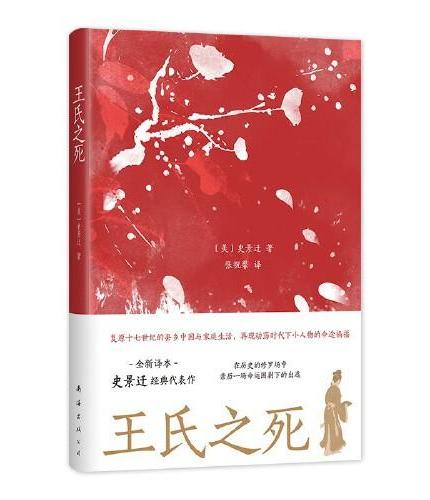
《
王氏之死(新版,史景迁成名作)
》
售價:NT$
2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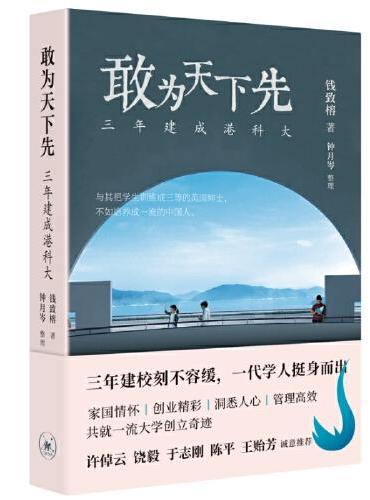
《
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
》
售價:NT$
352.0

《
直观的经营:哲学视野下的动态管理
》
售價:NT$
407.0

《
长高食谱 让孩子长高个的饮食方案 0-15周岁儿童调理脾胃食谱书籍宝宝辅食书 让孩子爱吃饭 6-9-12岁儿童营养健康食谱书大全 助力孩子身体棒胃口好长得高
》
售價:NT$
2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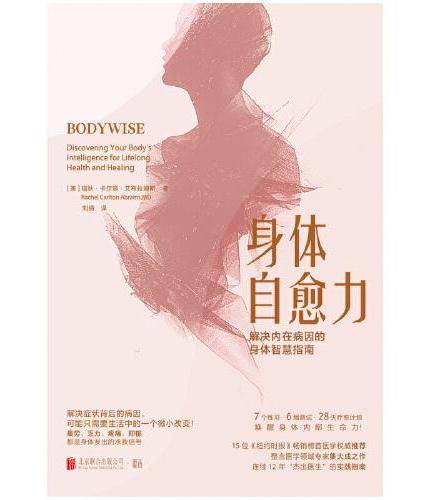
《
身体自愈力:解决内在病因的身体智慧指南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
晚清著名学者俞樾的散文骈文合集,透过流畅优美文笔展现卓识灼见。
|
| 內容簡介: |
|
《宾萌集》《宾萌外集》是晚清著名学者俞樾自编的文集。《宾萌集》共六卷,依次为《论篇》《说篇》《释篇》《议篇》《杂篇》《补篇》,收录俞樾所作的散文,文风平易流畅。 《宾萌外集》共四卷,以书序、寿序、书为主,另有赋、记、论、传、碑、启、墓志铭、诔、祭文、呈,都是骈文,辞藻华美,声调铿锵。本书以凤凰出版社影印光绪末增订重刊《春 在堂全书》本为底本进行点校整理,采纳蔡启盛《〈春在堂全书〉校勘记》的正确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
| 關於作者: |
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省德清县城关乡南埭村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 吴昌硕、日本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
滕振国,男,1947年生, 1981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师从戏曲史家钱南扬教授,曾任教于江西大学(南昌大学)、上海大学。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 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宋词与元曲。主要论文有《〈张协状元〉研究》等。
|
| 內容試閱:
|
前言
《賓萌集》《賓萌外集》是晚清著名學者俞樾自編的文集。《賓萌集》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春由時任廣東布政使的王凱泰出資刻印,共五卷,依次爲《論篇》《説篇》《釋篇》《議篇》《雜篇》。此後二十多年俞樾所作可歸入《論篇》《説篇》《議篇》的,數量不能各成一卷,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彙成一卷,題曰《補篇》,作爲第六卷刻印。俞樾自述體例取法乎《晏子春秋》,還説‘今之集即古之子’。這樣比附,固然是向前代經典致敬,也不無自信自許自得的意味。
‘賓萌’一詞,出於《荀子·解蔽》:‘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俞樾自己有解釋:‘孟,當讀爲萌。……所謂賓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游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往來諸侯之國’的‘游士’,很容易被理解成戰國時期的策士。他們操縱横之術,挾王霸之策,競走於權貴之門,雄辯於王侯之前,利口巧舌,攪動天下風雲,博取一己富貴。俞樾不是這樣的人。他於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中進士,僅當了一任河南學政,便因‘試題割裂經義’而被劾落職。之後四十餘年,他潛心學術,成一代樸學大師;全力講學,主講杭州詁經精舍三十一年,有‘門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之譽。《賓萌集》成書於他治學授徒之際,集中也無結交勢要、諂媚權貴之文。顯然,這樣的俞樾和戰國策士面目迥異,因此集名‘賓萌’一詞與戰國策士了然無涉。《吕氏春秋·高義》:‘(墨)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説墨子節衣縮食,與賓萌同伍,不求做官。高誘注:‘賓,客也;萌,民也。’很清楚,‘賓萌’就是客民,即外鄉人。這有利於進一步理解俞樾的解釋。‘游士往來諸侯之國’,重心在一個‘游’字,即游子、游俠、游民之‘游’,居無定所,謀生是求。其實,策士、縱横家是賓萌——客民、外鄉人的一種,其代表人物蘇秦、張儀,前者是東周雒陽人,游説六國,組建合縱聯盟,任合縱長,兼佩六國相印;後者是魏國人,得志於秦,任相國,以連横破合縱。還有一位大人物李斯,屬法家,也是一個賓萌,楚國人,入秦,立功而當上丞相。他的大作《諫逐客書》,勸諫秦王(後來的秦始皇)不要驅逐在秦的外國之人(也即‘賓萌’),説‘物不産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産於秦,而愿忠者衆’,理直氣壯,冠冕堂皇,説明楚材晉用是當時的普遍現象。俞樾是浙江德清人,落職後移居江蘇蘇州,并於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構築‘曲園’,思老子‘曲則全’之訓,故名,至今尚是蘇州名勝。德清人而寓居蘇州,自然是個外鄉人。但以‘外鄉人’命名自己的文集,未嘗没有一絲中年落職的無奈和落寞。
《賓萌集》是散文集。俞樾爲文寫詩,崇尚平易的文風。他曾借前人的話,主張‘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茶香室叢鈔·失黏》)。又説,‘余生平喜香山詩,所爲詩亦自謂近之’(《茶香室叢鈔·二李唱和集》)。香山,中唐詩人白居易,號香山居士。白居易寫詩,要求老嫗能解,淺顯通俗,所以有‘元(稹)輕白俗’的説法。準確、乾净、淺易、傳神,是文學語言很高的境界,源於作家創作主旨的明確,語言運用的自如,當然也是一種美學追求。俞樾是博學鴻儒,精研經學,旁及諸子學、史學、訓詁學、音韻學,乃至对詩詞、書法、小説、戲曲等,都有很深的造詣。滿肚子的學問,出而爲文,則華麗、典雅的文風,非不能也,乃不爲也。他自覺追求平易的文風,客觀上順應了文學由艱澀到淺易、由貴族而大衆的歷史發展潮流。俞樾同年進士兼兒女親家王凱泰所作《序》,稱道‘其論切當而不浮,其説精微而不腐,其釋詳明而不煩,其議正大而不詭,其雜文亦有法度不苟作’。雖有溢美之嫌,却也基本準確。
下面依照文集六卷的次序來介紹一下《賓萌集》的思想内容。
卷一《論篇》,共二十五篇,是俞樾治史的心得,主要對從春秋到明末的二十餘位歷史人物作了評論。比如《韓信論》,圍繞韓信於漢反與不反、吕后(實爲劉邦)殺信該與不該的公案,反復研探,斷語是‘夫漢始患無信,而項氏非所憂;繼患有信,而吕氏非所憂。故自淮陰侯之死,而高帝可以老矣’。著眼於國家安定的大局,立論自高;對韓信事漢的曲折心態也分析得絲絲入扣,令人信服。二十五篇中,值得一讀的是《秦始皇帝論》上中下三篇、關乎明朝國運的《鄒元標論》以及《明代争國本諸臣論》。
怎樣評價秦始皇,自漢以降,聚訟不已。概而言之,譽少毁多。始皇焚書坑儒,得罪了天下讀書人。而撰史著書,筆捏在讀書人手裏,自然不肯説他的好話。秦王朝短命,二世而亡,來不及製造輿論替始皇塗脂抹粉,揚美掩醜,他的形象也就不會太好看。其實,秦始皇很了不起,他改革國家政體、變封建制爲郡縣制就是很大的歷史功績,唐代柳宗元的宏文《封建論》對此有深刻的論述。俞樾的三篇《秦始皇帝論》,上承《封建論》,著眼於一個‘變’字。上篇説‘周、秦之際,古今之交也,雖欲無變,不可得也’,中篇説‘因時變法固當日之通論矣’,‘則使秦人不得天下而楚得之,其變改古制猶夫秦也’。這一觀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鴉片戰争,清政府割地賠款。老大帝國受辱於西方蠻夷,士大夫驚恐悲憤之餘,普遍有所反思。祖宗不足法,必須變法圖存。中興名臣李鴻章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驚呼‘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更是這種社會思潮的一次失敗的政治實踐。俞樾身處動蕩的時代,借古喻今,呼籲‘變則通’,其政治眼光和政治立場,都是值得肯定的。
俞樾是樸學大師,有《群經平議》五十卷,影響很大。他治學以‘通經致用’爲宗旨。‘通經’不是死背經義,墨守成規,而是爲了‘致用’,看重實際效果。《鄒元標論》是個好例子。儒家講道德教化,士大夫尤重氣節。孔子説殺身成仁,孟子説捨生取義,爲了仁義,不惜犧牲。因此,‘文死諫,武死戰’,歷史上那些犯顔直諫、遭貶遭戮的人,往往被後世視爲道德楷模,没有誰敢提出諫得‘對不對’或者‘值不值’的疑問。俞樾敢。明神宗萬曆五年(一五七七)九月,首輔張居正喪父。居正戀棧,居喪不丁憂。小皇帝爲他辯護:‘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説我年幼,方方面面都離不開張居正。鄒元標不顧居正勢盛、聖眷正隆,三次上疏反對奪情:‘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明史·鄒元標傳》)言詞激切,假設较爲。結果被杖八十,貶職流放荒遠之地,直到居正病死,纔得復起。鄒後來成爲東林黨首領之一,與趙南星、顧憲成號爲‘三君’。他的反奪情之舉,歷來被人稱頌,以爲是忠君愛國,不計個人安危。俞樾却直斥鄒‘進必不用之言,以徼必不免之辠’,是沽名釣譽,并説‘有明中葉以後,士大夫議論愈多,而國事愈壞’。在《明代争國本諸臣論》中進一步説,‘有明一代,士大夫喜名譽,好議論,乃宋以來之積習也’。他們泥古不化,膠柱鼓瑟,‘小而詩文之體,規規摹擬;大而乘朝車,議國事,亦徒泥夫古人之見,不知所以裁之’,對明代的文學、政治,具有洞見卓識。
卷二《説篇》,共十六篇,内容駁雜,於經、史、時政都有涉及,俞樾心有所感,即成一説。較諸《論篇》,《説篇》偏於感性。身處清季,撫時感世,内憂外患,危機感如影隨形,無法驅除,基調顯得沉重。比如《治説上》規勸爲政者要居安思危。這本是老生常談。但鴉片戰争、洪楊之亂後,時局哪來的安可居?唯有對危局的一聲長歎而已。又如《治説下》面對洋人的‘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作者反對師夷制夷,以爲‘學人以求勝人,大惑之道也’。那麽出路在哪裏呢?有何克敵制勝的良策奇謀呢?揭開謎底,無非是老祖宗傳下來的‘仁政’二字。心勞力拙,讀來深感悲凉。時局的衰敗,不僅在國力,也在人心。作爲經學大師的俞樾,對此更加痛心疾首。《性説》上下篇中,他力斥孟子性善説,以爲‘今天下之人爲善者少,而爲不善者多’,人‘其耳之聰、目之明、手足之便利、心思之巧變,可以無所不爲’,應從荀子性惡説,嚴刑峻法輔以道德教化,撥亂反正。《孔門四科説》中,他認爲把孔門弟子分爲德行、政事、文學、言語四科‘非孔子之意也’,後世置德行於其他三科之上,更是大謬不然,使‘空疎不學之徒得而託焉’。此説大有見地。衡人掄才,有才固然未必有德,而無才者德將焉附?倘能德才兼備,自然大好;不然,退而求其次,寧取有才少德者,竹頭木屑,終有一用。每見有才、學、能一無所長者,怡怡然左右逢源,青雲直上,自詡‘吃道德飯’,可見此種人物,源遠流長。
這裏重點推介《公私説》。這是一篇奇文。長久以來,公、私對舉,‘公者美名,而私者姦衺不正之號也’。爲政者總提倡先公後私,公而忘私,甚而至於大公無私,興公滅私。作者力排常識,獨立異説。首先引經據典,證明‘聖人先私而後公’;繼而説‘自營爲私’,‘於是推以及人,使人人得以自營,是即公矣’;又説‘古人之辭,言公必及私’,‘私固聖人之所不禁也’。結論是‘一家安而後一國安,一國安而後天下安也’。這一觀點至今還屬前衛,難怪俞樾在文末沾沾自喜道:‘吾斯言也,自漢以來儒者未有及此者也,其爲世所詬病必矣。然而後之君子得吾説而深思之,其諸可以治天下歟?’
卷三《釋篇》,共十三篇,幾乎都是不同意成説的求異出新之文。其中十篇依次考釋‘盤古’‘姜嫄’‘太公望’‘荆楚’‘公主’‘佛寺’‘相’‘主’‘欽’‘左右’,類似於《辭海》的詞條,而探其所以然,有理有據。有的結論平易確實。如表示‘宰輔’之‘相’,阮元釋爲‘襄’(助)之假借。俞樾反對這一‘曲説’,認爲由《説文解字》‘相’本義‘省視’引申,‘瞽者無目,不能省視,故必有人代爲省視,而扶助之、導引之,即謂之相。其後因以爲輔政者之稱’。有的闡述啓人神志。如表示佐助的‘左右’,《説文解字》釋‘左’爲‘手相左助’,從(手)工(左助),釋‘右’爲‘手口相助’(段玉裁説‘以口助手’)。作者考證‘左’從工乃從巨(矩尺)省,‘右’不從口而從囗(圓形的隸變):天下之形,不外乎方與圓,‘(左手)執方,又(右手)執圓,古人制字之意正如此’,‘“天道圓,地道方;君道圓,臣道方。”古之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不外乎此矣。是故“左”“右”二字之義,其所包甚大也’。另三篇是對某一史實的考證和評析。《釋孔子弟子三千人》考證《史記》孔子‘弟子三千’之‘三千’非確指,而是泛指數目之多。楚、漢之興的‘五諸侯’,衆説紛紜,《釋楚漢五諸侯》據史實排除了其中不能列入‘五諸侯’者。《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相傳孔子作《春秋》至此而輟筆。前人認爲麟出非時,謂之不祥。《釋〈春秋〉絶筆獲麟》則指出作爲仁獸,麟仍是‘王者之瑞’,從《詩經》《周易》的考察得出‘天下方治也,而聖人之心則已憂其亂;天下方亂也,而聖人之心則已望其治’的結論,斷定‘《春秋》絶筆於“獲麟”,思治也’,而非‘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據俞樾《江孔德孝廉〈穀梁條例〉序》,本文是其十六歲時所作。
卷四《議篇》,共六篇。《文廟祀典議》《孔忠移祀崇聖祠議》都是對卷五《奏定文廟祀典記》所記倡議的補充,前者倡議文廟配享應有許慎、從祀增入毛亨,名爲表彰毛亨和許慎,實乃强調《毛詩》的傳承尤其是《説文解字》的價值,‘義理存乎訓詁,訓詁存乎文字。無文字是無詁訓也,無詁訓是無義理也’,‘而《説文解字》一書尤爲言小學者所宗’。《學校祀倉頡議》歷數配享四位、從祀六位的業績,確立先秦兩漢文字學功臣。《考定文字議》主張以《説文解字》爲標準,考正字義與字體,‘悉羅列許書正字,辨俗體之誤,尤學者所不可不讀’(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子部·雜家類》),馮世徵曾爲此做《〈考定文字議〉疏證》。《取士議》是對‘罷去八股時文,别求取士之法’考試内容與方式的建議,針對同治元年黎昌庶條陳取士法的繁重,俞樾主張‘務宜簡易,使天下可以遵行,不必過涉繁重,轉致有空文而無實際’。《仿造浮梅檻議》倡議仿造明人黄汝亨西湖所建‘浮梅檻’:用巨竹做成竹筏,平鋪木板,編織篷屋,朱紅欄杆,青色帳幕,中可放置几席觴豆及彝鼎、罍洗、茶鐺、棊局。俞樾四十七歲起主講杭州詁經精舍,春秋佳日時至西湖,遂作本篇。蓋羨慕‘浮梅檻’新奇可喜,‘終此老之身逍遥容與’,而仿製不果。八年後,蘇州曲園落成,園有曲池十一丈見方,乃於池中仿造浮梅檻,因僅寬四尺長五尺,命名‘小浮梅’。容二人促膝,作者與夫人坐其中,相與閒話,往往考證傳奇、小説中俗事,於是録爲《小浮梅閒話》一卷(刻入《曲園雜纂》),可謂雅人清致。
卷五《雜篇》,共十九篇,内容龐雜。或爲圖、書作序作記,或爲廟碑、祠堂作記;或叙述以‘春在堂’命名所居及曾國藩題寫之緣起,或記載河南學政任上奏請文廟祀典應有公孫僑從祀、孟皮配享。更多的是爲親戚、鄉試同年、同年兼親家之父、所在書院監院之父、岳父與父親做塾師時的東家、任學政時職責所及者而作的傳或墓表、墓誌銘,傳主或墓主包括死難的守土之吏、地方好官以及‘烈婦’‘貞女’‘孝女’。雖多屬親朋好友圈,不無應酬之意,但特定時代的人物命運、文化現象尤其是作者的價值取向躍然紙上。《先府君行述》《先妣姚太夫人行述》兩篇(後者一八八五年補刻入《賓萌集》),記述先父、先母生平與爲人,筆下自有深情;《舅氏平泉姚公家傳》爲從小賞識自己的舅舅兼岳父立傳,介紹其著作大略及編著史書遺願,都是可供研究的珍貴資料。
卷六《補篇》刻印於俞樾七十五歲(一八九五年)之時,共十八篇:五論、五説、八議。憂國傷時是其主綫。列强侵凌,政府無能,有識之士争説自强。《自强論》反對洋務派師夷制夷的主張,以爲竊其唾餘,削足適履,‘庸有濟乎?盍亦反其本矣’——推行仁政,主要是整頓吏治。倘若官吏得人,‘官之與民若父兄子弟然’,一旦有警,‘效死而民弗去,夫何守之不固乎?’以後的歷史證明,這不過是一介書生的白日夢。《三大憂論》一憂列强欺辱,國將不國;二憂西學盛行,孔教將廢;三憂開礦采煤,竭澤而漁。現在看來,睁眼看西方,采礦辦工業,自有其進步性。但文章以‘憂’字立論,觸目驚心,可以想見作者的憂心忡忡,痛心疾首。《田獵説》主張教民以戰,以備不虞。《戰説》認爲士大夫也應知戰備戰,將帥更應身先士卒。《禦火器議》提議用藤牌兵破洋人槍炮火器。更有《弭兵議》《弭兵餘議》勸説列國,開戰終歸以和,然而‘荼毒億萬之生靈,糜費億萬之銀錢,勢窮力竭’,兩敗俱傷,有何益處?不如弭兵——消除戰争,‘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勿干預他國之政治,勿覬覦他國之土地,所謂兵者用之於本國,勿用之於他國’。書生論戰,紙上談兵;與虎謀皮,幼稚迂闊,却也足見其報國之志和仁者之心。
《醫藥説》主張‘不信醫而信藥’,即廢醫存藥。作者曾有《廢醫論》一卷,堅决‘廢醫’,至此稍有變化。俞樾是廢棄中醫論的代表人物。其門生章太炎深研中醫,一九一〇年作《醫術平議》云‘先師俞君僑處蘇州……累遭母、妻、長子之喪,發憤作《廢醫論》’,則不免想當然:俞樾長子俞紹萊病卒於光緒七年(一八八一),而《廢醫論》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已刻入《俞樓雜纂》;其母九十三歲高齡去世,‘醫者切脈,猶曰無慮。未卒前二日,諸病皆愈’(《先妣姚太夫人行述》),醫者無咎。太炎一九二〇年作《仲氏世醫記》云‘先師德清俞君,恨俗醫不知古,下藥輒增人病,發憤作《廢醫論》’,乃較平允。《廢醫論》之作,固然不排除愛妻爲醫所誤的因素,但‘憤然而議廢醫’原因明確:‘夫醫之所以知病者脈也,脈則久失其傳;醫之所以治病者藥也,藥則又不可恃。脈虚、藥虚,斯醫亦虚矣。’俞樾自陳‘廢醫論’是‘有益的偏見’:‘雖有激之談,然此論行則人之保其天年者多矣’(《〈春在堂全書〉録要》),‘此雖兄之偏見,然有益於世間實不淺也’(《致陳豪書》)。因爲有些偏激,‘廢醫存藥’立論亦不够堅實。《醫藥説》云藥丸傳世必經數百乃至上千年,因驗而靈;但行醫只是某些醫生謀生的手段,求得‘一輿之值、一飯之資而已’。此言自然偏激。醫生固有良莠,藥丸何嘗没有真僞?庸醫害人,假藥亦會致命。中醫中藥都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發揚光大。但於醫生要切實培養,於中藥要嚴格管理,人命關天,不可輕忽。
《賓萌外集》同治五年(一八六六)由曾國藩幕府、江蘇候補道杜文瀾出資刻印。集凡四卷五十六篇,以書序、壽序、書信爲主,另有賦、記、論、傳、碑、啓、墓誌銘、誄、祭文、呈,都是駢文。駢文承騷、賦餘緒,盛行於六朝,唐、宋以後漸趨式微,但綿延不絶,至今尚有寫作者。駢文是一種唯美的文學樣式,要求辭藻華美,聲律和諧,屬對工切,隸事精當。歷代雖不乏名篇佳什,但形式上的要求過於苛嚴,難免限制了作者表情達意的自由;艱澀的語彙、繁複的用典,也影響了讀者閲讀的順暢和愉悦,它的没落是歷史的必然。
俞樾是大學問家,精通經史子集,熟稔前事舊典;他深研音韻聲律,對寫詩作文的諧韻合律,更如庖丁解牛,得心應手。他當然喜歡駢文,寫作駢文。他贊美駢文‘意味深厚,文詞典雅,故可貴也’;對唐宋以後駢文的没落深感惋惜,認爲‘於古人修詞之道或反失之矣’。但他的文學觀不保守,能與時俱進,散文平易的風格即是一例;對小説、戲曲的喜愛和研究,更是明證。他説‘余自幼喜爲四六文(即駢文)’(《自序》),‘余三十歲前好爲駢四儷六之文,今《賓萌外集》四卷,皆其時所作也’(《朱鏡香〈竹南精舍駢儷文〉序》)。雖然《自序》中謙稱《賓萌外集》‘氣體卑下’‘鄙薄無足觀’,但晚年爲朱鏡香作序却感慨已經寫不出當年《賓萌外集》‘妃青儷白、侔色揣稱’的作品,對朱氏駢文‘搜逑索偶之工,翦月裁雲之妙’的贊美,未嘗不是《賓萌外集》的顧影自憐。讀者若喜愛華美的詞藻、鏗鏘的聲調,則閲讀本集之文會得到美妙的享受;對照《賓萌集》散文的樸實平易,更覺俞樾兩副筆墨,才大似海。
本書點校,以鳳凰出版社影印光緒末增訂重刊《春在堂全書》本爲底本,采納蔡啓盛《〈春在堂全書〉校勘記》的正確成果;改正文字訛誤并出校;異體字、古字、俗字原則上不改;因避諱而改字或缺筆的‘寧’‘玄’‘弘’等回改,不出校。
二〇二一年七月於上海證大家園
滕振國
論篇 賓萌集 一
丹朱、商均論
孟子曰:‘丹子朱不肖,商均亦不肖。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嗚呼!啓則賢矣,而丹朱、商均豈必皆不肖哉?武王數紂之辠,後世猶疑之,而況丹朱、商均乎?當堯之時而有舜,當舜之時而有禹,此丹朱、商均所以不有天下也。益之德不及舜,而功不及禹,則天下不歸益而歸啓。使堯不得舜,舜不得禹,天下固丹朱、商均之天下也。繼世而有天下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丹朱、商均而有天下,其視舜、禹固有間矣,而視太甲、成王宜無媿焉。然而曰不肖者何也?曰:仲尼之子不能復爲仲尼,堯、舜之子亦不能復爲堯、舜;以堯、舜爲之父,而責其子以必肖,此亦難矣。故丹朱、商均謂之不肖可也,謂之不賢不可也。且夫以天子之子,安然而處人臣之位,不賢而能若是乎?後世之君以百戰而得天下,天下既定,中外無復異志,而争敚之禍常起於門内。丹朱、商均處禪讓之際,拱手而去,没齒而無怨言,所謂‘知命’者歟?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所難者,以其子能安之也;舜、禹受人之天下而無所嫌者,以二子之無言也。昔武王克商,使武庚不反,則遂定矣。武庚反而天下從之,幾至於亂。及微子事周,然後復定。嗚呼!天下之心可知矣。夫使天下晏然戴舜、禹以爲君者誰乎?丹朱、商均也。聖人以萬全爲計,非丹朱、商均之賢,則堯、舜不敢與,舜、禹不敢受。然則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者,丹朱、商均之謂歟?
鄭殺申侯論
異哉!鄭之殺申侯也。當是時,鄭無人焉。夫鄭之從楚,天王命之,宰周公主之,非鄭之私計也。爲鄭謀者,宜告於齊曰:鄭雖從楚,非有貳心,以王命之故。君若以王命來,惟命是聽。夫齊桓方挾天子以令天下,其敢因區區之鄭而犯不韙之名乎?鄭之君臣聞有齊師,則不知所以爲計,而姑殺申侯以説焉。不知齊欲得鄭耳,雖朝刑一士,莫殺一大夫,齊師猶在城下也。魯僖公時,齊伐魯,魯使展喜犒師,對以先王之命,齊不敢伐而還。使鄭人而知此,則何以殺申侯爲哉?且夫小國,既無文德,又無武功,而惟知殺人以媚人,其不至乎亡者幸也。魯殺公子買卜以説于楚,衛殺大夫孔達以説于晉,皆非計也。夫無辠而殺大夫且不可,況爲敵國殺之乎?彼敵國何饜之有?殺其臣不足,則有出其君以説之,如衛成公者;出其君不足,則且有弑其君以説之,如齊莊公、悼公者,是尚足以爲國乎?
漢景帝用袁盎之言,殺鼂錯以謝七國,而七國不爲罷兵。唐昭宗時,李茂貞犯京師,殺兩樞密使以謝之;猶不足,又殺杜讓能,茂貞乃罷,而唐亦旋亡矣。宋韓侂胄謀恢復,金兵南下,問首謀。方信孺使于金,争之曰:‘縛送首謀,自古無之。’金人不可,宋卒殺侂胄,以首畀金。夫侂胄之罪誠可誅矣,而至於函首謝敵,其國尚可爲乎?昔樊於期亡秦之燕,太傅鞠武欲使入匈奴,太子丹不可。於是樊於期感其義,至爲之死。其後燕王喜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以説於秦,而燕卒亡。故夫殺人以媚人,無策之甚者也。
晉文公論
唐叔之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至晉文公而遂霸諸侯,其言信矣。楚成王曰:‘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而晉爲三家所滅,乃先諸侯而亡,何哉?烏乎!晉之所以霸者,其所以亡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今觀晉文與其臣所以取威定霸者,皆陰謀也。有陰謀者必有陰禍,晉祚所以不永歟?
自古以陰謀勝人者莫如越句踐,句踐雖能滅吴,而數十年之後,子孫竟亡於楚。故知天下之事,得之光明,乃可以久;得之曖昧,終必失之。漢高祖取天下於秦、項之亂,其事近正,故傳四百餘年,絶而復續。既篡於魏,而昭烈建號於一隅,又數十年,傳二世而後滅。宋太祖之代周,難言之矣。故南渡之後,不能爲光武之中興。而益王之立於福州,衛王之立於碙州,亦不足以比蜀漢。烏乎!天道神明不於此而可見乎?陳平曰:‘吾多陰謀,是道家之所忌。吾世即廢,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何坐法國除,竟不得續封。晉文之臣所與深謀者,胥臣、郤縠、狐毛、狐偃、欒貞子之徒,不久而子孫降於皁隸,豈非晉之君臣皆有陰禍哉?雖然,孔子稱齊桓公‘正而不譎’,而齊亡乃先於晉,何也?太史公曰:‘西伯昌與吕尚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由是言之,太公以陰謀興,宜其祚之不永也。
蹇叔論
有進説於其君者而君不聽,則亦已矣。必嘵嘵然語於衆曰:‘君之爲此也,吾知其不可也,吾言於君而君不用也。’則似幸其有失以中其言。不幸而其言果中,則人主將有所甚愧。且夫愧而能悔者,賢主也,豈可望之中主以下者哉?是故古之大臣,入以語其君,出不以告其子,使異日者君無所愧於我。君無所愧於我,則今日棄之,明日收之,略不芥蔕於其胸。昔秦穆公使孟明襲鄭,蹇叔以爲不可。及秦師既敗,穆公益用孟明而不及蹇叔,豈蹇叔已死歟?烏乎!蹇叔年雖高,有少年之氣,才識有餘而不能藏,雖不死猶不用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古君臣之閒豈好爲此戔戔小讓哉?懼傷君心也。今夫朋友之過,猶必忠告而善道之,而況君臣之閒乎?蹇叔一言不用,則悻悻之氣不能自默,既哭其師,又訣其子,必使通國皆知而後已。秦師一敗,崤函以西無不稱蹇叔之智,而笑秦穆之愚。秦穆何如主,而肯屈於其臣乎?一戰不勝則再戰,再戰不勝則三戰。不責孟明以僨事之罪,乃不欲自任失人之咎而使蹇叔受知言之名也。夫王官之役,晉人厭兵,自不出耳,非孟明之能勝晉也。以兩敗易一勝,兩戰之敗不以爲辠,一戰之勝遂以爲功,此秦穆之所以自解於國人也。其後晉以一旅拒桃林之塞,而秦遂不能東征諸侯,倖一時之功,貽數世之禍,秦穆君臣不足惜,然而激而成之者何人哉?向使蹇叔諫而不用,則杜門不出,深自諱匿。穆公始雖不用,終必能悔,悔而復用,成功名於天下,甚未晚也。惜乎蹇叔才識有餘而不能藏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