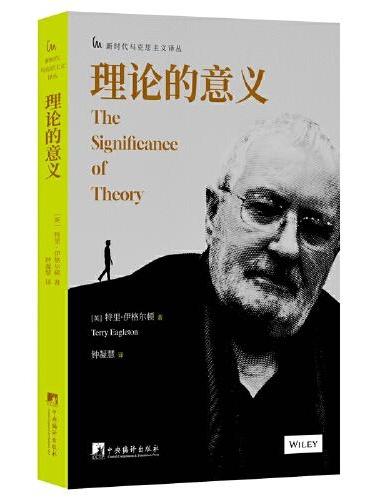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述异记汇笺及情节单元分类研究(上下册)
》 售價:NT$
475.0
《
环境、社会、治理(ESG)信息披露操作手册
》 售價:NT$
1190.0
《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
》 售價:NT$
440.0
《
理论的意义
》 售價:NT$
340.0
《
悬壶杂记:医林旧事
》 售價:NT$
240.0
《
谁之罪?(汉译世界文学5)
》 售價:NT$
240.0
《
民国词社沤社研究
》 售價:NT$
640.0
《
帕纳索传来的消息(文艺复兴译丛)
》 售價:NT$
495.0
編輯推薦:
☆这是一部著名的反战小说,也是一部个人成长小说。
內容簡介:
这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主要描写了一战期间8个普通士兵在西线战壕的生活和感受,共分12章。故事通过主人公保罗·博伊默尔的人称叙述展开。
關於作者:
作者:
內容試閱
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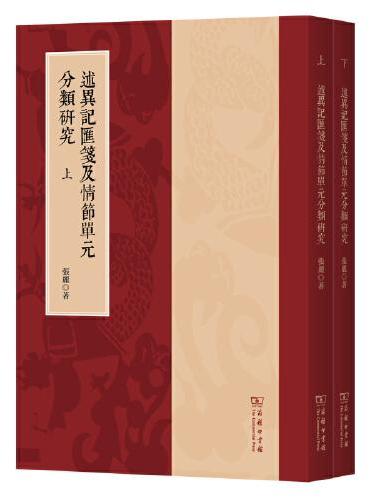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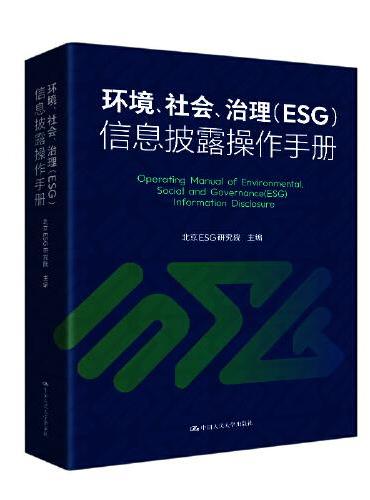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