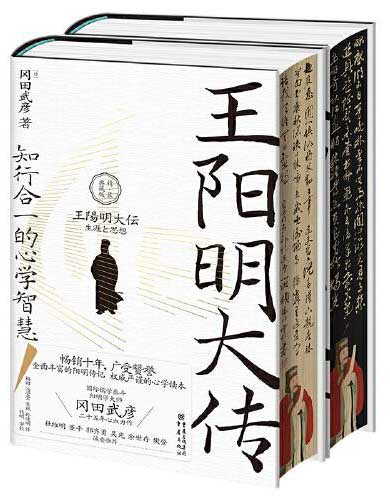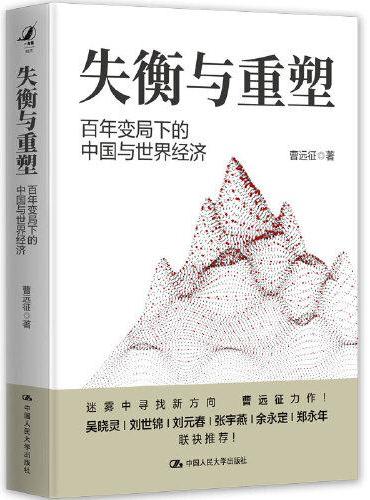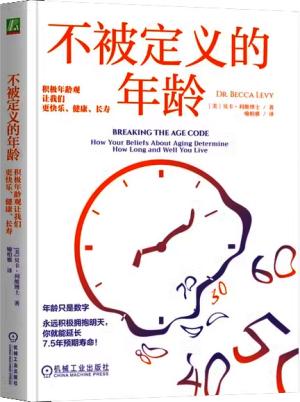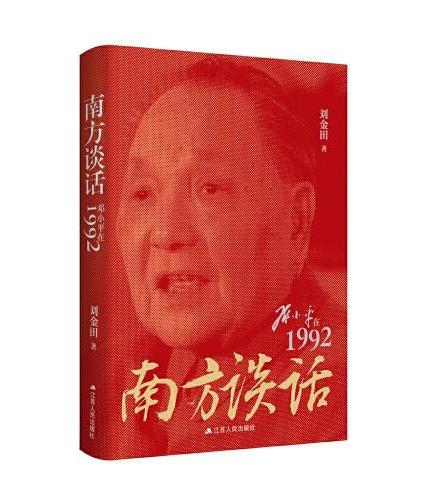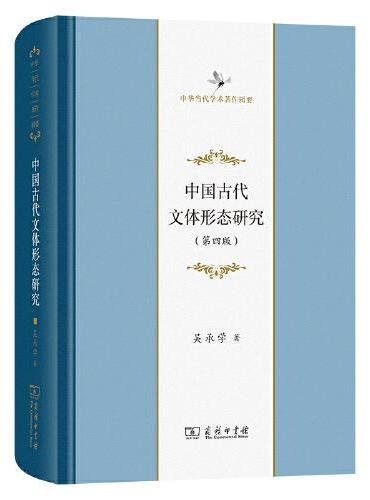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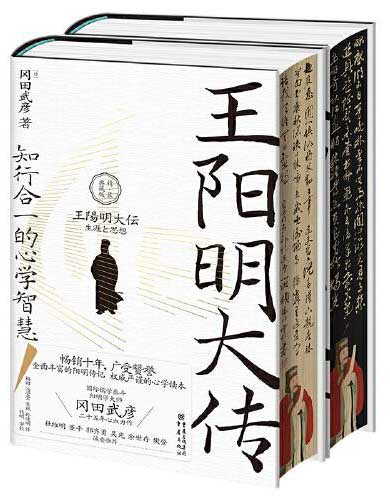
《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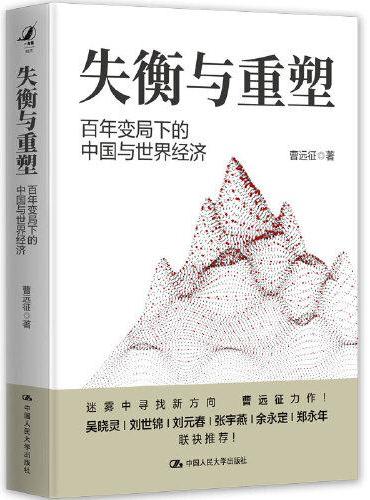
《
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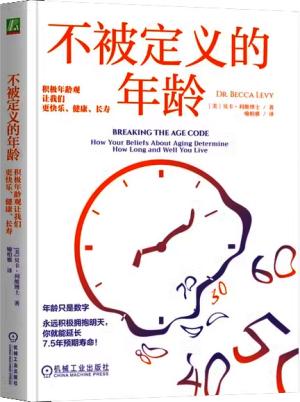
《
不被定义的年龄:积极年龄观让我们更快乐、健康、长寿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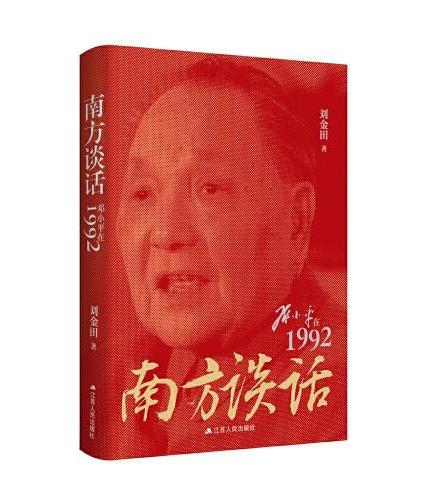
《
南方谈话:邓小平在1992
》
售價:NT$
367.0

《
纷纭万端 :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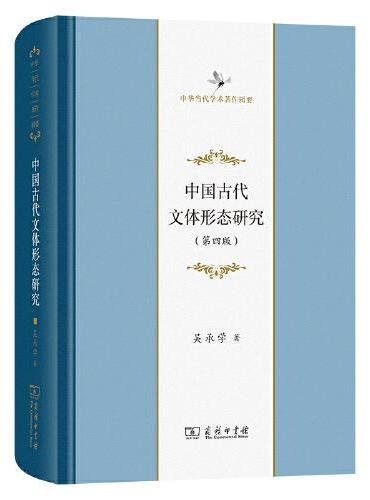
《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四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
售價:NT$
765.0

《
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大学问
》
售價:NT$
454.0

《
甲骨文丛书·波斯的中古时代(1040-1797年)
》
售價:NT$
403.0
|
| 內容簡介: |
|
本书基于日美同盟的研究视角,全面剖析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初期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具体内涵,探讨日美同盟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密切关系。具体内容包括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基本防卫政策蜕变,日美同盟与日本军备扩张,日美同盟与日本的海外派兵,驻日美军与日本的安全保障、日本的同盟扩张与“日美 1”模式,日本的“自主防卫”与日美同盟等。本书的研究视角新颖,弥补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日美同盟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论著不多的研究状况,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
| 關於作者: |
|
徐万胜,现任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问题与东亚地区安全,已出版个人学术专著《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2004年)、《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2006年)、《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研究》(2009年)、《当代日本政治》(2015)、《日本政权更迭析论》(2016年),代表性合著有《冷战后的日美同盟与中国周边安全》(2009年)、《日本近现代政治史》(2010年)、《秩序构建与日本的战略应对》(2018年)等,并在国内各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相继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全军军事科研年度规划课题2项等各类项目;荣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军队级教学成果奖等多种奖励。
|
| 目錄:
|
序章(1)
章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基本防卫政策(6)
节日美同盟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嬗变 (6)
一、《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
提出(6)
二、自卫队“国际合作”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
模糊(10)
三、日美安保体制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蜕变(12)
四、《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与日本“集体自卫权”立法(18)
第二节日美同盟与核潜力威慑战略(20)
一、“无核三原则”与核潜力威慑战略的实力基础(20)
二、“周边核威胁论”与核潜力威慑战略的升级倾向(23)
三、日美同盟与核潜力威慑战略的嬗变框架(25)
第三节日美同盟与“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嬗变(30)
一、日美同盟与“武器出口三原则”的例外(30)
二、日美同盟与“武器出口三原则”的修改(32)
三、“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提出与实践(36)
第二章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备扩张(39)
节日美军备合作的演变进程(39)
一、美国单方面对日援助阶段(1954—1980年)(39)
二、日美军备合作双向交流的过渡阶段(1980—1996年)(41)
三、日美军备合作双向交流阶段(1996年至今)(46)
第二节日美军备合作的个案研究(48)
一、日美联合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48)
二、日本选定“F-35”为新一代主力战斗机(51)
第三节日美军备合作的机制、方式与特点(55)
一、日美军备合作的机制(55)
二、冷战后日美军备合作的方式(59)
三、冷战后日美军备合作的特点(64)
第四节日美军备合作的促因(69)
一、同盟战略需求拉动日美军备合作(70)
二、军事技术基础夯实日美军备合作(73)
三、军火利益集团推动日美军备合作(77)
第三章日美同盟与日本海外派兵(85)
节冷战后日本海外派兵的发端(86)
一、冷战期间海外派兵问题的探讨(86)
二、《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成为废案(88)
三、自卫队扫雷艇的派出(90)
第二节联合国框架下日本海外派兵(92)
一、《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合作法案》的通过(92)
二、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96)
三、自卫队参与人道主义国际救援活动(99)
第三节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海外派兵(101)
一、日美同盟的“再定义”与“周边事态”立法(101)
二、美国的“反恐战争”与日本海外派兵(104)
三、联合军演与日本自卫队境外实战能力的提升(108)
第四节多样化任务与日本海外派兵(112)
一、国际紧急援助队与日本海外派兵(113)
二、防卫交流与日本海外派兵(116)
三、反海盗与海外基地建设(118)
第五节海外派兵与日本的防卫体制(122)
一、日本海外派兵的法制演变历程(122)
二、“国际和平合作”在自卫队任务中的定位(125)
三、海外派兵提升自卫队力量建设(127)
四、集体自卫权立法与海外派兵(130)
第四章驻日美军与日本的安全保障(133)
节20世纪驻日美军的产生与演变(133)
一、驻日美军的产生(133)
二、驻日美军的法律地位(135)
三、冲绳归还与驻冲绳美军基地(139)
四、驻日美军的编制体制与基地规模(141)
第二节21世纪初期驻日美军整编(144)
一、驻日美军整编的路线图(144)
二、驻日美军整编的进展(146)
三、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147)
第三节驻日美军对日美两国的作用与影响(150)
一、驻日美军对美国的作用(150)
二、驻日美军对日本的作用(151)
三、驻日美军的民生性问题(152)
第五章日本的同盟拓展与“日美 1”模式(156)
节日澳安保合作与“日美 澳”模式(156)
一、日澳安保合作的内涵(157)
二、日澳安保合作的动因(160)
三、日美同盟与“日美 澳”模式(164)
第二节日印安保合作与“日美 印”模式(166)
一、日印安保合作的内涵(167)
二、日印安保合作的动因(170)
三、日美同盟与“日美 印”模式(174)
第三节日韩安保合作与“日美 韩”模式(176)
一、日韩安保合作的内涵(177)
二、日韩安保合作的动因(179)
三、日美同盟与“日美 韩”模式(182)
第四节日菲安保合作与“日美 菲”模式(184)
一、日菲安保合作的内涵(185)
二、日菲安保合作的动因(187)
三、日美同盟与“日美 菲”模式(190)
第六章日本的“自主防卫”与日美同盟(193)
节日本“自主防卫”的基础:防卫力量建设(193)
一、“自主防卫”的传统:武器装备国产化(193)
二、“自主防卫”的强化:新式武器装备(196)
三、“自主防卫”的拓展:卫星情报与太空开发(200)
四、“自主防卫”的前沿:网络作战力量建设(206)
第二节日本“自主防卫”的对外交往:防卫交流(209)
一、日本“防卫交流”认知(210)
二、日本“防卫交流”实践(212)
三、日本“防卫交流”效用(215)
终章(219)
节安倍内阁的战略取向与中国周边安全(219)
一、安倍内阁的右倾修宪战略:削弱周边政治互信(219)
二、安倍内阁的岛争应对战略:难解周边领土争端(222)
三、安倍内阁的日美同盟战略:加剧周边大国博弈(223)
四、安倍政权的亚太外交战略:拼凑周边遏华网络(225)
第二节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227)
一、“新指针”的出台背景(227)
二、“新指针”的制定过程(229)
三、“新指针”的主要内容(231)
四、“新指针”的消极影响(234)
附录(237)
附录1日本安全保障大事记(237)
附录2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248)
附录3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250)
参考书目(264)
后记(271)
|
| 內容試閱:
|
同盟视域下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研究序章序章以“同盟视域下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为题展开研究,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昭示着21世纪初期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抉择。日本战后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成长为经济大国。但是,近年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诸多内涵,意味着其军事大国化进程加速,日本面临国家发展道路的再次抉择。因此,研究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有利于我们正确判断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走向。其次,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影响着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主要目标,就是遏制中国崛起以及应对包含钓鱼岛争端等在内的中日纷争。因此,研究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有利于我们主动维系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关联着21世纪初期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动。无论是日美同盟强化还是日本军事大国化,都可能诱发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变动。尤其是日本政府着力加强与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家的安全合作,试图构建“日美 1”的地区安全模式。因此,研究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有利于我们全面掌控地区安全态势变化。总之,本课题将力争为我国的对日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言,积极应对日趋复杂的中日关系。本课题以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初期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具体实践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日美同盟”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关联性。日美同盟既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内涵之一,也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所处的外部环境。近年来伴随着日美同盟的强化,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发生重大转型,主要表现为基本防卫政策蜕变、实施军备扩张与海外派兵、推动驻日美军整编、拓展同盟体系以及强化自主防卫等内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或“日美同盟”的研究虽不断取得进展,但探讨二者之间关联性的研究成果较为薄弱。在中国有关“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肖伟等著的《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新华出版社2000年),较为详尽地研究了战后50余年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从“小”到“大”、从“内”向“外”、从“柔”到“刚”的演变进程;王少普与吴寄南合著的《战后日本防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根据战后日本防卫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划分,系统地考察了日本防卫思想、防卫体制、防卫力量的发展与变化;孙成岗著的《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则剖析了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内涵,并按照不同领域较为系统地阐释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过程;肖伟著的《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点》(新华出版社2009年),采取史学研究方法并大量运用相关史料,系统分析了战后初期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过程;李秀石著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5年),系统论述了近年来民主党政权及自民党安倍晋三内阁的防务与外交战略,验证了民主党政府与自民党政府在同一战略轨道上的政策连续性。另外,在吴寄南著的《新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李秀石著的《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等著作中,也有部分章节论及日本的防务战略。上述成果虽对战后不同历史阶段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进行了梳理,但并未将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促因加以系统分析,更未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进行全面阐释。同时,中国学者有关“日美同盟”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以刘艳著的《冷战后的日美同盟解读:兼论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尚书著的《美日同盟关系走向》(时事出版社2009年)、徐万胜著的《冷战后的日美同盟与中国周边安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为代表,并有诸多期刊学术论文的公开发表。这些论著大多是从国际关系视角来分析日美同盟的演变,集中探讨了日美同盟的“再定义”、发展趋势与外延影响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内涵。在国外有关“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近年来,日本学者的代表性论著,包括松村昌广著的《东亚秩序与日本的安全保障战略》(芦书房2010年)、樋渡由美著的《克服专守防卫战略:如何理解日本的安全保障》(密涅瓦书房2012年)、中野刚志著的《日本防卫论》(角川出版社2013年)等在内,均基于国际环境的变化探讨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问题点与应对策略。此外,国外学者有关“日美同盟”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包括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著的《朋友还是对手》(新华出版社1998年)、迈克尔·格林等主编的《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新华出版社2000年)、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的《日美安保体制》(有斐阁1997年)等在内。其中,孙崎享著的《日美同盟真相》(中译本,郭一娜译)(新华出版社2014年)系统回顾了日本战后70年的历程,认为决定战后日本外交的动力,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外压所产生的“自主”路线与“追随”路线的斗争。加文·麦考马克与乘松聪子合著的《冲绳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争》(中译本,董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系统论述了日美同盟框架下冲绳问题的演变历程,并介绍了冲绳当地民众追求正义与自由的抗争。从整体上看,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同盟视域下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论著不多,尚停留在数篇期刊论文与专著部分章节的程度,并未形成体系。因此,本课题研究既有一定的前期基础,又有巨大的潜力空间。本课题的研究思路是,紧紧围绕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基本内涵,抓住日美同盟强化这条主线,分层次论述日美同盟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密切关系,并深入剖析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对日本国家发展道路抉择、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以及中日关系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在此基础上总结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演变的规律性内涵。本课题的研究方法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政治学、军事学与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辅之以同盟理论的研究视角,注重对政府相关文件等一手资料的解读,力求提升本课题研究的针对性与应用效益。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基于日美同盟的视角,全面剖析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初期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具体内涵,探讨日美同盟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密切关系。本课题的正文由以下六章组成:章,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基本防卫政策蜕变。在归纳日本各项基本防卫政策(包括“专守防卫”“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无核三原则”等)的基础上,分析日美同盟的强化对日本基本防卫政策的侵蚀与损害。第二章,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备扩张。在回顾日美军备合作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分析日美军备合作的机制、特点与促因,梳理冷战后日本的军备扩张脉络。第三章,日美同盟与日本的海外派兵。在论述冷战后日本海外派兵发端的基础上,分析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政府实施海外派兵的法律制度与实践历程,论证日美同盟强化与日本海外派兵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第四章,驻日美军与日本的安全保障。在回顾驻日美军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分析21世纪初期驻日美军整编的背景、内容与进展,探讨驻日美军对日本安全保障所产生的诸多影响。第五章,日本的同盟拓展与“日美 1”模式。在阐释日本拓展同盟体系的基础上,分析日本如何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加强与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家的安全合作,并试图构建“日美 1”地区安全模式。第六章,日本的“自主防卫”与日美同盟。在概述日本自主防卫战略的基础上,分析日本政府如何通过武器装备建设、卫星情报与太空开发、施行“西南防御”战略等方式提高防卫“自主性”,并“巧用”日美同盟。此外,在终章中,分析了2012年12月成立的日本安倍晋三内阁推行右倾修宪、岛争应对、日美同盟及亚太外交的战略取向,指出这些战略取向必将削弱政治互信、难解领土争端、加剧大国博弈且试图拼凑遏华网络,对中日关系及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产生了消极影响。本课题研究的基本观点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与日美同盟密切相关。日美同盟不仅构成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主要内涵,更是其转型的基本路径与重要平台,二者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尤其是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在推动国家安全战略转型方面举措不断,其背后总是伴随着日美同盟的调节与互动。日美同盟的强化带来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外向化发展;与此同时,日本在追求防卫自主化的道路上又与日美同盟存在着结构性冲突和矛盾。第二,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表明21世纪初期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倾向不断增强,日本政府偏重于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利益与解决国际纷争。近年来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的举措已充分表明:日本正利用日美同盟的强化来打破战后美国协助日本所建立起来的防卫理念与基本共识。同盟关系的构筑既为结盟方提供了安全保障方面的利益,也意味着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战争风险。第三,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对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及中日关系发展产生了严重消极的影响。特别是日本政府施行“西南防御”战略并力图构建“日美 1”安全模式,制约了包括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等在内的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一国安全战略转型既是国际安全局势变动的结果,也是国际安全局势变动的促因。本课题研究力争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到创新:1选题创新,以“日美同盟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型”为题,选题原创性强,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填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空白的意义;2观点创新,本课题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问题,其有关日本完善安保法制、实施“西南防御”战略、增强防卫力量建设以及开展安保合作等领域的内容与观点,具有创新性;3资料创新,本课题研究力求在深入挖掘一手资料方面下工夫,大量运用外文原始资料与资料进行解读,强化课题研究的实证性与学理性。章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基本防卫政策章
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基本防卫政策战后,遵循《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的精神内涵,日本政府在防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专守防卫”“不做军事大国”“无核三原则”与“确保文官统制”等基本原则。然而,在强化日美同盟并推进日美军事合作一体化的进程中,包括“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等在内,日本的诸项基本防卫政策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害,乃至发生质的蜕变。节日美同盟与“禁止行使
‘集体自卫权’”的嬗变 “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既是战后日本安全保障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其安全保障的重大战略抉择。冷战后,伴随着自卫队“国际合作”的实施以及日美安保体制的强化,日本安全保障的政策实践开始带有浓厚的“集体自卫权”色彩,国内主张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议论也日趋活跃。一、《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提出所谓的“集体自卫权”,一般是指即使本国未遭受武力攻击,但当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遭受武力攻击时,即认为是对本国的攻击并加以反击的权利。它是与“个别自卫权”相对而言的,而后者仅仅是指以实力排除对本国直接攻击的权利。在国际社会中,“集体自卫权”是作为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并得到普遍承认。例如,《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安理会断定侵略行为存在的情况下,可采取包括武力行使在内的必要措施。其中第51条明确提出,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王铁崖等编:《联合国基本文件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在北约组织的章程中,也将某一缔约国遭受的武力攻击视为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战后“集体自卫权”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是联合国各创始会员国为防范法西斯势力复活而制定的权利和措施。对于日本而言,《日本国宪法》的特殊性使其对自卫权进一步加以限制。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宪法第九条上。该条由前后两项组成,内容如下:“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唯有《日本国宪法》明确记载“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该宪法也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根据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战后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安全保障的基本原则,如“专守防卫”原则、“无核三原则”、文官统制原则以及“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其中,“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主要体现在日本政府有关安全保障的“统一解释”之中。1972年10月,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日本政府有关“集体自卫权”的“统一解释”为:“我国作为主权国家,当然拥有国际法规定的集体自卫权……但是,以和平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宪法不能解释为无限制地承认自卫措施……宪法所能允许的武力行使,仅限于应对针对我国的紧急且不正当的侵害,所以,以阻止施加于他国的武力攻击为内容的‘集体自卫权’,在宪法上是不允许的”。 『防衛ハンドブック』、朝雲新聞社2003年版、571-572頁。1981年5月,在对众议院议员稻叶诚一的质询答辩书中,日本政府认为:“在国际法上,国家拥有集体自卫权,也就是即使本国未遭受直接攻击,但对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别国所遭受的武力攻击,具有以实力阻止之的权利。我国在国际法上拥有这种集体自卫权,作为主权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宪法第九条下所许可的自卫权行使,应限制在以防卫我国为目的的必要小限度范围内,行使‘集体自卫权’则超出了该范围,为宪法所禁止。” 『防衛ハンドブック』、朝雲新聞社2003年版、571頁。此后直至2003年2月,小泉首相依旧在参议院表示不考虑修改关于“集体自卫权”的政府“统一解释” 李秀石:《“行使集体自卫权”与日本防卫转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6期,第16页。。在上述政府“统一解释”中,值得注意的表达方式就是,日本的自卫权行使应限制在“必要小限度”内。这与国际法上通行的自卫权观念相比,有着一定差距。例如,按照前述《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行使自卫权受到下列条件制约:一是在发生武力攻击的情况下;二是在安理会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采取必要措施之前。与之相比,1972年10月,在日本政府向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提出的资料中,主张行使自卫权必须满足下列三个要件:“对我国发生紧急不当侵害;在上述场合下没有其他适当手段;应限于必要小限度的实力行使。” 『防衛ハンドブック』、朝雲新聞社2003年版、545頁。因此,日本行使自卫权,不仅要受到国际性制约条件的限制,同时也应受到国内制约条件——“必要小限度”的限制。日本政府也正是由于认识到本国的宪法解释与国际法上的自卫权观念不相一致,才决定“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日本政府关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统一解释”,在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缺少宪法改革的情况下,宪法政治在日本持续出现。一些具体的、能向自卫队施加法律限制的做法,已经获得了准宪法的地位……政府提出的这些证词长时间内在许多会议上不断得以重申,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必须被满足的、引人注目的政治信条。” \\[美\\]彼得·J卡赞斯坦著:《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汉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对于日本国内主张增强防卫力量、争当军事大国的政治势力而言,宪法第九条以及有关“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政府“统一解释”,则成为影响其安全保障战略调整的一大障碍。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重整军备的背景下,日本国内即出现次改宪高潮。但在“1955年体制”时期,改宪派人数始终未能达到修改宪法所需要的众参两院全体议员2/3以上,所以,日本政府更多地是通过“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冷战后,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的步伐加速,其与可否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问题相交织,日本国内的改宪动向亦不断增强。1994年11月3日,《读卖新闻》首次刊载将改宪主张明文化的《宪法修改试案》,提出将宪法第九条第二项删除,并主张可以拥有用于自卫的组织。 『読売新聞』1994年11月3日。此后,不断有政治家、学者乃至民间团体纷纷发表各种所谓的“改宪试案”。当前,虽然日本国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改宪论调,但实际上许多论调未必非得通过修改宪法来实现。例如,对于主张明确载有保护环境条款的“改宪论”而言,即使写入宪法也未必就能做到保护环境,相反,只要采取完善环保立法、制定政策并附加预算等措施,不修改宪法也能做到保护环境。因此,日本改宪动向的核心在于修改宪法第九条第二项。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只尽可能简单地改正现行宪法给日本国政造成障碍的部分即可。必要小限度的修改就是删除或修正第九条第二项。” 北岡伸一:『憲法改正の停滞をいかに打破するか』、載『中央公論』2002年6月号、55頁。自民党前干事长山崎拓则表示:“修改宪法的观点各种各样,但修改第九条是改宪问题的核心所在”,“不涉及第九条的修改宪法没有任何意义”。 山崎拓:『私が考える平成憲法「前文」』、載『中央公論』2002年6月号、69頁。毫无疑问,改宪动向的焦点在于如何促使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除了履行高难度的改宪程序以外,更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更正政府的“统一解释”。有关自卫权问题的政府“统一解释”出尔反尔,这在战后日本政治中并非没有先例。例如,1946年6月,吉田首相在国会答辩中曾表示:“基于第九条第二项不承认一切军备与国家的交战权,结果作为自卫权发动的战争和交战权均被放弃了。” 杉原泰雄編著:『資料で読む日本国憲法』(上)、岩波書店1994年版、114頁。但至1954年12月,鸠山内阁的“统一解释”则明确主张宪法不否定自卫权。因此,仅就法律手续而言,日本距离行使“集体自卫权”只有一步之遥,即只要政府重新解释宪法并未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即可。换言之,即使日本政府在国会答辩中依然一如既往地表示“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但通过政策实践予以“悄然”否定,也能达到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的目的,而且是一种低风险的政治选择。二、自卫队“国际合作”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模糊1957年5月,日本政府颁布的《国防基本方针》规定,“支持联合国的活动,谋求国际间的协调,以期实现世界和平”。由此看出,不论其实质如何,日本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提倡以“联合国中心主义”来实现国家安全保障。问题在于日本自卫队如何在宪法的框架下实施“国际合作”,自卫队的“国际合作”是否涉嫌行使“集体自卫权”。因为,在此前的1954年6月,日本参议院曾通过了禁止自卫队向海外出动的简短决议:“本院在自卫队创立之际,按照现行宪法的条章和我国国民炽烈的爱好和平精神,在此重新确认不向海外出动。” 金熙德:《日本安全战略面临十字路口》,载《日本学刊》2002年第2期,第7页。实际上,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主体,日本政府试图派遣自卫队实施“国际合作”的意图亦早已有之。1966年,日本外务省曾制定“联合国合作法案”,拟对联合国所采取的符合宪章精神的军事行动,提供包括自卫队人员在内的援助支持。 肖刚著:《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105页。1980年10月,日本政府在对众议院议员质询的答辩书中称:“所谓的海外派兵,一般而言,是指以行使武力为目的将武装部队派遣至他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这种海外派兵通常超过了自卫所需的必要小限度,在宪法上是不允许的。与此相反,所谓的海外派遣,先前虽未加以定义,但不以武力行使为目的将部队派遣至他国,宪法上并非不允许。” 『防衛ハンドブック』、朝雲新聞社2003年版、554頁。1990年2月,在众议院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上的政府“统一解释”为:“向与战斗行为划清界限的地区运输医疗用品和食品,从宪法第九条的标准判断,应当不存在问题。” 同上、573頁。尽管如此,受美苏两极冷战格局的制约,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活动空间大体上局限于日本本土。冷战后,以1990年8月爆发的海湾危机为契机,日本政府开始正式启动自卫队实施“国际合作”的进程。当时,尽管日本先后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了总额达13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但仍被西方舆论抨击为“纸上盟国”,“只出钱、不流汗”。受此“刺激”,1991年5月,日本向海湾地区派遣扫雷艇编队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一起执行扫雷任务。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合法地”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人力支援,1990年10月,日本政府向临时国会提交《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在野党方面对该法案坚决反对,认为对以行使武力为目的的多国部队提供合作,即使是后方支援,也具有与武力行使成为一体的可能性,结果该法案成为废案。后经日本政府对法案内容加以修改,并与部分在野党势力加强磋商,1992年6月,日本国会终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正式从法律上为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扫清了障碍。在上述法案的国会审议过程中,朝野政党就“维和法案”与宪法的整合性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由于宪法禁止“以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且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在相当程度上有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嫌,所以日本政府主要就“参加”与“合作”、“武力行使”与“武器使用”、“指示”与“指挥”等问题进行了“统一解释”。关于对“联合国军队”的“参加”与“合作”的相互区别,1990年10月,日本政府在众议院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答辩中发表如下“统一解释”『防衛ハンドブック』、朝雲新聞社2003年版、560—561頁。:1对所谓“联合国军队”的介入方式有两种,即“参加”与“合作”;21980年10月28日政府答辩书中所谓“参加”,即意味着在“联合国军”司令官的指挥下,作为其中一员行动,和平合作队参加“联合国军队”,如果该“联合国军”的目的、任务伴随着武力行使,这同自卫队参加该“联合国军”一样,超出了以自卫为目的的必要小限度的范围,是宪法所不允许的;3与此相对,所谓的“合作”是一种包含上述参加“联合国军”在内的更广意义上的介入形态,含有在“联合国军”组织之外、未到“参加”程度的各种支援;4关于未到“参加”程度的“合作”,即使该“联合国军”的目的、任务伴随着武力行使,这也并非完全不允许,宪法禁止与该“联合国军”的武力行使成为一体,但允许与该“联合国军”的武力行使不成为一体。关于“武力行使”与“武器使用”的相互区别,1991年9月,日本政府在众议院PKO特别委员会上发表的“统一解释”为:“宪法第九条项的‘武力行使’是指由我国的物资、人员系统实施作为国际武力纷争一环的战斗行为……保护自己及与自己处于同一现场的我国成员的生命或身体,是一种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所以以此为目的的必要小限度的‘武器使用’,不属于宪法第九条项所禁止的‘武力行使’。” 『防衛ハンドブック』、朝雲新聞社2003年版、583-584頁。关于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的“指示”与“指挥”的相互区别,1992年2月,日本政府在参议院PKO特别委员会上发表的“统一解释”为:“自卫队的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场合,部队长官制定或变更实施要领应与联合国的‘指示’相适合,防卫厅长官根据该实施要领来指挥监督我国派遣的部队,进行国际和平合作业务。”同上、627頁。上述国会审议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与“国际合作中的武力行使”这两者的相互关系问题。显然,日本政府在国会答辩中的“统一解释”近乎于一种“文字游戏”,试图极力避免“国际合作中的武力行使”。这样,日本政府将自卫队实施的“国际合作”不得不暂时限制在维和行动中与行使武力无关的活动领域,《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第2条第二款中也规定“国际和平合作业务的实施等,并非武力威吓或武力行使”。但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与联合国制定的有关维和章程之间存有相互矛盾之处。例如,根据联合国的相关规定,从事后方支援的自卫队也具有保护其他部队的义务,并且在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之前,联合国秘书处已经向日本政府明确了这一点。 \\[英\\]赖因哈德·德里弗特著:《愿望与现实——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历程》(汉译本),高增杰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无论如何,依上述法案,1992年10月,日本政府首先向柬埔寨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此后直至2003年底,日本政府又先后向莫桑比克、卢旺达、戈兰高地、东帝汶、阿富汗等地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另外,据日本媒体报道,2004年1月,日本政府正在拟订中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其中原本被列为“从属任务”的“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将被提升为自卫队的“主体任务”,把自卫队的国际军事活动作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読売新聞』2004年1月6日。三、日美安保体制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蜕变1960年修改的《日美安保条约》的前言中规定:“两国确认拥有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个别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鉴于两国共同关心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决定缔结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该规定与政府有关“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统一解释”是相互矛盾的。整体上,“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是战后日本政府制定所有安全保障政策的基本根据。因此,“日本防卫政策存在着法理上的矛盾,即战后日本‘宪法’和‘日美安保法’这两个并行法系之间的矛盾”,“由‘日美安保条约’形成的日美安保体制对日本战后的防卫所起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它甚至动摇了‘和平宪法’对日本战后防卫所做的种种限制”。 汪晓风、陈霞:《日本战后防卫政策的演变及走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5期,第31页。长期以来,受日本政府“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统一解释”限制,日美安保体制是一种美国对日本实施保护,日本向美国提供基地与有条件支援的不均衡、不对称体制,即所谓的对美“依赖型”体制。冷战后,日本国内要求打破“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限制的呼声不断高涨,主张自卫队向能为美军提供战斗支援并与美军并肩战斗的方向发展,以便提高日美同盟的“可信赖性”。纵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美安保体制的“再定义”进程,诚如日本学者所言:“再次确认日美安保的重要性,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其核心工作就是将‘个别自卫权’与‘集体自卫权’之间的‘灰色’要素视为个别自卫权的行使,依此名目与形式来推进‘安保再定义’。” 室山義正:『冷戦後の日米安保体制―「冷戦安保」から「再定義安保」へ』、載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日米安保体制―持続と変容』、有斐閣1997年版、138頁。具体而言,1997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简称“新指针”)强化了日本发生“周边事态”时的日美相互合作,规定自卫队对美军行动提供各项“后方地区支援”。所谓的“后方地区”,“新指针”则明确指出:“虽主要在日本的领域内进行,但也包括与作战地区截然相区分的、日本周围的公海及其上空。” 『防衛ハンドブック』、朝雲新聞社2003年版、379頁。众所周知,在现代战争中很难将“后方”与“前方”区分开来,“指针和指针相关法案所规定的日本仅仅提供‘后方支援’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一旦发生‘周边事态’,美、日和冲突的第三方事实上都会处于‘交战’状态。” 朱锋:《“周边事态”:矛盾与问题——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相关法案的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8期,第25页。显然,在日本本国未受到直接武力攻击的“周边事态”中,根据“新指针”及《周边事态法案》等的规定,自卫队在军事行动上具有与美军一体化的可能性,即突破了日本政府有关“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对于“新指针”,曾任日本防卫大学教官的黑川雄三也坦然承认:“在新指针的各部分都强调完善日美合作的‘机制’,强烈主张努力使日美间的共同行动更加机制化且体系化”,“当朝鲜半岛‘有事’、台湾海峡‘有事’等亚洲危机发生之际,战后五十年来终于开辟了日本支援美军的道路。” 黒川雄三:『近代日本の軍事戦略概史』、芙蓉書房出版2003年版、286頁、292頁。另据报道,自1996年起,日本航空自卫队开始参加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举行“红旗阿拉斯加”(RFA)演习,并自2003年起派遣F-15战斗机参加,为执行轰炸任务的美国B-52战略轰炸机护航。对此,琉球大学教授我部政明表示:“可以认为这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为前提的训练。我了解到航空自卫队的这一训练,极为吃惊。难道日本的防卫需要战略轰炸机吗?这可能已经大幅超过专守防卫的框架。” 《日航空自卫队曾参加美轰炸演习》,载《参考消息》2013年8月14日。在日美安保体制强化的机制建设取得新进展后,美国国内更加重视日本的地缘战略地位与经济实力,鼓励日本突破“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例如,2000年10月,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发表特别报告《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认为:“日本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制约两国的同盟合作。如果解除这一禁止,两国就可望更加密切、有效地进行安全合作。……我们考虑以美英特殊关系为美日同盟的模式。” \\[日\\]《世界周报》2001年1月30日;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01页。随后,2001年初上台的美国布什政府也多次表明欢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2011年1月18日,美国国会研究部向国会递交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禁止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原则也是(日美)开展防务合作的障碍之一”。 钱文荣:《美国对日本修宪究竟是什么态度?》,载《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4期,第30页。与之相呼应,2001年3月23日,自民党国防部会(部会长为依田智治)决定提出政策建议,要求变更政府解释并行使集体自卫权,以便强化日美防卫合作。 『東京新聞』2001年3月23日。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后,日本政府借口承担“盟友”的义务与责任,日美安保体制下的“集体自卫权”问题更加突出。 根据《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等法案的规定,2001年11月,日本派遣自卫队舰艇前往印度洋地区进行“情报收集”和“后勤补给”,对美军展开支援活动。此次日本大规模出动自卫队为美军提供军事援助,无疑是“新指针”的一次具体落实和双方“战时”合作形式的实战演习。对此,日本国内舆论指出:“在远东地区以外实施后勤支援,不仅是对美国,还扩大到英国等其他合作国家”,“也可认为后勤支援已经构成集体自卫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实际上在反恐特别措施法下行使了集体自卫权”。 『日本は集団的自衛権を行使した』、載『産経新聞』2002年2月5日。即使是主张修改宪法的日本学者,也承认日本政府的安全保障政策自相矛盾,认为:“一般而言,提供基地即是行使集体自卫权。但是,与国际标准相比,日本政府采取了狭义解释,认为提供基地不属于行使集体自卫权。于是,事实上在周边事态法中集体自卫权的范围被缩小,在反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中又被进一步缩小。但是,内阁法制局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说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 北岡伸一:『憲法改正の停滞をいかに打破するか』、載『中央公論』2002年6月号、59頁。 此后,随着2002年11月美朝核危机的再度凸显和2003年3月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日本政府仅仅抓住在上述问题中与美国的“合作机会”:2004年1月9日,日本政府正式下达了向伊拉克派兵的命令。对此,日本民主党代表菅直人认为,自卫队队员是以作战为前提的、同美英军队一样的“盟军要员”。『朝日新聞』2004年1月23日。在2004年3月9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日本政府通过了《国民保护法案》等7项与“有事法制”相关的法案,并全部递交国会审议。其中,《自卫队法修正案》规定有日本在遭到攻击之前就可以向美军提供弹药、允许对第三国船只进行危害性射击等条款。对此,在野的社民党、日本共产党认为上述条款违背了宪法有关放弃交战权的规定和政府迄今表示不实施集体自卫权的承诺,并加以反对。 苏海河:《日本政府通过“有事法制”相关七法案》,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3月10日。同时,在日美两国联合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过程中,日本国内主张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呼声不断高涨。例如,据报道,2005年1月日本政府又表示准备对导弹防御做出“新解释”:如果对射向美国且经过日本上空的导弹进行截击,不属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范畴。其理由是要提高截击的准确率就必须尽早发布截击命令,且从导弹头上分离的导弹部件也有落到日本的危险,所以拟将截击弹道导弹作为行使“个别自卫权”来加以解释。『産経新聞』2005年1月14日。2006年10月朝鲜进行核试爆后,日本国内有关“集体自卫权”的讨论再一次普遍展开:10月1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对“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提出质疑,称“如果朋友在我的家中被打,我可以马上帮他,而他一旦迈出我家大门我便说‘无能为力’,这样能维持友情吗?”;同月29日,《产经新闻》载文主张“目前日本至少要在与美国一起防御导弹袭击时行使集体自卫权,让日本自卫队能够迎击并非面向日本(可能是面向美国)的导弹”。《日本大阅兵冲着朝鲜》,载《环球时报》2006年10月31日。2006年11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又表示将“研究拦截飞越日本上空攻击美国的弹道导弹的可行性”,被媒体普遍解读为是日本欲实施“集体自卫权”的重要暗示。此外,由于安倍内阁大力推动日本的修宪进程,实质上日本政府内部已经在研究有关集体自卫权的解释内容。因此,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强化历程表明,日本政府所谓的“集体自卫权”观念日趋模糊,与“个别自卫权”间的区别不断被缩小,从而导致自卫队正在“个别自卫权”的名义下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实质。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大国地位与作用,应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谋求亚洲各国的信任与支持为前提,并且其“国际贡献”也完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集中于非军事领域。否则,日本执意急于行使“集体自卫权”,不但与《联合国宪章》中以反侵略为宗旨的“集体自卫权”精神相去甚远,而且也只能充当美国单边主义军事干涉行动的一翼,给国际安全环境造成消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仅仅是日本政府根据宪法第九条而做出的“政府解释”,带有相当的法理脆弱性。一旦日本政府重新做出解释,该项政策瞬间即可发生变更,并不受限于任何法律规定。例如,2003年5月3日宪法纪念日之际,自民党资深政治家中曾根康弘和宫泽喜一在NHK电视节目中均表示在现行宪法下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督促政府变更解释,指出“只要小泉首相说能够行使就可以了”。『日本経済新聞』2003年5月4日。2012年11月21日,日本自民党公布了该党众议院竞选纲领,关于安全保障问题提出实现“可行使集体自卫队权”。2012年11月23日,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在讲演中再次强调了行使集体自卫权对日本的必要性,声称“如果在‘尖阁诸岛’防卫的过程中美国船只受到攻击,而自卫队却不出手相助,那么日美同盟就将终结”。『朝日新聞』2012年11月24日。2013年8月,安倍内阁起用日本驻法国大使小松一郎担任内阁法制局长官一职,安倍希望通过任用对修改宪法解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态度积极的小松来加快变更解释的工作。2013年9月,安倍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重建安全保障基础恳谈会”(安保法制恳谈会)在首相官邸召开会议,就修改宪法解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重新展开讨论。2014年1月24日,安倍首相在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再次表示将积极推动修改宪法,为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问题“铺路”。目前,对于安倍内阁第二次执政后积极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动向,美国大体上持支持态度。例如,2013年10月,岸田文雄外相、小野寺五典防相与美国的克里国务卿、哈格尔防长齐聚东京外务省饭仓公馆,举行日美安保磋商委员会会晤(“2 2”会议)。根据会议发表的共同文件,提及日本考虑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等事项,写明“美国欢迎采取这些措施,将与日本展开紧密合作”。在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等知日派一直要求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也是美方此次表示“欢迎”的背景之一。但是,美国的支持力度与安倍内阁的政策取向或许还是有距离的。在论证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同时,安倍政权还在讨论赋予自卫队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对于美国而言,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是对美军作战行动的一种辅助和补充,而不是超越同盟框架并摆脱美方限制。2013年5月,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安倍提到了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的必要性。美国政府人士对此表达了不快:“关于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一事,日本没有与美国进行事先协调。” \\[日\\]安全保障问题研究会:《站在十字路口的安全保障》,载《世界》2013年12月号。 2013年10月举行日美“2 2”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丝毫未提及安倍主张的攻击敌方基地能力一事,取而代之称“加强保卫本国主权以内范围的能力”。结果,2014年7月1日下午,日本安倍晋三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这意味着日本战后以专守防卫为主的安保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该内阁决议案推翻了日本历届内阁遵守的“自卫权发动三要件”,提出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1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或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遭到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的存亡,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明确危险;2为保护国家和国民没有其他适当手段可以排除上述攻击;3武力行使限于“必要小限度”。四、《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与日本“集体自卫权”立法为落实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安倍晋三内阁在2015年例行国会上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安保立法,此轮立法的核心内涵就是推动日本全面实施海外派兵的集体自卫权立法。2015年5月14日,安倍内阁通过了安保相关法案,并于次日提交国会审议。安倍内阁向国会提交的安保相关法案,由1项新立法和10项修正法组成(参见表1-1)。1项新立法是《国际和平支援法案》,据此日本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国家军队提供支援,其实质是“海外派兵永久法”;10项修正法统一“打包”为《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要旨大多涉及行使集体自卫权、扩大自卫队海外军事行动范围等内容。因此,安保相关法案的核心就是赋予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律权利,自卫队由此实现自由向海外派兵。
表1-1安保相关法案
《国际和平支援法案》(新法)自卫队可对多国部队实施后方支援的恒久法《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
(修正现行10部法律的一揽子法)(1)自卫队法(2)联合国维和活动(PKO)合作法(3)周边事态法→重要影响事态法(4)船舶检查活动法(5)武力攻击事态法→武力攻击·存立危机事态法(6)美军行动通畅化法案→美军等行动通畅化法案(7)特定公共设施利用法(8)海上运输规则法(9)俘虏对待法(10)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设置法注:(3)(5)(6)的法律名称发生变更。在安倍内阁推动安保立法的过程中,2015年4月,日美两国政府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根据新版指针,未来日本自卫队将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军开展更紧密的军事合作,实现所谓的“无缝”对接。因此,安保相关法案的制定,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为自卫队协助美军行动提供国内法律保障(参见表1-2)。
表1-2安保法制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关联性
目的安保法制新指针增设或强化的主要合作项目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包含灰色事态
的平时重要影响事态危机存立事态武力攻击事态
(日本“有事”)修正自卫队法,通过武器等防卫来护卫他国军队重要影响事态安全确保法(修正周边事态法),扩充对美军等后方支援修正武力攻击事态法,有限行使集体自卫权共同训练、警戒监视、装备护卫(以钓鱼岛、南海为想定)对美军等后方支援的活动地域·内容进行扩充(以朝鲜半岛、南海为想定)海面扫雷、海上限制、船舶护卫、弹道导弹防卫(以朝鲜半岛、海上运输线为想定)岛屿防卫(以钓鱼岛等西南群岛为想定)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制定国际和平支援法,对多国军队等实施后方支援对应对国际纷争的美军及多国军队实施后方支援修正PKO合作法,实施人道主义复兴援助及安全确保活动国际人道主义复兴援助活动、治安维持活动修正船舶检查活动法,平时参加国际性的船舶检查活动旨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船舶检查等海洋安全保障资料来源:安保協議、大筋決着…日米指針27日合意見通し\\[EB/OL\\]。http://wwwyomiuricojp/politics/20150422-OYT1T50005html?from=ycont_top_txt2015年7月16日,在民主党、维新党、日本共产党等主要在野党拒绝参加表决的情况下,由自民、公明两党联盟控制的众议院全体会议强行表决通过了安保相关法案。9月19日,不顾广大民众及在野党势力的强烈反对,参议院全体会议又强行表决通过了安保相关法案。总之,冷战后日本政府的安全保障政策实践表明,其所谓的“集体自卫权”观念日趋模糊,与“个别自卫权”间的区别不断被缩小,从而导致日本正在“个别自卫权”的名义下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实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大国地位与作用,应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谋求亚洲各国的信任与支持为前提,并且其“国际贡献”也完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集中于非军事领域。否则,日本执意急于行使“集体自卫权”,不但与《联合国宪章》中以反侵略为宗旨的“集体自卫权”精神相去甚远,而且也只能充当美国单边主义军事干涉行动的一翼,给国际安全环境造成消极影响。第二节日美同盟与核潜力威慑战略日本政府在核武器开发领域一贯坚持所谓的“无核三原则”,即“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但是,在拥有强大的核武器开发潜力的条件下,近年来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核武器开发问题上的“复杂”声音,开始对外形成事实上的“核潜力威慑战略”。“核潜力威慑战略”是指在拥有强大的核武器开发潜力的条件下,在是否进行核武器开发的问题上保持“模糊状态”,或者明确表示能够迅速开发且拥有核武器,以此作为筹码并对其他国家产生牵制与威慑作用。一、“无核三原则”与核潜力威慑战略的实力基础战后,日本广大民众基于“原子弹受害国”的立场形成了强烈的反核意识,并不断举行要求禁止原子弹的大众游行。受此影响,1955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原子能基本法》,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必须限于和平目的,禁止制造和拥有核武器。随后,1967年12月11日,针对社会党国会议员成田知巳的质问,日本首相佐藤荣作首次明确提出了“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政策要求日本不仅不能核武装自己,同时也将限制其他国家的核力量进入日本行政辖区。佐藤内阁所提出的“无核三原则”为其后历届政府所确认,成为日本防卫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1976年6月8日,日本国会又正式批准政府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开始承担不制造、不拥有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1996年9月24日,日本在开放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的当天加入,并于1997年7月8日得到国会批准。尽管日本政府一直对外公开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在内部探讨过核武器开发问题。例如,1969年外务省的一份内部文件指出,“我们权且维持不拥有核武器的政策”,但“保留生产核武器的经济和技术可能性,同时确保日本在这方面不受干扰”。这种“技术威慑”姿态本质上是暧昧的,而外务省坚称这份文件是研究论文,不是政策声明,令此事更添一份暧昧色彩。 《日本核政策或不再暧昧》,载《参考消息》2014年4月17日。在核武器问题上,日本是既有能力也有意图,但未按照意图行事的国家。它开创了一种核威慑类型,其所依赖的不是任何明显的威胁,而是纯粹的潜在可能性。在上述核政策框架的制约下,多年来日本政府一直积极开发商业用核技术,大力保障核物质和核设施。由于相当一部分商业用核技术可以转化为军事用途,结果日本的核武器开发潜力也得到了强化。具体而言,日本的核武器开发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光明日报》2005年9月21日。:1日本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已有足够的储量。日本众多核电站中的核燃料棒燃烧后,会生成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核材料钚-239。到2010年,日本钚的总储量将达到100吨(1000千克质量合格的钚-239可以制造出约120枚核弹头),从而成为世界大钚储存国;2日本的核技术研究已迈进核科学的前言。日本用10年时间,投入巨资60亿美元,建成“文殊”中子增殖反应堆,已于1995年8月试运行成功并正式发电。日本另一迈进核技术前沿学科的是对热核聚变技术的研究,已拥有大型螺旋核聚变实验装置,正在研究可控核聚变的超难技术;3日本可利用超高速计算机仿真核爆炸,无需进行核爆炸试验,即可研制出原子弹。日本是无核武器国家中拥有核材料多的国家。从技术角度看,日本拥有的大量武器级核材料已远远超出其民用核技术的需求,引发国际社会的疑虑和不安。关于日本储存的放射性物质钚,据日本共同社2014年1月26日报道,美国曾于冷战时期交给日本331千克钚,其中大多数为武器级丰度的钚,用于核研究,即在茨城县那珂郡东海村用作快中子反应堆核燃料,但亦可制造40—50枚核弹。2005年,日本政府又将原来的日本原子能研究所与核燃料循环开发机构合并,成立了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主要从事核能的基础研究开发、量子发射技术、核燃料循环利用以及核废弃物处理技术等。对于日本的核武器开发潜力,日本国内各种势力曾多次明确表示具有信心。例如,日本原子能资料情报室代表高木仁三郎指出:“日本如果决心制造核武器,一个月甚至两三星期就可以制造出来,日本实际上等于已经拥有了核武器”;1994年6月17日,日本首相羽田孜在国会称:“日本确实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但因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而没有制造。” 袁蕴华、吕云:《日本的核能力及核政策》,载《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11期,第2页。对此,美国前驻日大使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也承认日本已完全具备迅速开发核武器的潜力,“没有多少人怀疑东京在遇到刺激的情况下迅速获取核力量的能力,而其先进的空间计划将使它能够立即把洲际导弹运载系统投入战场”。 \\[美\\]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著:《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中文版),于铁军、孙博红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当然,即使是对日本的核武器开发潜力进行保守估计,那也只是所需的开发时间略长些而已。例如,2006年12月25日,日本《产经新闻》突然曝光了一份有关核武器制造能力的政府内部评估文件,认为“即使不存在法律和条约上的限制,利用目前日本拥有的核相关设施及核燃料,想要在一两年内实现核武器的国产化是不可能的。日本试制出小型核弹头少需要3—5年的时间,并要花费2000亿至3000亿日元的经费和动员数百名技术人员。如果在不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下进行开发,时间和费用将进一步增加”。『産経新聞』2006年12月25日。因此,对于日本而言,是否拥有核武器仅仅是一个政治决定,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技术障碍和物质材料问题。对此,日本政府高官也曾先后多次表态:2002年5月31日,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公开声称“如果只用于防卫,日本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日本不能拥有核武器是不合理的”,“现在,日本正处在将要修改宪法的时代,如果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民认为可以拥有核武器的话,说不定将要对宪法进行修改” 中国军控协会:《2004: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报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2006年11月29日,外相麻生太郎在参议院安全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日本有能力制造核武器,但不代表我们有计划拥有核武器”,并指出宪法容许日本以核武器来防卫,“拥有水平的防卫用武器并没有违反宪法的第九条,即使是核武器,如果它们在规定范围之内,也不应被禁止”。由此可见,日本拥有强大的核武器开发潜力是毋庸置疑的,是处在“核门槛”外沿的个潜在核大国。日本政府采取拥有“核潜力”而非“核武装”的方式,事实上形成了一种间接性“核威慑”的效用基础。当然,这种效用的发挥,则更多地体现为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应对所谓“周边核威胁论”的过程中不断要求进行核武装。二、“周边核威胁论”与核潜力威慑战略的升级倾向在如何判断冷战后日本所处的周边安全环境方面,日本政府一贯持有“周边核威胁论”的观点。仅以冷战后日本政府对外公布的《防卫计划大纲》为例,1995年11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通过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指出,在日本周边地区“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军事力量依然存在,许多国家以经济发展等为后盾,正致力于扩充军事力量以及实现其现代化” 。2004年12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通过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再次明确指出,在日本周边地区“依然存在着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大规模军事力量,同时多数国家正致力于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其中“北朝鲜在进行大规模杀伤武器及弹道导弹的开发、部署、扩散等的同时,还保持着大规模的特种部队。北朝鲜的这种军事动向是地区安全保障中的重大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成为国际性防扩散努力的严峻课题。对本地区安全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正在推动核力量、导弹力量和海空军的现代化,并谋求扩大海洋活动范围,对这一动向今后仍需加以关注”。另外,进入21世纪后,日本国内对包括恐怖袭击等因素在内的非传统型核威胁的关注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为了应对日本周边地区存在的所谓“核威胁”,日本政府在政策层面上依旧坚守“依靠美国的核威慑力量”的立场。同时,作为具体措施,日本又与美国共同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1999年8月16日,日美两国在东京签署了“共同研究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协议换文和列有具体研究项目的备忘录”, 标志着日美联合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正式启动。在2003年12月19日举行的“安全保障会议”上,日本政府又决定从2004年度开始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按照日本防卫厅的规划,日本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将分阶段建设,2007年建成个弹道导弹防御系统,2011年完成整个工程的建设。日本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将由在大气层外截击导弹的“宙斯盾”舰载“标准-3”型(SM-3)导弹系统和在地面附近截击导弹的地对空“爱国者-3”型(PAC-3)导弹系统两部分组成,从而构筑起由海基中段防御系统和地基末段防御系统组成的双层防御体系。日本建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是美国弹道导弹防御战略的有机组成以及日本军事大国化的重要体现。此外,日本还积极开发使用固体推进剂火箭的空间发射技术,这可为其远程导弹计划奠定基础。例如,日本的M-5型火箭、H-2A型火箭均较适合改装为洲际弹道导弹。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是个攻防兼备的作战系统,它的机载激光拦截系统和拦截导弹均具有强大的攻击能力,因此,对东亚地区安全形势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扩散了导弹防御技术,诱发新一轮地区军备竞赛。毋庸置疑,随着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建设的推进,日本的核武器开发潜力以及对核武器威胁的应对能力均将得到进一步提高,并以此来辅助美国的核遏制力量,共同应对所谓的“核威胁”。对此,在2005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指出:“对于弹道导弹攻击,应通过确立包括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必要的体制,予以有效应付。对于针对我国的核武器威胁,应配合美国的核威慑力量,通过此种努力予以妥当应付。”从中可见,对美国的核威慑力量,日本正由全面“依靠”向着局部“配合”的方向转变,即日本的核潜力威慑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转换为核威慑战略的升级倾向。与此同时,更为直接的是,2002年底朝鲜核危机再度爆发后,日本政界主张政府改变其核政策的呼声不断高涨,许多政治家在核政策上的政策取向趋于右倾。例如,2003年11月,根据日本媒体对新当选的480名国会议员所进行的“政策取向”问卷调查,在“关于日本的核武装构想”这个问题上,占总数17%的83名议员认为,“如果国际形势需要,日本应当发展核武器,实施核武装”;自民党籍议员中有30%表示应该解除核禁令。 『毎日新聞』2003年11月10日。在2006年10月朝鲜宣布进行了核试验之后,日本国内爆发了新一轮关于“核武装”的争论:10月15日,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在电视节目中称“宪法没有禁止日本拥有核武器。有核武器会降低受攻击的可能,即可以进行核报复。因此,可以(就日本的核武装)进行议论” 《美国担心日本“核武装”》,载《环球时报》2006年10月18日。;10月18日,外相麻生太郎在国会答辩中称:“邻国已经拥有(核武)时,我们不研讨、不交换意见——这当然是一种思考方式;但我认为就此展开讨论也是很重要的。” 《赖斯猛压日本核冲动》,载《环球时报》2006年10月19日。的确,日本政府也一贯坚持宪法并未禁止日本拥有核武器的统一见解。2006年11月14日,日本政府再次就拥核是否合法做出正式声明,一方面,表示“从纯粹的法理角度来看,宪法第九条没有禁止我国拥有自卫所必需的限度的核武器……即便是我国拥有核武器,我们也认为只要限制在这一程度内,拥有它们并不一定违反宪法”,另一方面,又称“政府并没有对‘无核三原则’进行修改的意向”。 《日本公开称拥核不违宪》,载《环球时报》2006年11月16日。 2012年11月20日,日本维新会代表、老牌右翼政治家宣称“不妨进行有关核武器的模拟演习,这将成为一种威慑力量”。『朝日新聞』2012年11月24日。日本政界的上述两面性政治表态,客观上只能是进一步增强了其核潜力的对外威慑效用。从实践中看,2006年11月9—16日,日美两国在日本海举行了为期约1周的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包括美国“小鹰”号航母和日本主力战舰“金刚”级导弹驱逐舰在内的102艘两国海军舰艇参加了演习,双方参演兵力超过1万人,演习科目主要为“反导”“防核”和“反潜”。这在相当程度上更是日本核潜力威慑战略的对外公开宣扬。 值得指出的是,在拥有巨大核开发潜力的条件下,尽管日本国内不断涌现有关“核武装”的争论,但制约日本进行核武装的外部因素依然存在。其中,日美同盟是影响日本核政策走向的基本因素,是规范日本核潜力威慑战略未来如何嬗变的重要框架。三、日美同盟与核潜力威慑战略的嬗变框架解密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文件表明,1957年9月24—28日,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曾在日本国内进行了名为“富士”的联合图上演习,演习中假定使用核武器。美军参联会在演习后指出“美国希望日本自卫队引进合适的核武器,自卫队必须配备的常规武器及核武器”。该结果被定为机密并传达给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美军曾提议日本自卫队配备核武器》,载《环球时报》2015年1月19日。同时,基于日美两国间的同盟密切关系,20世纪5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就向美国提出核能合作要求,试图通过钚的循环利用解决日本能源缺乏的尴尬局面。美国则试图通过向日本出口钚能源技术,既可以帮助日本发展民用核能,又可以在共产主义国家“门前”安放一种潜在的核威慑。在这项政策指引下,1955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题为《美国对日政策》的“5516号文件”,美日开始了核能项目的具体合作。在美国帮助下,1977年,日本在茨城县东海村个快中子反应堆开始运行。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其“无核三原则”政策是以日美同盟和美国的核保护伞为支撑的。日美同盟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同盟,其实质是日本把防御权和军事指挥权几乎全部交给了美国,换来美国保护日本的承诺。根据美国政府解密文件,美国首次向日本确认核保护伞是在1965年1月。当时,美国总统约翰逊对来访的佐藤首相表示:“日本不必拥有核武器。如果日本需要核遏制,美国将履行承诺提供给日本。”《日本向美要核保护伞》,载《环球时报》2007年3月22日。 然而,日本政府的“无核三原则”政策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却带有相当的模糊性与两面性。从日美同盟的视角看,一方面,防止核扩散是美国政府的基本对外政策,因此,同盟国日本“不制造”核武器是完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日本的安全保障是建立在日美安保体制之上的,其“无核三原则”(特别是“不运进”核武器的立场)必然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性。“这是因为美国在日本拥有的大量陆海空军基地随时都有可能带进核武器来”,“美国对日本的核保护伞与‘无核三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黄大慧:《论日本的无核化政策》,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161、162页。“无核三原则”提出后不久,1969年11月,佐藤首相访美并与尼克松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1972年归还冲绳,冲绳无核化,与本土同等对待”的归还原则。但佐藤首相访美前曾派京都产业大学教授若敬泉赴美,与美国方面起草了一个密约,规定美国经与日本政府协商,有权在紧急事态时把核武器重新运进和通过冲绳。11月21日,佐藤首相与尼克松总统签此密约。『朝日新聞』1999年1月11日。另据2005年解密的美国国务院文件记载,因宣布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与美国驻日大使会谈时居然说“无核三原则纯属胡说八道”。 林治波:《日本核欲望令人担忧》,载《环球时报》2006年11月17日。此后,在冷战期间,美军核动力航母曾多次停靠驻日美军基地。例如,1983年3月,携带核武器的美军核动力航母进入佐世保港口,遭到当地居民和反战反核团体的强烈抗议。另外,1986年9月,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参加“星球大战计划”研究,其国会论争关注的焦点就在于“星球大战计划是否包含核武器”。事实上,关于冷战期间日美双边关系中的“核密约”问题,2010年3月9日,日本外务省有识者委员会会长北冈伸一面见外务大臣冈田克也,并提交了日美密约调查报告书。报告显示,在1960年日美修改安全保障条约之际,确实签订过《美核舰艇停靠、经过日本港口密约》:美国核舰艇停靠、经过日本港口时无须事前协商,属于“默许”范围内的“广义密约”。报告还显示,关于冲绳归还后继续允许美核舰艇进入日本的密约问题。1969年11月,首相佐藤荣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确实交换过秘密讨论的文件《合意议事录》。 《日本政府证实“日美核密约”存在》,载《环球时报》2010年3月10日。冷战后,日本政府在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同时,依然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下选择了“依靠美国的核遏制力量”来确保国家安全的道路。其间,1995年日本政府决定赞成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日本国内的核武装论一度偃旗息鼓。此外,在1995年村山富市内阁执政期间,防卫厅曾经就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进行过内部探讨,并提交了报告书。该报告书认为日本一旦拥有核武器,“不仅降低美国核保护伞的可信赖性,而且很有可能被认为是(日本)对日美安保条约持有怀疑的表现”,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日本的“选择是依靠美国的核遏制力量”。此后,日本政府内部未再对该问题进行探讨。『朝日新聞』2003年2月20日。同时,美国政府也多次重申核保护伞并未失效,特别是在东亚,核保护伞依然是美国与日本维系盟约关系的基石。但进入21世纪后,在朝鲜核危机加剧的背景下,2005年10月,日本政府正式对外宣布,将允许美军核动力航母常驻日本横须贺基地。目前,由于美军常驻横须贺基地的常规动力航母“小鹰”号的舰龄已超过40年,美军计划让其在2008年或2009年退出现役,并用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接替“小鹰”号。显然,美军核动力航母进驻日本将涉嫌违反日本的“无核三原则”。在2006年10月朝鲜宣布进行了核试验之后,对于日本国内的“核争论”,美国国务卿赖斯明确表示美国不希望日本成为拥核国家,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对外界多次表示日本将坚持“无核三原则”,并与美国一起加快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这表明美国政府至少在现阶段并不赞成日本独自开发(或是“制造”)核武器,一个具有危险性的核伙伴(日本)也是违背美国国家利益的。特别是自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海啸触发核泄露危机以来,美国多次表达对日本使用核材料安全性的担忧。并且,美国国内对日本政府进行核开发的前景预期也存有一定的判断与担心。例如,2007年1月22日,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约翰·洛克菲勒称:“我了解日本人,我怀疑他们可能在五六年内获得一枚核弹,甚至可能更快。这是他们对中国和朝鲜总体局势的反应。” 《日本6年内可能拥有核弹》,载《环球时报》2007年1月25日。美国国内主张日本发展核武器者也不乏其人。例如,2006年11月,美国学者哈罗兰就载文称,日本如果发展核武器,能选择的核武器便是在离日本遥远的海域,通过核潜艇发射核导弹,这不仅难以被对手的声呐所捕捉,还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发射。 《美学者:日本应选择核潜艇》,载《环球时报》2006年12月1日。同时,日本国内也存有各种判断与主张。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日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拥有核武器是不成立的。如果不光朝鲜连韩国都拥有了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失效、美国的核保护伞也由于某种原因其信赖性大打折扣,那时,情形也许会发生变化。” \\[日\\]北冈伸一:《日本应对“朝核”的五个选项》,载《环球时报》2006年12月1日。有的学者主张,仰仗美国核保护伞的“英国型”核战略是日本有望实施和效仿的,为此日本必须成为美国值得信赖的同盟国,必须担负起美国核战略的一部分义务。『世界週報』2007年1月16日。此外,2006年11月16日,日本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公然提出:“核武器紧贴着日本航行的行动不属于引进核武器”;17日,他又表示可以允许美国搭载核武器的战略核潜艇在日本近海航行,近海的活动范围为沿岸3海里以外、12海里以内的区域。 《日暗中找核武突破口》,载《环球时报》2006年11月20日。显然,上述讲话是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原则的修正,偏离了日本政府不允许搭载核武器的外国舰艇在日本港口停泊、也不允许其在日本领海航行的传统立场,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美军装备的14艘战略核潜艇分别部署在大西洋沿岸的金斯湾潜艇基地和太平洋沿岸的班戈潜艇基地,配有“三叉戟”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具备远距离精确打击能力,故从军事作战的角度讲并不需要抵近发射。另外,尽管钚元素危险且难于控制,又容易落入恐怖分子和急欲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之手,但美国政府却在钚能利用上对日本采取“放任”态度。至20世纪80年代,全球只剩下英、法、日三国在发展钚能产业,形成了美国提供核废料、英法提供纯工厂、日本提供金钱的畸形产业链。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2014 年3月24日晚,日美两国政府发表一份声明,决定将美国提供给日本的高浓缩铀和分离钚,全部返还给美国。但是,4月11日日本内阁批准了生产钚的乏燃料回收项目,再度开始推进生产并储备钚的计划。在可预见的短期内,日本政府独自开发核武器、将“核潜力”转化为“核力量”的可能性并不大。除受日本国民反核意识强烈、人口密集且国土狭小、国际社会反核扩散声音高涨等因素的限制外,只要美国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下一直承诺向日本提供有效的核保护,日本政府很难悍然走上独自开发核武器的道路。因为日本一旦进行核武装,将会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甚至诱发这一地区的核竞赛,这完全违背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对美国防止核扩散的努力也将产生负面作用。中国学者认为:“防止全球范围内出现挑战对手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美国不希望作为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成为军事大国,更不会容忍其成为核大国”,日本进行核武装“会给对日本来说重要的双边关系即日美关系带来巨大甚至致命打击”。 胡继平:《日本核武装?》,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9期,第43页。无论如何,日本进行核武器开发的前景预期必将与日美同盟的未来演变密切相关。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政府采取核潜力威慑战略,除有利于同盟的维系以外,其益处在于:可向日本的所谓“假想敌”表明其拥有核武器开发技术潜力,从而震慑对方避免与日本及其盟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有利于继续保持日本的和平形象,稳定与邻国的正常经贸关系,进而有利于日本实现大国目标。但从目前日美同盟的强化实践中看,在美国政府将日本视为“自由与民主”的盟友国家的情况下,特别是由于不断受到朝鲜“核威胁”的刺激,美国在日本列岛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并非丝毫不存在。因此,“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有可能首先受到日美同盟强化的损害。第三节日美同盟与“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嬗变一、日美同盟与“武器出口三原则”的例外1967年,日本国会对于东京大学开发的小型导弹(高空气象观测用)出口至印尼等国是否违宪这一问题展开了政策争论。在此背景下,1967年4月21日,首相佐藤荣作在众议院决算委员会宣布了日本出口武器的具体方针,即所谓的“武器出口三原则”:1不向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出售武器;2不向联合国决议明文禁止出口武器的国家出口武器;3不向国际争端的当事者或有这类危险的国家出口武器。此后,1976年2月27日,针对日本国会中关于川崎重工公司制造的C1运输机出口至海外后是否被当作军用飞机的争论,首相三木武夫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又表明了“政府统一见解”:禁止向“武器出口三原则”中所规定的三类对象地区出口武器;对于上述三类地区以外的国家,根据宪法及外汇管理法、出口贸易管理法的精神,在出口武器问题上也要慎重对待;对于武器制造相关设备的出口,参照“武器”的标准执行。在此基础上,1981年3月20日—21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有关武器出口等问题的决议》,指出“根据‘武器出口三原则’及1976年政府统一方针,……政府应以严肃且慎重的态度对待武器出口,同时采取包括改善制度在内的有效措施”。『防衛ハンドブック』、朝雲新聞社2003年版、第746頁。然而,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出于分担盟友责任的现实需求,日本政府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却不断受到蚕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美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基本上仅限于美国单方面向日本提供技术。但随着日本科学技术的进步,美国对这种状况日益不满,并于1981年6月和1982年3月先后两次提出,要求日本向美国提供可用于军事领域的通用技术。1982年底中曾根康弘内阁执政后,日美双方进行了多次协商,于1983年11月8日完成了有关对美提供武器技术的换文。该换文决定将美国作为“武器出口三原则”的一个例外,向其提供武器技术及其试制品,但不出口武器及进行共同生产。1984年1月,中曾根内阁以官房长官谈话的形式宣布,根据日美两国有关防卫领域开展技术交流的协议,日本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不违反“武器出口三原则”。结果,1986年9月5日,日本决定向美国提供携带式地对空导弹(SAM)相关技术以及海军舰艇武器制造技术;同年12月30日,日本又决定向美国提供海军舰艇武器改装技术。1987年日美两国政府又共同签署合作开发新一代战机的协议,即“以美军现役F-15战机、F-16战机为基础,集合日美秀技术,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机”。 张玉来:《战后日本军工产业发展与“美国因素”》,载《日本侵华史研究》2013年第2卷,第45页。翌年双方就开发计划框架签署了备忘录,确定以三菱重工为总包企业,美国通用动力(后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川崎重工以及富士重工为配套企业的开发模式,至1995年10月该项目开发的F2战机正式下线。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出口至美国的半导体芯片和摄像机镜头等,也有许多被用于导弹及侦察系统。冷战后,随着日美同盟的强化,日本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的力度明显加大,对美国而言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已经名存实亡。从1990—2002年期间,日本决定向美国提供的武器技术范围广泛,详情参见表1-3所示:
表1-3冷战后日本决定向美国提供的武器技术(1990—2002)
项目名称决定时间下一代支援战斗机(FS-X)的相关技术1990年2月20日P-3C搭载用数字飞行控制系统的相关技术1992年4月17日涵道式火箭发动机共同研究的相关技术1992年10月23日先进钢技术共同研究的相关技术1995年10月30日支援战斗机(F-2)系统生产的相关技术1996年7月29日ACESⅡ弹射椅共同改装的相关技术1998年4月10日先进混合推进技术共同研究的相关技术1998年6月10日弹道导弹防卫共同技术研究的相关技术1999年8月20日野战炮用高安全性发射药共同研究的相关技术2000年4月5日海上巡逻机(P-X)及海上多用途飞机(MMA)的电子航空装置与指挥系统的共同研究的相关技术2002年4月5日在日本政府不断向美国提供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