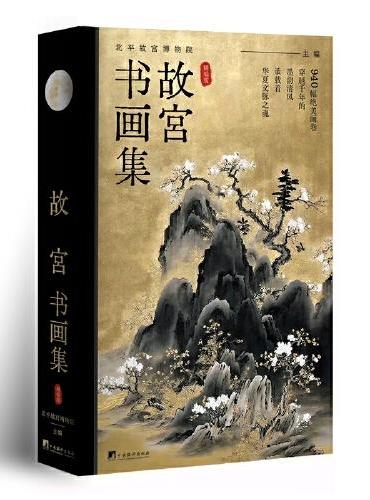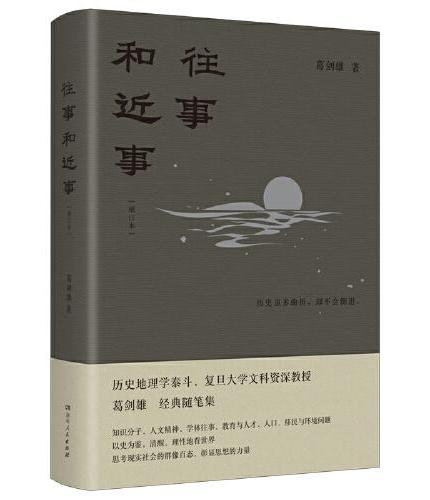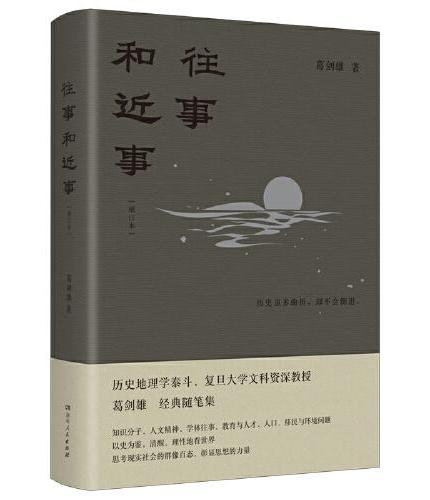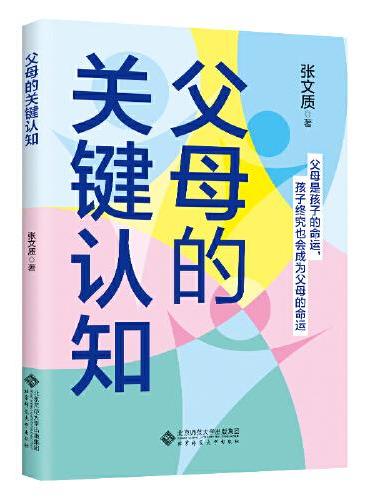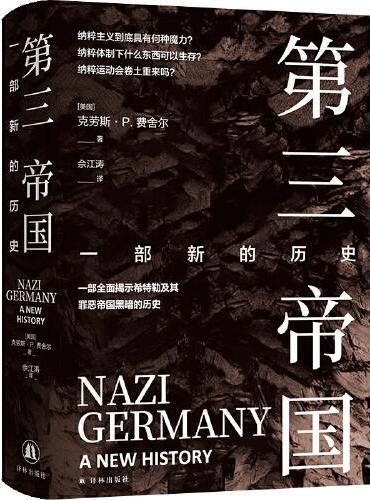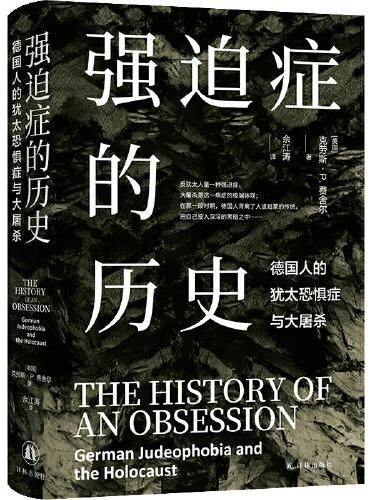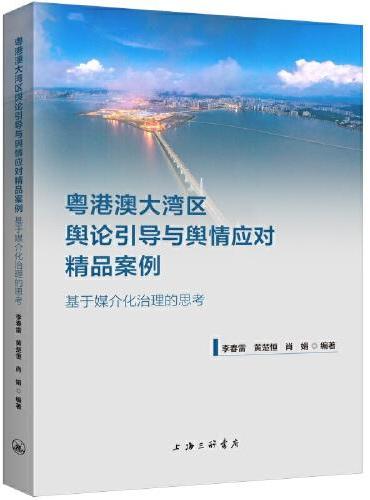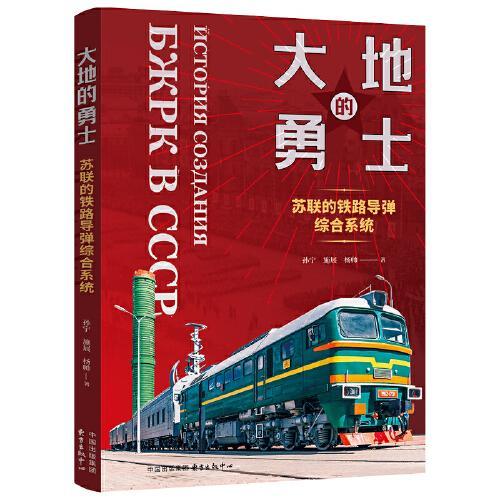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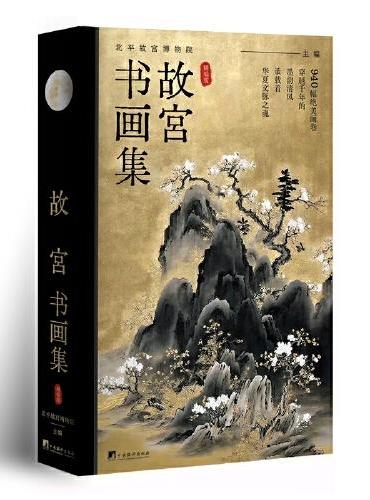
《
故宫书画集(精编盒装)版传统文化收藏鉴赏艺术书法人物花鸟扇面雕刻探秘故宫书画简体中文注释解析
》
售價:NT$
1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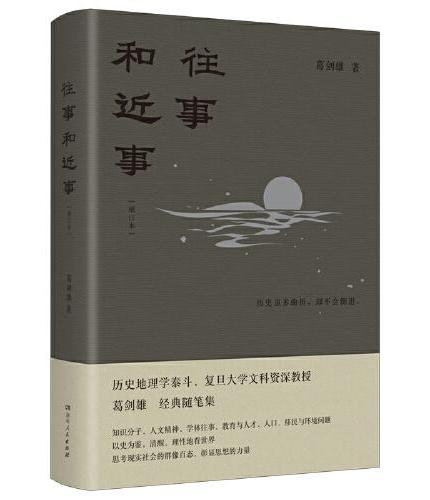
《
《往事和近事(增订本)》(著名学者葛剑雄教授代表作,新增修订、全新推出。跨越三十多年的写作,多角度讲述中华文明)
》
售價:NT$
3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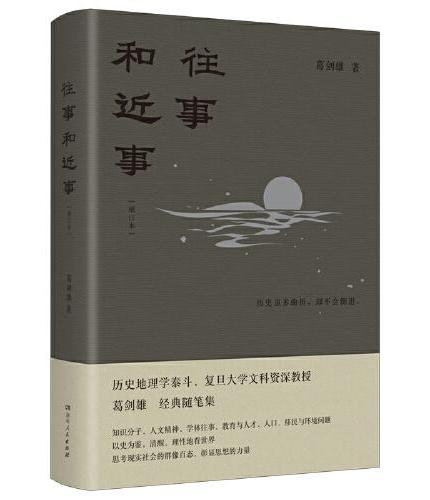
《
往事和近事:历史地理学泰斗、百家讲坛主讲葛剑雄经典文集
》
售價:NT$
3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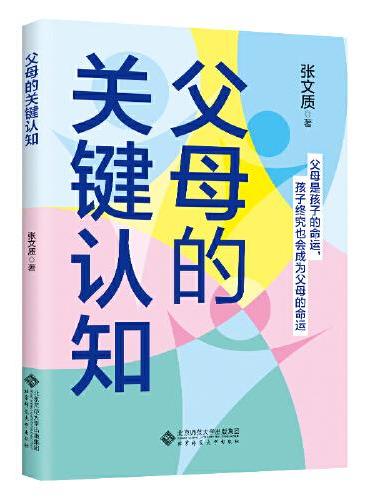
《
父母的关键认知
》
售價:NT$
2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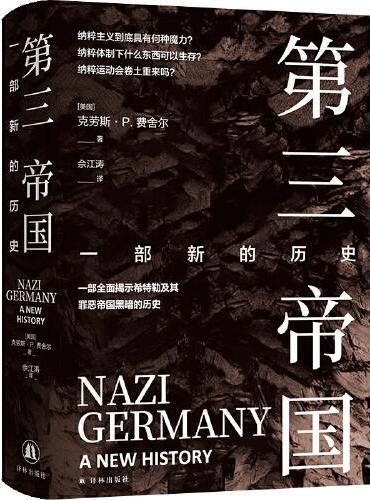
《
第三帝国:一部新的历史(纳粹主义具有何种魔力?纳粹运动会卷土重来吗?一部全面揭示希特勒及其罪恶帝国黑暗的历史)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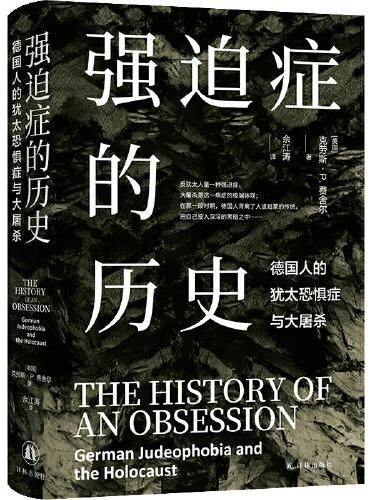
《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德国历史上的反犹文化源自哪里?如何演化为战争对犹太人灭绝性的种族杀戮?德国历史研究专家克劳斯·费舍尔叙述德国反犹史及其极端形态的典范之作)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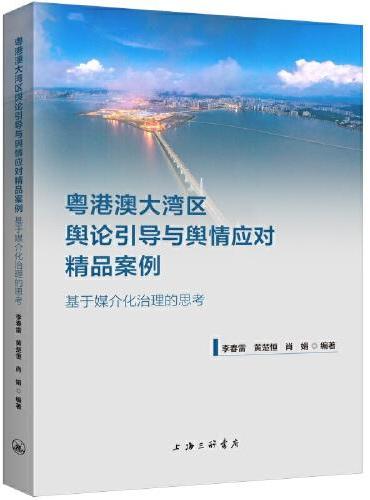
《
粤港澳大湾区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精品案例:基于媒介化治理的思考
》
售價:NT$
4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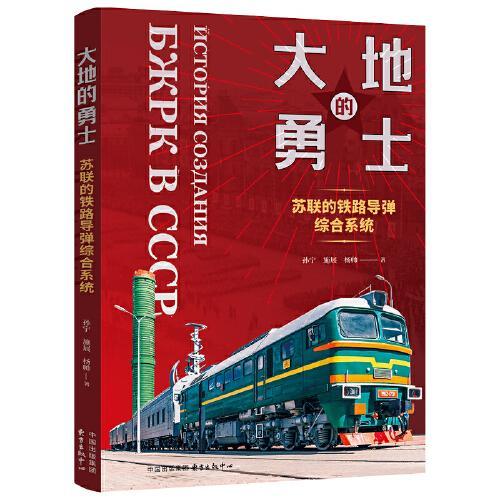
《
大地的勇士
》
售價:NT$
340.0
|
| 編輯推薦: |
融先锋文学和社会小说于一身,14个精彩故事诉尽荒诞怪异的人生百态
外星人迫降地球,燃料竟是从猫粪中提取;那个婴儿甫一出生便霸占了我仅有的一位交谈对象;宾利被砸案引发邻居热议,结果却无法用常理解释……
赵刚对“新小说”痴迷超过三十年,始终在小说中呈现生活的怪异荒诞,本质上是在孤独中向往舒适的生活。
|
| 內容簡介: |
|
13篇中短篇小说,各具特色,带有明显的赵氏风格。《一个人或三十岁》独语般的、自我陈述式的追忆了一个青年作家从17岁开始写作到30岁的突转的心路历程,道出现代人在三十而立这个词语面前的局促;《女贼》围绕我和妻子以及表妹卫离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轨道展开叙述,在对卫离青春荒诞的生活旁观的同时,目睹了卫离的偷窃行为,折射了偷窃者心理的病灶;《卖鬼记》则颇具奇幻色彩,在父亲的行商生涯里,“鬼”是一个带着隐喻性的词汇,跟着父亲卖鬼,从一个14岁少年的视角旁观着一个成年人的内心世界……
|
| 關於作者: |
|
赵刚,写作者、电影导演,主要从事中国新小说、艺术电影的探索与创作。
|
| 目錄:
|
一个人或30岁1
女贼19
卖鬼记59
怯了85
外星人和自行车99
赵刚,祝你玩得愉快!121
窗户157
我朋友171
魔方193
K煮出姓名的大米或熊猫的饲养249
时间追击297
迷路313
你以后就不求人了?349
抄近路369
|
| 內容試閱:
|
一个人或30岁
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就画一辆汽车和一条公路,公路的一头从我的门前开始,另一头将到大街为止——无论它在那里——哪怕在英国。我开着画出来的汽车沿着画出来的公路飞驰而去,在路上我还要画出翻动的风景和变化的人们,让他们随着时间衰老,让他们在不停地生长和晃动中结婚生育死于肺病。
一切都像早已策划好的,甚至天气的变化也在预料之内。结局在开始之时便已被爱情注定,被想象中的大街注定。再过两天我就到30岁了,一个人到了这份上的确该为自己今后的生活准备准备了。在这之前我根本想不到这么远,就在上星期我还觉得自己年轻得跟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似的充满了生气和一切意外的可能,可是一个星期之后我突然一下就老了。一个人和30岁,真不敢想象这么一个巨大的数字现在竟然摊在了我的头上。我是1965年出生的,17岁时意外地发表了平生的篇小说,从此便有机会结识了一帮同是写小说的朋友。我们这些朋友中的年龄分为三个档次,20岁以下是一个年龄档,其中以我为代表,17岁。顶呱呱的数字,顶呱呱的年龄,现在想起来仿佛就是昨天;面容苍白表情稚嫩,嘴唇上刚长出一层细细的绒毛,对所谓的生活充满了奇异的想象和渴望,经常因为突然的灵感从床上跳起来,刷刷地写出十来页的文字,然后趿拉着拖鞋从家里跑出来,穿过黑夜和灯光的大街,绕过那些在微风中装腔作势的树梢,径直地来到你的窗户前砰砰地敲响你的梦境,使你在一阵欢天喜地的锣鼓和鞭炮声中失去貌美如花的新娘,也从此失去了那一面砰砰作响的窗户和玻璃——那是一面会做梦的玻璃,它冰凉之处在于透明或者透澈。当然这是玻璃不是小说,我也不在这上面多作文章了,还是继续年龄的话题吧。中间档次的人比较多,他们当时的年龄一般都在二十五六岁上下,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相对于17岁而言,二十五六岁更是一个金光灿灿的时期;男人器宇轩昂女人风情万种,相互间充满了恋爱的愿望。这一点尤其让17岁的人着急。后一档的朋友是30以上年龄层的人,有个把个已经三十五六岁了。根据我当时的认识,他们和那些四十五六岁的中年人已经没有了什么区别,而四五十岁与那些五六十岁和七八十岁的人也没有多少差别,依此推算三四十岁的人跟那些躺在坟墓里瞧着活人说风凉话的死人相比也就没有多少差别了。按照我们当时的普遍看法,这一年龄层的男人大多是平庸之辈,与我们这两个年龄档的人相比,他们普遍地缺钱、缺勇气也缺乏才情;在外面吃饭他们从不主动掏钱,遇到打架他们先是拼命地劝阻,劝阻不了就闪身避开,把危险一股脑儿地留给了17岁、二十五六岁的男人和女人们。大家想想,这种事是17岁和二十五六岁的年龄的人能干得出来的吗?至于才情他们更是不值一提。尽管他们也写小说,但是堆砌起来的文字尽是一些男欢女爱的色情描写,或者是貌似高深玄虚之谈且自我感觉无来由地良好,号称由于他们的出现,中国文学得诺贝尔奖已经只剩下时间问题了。他们趾高气扬神气活现地在文坛上走来走去指手画脚,却不知在别人的眼中则是皇帝的新装一般滑稽可笑;自己的屁股都露在外面了还浑然不觉地得意扬扬,换上二十五六岁或者17岁的人谁会没事当众亮出自己的那玩意呀!即使瑞典许诺要把诺贝尔奖的奖金发给我们,那也得找一个恰当的时间和场所——时间好是在颁奖前的二三分钟,地点应该是在斯德哥尔摩,等到了那时候再亮出闪烁的那一玩意吧,然后再让那些文艺评论家们针对它的光洁度和硬度品头论足一番。我在17岁时便对30这一数字充满了恨意和恐惧,那时候我常跟要好的朋友们说,我只要一活到30岁就死,就算别人不杀我我也得自杀,绝不丢人现眼死乞白赖地厚着脸皮往下活了。从17岁到30岁就像无意之中踩到一块被水浸透的湿肥皂,自己还没做好准备,便吱溜一声滑进岁月的圈套中去了。于是30岁就到来了。不知是为了证实我17岁时的誓言还是另有其他目的,30岁从时间的沼泽中刚一露出丑陋的脑袋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它的这一股恨意首先使我的头发里生出了无数根闪亮的白发,脸上隐隐地现出了数条皱纹的痕迹,紧接着皮肤也失去了光泽和弹性,记忆力衰退,视力模糊,一种难以名状的对未来生活的忧虑使我变得易怒、脆弱、敏感、多疑、尖刻、胆怯,而所有的这些情绪与我已经拥有的生活内容是多么的不协调。我在25岁那年与一位多年的朋友结了婚。她在我17岁时就已经25岁了,当时她是我们这些朋友中较受男人青睐的一个女人,她仗着自己的青春美貌和来自男人的一份无端的青睐在我们之中挑挑拣拣。只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魅力或者说过分轻信了男人们的那些海枯石烂心不变的鬼话,后一转脸稍有点内容的男人不是被别的女的骗走了就是骗上了别的女的,迅速地失去了踪迹。她这时候慌神了。正巧经过食物和营养的补给,我终于一路顺风顺理成章地在此时此刻成长到了25岁,从一个面容稚嫩的纯情少年摇身一变而成了一名标准的男人。于是左顾右盼遍寻情郎不得的她就把我当作了后一个操练技术的对象。我当然不是她的对手,一个回合还没战完便心甘情愿地被她领入了漆黑的爱情中去,晕晕乎乎地和她结了婚。结婚一年之后我们有了一个孩子——一个非常漂亮的“布娃娃”,本来我不想这么快要孩子的,但是亘却执意想要,她说自己的年龄已经很大了,再不抓紧时间这辈子也许都不可能生孩子了。话说到这份上我也不好再坚持了,任由她去医院生出了一个孩子——我们漂亮的女儿。从此以后城市上空便多出了一声啼哭,今后的世界上多出一个女人,学校里多了一个女学生,工厂里多了一名女工(或者女干部),奥运赛场上多了一名为国争光的女子中长跑运动员(当然也可能是女子撑竿跳高、女子跳远、女子国际象棋、女子乒乓球、女子羽毛球、女子网球、女子篮球、女子排球、女饲养员、乡村女教师、商界女强人、政坛铁娘子等等)。确切地说,时间是在这时候突然地加快了步伐,某些已经习惯的生活内容和节奏因此而改变并朝着与当初愿望相反的方向流动而去。我首先遭遇到的是写作上的难题。自从这个名叫花朵的女儿一出世,我的写作再也无法进行下去了,灵感被封闭,激情被中断,只要一摊开稿纸提起笔,脑子里首先出现的就是一些诸如奶瓶、奶嘴儿、尿布、啼哭等字眼,有时候那个孩子还会出现在我的稿纸上面,在格子与格子之间行走,或者提起一条腿用另一条腿在稿纸间跳来跳去,玩一玩跳房子的游戏。反正自从世界上多了一个孩子之后,我就被一些忙也忙不完的生活琐事完全地缠住了,买菜烧饭取牛奶洗尿布哄孩子。这么说吧,自从有了一个孩子之后,我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无论小说或者别的什么,哪怕是一份情书。更为可怕的是后来我竟然也习惯了这样一种没有文字的生活,偶尔空闲时心中隐隐会感觉少了一点什么,但是一觉睡过去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日子飞快流逝,一晃五年过去了,在这五年中我们吃饭睡觉极其规范地生活着,我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注视上面,集中在我那可爱的布娃娃一样的女儿身上,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或者说被我遗忘在五年前的时间里了。身边的孩子在注视中一天天地变化和长大,有一天我从床上醒过来时意外地看见了枕头旁边有一枝鲜艳的玫瑰花。亘将鲜花放在我的床头轻轻地说了一句,30岁快乐!我微微一愣,心中一下子就乱了。我30岁了?难道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30岁了?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这时突然拐了一个弯,将毫无防备的我甩出了正常的生活轨迹。在抵达地面之前我长久地飘浮在空气中,所有的想法都显得空虚和空洞,整个人轻飘飘的像一根羽毛。下午亘拽着我和孩子出了门,她说晚上要请我吃饭,祝贺生日。今天是星期天,大街上的人非常多,在经过一家新华书店的门口时,我们看见一个作家在签名售书。等待签名的读者队伍排得很长,队伍中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近乎上帝的神情。那个签名的作家忙得不亦乐乎,一本接一本地为他们签名。亘拽了我一下指着那个埋头签名的作家说,那不是王积吗?我一看还真是,不假思索地张嘴叫了他一声,王积!王积抬起头看着我们好一会儿才认出来,他从座位上跑过来说,哎呀!怎么是你们俩?所有的读者都把视线集中到了我们身上,让我有点不自在。和王积聊了两句后我说,你先忙吧,我们以后再找机会聊。王积给我留了他的电话号码,末了还送了我们三本书,连我的女儿也单独得了一本。他说,过两天约个时间我们好好聊聊。王积曾经是我们朋友圈子中的一员,他大我八岁,在朋友圈子里他是不自信的一个人,刚开始时他迷信所有发过作品的人,无论自己写出什么新作品都要先拿给他们看,态度虔诚至极,连当时只有17岁的我他也没有放过。后来因为我发表的机会增多,再加上大伙对30岁以上的那一帮人的普遍反感,终使得他将所有的信任全部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在当时他是一个能满足我虚荣心的客体,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许多年以后的今天我要为当初的虚荣付出代价。离开王积之后,我的妻子亘首先承受不住了。在接下去的走动中,我们老半天没说话,连女儿也被这一份来历不明的沉默压抑住了好动的天性,抱着书一声不吭地跟在我们后面,不时还饶有兴致地翻上两页。她不过五岁多一点,还没识字。我实在忍受不住这种沉默,为了调节气氛就对女儿说,来把书给妈妈,让妈妈给你拿着。女儿却把书往怀里深深地一抱说,不,我要自己拿!这是那个叔叔送给我的。这副神情不知怎么就把妻子激怒了。她毫无预兆地发起火来,飞快地伸出手一把将书从女儿的怀抱中抽出来,连同自己手中的那本书,重重地扔在了地上,吧哒一声。孩子被吓得哇地大哭起来,我也愣住了,不知她为什么要这样。孩子还在嚎哭着,一张小嘴咧得大大的,以此表达着自己的无辜和委屈。我捡起那两本书,问亘你这是干什么?看把孩子吓的!亘愤愤地说,没什么,我就是看不惯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我说究竟怎么了?谁得罪你了?亘就火了,说,你是瞎子呀!难道你没看见?我说,什么呀?我看见什么了?亘定定地看着我,看着看着就哇地一声,双手掩面痛哭出来。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当时我们是在人如潮车如流的大街上,女儿和亘这么一闹就把整个大街的注意力全吸引过来了,许多人围在一边像看西洋景似的。我看不是事,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一大一小两个嚎哭着的人弄上了车。一辆出租车载着两个人尖锐的哭声向前奔驰,大街有多长哭声就有多长。到家时女儿已经在我的怀中睡着了,胖嘟嘟的腮帮子上还挂着两颗硕大的泪滴;亘这时的哭泣已经渐入尾声,她哭累了。进了家门后往沙发上一坐就怔怔地犯起傻来。我先把孩子放到床上,给她盖好被子安顿她睡下,回身坐到沙发上伸手搂住亘的肩膀问,今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