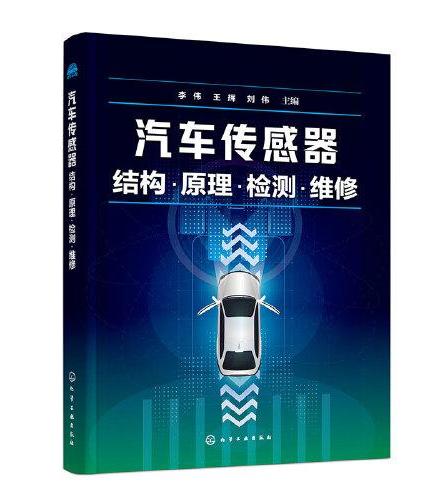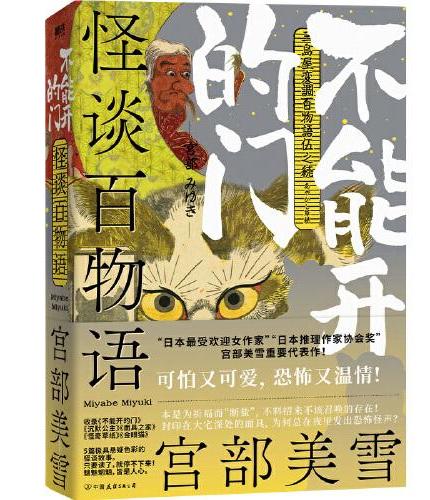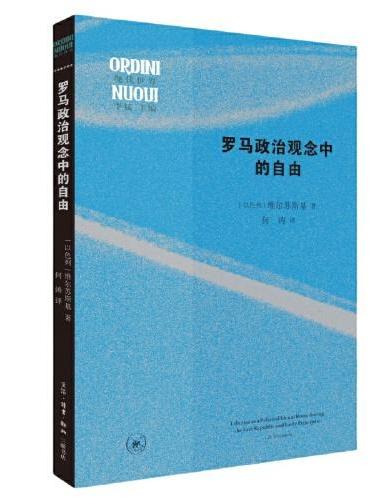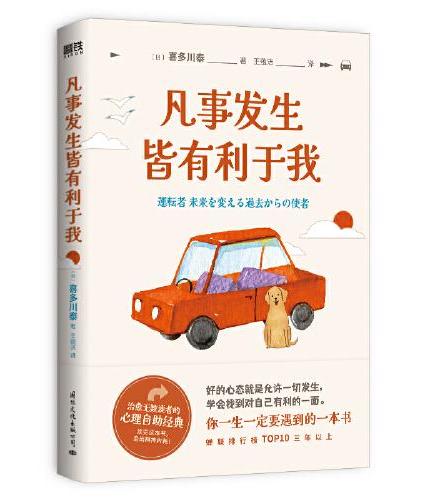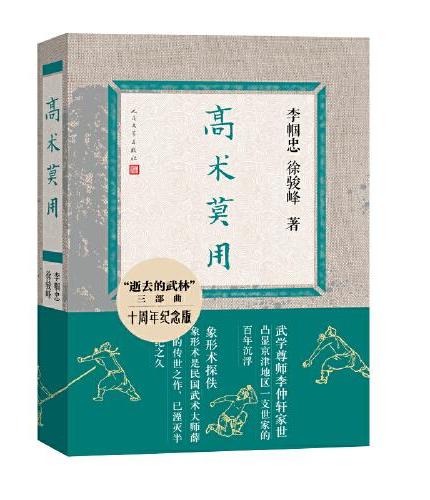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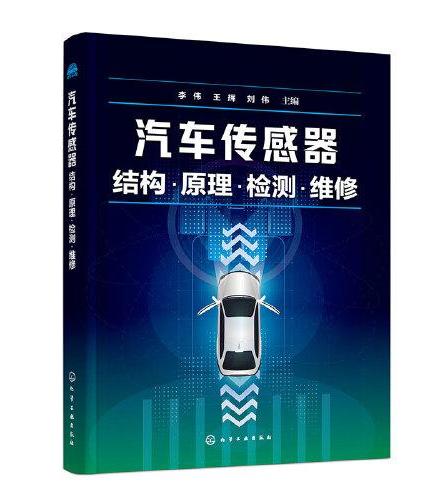
《
汽车传感器结构·原理·检测·维修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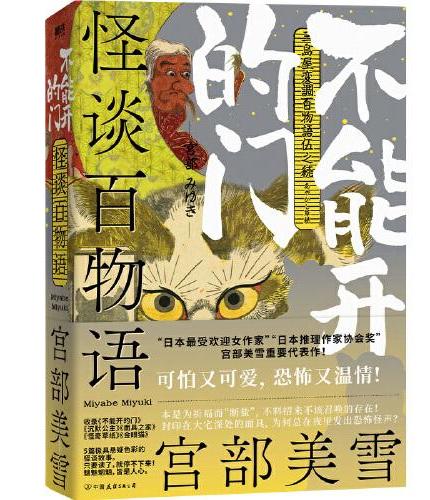
《
怪谈百物语:不能开的门(“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宫部美雪重要代表作!日本妖怪物语集大成之作,系列累销突破200万册!)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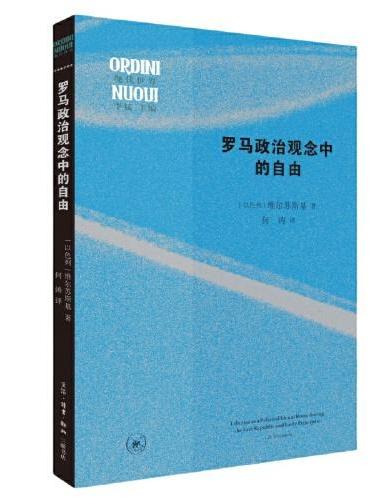
《
罗马政治观念中的自由
》
售價:NT$
230.0

《
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宠位厮杀
》
售價:NT$
2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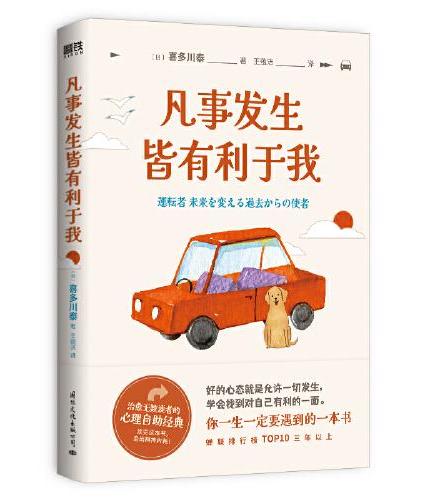
《
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这是一本读了之后会让人运气变好的书”治愈无数读者的心理自助经典)
》
售價:NT$
203.0

《
未来特工局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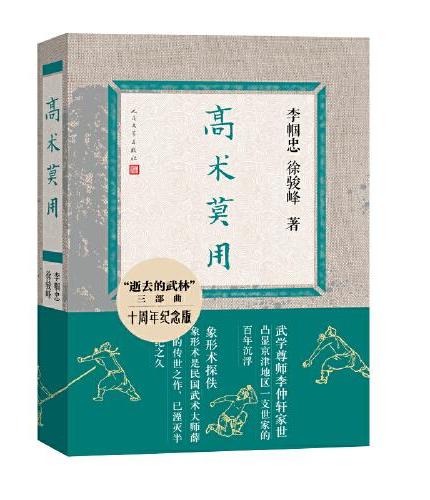
《
高术莫用(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续篇 薛颠传世之作 武学尊师李仲轩家世 凸显京津地区一支世家的百年沉浮)
》
售價:NT$
250.0

《
英国简史(刘金源教授作品)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史学大师吴晗推荐的经典
历史的车头轰轰隆隆地向着民主化、现代化的前途猛进,这是谁也违拗不了的前进的主潮
一本书透彻剖析秦以来两千年的中国历史
从历史来说明现实,也从现实去明白历史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从皇权、官僚、军队、农民等角度,叙述了自秦朝到清末两千年间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发展到崩溃的历史,剖析了专制社会的根本矛盾和必然灭亡的命运。指出历史的车头轰轰隆隆地前进,把旧的时代撇在后面,产生了新的事物,出现了新的情势,提出了新的问题,向着民主化、现代化的前途猛进,这是谁也违拗不了的前进的主潮,读来催人奋进。
|
| 關於作者: |
|
胡绳(1918-2000),出生于江苏苏州,原名项志逖,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等职务。著作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主编)、《二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结集为《胡绳全书》,深有影响。尤其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发行三四百万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经典之作。
|
| 目錄:
|
导言
章 二千年的鸟瞰
一、纵剖面和横剖面
二、时间之流
三、速写一个轮廓
第二章 在“万人之上”的人
一、专制皇帝的产生
二、皇帝是“天生的圣人”么
三、帝位的世袭和换朝易代
四、在皇族内部的纠纷
第三章 一种特殊职业——做官
一、 “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
二、君主专制和官僚制度
三、官僚是怎样产生的
四、官僚的膨胀
五、 “国家之败,由于官邪”
第四章 又一种特殊职业——当兵
一、从车战到骑战步战
二、当兵变成了专门职业
三、募兵·拉丁·世袭兵
四、军权的集中和分散
五、 “养兵千日”
第五章 一切寄托在土地上
一、个体劳动的小农经济
二、谁是土地的主人
三、农民出谷出钱又出力
四、千灾百难下的农民生活
第六章 大地下的撼动
一、农民创造了奇迹
二、奇迹是如何造成的
三、走向城市的失败
四、农民战争的意义
第七章 不安静的北方边塞
一、塞外各族的兴替
二、冲突的原因
三、羁縻控制的失败
四、民族的苦难
第八章 当胡骑踏进中原的时候
一、 “儿皇帝”和“贰臣”
二、英雄如何产生
三、 “南渡君臣轻社稷”
四、不死的人民力量
第九章 逃不了的灭亡命运
一、失败的“变法运动”
二、没有救自己的能力
三、在不变中坐候末日
四、历史不会回头
附录 读《二千年间》(吴晗)
|
| 內容試閱:
|
导言
《二千年间》这本书是在1944—1945年间陆续写成的。当时我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的编辑部工作,我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公开出版的的一种报纸。设在重庆郊外的化龙桥的报社周围经常有国民党的特务驻守,报馆工作人员进城出城常有特务追随,所以可以说是在紧张的状态中。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停止工作和学习。只是在那种条件下我不可能全得到任何想读的书。我尽量利用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著作,并且做了很多笔记。《二千年间》的各篇文章就是整理这些笔记而写成的。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二三年间,叶圣陶先生在成都主持由上海移来的开明书店的编辑部,并且主编早在30年代初已在上海创刊、在教育界和学生中素负盛誉的《中学生》杂志。我在抗日战争前已认识圣陶先生,他是我所尊敬的前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大后方,但不在重庆。在他有事到重庆时我也曾拜见过他。在我写出这些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文章后,寄给在成都的圣陶先生,他很高兴地把这些文章发表在《中学生》上。大约每一个月我就寄一篇给他。在圣陶先生逝世后出版的《叶圣陶集》的第20卷中提到这些文章。那一卷收录了圣陶先生在1944年到1945年的日记,其中有他陆续收到这些文章的记载。
在这些文章刊载完毕以后不久,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回到上海复业的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这本书。当我把这些文章编辑成书的时候,就给了它《二千年间》这个书名。由于在当时情况下我在《新华日报》用的名字出现在《中学生》杂志上是不适宜的,所以改用了“蒲韧”这个笔名。在上海出书时也用这个笔名。
我的这些文章本来是自己学习历史的笔记,并没有想借此对现实有所讽喻,但写文章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六七年,而国内政治仍然使人焦虑,由这些客观形势引起的感触不可能不流露到笔端上来。中国的历史上经常有塞外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事。这些历史旧事和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完全不同。但就历史上胡骑踏进中原引起的种种反响来说,也确有某些和现实相似的地方。写这些文章时对相同相似之处不免注意较多,而且因为是讲过去的历史,对于当前的帝国主义侵略与前代事情相异,当然就不可能说到了。在1946年开明书店编辑部的先生们处理这本书稿时,把书中有几处说到当前正是抗日战争的话改成了已在抗日战争后的语气,现在我又改回去了。这毕竟是留着抗日战争时期的印痕的书。
也许因为这本书的写作体例可说是别创一格,所以它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年代里出版还颇受到读书界的注意。记得在1946年吴晗同志从大后方到北京路过上海时,曾写了一篇篇幅比较长的文章评论和介绍这本书,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但可惜现在我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了。
这本书出版后三年多全国解放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两三年间,因为学校里没有适当的历史教科书,有些地方的中学曾用《二千年间》这本书当作新的教本代替以前暂用的教科书。显然这本书是不适合这个用途的。我想那时曾用过这本书的老师们是很吃力的。以后虽然有的出版社建议把这本书作为普通读物出版,但没有得到作者本人同意,也就没有再出版过。在这次《胡绳全书》重印以前的例外是1994年上海书店刊印的《民国丛书》。这套丛书编辑的用意是把被认为还值得保留的民国时代出版的书重印若干以免流失。我的三本书被收入在内,《二千年间》就是三本书中的一本。
第三章 一种特殊职业——做官
一、 “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知道一个有趣味的故事。
范进到了50岁时才考中了举人,一接到消息时就欢喜得发了疯。当时有人说要有个他平日害怕的人来吓醒,于是请了他的丈人胡屠户来。胡屠户却道: “虽是我的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但禁不住旁人的敦促,他果然去做了。你看:胡屠户凶神般走到(范进)跟前,说道: “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将去……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第二下。范进因这一个嘴巴……不疯了……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这个故事真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于官的看法。范进家里本来是三餐饭都不周全的,但是一中了举就算踏进做官的门,就是“老爷”,就能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尊荣的地位了。无怪乎像胡屠户这样的人以为中举做老爷的都是天上文曲星下凡了。
人们对于官抱着这种敬而畏之的看法,正因为在实际上官享有超于常人以上的特权地位。
固然,在君主时代,做官的人也有很多本来是穷家子弟,像《儒林外史》中范进那样的人。有人根据这一点就说,那时是人人都有做官的机会,政权开放给全体人民,所以这种政治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这种看法其实完全不对。因为要做官必须读书能文,而在当时的经济条件的限制下,受教育决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的权利,对必须靠自己劳动来生活的穷人子弟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当时对做官的人,在其出生的家族的身份上仍有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限制。所以真正出生于较低级的社会层而能做官的人,究竟只是例外的少数。大多数的官都是从地主士绅家庭中出来的。纵然是由较贫寒的人家出身,一做了官,在政治上也决不能代表他所从出身的社会层了。因为他之所以能做官,不是由自己所出身的这一社会层的拥戴,而是由于在政治上的统治者的提拔。假如他不是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和统治者一致,他是永远不能做官的。所以只要他一旦取得做官的条件,他就已获得社会上特殊的身份,远远地而且永远地离开了原来所属的较卑微的社会层了。像《儒林外史》中的那位范进,一中了举,就有张乡绅来拜,送他银子和房产,而且“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托身奴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所以这时他虽然还没有官职,但已经有了田产,有了地位,可以结纳官府,交往士绅,取得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也被旁人看作特殊的人了。等到实际做了官时,那就更不待说了。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从旧社会中流传下来的这句谚语表明了当时官的特权地位。做地方官的人被称为“民之父母”,这也是表明官并不是人民中的一员,而是高出于人民以上的人。在一个县里,县官所说的话就是法律,他掌握着全县的行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使审判。他固然还要受上峰的节制,但在人民看来,他已经是一县中的小皇帝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官都只向他的上级负责,决不向人民负责。官还不仅在担任着官职的时候有着特权地位,而且到了卸任退休的时候,依然可以作为地方上的绅士而继续保持特殊的身份。
秦汉以后2000多年间,在君主专制政治下的官都是如此的。由这样的官来行使政治上的统治,我们可以特称之为官僚政治。
很显然的,这种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是不容混淆的。在民主政治下固然也有官,但和专制政治下的官,含义是不同的。在民主政治下,至少从法律上说,是不承认官有高出于常人的特殊权利和地位的,他不过是为公众服务的人;他不具有特殊的身份,当他不做官时,依旧要和平常人一样地从事某种职业的生活。就是说,民主政治下的一切官都应该是名实相符的公务员,而不是在专制政治下的官僚。但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前,自然是连民主政治的名义也从来没有过的,那时只能有官僚,而一般人民也不敢、也不能想到一个官应该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既不敢以为官应该只是人民中的一员,便只能设想官是从天上下凡的星宿了。
三、官僚是怎样产生的
世袭的贵族生来就是贵族,但官僚却是从非官僚中产生的。那么官僚是怎样产生的呢?
汉时有两种制度:一种叫做“察举”,又一种叫做“征辟”。 “察举”是由中央政府下诏规定所需要的人才的性质,要各地方政府在自己境内发现这种人才,推荐上去。至于各地方政府选拔人才给自己用,或者是中央政府直接从“布衣”或地方上卑微的官吏中征召有名望的人做大官,那便叫做“征辟”了。这两种制度固然都有打破世袭贵族独占做官权利的作用,但是为了中央集权的强化,这两种制度并不是好的方法。因为地方政府有权自行征辟属官,这显然是妨碍中央集权的;而由中央政府直接征辟,又很难提拔出多量的人才,事实也只是偶一为之,作为政府尊贤重士的标榜而已。至于察举制,也还是授权地方政府来选录人才,更难以避免地方上的豪族权门把持操纵的流弊。所以东汉时察举虽是经常定制,但已渐参用考试的办法;就是对地方察举而来的人才,中央还要加以考试,才决定是否给官做。魏晋时行所谓“九品中正法”来选拔官僚,其实就是类似于察举制的方法,但不是由地方政府来行使察举,而由地方人士推荐,其结果更是显著地为巨姓大族所操纵,以致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实际上又成为一种少数贵族独占做官权利的现象。
所以到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加强并建立了更集中的官僚政治时,就不能不探求更适当的方法使所需要的官僚能够不断地产生出来。于是科举考试制度便被采用了。
科举考试制是能满足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的。因为:,科举考试完全由中央政府来行使。中央政府通过科举考试,从全国各地选拔出做官的人才,再分发到各地去做官,这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集中。第二,实行了科举考试制,选拔官僚便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必须努力去适应这种标准,这无形中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并且,科举考试制看起来又好像是公平不过的制度,任何人只要有资格读书,就有资格应考,也就有可能做官。这既可以掩蔽官僚政治的实际,又可以使天下儒生除了汲汲于按照科举考试制的需要而埋头读书,不再生任何对君主统治不利的妄念。所以唐太宗初行考试时,眼看着天下才子被录取后“缀行而出”,不禁高兴地说: “天下英雄都被我收用了!”后来赵嘏也作诗道: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从唐以后科举考试就日益严密,成为官僚进身的主要途径。
“赚得英雄尽白头”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试拿明清时科举考试制充分确定了的情形来看。那时各府州县都设有“儒学”,进学是科举考试的步。政府派有管考试的大员到各地来举行这种入学考试,参加考试的是已经在各县考取了的童生。考取入了学的叫做秀才,考不取的到老还是童生。所谓入学并不是现在的进学路的意义,而是表示从此踏进了做官的门路。所以入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儒林外史》一开首写的周进,便是“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到60多岁还是一个老童生。而上文提到过的范进,也是从20岁应考,考过20多次,到54岁才入了学的人。入学成为秀才后就立刻取得一种资格,以后倘不能一路考上去、做到官,也可以退一步做教书先生。所以范进一入了学,他的丈人胡屠户就向他说: “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常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彩了。”
既入学之后,还要经过考试,考到一、二、三等的才可以到省城去应乡试。乡试3年举行一次,考中了的便是举人。全国举人又要集中到京城去会试,也是3年一次。后会试考中的人更由皇帝亲临举行一次考试,那叫做廷试或者殿试,评定高下。这些考中的人便叫做进士。大大小小的官僚就由这些举人、进士中产生了。到老都是穷秀才、上京考试一辈子也考不上的,自然占绝大多数。
至于科举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呢?唐代有很多科目,其中诗赋是主要的。诗做得好,便有做官的希望。到了宋代,人们认为诗没有用处,改重经义。所谓重经义,也不过是叫每个应举的人把被认为圣书的“五经”中先定一种,死死读熟,并且读熟由政府规定的一种训诂。这自然也并不比诗赋有更多的实际用处。明代创行了所谓八股文。那是专取“四书五经”上的句子做题目,应考的人就按照法定的解释来发挥做文章,文章的格式是一定的。这种文章,除了作为做官的敲门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正因为可以使人做官,所以当时多数读书人都把毕生精力用在这种无用的东西上去了。 《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坐在书店里选批的《历科程墨持运》,就是编集每一届考试优胜的举子的文章,供人作熟读揣摩之用。这位马二先生曾向一个年轻人忠告道: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贤弟,你少年英敏,可细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宦途相见。这一段谈话,正可以说明在科举考试制下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在当时人看来,读书——应举——做官,这是必然地互相联系着的三部曲。
科举考试的作用本来是要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选择有才能的人做官,但从这样的科举制度中显然是产生不出有才能的人来的。因此,科举考试制度越是严格,所产生的官僚也就越是糊涂无能。但是专制统治者的主要目的还是达到了的。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从消极意义上说,固然是“赚得英雄尽白头”;但更主要的,在积极意义上,是为自己培养一批忠诚可靠的奴才以供役使。这些念了一辈子死书、好容易戴上乌纱帽的人,对于现行统治秩序自然是竭诚效忠了。
可是专制统治者一遇到国难危急时,却不能不坐食这种科举考试的恶果了。像明代末年,内忧外患日迫,而那些从科举场中出身的官僚, “文不能安邦定国,武不能临阵出征”,束手无策。当时有一个举人就慨乎言之说: “设制科,限资格,皆所以弥乱,非所以戡乱也……今日救生民,匡君父,无逾于灭寇,然生平未尝学,父师未尝教,所殚心者,制举之业。一旦握兵符,驱强寇,其良者惟守义捐躯,何益于疆场哉!”所以到了后,官僚中大多数眼看着这个统治政权将要崩溃,覆巢之下无完卵,就索性另求生路去了。不论是被他们骂做是流寇的李自成来做皇帝,还是满洲人来做皇帝,只要给他们官做,他们都可以俯伏称臣, 因为他们生活中的的的内容和目的本来只是做官而已。
四、官僚的膨胀
既然官的地位如此崇高,又有较公开的入仕途径,奔趋到这条路上来的人自然是多到极点。但官的数额究竟有限,科举考试录取名额也不能不有限度,许多想做官而做不了的人岂不也要生怨望么?
使读过书的知识分子争着来做官,并尽可能使要做官的人有官做,这是专制统治者维系其现行统治秩序的方法。
因此不管是否需要这样多的官僚,科举考试仍是非经常举行不可的。唐代,由科举考试及第的人还须通过吏部的考试才给官做;宋以后,是一及第就立刻可以做官的。在宋朝还有一个故事,说是张元应举,已考中进士,在殿试时却被黜落,怨愤之下就投降了西夏国主李元昊,来给中国捣乱。从此以后,就明定了进士在殿试中一概不再黜落。这故事可以表明,多多使人做官正是稳定统治政权的一法。清朝以异族统治中国,更尽量在科举考试上与人方便:除了3年一次的考试外,在每遇到国家庆典时还另开特科;又特颁恩典,对于蹭蹬考场、年老尚未及第的人破格录用为官;并且倘若童生考不进学,也可花钱买一个监生的名义,一样能参与乡试,走上做官的途径。这自然都是为了笼络人心。
唐宋以后科举考试虽被认为是做官的正途,但除此以外,也还有各种各样路子可走。
汉朝的察举、征辟之制,在后代仍以别的形式与科举考试制并行。特别在异族统治的朝代,因为一时还有些知识分子不甘愿来应付科举考试,便更特别推行其他方法。如元朝初年曾大举征访所谓“山林隐逸”,清朝初年也下诏荐举“山林隐逸”,征召“博学鸿儒”,来表示他们是有诚意和中国读书人合作,愿意给他们官做的。明朝也曾特别重视荐举,广开做官的门路,使人们不必经过艰难的科举考试也有官做。
既然科举考试制的目的不外乎求得忠顺的人来做官,那么予官僚的子孙以做官的更多方便,也是使官僚更加忠顺的方法。所以官僚虽非法定的世袭,但作为皇上的恩典,官僚子孙常可以不经过考试就取得官爵。这是各代都有的情形,而在宋代为盛行。在那时,不仅一人做官,他的子孙可以连带得官,甚至只要官做得大,连他手下的门客也都被封官。
至于因接近皇帝或掌权大臣,以特殊技能或特别殷勤而被赐官爵,也是常有的事。
甚至官职可以公开用钱买。这也是古已有之的办法。汉武帝时,已有输纳一定数额的粟帛给政府就可以做官的规定。东汉时政府出卖官爵,还公开定得有价目表。像灵帝时, 二千石的官(当时官级高下以所得俸的多少来表示,俸以米计)卖钱2000万文,四百石的官卖400万文,也可以讨价还价,打折扣。曹嵩买太尉,出了1亿文。崔烈买得司徒,照定价要1000万文,却只出了半价。授职后,灵帝很懊悔,向左右说,应该敲他一下,让他出1000万文才对。那时买官职还可以暂欠,到上任后再加倍还。唐代也有定价卖官的制度,纳钱30万文便可得官职。清代除了在科举方面可以花钱买监生外,也可以直接花钱买官做,号为“捐纳”。这种办法一方面既可以满足那些有财产而不读书的人的做官欲望,加以笼络,一方面也可以弥补国用的不足,在专制政府看来正是一举两得的好法子。
既有科举考试制不断引进官僚,又有这种种进入仕途的方便之门,结果官员数量不断增加,以致超过实际需要量。
我们都知道在经济上有所谓通货膨胀的现象,那么对于在官僚政治下官员无限度地增加的现象也可以加上一个名称,叫做“官僚膨胀”。由以上所述,可知这种膨胀正是在官僚政治下必然产生的现象。汉、唐、宋、明各代,无一代不显著地发生这种现象。
譬如唐代,在高宗时全国文武官一共是13465人,而这时每年经考选有资格做官的人就有1400人。官数不断增加,到了玄宗时,相距不过五六十年,官数已增至17686人之多。所以这时已有人说: “现在的情形是官数比古代多一倍(东汉的官只有7567人),有资格做官的人比官又多10倍。”宋朝开国以后不久,在真宗景德年间,有官1万多人。过了四五十年后,在仁宗皇祐年间,官数已增了一倍。又过10年,在英宗治平年间,官数更增加到24000人。以后仍不断增加,多时一共有34000人。到了明代,膨胀得更厉害了,武宗正德年间,全国的文官有2万多人,武官有8万多人。以上这些数字还只是指正式的官,官下还有所谓吏。吏虽不如官的地位,他们的出身也和官不同,但他们是官的爪牙、官的附庸。倘把吏也计入在内,数目就更大了。如在唐玄宗时,有官18000人,而较高级的吏就有近6万人。明代文武官加吏在内一共有近18万人之多。
由于官僚的膨胀,就会引起许多对于专制统治也是不利的恶果,其中显著的是:
,官僚在量上的增加,同时就一定是质上的降低。使这些走上仕途的人都对现存统治秩序深感满意的目的虽然达到,但是选择有能力的人来为统治政权效劳的目的却完全被抛开了。
第二,为了容纳这不断新添的官员,势必扩大政治机构,并增设不必要的机构,平添许多冗员。关于历代政治机构的情形,详细说来是很麻烦的且也不必要,因为历代政权性质既无改变,其政治机构在基本上也是相继承袭的。不过每一代在因袭前代制度后,必又增添上新的官职机构,或把本来是较不重要的官职加以扩大,使成为庞大机构,以致政府中添了许多根本无用的官员与机构;并且在各种官职和机构之间,职务不能划清,事权重复,更使我们今日研究起来难以一一弄清。这种情形之所以产生,固然因为这种政府机构互相牵制重叠的情形恰恰有利于专制集权的统治的运用,同时也显然是因为要容纳那日益增多的官僚。整个政治统治机构一天天更加庞大,不可免地陷于臃肿不灵、没有活动能力的情况,尤其在遇到突发事变时自然更完全暴露出其无能来了。
第三,官吏的膨胀就使国家开支浩大,人民负担加重。在专制时代,王室的费用和官吏的供养是国家支出中极大甚至是的一项。如宋代官僚的待遇厚,不仅有钱有米,而且有田。所以当时人说,政府对百官加恩唯恐不足,而向万民敛财不留其余。且官僚不仅有合法的收入,更可靠官的地位来增加不合法的收入。明代官俸,然而官僚的贪污腐化也盛,他们一面向人民巧取豪夺,一面截取国库中的收入,虽小小的官也可立致豪富,这自然是把做官看作有利的职业的情形下必然发生的现象。所以官僚的不断膨胀对于人民的意义不过是背负担子的日益沉重。
五、 “国家之败,由于官邪”
由以上所述,我们对于官僚政治下的实际情况也就不问可知了。
官僚职位的升迁,一般说来都是凭资格而不凭能力的。从唐宋以后就已确定了所谓“磨勘制度”:人们一入仕途就有了的保障,只要循规蹈矩地做下去,过一定期限就可以升一级官。这种升迁的制度和科举选官制度一样,是看起来公平的办法,但事实上只能养成无能的官僚。
假如不满足于这种按部就班的升迁,怎样呢?那就多半要靠私人请托、行使贿赂以至种种暗地进行的方法了。
在这情形下,自然就造成了只有权奸小人能够当政的现象。专制政治下的权奸小人,无非就是那种善于伺候皇帝,取得皇帝信任,而在实际上只顾个人私利的人。在上面当政的是这样的人,在下面从政的全部官僚都得到了极大方便,更可以称心如意地向人民诈索,更可以毫无顾忌地通过不合法的方法来取得高官。人们都骂唐代的李林甫、宋代的蔡京、明代的严嵩、清代的和珅,这些都是所谓奸臣;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权奸专政之所以代不绝书,正是因为这是在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下的必然产物。由此也就可以懂得汉、唐、明各代宦官政权的由来了。假如以为这少数无知无识的宦官真能够蒙上蔽下,因而取得实际政权,那就错了,因为宦官之得势完全由于在上有皇帝的信托,在下有官僚集团的拥护。那时候,自命为“读圣贤书”的官僚士大夫纷纷拜倒在宦官前面,无非是利用这种宦官的无知无识,利用在宦官统治下的政治,使每个人都可以方便地取得自己所要得到的利益。
于是贪污就成为历代官僚的一个必然属性。升官、发财向来被视为互相联系的,而在法定的官俸以外用任何手段来增加财富都统属于贪污的范围。
历代的皇家,不仅通过官僚机构来向人民征收赋税,而且要由各地官僚进奉额外的钱财。地方官僚之所以要尽力进奉,自然是因为这样做了,官位才可靠,才更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更快地升官。中枢官员因为有权管理地方上的用人行政,考核地方政绩,所以地方官员也就非报效不可。 《水浒传》上写晁盖等智取生辰纲,所取的就是地方官僚送到京城去孝敬中央大员的财礼。历史上有一些当权大臣后来失势被皇帝抄了家,从至今保存下来的抄家时的登记清单中,我们可以具体知道这些人的财富实在是大得惊人。譬如明代严嵩的家产,光是黄金就有3万多两,银子200多万两。据说这还只是他实际财产的十分之三四。明代当权的太监,财富更是巨大,如朱宁、江彬都有黄金10万多两,银子500万两左右,而刘瑾甚至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万两。清朝和珅有金4万两,银300多万两。由他们的巨大财富,也就可以想见当时整个官僚集团中的贪污情形了。
明清两代,由于商业资本的发达,使官僚的贪欲更甚,由此官僚贪污的情形也空前严重。中央大员既然一心一意凭借地位聚敛财产,地方官员当然更是要拼命赚钱了。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绝好的写照。 《儒林外史》写一个知府新上任,向前任打听的一件事便是: “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这话正是问怎样可以贪赃枉法。 《明史》中有《循吏传》,载循吏一共有125人。但其中属于明代前半期的有120人,后半期的只有5人。所以历来人们都认为明代前半期官吏的风气较好,而到了嘉靖朝以后就贪污公行了。但实际上并不然,不过是在明朝前半期,一般官僚从事非法的贪污还遮遮掩掩,不敢公开,后半期却明目张胆,在官场上公开送钱,不以为讳,所以几乎连一个清白的官也找不到了。
有人以为,明清两代官僚之所以贪污盛,是因为这两代官俸薄。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并不足以说明贪污现象之由来;因为唐宋的官僚的待遇非常优厚,而贪污情形也同样存在。原来,有粪坑就必然有蛆虫,有官僚制度就必然有贪污。
固然在官僚制度下并非没有个别的清白的人,但是当作全体看,官僚制度是只能产生贪污的。而且在当时对于清官的定义和我们今日所了解的真正廉洁并不相同。原来历代对官僚的待遇虽然有厚有薄,但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上的行政费用是并不负担的。各地方的官僚除了收足中央额定的赋税缴上去,更得设法筹措自己的行政费用。这就是说,各地本是有权向民众求取非法的额外收入的,同时中央官员则乘机向地方官员分肥一部分。所以历代专制政府虽然以整肃官常为口号,但实际上官吏一定限度的贪污是被默认的。清朝康熙皇帝就曾坦白地说过: “所谓廉吏,并不就是一文不取的意思。若是一丝一毫没有什么收入,那么居常日用和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呢?如州县官止以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算是好官了。”所谓火耗是明清两代赋税制中的术语。州县官向民间征收钱粮,除了国定的税额外,另加的额收归于私囊的部分便是火耗。康熙皇帝以为在一两正税上揩油一分的(百分之一)便算好官,但实际上当时的火耗都在一钱二钱(十分之一二)以上。既然无法禁止贪污,那么要加以某种程度的限制是不可能的。
贪污的结果是很显著的。人民在官僚剥削下的负担无限度地增加,国家的收入在官僚的侵占下日益感到不足,而官僚机构本身由于贪污的流行,群趋于如何赚钱的打算,政事便更加败坏了。
所以历来有句话道: “国家之败,由于官邪。”这是说,专制政权的败坏是由于官僚的贪污腐败。其实我们已看出,官僚的贪污腐败正是在专制政治下造成的必然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