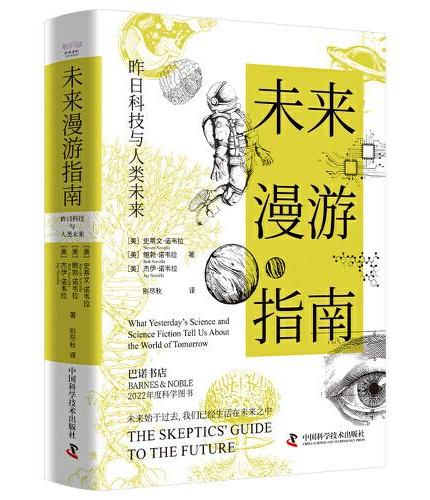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无法从容的人生:路遥传
》
售價:NT$
340.0

《
亚述: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的兴衰
》
售價:NT$
490.0

《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采煤机智能制造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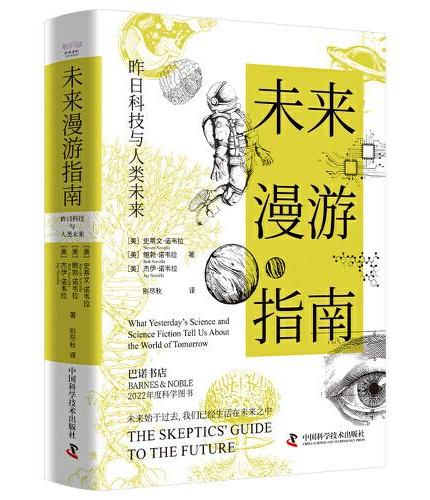
《
未来漫游指南:昨日科技与人类未来
》
售價:NT$
445.0

《
新民说·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上下册)
》
售價:NT$
790.0

《
我从何来:自我的心理学探问
》
售價:NT$
545.0

《
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
》
售價:NT$
390.0

《
送你一匹马(“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看三毛如何拒绝内耗,为自己而活)
》
售價:NT$
295.0
|
| 編輯推薦: |
1.关于萧红的作品有很多,这一本更为动人!
本书以萧红(悄吟)坎坷多难的身世为艺术原型,用抒情明快的细腻笔触,曲折跌宕的动人故事,展示了她富于传奇色彩的悲剧命运。
2、用一生讲述一个传奇,萧红无畏的精神令人感动。
本书除了讲述萧红的传奇经历,还可以看见萧红的精神是无畏的、敢于抗争的。同时在较为深广的历史背景上,塑造了多个一代文学青年的形象,并对鲁迅等文学前辈在为人为事亦有生动的记叙,是一本读来令人感动的传记体小说。
3、认识萧红的骆宾基读过此书,是一本上佳的了解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的文学作品。
有人说萧红是现代文学史上ZUI为迷人的女作家,有人说她活成了以一本小说,有人说她活成了一个传奇。《萧红小传》作者、萧红去世前陪在萧红身边的骆宾基读过此书,足见本书的成功。
4、非常难得,这是一本用传记的方式写的小说
读萧红的小说可以理解她的人生,读萧红传可以更加细致地了解她的一生。《落红萧萧》是一本用小说的方式写的传记,题材独特,情节丰富,是了解萧红的一本好书。
5、重新编订,精美设计
本书文字重新编订,增加了作者松鹰再版后记,同时本书设计精美,开本适中,纸张精良。在一众萧红生平
|
| 內容簡介: |
萧红,曾被鲁迅赞为“当今中国有前途的女作家”,但在生命的黄金时代却悄然凋零,为后人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还有未完成的《马伯乐》等用血书写的近百万灼热文字。她在大起大落的生活与情感波涛之中,度过了自己三十一岁的短暂生命。
《落红萧萧》以萧红坎坷多难的身世为艺术原型,用抒情明快的细腻笔触,曲折跌宕的动人故事,展示了她富于传奇色彩的悲剧命运。同时,在较为深广的历史背景下,塑造了萧军、骆宾基、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一代文学青年的形象,讴歌了他们冲破封建藩篱、抗日爱国、追求自由光明的无畏精神。本书对鲁迅、丁玲、茅盾等文学前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活动亦有生动的记叙,是一本难得的有血有肉的长篇小说。
|
| 關於作者: |
刘慧心,河北保定人。早年为工人,后历任《甘肃日报》记者、编辑,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为鲁迅文学院学院。197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落红萧萧》,散文集《文坛人物剪影》,电影文学剧本《萧红》等。
松鹰,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国家一级作家,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社会派推理小说领军人物。著有《落红萧萧》《杏的复仇》《白色迷雾》《空瓶子密码》等四十余部作品。其作品多次获全国大奖。其中《杏的复仇》英文版曾荣登2016年美国《图书馆杂志》推理小说榜。
|
| 目錄:
|
目 录
一 心的呼唤
二 流水落花
三 命运的洪波
四 燕子啁啾
五 笔和剑
六 血红的广告
七 黑夜的星星
八 珠联璧合
九 逃亡
十 希望之光
十一 两颗漂泊的心
十二 啊,主将
十三 文坛新秀
十四 震撼了奴隶们的魂魄
十五 决斗
十六 摆脱不了的寂寞
十七 她漂海而去
十八 巨星陨落
十九 魂兮归来
二十 我心残缺
二十一 昨夜的明灯
二十二 要朝上飞啊
二十三 奴隶的死所
二十四 落红萧萧
呼兰河寻梦——《落红萧萧》再版代后记
|
| 內容試閱:
|
何人绘得萧红影?
——关于萧红、《呼兰河传》和《落红萧萧》的记忆碎片
梁由之
1
百年以还,中国好的东北籍女作家,前有萧红,后有迟子建。
萧红的书,我喜欢《呼兰河传》。
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国的中篇小说,以“两传一城”为经典。两传,即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铁木前传》;一城,指沈从文的《边城》。
写萧红的书也很多。我印象深的,当数刘慧心、松鹰合著的长篇小说《落红萧萧》。
2
初知道萧红,应该是从小说《红岩》中,一看到,就记住了。当时刚十来岁吧,认识几个字,父母和姐姐们的书,找着就看,瘾头奇大。
银行职员、地下党员甫志高开了家书店,交给手下的青年工人陈松林打理。一个头发长长、脸色苍白、衣衫破旧的青年,常来看书,间或也买一点。有一次,他买了本《萧红小传》,发感慨说:萧红是中国有数的女作家,是鲁迅先生一手培养的,可惜生不逢辰,年纪轻轻就被万恶的社会夺去了生命。
陈松林大受感动,认为这个名叫郑克昌的青年值得关注,引为同类,想发展他入党,却险些吃了大亏——其实,那厮是个伪装进步的军统特务。
3
接下来,先看到鲁迅的《萧红作〈生死场〉序》,那是一篇要言不烦、笔力千钧的名文。迅翁写道: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随后,才读到《生死场》,和萧红若干其他著作。
顺便说一句。怀念鲁迅的文章,车载斗量。我以为写得好的,出自迅翁当年偏爱的两位青年作家的手笔——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徐梵澄的《星花旧影》。
4
孙犁晚年,曾用罕见的饱含深情的笔墨写道:
鲁迅是真正的一代文宗。“人谁不爱先生?”是徐懋庸写给鲁迅的那封著名信中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这是三十年代,青年人的一种心声。
书,一经鲁迅作序,便不胫而走;文章,一经他入选,便有了定评,能进文学史;名字,一在他著作中出现,不管声誉好坏,便万古长存。鲁门,是真正的龙门。上溯下延,几个时代,找不到能与他比肩的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都不行。
耕堂又说:萧红是带着《生死场》的手稿去见鲁迅的。
这些话,大有深意,值得反复吟味。
5
1983年,我读到了新出的长篇小说《落红萧萧》,很喜欢。推荐给母亲看,她一口气读完了。她爱惜萧红,也很喜欢这本写萧红的小说。
一年多后,母亲病逝。我挑了几种她爱看的书,放入棺木相伴。现当代小说,有《青春之歌》《晋阳秋》,还有《落红萧萧》。
6
2005年,我开始写作。年底,开敲《百年五牛图之四:关于陈寅恪》,其中一段写道:
1999年大约是春天,梁某特意去了一趟广州。主要目的有二:到银河公墓凭吊萧红,到中山大学瞻仰陈寅恪旧居。
在陈先生故居,绕室彷徨,心事浩茫。不由想起何士光的中篇小说《青砖的楼房》里面的句子:
“要是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人预先地告诉你,说你后来能有的日子不过只有这样的一条远远的楼廊,那你会怎样想?那时你还愿不愿意再往前走?”
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春草芊芊,燕子呢喃,阳光暖洋洋的,微风中略带一丝薄寒。
人去楼空,旧游飞燕能说。
整整20年后,2019年初冬,我重复了当年的两个举动。在萧红墓地,想起聂绀弩的诗句:
浅水湾头千顷浪,
五羊城外四山风。
7
我正在编撰的多卷本《清晰与模糊的背影:百年文人》中,破例选了一首诗——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8
1961年3月,夏志清的力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初版。十年后,又推出增订二版。列专章论述的作家有: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吴组缃、张爱玲、钱锺书、师陀。夏志清未提到《呼兰河传》。关于萧红,也仅有寥寥数语:
萧军(亦名田军,1908年生)、萧红(1911—1942)抵达上海后,同鲁迅极为亲近。鲁迅也斥资为他们出书写序。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高。
1979年9月,《中国现代小说史》港版中译本面世。夏志清在《中译本序》中特别补充说明:
抗战期间大后方出版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期刊我当年能在哥大看到的,比起二三十年代的作品来,实在少得可怜。(别的图书馆收藏的也不多,但我如能去斯坦福的胡佛图书馆走一遭,供我参阅的资料当然可以多不少。)四五年前我生平次有系统地读了萧红的作品,真认为我书里未把《生死场》《呼兰河传》加以评论,实是不可宽恕的疏忽。
三十多年后,他又这样说到萧红和《呼兰河传》:
《中国现代小说史》未提萧红,因为我当年尚未读到过她的作品。后来我在中译本《原作者序》里对自己的疏忽大表后悔,并在另一篇文章里对《呼兰河传》予以的评价:“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
9
迟子建有次坐飞机旅行,邻座是一位干净体面的青年。他不玩电脑,不听耳机,也不翻报刊,兀自静静地读书。迟子建有点好奇。及至终于看清他读的什么书时,她不能保持淡定了:万米高空上,青年手中,正是萧红的《呼兰河传》。
她克制不住好奇心,破例主动搭讪:为什么喜欢看这种书呢?
青年回答:这个世界,太过喧嚣热闹,我更愿意读点冷清寂寞的文字。
迟子建听闻此言,甚是感动,泪珠盈睫。
这个故事也感动了我。时隔多年,仍能记住梗概。
10
2011年初,机缘巧合,我出高价,在长沙买到一本1947年6月寰星书店的初版《呼兰河传》。内容包括:著者遗像、萧红小传(骆宾基撰)、序(茅盾撰)、正文。
此书原由望城一中一位高中语文老教师收藏,书中夹有一张“上海旧书店门市发票”,时间是1964年4月23日。
老人去世后,晚辈对文艺无感,开始售卖旧藏,我方得以入手。
有次在尚书吧,带给陈子善过目。据他说,那是他见过的该书品相好的一本。
11
2018年,在电视上看到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汤唯饰萧红,郝蕾饰丁玲。若有所思。
翻出《落红萧萧》,又看了一遍。检索了一通,那么多年,时光流逝,花开花落,此书仍只有当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旧版行世。
该出个新版了。它配。
当年年底,经朱晓剑协助,我与作者之一松鹰顺利接上头。他的写作,早已转向,却念念不忘壮年时这部呕心沥血之作。
12
2019年6月7日,端午节,我从上海飞成都。松鹰当晚为我接风,一见如故,一拍即合。
随后,《落红萧萧》新版正式排上日程。我们商定,除将原书真实人物姓名尽量改回本名或常用笔名(如聂长弓改为聂绀弩,司马少白改为端木蕻良,罗铮改为骆宾基)外,一仍其旧。
尤为令人开心的是,“九○”后的编辑,很喜欢这本书,看得感动、入迷,工作积极、认真。
钱锺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看来,好的书籍,经受得住地域、时间和不同读者群的综合考验。
新版即将出炉,松鹰兄坚持要我写篇序。辞不获已,遂在岭南冬日的艳阳下,敲下这篇拉杂的文字,聊以塞责。
2020年12月29日,夏历庚子冬月十五,写定于深圳天海楼。
二十四 落红萧萧
萧红赴香港后的第三天,舒群回到重庆。因为采访地区遭到日本飞机轰炸,途中耽误了数日。
他一到报社,就看见萧红的信。他匆匆地拆开,信是用报社的稿笺写的,只有寥寥数语:
舒群:
后天,我就要去香港了,端木应邀去那里办刊物,那里的环境对我写作也许有些帮助,端木说茅盾先生也在那里……我来过两次,你都不在,不能当面向你告别了,真有说不出的遗憾!
萧红
读完这封短信,舒群知道事已不能挽回,不禁喟然长叹。
从信的内容看,萧红完全是在端木蕻良的鼓动下决定去港的,她希望有个安静的写作环境,可香港并不是蓬莱仙岛啊!而且舒群很清楚,茅盾此时正在新疆学院任教,并不在香港。萧红太轻信,也太善良了,总以孩提般天真的心灵来看待别人,她的不幸也正在这里。
萧红悄然飞港,在重庆文艺界圈子里,引起了许多猜测和议论,但更多的人是在为她担心。
过了几个月,有消息隐约传来,说萧红在香港除了写作外,几乎过着“蛰居”的生活。她正在写《呼兰河传》。这是一部酝酿了几年的长篇小说。舒群曾听她谈起过。她说这个作品在武昌就开始构思了,她在汉口码头摔倒时,躺在湿地上,望着蒙蒙的天空,就想到这个题材,如同一个走到人生旅途终点的人,突然发现了充满着阳光的童年和故乡而久久地怀念。现实的寂寥、悲凉,淡淡的乡愁,都被这回光温暖了。这是一种甜蜜而又哀伤的回忆,是一种感情的回归,就像一个流落异乡的孤儿怀念自己母亲的一样。即使走到天涯,她也永远记得她的母亲。每当晚霞染红了西天的时候,她就觉得母亲的目光布满整个天空……
舒群终于收到了萧红的来信,这时他才知道她是这样的寂寞和孤独: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抑郁,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漫山遍野的鲜花,有婉转的鸟语,还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常令人神醉,这一切不都是我往日所梦想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若可能我将在冬天回去……
然而冬天来了,又过去了,萧红并没有回来。有关她的消息越来越少。与此相反,战争的噩讯却甚嚣尘上。不久,舒群奉命调赴延安,从此与萧红失去了联系。
一九四一年春天,内战的阴云笼罩全国。一些进步作家南下到了香港,茅盾这时也来了。他看到萧红写作很勤奋,鼓励她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四月,史沫特莱在回国途中路过香港,特地去看望了五年不见的萧红。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史沫特莱在九龙尖沙咀乐道找到萧红的住处。她推开房门时,萧红正靠在一张躺椅上,房间像鸽子笼一样窄小,空气也不流通。一缕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照在萧红的脸上,她容貌苍白、消瘦,漆黑的头发被阳光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
看见这种情景,史沫特莱非常吃惊,她问:“亲爱的,你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笼子里?”
萧红紧握着史沫特莱伸过来的手说:“中国作家的生活是世界上等苦闷的。”史沫特莱的来访,使她很高兴,苍白的脸上微微呈现出红光。她不能多说话,一说话就拼命地咳嗽。
史沫特莱感觉到萧红的病已处在危险边缘,深情地望着她:“你应该到医院去疗养,这里对你的身体太不利了。”
“我还好,反正已经习惯了。”萧红喘着气说。
“不行,一定得去医院。我可以先为你接洽住院费打折扣,回美国后再给你筹款。”这位五十一岁的美国进步女作家,伸出了友谊的手。萧红为史沫特莱的真诚所感动,颔首表示同意。
“这就对了。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史沫特莱灰色的眼睛闪着愉快的光芒,从提包里取出一套崭新的西服,有大衣、上装和西服裙,全是紫红色的。她知道萧红喜欢红颜色。
“真漂亮!……可我穿不出去了……”萧红的脸上掠过一抹凄凉的笑容。
“你才二十九岁,正是穿的时候呀!”史沫特莱把双手放在萧红的肩上说。
在史沫特莱的劝告下,萧红同意到玛丽医院去治疗。当时对肺病的主要治疗方法,就是空气和营养。玛丽医院在香港郊区的山野上,可以望见大海,环境很幽静,医院还在试行一种打空气针的新疗法。史沫特莱通过在港的熟人,为萧红联系好了这个疗养的好地方。
端木蕻良住在时代批评社,不常回来。萧红给他挂了电话,说她过海去医院,打完空气针,一个小时就可以回家。
史沫特莱的友谊使她感到温暖,乘船过海时,心境很愉快。海峡的风景很美,一片碧澄,她觉得自己又像追随船尾的海鸥一样,可以飞起来了。
可是,在医院打完空气针后,她就躺倒了,再也站不起来了。几年来一直折磨着她的所有病痛,都显露出来,她太虚弱了!
萧红躺在病床上,脸色白得像蜡一样,不停地咳嗽、发喘,就这样在玛丽医院住了下来。
夏天到来时,她稍稍好了些,被移到阳台上,这样可以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晚间,就在阳台的床上安寝。海上风平浪静,漆黑一片。从下面海湾外传来阵阵涛声,低沉而忧郁。萧红常常难以入睡,她睁着眼,默想着遥远的过去,童年、故乡、少女时代、东北的沃野、漫山遍野的高粱……这一切使她深深地怀念。离开东北七年,在战乱和人生的波涛中颠沛流离,如今真成了异乡的游子,漂到海角天涯!也许她永远回不去了,她真想再看一眼呵,那可爱的松花江,呼兰河……
与她同在阳台上的病友,是一位香港女工,二期肺病患者,只有她和萧红同病相怜。
“陪我吃一半苹果吧。”萧红递过半个苹果给她。
“谢谢,我不吃。”女工友好地点点头。
“你要吃一半的。我们俩在这世界上都是举目无亲……吃吧,要留下一个记忆,说是那一年,我和一个名叫萧红的人,同在玛丽医院养病,我们一块吃着苹果……”
那病友接过苹果,望着萧红笑了笑,那笑容含着怜悯和凄婉。
有一天夜里,海上风很大,萧红受了凉,病情突然加重。她咳嗽不止,要求医生给她打止咳针,但医生漫不经心地哼了一声,转身走了。护士也显得很不耐烦。这里是三等病房,一切都只能按“三等公民”对待。十年前,她在哈尔滨医院里遭到的冷遇,如今又重演了,但这时,再也没有谁拦住医生大喝一声:“……要是她死了,我会杀了你,杀了你的全家,杀了你们医院所有的人!”
她想起了萧军,他那凌乱的头发、粗犷的声音,他们相爱时的一切细节,从来没有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她默默地平躺着,思绪纷繁。
天花板是苍白的,病房的墙也是苍白的,甚至连护士的身影也显得那样苍白。同样的白色,竟然迥然各异;一种是冷漠,一种是圣洁。萧红回忆起她和萧军新婚初夜时那间难忘的小房间,雪白的墙,雪白的床单,雪白的桌布。
“我们将在这银色世界度蜜月啦!你是白雪公主,我是赤膊王子……”
这一切真像一场遥远的梦!
“这真是奇妙的结合。你身上既有艺术家的那种才气,又有艺术家所没有的那种粗犷和憨厚。”一次她望着萧军说。
“我是行伍出身,首先是个军人,其次才是艺术家。”萧军答道。
“你是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呀!”
“不,我的事业应该在战场上。”
也许他现在真的走向战场了吧?他们为了这一点争吵过多少次啊!他终于自由了,可以去干他的事业了……想到这里,萧红心里升起了一缕暖意和无限感伤。
当天夜里,她挣扎着起来,悄悄披上衣服,慢慢向楼梯口走去。
“你要干什么?”一个值班的护士发现她。
“我要离开你们这个医院,我不住了。”
“回去躺着吧,”护士对她说,“明天让你丈夫来签了字,就领你回去。”
萧红回到病房,躺在床上,觉得四周都是阴森森的墙壁,插翅难飞。明天要是端木蕻良来了,决不会让她出院的,他一定会推脱,会宽慰,劝她在这里一直住下去。
夜沉沉,听着梦呓般的海涛声,她想:“如果我知道萧军在哪里,打一个电报给他,他一定会来接我的。”可是,神州茫茫,他在哪里啊?
第二天,萧红给另一位友人挂了电话,请他帮助。那友人是东北救亡协会香港分会主持人于毅夫先生,接到电话后,他立即赶到玛丽医院,经过一番交涉,替萧红办好了出院手续。
当天下午,萧红回到了九龙尖沙咀乐道住宅。她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进阴暗的小屋,气喘吁吁地倒在躺椅上。端木蕻良还没有回来,她瞥见桌上摆着一个信封,好像是外国寄来的航空信,上面写着她的名字。萧红拆开信,是史沫特莱写的。她在信中告诉萧红,她将萧红的散文《手》译成英文,在斯诺夫人主编的《亚细亚》月刊上发表了,不久即把二百元港币稿酬汇上。这封从千里之外寄来的信,给萧红莫大的慰藉,她的作品已经飞过了太平洋,为美国人民所了解,她笑了。她多么盼望自己的病能好起来,再写一些东西呵,在人生的旅途上,她才度过三十个春秋。她的《呼兰河传》已经脱稿,还没有出版,她还有许多东西要写,还有那与丁玲、聂绀弩、萧军等人相约写《新红楼》的夙愿……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声毁灭了这位青年女作家的憧憬和希望。没过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飞机拼命轰炸香港,港九两岸顿时烟火弥漫,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
这天早晨,萧红躺在床上,神情惶乱不安,不停地咳嗽着。端木蕻良在收拾箱子里的东西,像是要远行。他一面收拾一面唠叨着:“……我只带些衣服,其他都留给你。”他翻着箱子,把一些零星什物拣出来。在一堆旧书旁边,出现了一根细竹棍,二十几节,他拿在手里看看,不经心地将它扔在床上。“你不用害怕,日本人不会马上来的……我到新加坡先安排一下住宅和职业,随后你再来……”
萧红一语不发,痛苦地咳嗽着。
“……他早想离开我了……”她心里想道,“可鄙的是……他选择了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萧红注视着他扔在床角的小竹棍。“那根竹棍……”她吃力地说。
端木蕻良拾起竹棍,随手扔给萧红:“噢,是你的纪念物吧?你留下好了。”他拎着一个小包,向萧红说声,“再见”,便向外走。
萧红把竹棍握在手里,她的手颤抖着,颤抖着——“叭,叭”,竹棍在她手中折断了。
端木蕻良回头看了一眼,这时,一个敦实的青年匆匆地闯了进来,差点与他撞个满怀。
“端木君,要走呀?”他瞅了一眼端木蕻良手中的小包。
“不……我……准备去托一个熟人。”端木蕻良支吾着。
“骆宾基!……”萧红认出那个青年。
“九龙十分危急,我想问问你们有什么打算?”骆宾基进屋坐了下来。端木蕻良也提着小包返回屋子。
“你怎么来香港的?”萧红声音很微弱。
“我从桂林来不久,住在时代批评社。茅盾说你病重,关照我来看看。”
“谢谢他……”萧红眼里闪着莹莹泪光。
“你先照看一下萧红,我去找找朋友商量一下去留之计。”端木蕻良对骆宾基说,然后出去了。这一次他没有拎提包。
萧红已极度虚弱。她抓住骆宾基的一只手,闭上眼睛休息,仿佛害怕一松开对方就会悄悄溜走。这使骆宾基很感慨,他崇敬她,因为她是《生死场》的作者,又是秀珂的姐姐。
“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好了!大家决不会丢下你不管呀!”他竭力地安慰着萧红。
不一会儿,响起敲门声,一位老先生神色肃然地走进来,骆宾基认出是国民党左派元老柳亚子先生。
萧红睁开眼睛,面容极为苍白。
“好些了吗?”柳亚子俯身问她。
“我……有些怕。”萧红声音微弱。
“你怕什么呢?”柳亚子安慰她,“不要怕。”
“也许……我就要死了。”
柳亚子站起来,悲愤地说:“这时候谁敢说能活下去呢!这正是发扬民族正气的时候,谁都可能死,人总是要死的,为了发扬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这时候就要把死看得很平常……”
萧红平静了些,一双因为憔悴显得过大的眼睛,透出圣洁的光泽。
这时,端木蕻良从外面回来了。待了一会儿,陪柳亚子先生走了。
“你再陪陪萧红,我一会儿就回来。”出门时他嘱托骆宾基。
萧红面色惨白,静静地躺着。骆宾基一直在旁边守护着。
到了傍晚,端木蕻良回来了。他说街上所有的车辆都已停驶,港九之间的水路也封锁了。于毅夫先生为萧红准备了一条渔船,可以在半夜时偷渡海峡。萧红病重,不能自己行走,骆宾基再次留下来,准备护送她过海。他和端木蕻良席地而坐,等候夜幕降临。遥远的海滩方向偶尔传来日军的炮火声,像雷鸣一样低沉而摄人心魄,空气中充满了异样的紧张。
午夜之后,他们开始行动了。骆宾基背着萧红下楼,端木蕻良身单力薄,只提着箱子和随身的小包。他们乘三轮车到了约定地点,登上已在那里等候的小划子。
次日凌晨,海面上寒气袭人,四周像死一般沉寂,只听见小船轻轻的划桨声,船上的人谁也不说话。小划子悄悄地偷渡过海峡。经过几番周折,他们终于在市中心思豪大酒店找到安身处,这时暮色已降临。骆宾基将萧红搀上五楼,安置下来,却发现端木蕻良不见了。起初,骆宾基还没有在意。不一会儿,香港《大公报》一位记者登门访问萧红,待记者走后,骆宾基到萧红床旁,问她是否要等端木蕻良回来后,他再离去。
萧红神色凄然。“他不会回来了。”她说,“我们从此分手,各走各的了。”
“这是为什么?”骆宾基大吃一惊。
“他要‘突围’,去新加坡……”
骆宾基木然地站在原地,像一尊石像,他此刻才意识到,萧红的安危完全落在自己一个人肩上了。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但这个责任,对任何一个流亡的正直的作家,都是不容推卸的。
“可是……我必须先回九龙,把寓所里的稿子取出来。”他焦急地说。那些在桂林桐油灯下写的长篇小说稿,他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天要黑了,你怎么回得去呢?”
“我可以偷渡。”
“那……你尽管去好了。”
骆宾基正准备转身离去,忽然看见萧红背过脸去,在暗自抹泪。他一下犹豫了。
“红姐,我取出稿子,一定马上回来。”
“我不是替自己担心。”萧红转过脸,和婉地说,“我好歹已经脱了险,你想想,你真的说回来就能回来吗?这是战争呀!你听那炮声,你知道九龙现在是什么样子?也许在打巷战,你怎么能冒这个险呢?”
萧红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日本侵略军的海军陆战队很可能已在九龙登陆,英国守军只有几千人,很难守住海峡两侧,香港随时可能失守。骆宾基还想到,假如他离开了,萧红身边没有人照料,发生意外怎么办?说不定什么时候,市区就会遭到大轰炸,到时候酒店里的旅客、侍者都会一逃而空。
“好吧!我不去了。”骆宾基下了决心。
萧红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她把头靠在枕头上,轻声地说:“谢谢你……艺术上讲真、善、美,在生活里也要追求真、善、美……”
她的眼睛里含蓄着一种圣洁的、希望的光辉,使骆宾基深受感动。
骆宾基终于留了下来。他问萧红以后的打算:“战争过去后,你准备去哪里?”
“到上海。”萧红希冀地说,“只要把我安排到许广平先生身边就可以不用你操心了。等我好起来,我一定要试探一下人生的海底。等抗战胜利后,我还要遍访红军到过的革命根据地。”
他们谈了许多,像亲姐弟一样亲切融洽。骆宾基谈起与秀珂一同参军的经过,他们到新四军后分了手,秀珂分在军宣传部,在战场上非常勇敢。萧红听后感到莫大欣慰。
“看见你,我就等于看见了珂弟。”
骆宾基又问起端木蕻良为什么撒手而去。
“他吗?”萧红愤然地说,“我们不能共患难。”
她说完,又喃喃自语道:“我为什么要向别人诉苦呢?有伤就自己用手掩盖起来,一个人不能生活得太惨了,要生活得美……”
在骆宾基听来,这话是发自萧红心灵深处的痛苦呻吟,他年轻的心战栗了。
“为什么你要和萧军分离呢?你们是从哈尔滨一同流亡关内的患难夫妻呀!”骆宾基问。
萧红的心事被触动了。“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太恃强了!”萧红的眼神好像在追溯遥远的记忆,喃喃地说,“我不愿做家庭的附属……”
萧红滔滔不绝地谈起往事。在这患难之际,她把骆宾基当作了自己的朋友、知己、弟弟,当作了生死之交。她向他倾述了自己的身世,少女时代的初恋,与萧军的邂逅、相爱,萧军的豪爽和自傲,他们的冲突,她的出走,后的分手,以及她默默的遥远的怀念……这时,骆宾基才发现她对萧军的感情是如此的深厚而真挚,她的全部叙述和表情里,都蕴含着这样一句始终没有说出来的话:“他是真正爱我的……”
一周之后,思豪大酒店遭到日军炮击,炮弹从九龙隔海打来。顿时大楼里秩序大乱,骆宾基慌忙托起萧红到地下室躲避。第二天,旅客开始向南山一带疏散。
南山的山腰有一幢幽静的别墅,原是避暑用的,这时成了避难的场所。从思豪大酒店逃出来的寓客,都挤进了这里,也有从别的酒店转移来的人。骆宾基背着萧红走进别墅时,就像踏进了一条海轮的三等统舱,逃难者们席地而卧,把铺着花砖的大厅挤得满满的,有说广东话的商人、衣冠楚楚的富翁、外籍绅士,也有涂口红的仕女。骆宾基搀扶着虚弱的萧红,在大厅的角落找到一块空隙,当作栖身之地。一位微胖的中年男子看见骆宾基扶着病人,慷慨地递过一条羊毛毯来。那人穿着中式长袍,态度高雅,留着胡须,萧红认出是蓄胡明志、久未登台的梅兰芳先生,于是点头一笑,以示谢意。大家都没有说什么,在这种战乱的非常时刻,一切礼仪都从简了。
夜幕降临以后,气氛更紧张了。大家都担心着日军从九龙打来的冷炮。萧红躺在羊毛毯上,好像睡着了。骆宾基坐在她的身旁,静静地聆听着楼外的动静。
半夜里,突然响起了猛烈的排炮声,市区里的一幢建筑起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有人悄声地问:“哪里在着火?”也有人在嘘嘘地警告不要出声。又是一阵炮轰,爆炸的地点比刚才近,别墅的玻璃窗被震得哐哐直响。萧红被惊醒了,火光映着她苍白的面孔。
“你害怕吗?”骆宾基问她。
“不怕!有你在身旁,我一点也不怕。”
骆宾基听见这个回答,感到无比的宽慰。在这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一名勇士,强大得像一座抵御炮火、护卫战友的城堡。
大厅里经过一阵轻微的骚动之后,又变得哑然无声。人们敛声屏息,仿佛在默然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萧红仿佛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她的心中充盈着悲哀和愤怒。从哈尔滨到上海,再到武昌、重庆、香港,那日寇法西斯的炮弹好像一直在追着她,步步紧逼。国土沦陷,同胞惨死,个人的不幸和民族的苦难交织在一起,真让人肝肠寸断!
经历了这个动乱、惊惶的夜晚,别墅里的寓客再不敢待下法,第二天就走空了。
骆宾基背着萧红,在皇后大道背后一家民宅找到栖身之地。这时,日军的炮轰稍稍平息。萧红的身体已非常虚弱。她脸色惨白,面容消瘦,两颗深黑的眸子显得更大了。战火反倒使她平静,她似乎觉到生命于她已不久长。于是,萧红一反缄默,同守护自己的骆宾基倾心地交谈起来。
“还惦记你在九龙的那些稿子吗?”她问骆宾基。
“唔……”骆宾基点点头说,“只好听天由命了!”
“什么题材的?”
“就是《人和土地》,在杂志上连载过一部分,”青年作家的眼睛闪着亮光,兴奋地说,“你设计的那幅题图画得真好!”那幅题图是画的几棵高粱,挺拔,茁壮,笔墨简洁,构思耐人寻味,与《人和土地》的主题很协调。骆宾基一直很佩服。
“可能有些乡土气。”萧红沉静地一笑。
“红姐,你什么时候学的画呀?”
“中学时候,那时我很喜欢美术。学校里的美术老师很器重我,不过我终还是没成为画家。我觉得绘画和文学一样,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
“鲁迅先生也很重视美术。”
“是啊……他推崇珂勒惠支的木刻。”
“鲁迅先生也称赞你的散文,说你比谁都有前途。”
“不过,我还是会写小说的。”萧红莞尔一笑说,“有人总以为我只会写散文。实际上小说的写法是各式各样的,并不一定非写得像契诃夫或巴尔扎克。”
“我很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那种大场面非得大手笔不可。”骆宾基发表见解。
“我读过他的《战争与和平》,确是波澜壮阔……”
“可以算是一部伟大的杰作,艺术的高峰!”骆宾基赞叹道。
“……我觉得,在艺术上不存在高峰。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应该走自己独创的道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有些人认为,小说要有固定的章法和格局,不写则已,一写就要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那样,否则就不成其为小说。实际上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作家也是各式各样的。托尔斯泰有托尔斯泰的写法,曹雪芹有曹雪芹的写法。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作家,产生不同的杰作。”萧红说到这里,显得很兴奋,她把头搁在枕上歇了片刻,接着说,“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应该出现比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更伟大的作家!”
萧红的话说完了,苍白的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她微微闭上眼,喘息着,骆宾基望着她,心潮久久不能平息。他觉得她道出了艺术的真谛,心头豁然明朗。可是她自己却像一条春蚕,吐尽了后一缕丝……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三日,萧红被转入跑马地养和医院。这时她的身体已极度虚弱,呼吸短促急迫。当天下午,端木蕻良像突然失踪一样,又突然出现了。他面有内疚之色,递给萧红两个苹果。萧红默然地转过头去,像不认识他一般。
“还没有突围呀?”骆宾基问他。
“小包都打好了,随时准备渡海。”
当天,萧红动了手术。医生误诊为喉瘤,她的喉管被切开。手术后,萧红平静地躺在床上,脸色像玉雕一样光洁、惨白。
“我本来还想写些什么,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哪有不死的呢?生活是这样,身体又这么虚。死,算什么呢?”她断断续续地说。
骆宾基低着头,伤心地哭起来。
“不要哭,你要好好生活,我也是舍不得离开你们的……”萧红安慰着他。
她的两眼闪着泪光,异常明亮,低声地说:“这样死,我真不甘心……”
端木蕻良站在床侧,也落下眼泪。“我们一定要救活你!”他突然悲切地握住萧红的手。
萧红摇摇头,勉强支起身子,从枕下取出几页稿子,那是她几个月前写的《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示意骆宾基读给她听。
骆宾基捧着稿子,一面流泪,一面读着:
……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
东北流亡同胞们,我们的地大物博,决定了我们的沉着英勇,正如敌人的家当使他们急攻切进一样。在后的斗争里,谁打得沉着,谁就会得胜。
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作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
萧红听着听着,渐渐喘息急迫,一口鲜血咯出,昏迷过去。
萧红病情恶化,已讲不出话,又被转入当初她住过的玛丽医院。一月二十一日晚,玛丽医院被日军占领,萧红被赶出后,送到圣士提反女校临时医院。
在弥留之际,萧红在纸上给骆宾基写道: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
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平生尽遭白眼冷遇……
身先死,不甘,不甘!
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三十一岁的萧红静静地闭上了眼睛。她的黑发散垂在洁白的枕头上,嘴唇还保持着淡淡的红润,但她一颗孤寂的心,却永远不能跳动了。
她的床侧只有一个青年,悲哀地伫立着,泪水默默地滴落在地板上。
他手里拿着一本《跋涉》,是死者弥留时赠他的珍贵遗物。
海风从窗外吹进来,掀起了书页,突然有两片小东西飘落下来。骆宾基躬身拾起,发现是两片保存了很久的枫叶,已经干枯了,但那暗红的色泽,却没有消退。
他把枫叶放进书里,推开阳台的门,向外眺望,远处的蓝天碧水间,一群白色的海鸥在飞翔——它们扇动着翅膀,似乎也在为长眠的萧红悲啼:
“不甘——”
“不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