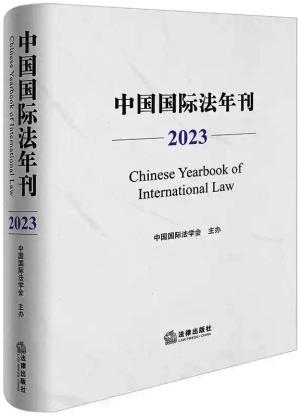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有兽焉.8
》
售價:NT$
305.0

《
大学问·明清经济史讲稿
》
售價:NT$
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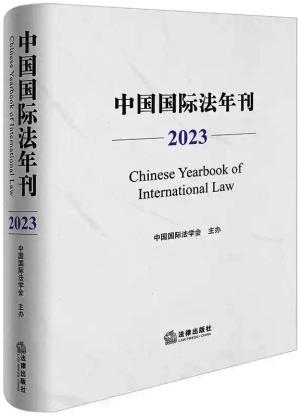
《
中国国际法年刊(2023)
》
售價:NT$
539.0

《
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
》
售價:NT$
295.0

《
迈尔斯普通心理学
》
售價:NT$
760.0

《
古典的回響:溪客舊廬藏明清文人繪畫
》
售價:NT$
1990.0

《
掌故家的心事
》
售價:NT$
390.0

《
孤独传:一种现代情感的历史
》
售價:NT$
390.0
|
| 編輯推薦: |
|
德文原版是在韦伯逝世后,在韦伯遗孀玛莉安妮的主持下,由两位德国学者赫尔曼和帕尔伊整理出版的。英译本则由著名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的开山鼻祖弗兰克?奈特于1927年译成英文。20世纪60年代初翻译家姚曾廙先生根据奈特的英译本将此书翻译成中文,以《世界经济通史》的书名出版。此次出版由著名经济学家韦森校完善。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马克斯?韦伯自1919年起在慕尼黑大学所作一系列讲演的笔记汇编。《经济通史》对整个世界经济演变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起源(这是韦伯毕生关注的课题)所作的全局性思考与宏观解绎,超越了前人的思想深度,对于我们现在探讨现代化的条件、前提、模式与道路,比较东西方文化,均有一-定的意义。
本书分别考察了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工矿业、商业及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经济导因与文化根源,探讨典型的日耳曼定居制度的传布、演变及其内容,也将日耳曼农村组织与苏格兰敞地制度、俄罗斯米尔(村社)土地制度、中国的井田制、印度的村落等作了比较研究,后指出:“关于原始人的经济生活确实无法作出任何概括的论断。如果我们就欧洲影响所未触及的人口中去寻求答案,我们总是发现彼此相差悬殊,而毫无一致之处”。
|
| 關於作者: |
马克斯?韦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韦伯初在柏林洪堡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即魏玛宪法)的起草设计。
译者简介:
姚曾廙,翻译家。
|
| 目錄:
|
英译者原序
德文版编者序
篇 家庭、氏族、村落和庄园(农业组织)
章 农业组织和农业共产主义问题
第二章 财产制度和社会集团
第三章 领主产权的起源
第四章 庄园
第五章 在进入资本主义以前西方各国农民的地位
第六章 庄园的资本主义发展
第二篇 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的工矿业
第七章 工业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
第八章 工矿业发展的阶段
第九章 手工业行会
第十章 欧洲行会的起源
第十一章 行会的瓦解和家庭工业制度的发展
第十二章 作坊生产――工厂和它的先驱者
……
第二十九 章合理的国家
第三十章 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变
|
| 內容試閱:
|
在近现代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作为一个思想深邃、视野广阔和见解独到的思想巨人,韦伯已对世界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界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有的论者把他视作为与马克思(Karl Marx)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齐名的三大思想家和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对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曾评价道:“在我看来,韦伯是站在西方文明发展的转折点上。他看到了古老体系的解体,并抓住了它的实质,而这是他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做到的。对于构思科学发展的方向,韦伯做出了比其他任何名人都更多的贡献。这个新的方向预示了把握即将到来的新社会的根本意义。”(转引自汉?诺?福根:《马克斯?韦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63页)
韦伯对西方思想界的巨大影响,首先是经由帕森斯译介韦伯的著作而在美国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韦伯的影响经由“出口转内销”的方式,重新回复到德国本土和欧洲学界。在德国和欧洲的学者重新认识到韦伯思想重要性的同时,一些德国学者也开始从韦伯本人的文本脉络、思想渊源、时代历史背景以及韦伯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精神历程等多维视角来重新解释韦伯,从而发生了一个“祛‘韦伯美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曾有人对帕森斯把韦伯塑造成“社会学家”的做法提出异议。这里,且不管是否应该把韦伯视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一个法学家、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经济史学家,但迄今为止,还似乎无人怀疑韦伯在人类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随着韦伯一些学术著作和生前的手稿的整理出版,以及随着国际学术界和文化界对韦伯思想研究的深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韦伯思想世界”。并且,这个韦伯思想世界是如此的博大纷杂、深邃繁复和扑朔迷离,以至于当代许多研究者都把韦伯的著作和有关韦伯研究的文献,视作为一种巨大的学术资源和理论思想的“采矿场”,而这部〈经济通史》,无疑也是韦伯存留在人类学术思想资源“矿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通史/经济学名著译丛》:
我们所知道的古老的凯尔特人的经济既然只限于畜牧方面,那么关于日耳曼农业的原始阶段,无论是从爱尔兰或者从苏格兰的共耕习惯中,也就得不出什么结论了。就我们所知,典型的日耳曼农业制度一定是开始于耕作和畜牧两者差不多有同等必要的一个时期。这种制度也许在恺撒(Caesar)时代方始渐渐出现,在塔西佗(Tacitus)时代则显然以粗放草田农业占优势。但是用这两位罗马作家中任何一位的记述来进行研究都是有困难的,其中塔西佗的华丽词藻,更使人怀疑。
同日耳曼土地制度成一鲜明对照的,是俄罗斯米尔(mir,村社)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虽在大俄罗斯占支配地位,但也只局限于内地各行政区,至于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却没有这种制度。俄罗斯米尔的村落是一种街道村落,其规模往往极其庞大,居民常不下三五千人之多。园圃和耕地都位于宅地的背后。新成立的家庭就安置在这排份地的末端。除耕地外,也有公共牧场可供利用。耕地划分成为大块,大块又划分成为长条地。同日耳曼土地制度不同,在俄罗斯长条地并不是硬性按户分配,而是在分配时把一户有多少人口或有多少劳动力一并加以考虑的。长条地既是按人口进行分配,所以这种分配决不会就此一劳永逸不再变更,而只能是暂时性的。法律规定每12年进行一次重新分配,但事实上这种重新分配进行得很频繁,往往每6年、3年甚至1年就进行一次。土地权属于个人,同家庭公社无涉,但却与村落有关。这种权利是永久性的;甚至祖先早在几代之前就已迁出米尔的工厂工人也可以还乡行使这种权利。反之,无论何人未经公社的许可,也不能离开公社,迁往他处。土地权可从定期重新分配的权利中表现出来。但所谓村民一律平等通常只是徒具形式,因为进行重新分配所需要的多数几乎是永远得不到的。凡人口增长率大的家庭固然赞成重新分配,但是却也有不利于他们的其他利害关系。米尔的决议仅仅在名义上是民主的,而事实上往往是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作出决定的。一些单个家庭往往因缺粮而对农村资产阶级或“富农”负有不同程度的债务,因而这些农村资产阶级便凭靠借贷关系控制了无产者群众。重新分配问题一旦发生,他们就要看究竟是让他们的债务人继续穷困下去,还是让他们多得到一点土地,哪一种做法对自己有利,便根据哪一种做法来操纵村中的决议。
关于米尔的经济作用,直到这个制度在俄罗斯瓦解时止,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它同个人主义的农村组织截然不同,乃是经济生活的救济手段;并且把每一个迁徙出去的工人可以回乡要求一份土地的权利,看作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一方面虽承认这会成为农艺方法和其他方面进步的障碍,但是又认为土地权迫使每一前进都要把每一个人包括进去。反对他们的人则无条件地把米尔看作是进步的障碍和反动的沙皇政策有力的支柱。
社会革命的力量在20世纪初期具有威胁性的发展,终于导致米尔的瓦解。斯托雷平在1906-1907年的土地改革法中给予农民以这样的权利:准许农民在规定的条件下退出米尔,并得要求他们所领受的那一部分土地嗣后免予重新分配。退社成员的那一份土地必须是连在一起的整块土地,从而在原则上像阿耳高的圈地一样,把农民分散开来,使他们分别居住在自己持有地的中央,单独地进行经营。于是沙俄内阁总理维特所渴望的米尔的瓦解终于实现了。自由主义的各政党始终不敢作这样的主张,或者像立宪民主党人一样,不敢相信改革土地制度的可能性。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使比较富裕的农民,也就是拥有大量资金以及按家庭成员比例来说占有较多土地的那些农民,退出了米尔,于是俄罗斯的农民就分成为两个阶级。一个是富有的大农场主阶级,他们退出了米尔而转向个体农场制;另一个是被抛在一边的为数大得多的农民,他们本来占有的土地就很少,现在又被剥夺了重新分配的权利,以致绝望地陷于农村无产阶级的地位。后者仇恨前者,把他们看作是米尔的神圣法律的破坏者;而前者则成为现行制度的无条件的支持者,要不是其间发生了世界大战,他们未始不会给沙皇制度以新的支持和“武装保卫”。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