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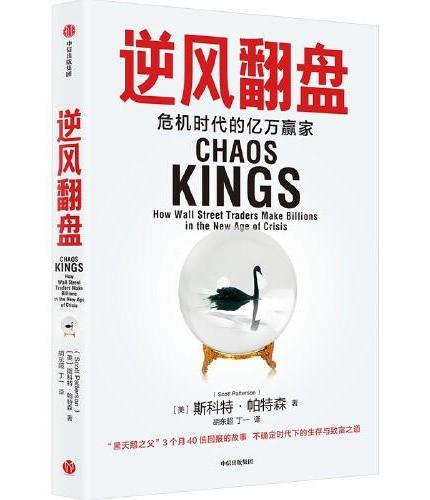
《
逆风翻盘 危机时代的亿万赢家 在充满危机与风险的世界里,学会与之共舞并找到致富与生存之道
》
售價:NT$
6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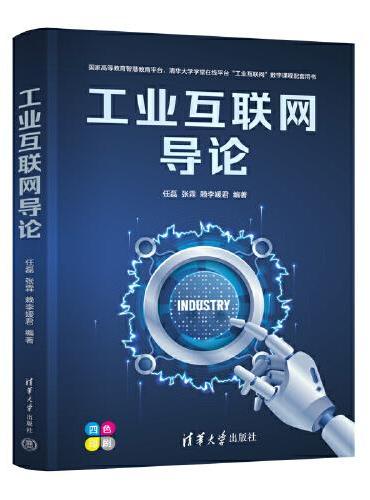
《
工业互联网导论
》
售價:NT$
445.0

《
孤独传:一种现代情感的历史
》
售價:NT$
390.0

《
家、金钱和孩子
》
售價:NT$
2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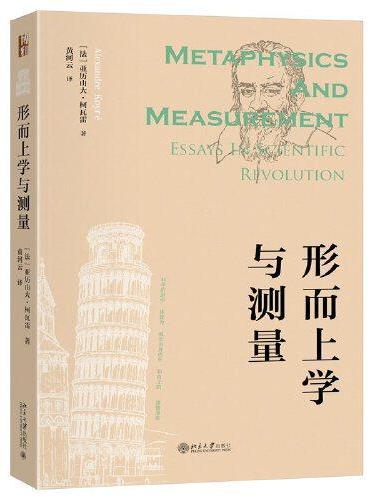
《
形而上学与测量
》
售價:NT$
340.0

《
世界航母、舰载机图鉴 【日】坂本明
》
售價:NT$
340.0

《
量价关系——透视股票涨跌脉络
》
售價:NT$
340.0
![创伤与记忆:身体体验疗法如何重塑创伤记忆 [美]彼得·莱文](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46645.jpg)
《
创伤与记忆:身体体验疗法如何重塑创伤记忆 [美]彼得·莱文
》
售價:NT$
295.0
|
| 編輯推薦: |
一个时代的童年“老照片”
“我们小时候……”长辈对孩子如是说。接下去,他们会说他们小时候没有什么,他们小时候不敢
怎样,他们小时候还能看见什么,他们小时候梦想什么……翻开这套书,如同翻看一本本珍贵的童年老照片。老照片已经泛黄,或者折了角,每一张照片讲述一个故事,折射一个时代。
一套大作家写给小读者的儿时回忆
王安忆、迟子建、苏童、叶兆言、毕飞宇、张炜、郁雨君……作家们没有美化自己的童年,没有渲染贫困,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从童年记忆中汲取养分,把童年时的心灵感受诉诸笔端。
一套适合家长与孩子共读的名家美文
我们希望,少年读了这套书可以对父辈说:“我知道,你们小时候……”我们希望,父母们翻看这套书则可以重温自己的童年,唤醒记忆深处残存的儿时梦想。
|
| 內容簡介: |
《文学少年》由著名作家叶兆言写就,是一本主要由作者本人的童年回忆选编构成的散文集。由于作者本是文学大家的家庭,所以童年趣事中不但有自己,更有一个家族的回忆。作者文笔举重若轻,大事写来也轻巧无比,十分具有可读性。
记忆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叶兆言
|
| 關於作者: |
|
叶兆言,1957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著有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太顽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叶兆言文集》(七卷)、《叶兆言作品自选集》等。
|
| 內容試閱:
|
编者的话:大作家与小读者
(我们小时候序言)陈丰
“我们小时候……”长辈对孩子如是说。接下去会说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我们小时候不敢怎样,我们小时候还能看见什么,我们小时候梦想什么……翻开这套书,如同翻看一本本珍贵的童年老照片。老照片已经泛黄,或者折了角,每一张照片讲述一个故事,折射一个时代。
很少人会记得小时候读过的那些应景课文,但是课本里大作家的往事回忆却深藏在我们脑海的某一个角落里。朱自清父亲的背影、鲁迅童年的伙伴闰土、冰心的那盏小桔灯……这些形象因久远而模糊,但是永不磨灭。我们就此认识了一位作家,走进他的世界,学着从生活平淡的细节中扑捉永恒的瞬间,然后也许会步入文学的殿堂。
王安忆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记忆也是,谁的记忆谁有发言权,谁让是我来记忆这一切呢?那些沙粒似的小孩子,他们的形状只得湮灭在大人物的阴影之下了。可他们还是摇曳着气流,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与描画着他人记忆的图景”。如果王安忆没有弄堂里的童年,忽视了“那些沙粒似的小孩子”,就可能没有《长恨歌》这部上海的记忆,我们的文学史上或许就少了一部上海史诗。儿时用心灵观察、体验到的一切可以受用一生。如苏童所言“童年的记忆非常遥远却又非常清晰”。普鲁斯特小时候在姨妈家吃的玛德莱娜小甜点的味道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由此产生了三千多页的长篇巨著《追寻逝去的时光》。苏童因为对儿时“空气中漂浮的化工厂樟脑丸的气味”和“雨点落在青瓦上清脆的铃铛般的敲击声”记忆犹新,因为对苏州百年老街上店铺柜台里外的各色人等怀有温情,他日后的“香椿树街”系列才有声有色。汤圆、蚕豆、当甘蔗啃的玉米秸……儿时可怜的零食留给毕飞宇的却是分享的滋味,江南草房子和大地的气息更伴随着他的写作生涯;迟子建恋恋不忘儿时夏日晚饭时的袅袅蚊烟,“为那股亲切而熟悉的气息的远去而深深地怅惘着”,她的作品中常常漂浮着一缕缕怀旧的氤氲。
什么样的童年是美好的?生长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动乱时期的中国父母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团花似锦的童年。“在漫长的童年时光里,我不记得童话、糖果、游戏和来自大人的过分的溺爱,我记得的是清苦,记得一盏十五瓦的黯淡的灯泡照耀着我们的家,潮湿的未浇水泥的砖地,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苏童的童年印象很多人并不陌生。但是清贫和孤寂却不等于心灵贫乏和空虚,不等于没有情趣。儿童时代温馨的记忆是玩过什么。那个时代玩具几乎是奢侈品,娱乐几乎被等同于奢靡。但是大自然却能给孩子们提供很多玩耍的场所和玩物。毕飞宇和小伙伴们举行不定期的“桑树会议”,每个屁孩在一棵桑树上找到自己的枝头坐下颤悠着,做出他们的“重大决策”;辫子姐姐的宝贝玩具是蚕宝宝的“大卧房”,半夜开灯看着盒子里“厚厚一层绒布上一些小小的生命在动,细细的,象一段段没有光泽的白棉线,头上顶着一小点黑,蹲在那里看蚕宝宝吃桑叶。好几条伸直了身体,一齐对准一张叶子发动‘进攻’,叶子边有趣地一点点凹进去,弯成一道波浪形。”那份甜蜜赛过今天女孩子们抱着芭芘娃娃过家家。
热闹的大概要数画家黄永玉一家了,用他女儿黑妮的话说“我们家好比一只满近似诺亚方舟载着动物的的大船,由妈妈把舵。跟妈妈一起过日子的不光是爸爸和后来添的我们俩,还分期分段捎带着小猫大白、荷兰猪土彼得、麻鸭无事忙、小鸡玛瑙、金花鼠米米、喜鹊喳喳、猫黄老闷儿、猴伊沃、猫菲菲、变色龙克莱玛、狗基诺和绿毛龟六绒”,这家人竟然还从森林里带回家一只小黑熊。这只大船的掌舵人张梅溪女士让我们见识了上世纪50年代小兴安岭,走进森林动物世界。
物质匮乏意味着等待、期盼。比如等着吃到一块点心,梦想得到一个玩具,盼着看一场电影。哀莫大于心死,祈望虽然难耐,却不会使人麻木。渴望中的孩子听觉、嗅觉、视觉和心灵会更敏感。“我的童年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我的少年也是在等待中度过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我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忍受力。我的早熟一定与我的等待和失望有关。在等待的过程中,你内心的内容在疯狂地生长。每一天你都是空虚的,但每一天你都不空虚。”毕飞宇在这样的期待中成长,他一年四季观望着大地变换着的色彩,贪婪地吸允着大地的气息,倾听着“-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没有他少年时在无垠的田野上的守望,就不会有他日后《三姐妹》、《平原》等乡村题材的杰作。
而童年留给迟子建的则是大自然的调色板。她画出了月光下白桦林的静谧、北极光令人战栗的壮美还有秋霜染过的山峦……她笔下那些背靠绚丽的五花山“弯腰弓背溜土豆的孩子”让人想起米勒的《拾麦穗》。莫奈的一池睡莲虚无缥缈,如诗如乐,梵高的向日葵激情四射,如奔腾的火焰。可哪个画家又能画出迟子建笔下炊烟的灵性:“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飘渺。无云的天气中,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的长裙下飘逸着的流苏。”
所以毕飞宇说:“如果你的启蒙老师是大自然,你的一生都将幸运。”
作家们没有美化自己的童年,没有渲染贫困,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从童年记忆中汲取养分,把童年时的心灵感受述诸笔端。
如今我们用数码相机、iPad、智能手机不假思索地拍下每一道风景、每一个瞬间、每一个表情、每一个角落、每一道佳肴,然后轻轻一点,很豪爽地把很多图像扔进垃圾档。我们的记忆在泛滥,在掉价。几十年后小读者的孩子看我们的时代,不用瞪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发呆,遥想当年。他们有太多的色彩斑斓的影像资料,他们要做的是拨开扑朔迷离的光影,筛选记忆。可是今天的小读者们更要靠父辈们的叙述了解他们的过去。其实精湛的文本胜过图片,因为你可以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
我们希望少年读者读了这套书可以对父辈说:“我知道,你们小时候……”,父母们翻看这套书则可以重温自己的童年,唤醒记忆深处残存的儿时梦想。
童年印象,吉光片羽,隽永而清新。
祠堂小学
我在农村念过两年小学,其中有大半年是在村祠堂小学度过。祠堂小学顾名思义,是一极小的祠堂改建的。就一间教室,一个老师,门口挖了个坑,埋上一口大缸,中间隔一块木板算是男女厕所。大约三十名学生,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
老师大约三十多岁,胸前挂着哨子,上课下课,十分潇洒地吹几声哨子。他长得很白净,见了大姑娘小媳妇,眼睛顿时发亮,常常忍不住说几句荤话,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小学门前是生产队的打谷场,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有一次正上着课,老师的媳妇找来了,把他拉到打谷场上训话,一训就是半天。早过了下课时间,学生们在教室里自然不肯老实,除了不大声喧哗,什么调皮捣蛋的事都敢干。黑板上被涂抹得一塌糊涂,画了只大乌龟,几句标语似的下流话后面跟着好大的感叹号。的一把扫帚和一个铁皮小桶放在了虚掩的门上。老师的媳妇火冒三丈,训起话来没完没了,老师一头一脸低头认罪的模样,正在教室里的学生早被他忘到九霄云外。
做好的圈套迟迟派不上用场,等得不耐烦的学生黔驴技穷,终于大叫:
“老师,我们肚子饿了。”
老师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奔过来,一边吹哨子,一边往教室里冲。铁皮小桶咚的一声砸在地上,那把扫帚非常准确地落在他头上。所有的学生快活地大笑,老师的年轻漂亮媳妇也笑,老师一边生气,一边也乐呵呵地傻笑。
我那时仍然算是三年级的学生。当时正是“文革”激烈的年头,我父母在同一天里双双进了牛棚,转眼间我成了无人管教的野孩子,便避难到了农村的外祖母家。既然是避难,也顾不上许多。三年级是祠堂小学的学历,于是我不得不做留级生,屈尊再读三年级。
上课要教的内容我似乎都懂。老师同时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一年级做算术,二年级写毛笔字,三年级大声地朗读课文。教室里永远乱糟糟,永远生气勃勃。老师仿佛是乐队的指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条不紊安排着一切。祠堂小学没什么太较真的事,出点小差错也无妨。老师严格起来,学生随便笑一笑他都会发火,马虎的话,学生上课时,跑出去撒尿拉屎也没关系。常常有学生很潇洒地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来,急匆匆跑出去,屁股撅多高的,光天化日之下,大模大样地在离教室不远的茅坑里方便。
教室里的学生叫道:“喂,你屁股都让人看到了!”
那边不服气地说:
“看到就看到,你又不是没有。”
有时老师上着课,忽然心血来潮,便把我叫到侧面的厢房里。那是老师简陋的办公室,放着一张课桌,一把椅子,桌上堆着作业本,一盏油灯。老师将作业本往边上挪挪,摊开了象棋,拿掉自己的一个车,然后和我厮杀,不杀得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绝不罢休。有时棋下多了,影响他批改作业,他一本正经地改出几个样本,指使我依葫芦画瓢,照着他的样子改。像抢什么似的,不一会儿工夫就把作业改完,火烧火燎地发还给学生,然后接着下棋。
我的棋艺很快有了长进,先是承让一个车,再下来是让马,到了后来,不用让一子,我和老师下棋也竟然互有胜负。老师是小孩脾气,不能输也不能赢,赢了喜欢乘胜追击,轻轻哼着“宜将剩勇追穷寇”,眉飞色舞。输了当然不肯服气,一遍遍重来,脸色沉重地将棋子重新放好,走到教室里,吹吹哨子,“下课了,下课了,”再回来,看着棋盘说:
“好,再来一盘,决一雌雄。”
于是昏天黑地乱杀一气,一直杀到我外祖母找来。
老师终于吃了批评,谁批评了他,我始终不曾知道。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脸色深沉地说:
“我们再下后一次,以后不下了,省得人家乱说话。”
这一盘棋下了很长时间,临了到底是谁赢了,已经记不清。我记得清楚的是,这以后,我再也没和老师下过棋。事实上,我从此也就失去了下象棋的兴趣。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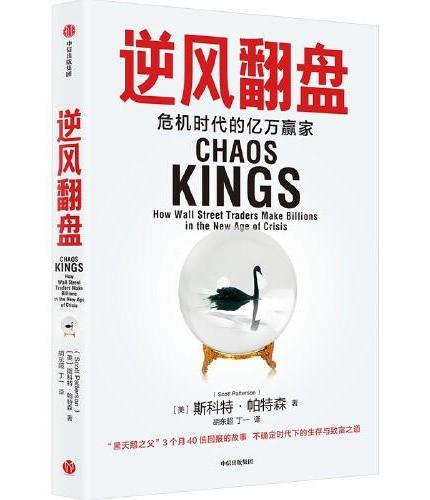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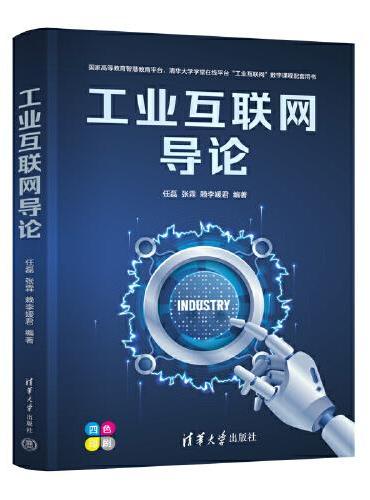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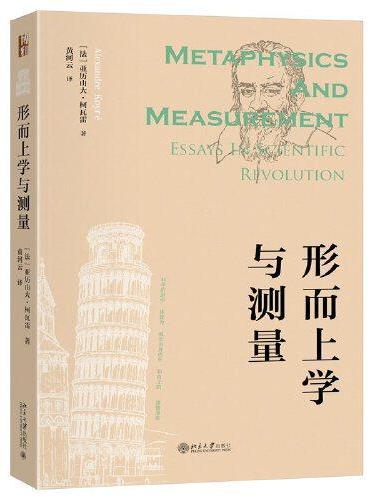


![创伤与记忆:身体体验疗法如何重塑创伤记忆 [美]彼得·莱文](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4664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