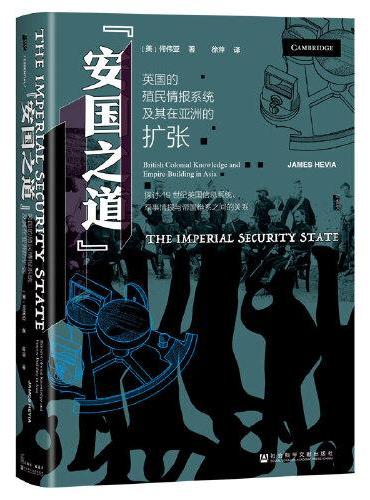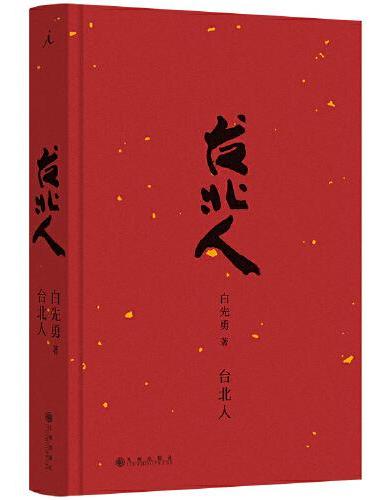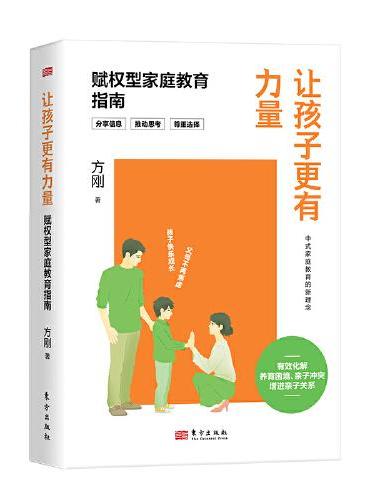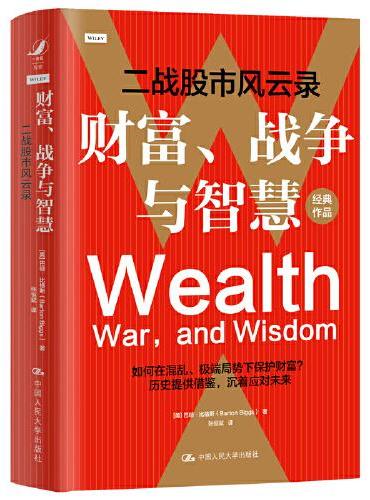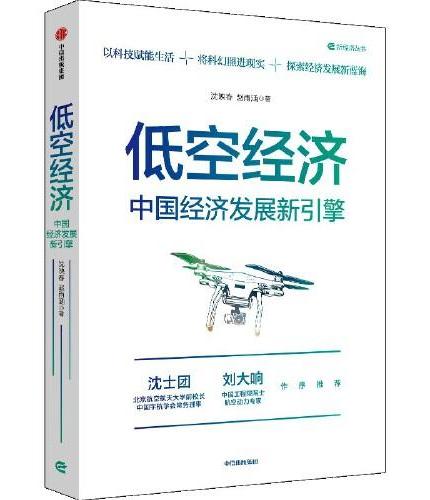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甲骨文丛书· “安国之道”:英国的殖民情报系统及其在亚洲的扩张
》 售價:NT$
403.0
《
台北人(2024版)
》 售價:NT$
398.0
《
万千心理·成人情绪障碍跨诊断治疗的统一方案:应用实例
》 售價:NT$
602.0
《
让孩子更有力量:赋权型家庭教育指南
》 售價:NT$
305.0
《
白夜追凶(上下)
》 售價:NT$
500.0
《
财富、战争与智慧——二战股市风云录
》 售價:NT$
602.0
《
纳特·特纳的自白
》 售價:NT$
383.0
《
低空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
》 售價:NT$
403.0
內容簡介:
对读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部长篇巨著都是一次终生难忘的阅读体验。作家的一生也和他的小说一样,从内到外充满了戏剧性,令人为之扼腕。安德里亚斯?古斯基这部传记作品是25年以来德语文学界的部陀氏传记。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目錄
引子 / 003
內容試閱
去世与封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