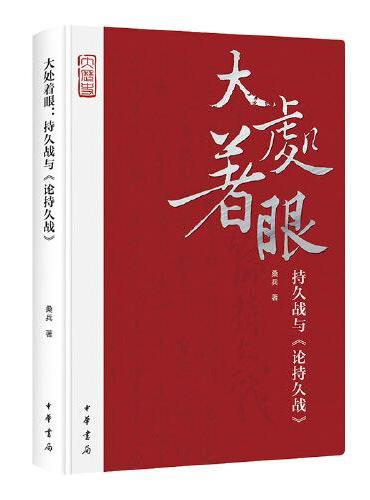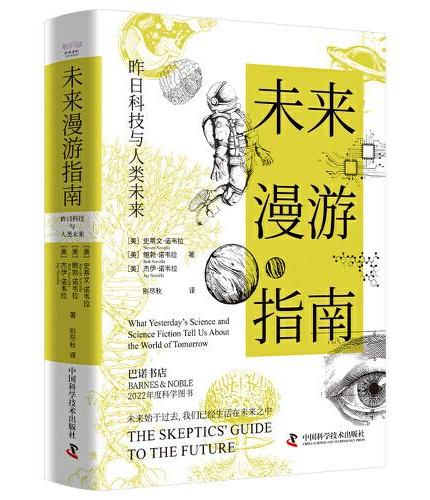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天生坏种:罪犯与犯罪心理分析
》
售價:NT$
445.0

《
新能源材料
》
售價:NT$
290.0

《
传统文化有意思:古代发明了不起
》
售價:NT$
199.0

《
无法从容的人生:路遥传
》
售價:NT$
340.0

《
亚述: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的兴衰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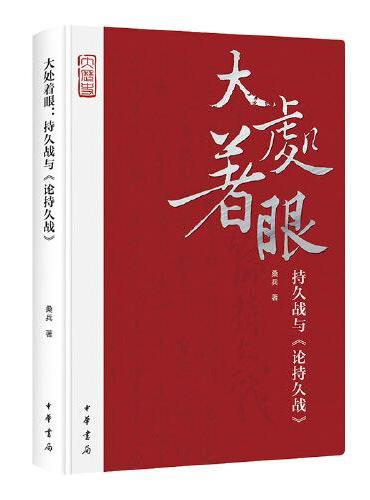
《
大处着眼:持久战与《论持久战》
》
售價:NT$
390.0

《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采煤机智能制造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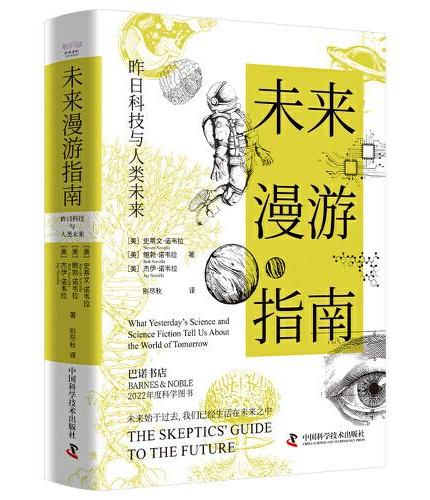
《
未来漫游指南:昨日科技与人类未来
》
售價:NT$
445.0
|
| 編輯推薦: |
★斩获多项大奖、台湾实力派作家郭强生散文代表作。白先勇、席慕蓉、王德威、骆以军等诚挚推荐!堪称《断代》之后冲击人心的诚恳之作。
★《何不认真来悲伤》荣获多项文学大奖。某瓣评分高达8.6。尚未出版,已火遍文学粉丝圈。
第40届金鼎奖·文学图书奖;
2015开卷好书奖·中文创作年度好书;
2016台湾文学金典奖。
★被誉为“华语当代文学创作书写的新页”,读者感叹“这是我继张爱玲之后看过的至为诚实的写作者”。这是一场对自我、原生家庭、孤独与爱的一场私人化献祭,因其自剖的姿态坦诚无私。关于背叛与自强、离弃与守护,关于亲人的衰老和离世,关于浮世过往与将来之种种,真相只有一个——悲伤。是私人回忆,也像是无数家庭的群像缩影。
★这是作者灵魂和真相搏斗后所留下的文字。家本该是好的港湾,他却成为汪洋中仅剩的漂流木。一个分崩离析的家,一个近乎破碎的自己,他用一支笔,一字一字,绘出重生的父子关系。写到尽头,终于和家人和解。
★并非得到了爱才让我们成为一个幸福或完整的人,更重要的其实是,在发现自己被爱蒙蔽、或失去了爱之后,我们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
| 內容簡介: |
当浓浓的爱意闪烁着星火,无从抽离的心境欢乐如昨时,原本温暖的家庭在纷繁的压迫与纠葛中展开了一场令人撕裂的对决:远走他乡的哥哥,溘然长逝的母亲,晚年罹患阿兹海默症、被骗光所有钱的父亲,而他则开始了一段无法停止的两地奔波的岁月……
这是郭强生对自我、孤独、原生家庭、爱的一场非常私人化的献祭,记录人生沧桑之中的阵痛与印记、挣扎与困顿。因其自剖的姿态坦诚无私,故在一年内不但写出了五十年的故事,甚而将其晒干晾透成了斑斑印痕,动人心肺于无形中。寥寥数语,揉碎伤痛,在幽深的笔触里散发出温柔的气息。
|
| 關於作者: |
郭强生
生于1964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纽约大学戏剧博士,现为台湾东华大学英美语文学系教授。曾获时报文学奖、金鼎奖、台湾文学金典奖、开卷好书奖、九歌年度小说奖、金石堂年度影响力好书奖、台北国际书展大奖等。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说集《夜行之子》,长篇小说《断代》《惑乡之人》《寻琴者》,散文集《就是舍不得》《我将前往的远方》,文学论著《文学公民》等。
|
| 目錄:
|
春余:今生一场聚散已足够
何不认真来悲伤
你不知道我记得
总是相欠债
家,有时就不见了
请带我走
四十四
一个人面对就好
夏暮:我的一生献给你,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
母亲不像月亮,像太阳
一个外省家庭的由来
他们是怎样长大的?
失去的预感
婚姻的伤感
生死发肤
妈妈,我在湖南了
摇到外婆桥
冬噩:为什么总是家人,伤我深
微温阴影
谁在灯火阑珊处?
独角戏
说不出口的晚安
关于痛苦的后见之明
雾起:不过是陌生人
放不下
儿子与弟子
流离
一厢情愿的幸福
偿还
有一天我们都会老
霜降:青春让人惆怅
相逢不恨晚
过眼烟云
一段琴
消失的圣诞树
电影散场
岁月的尘埃
清明:所有的坚强都是不得已
谁配当亲爱的?
没那么简单
我不过是假装坚强
如果可以不再有后悔
悲伤是记忆的光
后记
悲伤,我全力以赴
|
| 內容試閱:
|
何不认真来悲伤
面对过往的幸福,对我而言,远比回忆悲伤更需要勇气。
逼视曾让我受伤的记忆,至少证明我不再惧怕面对。就算偶有暗影反扑,也只像是遥望对岸的浓雾。
在悲伤的回忆中,我才能保持一种战斗的姿势,在空灭颓亡来临前。
幸福的记忆却让我感觉软弱,因为发现自己曾经对生命的流逝毫无警觉,总要等到它成为记忆后才懂得,那就是快乐,而当下只道是寻常。
中年后不敢多想那些无忧的过去。无忧源自无知,不知道烦恼有父母在顶着,不知道何为生老病死,不懂得无人共享的快乐其实不算快乐……
也因此,快乐的回忆只能点到为止,否则就要惊动了失落与遗憾。
偏偏总有久远的往事偷渡登岸。
翻开了堆放已久的积灰相簿,企图捕捉那其实已很遥远的、我们曾经一起去拍的全家福,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那时,我们总是为了拍全家福专门跑去照相馆。除了其中一次是因为哥嫂带着初生的女儿首次回台,连年近九十的外公都出动了,其他去照相馆拍照的动机背景我已一概模糊。
或许都只是临时起意。那总有个提议的人吧?如果要我猜,准是母亲。
母亲喜欢玩相机,或许说,她喜欢记录家人的生活。台湾家彩色冲印照相馆到底是哪间?这些年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形。但据母亲告诉我的,真正的家是早在一九五几年的名为“虹影”的照相馆。母亲是他们当时招考录取的位员工,担任会计职务。老相簿里还有摄影师为母亲拍的沙龙照。那时的母亲真是美。
继续翻阅相簿,发现都是母亲掌镜的时候居多。记忆中家里的台相机颇难操作,要将一个长方匣捧在胸前,从上往下看进匣里对焦,光圈和速度全靠手调,只有母亲会用。家里其他三个男生爱笑那是老古董,该丢了。等到父亲接触到拍电影的工作,有一天回家告诉我们,剧照师都还是用这一款,说是比起后来的单反,它的画质好太多,那时我们才知那相机是属于“专业人士用”的,从此对它刮目相看。
想必是我们懒于学习操作,才会忽略了该让母亲多当模特儿而非总在掌镜。是不是因为这样,母亲才总会兴起去照相馆留影的念头呢?
* * *
不仅拍照总是母亲的工作,连全家旅游也向来是母亲在规划。
说起来,真正一家四口出游也就那一次,去日月潭。那年哥哥高一,我还在上幼儿园。之后哥哥就再也没有跟我们一起去旅行了。一家人留下了难得的户外合影,每一帧的场景时空我仍印象清晰。有一张是我们全翻滚在草坪上,将那台专业级相机设定好自拍模式,并很有创意地倾斜放置,形成对角线的构图。而另一张是造访“毛王爷”时当地导游为我们拍的。除了哥哥坚持不肯外,我们全都穿戴起高山族的服装。关于那次旅游,更深的印象是我一路晕车呕吐,到了教师会馆已手脚僵冷。偏偏都没空房了,我们一家睡的是地下室的通铺。
想起来还是欢乐。的一次合家欢。之后在溪头、垦丁、花莲、纽约、费城、华盛顿,总是三人行。
两个孩子都在异地他乡的日子,没想到父母还是去照相馆拍过几帧二人合影。那时的母亲心里在想什么呢?
* * *
小学时次读到《蒋碧薇回忆录》,书里附图中有许多是她任画家丈夫徐悲鸿为她画的肖像,便以为画家都爱为妻子或者家人画像。但父亲这辈子只为母亲画过两张油画像。更不用说,我和哥哥自然是没份的。母亲对此难免心有遗憾,却总另找借口表达不满:“一直希望你为我父亲画张像,人都死了你还是没动过笔!”
毕竟比起照片来,画像无疑更有纪念价值。至于母亲那两张画像,都是完成于新婚后。一幅画中她穿着水绿旗袍,但该画因台风泡水,油彩早已龟裂破损,却仍被母亲以玻璃框裱起挂在卧室。另一幅画的则是还留着少女马尾的她。
现在那张人像哪里去了?
我竟然这么多年都没注意到它已下落不明。
* * *
父亲盯着电视屏幕上的足球赛目不转睛,我坐在一旁的板凳上打量着他。过了一会儿我也把视线移到了电视上逐球的一群小人,只是放空注目,为了打发掉父子间像这样完全无言共处的时间。
已经六七年了,我们都早已习惯这种形式上的亲情。已经很久,对于彼此都存在着不撕破脸就好的应对方式。
我仿佛知道整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却不愿接受。
一开始先是发现,与哥哥一同出席父亲的画展揭幕仪式,父亲怎么只向众人介绍这位“在美国当工程师”的大儿子,对于他身旁在台湾当教授的另一个儿子却略过不提?又有一次,忘了为什么细故争执,扯到了他的一位学生,父亲竟然对我说出了“我跟他更像父子”这样的话。
那年,发现八十五岁的他跟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交往,我一再提醒他那女人肯定没打什么好主意,父亲竟用轻蔑的口吻回我一句:
“这是我们男女之间的事,你懂什么?”
四十四岁那年搬出了老家,把家让给了他与那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但仍不敢住得太远,毕竟在台湾父亲没有任何亲友,跟他“情同父子”的学生们,哪个不是拿到学位就不再出现了?
那时觉得父亲仍需要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是我更需要他。母亲已过世,而与我年纪相差十岁的手足,从来也算不上亲近。我赖在父亲身边,怕离得太远,就会失去自己跟“家”这件事的后联结。
一年多前父亲开始出现轻度失智的症状,每周日我回“家”一趟,陪他上上馆子。问他什么,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或“不记得了”,语气却很平静。有时我心中会暗自怀疑(或期望),他的不记得会不会是伪装的?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印象,母亲经常为他爱拈花惹草费神又伤心。惯爱偷吃的男人擅于伪装、说谎与耍赖,也许老来可用来自我保护,让他不想见的人无法靠近。
因为缺少互动,究竟失智程度是在恶化,还是药物控制有帮助,我无法判断。问那女人父亲现在的情况如何,她总说好得很。直到过年时那女人外出,我才发现她一直在盗领父亲的存款。
以前我从不过问父亲的财务状况,怕让已有心结的父子之间,徒增了更多的不信任。但我发现父亲名下已经没有任何定存的钱了。我还发现,那女人把失智症与高血压的药藏了起来,有两个月没给他服用。
我决定跟那女人开战。
这回父亲完全不像失智的病人,吼得雷霆万钧:“这就是我要的生活,你是什么人敢来干涉我的生活?”
他并非失智到认不得我是谁,但我恍然惊觉,亲情与家人对他而言,会不会只是他人生中曾经走岔的一段路?
* * *
母亲过世第二年,有一次我与好友餐聚,散会前她像忆起了什么趣闻似的,转身小声跟我说:“我一直忘了告诉你,你那时候还没回台任教,有一天我很意外接到你妈妈的电话,她跟我说,她很不快乐。”
我当下感觉像被突然宣判,我的母亲不是死于癌症,而是因我的疏忽意外致死。“你怎么到现在才跟我说这件事?”我激动得浑身发抖。
对方无辜地眨着眼睛说她忘了。在那之前,我并非不知母亲不快乐,只是没想到,她有那么不快乐,不快乐到会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以为她一定会把她的心声传到我耳朵里。
记忆中,母亲那时偶尔会在奇怪的时间打越洋电话来。台北时间凌晨四五点,我问她怎么不睡觉,她说睡不着。母亲说话总是嗓门很大,只有在那几通电话中,我听到她细弱如小女孩的声音。
我只能安慰她别胡思乱想。
我考上大学那年,母亲次罹癌,身体一下子垮了,体重从以前的五十五公斤,到只剩不到三十九公斤的皮包骨(后来十几年始终如此)。她一直都在抗病的抑郁低潮里,难得见她真正开心的时候。
除了我将启程返台任教的几天前,她打来的那通电话。那次她心情极好,对着答录机说个不停,念完了当天报纸的头条新闻,还是等不到人的母亲后干脆对着机器唱了一首歌:“我有一帘幽梦,不知与谁能共……”
然而我终究没能接到那通电话。
答录机中的卡带被我取下,装进行李,但是还没等到有那个心情放来重听,母亲就在我返台次年病逝。
一直记着那留言的存在,却也不敢再碰。
这些年我一直会幻想着,如果接到电话,跟母亲可能会有怎样的对话?会不会发现也许跟在听答录机时一样,除了想哭,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已太习惯面对那个不快乐的母亲,偶尔开心的她反愈教我悲从中来。
回台前我原本是这么打算的,至少也回来住个一两年,不能像哥哥赴美后,三十几年来都只是浮云过境般回来吃几次饭就走人,连接父母去他美国的家中小住也一次都没有过。
回台却成了送母亲后一程。母亲第二次癌症来得意外且凶猛,从扩散到往生,前后不到五个月。
* * *
后一个母亲节,与母亲多年不和的哥哥从美国打来电话,我暗示他有空回来一趟,妈妈身体很不好。
他说他工作很忙。
“晚了怕来不及了。”我说完便挂了电话。
哥哥在外三十多年,在美国成家定居,和我们这个家甚是疏离,见面次数屈指可数。还有好几次,忘了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后竟以不欢而散收场。从母亲确诊到癌细胞扩散,她便一再叮嘱,别把她生病的事跟哥哥说。等医院发出母亲的病危通知,我不得不跟他说了实话,没想到他还是说他很忙。次日他拨电话到病房,我劈头就问:“机票订到了吗?”他说:“还没去订。”我气得大骂:“那你打电话来干吗?”
没赶上见母亲后一面,他却在告别式前夕说出了教我非常吃惊的话:“妈妈是被老爸磨死的。老爸当年为什么要回来?他不在的时候,老妈过得很好。他一回来把老妈的生活全毁了……”
母亲对哥哥隐瞒病情,难道因为她太了解自己的儿子,知道他是不会赶回来的?一旦说了,就会有期待,到时等无人影,情何以堪?
母亲走了,父亲老弱了,哥哥与这个家的距离早就很远了。只剩下我还在努力拼凑着许多仍然断裂的剧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