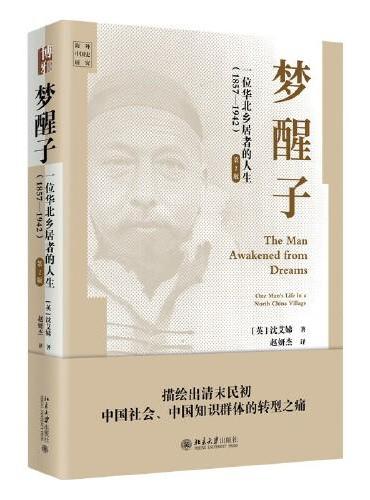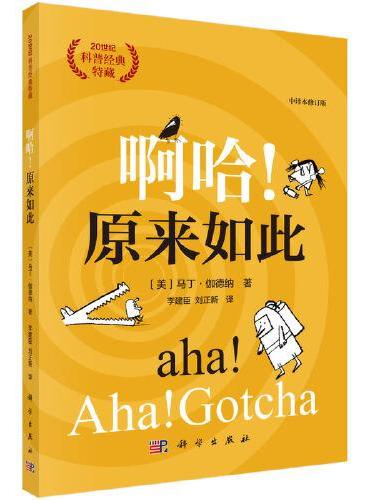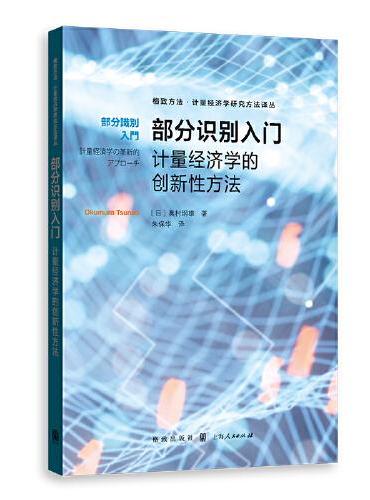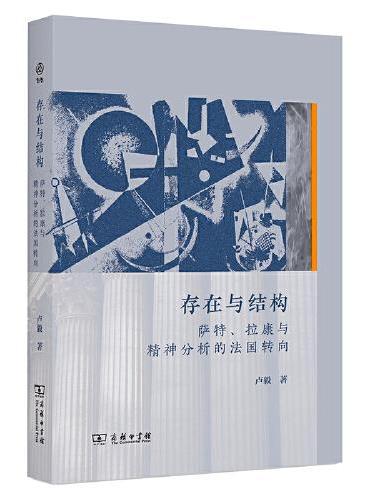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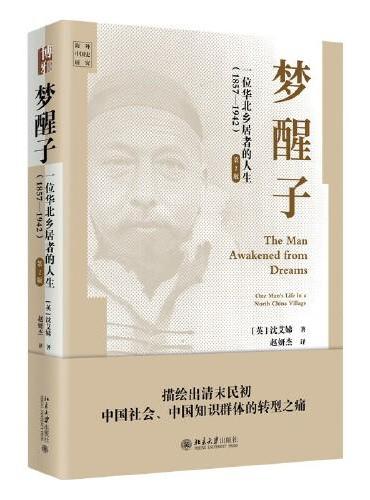
《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第2版)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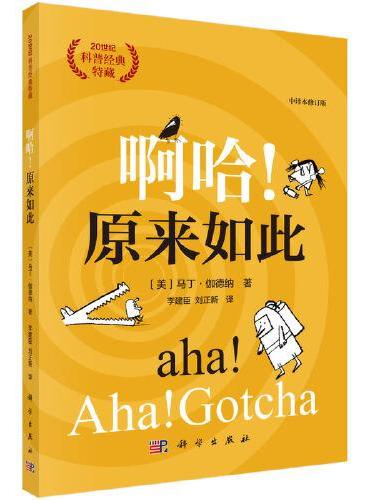
《
啊哈!原来如此(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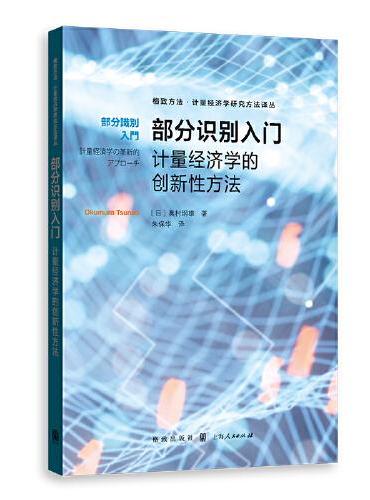
《
部分识别入门——计量经济学的创新性方法
》
售價:NT$
345.0

《
东野圭吾:变身(来一场真正的烧脑 如果移植了别人的脑子,那是否还是我自己)
》
售價:NT$
295.0

《
严复与福泽谕吉启蒙思想比较(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750.0

《
甘于平凡的勇气
》
售價:NT$
2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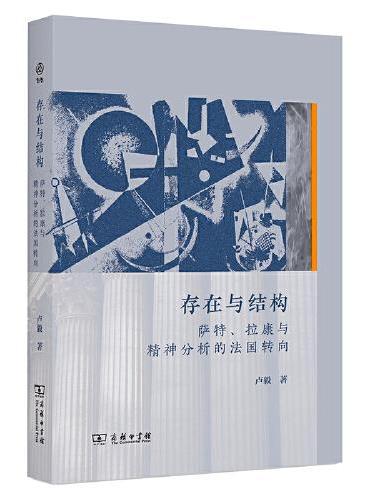
《
存在与结构:精神分析的法国转向——以拉康与萨特为中心
》
售價:NT$
240.0

《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与多模态技术应用实践指南
》
售價:NT$
495.0
|
| 編輯推薦: |
|
入选《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一线名师推荐,学生课外阅读经典匹配全学段,打通课内外,全面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和综合素质北师大教授郑海凌根据俄文原版翻译2000年《纽约时报》和《读者文摘》组织评选的“世界十大名著”位列第三名。
|
| 內容簡介: |
|
《童年》是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之一,讲述了他是如何在灰暗的生活中成长的故事。阿廖沙幼年丧父,跟随母亲和外祖母来到外祖父家生活,祖父专横暴躁,舅舅们自私冷漠,但有善良的外祖母、淳朴乐观的小茨冈、正直的老工人格里戈里始终给他带来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童年》展现了十九世纪俄国底层社会的生活画卷,歌颂了人性美,是苏联文学的里程碑。
|
| 關於作者: |
高尔基(1868—1936),前苏联作家、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学者。苏联文学创始人之一,被列宁誉为“无产阶级艺术杰出的代表”。其代表作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生动演绎了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生活的百态,也极致再现了高尔基卓尔不凡的一生,被誉为那个时代的艺术性史册。
郑海凌,著名翻译家,曾在军队和中国民航总局担任翻译,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译作有《童年》《母亲》《死魂灵》等。
|
| 內容試閱:
|
狭小的房间里,光线很暗。父亲直挺挺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蒙着白布,身子显得特别长。他的光脚露在外面,脚趾古怪地张开着;那双时常抚爱我的手一动不动地放在胸前,手指也是弯曲的;他那双时常乐呵呵的眼睛紧闭着,眼皮上盖着两枚圆圆的铜币;他那张和蔼的面孔变得乌黑,难看地龇着牙,看上去怪吓人的。
母亲穿着一条红裙子,跪在父亲身旁,正在用那把小黑梳子给我父亲梳头,把父亲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那把小黑梳子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常常用它锯西瓜皮。母亲给我父亲梳头的时候,嘴里不停地唠叨着,嗓音低沉、沙哑。她眼睛红肿,仿佛融化了似的,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里流下来。
外婆拉着我的手。她长得胖乎乎的,大脑袋,大眼睛,鼻子上皮肉松弛,令人好笑。外婆身子软绵绵的,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这时她穿着一身黑衣裳,也在哭,但她的哭跟我母亲不同,她总是伴随着我母亲哭,像唱歌似的,哭得很老练。她全身颤抖,使劲拉着我,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我向后扭着身子,躲在外婆身后,不肯朝前去。我心里害怕,同时又感到难为情。
我还从来没见过大人哭。外婆一再对我说的话,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快去跟你爹爹告别,往后你就见不到他了,他死了,乖孩子,他不该死啊,他还不到年龄……”
我刚刚大病初愈,才能下床走路。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生病期间,父亲照料着我,他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后来,他突然消失了高尔基三岁时,在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城患霍乱,父亲看护幼小的孩子,不幸染病而死。,外婆接替父亲来照料我。我外婆是个很古怪的人。
“你是从哪儿走来的?”我问外婆。
外婆回答说:
“从上头来,从下面来,我不是走来的,是搭船来的!在水上可不能走路这句话里的“上头”是指伏尔加河上游,“下面”是指下新城(后更名高尔基城),这些词在俄语中是谐音字。俄语中的“走来”和“乘船来”是不同的动词。此处孩子用词不当,外婆纠正他。,傻瓜!”
她这话真可笑,简直让人莫名其妙:我家楼上住着一些留着大胡子并且染了头发的波斯人,楼下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黄脸皮的加尔梅克族老头,是个卖羊皮的小贩。在楼梯的栏杆上可以玩滑滑梯,要是不当心摔倒了,就翻着跟头滚下去,这一点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这里哪儿来的水呢?全是哄弄人,前言不搭后语的,真叫人好笑。
“为什么说我是傻瓜?”
“因为你爱吵闹。”外婆说,她脸上也带着笑。
外婆说话语气亲切、快活,富有乐感。自从我天见到她,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此刻,我多么希望她快点带我离开这间小屋啊。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泪水,她的号哭,都使我感到新奇,使我惊恐不安。我次看见她今天这个样子。母亲平日神色很严厉,很少说话。她个子很高,牛高马大的,总是打扮得干净利索。母亲的身体很结实,一双强壮的大手有劲极了。可是现在,她似乎全身肿胀起来,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看上去令人难受,仿佛她的一切都乱了套。往日头发整整齐齐地盘在头上,像戴了一顶油光锃亮的大帽子,现在却披散在赤裸的肩头,滑落到脸上。她有一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不时摆来摆去,轻触着父亲那张沉睡的脸。我在房间里站着,站了好长时间,但母亲没有理睬我,甚至没有抬眼望我一下。她一直在给父亲梳头,不停地号哭,哽咽着,泣不成声。
几个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一名巡警站在门口朝屋里望了望,那巡警气呼呼地喊道:
“快点抬走!”
窗户上挂着一条深色的大披巾,代替了窗帘。披巾被风吹得鼓起来,恰如一张船帆。有一回,父亲带我乘小帆船游玩,忽然,响起一声霹雷。父亲笑了。他用双膝紧紧地夹住我,喊道:
“别怕,卢克父亲对幼小的高尔基的称呼,意为“葱头”。,没事儿!”
这时,母亲忽然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但立刻就坐下了,仰面躺下,头发铺散在地板上。她那张惨白的脸变得铁青,两眼紧闭着,像父亲那样龇着牙,用吓人的声音说:
“快关上门……把阿列克赛抱出去!”
外婆连忙把我推开,跑到门口,喊道:
“亲爱的街坊们,不要害怕,不要多管闲事,看在基督分上,快走开吧!这不是霍乱症,是女人临产。老爷子们,行行好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