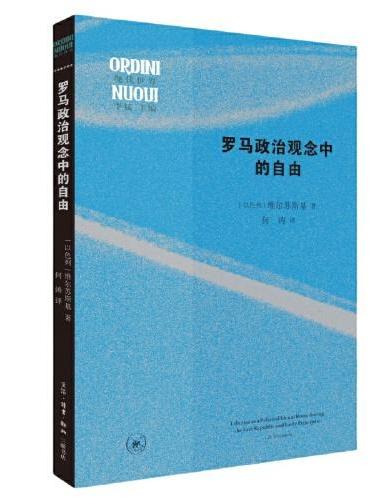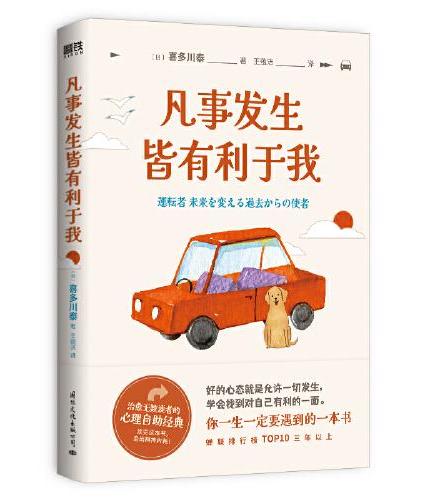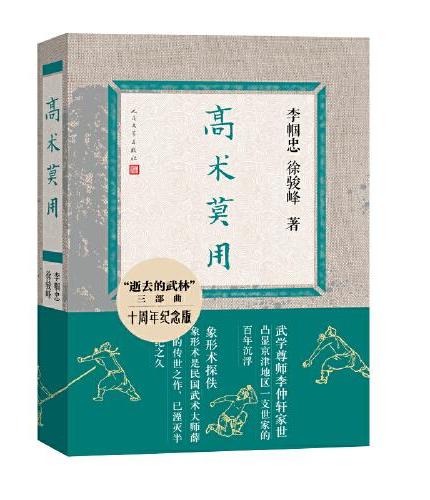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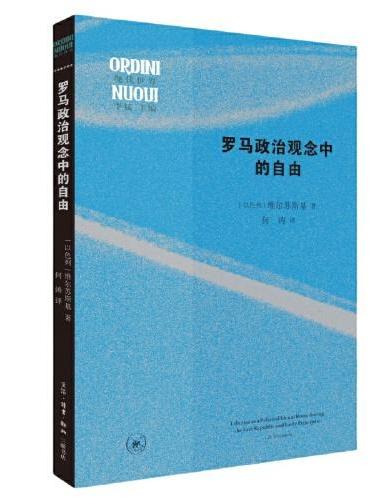
《
罗马政治观念中的自由
》
售價:NT$
230.0

《
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宠位厮杀
》
售價:NT$
2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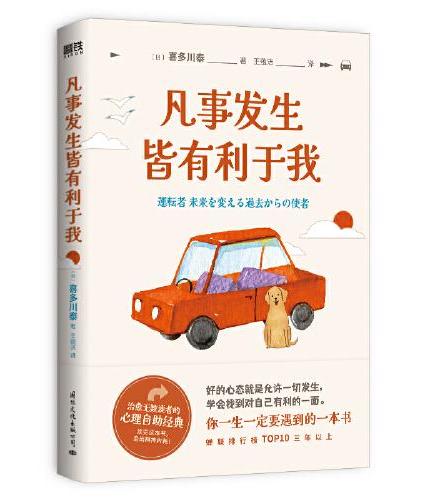
《
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这是一本读了之后会让人运气变好的书”治愈无数读者的心理自助经典)
》
售價:NT$
203.0

《
未来特工局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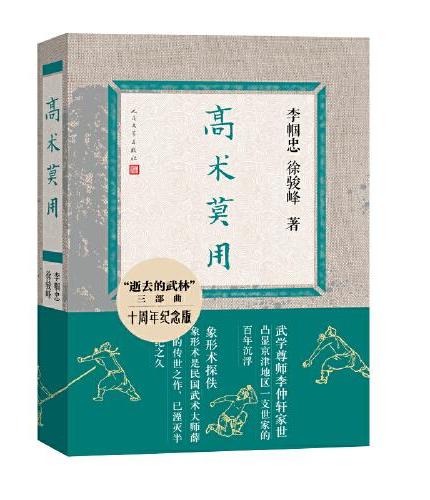
《
高术莫用(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续篇 薛颠传世之作 武学尊师李仲轩家世 凸显京津地区一支世家的百年沉浮)
》
售價:NT$
250.0

《
英国简史(刘金源教授作品)
》
售價:NT$
449.0

《
便宜货:廉价商品与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
》
售價:NT$
352.0

《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2024年新版)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
本书为“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之一。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纵古今,跨经纬,全面系统介绍中华历史上著名翻译家以及他们的翻译思想,选择他们代表性的译文,列出每位译者的译事年表,该文库积极回应国家文化战略,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册收录了著名翻译家刘半农的代表性译文,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前言、代表性译文和译事年表。前言包括刘半农生平介绍、翻译思想、对刘半农的研究、代表性译文选择的原因、对所选译文的介绍与研究等。第二部分为刘半农代表性译文。第三部分为刘半农译事年表,把刘半农所有的翻译实践活动按时间顺序排列,包括年代与发表渠道。
|
| 內容簡介: |
■作者简介
刘云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理事。著作包括《翻译批评研究》《翻译批评研究之路:理论、方法与途径》《葛浩文翻译研究》等。
总主编简介
许 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与法国文学。
郭国良,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协会理事。研究方向为当代英美文学、文学翻译。迄今已翻译出版40多部文学名作,译有菲利普?罗斯、石黑一雄等诺贝尔文学奖、国际布克奖作家的作品。
|
| 內容試閱:
|
导 言
鲁迅说:“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①] 他,就是刘半农(1891—1934),新文化运动先驱,我国著名的现代诗人、文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以其多方面的卓越成就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文学史和语言学史上占据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刘半农的名字前应冠以许多个 “家”,但称其为“杂家”合适不过。他一生兴趣广泛,研究工作涉及多个领域,如其弟刘北茂所言,“他所参加过的工作和活动而有著述的,择其重要者有下列各项:文学创作和翻译,文艺批评,语音学研究和仪器发明,中国文法研究,民歌收集与研究,方言调查,考古和历史语言研究,乐律及古代音乐史研究,编辑书报、字典以及艺术摄影等等”[②]。
一[③]
刘半农生于 1891年5月29日,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后改名复,初字半侬,后改为半农。1907年,刘半农以江阴考生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911年10月,常州府中学堂因政局动荡宣告停办,刘半农不得不终止学业。
1912年春,刘半农赴上海,在开明剧社任文字编辑,编译过剧本《好事多磨》,时而也充当演员。
1913年,经人介绍,刘半农进入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任编译员;10月在上海《时事新报·杂俎》发表百字小说《秋声》,揭露张勋部下镇压二次革命、荼毒地方的罪行,获该栏悬赏第 33次一等奖。
1917年5月1日,刘半农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夏末秋初,他受蔡元培之邀赴京,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
1919年4月21—25日,刘半农与北京大学代表蔡元培、朱希祖、马裕藻、钱玄同、胡适等一同出席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大会,负责拟定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经大会决议通过;同年,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本科讲师。
1920年1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大会,成立国语辞典委员会,刘半农被推选为委员;3—4月,受派遣赴欧洲留学,乘船抵达英国伦敦,入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8月9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她字问题》,首创“她”“牠”二字,作为第三人称女性和无生物代词;9月4日,作歌词《教我如何不想她》,后由赵元任谱曲;同年,入伦敦大学语音实验室工作。
1921年6月,刘半农从英国伦敦转赴法国巴黎,入巴黎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并在法兰西学院听讲。
1922年初,因实验语音学首创于德国,刘半农选择赴德国柏林继续学习语音学方面的知识。
1923年,刘半农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录该馆所藏我国敦煌写本中有关文学、语言、历史等方面的珍贵资料,时约半年。
1924年3月,刘半农的专著《四声实验录》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由蔡元培题签封面,吴敬恒、傅斯年作序;12月6日,法国巴黎语言学会召开常委会,经巴黎大学语音学院院长提名,刘半农被推举为该学会会员。
1925年3月17日,刘半农以《汉语字声实验录》与《国语运动略史》两篇论文及自行设计制造的测音仪器“音高推断尺”与“刘氏音鼓甲种”参加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答辩,获得优异评语并被授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4月15日,《法国文艺学院公报》宣布,《汉语字声实验录》获1925年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6月,刘半农由法国马赛启程回国;9月,刘半农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课程,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中法大学讲师,并积极筹建北京大学语音乐律实验室。
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爆发,刘半农当晚作“敬献于死于是日者之灵”的战斗诗歌《呜呼三月一十八》,表达对牺牲者的悼念之意及对当权者的愤慨之情;4月,其民歌体诗集《瓦釜集》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6月,其作品《扬鞭集》上卷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6月中旬,刘半农应邀担任《世界日报·副刊》主编;7月1日,其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出版;秋,刘半农兼任中法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讲授中国文法、语音学、法文戏曲,并任图书馆顾问;12月6日,由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刘半农任北京大学聘任委员会委员;同年,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本科讲师。
1927年10月1日,刘半农兼任北京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中国文法、语音学、法文戏曲、中国名著选读等课程;秋,因不满奉系军阀统治和长刘哲的作为,辞去所任国立各校的教职。
1928年4月初,刘半农与马衡同去日本,出席东亚考古学协会举办的学术会议;8月13日,中央研究院第三次院务会议议决,聘请吴稚晖、胡适、陈寅恪、赵元任、顾颉刚、刘复(刘半农)、林语堂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冬,刘半农和李家瑞合作,着手中国俗曲的研究整理工作。
1929年1月17日,刘半农被选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即北京大学)评议会候补评议员,由评议会议决,任图书委员会委员长、仪器委员会委员;当月,与钱玄同、刘大白等七人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名誉编审;6月15日,被聘为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委员;7月,应邀兼任北京辅仁大学教务长,赴南京办理辅仁大学董事会立案及恢复辅仁大学名称等事宜;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设图书馆委员会,刘半农被聘为该委员会委员;9月,刘半农两次出席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会议,被推选为北平图书馆建设委员会委员;11月4日,经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任评议会书记,兼任仪器委员会委员。
1930年4月28日,刘半农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5月25日,出席国立北平大学校务会议,继任第五届校务会议主席;5月31日,主持国立北平大学第三十九次校务会议,讨论向催索积欠经费等问题;夏,开始测试故宫收藏的古代乐器的音律;暑期,应北新书局之约,为高中生编写《中国文法讲话》;同年,将 1925年创制的“音高推断尺”改进为“简音高推断尺”,将“刘氏音鼓甲种”改进为“刘氏音鼓乙种”。
1934年6月19日,刘半农率助手离京赴西北一带调查方言,先后抵达包头、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等地;7月9日,因病返京;14日,入协和医院,被诊断为回归热,14时15分病逝。10月14日,北京大学的各级负责人、教职员、学生代表及北京各界代表共五百余人,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大礼堂为刘半农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主持,胡适、钱玄同、魏建功报告其生平与思想。
胡适致哀辞曰:
半农与我相处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回忆过去,我等同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寓今日第五宿舍之卯斋 ……今日回忆斯情,不胜留恋。又谓半农先生为人,有一种莫名其妙之 “热”处。共作事素极认真,其对于学术之兴趣极广博,故彼卒能成为歌谣收集家,语言学家,音乐专家,俗字编辑家。彼之成功,完全由于一“勤”字,兹有一例可证,当彼在世时,对于音乐感兴趣,然而喉不能唱,耳不能听,手不善弹,由此可见其天资愚笨,但伊并不因此灰心,终日以机械之方式,来作声音之探讨,结果不但对音乐能以讲通,且发明各种测量声音之器械,由此一点,足以代表半农一生治学之精神。[④]
钱玄同挽曰:
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情感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乱思想;曾仿江阴 “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溯在文学革命旗帜下,勋绩弘多,更于世道有功,是痛诋乩坛,严斥 “脸谱”。
自首建 “数人会”后,亲制测语音的仪器,专心于四声实验,方言调查,又纂《宋元以来俗字谱》,打倒烦琐谬误的《字学举隅》。方期对国语运动前途,贡献无量,何图哲人不寿,竟祸起虮虱,命丧庸医。[⑤]
二
刘半农一生致力于文学、语言学领域的探索和实践,“在文学革命、新文学创作、语言乐律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⑥]。1916年,他积极投身文学革命运动,开始在《新青年》发表《灵霞馆笔记》,逐步与鸳鸯蝴蝶派报刊分道扬镳。对改良文学,刘半农不仅有热情,更有行动的自觉。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把文学改良比为“做戏”,称“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⑦]。正是在这份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驱动下,他不计毁誉,身体力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干将。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的“四台柱”也颇为认同,在《伪自由书 ·后记》中曾写道:
到了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这时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烦闷,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⑧]
1917年5月、7月,刘半农接连在《新青年》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与《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两篇重要文章,极力赞成胡适提倡的文学改良之议,并为文学革命提出许多可贵的新见解,如:打破崇拜旧时文体的迷信,将古人作文的死格式推翻,脱离老文学的窠臼而建立新文学;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将诗的精神从诗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等等。1918年,为推动文学革命的发展,刘半农与钱玄同合作完成著名的“双簧信”,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归纳了封建文人反对新文学的种种荒谬言论,用文言文写了致《新青年》编者的信,再由刘半农以记者的名义,用白话文写出《复王敬轩书》,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谈及“双簧信”的影响,朱湘所言颇具代表性:“是刘半农的那封《复王敬轩书》,把我完全赢到新文学这方面来了。现在回想起来,刘氏与王氏还不也是有些意气用事;不过刘氏说来,道理更为多些,笔端更为带有情感,所以,有许多的人,连我在内,便被他说服了。将来有人要编新文学史,这封刘答王信的价值,我想,一定是很大。”[⑨]
刘半农的重要成就体现在新诗创作方面,代表性诗集有1926年出版的《瓦釜集》和《扬鞭集》。正如沈从文所言,“在新文学新方向上,刘先生除曾经贡献给年青人以若干诚实而切要的意见外,还在一种勇敢实验中,写了许多新诗”[⑩]。我们知道,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核在于革新,“在那个时期,对‘新’的追求有着革命性的意义,《新青年》的根本立场,更是出自于‘新’: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11]。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刘半农在新诗创作上以 “拓荒者的姿态”[12]积极探索,在诗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力求新颖——不仅诗要有新的思想内容,并且在形式和语言运用上也始终追求创新。在《扬鞭集》中,他将民歌、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的各种形式融合在创作中,进行了多方面新的尝试。其“幻想之丰富,用笔之灵活,格式之新奇”[13],在现代新诗中堪称出类拔萃。《瓦釜集》收录的是刘半农用江阴方言,依据江阴普通的民歌之一“四句头山歌”的声调所创作的诗歌。对为何要用江阴方言和江阴民歌的声调写诗,他在《〈瓦釜集〉代自叙》中明确表示:“我们做文做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是能于运用到等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14]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彰显出刘半农对诗歌创作及新文学的立场,应和了他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所提的文学应表现自我的真情实感这一主张。
刘半农对于文学革新的追求,与他率真的性情和文艺上求“真”的目标息息相关。对于文学的精神与价值,他有明确而精辟的见解:“文学为有精神之物,其精神即发生于作者脑海之中。故必须作者能运用其精神,使自己之意识、情感、怀抱,一一藏纳于文中。而后所为之文,始有真正之价值,始能稳立于文学界中而不摇。否则精神既失,措辞虽工,亦不过说上一大番空话,实未曾做得半句文章也。”[15]也就是说,文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展现作者真实的思想与情感,任何矫揉造作或空洞无物的表达都有悖于文学的求真精神,也就不是文学应有的姿态。因此,他指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所谓‘以手写日’,所谓‘心手相应’,实在是做文章的个条件”[16]。而他正是一个性情率真之人,对自然界的景物、对文艺都有自己的“偏见”。关于自然界的景物,他写道:“我爱看的是真山真水,无论是江南的绿畴烟雨,是燕北的古道荒村,在我看来是一样的美,只是色彩不同罢了。至于假山假水,无论做得如何工致,我看了总觉不过尔尔。”[17]关于文艺,他直言:“我的偏见简单说来,是爱阔大,不爱纤细;爱朴实,不爱雕琢;爱爽快,不爱腻滞;爱隽趣的风神,不爱笨头笨脑的死做。”[18]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一文中,刘半农强调文学的真实性,批判无病呻吟、背离现实的虚假诗文,明确提出“做诗”的本意就在于“将思想中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19]。
在语言学方面,刘半农同样孜孜以求,并有很深的造诣。留学期间,他辗转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柏林,专攻实验语音学。1924年出版的《四声实验录》,是一部运用近代实验语音学的仪器和方法研究汉语四声的重要学术专著。该书指出:“声音的要素在于强弱、音质、长短、高低,但汉语的四声与强弱绝不相干,与音质、长短有某种关系,但不起决定作用;决定四声的主要因素是高低。但这种高低是复合的,不是简单的,两音之间的移动是滑动的,不是跳跃的。”[20]书中还记录了北京、南京、武昌等十二地方言的声调实验结果,厘清了汉语调类和调值的关系。《四声实验录》的出版破除了“一千五百年间在四声解释上的层层疑云,给了四声以科学的说明,在我国音韵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1]。此外,刘半农 1925年在法国提交博士论文答辩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
三
在刘半农涉足的诸多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中,文学翻译是重要而有特别意义的一项活动。刘半农的翻译生涯可追溯至 20世纪 10年代初:辛亥革命后,他曾北走清江,“在革命新军中担任文牍和翻译工作”[22];在上海开明剧社任文字编辑期间,曾编译过剧本《好事多磨》。1912年,经徐半梅,刘半农在《时事新报》和《小说界》发表了两篇译文,这可以说标志着他持续近一生的翻译事业的肇始。刘半农的译作涉及小说、戏剧、诗歌、民歌等多种文学体裁,被认为是早将高尔基、狄更斯、托尔斯泰、安徒生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译者,也是首批译介外国散文诗的作家之一。他于 1914年翻译发表了英国狄更斯的《伦敦之质肆》、俄国托尔斯泰的《此何故耶》,以及丹麦安徒生的《洋迷小影》(根据安徒生的《皇帝之新衣》改写);1915年翻译了俄国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及美国欧文的《暮寺钟声》,由于转译及散文诗叙事性强等,他将屠格涅夫的《乞食之兄》等四首散文诗作为短篇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1916年译出了俄国高尔基的《二十六人》、美国霍桑的《塾师》;1918年将美国欧 ·亨利的《后之一叶》译为中文,同时翻译了印度泰戈尔的《恶邮差》《著作资格》《海滨五首》《同情二首》等诗作。同年,刘半农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狗》和《访员》并发表在《新青年》上。其出版的译著主要有《欧陆纵横秘史》(1915)、《乾隆英使觐见记》(1916)、《茶花女》(1926)、《国外民歌译》(1927)、《法国短篇小说集》(1927)、《苏莱曼东游记》(1937)等。除文学译著外,刘半农还译有学术著作《比较语音学概要》(1930)。
刘半农不仅翻译数量可观,对原著的选择有独到眼光,而且他的文学翻译观与文学创作观一样,彰显出革新与求真的鲜明特征。革新是五四时期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追求,五四运动所选择的求“新”途径在于与旧思想、旧道德决裂,在于向域外寻求新的思想和道德,“这样一来,翻译便成了必经之路”[23],必然在语言、文学、文化等多个层面肩负起创新的使命。就翻译而言,革新与求“真”密切相连,若没有不断寻求翻译之“真”的精神,翻译就无法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甚至可能沦为保守势力的同谋共犯。显然,晚清文人所提倡的“旧瓶装新酒”式的翻译方法及其背后的文化立场,都无法满足那个时代的革命需求。因此,刘半农积极投身翻译活动,希望通过翻译推动对文学与文化之“新”的追求。他提倡选译文学价值高的外国作品,坚决反对林纾式的“豪杰译”,主张在翻译中应尽可能保留原文的意义和神韵。著名的“双簧信”所涉及的一个主要译学问题便是“用笔措词”,即翻译方法的问题。“王敬轩”在致《新青年》的信中写道:
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词。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而贵报乃以不通相诋。是真出人意外。以某观之。若贵报四卷一号中周君所译陀思之小说。则真可当不通二字之批评。某不能西文。未知陀思原文如何。若原文亦是如此不通。则其书本不足译。必欲译之。亦当达以通顺之国文。乌可一遵原文迻译。致令断断续续。文气不贯。无从讽诵乎。噫。贵报休矣。林先生渊懿之古文。则目为不通。周君蹇涩之译笔。则为之登载。真所谓弃周鼎而宝康瓠者矣。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香钩情眼之名。若依贵报所主张。殆必改为革履情眼而后可。试问尚复求何说话。[24]
对信中的种种谬论,刘半农从翻译选材、翻译方法和译文风格等方面逐一予以驳斥: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 !何以呢 ?因为他所译的书:——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第三层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的病根 ……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25]②
他还以鸠摩罗什的《金刚经》和玄奘的《心经》为例,对实事求是的翻译方法大加赞许,认为在“我国古代译学有名的两部著作”中,译者
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皆是,岂不比林先生仿造二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是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 “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 “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26]
尽管刘半农的回复中对林纾翻译的评价难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对拟译文本选择、翻译方法与原文风格再现等方面的关注,以及他就这些翻译根本性问题所阐发的富有洞见的观点,无疑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体现出重要价值。“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正是出于这一明确的革新诉求。刘半农对翻译活动的认识不仅鲜明地代表了《新青年》派的进步翻译见解,而且在中国译论史上也理应成为值得重视的一部分。
在1927年《语丝》第139期发表的《关于译诗的一点意见》中,刘半农更为明确地提出其直译观,表示 “我们的基本方法,自然是直译”。就此,他进一步指出:
因是直译,所以我们不但要译出它的意思,还要尽力的把原文中的语言的方式保留着;又因直译(Literaltranslation)并不就是字译(Transliteration),所以一方面还要顾着译文中能否文从字顺,能否合于语言的自然。在这双方挤夹中,当然不免要有牺牲的地方。但在普通应用的文字里,可包含的只是意义(很粗略的说);而所以表示这意义的,只是语言的方式:此外没有什么。到了文艺作品里,就发生一个重要问题:情感。感情之于文艺,其位置不下于(有时竟超过)意义,我们万不能忽视它。但感情上种种不同的变化,是人类所共有的;而语言的方式,却是各不相同的 ……因此在甲种语中,用什么方式或用什么些字所表示的某种情感,换到乙种语言里,如能照它直译固然很好,如其不能,便把它的方式改换,或增损,或变改些字,也未尝不可;因为在这等“二者不可得兼”之处,我们斟酌轻重:苟其能达得出它的真实的情感,便在别方面牺牲些,许还补偿得过。[27]
在这一段不长的文字中,他围绕直译进行了相当精彩的论述,并着重分析了情感传达之于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以及翻译中面对 “异”如何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等问题。这样的翻译思想不仅在当时的语言变革与思想启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