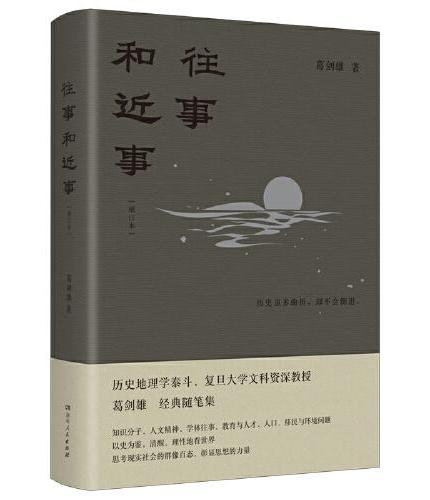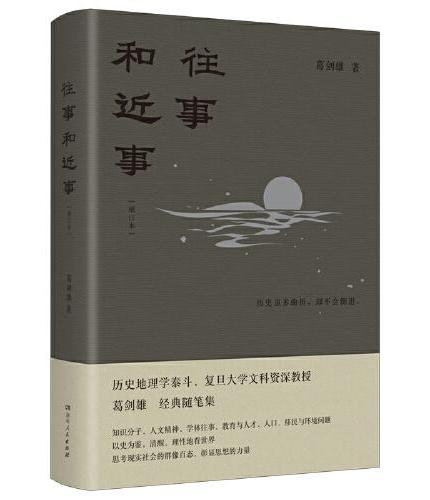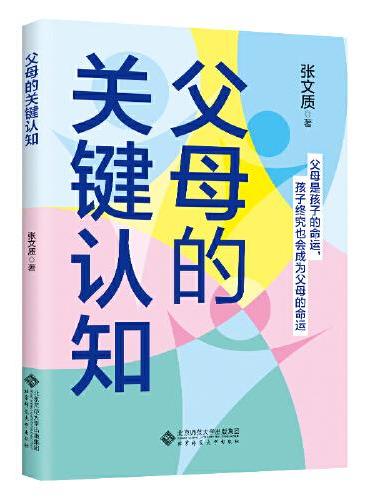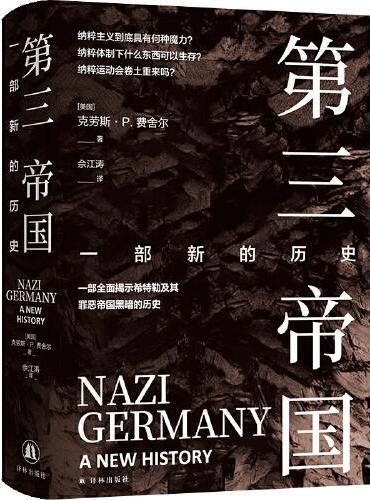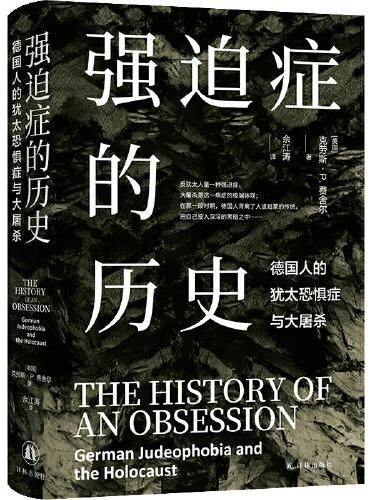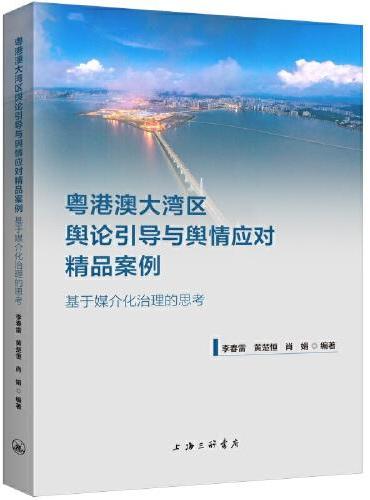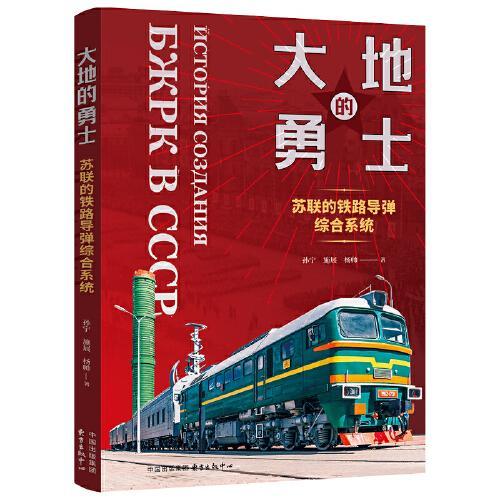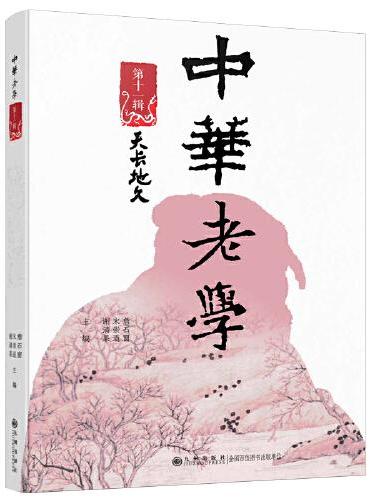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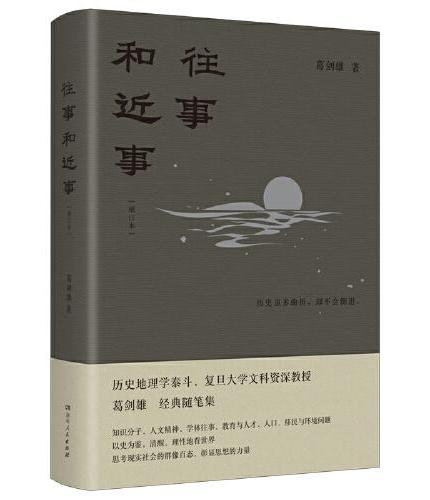
《
《往事和近事(增订本)》(著名学者葛剑雄教授代表作,新增修订、全新推出。跨越三十多年的写作,多角度讲述中华文明)
》
售價:NT$
3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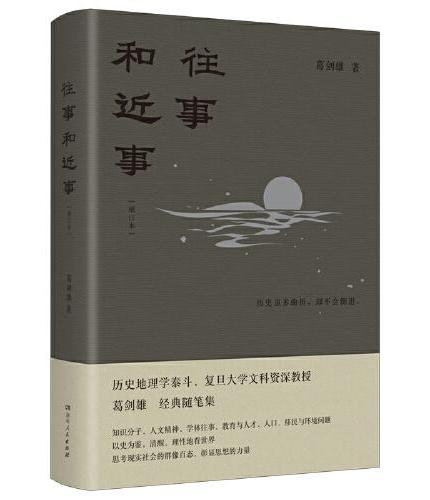
《
往事和近事:历史地理学泰斗、百家讲坛主讲葛剑雄经典文集
》
售價:NT$
3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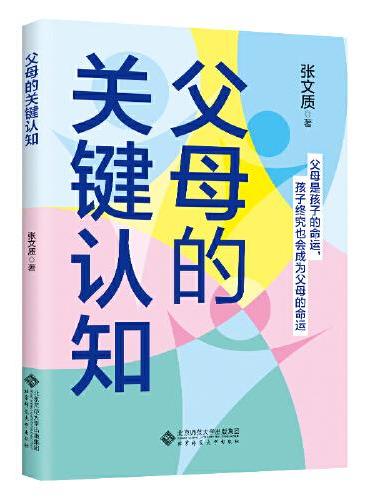
《
父母的关键认知
》
售價:NT$
2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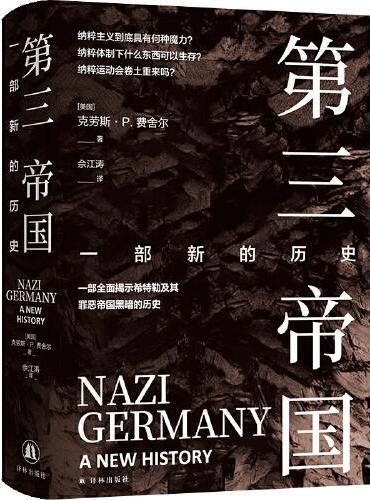
《
第三帝国:一部新的历史(纳粹主义具有何种魔力?纳粹运动会卷土重来吗?一部全面揭示希特勒及其罪恶帝国黑暗的历史)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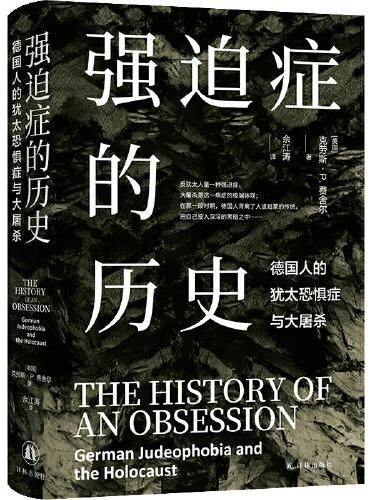
《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德国历史上的反犹文化源自哪里?如何演化为战争对犹太人灭绝性的种族杀戮?德国历史研究专家克劳斯·费舍尔叙述德国反犹史及其极端形态的典范之作)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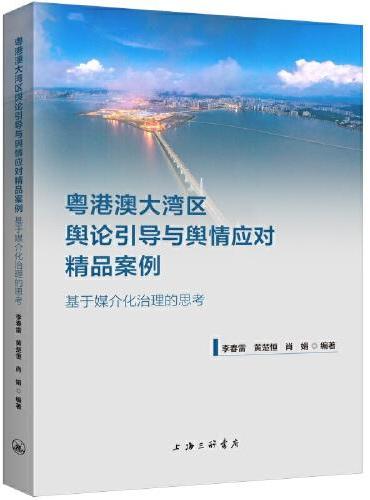
《
粤港澳大湾区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精品案例:基于媒介化治理的思考
》
售價:NT$
4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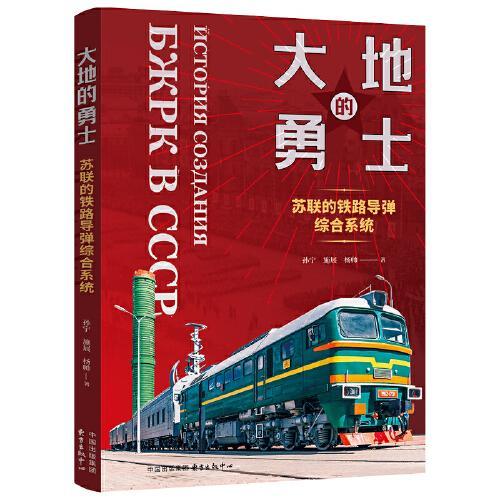
《
大地的勇士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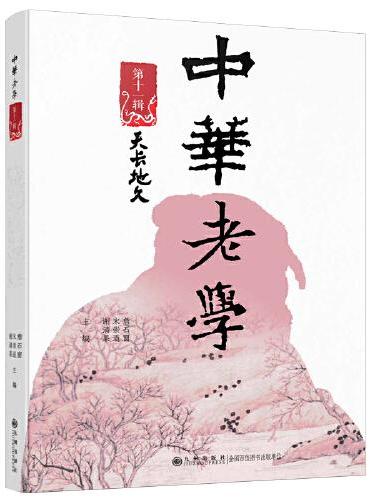
《
中华老学·第十一辑
》
售價:NT$
380.0
|
| 內容簡介: |
|
上海著名演员费克群离奇死去。死者的侄子费城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一份茨威格从未公布的戏剧手稿,于是决心将其搬上中国的舞台。就在费城着手为此准备的时候,茨威格自传《昨日的世界》中关于接触茨威格剧本的主创总有厄运降临的迷咒再次应验。
|
| 關於作者: |
|
那多,原名赵延,上海人,著名悬疑作家。他擅长从新闻事实、历史事件出发,结成一个个新奇的故事。2001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创作“三国事件簿”系列、“星座爱情小说”系列、“那多手记”系列、“巫术”系列等小说三十余部。2012年后,创作转向当下,以逻辑推理和对人性的拷问见长,著有《19年间谋杀小叙》《骑士的献祭》等。
|
| 內容試閱:
|
楔子
天气阴阴的见不到太阳,云层很低,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下了很小的空间。茨威格微微佝偻着身子,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真正直起腰来了。
和他的故乡相比,这个国家就像是个天堂。生活在这片净土上的人们恣意地歌唱跳舞和欢笑,可是透过这些表面上的快活,茨威格觉得他们和自己一样在内心深处惶恐不安。每一天,在大洋的彼岸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这座世外桃源能永远这样遗世独立吗?
茨威格很喜欢研究历史,他喜欢看那些伟大或渺小的人物,在奔腾的历史洪流中,怎样作出自己的抉择。而这些抉择又反过来,或多或少地改变着历史。
当以往茨威格完全沉入到他所研究的对象,比如歌德、卡斯特里奥或者斯各特船长的时候,他既有与人物命运同悲的感慨,又有一份置身事外洞若观火的通明。欧洲历史长卷在眼前慢慢铺开,以史为鉴,他曾经觉得这世上的一切在历史上早已经重演过许多次,没什么可惊讶的。
现在他知道自己当初有多么可笑。这个世界会走向何方,他期盼的未来还要等候多久。
从德国到英国,再到美国和巴西,他早已经精疲力竭。
“斯蒂芬……”他似乎听见阿尔特曼在叫他。
再看了一眼窗外的世界,他支撑着拉上窗帘,转身来到床前。
阿尔特曼穿着和服式的印花衬衣,侧卧在床上。她面容安详,脸上细微的皱纹已经舒展开。
茨威格凝望着自己的妻子,他想自己刚才是听错了。阿尔特曼比他更早服药,现在可能已经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了。
“亲爱的,请原谅我的自私,我无法听着你的呼吸在我耳边慢慢停止,就让我先去吧。”他还记得妻子后对他说的话。
茨威格拉开床头柜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件青黑色的铜牌。这块铜牌经过多年来千百次摩挲,泛起幽深的光泽。茨威格把铜牌放在双手的中间,托到自己面前,看着上面的浮雕。数十年了,他每天临睡前都以全副心神贯注其中,真要算起来,看了得有一万多遍,上面的每个细节都刻在心中不可磨灭,但越到后来,看在眼里越觉得其中有无尽的意蕴和神秘。
该履行仪式了。
每日睡前一次的仪式,茨威格哪怕是在窘迫的境地里,都没有中断过。现在他就将一睡不起,这是他此生后一次仪式。
铜牌上无数只眼睛正在看着茨威格,看着他虔诚地进行着仪式。这样的仪式,只在这个世界上某个极小的团体里流传,无论这个仪式带来怎样怪异或可怖的后果,这个团体的任何成员都曾承诺,绝不对外透露。
茨威格从未违反过自己的承诺。啊,其实也不能完全这样说。这个隐忍了数十年的骇人秘密,随着他近两年精神状态越发不佳,在刚写完的自传里,还是情不自禁地透露了出来。但那只是一个小尾巴,没人能从里面找出真相。天知道他一直承受着多么巨大的压力,正如在自传的某处写的,“那是一种连我自己都不清楚的出自幽冥的念头……驾驭我生活的神秘力量是不可捉摸的……”
铜牌上的眼睛直看入茨威格的内心,又从内心穿透出去,投入冥冥。茨威格觉得浑身都贯通了,他和令人震慑的庞大力量慢慢靠近,终合为一体,又化入无形。这是他感觉强烈的一次仪式,因为死亡就在眼前。
仪式结束了。茨威格觉得视野一阵阵的模糊,就像极度疲惫时那样,双眼的焦距难以对准在一个地方。茨威格知道自己的时刻快要到来了,他把铜牌塞回抽屉,在自己死后,没人会注意到它的,它将沦落为一件无人知道创作者的艺术珍品。茨威格和他妻子阿尔特曼被发现死亡时的照片
茨威格在妻子身边躺下,小心地让阿尔特曼的头枕上自己的肩膀。在闭上眼睛之前用手摸索着整理了衣襟,然后轻轻抓起妻子的手。虽然自己选择了逃避,但仍希望能比较体面地离开。
在意识慢慢消失的时候,许多画面浮现起来。茨威格恍然觉得,在屋子上空某个莫测的地方,一个通道正在打开。
那并不是白色的,发着光的,通向天堂的通道,而是幽深黑暗,隐隐流露出令人恐惧的神秘味道。一种有些熟悉的气息。
茨威格安静地躺在阿尔特曼的身边,可是他的整个精神世界,整个灵魂都已经战栗起来。
1942年2月22日,斯蒂芬·茨威格和妻子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郊外的寓所内自杀。巴西决定为其进行国葬,包括总统在内的四千人为这位当时全球著名的作家送行。
这一天阳光灿烂,抬棺者们走到墓穴前,准备把棺木放下,让死者入土。
几乎在转眼之间,灰黑色的云聚集起来,隔绝了阳光。
大雨。
安葬完毕时,大雨骤停。
后记
大约在两三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屋里写小说。父亲忽然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本书。
“我看到一些东西,很适合你用来做小说素材。”他说。
他手里拿着的这本书,就是茨威格自传《昨日的世界》。
我把手头的事情干完,才开始看父亲指给我的相关内容。看完之后已经是凌晨,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忽然感觉毛骨悚然。我从前写的此类小说,当然也有惊悚的情节,作为作者,虽然有时也不免入戏,总还知道那一切都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可是茨威格写到的诅咒,则是真真正正发生过的事情,这诅咒让茨威格在临死前写自传的时候都不能释怀,也让数十年后看他自传的一个中国人深觉畏怖。
这个世界终究还是有一些事情难以解释,这让我们学着在看似科学昌明的今天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在这之后的几年中,这个诅咒一直潜伏在我脑海,或者说潜意识的深处。哪怕我在写作其他小说的时候,也在心中默默构思着,要怎么把这个题材写成一部新的小说。
直到2006年9月,关于这部小说的基本构想才全部完成,然后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小说大纲,又花了四个多月全力写作。我投入了双倍于以往的时间和精力,当小说终完成时,我想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我完成了一次跨越。
这部小说中当然有许多的虚构成分,比如那个为情杀人的刑侦队长,在真实的制度中,这样一个身份的人,是不能轻易出国的,在向上级汇报清楚之前,他甚至可能拿不到出国的护照,更不用提偷偷在加拿大和另一个男人结婚。拉比威尔顿也同样如此,当年摩西会堂的大拉比另有其人。
可是,更有许多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真实生存过的人。比如那三位死去的演员,为了写作这部小说,我真的托我在德国的朋友,帮助查这三人的死亡日期和死因。而他给我的回信,大致的内容也和小说中小望的回信一样。茨威格所说的死亡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
达利的画展在上海也办过,不过并不是小说中的时间。看达利画展的人,有许多真的会在他的画前感到不适,而我自己因为写小说看达利传,发现由他写作的剧本《一条安达鲁狗》的男主角在演完此片就自杀,也觉得有些惊讶。同时,我几次去位于上海老城区的摩西会堂,拍了很多照片,那儿的情况,基本就如我小说中描绘的,除了地砖之外,其他的都翻新过了。要是在圣柜间的地砖下真有什么东西的话,大概还在那儿吧。出现在韩裳梦中的几位犹太人,像小格尔达一家,也曾在六七十年前的上海生活过,摩西会堂就是他们在礼拜日会去的地方。
弗洛伊德晚年对神秘主义态度的转变,早就明明白白在他的著作中反映出来,而关于小说中的神秘实验,实际上我有一个更完整的构想。可是在这部小说中,没办法把所有的线索都交代清楚,因为主角已经死了,属于他的故事,也只能就此结束。关于卡蜜儿、弗洛伊德的继承人、其他的实验者、神秘实验的结果这些都存在于我的脑海中,也许有一天,会在另一部小说中揭露出来吧。
2006年10月19日。中国,上海。
天气已经开始转秋,暑热虽然没有完全散去,但在这样的深夜,窗外的风还是能吹来些许凉意。
费克群早不是年轻人,不过很多年来他已经养成了晚睡的习惯,在这个时候依然毫不困倦。
他正坐在电脑前,看着一篇和自己有关的新闻。
费克群一直以温和谦逊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私底下的性格却很有些自恋。他常常在网上搜索关于自己的新闻,以及网友们对自己演技的评价。由于形象一直都不错,所以大多是正面的消息,比如现在正在看的这条。
费克群的脸上浮起一抹笑容。现在并没有镁光灯摄影机,他可以不加克制地自由表露心底里的情绪。
一个特殊的提示音响了起来,他看到某个网上的熟人上线了。很快,一个聊天窗口在屏幕下方闪动起来。
费克群觉得自己血液的流动稍稍加快了一些。鼠标移过去,把窗口点开。
“这么晚了,还不准备睡吗?”凌说。句子的后面,一张微开的唇,闪着粉色的光泽。
“看我的新图标怎么样?”凌接着打道。
费克群修长的手指也开始在键盘上跳跃,他很注意保养自己的手,曾经不止一个女人说过它很性感。
“从哪里找来的?”
“我自己从照片上截的。”
“谁的照片?”
“你猜呢?”
“你的?”
唇再一次出现,不过这次噘了起来,然后放送出一个诱惑的吻,费克群甚至看见了双唇间一闪而过的舌尖。女人常被比作蛇,此时他真的联想到了嫩红的蛇芯,心也随着蛇芯一起颤动了一下。
现实中身边的美女也不少,可是没一个能让他感兴趣,反倒是这个始终不知长什么模样的凌,总能叫他心神动荡。
这是距离造成的神秘美感,还是自己纯粹有些变态?费克群没有深想,许多事情不需要想得太多,这样才能活得更轻松。
“这两天想过我吗?”
“天天想着呢。”刚上网那会儿,费克群还很矜持,不过现在他已经想通了,放开了。
“有些急色哟。”
费克群笑了笑,从一堆动画图标里挑出一个扭着屁股的背裸帅哥发给凌。
“这不会是你的屁股吧。”
费克群仿佛能看见凌在那一边笑得花枝乱颤。
……
从调情到诱惑,再到比暧昧更进一步的挑逗,两个人一来一回地触碰磨蹭着。费克群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果然,在嘴里的烟快要抽完的时候,凌发来了视频邀请。
“等我一会儿。”把烟熄灭,费克群点了同意,然后打出一行字,起身离开。
把窗帘拉上,从橱柜里取出一个精巧的烛台,放在电脑台上,点燃上面的蜡烛。大灯熄灭了,屋里亮起一盏台灯,并且光亮被调节得很昏暗,这让烛台透出的那一星飘忽的火光格外明显。
费克群小心地调整了摄像头的角度,好让它不会拍到脖子以上的部分。双方都有着这样的默契,费克群的确很好奇对方的长相,可要是他自己的身份被踢爆,“费克群网上视频性爱”的丑闻足以让他堕入万丈深渊。
正像在车里做爱一样,危险感带来的额外吸引力,让费克群欲罢不能。
坐回电脑前的时候,费克群在屏幕上看见的,是一截温润的颈,往下是柔和的肩膀弧线和性感的锁骨。淡蓝色的睡袍丝带松松地搭在肩上。
费克群的喉结缓缓蠕动了一下。
凌的肩动了起来,她又开始打字。
“你又点了那个小玩意了吗,给我瞧瞧它。”
费克群把摄像头朝烛台那儿一扭。
烛台上人影起起伏伏,慢慢转动。
与其说这是一个烛台,不如说是一个精巧的小型走马灯更合适,一年多前费克群在尼泊尔的一个古玩地摊上看见的,花了大约近三千人民币买了下来。
烛台的莲花台底座由纯银打造,花瓣伸展着,上面还阴刻着云气般的纹路,丝丝缕缕,在精妙中透着些许慵懒倦怠。
出于热力学上的设计,插蜡烛的位置并不在莲花台的正中,而在一侧。上面的灯罩有螺旋桨状的扇叶转盘,点起蜡烛盖上灯罩,上升的热气流就会带动扇叶缓缓转动。
扇叶下方连着六道向四周伸出去的分支,每根分支的端部,都连接着一对薄如银箔的裸身男女,姿态各异,雕刻得栩栩如生。这六对男女各有高低起伏,在烛光中转动起来,隔着蒙着灯罩的那层透光薄羊皮,显现出的光影效果无比曼妙,直让次瞧见的人目瞪口呆,知道什么才叫巧夺天工。
费克群在买下的时候,也没曾想到会有这样的效果。回了国内,托了一位道具高手把烛台略作清洗。道具师去掉原先残破污秽的灯罩蒙皮,重新蒙上新皮之后试点了一次,有人立刻出价十万要买。
费克群是个很讲究情调的人,所以每一次和凌视频,他都会点起这个烛台。烛火人影交错间,与他年纪不相称的欲火很快就会轰然升腾起来。
凌的睡裙早已经褪去,白皙的肌肤泛起潮红,对着她的摄像镜头已经往下移,再往下移。费克群的汗衫也甩到了一边,修长的手只剩了一只在键盘上,打出些简单的字词。
屏幕下方的对话框有时长时间才会跳出新的一行,而上方视频中,彼此的躯体都在剧烈扭动着。他们没有开启音频传送,但对方的喘气声却仿佛很清晰地在耳边响起。
费克群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忽然喉间发出一阵哀鸣和低吼混杂在一起的声响。他的胸口起伏着,整个人都软在了椅子上,然后用鼠标选了个大口呼气的夸张图标发过去。
凌的手已经绷直,小腹上的肌肤战栗着,很快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歇了半分多钟,她给费克群发了个吻,关闭了视频。
费克群勉强起身,此刻明显的精力不济让他叹息起逝去的年华。他走去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洗去另一只手上的污秽。他的胸口起伏得越发厉害,心脏还在疯狂地跳着,急促的呼吸一点都没缓和。
今天兴奋过头了吧,不过还真是刺激。费克群这样想着,按紧了洗脸槽的塞子,积了些冷水,准备洗把脸让自己清醒一下。
低下头半浸在水里,用手往脸上泼水的时候,他把水弄进了鼻子,顿时呛了起来。
胸口收缩得有些发痛,气管火辣辣的像被灌过辣椒水,每一次勉强吸进半口气,就忍不住呼出一口。费克群觉得越来越气急气闷,眼前一阵阵发黑。突然之间,他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兴奋而引起的呼吸急促,而是自己的哮喘病发作了。
费克群有三十多年的哮喘病史,可是近些年症状已经减轻许多。这一次的急性发作,竟然比三十多年来的任何一次发病都更凶猛。
费克群心里隐约有些不妙的预感,他扶着墙走到卧室,只是摸索着开灯的片刻,他的胸口就像有根钢丝勒住了心脏,硬生生地痛起来。他俯身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双腿支撑不住坐在了床沿上。
00好在沙丁胺醇气雾剂就放在抽屉里相当明显的位置,费克群一把抓起,哆嗦着把气雾剂从外包装的纸盒里倒落在颤抖的手心,又准备拧开塑封的盖子,却愣了一下。
这瓶哮喘特效气雾剂是一个多月前他的侄子费城为他买的,从买来到现在费克群并没有发过病,所以这瓶沙丁胺醇在他的记忆里,应该是没有拆封过的。不过现在,盖子上的塑封已经没有了。
这时费克群已经管不了这些细枝末节,把喷口对着嘴猛按了十几下。
料想中凉凉的救命气雾竟然并没有出现,这瓶药是空的。
就这么短短的时间里,费克群觉得自己的症状已经比刚才在卫生间里又加重了一倍。
要打电话求救,要打电话求救!
准备拨打120的费克群,手还没有碰到床头柜上的电话机,铃声却突然响了起来。
费克群抓起电话,里面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
费克群心里松了一口气,他想告诉对方自己现在的情形,却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完整地说出一句话。
深呼吸,再深呼吸,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动作,气管纠结在一起,吸到一半就得痛得停下来。他拼了命地回想着哮喘发作时自救的措施,仰着头挺直了脖子,右手狠命地掐左右的虎口,只希望能对电话说出些什么来。这个时候,他听见对方开口了。
两分钟后,放下电话的费克群倒在床上,他的呼吸发出类似哽咽的声音,像一条正在呜呜哀伤的狗。
费克群瞪着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枕沿,连转动眼珠都感到困难,心脏一抽一抽,那根死命拽着心脏的钢丝不知什么时候会绷断。
天哪,他忽然想起来了,聊天记录!那个窗口他还没有来得及关掉!
可是他现在连一个小指头都动不了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