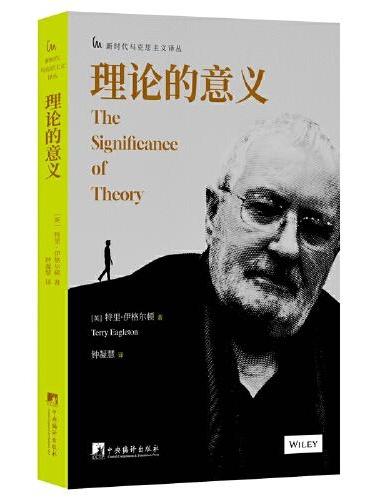新書推薦: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
《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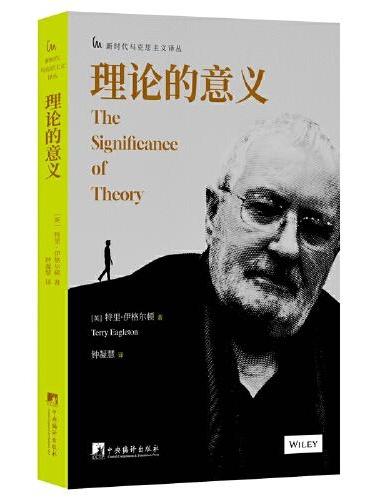
《
理论的意义
》
售價:NT$
340.0

《
悬壶杂记:医林旧事
》
售價:NT$
240.0

《
谁之罪?(汉译世界文学5)
》
售價:NT$
240.0

《
民国词社沤社研究
》
售價:NT$
640.0

《
帕纳索传来的消息(文艺复兴译丛)
》
售價:NT$
495.0

《
DK威士忌大百科
》
售價:NT$
1340.0

《
小白学编织
》
售價:NT$
299.0
|
| 編輯推薦: |
★《东京梦华录》《洛阳伽蓝记》式的记录,勾勒出栩栩如生的江南水乡生活全景图,描绘乡村生活的肌理。
★地点、虫兽、节日、草木……一部记录20世纪江南乡村的一草一木,岁时流转的“自然史”。
★文学的自然地方志,诗意的江南风物回忆录。
★逝去又永存的故乡:
“此时,远非塔鱼浜时光的尽头,而是另一种时间的开始,在云朵崩断的天象之下,塔鱼浜的泥土以及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汉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从此塔鱼浜藏身在过往细节的名词和动词中——但我要说它仍是及物的。
从此塔鱼浜的少年在有限的疆土里做着无限的漫游——但我必须说,这种漫游的脚尖固执地指向未来。”
★邹汉明走进了南方的腹地,走进了人迹罕至的乡野之地,走进了寻常庭院,走进了一棵树的年轮,并将沿着一片树叶的茎脉,一直走进自己的掌纹:他把自身的微命揉入了整个南方乡村远为繁杂的历史与命运之中。—— 东君
|
| 內容簡介: |
本书缘起于作者经家乡塔鱼浜拆迁后,由一只旧碗开始回忆童年的故乡。从“一只供碗”引入,后分为七卷,每卷主题鲜明,进行“关键词回忆和写作”,以物为题展开写江南乡村人的生活,七卷分别为:“地理志”——以单个地点,如“西弄堂”“水泥白场”展开;“地理志附:父亲的老屋”——以老屋各处,如“厢屋”“灶头间”展开;“岁时记”——以各种节日展开;“动物记”——以动物,如“母牛”“狗”等展开;“昆虫记”——以亲近的昆虫,如“蜻蜓”“萤火虫”等展开“农事诗”——以作物的播种、收割、收购的生命历程展开;“草木列传:农事诗补遗”分写了各种童年时期亲近的各种草木。
作者“为物立传”,将童年生活的细枝末节作为线索聚集起来,写故乡“自然中人”的日常生活:地点、虫兽、节日、草木……众多的回忆片段汇聚成记忆的河流,还原了江南乡村的肌理,勾勒出栩栩如生的江南水乡生活的全景图。是一部“文学的自然地方志”,一本“诗意的江南风物回忆录”
|
| 關於作者: |
|
诗人、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生于嘉兴,创作以诗歌为主,兼有散文、文论和诗歌批评等,在《诗刊》《花城》《十月》《诗神》等刊物发有作品,现供职于嘉兴报社。出版有《江南词典》《少年游》。所著的《穆旦传》将于202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出版。
|
| 目錄:
|
引言 一只还魂的供碗
卷一 地理志
卷二 地理志附:父亲的老屋
卷三 岁时记
卷四 动物记
卷五 昆虫记
卷六 农事诗
卷七 农事诗补遗:草木列传
后记
|
| 內容試閱:
|
引言 一只还魂的供碗(节选)
我在塔鱼浜的废墟上来来回回走动着。村坊拆除以后,这家与那家的隔阂不存在了,一个梦境可以进出另一个梦境了。这应该是梦境自由自在的一刻。这诚然是真实的一刻。2009年12月4日的太阳,高高在上。这且不说,这时的天空蓝得反常,云朵也是出奇的白,但是,消失的塔鱼浜也还有太古的气息。
我觉得应该带走点什么。余生的念想也需要一个支点,此后的祭奠也需要有一个可以依托的对应物。于是,我顺着这段无比巨大的废墟,由东向西,即由不存在的塔鱼浜的邹介里向着不存在的塔鱼浜的施介里走去。我的眼睛—套用张爱玲的一句话——始终在断壁残垣间“瞄法瞄法”,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搜寻点什么。突然,一只怯懦的小供碗出现在我面前。这是一只高底浅口的民国小供碗,属于瓷器中很普通的一种。碗口下面,釉上粉彩、红青绿蓝白五种颜色的牡丹花漂亮极了。碗肚,还有一朵含苞绽放的牡丹花蕾,旁边是一个机制的“艮”字。多年的乡村生活告诉我,这不是普通的饭碗,而是从前民窑所产的供碗—一件供奉在祭台、供老祖宗歆享祭品的祭器。这只易碎的小供碗,就这么夹杂在硬邦邦的钢筋水
泥堆里,躲过了推土机凶猛的击打,躲过了塔鱼浜分崩离析时的后一击。这太不容易了。它仿佛一直在等着我的到来,以它坦白的碗口,吁请我把它带走似的。这只完整无缺的供碗,完好无损地,这一刻待在坚硬废墟的某处。它小得无助,但相当出挑。此刻我目力所及,它的周围—砖头、水泥板全都断裂,而唯独它君临废墟的高处,坚持着自己的完整。这太奇妙了。莫非冥冥之中,临终的塔鱼浜对我有什么昭示?难道它想借这么一件独自完整的祭器,来还一个塔鱼浜的老灵魂?
很明显,废墟上的这只供碗,从它来到我手上的这一刻起,就开始高出这堆废墟。它使得塔鱼浜破碎而混乱的事物,全部围绕着它并匍匐在它的周围。这也使得一个四散而去的塔鱼浜,开始归拢并归位。这一刻——或许我可以推至久远——它就是塔鱼浜的中心。正是它的出现,把一个彻底打散的老灵魂重新聚合,从此有了再次上路的可能。我不是基督徒,当我俯身,触摸它的瞬间,我确实相信,那一定是上帝之手,把它交在了我的手上。
在塔鱼浜还活着的20世纪后三十年,很荣幸,足足有十五年时间,我曾陪伴在它的左右。我经历了乡村后一段夜不闭户的旧时光。我在它古风犹存的节气里出生、长大,看到了它古老的安静,初的不安,也看到了它后的消散。我曾是它的一个泥巴男孩,是它欢声笑语的一部分。可是,很快,故土已无歌哭之地,塔鱼浜再没有袅袅升腾的烟火气。眼看着它走入一条断头的弄堂,我却无力喊它出来。等到21世纪的脚劲迈开,新世纪的曙光照临,一个歌哭生聚、极有活力的老村坊,从此地老天荒,走到它的尽头。可是,当我接到临终的塔鱼浜递给我的这只供碗,我的固执又顽强地上来了,我想说,此时,远非塔鱼浜时光的尽头,而是另一种时间的开始,在云朵崩断的天象之下,塔鱼浜的泥土以及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汉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从此塔鱼浜藏身在过往细节的名词和动词中——但我要说它仍是及物的。
从此塔鱼浜的少年在有限的疆土里做着无限的漫游——但我必须说,这种漫游的脚尖固执地指向未来。
岁时记·七月半
农历的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又叫鬼节。这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鬼,塔鱼浜土白即“祭拜拜”。鬼是人的反影,它在人的暗处,它掌管着与光明同样庞大的黑暗。这当然是不能小瞧的。俗语:鬼由心生。为了求得心安,七月十五这个鬼节,是怠慢不得的。因此,这俗称的七月半,村里的每户人家都非常庄敬地去度过。家里过七月半,在我们这些小屁孩,原是少不了磕一番头拜一番揖的。
其实,早在七月十二,各家各户就忙着准备过七月半了。这前面的三天,主要是祭祖。这事我母亲起劲。她忙着做菜,做馍馍,里里外外张罗着。做好的几碗小菜,无非香干肉丝、红烧鲫 鱼、蛋夹子、东坡肉……也不多,大抵六碗,也或者八碗,都是很家常的小菜。平时,要是没客人,很少做这么多的。
我帮父亲早洗好了筛酒的小盅,以及祖先们专用的筷子。这会儿,一只盅子配一双筷,东西两边摆端正。父亲将热气腾腾的六只 或八只小菜摆到八仙桌上。蜡烛点上,他先拜一拜,接着是我拜, 我大弟汉良再拜。我们家原先是有一个蒲团的,两个小膝盖跪在有弹性的蒲团上,也很适意。后来,这个稻柴蒲团不见了,父亲就扯 一把稻柴,扭一个松松垮垮的结,将就着拜揖。这样的场合,我母亲是不出场的,她难得也来拜一拜,她心里想的,大概这祭祖拜阿太的家事,轮不到她一个女人家吧。但我母亲另有一个任务,就是祭拜刚开始的时候,她隙开大门的一条缝,手搭在门边,小半个头探出门外,小声地喊一声:“阿太哪,来吃!小囡也来吃!”我起初感到奇怪,后来知道了,她这是在特别关照我那位早夭的姐姐。母亲生怕姐姐年龄小,玩得兴起,忘了回家吃饭吧。
七月半的元宝是盲太太折的,佛柴也是他念的。盲太太一年四季,除了搓绳,就是做这两样事体。祭祖仪式的高潮部分,就是去墙角边给祖先们烧这些盲太太念过佛的元宝和佛柴。这活计一般就靠我们两兄弟完成,父亲反而做帮手。主要是怕火势烧到别的物事,他在一边警戒。烧纸钱的时候,母亲也会走过来,她在一大堆 元宝佛柴之外,另堆开一小堆,这也是她的特别关照—烧给我的姐姐的。有一年,我们忘了堆这一堆,她就裁了一小刀煤头纸,自己念佛,念完,重新烧给我这位从没有见过面的小姐姐。
真的到了七月半这一天,这祭祖的大事,似乎都已提早做完。这一天,父亲一早去翔厚或对丰桥,回来的时候,篮子里就多出了一叠馄饨皮子。那时候,馄饨不常吃到。据说七月半吃馄饨有来历,一百多年前的咸丰年间,我家乡曾有一小支太平军的残部,因为打散了,不得不散落此间,他们或种田,或给家境殷实的人家打短工,与村里人家相处甚为亲密,但此事终于被清廷发觉, 于是一个个捉去杀了头,每割一颗头颅,即将他们的耳朵割下报功领赏。村民为了祭祀这些没了耳朵的亡灵,就以面粉捏成耳朵的形状,摆在八仙桌上祭供。这就是七月半吃馄饨的由来。
村里没有人知道这些老古话了。但七月半的馄饨,我一直记得,它实在是一次不小的口福。
传说七月半是鬼门关大开的日子,因此,即使有堂堂的月亮高 挂天空,夜里,孩子们也不敢走到塔鱼浜的前埭去。
眼前的严家浜,已经有人在放河灯了,灯是自己做的,简单 的就用一张香烟纸折一只万吨海轮的形状。然后,放上短短的小半截蜡烛,纸船随着微微荡漾的水波,去留无心,也随意。这纸船我会折,这河灯我会放,只是这黑漆漆的严家浜,我一个人还不敢下到河埠头呢。
好看的河灯当然是西瓜灯。我把一只小西瓜的挖一个洞,用调羹一勺一勺挖去它的瓤,再把西瓜由里往外刮得薄薄的, 只剩外面的一层绿色的皮。瓜里面,横着撑一根竹片,摆上一截红蜡烛,划出一朵洋火,点燃了,放到河面上去。青绿的瓜皮衬托着 红扑扑的火苗,飘摇在黑黢黢的河面上,好看好看。这些河灯,千百年来,为的是安慰村里的孤魂野鬼吧。大人和孩子们只有一个心愿:求它们不要来打扰村里活着的人。这个小小的愿望,我满溢着幸福的双手去放河灯的时候,哪里会知道呢?
昆虫记·蚕
蚕的第四眠俗称大眠。春蚕进入大眠,离上山吐丝结茧也就不远了。这时的乡村安安静静的。狗也知趣,很少吠叫。人们走路也格外轻手轻脚,路上见了面,面对面说话,交代三句或点个头,就各自走开。大家的后背心上,似乎都贴着一个“忙”字。
地气正从地缝里咝咝地透出来。这安静里其实也暗含着闹热,且还有一股喜气。蚕忙时分,亲戚家甚少走动,大家各自忙于蚕事。蚕娘无心梳妆打扮,一个个蓬头垢面,满脸疲倦之色,但这疲倦的脸上,分明又全是希望的底色。
木桥头的广播里,桐乡电台的女播音员用桐乡土白播报养蚕的新闻和科普知识。连翔厚大队广播站六和尚的会议通知,也三句不离本,离不开“蚕桑”两字。我那时经常听到六和尚以威严的口气代表大队书记发话,要求附近大小砖瓦厂一律停火歇工。六和尚这是秉承县里的指示吧。那时,整个桐乡县的砖瓦厂,土窑不算,单说轮窑,我记得就有五十二座之多。塔鱼浜附近的轮窑,以白马双桥的那座为,远远地就可以看到它的那根戳向天空的大烟囱。当然,看蚕的时节,双桥的轮窑很听话地熄火了。从我们村里任何 一个点望去,那根阴茎似的大烟囱,已经不再冒黑烟或白烟。
如果再往前推一段时间,我家乡的看蚕,广播机里的女播报员,一定会柳眉倒竖、义愤填膺地要大家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可是,时代在变化,这会儿换上的播音员,声音绵软多了,口气也大变,她只是提醒桐乡范围的广大群众,一定要提防蚕宝宝中毒。好像这时候的“阶级敌人”,已不是地主四类分子,而是附近轮窑这些个老流氓高高竖起的那一根根大烟囱。还有,女主播很耐心地告诉她的广大听众朋友:不可随便使用农药。
这个季节,小队的蚕桑队长吃香。他要去大队开会,开完会,还要去炉头公社开会。会议结束,总有一些指示带下来。蚕妇们走拢来,围着他问长问短。那时的蚕桑队长是坤祥吧,年轻,浓眉大眼,一说话,两条眉毛缓缓地舒展开,嘴里的一抹微笑就出来了。坤祥的样子在小队里当然长得很出挑的。
蚕宝宝上山在望,蚕户们该早做准备。其中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家家户户在稻地上绞柴龙。
幸好,邻近春末,黄梅天气也还没到,偶尔飘过一阵斜风细 雨,老天也颇知趣,立即就放晴,而且,总是天朗气清的日脚多。 这就有利于稻地上摆开阵势,绞出一条条威武的柴龙来。
绞柴龙,我家盲太太搓的稻草绳就派上用场了。我以前一直不明白,盲太太一年四季都没闲着,总是给轮到吃饭的那家搓很长很长的稻柴绳。原来,这些绳子,就是为了绞柴龙用的。 绞柴龙需四个人,一个都不能少。所以,这活儿,需要全家人一齐上阵,互相帮忙,方可成功。这四个人的分派是:两头各一人,一人坐,一人站,我喜欢干站的那个人的工作,我觉得站着爽气。我有一小股蛮力,需要随时地使唤出来。此时,两股稻柴绳已经拉挺。我用一只脚撑住一根装了摇把的木头的下端,左手拿住杉木的上头,右手顺时针方向摇动把手。另一头,多半是我的母亲, 坐在一只条凳上,双手各自摇动一个小摇把,不急不慢,也是按顺时针方向摇。汉良则跑前跑后,将两头已经铡断的麦柴或稻柴束递给正后退着喂柴的父亲。父亲的一脚跨在两根绳子中间,另一只脚跨在绳子外。他一边后退,一边将双手捧着的麦柴或稻柴均匀而缓 慢地退出来,随着两头的转动,两股绳子夹住稻柴,越夹越紧,这柴龙也就渐渐地绞成了。父亲退到母亲身边,随即从两个摇把上解下两股稻绳,绾一个死结,一条与地铺等长的柴龙就绞合成功了。 父亲手一抬,将柴龙摊放在稻地一侧。
小孩子,多少有一点贪玩,柴龙绞到一半,我们就开始发人来疯:一根摇把,抓在手里拼命地摇。柴龙只成了一半,绳子绷得太紧,吧嗒一声,终于崩断。大人赶紧交代:“慢点,慢点,小棺材!”其实这活儿是性急不得的。重新接上绳子,重新摇把,喂柴,把一条愿想中的柴龙一段一段地放出来。绞柴龙绞到末梢,绳子崩断是常有的事。此时的柴龙,因为冗长,中间部分几乎拖到地面了。我摇动的手把,也几乎翻滚不了整条柴龙。每到这个时候, 柴龙就绞成了。
看蚕看到绞柴龙这个环节,那是丰收在望了。我也很愿意给大人当帮手。但,与其说帮忙,不如说捣乱更贴切一些。大人对于我们捣乱的惩罚,就是坚决不让我们摇手把,而只叫我们递麦柴或稻 束。或者,后柴龙绞成,叫我们拎住一头,一二三,连喊三声,相帮扔到稻地外高高的柴龙堆里。
|
|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