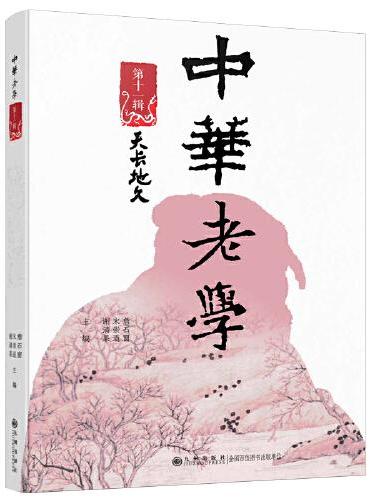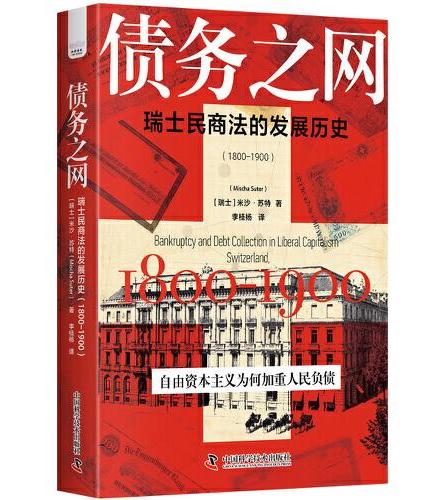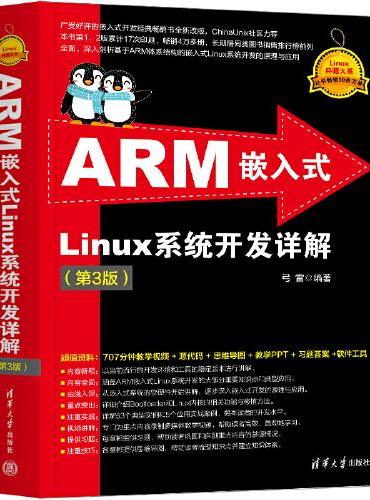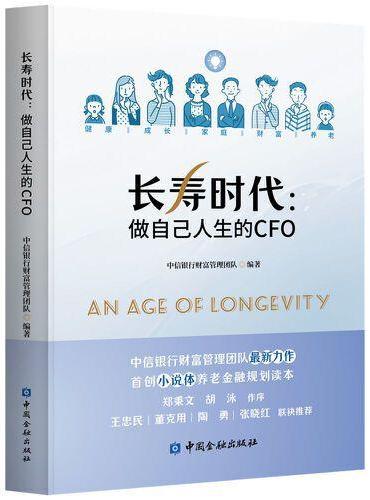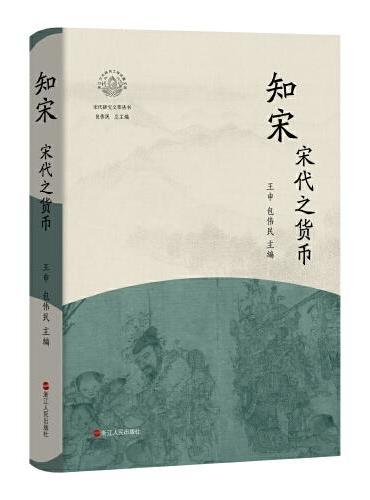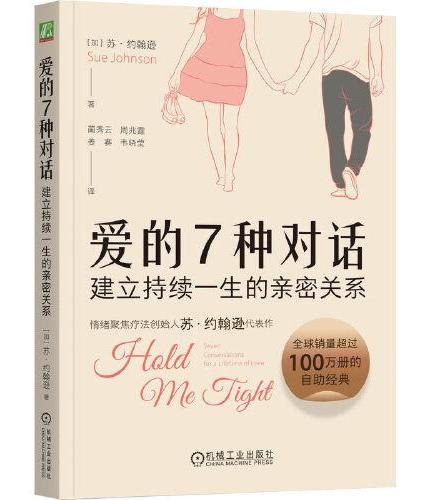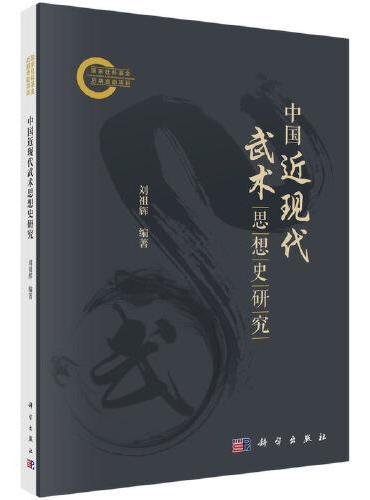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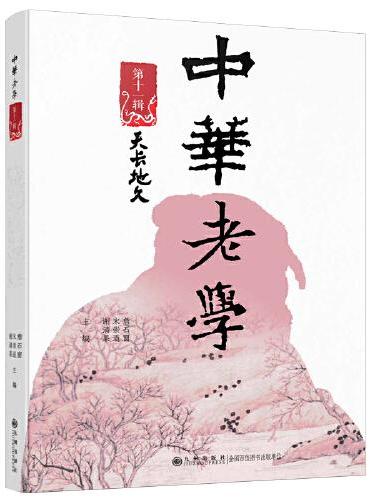
《
中华老学·第十一辑
》
售價:NT$
3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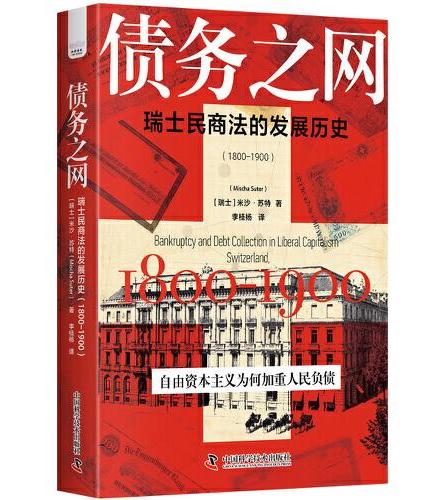
《
债务之网:瑞士民商法的发展历史(1800-1900)
》
售價:NT$
3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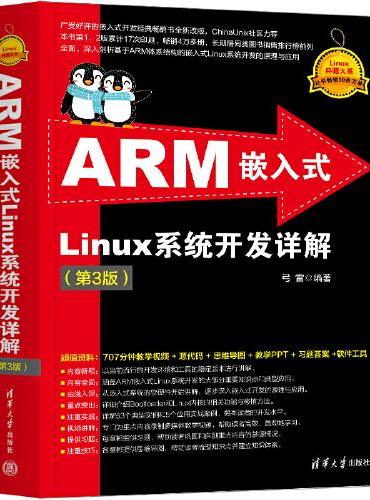
《
ARM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详解(第3版)
》
售價:NT$
5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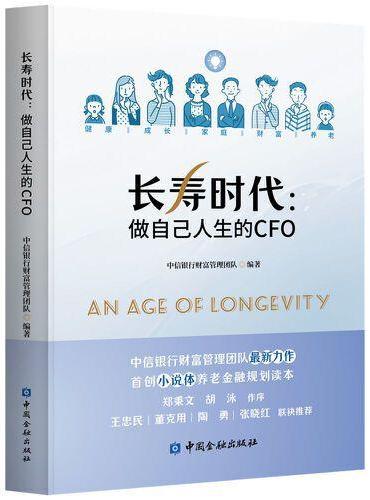
《
长寿时代:做自己人生的CFO
》
售價:NT$
310.0

《
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
》
售價:NT$
2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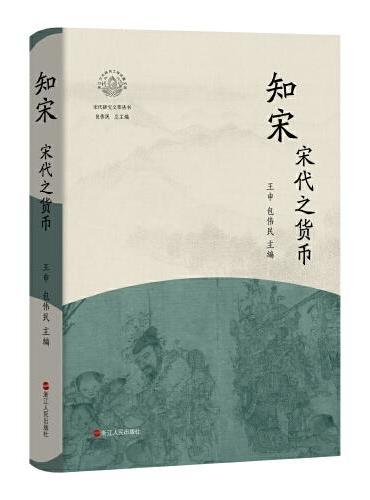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货币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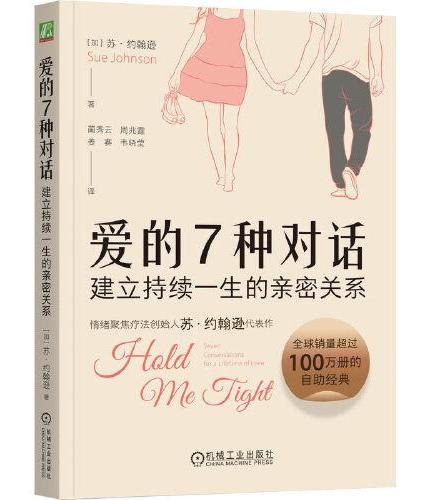
《
爱的7种对话:建立持续一生的亲密关系 (加)苏·约翰逊
》
售價:NT$
3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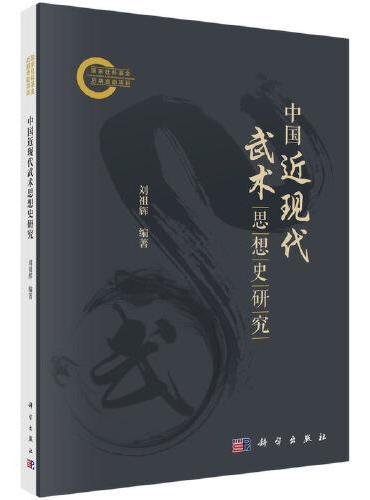
《
中国近现代武术思想史研究
》
售價:NT$
500.0
|
| 內容簡介: |
|
2019年8月,“魏晋风流与中国文化:第二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在南京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由南京大学文学院主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马来西亚等3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位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的发表和评议。该论文集从50篇参会论文中精选19篇,内容涵盖中国古典文献、文学、历史、美学、接受学、书籍史、域外汉籍等多方面议题,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多样,理路多元,较突出地呈现了中西学者有关“世说学”研究的*成果和关注点。
|
| 關於作者: |
|
赫兆丰,男,1987年5月生,河北邯郸人。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2012年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16年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在日本广岛大学访学。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历史,中国古典文献学。
|
| 目錄:
|
目次
前言赫兆丰1
从《世说新语》及其刘孝标注看魏晋南北朝书籍史程章灿
“豫章太守陈蕃”的德行
——《世说新语》与地方官吏文化大平幸代
《世说》时代的“早慧”与“天真”
——以“礼教”与“自然”的冲突为视角稻畑耕一郎
《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学风气胡大雷
日藏古钞本《世说新书》鉴藏者略考金程宇
谢道韫与十七世纪朝鲜社会的家门意识金贞淑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平议刘强
王导与嵇康
——永嘉之际士风转变的一个观察陆帅
关于汪藻《世说叙录》的几个问题罗鹭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饮酒文化的内涵嬗变宁稼雨
在汉文化圈寻觅“贤媛”精神钱南秀
“渡江”
——试探《世说新语》中创造名士家族过江的形象沈柯寒
酒德辩
——以《世说新语》论汉、晋时期的饮酒与道德王楚
人物品鉴与赋学流变
——《世说》司马相如论述在汉魏六朝“辞宗”赋学系谱的位置
许东海
王羲之前期经历考补
——以《世说新语》及前人笺注为线索姚乐
文献重组与思想建构
——李贽《初潭集》的材料来源和使用俞士玲
也谈《世说》的早期接受张蓓蓓
日本“《世说》学”总案张伯伟
释六朝之“风流”朱晓海
魏晋风流与中国文化
——第二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
| 內容試閱:
|
前言
2019年8月21日至23日,“魏晋风流与中国文化:第二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成功举办。两个月后,南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的称号。南京也是中国个获此殊荣的城市。这两件表面看来并无关联的事情,实际上都与辉煌且富有特色的六朝文化息息相关。
时间倒回到71年前。1949年11月25日,时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金陵大学兼任教授的胡小石先生,应中奥文化协会邀请,在金陵大学做了题为《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讲座。讲稿原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九卷。这篇文章首次论述了南京作为“世界文学之都”的历史文化依据。在文章中,胡先生盛称:“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尤以在六朝建都之数百年中,国势虽属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学思想,多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传统之桎梏,而又富于创造能力,足称黄金时代,其影响后世至巨”;“南京文学之发展,实为东晋以下南朝时期之诸代。”由此可见六朝之于南京城市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如果要在众多典籍中,推选一部能反映六朝时期思想、政治、宗教、文学、艺术、士人人格气度的著作,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编写的《世说新语》,毫无疑问是合适的。《世说新语》所收条目虽然主要是魏晋间事,但清谈尚玄的风气和事例,在南朝仍然史不绝书。正是这部书,为我们塑造了魏晋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至今仍然散发着六朝文化的韵味,对于任何一位研究中国文学文化特别是中古文学文化的人来说,这部名著都有不可抵挡的魅力。读这部书,我们仿佛回到魏晋的历史时空当中。魏晋士大夫的行事风格、思想、人生观,魏晋时代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特征,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世说新语》的条目大都短小精炼,语言隽永,很多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逸事,而且很多故事,就发生在南京。比如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生命感叹,比如南渡诸人“新亭对泣”的家国之念,比如谢道韫“未若柳絮因风起”的机敏回应,比如王羲之“坦腹东床”的潇洒气度……
对《世说新语》的研究,早以注释的形式出现。宋齐间人敬胤个给《世说》作注。其后梁代刘孝标注凭借极为丰富的资料,为我们展示了更为多元、鲜活的历史和文献图景。唐代以后,又涌现出许多模仿、增补、点评《世说新语》的著作,如《续世说新书》《大唐新语》《唐语林》《何氏语林》《世说新语补》《世说新语鼓吹》《女世说》等等,不可胜数。《世说新语》的影响还扩展到东亚,在朝鲜和日本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世说学”。因此,无论是从《世说新语》的内容价值,还是从它所带来的长久且深广的影响来看,这部书都称得上是一部中国文学经典,也是中国文化经典,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建构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与国际传播中,占据着突出地位。
早提出“世说学”一词的,是明代学者王世懋。明人顾懋宏在《世说补精华序》中说:“弇州王长公伯仲,特加删定,以续《新语》,次公敬美(即王世懋)尤嗜此书,至谓之‘世说学’。”诚然这里提到的“世说学”并不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概念,但正所谓“作者之心未必然,读者之心未必不然”,20世纪以来,随着有关《世说新语》的专题论文、系统性专著和重要注本、译本的相继问世,《世说新语》已隐隐呈现出继《文选》和《文心雕龙》之后,成为中古文学领域又一专门之学的势头。
2017年11月初,河南师范大学举办了“首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年8月,第二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南京大学文学院主办。会议得到了众多海内外学者的大力支持。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马来西亚等3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本论文集从50篇参会论文中精选19篇,内容涵盖中国古典文献、文学、史学、美学、接受学、书籍史、域外汉籍等多方面议题,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多样,理路多元,较突出地呈现了中西学者有关“世说学”研究的成果和关注点。
需要说明的是,为适应出版要求,原文为繁体字书写的论文收入论文集时一律改为简体。编者还适当调整了全书的注释格式,以尽量保持全书格式的大体统一。至于文前的提要和关键词,原文有,则保留;原文无,亦不补。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资助。凤凰出版社许勇编辑为论文集的编校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就在编者编辑论文集期间,同济大学中文系已于2020年10月16日至18日,成功举办了“魏晋风度与江南文化暨第三届‘世说学’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特别提出了筹备和成立《世说》学会的建议。这无疑是推动“世说学”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步骤。编者热烈期盼《世说》学会的早日成立,更期待《世说》研究领域涌现出更丰硕的成果!
赫兆丰
2020年10月31日
从《世说新语》及其刘孝标注看魏晋南北朝书籍史
南京大学程章灿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贡献的一部名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世说新语》的原本虽然产生于南朝刘宋时代,但书中的内容,仍以魏晋时代人物言语轶事为主。另一方面,至迟从南齐时代开始,就有人为《世说新语》作注例如至今仍有佚文的南齐史敬胤注,参看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三章《〈世说新语〉古注考论》节《敬胤的〈世说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9—114页。,其中以征引繁博著称并在后代流传遐迩的则是梁代刘孝标的注。无论是《世说新语》原文,还是刘孝标注,其中都有不少有关魏晋南北朝书籍形态、书籍流传,以及当时人阅读情况的内容,因此,透过《世说新语》及其刘孝标注,管窥魏晋南北朝书籍史,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视角,而这个视角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潘建国《〈世说新语〉在宋代的流播及其书籍史意义》(《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主要从《世说新语》的宋代版本来看其本身的书籍史,是以《世说新语》为主体,而本文是以《世说新语》为客体。二者视角不同。。本文希望由此切入,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书籍史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书籍形态与书籍结构,也包括当时人的阅读史尤其是经典阅读史。
一、 钞本时代的文本形态
在中国书籍史上,魏晋南北朝属于钞本时代。从魏晋时代开始,纸逐渐成为当时主要的书写媒介。《世说新语》及刘注提到纸的地方不算多,据我统计,共有八次,分别见于七条故事之中,其中刘注提到的两次见于同一条。这七条都是魏晋时代的故事。其中两条见于《世说新语·方正》,说的是晋元帝父子的事:晋元帝探怀中所藏黄纸诏裂之,晋明帝作手诏写满了一张黄纸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05、311页。。可见当时的诏书是写在黄纸上的。另外五条虽然皆用于一般场合,但基本上也是贵族文士所用。当时贵族名士之间通信,多半写在纸上。例如据《雅量》记载,郗超与释道安之间就有过通信,只不过郗超寄的信写了好几张纸,而释道安的回信却只有寥寥数语:“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饷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372页。按:余氏标点,以“愈觉有待之为烦”一句为“记者叙事之辞”,非安公语也”,故列在引号之外,余书所引刘盼遂说,则以为安公此处盖引《庄子·齐物论》之语。窃以为刘说较胜,故标点改从刘氏。《雅量》中另有一则故事,说的是“裴叔则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后位仪同三司”《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351页。。裴楷被收监之时亦能求得纸笔,可见彼时纸之获得并不是那么艰难。此事发生在西晋之时。《文学》记东晋桓温北征途中,“会须露布文”,当时袁宏虽然随军从征,但正“被责免官”,桓温“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73页。。可见即使在行军途中,也随身携带有纸张,以供不时之需。总之,魏晋时代纸已成为主要书写媒介。
“纸贵洛阳”是魏晋书籍史上流传广的一段轶事。《世说新语·文学》写到左思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后人经过张华、皇甫谧两位文坛前辈的揄扬,才扭转了舆论风向,“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47页。。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故事及其刘孝标注所引《(左)思别传》、王隐《晋书》等文献中,并没有出现后来广为流传的“纸贵洛阳”的故事情节。臧荣绪《晋书》中,虽然有《三都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的描写《文选》卷四《三都赋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中华书局,1977年,第74页。《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47—248页亦引录臧书此节,刘跃进《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2册第838页汇辑各本,此处皆无异文。,但仍然没有出现“纸贵洛阳”的情节。相反,《文学》中的另一条故事,却有非常类似的描述:“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58页。这条轶事的首句与结构,与同见于《文学》的“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条如出一辙,庾亮所谓“可三《二京》,四《三都》”,与“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张华所谓“此《二京》可三”,亦极其相似,因此,这两条故事很容易被视为同一母题的叙述,而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相互纠缠、影响乃至融合。于是,在唐修《晋书》的《文苑·左思传》中,就出现了左思造《三都赋》成,“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7页。的描写。正如余嘉锡所言,“唐史臣专以臧书为本”《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48页。。具体到唐修《晋书·左思传》,其叙事就是糅合臧荣绪《晋书》和《世说新语·文学》“庾仲初作《扬都赋》成”条而成。换句话说,《三都赋》引起洛阳纸贵,应该是唐初史臣“制造”出来的神话。真正“纸贵洛阳”的,恐怕不是西晋左思的《三都赋》,而是东晋庾阐的《扬都赋》。从庾阐所处的时空环境来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纸贵建康”,而不是“纸贵洛阳”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一一就将庾阐作《扬都赋》事作为“纸贵洛阳”一典的出处。。由于《晋书》作为正史所具有的文献权威及其历史影响力,《世说新语》及其他《晋书》的声音遂被屏蔽,自唐以后,《三都赋》“纸贵洛阳”的说法,在书籍史上刻下了越来越深的烙印,积重难返。
魏晋南北朝的书籍,主要以稿本或抄本的形式流传。《世说新语》及其刘孝标注中所提到的书籍,除了经典名著之外,大多数是以篇章的形式出现或者存在的。这一点,只要将《世说新语笺疏》所附《〈世说新语〉引书索引》翻阅一遍,就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倒起,第107—131页。。
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魏晋南北朝人撰写书籍,较少大书,而更多是以篇章形式,其中,以“论”“传”标题(基本上属于论体、别传体)比较多。《世说新语·文学》载:“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195页。显然,钟会置于怀中的《四本论》,是他亲自抄写的稿本。他希望得到嵇康的反馈意见之后,再进行修改定稿。这样一篇作品,可以看作一种著述。事实上,《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四种钟会著作,亦即《周易尽神论》一卷、《周易无互体论》三卷、《老子道德经》二卷、《刍荛论》五卷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都是以“论”的面目出现的,可以确定都是以写本的形式出现。可惜的是,钟会《四本论》今已不传,但其曾经有写本存在则是可以确定的事实。
魏晋南北朝时代,纸帛简牍是书籍的主要物质媒介,篇章或书籍的分卷分篇,与纸帛简牍的物质媒介密切相关。某书有多少篇、多少卷,一篇或一卷有多长,既体现书的内容长短,也体现书的物质媒介大小。《文学》载:“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04页。我们无法确定庾敳(子嵩)所读《庄子》究竟是怎样一种版本,但是可以知道他所读的一定是个抄写本,从“开卷一尺许”来判断,此书全部展开应该是很长的,庾敳仅打开一尺多,可见其所读有限,充其量只是《庄子》篇《逍遥游》而已。
《周易》《老子》《庄子》历来被视为魏晋玄学的“三玄”,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为流行的书籍。“三玄”之中,研读《庄子》、讲论《庄子》及为之作注的学者甚多,向秀、郭象便是其中为著名的两家。“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05—206页。从此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向秀注《庄子》,并非按照《庄子》原书篇章先后顺序来进行的,其作注顺序较为随意;第二,虽然全书未竟而向秀去世,但毕竟留下了至少两种写本,其中一种是后出的别本。第三,由于这两种写本传播不广,向秀作为真正注者的身份罕为人知,郭象才敢于利用这点而欺世盗名。第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谓郭象注其实是向秀、郭象二家合作的产品。总之,此条轶事从多方面显示了写本时代文本所特有的不稳定状态,涉及形态、作者、流播、传世等方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