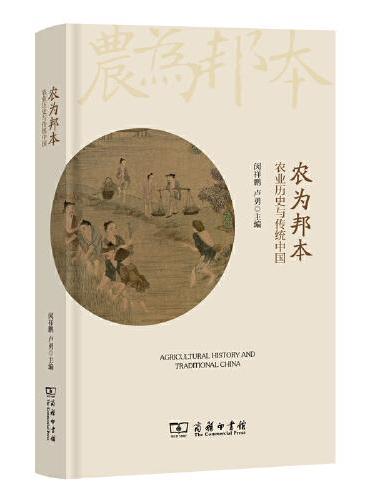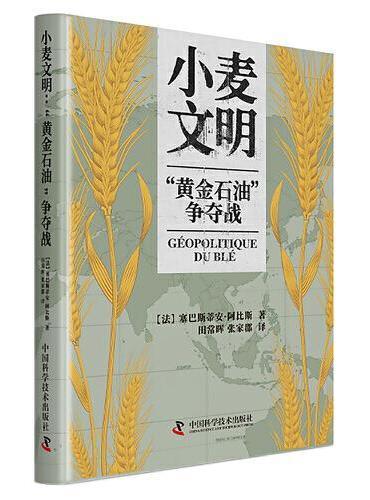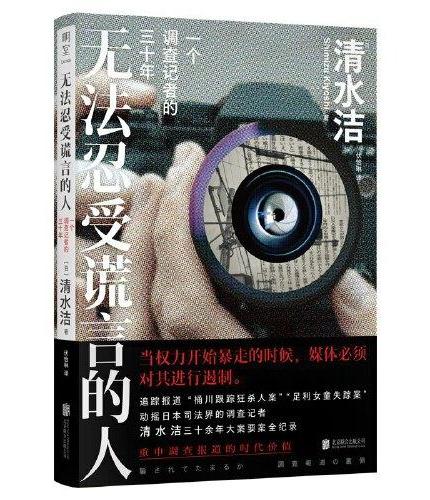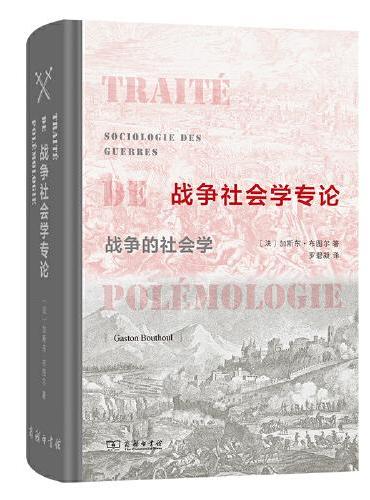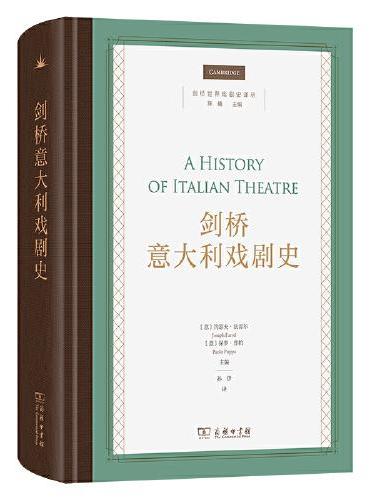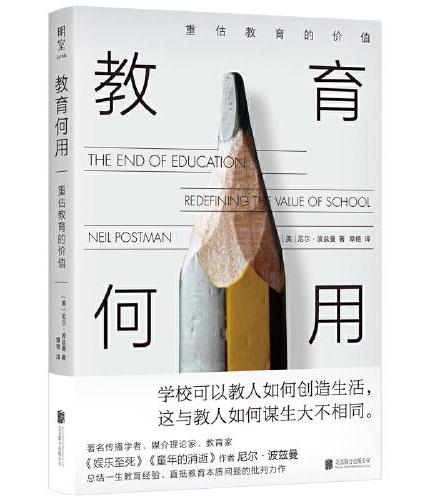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掌故家的心事
》
售價:NT$
3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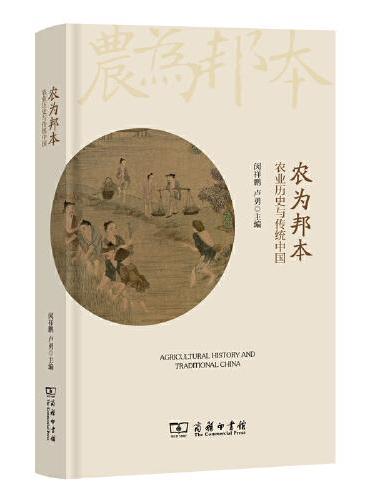
《
农为邦本——农业历史与传统中国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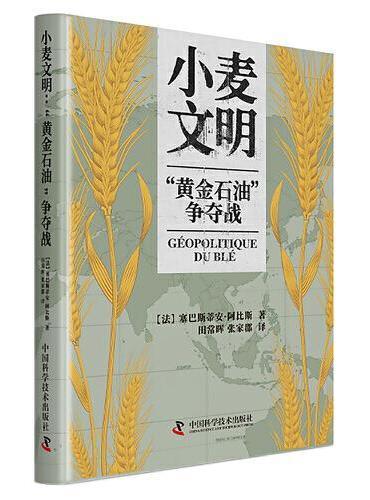
《
小麦文明:“黄金石油”争夺战
》
售價:NT$
445.0

《
悬壶杂记全集:老中医多年临证经验总结(套装3册) 中医医案诊疗思路和处方药应用
》
售價:NT$
6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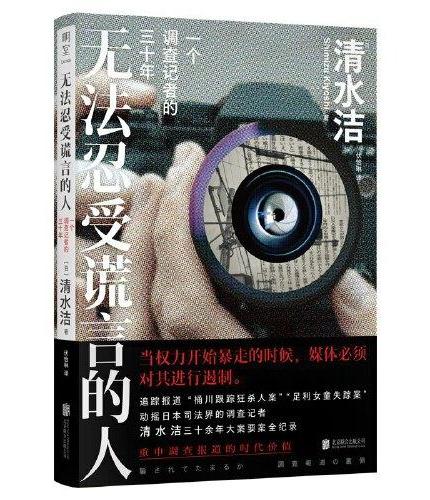
《
无法忍受谎言的人:一个调查记者的三十年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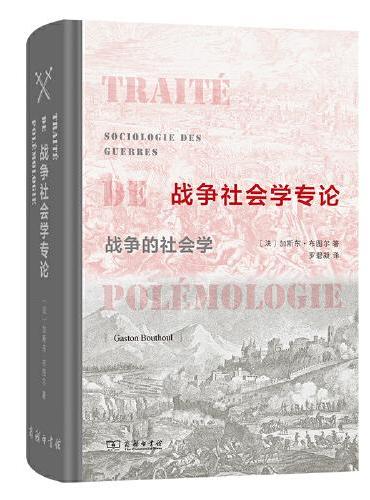
《
战争社会学专论
》
售價:NT$
5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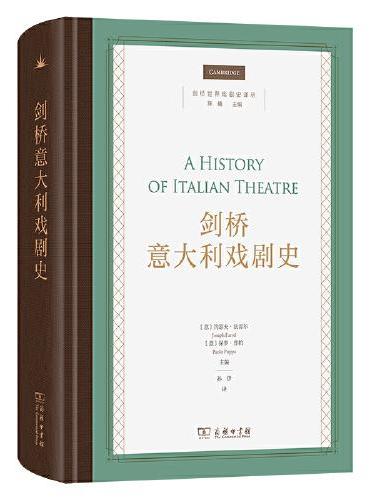
《
剑桥意大利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NT$
7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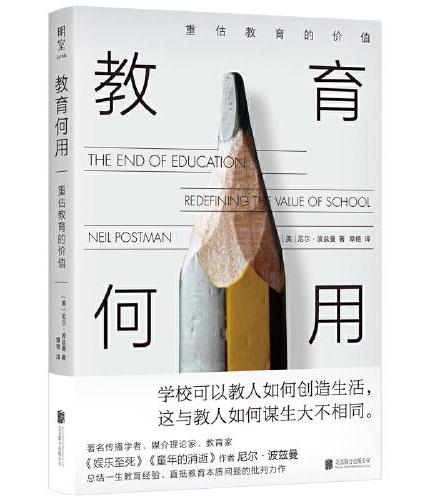
《
教育何用:重估教育的价值
》
售價:NT$
299.0
|
| 編輯推薦: |
1. 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小的女儿帕蒂·戴维斯倾心记述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的*后十年
帕蒂·戴维斯,里根*小的女儿,曾因政见不同与家人决裂,以叛逆的行径震惊世人。因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她与父亲和解,重回家庭,与家人共同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告别旅程,并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陪伴父亲的日子,以及童年记忆里与父亲、与家人的弥足珍贵的共处时光。
2. 关注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医学难题,直面每个成年人不可避免的心理挑战
平均每3秒钟全球就会产生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我国目前有1000多万患病人群,关心和照护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课题。
面对父母至亲终将老去的现实,我们该如何珍惜与之相伴的每一天?当那一天终将到来时,我们该如何与他们好好告别,又该以怎样的态度继续以后的生活?
3. 内容与形态双重匠心打磨,绝版十年后的再造与升级
特邀擅长文学翻译的译者精心重译,亲人间的温情与细腻柔软的力量氤氲纸上。文本经译者与编者数次推敲打磨,力求还原原著之精髓。
形态与内容珠联璧合,书名字体仿阿尔茨海默病做“渐退”设计,封面上的马、橡树、风筝等象征着作者记忆中与父亲一起度过的珍贵时光。
4
|
| 內容簡介: |
罗纳德·里根,美国前总统,一位慈祥的父亲,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本书记录了里根*小的女儿帕蒂·戴维斯陪伴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度过的*后十年时光,以及在其成长过程里,关于父亲的时光片段。帕蒂·戴维斯曾经年少轻狂,与父亲和家庭几近决裂,用叛逆的行为昭示着与家庭的对抗。多年后,因为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她重回父亲身边,与家庭和解,与家人一起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告别旅程。
|
| 關於作者: |
|
帕蒂·戴维斯(Patti Davis),原名帕特里夏·安·戴维斯·里根,美国前总统里根小的女儿,里根与南希·里根WEIYI的女儿,演员,作家,模特。著有《我的视角》《天使不死》。她的许多文章被刊登在《时代》《新闻周刊》《时尚芭莎》《名利场》《城乡之间》《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上。帕蒂·戴维斯曾经以叛逆著称,以各种出格的行为与父母对抗,就连帕蒂·戴维斯这个名字也是她为了抹去父亲和家族的烙印而取的艺名。
|
| 目錄:
|
1995 年4 月 / 希望的光芒
1995 年5 月,洛杉矶 / 死亡:生命永恒的伴侣
1995 年6 月 / 一次重生之旅
1995 年6 月末 / 面纱
1995 年7 月 / “漫长的告别”
1995 年7 月末 / 伟大的爱情
1995 年8 月,洛杉矶 / 父爱如山
1995 年8 月 / 失落、恐惧、成熟
1995 年9 月 / “只要我还能说话”
1995 年10 月 / 充满情感的心脏
1995 年10 月末 / 定格在心中的画面
1995 年11 月 / “我已经八十四岁了”
1995 年11 月,洛杉矶 / 平静之下的巨大力量
1995 年12 月 / 梦境
1995 年圣诞假期,洛杉矶 / 河流与牧场
1996 年1 月 / 阴沉的世界
1996 年2 月,洛杉矶 / 苦涩的甜蜜
1996 年3 月 / 你将如何度过后的日子
1996 年4 月 / 爱的纽带
1996 年4 月,洛杉矶 / 牧场里,他无处不在
1996 年5 月 / 里根图书馆
1996 年7 月,洛杉矶 / “就像在和云彩说话”
1996 年7 月 / 刻在照片中的记忆
1996 年8 月 / 失去牧场,父亲缺席
1996 年10 月 / 他正在慢慢离去
1997 年2 月,洛杉矶 / 活在当下
2004 年6 月3 日 / 月圆之夜
2004 年6 月4 日 / 那一刻已经近了
2004 年6 月5 日 / 他从未离开
后记
|
| 內容試閱:
|
序言
大约十岁时,我会和父亲一起驱车前往儿时家中拥有的牧场。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我们驶离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走上了熟悉的山路。这条路将把我们带往阿古拉山的田野与荒芜的原野。出城的路上,我们聊起了父亲那匹名叫南希·D 的马和它即将出生的马驹。这次怀孕并不在计划中。别人送给父亲的一匹阿帕卢萨种马冲破两道围墙来到南希·D 的身边,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功。
车子刚一驶入牧场的仓院,我们就看到了牧场照管员雷,心知肯定大事不妙。他的脸上布满泪痕,哭肿了双眼,垂着脑袋站在父亲面前,无法直视他的目光。前一天夜里,南希·D 死于一种未知的病毒。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被感染的。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迹象。病毒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杀死了它和它腹中的马驹。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南希·D 是我骑过的匹马。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常把我抱上马鞍,让我坐在他的前面。等我长大些,他会把我拽到南希·D 的背上,领着我在马场上转悠。它很有耐心,性情沉稳,似乎知道自己背上的这个小姑娘还年幼无知、缺乏骑马的经验。那天早上,当我在蔚蓝的天空下抬头望向父亲时,他并没有流泪,而是用深情、温柔的表情仰望着蓝天…… 仿佛思绪已经飘向千里之外。
“你为什么不哭呀?”泪眼蒙眬中,我问他。
他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头,望着我的双眼说:“因为我正在回忆自己和它共度的所有美妙时光。我们一同经历过一段美好的岁月。”
这是我学到的关于死亡的课—超越它,回顾已经逝去的生活,哪怕只有一瞬间的美好,也是珍贵的记忆。它们能使我们的生命得以维系,而这也是父亲试图传授给我的经验。
父亲去世的那一天,我曾在他的耳畔低语:“你又能见到南希·D 了。你们可以像过去一样,踏上漫长的旅途。”这话充满了他一直希望我能拥有的期盼—期盼他安息的灵魂能够听到。
他去世后的那些天,那几个星期,我发现自己的脑海中总是浮现我们站在牧场上的画面: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清晨,父亲的目光仰望着天空。他对死亡的反应是记住逝去的美好生活。回忆涌上心头之际,我发自内心地问:你在哪里?
撇开更大的问题不谈,我知道有个地方一定能够找到我的父亲。那就是我从1995 年4 月开始书写的手稿。1997 年2 月,我把已经写了好几百页的手稿搁在了一旁。我动笔,是为了缓解那年春天突如其来的悲痛—六个月前,父亲向全世界宣布,他被确诊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我不知道,为何过了这么多个月,我才在谁也无法掌控的命运下崩溃。悲痛拥有自己的时间表。它说不定也有仁慈的一面—先是震惊,然后是麻木。我们随波逐流,心知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还是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意味。
无论如何,那一年的4 月,我开始动笔书写某种日记—在辗转无眠的夜晚,在万籁俱寂的黎明;有时是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有时是在哥伦布大道上的室外咖啡馆。我当时住在纽约。中央公园里的树木已经萌发出新的叶片,处处花团锦簇。温暖的空气如同波浪般翻涌。我沉浸在崭新的生活中,就连与母亲的关系也开始发生转变……
在令人寒心沮丧、让父亲深深受伤的多年家庭战争之后,我们悲喜交加、心平气和地一同踏上了失去父亲的艰难旅程。母亲称这段路为“漫长的告别”。当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在创作一本书时,用它作为书名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近两年的时间里,我都在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悲痛中穿梭,在回忆、恐惧与沉重得令人几乎无法忍受的哀痛中蹦跳。我在纽约谋了一个生计,对母亲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还会尽可能回到加利福尼亚州,花时间陪伴父亲。我笔耕不辍地疯狂写作,试图去理解死亡,因为它一直在拖住我们的家庭,予取予求,定义我们的人生。我们还将从哪些方面失去我的父亲?残忍的阿尔茨海默病治疗过后,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年复一年眼睁睁地看着他日渐远去,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多年来,我和姐姐莫琳一直在互相争斗,彼此忌妒,多半是为了父亲。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抛却了矛盾,学会了如何成为姐妹,两人之间充满了关爱的长途电话也拨得越来越频繁。
她做了黑色素瘤手术,正在接受长达一年的干扰素治疗。治疗使她备受折磨,她变得体弱多病,无法从萨克拉门托的家中赶来洛杉矶探望父亲。我想,相比癌症治疗,她为此所受的折磨肯定更令她心痛。
1997 年2 月,我将手稿放在了一旁。令我心绪不宁的悲痛已经日渐平息。展望未来,我明白自己将不可避免地花上数月,也许是数年去等待一个结局。阿尔茨海默病紧紧锁闭了所有的门与出路。无法赦免,无处可逃。时间成了敌人,如同绵延数英里的休耕田,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我推断,要是我锲而不舍地为这本书添枝加叶,终肯定会写出一本上千页的大部头,其中大部分讲述的都是漫长的等待,等待事情的恶化或是终结,而我和我爱的人只有无助,束手无策。用医学术语来说,这属于“停滞期”。也就是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病情会沿着某种平稳得出奇的轨迹发展,一日日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这种状态能够持续数月,然而他们却是如履薄冰。改变终将到来。摔倒。下一阶段。要是死亡没有先一步夺走他们的性命,那么病情就会恶化。
1997 年,我搬回洛杉矶,离父母更近了,离父亲的离开也更近了。接下来的七年间,我曾为杂志报纸投稿,偶尔还会写写我们全家的经历。我会把这些文章看作明信片。我越发清楚地意识到,世界竟然如此在乎我的父亲,想要知晓他的病情,知晓我们过得如何。那些年间,阿尔茨海默病已经走出了阴影。人们会公开讨论这种病症,既不会感到羞耻,又不会感到尴尬。于是,在某个特定的节日到来,唤起了某些记忆(许多遭到阿尔茨海默病侵袭的家庭都会被这样的记忆困扰)时,或是在我们漫长的告别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一定要被记录下来的剧变时,我都会书写这样的“明信片”。
那些年间,我们的家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莫琳再次被黑色素瘤击倒。不过这一次,黑色素瘤已经无处不在,在她的身体里横行霸道,所向披靡。她是个英勇的斗士,拒绝投降。2001年2 月,她住进了圣莫尼卡的圣约翰医院约翰·韦恩癌症病房。父亲也在那段时间摔伤了髋部,被火速送进了同一家医院。罗恩从西雅图飞了回来。我们去了某一层楼探望莫琳,又去了另一层楼探望父亲。莫琳已经病入膏肓,连迈下三层楼去看看她崇拜的父亲都做不到。就算她去得了,父亲也未必认得出她。
如今,我的母亲不得不独自一人睡在他们的床上。她的爱人、她数十年的伴侣此刻不得不睡在医院的病床上。父亲昔日的办公室现在已经变成了他的卧室。我们必须找护士照料他。有人告诉我们,他几个月内就将离开人世。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还能再活四年,成为阿尔茨海默病的俘虏,卧床不起。
2001 年8 月9 日,莫琳在萨克拉门托的家中去世,身旁有丈夫和女儿的陪伴。我们的家庭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日渐缩小。
接下来的一个月,整个世界天翻地覆。9 月11 日,两座摩天大楼在那个可怕的日子里轰然倒塌,摧毁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它摧毁了人们的信仰和对未来的希望,也毁灭了所有人心中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所熟知的生活结构被撕得粉碎,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恐惧感。
我和母亲站在父亲的床边,将发生的事情悉数告诉了他,即便他已经无法清醒地理解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遭遇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对他耳语,“我们再也无法和从前一样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我比前几年更加想念他了,而我从未想过这份思念还能更浓。可事实就是如此。作为他的女儿,我想念他。我知道他至少能说些什么,让我展望没有眼泪、不再心如刀绞的将来,想象一下不再那么痛苦的明天。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也想念他。我们的国家正创巨痛深,迫切地需要慰藉与安抚,需要一只引导的手和一个令人安慰的坚强声音…… 没有人能够给予我们这些。我的父亲是沉默的。那个正占据着美国总统办公室的人并不知道如何安抚一个沉浸在悲痛中的国家。
贝莱尔的基督教长老会举办了一场礼拜仪式。我和母亲参加了,坐在我的父母昔日常坐的一张靠背长凳上。我所坐的靠近通道的座位就是父亲常坐的位置。他有幽闭恐惧症。我和他一样备受这种恐惧症的折磨,所以很高兴能够坐在他的座位上。当唱诗班唱起《美丽的美利坚》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为父亲深爱过的这个国家哭泣。我曾在20 世纪60 年代为她挥舞过拳头,也曾在80 年代恨她夺走了我的父亲。他成了总统,她则成了他更加重要的孩子。我为躺在几英里外病榻上的那个男人而哭泣,因为他无力帮助自己如此深爱的国家复原。我为每一个面对骤然残忍失去的人哭泣,因为他们本以为明天还能见到自己心爱的、在意的人。我希望能探寻父亲要说的话,知道它多多少少可以安抚遍布全身、敞开大口的新鲜伤口,可我不能。他的智慧,他在危急时刻抚慰人心的能力都已被某种疾病带走。它不在乎你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只会因为你挡了它的路而袭击你。
父亲去世后的第十天,我从书架上取下一盒稿件。这些稿件是我自1995 年4 月以来写下的,题目名为《漫长的告别》。那是个雾霭重重的早晨,让我想起了父亲生命的后一天,那个柔和的、白色的早晨。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慢慢阅读,在回忆当年的过程中又成了那个刚刚开始克服丧父剧痛的女儿—他的离开给世界留下了一个空洞,永远无法被填满。当时我并不清楚,作为缓慢死亡的前奏,阿尔茨海默病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又将如何模糊父亲身上独一无二的本质。1995 年,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疾病。我们知道它是一片不毛之地,但那又意味着什么?在死亡的土地上,我们都会想象自己能够偶然发现几片绿洲,意外地找到郁郁葱葱的森林。在阅读这些书稿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和莫琳都曾短暂怀抱过这种幻想。
经历了阿尔茨海默病之旅,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片甲不留”的疾病。你以为会被留下的东西,一样都不会留下。不过,在告诉你这一点时,我必须对你说的是,如果你的身边有谁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只要你敞开心扉、放开思想去密切关注,就会发现这种疾病永远不会跨越灵魂的界限。多年来,我一直都在与父亲进行温情、真诚的交谈。这是我们两人之间心灵的交谈,有时还是在彻底的沉默中进行的。有人会说,这是不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的,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不要相信他们。
1995 年,我动笔创作这本书时曾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这不是一本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书,而是一部仅仅与悲伤有关的作品。我错了。阿尔茨海默病在这些书页间成了挥之不去的存在。它是一个无情的海盗,一个无人能及、可以偷走整个人的小偷。能够战胜它的是灵魂。父亲用自己临终前的后一刻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但这终究还是一个悲痛的故事。它讲述了学习如何跌跌撞撞地迈出凌乱的步,即便前路昏暗、布满意想不到的障碍,也要努力走下去的故事。
书中还包含一些混乱的内容—我对母亲出售牧场的决定感到十分矛盾。我想要紧紧抓住曾属于父亲的一切不放,主要是因为我无法紧握住他不放。他正在离去。什么也无法将他归还给
我们。要是我能够留住他如此深爱的那片土地……
对于里根图书馆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我也十分矛盾。我对它的看法与我过去对美国的看法一样。它就是一个机构,以我无法想象的方式拥有了我的父母。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我读到这些手稿时,还有想要撕掉那几页的冲动。但是我没有。当时刚刚陷入悲痛的我就是如此心烦意乱。故事的叙述被我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如今,父亲已经被安葬在图书馆里,母亲也将长眠于此。在漫长的一周哀悼活动的后一天,我们站在那里,头顶是绵延数英里的天空,脚下是起伏数英亩的土地。我终于明白父母为何会爱上那座山巅,又为何希望将自己安葬在那里。
我们发现自我,安排生活中的轻重缓急,从开端到结局,经历了悲欢离合。时间如长流般,载着我们一路改变。在学习哀悼的过程中,我们逐渐长成了自己一直立志要成为的人。原来回首过去就是为了了解现在的自己。
在一个晴空万里、落日熔金的傍晚,我们按照父亲的遗愿将他的骨灰盒留在了图书馆。但我们永远也不会丢下他,他也永远不会远离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都会记住这个男人。他热爱美国,相信这片国土和它所能带来的希望。他们还会记住他对总统一职的重要性。
作为他的女儿,我会记住他那健壮的双臂曾将我抱上马背,教导我无论何时跌倒,重要的都是重新爬起来,这样才不会让恐惧有机可乘。我会记住他曾在大海上教我如何乘着海浪冲向沙滩,或是径直游向海浪,从浪头滑向较为平静的水域。我会记住他对天空了如指掌—能够指出飞马星座、北斗七星、猎户星座…… 而且永远都知道北极星的位置。我小时候去芝加哥探望祖父母时,他曾告诉我,北极星能为水手指引回家的路。如果你迷路了,就抬头去找北极星。
在芝加哥的那个晴朗的夜晚,他教会了我抬头仰望。那时我还太过年幼,父亲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我是怎么记住这一切的。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某个清晨,阳光如同奶油糖果般洒在我们的肩头。他的爱马在午夜时分死去了,他却教我要抬头仰望。
我一直在努力做一个优秀的学生。我会在夜晚安静的时候醒来,通常是凌晨三点钟左右。不知为何,我就是会在那时醒来。和他为我讲述的水手一样,漂泊的我迷失了方向,分不清东西。我想要知道父亲去了哪里,于是走到床边,在天空中找到了那颗北极星。这就是父亲教我的,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时,就去寻找北极星。
我的父亲永远向往着回家。
1995 年7 月 “漫长的告别”
与所爱之人道别,
那句再见,不仅是道给即将离开的人,
也是道给他在人生旅途中积攒下来的点点滴滴。
阿尔茨海默病缓缓夺走一个人生命的过程被我的母亲称为“漫长的告别”。这是她公开发表过的少有几句评论之一。面对论及我父亲健康状况的话题,我们一致选择了用毕恭毕敬的沉默来掩饰。这是一种令人心碎的说法。她告诉我,自己再也不会重提这句话了,因为它催人泪下。
我刚刚结束《天使不死》的巡回售书活动,没有多少时间顾得上流泪。在飞机和陌生的酒店房间中,我一有空就睡觉,在根本没有机会整理的行李箱中飞快地东翻西找,从一个采访奔赴另一个采访。绝大多数采访都是友好的,充满了鼓励的意味。成为一名作家、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是我的选择。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历次的巡回售书“战役”中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可以想见,即便是顺利的巡回售书活动,也总会有一场采访令你对采访者的粗鲁迷惘地摇头。
事情发生在一座小城市里。城市的名字我就不提了。那是一场午后的脱口秀节目。节目主持是一个想成为却永远成不了奥普拉的女人。她开口询问了我父亲的状况。针对这个采访问题,我的答案一成不变。“他很好。”我说,“在涉及他健康状况的问题上,我的家人需要保留隐私。不过他很好。”
这样的答案通常就已足够,谁也不会进一步逼问。“那他还记得你吗?你能和他对话吗?”她显然认为,问几句我已明确表示不会回答的私人问题是完全合理的。
“如我所言,我们需要保留隐私。我觉得我们有这个权利。”
“你们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现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是不是开始注意到他会忘东忘西,或是把事情搞混?”
“我已经明确说过了,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我的语气更强硬了。我能感觉到现场观众的尴尬。她却又试了一次。
“现在和他对话是什么感觉?你都会和他聊些什么?”
“这是我第四次也是后一次给出同样的答复了。我们需要隐私。无论你用多少种不同的措辞问相同的问题,我都不会回答你的。”
观众鼓起掌来。她终于把话题转移到了另外一系列的问题上。
节目结束后,当我急匆匆地走向出口时,她开口说道:“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只不过是在尽一名记者的责任。”
我想我没有搭理她。
巡回售书的另一个难处虽然有些悲哀,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甜蜜的。一次又一次,在谈及父亲和我为他写的书时,我都会沉浸在记忆的荣光中,想起他忠实的信仰和讲过的故事中饱含的精神食粮。“漫长的告别”这句话时常在我的脑海中低语,如同一缕清风穿过敞开房门的屋子。我想流却没空流的眼泪在心里积成了一汪池水—耐心等待我靠近、深不见底的池水。回到纽约,我一心只想睡觉和哭泣。
在某种程度上,这趟巡回售书让我能够直面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直面自己过去的选择,直面我与父母经年的斗争。采访前,我会在演员休息室给母亲打电话,或是在酒店房间和机场里拨通她的号码。她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我还是能够看到,那些年的放逐如同荒原般在我的身后铺展开。
名望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即便你是伴随它长大的,也还是会被它惊得目瞪口呆。你以为自己已经对它了若指掌,能够按顺序安排好轻重缓急,思维清晰地做出选择,但大多数人都会犯错。我觉得聚光灯次照在你身上的那一刻才是重要的。没有哪个错误能比那一刻犯下的错误更加严重。它是个黄金时刻,并且永远不会重来。其他的时刻还会到来—我不相信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能把事情做好—但永远不会再那般纯粹、毫无负担。
父亲当选总统那年,我28 岁。尽管对人们强烈的关注并不陌生,但我们还是陷入了媒体的旋涡中。显然,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父亲,我们其余的人也处在了聚光灯下。我犯下的个错误就是以为自己能够应付一切。要是我能多一些犹豫,少一些笃定,就能多提几个问题,思考更多的选项。结果,陪伴我前行的却是对自身政治信仰极度的热诚。我曾在大型反核集会上发言,接受采访,把自己塑造成了父亲的政策引人注目的反对者之一。要是我能多一些外交手段,少一些尖锐的言辞,其实本可以成为父亲与自由主义观点之间的桥梁。相反,即便是在那些与我持相同政治信仰的人眼中,我也不过是个愤怒的女儿。
宣泄完初的愤怒,我又开始表达更加私密的情感,把在全世界面前展示我家庭的创伤视为己任。我的怒火招致其他人的愤怒。说我收到过恐吓信,那是轻描淡写。
这些问题大多是在巡回售书的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我其实很难摆脱自己的过去。每个人都在成长、转变和学习,但在公众的瞩目下经历这一过程会更加艰辛。大多数人都是宽容的,但我能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记忆是长久的。这就是在公众的目光中成长的难处:你永远处在别人对你的记忆之中。
在我的想象中,我会和父亲谈论此事,告诉他我多希望自己当初能以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发生过的一切。也许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针锋相对的观点可以是一种启示,而不是一场战争。在我的想象中,他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微笑地说着“我很高兴我们现在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了”之类的话。然而这段对话只能发生在我的想象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他身上可以参与对话的那一部分已经远去了。
碰上阿尔茨海默病之类的疾病,荒凉的感觉也会属于患者的朋友和爱人—那些见证了过程还要被丢下暗自神伤的人。你会眼睁睁看着一个人退到某个陌生的地方,心知自己无法跟上。失去他,你将一个人在荒野中徘徊,耳边回响着山坡上传来的回音。那只是回音—声音传来的地方越来越安静—于是你会更加仔细地聆听。
如今,母亲的很多话都是以“我记得……”开头的。
你之所以会为自己的记忆注入生机,是因为就在那里、就在你的眼前,坐在他过去经常坐着的椅子上,或是走在楼道里,抑或凝视窗外时,你都会想起往事。记忆被抹除后,剩下的就是一片空白,因此,每当想起某些画面或是只言片语,你都会欣然接受,紧紧抓着它们,拂去上面的灰尘,期待它们能永远鲜活。
现在,我时常想起父亲讲过的故事,希望能再听到他讲故事的声音,看到那双可以激活孩子的想象力、闪烁着喜悦光芒的蓝色眼睛。但我只能依靠回声来滋养自己。我想要他再告诉我一次,鹰与秃鹫的区别。它们的飞行轨迹、翅膀存在细微的差异。其中一种在朝猎物俯冲前会多盘旋一会儿。我过去常把它们弄混。要是我们在牧场上发现了二者中的任何一种,他就会耐心地为我一遍遍解释说明。我还是会把它们弄混,但我已经不能再问他了,因为他也记不得了。我想和他骑上马,朝着翠绿的山坡飞驰,可他已经永远无法再骑马了。
一次,在前往牧场的途中,车子正沿着穆赫兰道行驶。他停下车,对山坡上的一个男人说,他正在采摘的蓝羽扇豆是受保护植物。父亲解释得彬彬有礼,于是那个男人从山上爬了下来,手中却仍攥着非法采来的花朵。父亲相信,只要有可能,鲜花和野生动物都应该留在它们的应属之地。我五岁那年便能认出响尾蛇,知道要绕一个大圈才能躲开它们。我还知道,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能杀害一个生命。
我从未如此深切地渴望过童年—哪怕只是尝上一口,都如舌头上的威化饼,成为我与已然失之交臂的过去甜蜜的交流。成年人会带着可悲的智慧回首往事,想起儿时的我们是何等幸福,根本不知道人生在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进,也不知道岁月在倒数计时,仿佛时间不可能在我们的肉体上刻下痕迹。蓦然回首,我们才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地把握某些时刻,久久凝视某个人的面庞或是壮观的夕阳,更仔细地聆听某个终有一日会归于沉寂的声音。我们还希望自己走得再慢一些,徘徊得再久一点儿,踏上不同的道路。我们将大大小小的往事储存在记忆中,期盼它们不会破碎或褪色,因为它们是我们活过这一世的见证。
与所爱之人道别,那句再见,不仅是道给即将离开的人,也是道给他在人生旅途中积攒下来的点点滴滴。我的父亲正迈着坚定的小步远离曾经的自己。我不知道还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东西—有关土地、马儿、鸟儿的飞行轨迹,还有只能在某些区域茁壮成长的植物。在牧场的橡树林里,他曾找到过一种打湿后会像肥皂一样起泡的植物。
他相信,要让孩子们为生活中的灾难做好准备,否则这些波折和突变有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他会为我们设定几个情景,问我们打算怎么应对,然后温和地纠正我们。这样一来,就算灾难降临,知识也能成为我们的盟友。
有一次他问我:“如果你的卧室起火,房门却被堵住了,你会怎么做?”
看过无数电影的我回答:“我会冲破房门。”
“那你就没命了。”父亲冷静地回答,“你刚走到距离火苗不到两英尺的地方,就会被热气灼伤肺部。”
“那我就打破玻璃,跑到院子里去。”
“好的。”他点了点头,“你怎么打破玻璃?”
“用一把椅子。”
我总是能够清楚地分辨出,课程重要的一部分何时到来。父亲会俯下身,用缓慢而谨慎的语气对我说话,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话能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你可以拿出一只抽屉,把它从窗户里推出去。”他告诉我,“这样就能形成一个整齐的缺口,不会在你爬出窗户时将你割伤。”
他让我为火灾、空袭警报和地震都做好了准备,却没有让我准备好失去他,没有给我工具去应对满腔悔意的冲击。我后悔自己厌恶他的那段时光,后悔曾甩掉他伸出的手,选择了如矛刺般尖锐的言语。那些都是深埋在我心里的记忆。如果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那么我还没有找到。
失去父亲或母亲的故事中通常都包含着发现的过程。打开一只抽屉、一本书、一盒信,你便能知晓从前并不了解他们的地方。他或她在喜欢的书本空白处潦草地写下想法,或是你无意中发现某封信。有些时候,我们是在父母去世后才了解他们的。我的母亲一直在收拾抽屉—我想,她应该是有意这么做的,因为她知道我们的生活有一部分是公开的,要面对全世界窥探的目光。她想要知道别人会发现什么。在父亲的其中一只抽屉里,她找到了给我的一封信。那是一份草稿,尚未寄出,是在我的自传出版前写下的。信中,他表示自己被我的怒火伤透了心,也表达了家庭和解的愿望,还有他对更多美好时光的记忆。信的开头,他写道“随着我年近八十一岁……”然后又划掉了自己的年龄,在上面写了一行“如今我已经八十一岁了……”
我想象,在日子缓慢流逝的过程中,他也许曾无数次拿出这封信,感觉自己的生命已所剩无几。我永远都无法知道他多久便会把它拿出来添上几笔,再重读一遍,也不知道他为何永远不曾将它寄出。在信的末尾,他写道:“求你了,帕蒂,别带走我们对那个真心疼爱、心心念念的女儿的回忆。”
如今,这封信已经被放进了我的抽屉,陷入了无边的沉寂。我多希望自己能和他聊一聊它,然而他对它的记忆可能已经消失在了地球的边缘。
人们离世时都会带走自己隐藏的秘密—烛光闪烁的欢乐记忆、支离破碎的悲伤记忆。他们离开了,记忆也将随之而去。我们剩下的人则会被丢在黑暗中,怀抱着再也没机会提出的问题,和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语。因为我们来得太迟了。
讲述这场“漫长告别”的任务已经落在了我的身上。尽管这些日子并不沉重,却还是需要被记录下来,因为它们珍贵万分。我们跨越苦痛去寻找救助,双手如同伸向圣杯,充满渴望。我们碰不到它,却知道它的存在。我还精进了忍住眼泪这门艺术,像只骄傲的野兽,将泪水储存起来,然后退回我的洞穴,好给它们应有的地位,尊重其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段漫长的旅程就是曾经似乎缝合在一起的确定性—我们在另一个人身上了解到的一点一滴—逐渐分崩离析的过程。你会习惯这样的疾病带来的惊喜,习惯那些令人困惑的短语,习惯突如其来的转折。你不指望什么,但已经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更加自如地呼吸。这将永远是一场等待的游戏。
即便没有疾病带来的并发症,对于年逾八十的人来说,人生的隧道也越来越窄。多年前,父亲在给我写信时就已经有了这种感觉。有些时候,我很想知道事情会在何时发生,我何时才会得到消息。半夜吗?黎明吗?无论是什么时候,我都十分清楚,父亲的离去将是一段平静的旅程。
昨天,我在针灸师的床上睡着了,身上各处经络上插着活血化瘀的针,坠入了漆黑一片的深度睡眠中,身陷紧张得令人心惊肉跳的鲜活梦境。我看见父亲从身体里迈了出去,离开八十四岁的自己,成了一个更加年轻、更有活力的男子,脸上还带着灿烂的微笑。他生龙活虎、热情洋溢地张开双臂,走向我的母亲,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的。
尽管一切终将有所不同,但都会归于平静。摆脱了悲伤、恐惧与无情的苦痛,生活将进入某种模式。就眼下的情况而言,生活就是等待。这就像是在闪电后数秒,等待你知道必将到来的雷鸣,试图预测风暴还有多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