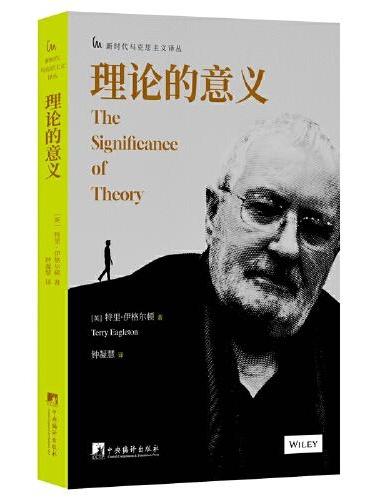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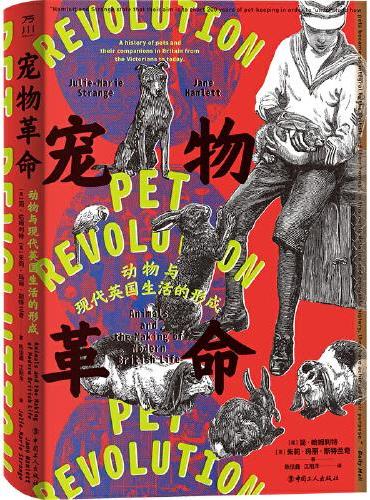
《
宠物革命:动物与现代英国生活的形成
》
售價:NT$
3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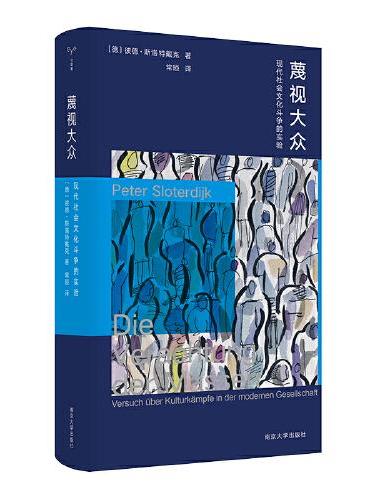
《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蔑视大众:现代社会文化斗争的实验
》
售價:NT$
2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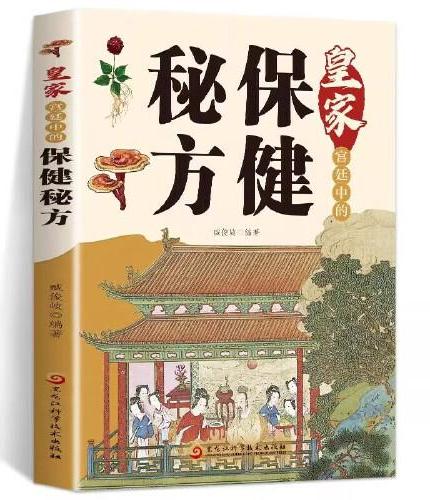
《
皇家宫廷中的保健秘方 中小学课外阅读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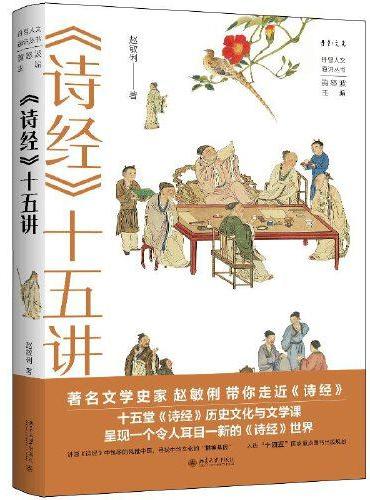
《
《诗经》十五讲 十五堂《诗经》历史文化与文学课 丹曾人文通识丛书
》
售價:NT$
3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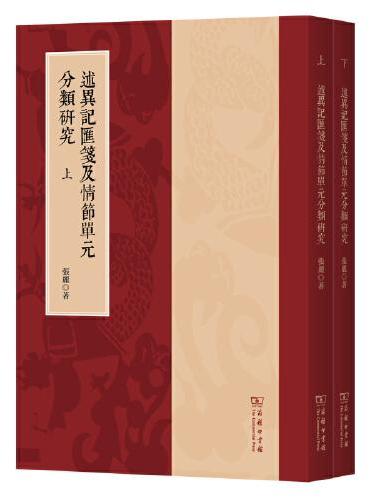
《
述异记汇笺及情节单元分类研究(上下册)
》
售價:NT$
4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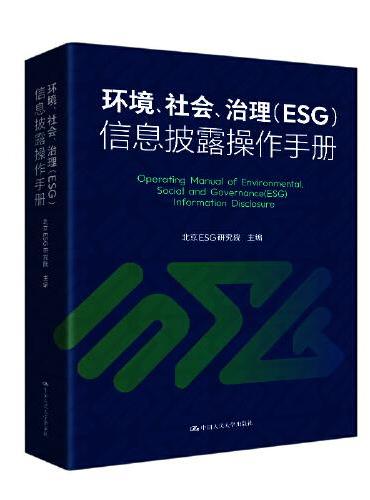
《
环境、社会、治理(ESG)信息披露操作手册
》
售價:NT$
1190.0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
《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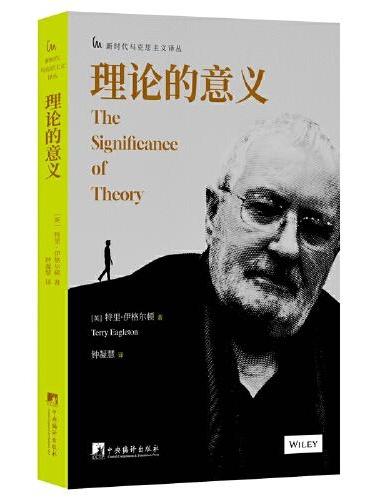
《
理论的意义
》
售價:NT$
340.0
|
| 編輯推薦: |
关键词:被辜负的爱情,遗憾的婚姻,人生的意义,创伤与疗愈你的生活方式,就是你的才能所在。——海明威海明威短篇杰作精选,充分代表海明威的创作成就。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译者小二增补修订本
赠送天然香氛书签(松林香型),浸入式的阅读体验。
创意装帧形态,整书刷边。
32开精巧小开本,随身携带。
软糯蒙肯纸,触感舒适。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收录了海明威的十六篇短篇佳作。雪山上的豹子,河边的垂钓人,咖啡厅中的老者……十一个貌似淡薄的故事蕴含了人世间言不尽的沧桑。海明威独特的“冰山”式文风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得到了高度的呈现。
|
| 關於作者: |
|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20世纪著名作家,善于运用极其简练的语言表达极其复杂的内容,其独特的“冰山理论”对20世纪英美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54年因《老人与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生性喜欢冒险,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有过四次婚姻,于1962年饮弹自尽,结束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
| 目錄:
|
乞力马扎罗的雪
白象似的群山
弗朗西斯 ? 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印第安人营地
杀手
雨中的猫
桥边的老人
某件事情的了结
三天大风
医生和医生的太太
世上的光
大双心河(一)
大双心河(二)
一天的等待
在异乡
|
| 內容試閱:
|
乞力马扎罗的雪
覆盖着积雪的乞力马扎罗山高19 710英尺,据说是非洲境内的一座山峰。山的西主峰被马赛人1称作“纳加奇—纳加伊”,意思是“上帝的殿堂”。靠近西主峰的地方有一具冻僵风干了的雪豹尸体。雪豹在那么高的地方寻找什么,没有人做出过解释。
“神奇的是一点都不疼,”他说,“这时候你才知道它发作了。”
“真是这样吗?”
“是。很抱歉,你肯定受不了这股气味。”
“别这么说!请快别这么说了。”
“你瞧瞧,”他说,“到底是我这副样子还是这股气味把它们给引过来的?”
男人躺着的那张帆布床放在金合欢树宽大的树荫下,他越过树荫,看着前方令人目眩的平原,除了地上蹲着的那三只令人生厌的大鸟外,天空中还有十多只在盘旋,它们掠过天空时,在地面上投下了迅速移动的影子。
“从卡车抛锚的那天起,它们就在这里打转了,”他说,“今天是它们次落下来。刚开始我还仔细留意过它们飞行的姿态,想着有朝一日写小说时能用上。现在想想真好笑。”
“你别这么想吧!”她说。
“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他说,“说说话我觉得轻松多了,但我不想烦你。”
“你知道我不会烦的,”她说,“我只是因为什么都做不了,感到特别不安。我觉得我们应该尽量放松一点,等飞机来。”
“或者等飞机不来。”
“请告诉我我能做些什么。肯定有我能做的事情。”3
“你可以把这条腿割掉,这样也许会阻止它的蔓延,不过我很怀疑。要不你一枪把我崩了。你现在的枪法很不错了,还是我教会你射击的,不是吗?”
“请不要这么说话。我可以给你读点什么东西听听吗?”
“读什么?”
“随便在书袋里找一本我们没有读过的。”
“我听不进去,”他说,“说话容易。我们吵会儿架,时间就过去了。”
“我不吵架。我从来就不愿意吵架。不管我们有多紧张,都别再吵了。说不定他们今天会搭另一辆卡车过来。说不定飞机会来。”
“我不想动了,”男人说,“现在走不走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除了能让你心里轻松一点。”
“这是懦弱的表现。”
“你就不能让一个人死得舒服点吗?干吗非得骂他?对我说粗话又有什么用?”
“你不会死的。”
“别说傻话了,我眼看着就要死了,问问那帮狗日的。”他朝那些脏兮兮的鸟蹲着的地方望过去,它们光4
秃秃的脑袋埋在耸起的羽毛里。第四只鸟飞落下来,它先紧走了几步,然后摇摇晃晃地朝着蹲在那儿的其他三只鸟慢慢走去。
“每个营地里都有这种鸟,只不过你从来没有注意到它们。你如果不自暴自弃,就不会死。”
“这是从哪儿读到的?你真够蠢的。”
“你应该考虑一下别人。”
“老天爷,”他说,“这可是我的老本行哟。”
他随后安静地躺了一会儿,他的目光越过热气腾腾的平原,落在了灌木丛的边上。黄色原野上点缀着小白点一样停留片刻的野羚羊;更远处,绿色的灌木丛衬托着一群斑马的白色。这个营地很舒适,背靠山丘,大树遮阴,不远处就有上好的水源。清晨时分,一个几乎干涸了的水塘里扑腾着几只沙鸡。
“你不想让我念一段?”她问道。她坐在他帆布床边上的一张帆布椅子上。“有点凉风了。”
“不想听,谢谢。”
“也许卡车会来。”
“我根本就不在乎卡车来不来。”
“我在乎。”5
“很多我不在乎的事你都蛮在乎的。”
“没那么多,哈里。”
“喝一杯怎么样?”
“这对你有害。黑皮书1上说了,什么酒都不能碰。你不能喝酒。”
“摩洛!”他大声叫喊道。
“来了,先生。”
“拿威士忌苏打来。”
“是,先生。”
“你不该这样,”她说,“这就是我说的自暴自弃。书上说了酒对你有害。我知道它对你有害。”
“不对,”他说,“它对我有好处。”
这么说一切都完了,他想,看来再也没有机会去完成它了。就这样结束了,在为该不该喝一杯的争执中命丧黄泉。右腿染上坏疽后,他不但不感到疼痛,连恐惧也随着疼痛一起消失,他现在感觉得到的就是疲乏,还有因为这结局而引发的愤怒。对即将来临的终结,他已经失去了好奇。多年来,这件事一直让他困惑,但现在它却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真奇怪,疲倦很容易让你不再去想那些东西了。
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写那些特意积攒下来、想等自己能写得足够好了再去写的东西了。不过,他也不会因为试图去写它们而经历挫折了。也许你根本就写不出什么来,而那才是你迟迟不肯动笔的原因。不过他现在永远也无法知道了。
“我真后悔上这儿来。”女人说。她端着酒杯,咬着嘴唇看着他。“要是待在巴黎你绝不会得这种病。你一直说你喜欢巴黎。我们本来可以待在巴黎,或者去别的地方。去哪儿都行。我说过我会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如果你想打猎,我们可以去匈牙利,那样也挺舒服的。”
“你的臭钱。”他说。
“太不公平了,”她说,“我的钱从来也是你的。我丢下了一切,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我后悔我们来了这里。”
“你说过你喜欢这里。”
“那是在你出事之前。我现在恨这个地方。我不明白你的腿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要遭这样的报应?”
“要我说的话,先是在腿刚划破时忘记擦碘酒了,然后是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被感染过,就没去管它,再后来,当伤口恶化,所有抗菌药都用完了的情况下,用了那种药性不强的碳化溶液,损坏了毛细血管,导致了坏疽。”他看着她,“还有什么?”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雇一个好一点的机械师,而不是那个半吊子的吉库尤1司机,他就会去检查车子的机油,卡车的轴承也就不会烧坏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不离开你那帮人,离开住在旧韦斯特伯里、萨拉托加和棕榈滩2的那帮该死的家伙而找上我……”
“因为我爱你。你对我太不公平了。我现在爱你。我将永远爱你。你爱我吗?”
“不爱,”男人说,“我觉得不爱。从来就没有爱过。”
“哈里,你在说什么?你昏头了。”
“没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头好昏。”
“别喝那个,”她说,“亲爱的,你别喝了。我们必须尽的努力。”
“你努力吧,”他说,“我累了。”
他脑海里出现了卡拉加奇1的一个火车站,他背着包站在那里,辛普伦东方快车的大灯划破黑暗的夜空,撤退后他正要离开色雷斯2。那是他积攒下来要写的故事之一,还有,早餐的时候,看着窗外保加利亚群山上的积雪,南森3的秘书问老人那是不是雪,老人看着外面说,不是,那不是雪,现在离下雪还早着呢。秘书对其他女孩重复道,不是雪,你们看,那不是雪,她们齐声说道,那不是雪,是我们弄错了。但那确实是雪,在他促成的那次难民交换行动中,是他把她们送进了雪地。在那个冬天,她们正是踏着那些积雪走向死亡的。
那一年圣诞节在高尔塔尔山,也是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雪,他们当时住在伐木人的小屋里,那个庞大的方形瓷炉子占去了房间一半的地方,当那个在雪地上留下血脚印的逃兵进来时,他们正睡在填满榉树叶的床垫上,他说警察就跟在他的身后。他们给他穿上羊毛袜子,然后去和宪兵们周旋,直到那些足迹被雪覆盖住了。
圣诞节的那一天,施伦茨1的雪是那么的耀眼,你从小酒馆里往外看时,眼睛都被刺痛了,你看见大家都离开教堂往家走。就在那里,他们扛着沉甸甸的滑雪板,沿着河边那条被雪橇压平了的尿黄色的小路,往长着松树的陡坡上走,也是在那里,他们从马德伦小屋上面的冰川一路滑下来,雪像蛋糕上的糖霜一样光滑,像面粉一样蓬松,他记得那种悄无声息的滑行,速度之快,让你觉得自己像一只从高处落下来的鸟。
那次在马德伦的小屋里,被暴风雪困了一周,他们在马灯冒出的烟雾中玩牌,输得越多,伦特先生的赌注就下得越大。后他把什么都输光了,所有的一切,滑雪学校的资金和整个季节的收益,外加他自己的钱。他能看见长鼻子伦特拿起牌来叫道:“Sans Voir2.”那时候赌局不断。不下雪的时候赌,雪下得太大了也赌。他在想这一生他把多少时间花在了赌博上。
但是关于这些事他一个字都没有写,也没有写那个寒冷的圣诞节,山的影子倒映在平原上,巴克飞过分界线,去轰炸那些撤离的奥地利军官乘坐的火车,在他们四处逃窜时用机枪扫射他们。他记得巴克后来走进食堂谈起这件事,大家听得鸦雀无声,接着有个人说:“你这个狗日的杀人犯。”
他们杀死的人和当年与他一起滑雪的那些人一样,都是奥地利人,当然,不是同一批人。那年一直和他一起滑雪的汉斯曾属于“皇家猎人”1。他们在锯木厂上方的一个小山谷打野兔时,谈起了帕苏比奥战役和对波蒂卡与阿沙诺内发起的攻势,他也从未就此写过一个字。没有写蒙特科尔诺,没有写希艾苔科蒙姆,也没有写阿希艾多。
他在福拉尔贝格和阿尔贝格3究竟待过几个冬天?四个。他想起了那次去购买礼物,他们刚走进布卢登茨碰到的那个卖狐狸的人,想起了那种上好樱桃酒特有的樱桃核味,还想起了在落满粉状积雪的山顶上的快速滑行,唱着:“嗨!嚯!罗丽说!”滑过后一段坡道,从那陡峭的山崖笔直地冲下去,转三个弯穿过果园,再飞越那条沟渠,落在小客栈后面那条结了冰的路上。松开捆绑的带子,甩掉滑雪板,把它们靠放在小客栈的木头墙上,灯光从窗户透出,屋里一片烟雾缭绕、充满新酿酒香的温暖中,有人在拉着手风琴。
“我们在巴黎的时候住在哪儿?”此刻,在非洲,他问坐在身旁帆布椅子上的女人。
“‘格丽朗’。你知道的。”
“我为什么知道?”
“我们一直都住在那里的。”
“不对,没有一直住那儿。”
“住那儿,要不就是圣日耳曼区的‘亨利四世’2。你说过你爱那个地方。”
“爱是一坨屎。”哈里说,“我就是那只站在屎堆上喔喔叫的公鸡。”
“如果不得不离开,”她说,“你非得毁掉身后的一切?我是说你非得带走所有的东西?你非得杀了你的马、你的妻子,烧掉你的马鞍和盔甲?”
“是的,”他说,“你的臭钱是我的盔甲。我的快马和盔甲。”
“别这样。”
“好吧。我不这么说了。我不想伤害你。”
“现在说这个有点晚了。”
“那好,我接着伤害你。这样更有意思。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现在却做不了了。”
“不,不对。你喜欢做很多事情,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我都做了。”
“哦,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再吹牛了,好不好?”
他看着她,发现她哭了。
“听着,”他说,“你以为我喜欢这么对待你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估计我是想通过摧毁他人来支撑自己。我们刚开始说话的时候我还好好的,并没有打算开这个头,可现在我像个傻瓜一样蠢,而且在尽我所能地折磨你。亲爱的,别在意我刚才说的话。我爱你,真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从来没有像爱你一样爱过其他女人。”
他又缩回到他熟悉的、赖以生存的谎言之中。
“你对我很好。”
“你这个婊子,”他说,“你这个有钱的婊子。这句话是诗。我现在诗兴大发。腐烂和诗歌。腐烂的诗歌。”
“住口。哈里,你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恶魔呢?”
“我不想留下任何东西,”男人说,“我不愿意死了以后还留下点什么。”
现在已经是傍晚了,这之前他一直都在睡觉。太阳已经落到了小山丘的后面,平原被阴影笼罩着,一些小动物在营地附近觅食,他注意到它们已远离灌木丛,脑袋正快速地起落,尾巴扫来扫去。那些大鸟不再守候在地面上。它们沉甸甸地栖息在一棵树上,数量更多了。他的随身男仆坐在床边。
“太太打猎去了,”男仆说,“先生想要……”
“什么都不要。”
她去打猎了,想弄点肉回来。知道他爱看这些小动物,她特意去了一个远离这里的地方,这样就不会破坏14
平原上这一小块他能看到的地方的宁静。她总是这样,什么都考虑得到,他想,不管是她知道的还是在哪儿看到的,甚至包括听来的事情。
来到她身边时他已经心灰意冷,这不是她的错。一个女人怎么会知道你在口是心非?知道你只是出于习惯和贪图舒适才这么说的?自从他开始言不由衷,和说真话时相比,他的谎言反而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女人。
倒不是因为没真话好说他才撒谎的。他有过自己的生活,但这已经结束了,随后他却又在不断地重复这种生活,在那些他待过的好的地方和一些新的地方,与不同的人在一起,拥有更多的钱。
你不去深究,觉得一切都很好。你已经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不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受到伤害,而对那些自己曾经做过、现在已不能再做的工作,你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你在背地里对自己说,你要去把这些富得流油的人写出来,你其实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是打入他们内部的一个间谍,你终会离开他们并把这些都写出来,而且这次是由一个知道自己在写什么的人来写。但他永远也做不成,因为日复一日,那些舒适的、什么都不用写的生活,那些他曾经痛恨的生活15
方式让他变得迟钝了,他工作的愿望也在减弱,以至于到头来他根本就不工作了。他不工作的时候,那些认识他的人觉得舒服多了。非洲是他在人生美好的时光里感到幸福的地方,所以他来到这里重新开始。他们安排的这次非洲狩猎之行,其舒适程度被降到。虽然谈不上艰辛,但一点也不奢侈。他以为他可以通过这种训练方式复苏,去掉他心灵上积累的脂肪,就像一个拳击手为去掉体内的脂肪而去深山训练那样。
她原本很喜欢这趟旅行。她说她极爱这趟出行。她喜欢刺激的事情,凡是能变换环境,结识新面孔,让人心情愉悦的事情,她都喜欢。他曾经有过这样的幻觉,觉得自己工作的意志力已经重新恢复。但是现在,如果就这样了结,他也知道这就是结局,他没必要像条断了脊梁的蛇一样把自己咬死。不是这个女人的错。如果不是她,还会有另外一个女人。如果他以谎话为生,他就应该努力把谎话说到死。他听见山那边传来了一声枪声。
她枪打得很好,这个善良的、有钱的婊子,这个善良的看护人,他的天赋的摧毁者。胡扯。是他自己摧毁了他的天赋。为什么要责备这个女人呢?难道就因为她尽心地供养他?他之所以失去天赋是因为没有去使用它,是因为他背弃了自己和自己的追求,酗酒无度、懒惰、散漫、势利、傲慢偏见、不择手段。这是什么?一篇旧书目录?他的天赋究竟是什么?那只不过是一种还过得去的天赋,但他没有好好地利用它,而是拿它去做交换。他总是在强调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做了什么。他不是选择用笔和纸,而是其他东西作为谋生手段。每当他爱上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一定会比上一个女人更有钱,这难道不奇怪吗?可是当他不再爱了,当他只在那里撒谎的时候,就像现在,就像对待面前的这个女人,这个有着无数的钱财,曾经有过丈夫和孩子,有过不如意的情人,并把他当成作家、男人、伴侣和值得炫耀的占有物来爱的女人。说来也怪,当他一点都不爱她,对她谎话连篇的时候,反而使他比真心恋爱时更能让她付出的钱财物有所值。
我们这一生做什么都是已经注定了的,他心想。你生存的方式就是你的才能所在。他这一生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出卖生命力,在感情里陷得不是很深时,你反而能够物超所值地付出。他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但从来没有把它写出来,现在也不会写。不会,他不会去写它,尽管这很值得一写。
她这会儿进入了他的视线,穿着马裤,扛着来复枪,正穿过旷野朝营地走来。两个仆人抬着一只羚羊跟在她身后。她仍然很好看,他心想,有着让人愉悦的身体,她对床笫之欢有着极高的天赋,知道如何去享受它。她不算漂亮,但他喜欢她的脸庞。她读过大量的书,喜欢打猎骑马,当然了,她酒喝得也很多。她丈夫去世时,她还比较年轻,有那么一阵,她把精力完全放在两个刚长大的孩子身上,他们并不需要她,她围在他们身边让他们感到难堪,于是她把精力转移到了养马、读书和酗酒上面。她喜欢在晚餐前喝着威士忌苏打读一会儿书。到进晚餐的时候,她已经有点醉了,晚餐的那一瓶葡萄酒,往往足以让她醉入梦乡。
那是在她有情人之前。有了情人之后,她不再需要通过醉酒来入眠,酒喝得没过去那么多了。但那些情人让她感到乏味。她曾嫁给一个从未让她感到乏味的男人,而这些人却很无趣。
后来她的一个孩子死于空难,从那以后她不想再以情人和酒作为麻醉剂了,她必须重新开始生活。突然,独自一人让她感到害怕,但她想要找一个值得她尊重的人一起生活。
开始很简单。她喜欢他写的东西,她一直很羡慕他的生活方式,觉得他总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获取他的步骤以及终爱上他的方式,都是一个正常过程的组成部分,她在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生活,而他则出卖了他剩余的旧生活。
他以此换来了安全,也换来了舒适,这没什么好抵赖的,可还换来了什么呢?他不知道。她会为他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这他是知道的。她还是个特别善良的女人。像对待其他女人那样,他很愿意和她上床,更情愿上她的床,因为她更有钱,因为她让人感到舒服,有品位,也因为她从不与人争吵。现在这个她重新建立的生活就要走到头了,就因为两星期前他们为了拍摄一群非洲水羚,在向羚羊靠拢时一根荆棘划破了他的膝盖,他没有及时给伤口涂上碘酒。水羚羊抬头站在那里,一边用鼻子嗅着空气一边张望,耳朵向两边张开,只要听见一丝响动,它们就会跑进灌木丛。没等他拍好,它们就逃走了。
现在她来了。
他在帆布床上转过脸来对着她。“嗨。”他说。
“我打了一只羚羊,”她告诉他说,“可以用它来做一锅好汤,我会让他们再做点加奶粉的土豆泥。你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太好了!我觉得你可能会好起来的。我离开的时候你正在睡觉。”
“我睡了一个好觉。你走得很远吗?”
“不远,就在小山的后面。我那一枪正中那只羚羊。”
“你枪打得很好,你知道的。”
“我喜欢打猎,我喜欢非洲。真的。如果你没事的话,这会是我开心的一次出行。你不知道和你一起打猎有多开心。我喜欢这个地方。”
“我也喜欢。”
“亲爱的,你不知道看见你心情好转了我有多高兴。你刚才那副样子真让我受不了。你不会再那样和我说话了,是不是?答应我?”
“不会了,”他说,“我都不记得我说过些什么了。”
“你没必要把我也毁了,对吧?我只是个爱你的中年女人,愿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已经被毁过两三次了。你不会再毁我一次吧,对吗?”
“我想在床上把你毁上个几次。”他说。
“很好。那是一种好的毁灭。我们就是为了这种毁灭而生。飞机明天会来这里的。”
“你怎么知道?”
“我敢肯定。它一定会来。仆人们已经把柴火准备好了,还准备了生浓烟的草堆。我今天又过去检查了一次。那里有足够的地方供飞机降落,我们在两端都准备了草堆。”
“什么让你觉得它明天会来?”
“我肯定它会来。已经来晚了。到了镇上他们会把你的腿治好,我们就可以来点儿美妙的毁灭,而不是那种恶言相向的毁灭。”
“我们喝一杯吧?太阳落山了。”
“你行吗?”
“我正喝着呢。”
“那我们一起喝上一杯吧。摩洛,来两杯威士忌苏打!”她大声喊道。
“你好穿上你的防蚊靴。”他告诉她说。
“等我洗完澡再……”
他们喝酒的时候,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就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光线已暗到无法瞄准开枪时,一只鬣狗穿过旷野,朝小山那边走去。
“这个狗日的每天都经过那里,”男人说,“每晚如此,已经两个星期了。”
“晚上的那些叫声就是它发出来的。我倒是不在乎。不过它们长得也真够恶心的。”
他们一起喝着酒,现在,除了老是用一种姿势躺着有点不舒服外,他并没有感到什么疼痛。仆人点着了一堆篝火,火光的影子在帐篷上跳跃,他能感到自己又开始对这种“愉快地屈服”生活听之任之了。她确实对他非常好。他今天下午对她太残酷,也太不公平了。她是个善良的女人,真是没什么好挑剔的。就在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
这个念头伴随着一股冲击而至,但这冲击既不像流水,也不像一阵风,那是一股带有恶臭的、突然的空虚感,奇怪的是那只鬣狗却沿着这味道的边缘悄悄地溜了进来。
“怎么了,哈里?”她问他。
“没什么,”他说,“你好坐到另一边去。坐到上风去。”
“摩洛给你换绷带了吗?”
“换了。我刚上了硼酸。”
“你感觉怎样?”
“有一点晕。”
“我进去洗个澡,”她说,“我一会儿就出来。我们一起吃饭,完了再把帆布床搬进去。”
他对自己说:这么说来我们至少停止了争吵。他从未和这个女人大吵大闹过,可和那些他爱过的女人在一起时,他吵得很凶,由于争吵的腐蚀,终总是把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毁灭掉。他爱得太深,要求也太高,一切都被消耗殆尽。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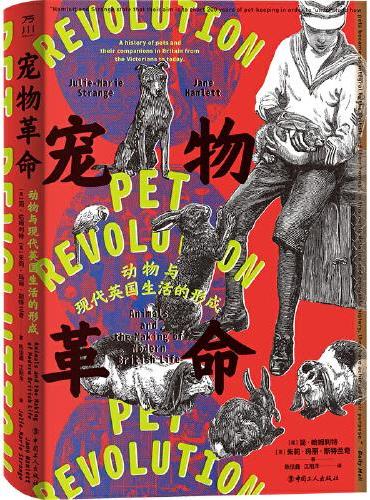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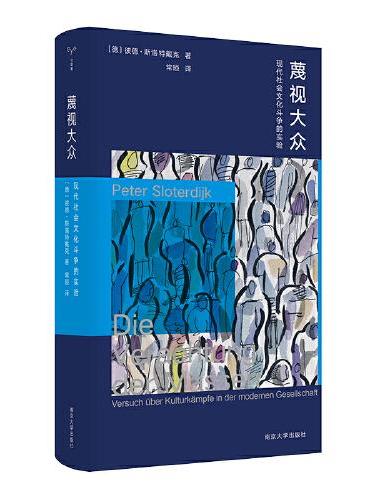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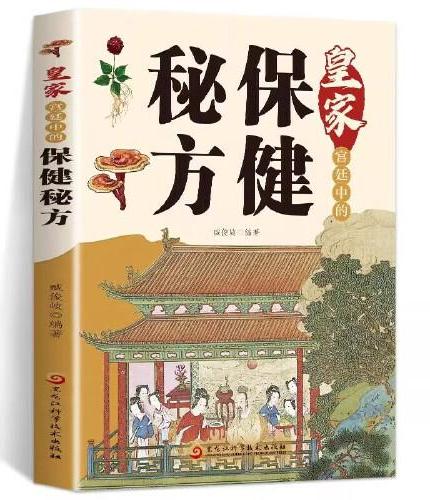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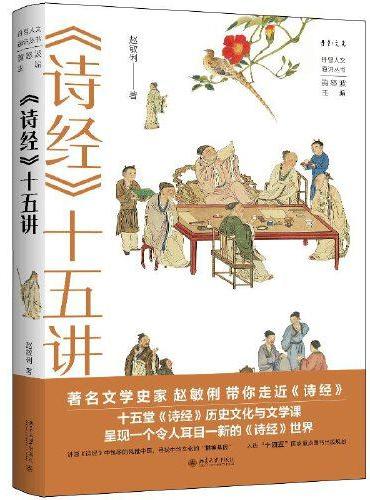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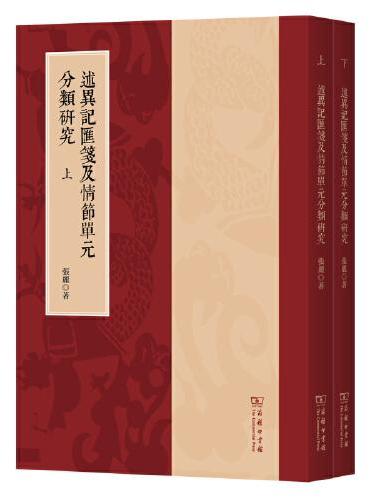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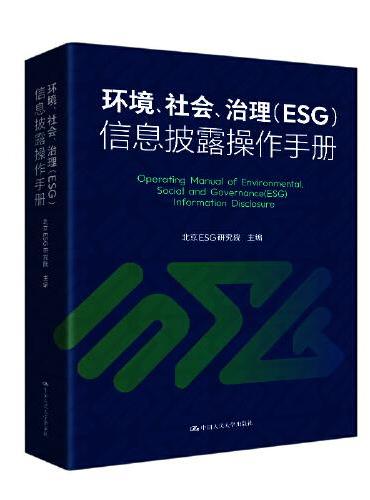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