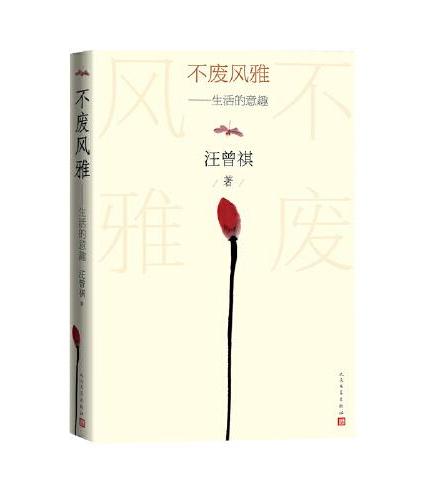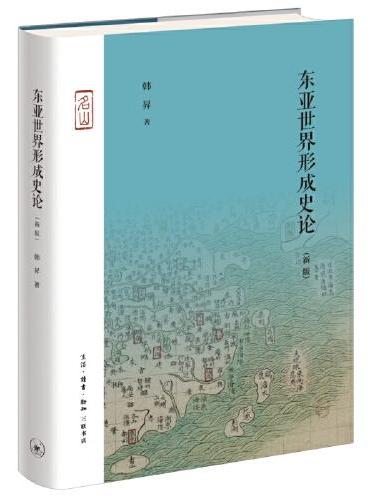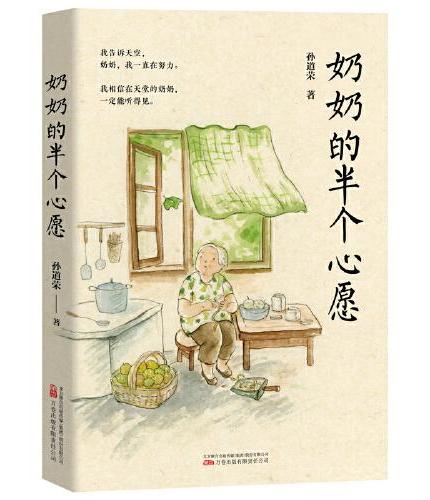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简帛时代与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上下册)(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1400.0

《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9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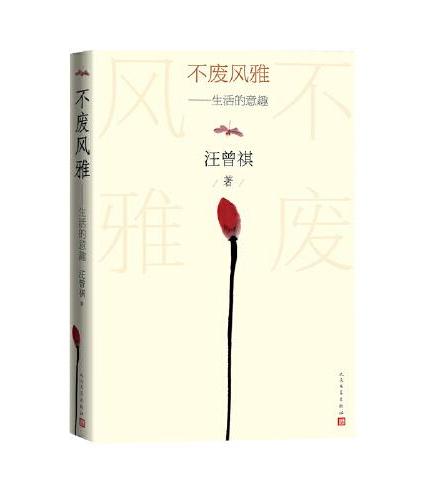
《
不废风雅 生活的意趣(汪曾祺风雅意趣妙文)
》
售價:NT$
2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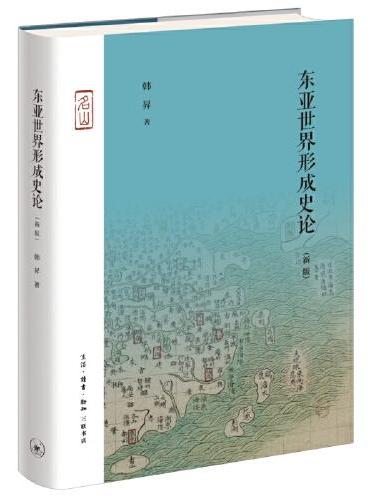
《
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新版)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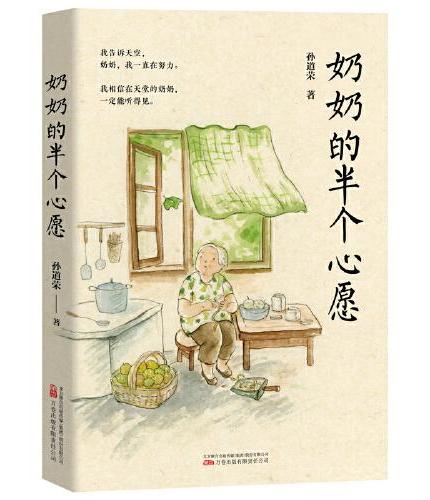
《
奶奶的半个心愿 “课本里的作家” 中考热点作家孙道荣2024年全新散文集
》
售價:NT$
190.0

《
天生坏种:罪犯与犯罪心理分析
》
售價:NT$
445.0

《
新能源材料
》
售價:NT$
290.0

《
传统文化有意思:古代发明了不起
》
售價:NT$
199.0
|
| 編輯推薦: |
天真纯朴的青春恋爱物语
希腊古典主义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
时代的潮涌,青春的牧歌
荣获*届新潮社文学奖
|
| 內容簡介: |
|
《潮骚》是三岛由纪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在1954年发表,小说曾获*届新潮社文学奖。作品讲述了主人公青年渔民新治,认识了刚从外地回来的船主的女儿、美丽活泼的姑娘初江。他们俩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地相爱了。不料这时谣言四起,姑娘的父亲听到后勃然大怒,反对他俩再见面。后来在一次驾船捕鱼时,小伙子冒着生命危险,从惊涛骇浪中挽救了初江父亲的一条船,受到船主赞赏。*后凭着他的勇敢顽强赢得美人归。
|
| 關於作者: |
作者:
三岛由纪夫(1925-1970),原名平冈公威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日本小说家、剧作家。1925年(大正14年)1月14日,三岛由纪夫出生于东京市四谷区永住町2番地(今东京都新宿区四谷4丁目)。6岁时,三岛由纪夫进入皇族学校学习院初等科学习,并开始在内部刊物上发表诗歌 、俳句作品 ,展露文学天赋 。1938年,三岛在《辅仁会杂志》 的161期上发表了他个人的部短篇小说《酸模》 。1939年,清水文雄担任三岛的国文老师 ,成为其文学伯乐 ,对三岛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9年河出书房出版三岛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假面自白》,让其一举成名 ,在日本文坛的地位得以确立。此后三岛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 ,创作出《金阁寺》《潮骚》《丰饶之海》等一批享誉世界的作品。逆反 、冒险 、强烈的对立和矛盾、毁灭,让他的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日本文学作品哀伤的阴柔美 ,具有一种强烈的冲击力 ,富有浓厚的东方艺术神秘色彩。其文风唯美 、工于修辞 ,擅于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从隐微的颓唐中探寻人性的真实 ,曾三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成为海外知名度的日本近现代作家,被誉为“日本的海明威”。1970年11月25日三岛写完《丰饶之海》第四卷《天人五衰》后自杀身亡 。
译者:
唐月梅,1931年生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编委 ,日本早稻田大学 、 立命馆大学客座研究员 ,横滨市立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 目錄:
|
章 002
第二章 009
第三章 018
第四章 024
第五章 031
第六章 041
第七章 052
第八章 060
第九章 076
第十章 088
第十一章 101
第十二章 111
第十三章 125
第十四章 136
第十五章 153
第十六章 162
|
| 內容試閱:
|
章
歌岛是个人口一千四百、方圆不到四公里的小岛。
歌岛有两处景致美。一处是八代神社,坐落在岛的点,朝西北而建。
从这里极目远望,可以望及伊势海的周边,歌岛就位于其湾口。北面濒临知多半岛,由东向北伸展着渥美半岛。西面隐约可见从宇治山田到津的四日市的海岸线。
拾二百级的石阶而上,来到由一对石雕唐狮子守护的牌坊前,猛然回首,可以看到被这种远景包围着的像是古代的伊势的海。这里,原先松枝交错,形成一座“松牌坊”,为赏景的人提供了一个别有风趣的自然画框。但是,松树在几年前已经完全枯死了。
松树的绿还是浅淡时,靠岸的海面已经被春天的海藻染上了红赭色。西北的季节风不断从津的风口吹拂过来。在这里赏景,寒气袭人。
八代神社供奉着绵津见命海神。这种对海神的信仰,是渔夫们从生活中自然产生的。他们经常祈求海上平安,如果遭遇海难,获救后就首先来到这座神社奉献香资。
八代神社有珍宝六十六面铜镜,有八世纪的葡萄镜,还有在日本仅有的十五六面中国六朝镜复制品。镜子背面所雕刻的鹿和松鼠群,是在遥远的过去从波斯的森林辗转漫长的陆路,再渡重洋,旅游了半个世界,来到如今这个岛上安家落户的。
岛上景致美的另一处,就是靠近岛上的东山山顶的灯塔。
灯塔耸立的断崖下,不断地传来伊良湖海峡的海潮声。起风的日子里,这连接着伊势海和太平洋的狭窄海峡,翻卷起无数的旋涡。与这海峡相隔,靠近渥美半岛的一端,在多石而荒凉的岸边,耸立着一座伊衣湖海岬的无人小灯塔。
在歌岛的灯塔上,东南可以望及太平洋的一角。刮西风的拂晓时分,在东北隔渥美湾的群山远方,有时还可望及富士山。
从名古屋和四日市出入港的轮船,擦过星散在湾内至外海上的无数的渔船,经由伊良湖海峡时,灯塔看守从望远镜中窥视,很快就念出了船的名字。
在望远镜的视野里,摄入了三井航线的一千九百吨货轮“十胜号”。货轮上的两个身穿工作服的船员一边踏步一边在闲谈。
过了片刻,又一艘英国的“塔里斯曼号”轮入港。可以清楚地看见上甲板上一个正在投套圈的船员小小的影子。
值班小屋里,灯塔看守坐在办公桌前,将船名、信号、符号、通过时间和方向,都一一记在船舶往来报表上,并将它拟成电文进行联络。多亏这种联络,港口上的货主才能及早做好准备。
一到下午,落日被东山所遮挡,灯塔周围变得阴暗起来。老鹰在明亮的海的上空翱翔。它仿佛欲与天公比试,轮流扇动着双翅,刚要俯冲,却又突然畏缩在空中,飞翔而去。
傍黑时分,一个年轻的渔夫拎着一尾大比目鱼,从村里急匆匆地只顾攀登通向灯塔的山路。这个年轻人方才十八岁,前年从新制中学毕业。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唯有脸上的稚气同他的年龄是相称的。他的肌肤黑得发亮,一个具有这个岛的岛民特点的端庄鼻子,搭配着两片干裂的嘴唇,再加上闪动的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这是以海为工作场所的人从海所获得的恩赐,而绝不是属于智慧的澄明的象征——因为他在学校的成绩非常之差。
他依然穿着一整天都裹在身上的捕鱼工作服,即已故父亲遗留下来的裤子和粗布工作服。
这年轻人穿过静谧的小学校园,踏上水车旁的坡路,拾级而上,来到了八代神社的后面。可以清晰地看见神社的庭院里在薄暮笼罩下的桃花。从这里再攀登,不足十分钟就可到达灯塔了。
这山路实在是崎岖不平,即使白天,走不惯这条路的人也难免会绊倒。可是,这年轻人就是闭上眼睛,他的脚也能蹚着松树树根和岩石前进。纵令像现在这样一边沉思一边行走,也不会绊跤。
方才还在夕阳残照的时候,载着这年轻人的“太平号”返回了歌岛港。每天,年轻人和船主以及一名伙伴都一起驾驭这艘小汽船出海打鱼。回港后,年轻人就把捕获的鱼移到合作社的船上,然后把船靠在海边,拎起比目鱼准备到灯塔长家去。这时,他想先回家一趟,于是沿着海岸走了起来。这傍黑时分,还有许多渔船靠岸,一阵阵吆喝声,使海滨沸腾起来。
一个陌生的少女站在沙滩上,靠在一个名叫“算盘”的坚固的木框边小憩。当起重机把船拖上来的时候,这木框就做垫船底用,是依次往上挪动的工具。少女操作完毕,像是在那里喘气歇息的样子。
少女额上渗出汗珠,脸颊红彤彤。寒冷的西风十分强劲,她因干活而发热的脸袒露在劲风之中,秀发飘逸,像是十分快活的样子。她身穿棉坎肩和扎腿劳动裤,手戴沾着污渍的粗白线劳动手套。健康的肤色与其他的妇女别无二致,但她眉清目秀。她的眼睛直勾勾地凝望着西边海面的上空,那里黑压压的积云中,沉入了夕照的一点红。
年轻人未曾见过这张面孔。按理说,他在歌岛上没有不认识的人啊。要是外来人,他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可少女的装扮又不像是外来人。只是,她独自一人面对大海看得入神的样子,与岛上的快活的妇女迥然不同。
年轻人特意打少女面前走过,在少女的正面停下了脚步,认真地望着少女,就像孩子望着陌生人一样。少女微微皱了皱眉头,眼睛依然直勾勾地凝望着远方的海面,连看也不看年轻人一眼。
寡言的年轻人实地调查完毕,旋即快步离开那里。这时候,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沉湎在一种好奇心得到满足的幸福感中,这种失礼的实地调查在他脸上反映出来的羞怯,直到后来,也就是直到他开始登上通往灯塔的山路时,才渐渐地消去。
年轻人透过一排排松树的间隙,鸟瞰眼下汹涌澎湃的大海。月亮露脸前的大海,漆黑一片。
转过“女人坡”——传说这里会迎面碰见魁伟的女妖——就可以望见灯塔的明亮的窗户。那亮光刺痛了年轻人的眼睛。因为村里的发电机发生故障已久,村里只能看到昏暗的煤油灯的灯光。
年轻人为了感谢灯塔长的恩情,经常这样把鱼送到灯塔长那里。临近新制中学毕业,年轻人考试落第,眼看就要延长一年才能毕业,他的母亲对灯塔长太太——他的母亲平时常到灯塔附近来捡引火的松叶,同灯塔长太太有一定交往——诉苦说:儿子延期毕业的话,家中生活难以维系。太太转告了灯塔长,灯塔长去见了他的挚友——校长。这样,年轻人才免于留级,获准毕业了。
从学校出来,年轻人就出海捕鱼。他经常把捕获的鱼送到灯塔,还不时地替灯塔长夫妻采购,博得了他们的欢心和喜爱。
登上灯塔的钢筋水泥台阶这边,紧靠着一小块旱田,便是灯塔长的官邸。厨房的玻璃门上,摇曳着太太的影子。她像是正在准备晚餐。年轻人在外面扬声招呼。太太把门打开,说:
“哟,是新治。”
太太接过年轻人默默地递过来的比目鱼,高声地说:
“孩子他爹,久保送鱼来了。”
从屋里面传来了灯塔长的朴实的应声:
“你总是送东西来,太感谢了。请进来吧,新治。”
年轻人站在厨房门口,显得有点腼腆。比目鱼已经躺在一只白搪瓷大盘里,从微微喘息的鱼鳃里流出来的血,渗入又白又滑的鱼身上。
第二章
翌日清晨,新治乘上师傅的船儿出海捕鱼去了。黎明时分,半明半暗的云层,在海面上映出一片白茫茫。
开到渔场,约莫得花一个小时。新治身穿工作服,胸前围着耷拉到膝头的长黑胶围裙,手戴长胶手套,站在船头,遥望着航行前方的灰蒙蒙的晨空下的太平洋方位,回想起昨晚从灯塔回家后就寝前这段时间的事来。
……在小屋的炉灶旁,吊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母亲和弟弟在等待着新治归来。弟弟十二岁。自从父亲在战争后一年死于机关枪扫射之下以后,到新治出海劳动这数年间,母亲一人以海女的收入来维持一家的生计。
“塔长很高兴吧?”
“嗯。他一再让我进屋去,还请我喝了可可呐。”
“可可?可可是什么?”
“是西方的红小豆汤吧。”
母亲什么烹调都不会,只会切切生鱼片,拌拌凉菜,或者烤整鱼,一锅煮熟。盘子里摆了一尾新治捕捞上来的绿鳍鱼,是整条煮熟的。由于没有好好洗干净就下锅,吃鱼肉时,就连鱼肉带沙子一起吃了。
在饭桌上闲谈的时候,新治盼望从母亲的嘴里吐露出有关那位陌生少女的一些传闻。然而,母亲这个人是不爱发牢骚,也不喜欢背地议论人的。
饭后,新治带弟弟到澡堂洗澡去,他想在澡堂里听到少女的一些传闻。但时间太晚,浴池空空荡荡,洗澡水也脏了。天花板上回响着粗哑的嗓音,原来是渔业合作社主任和邮局局长泡在浴池里谈论起政治问题来。兄弟俩以目致意后,就泡在浴池的一端。新治一味竖起耳朵倾听,他们的政治话题总是没有移到少女的新闻上来。这时候,弟弟很快就洗完澡走出了浴池,新治也只好一起走了出来,问明缘由。原来是弟弟阿宏在玩剑戟游戏的时候,用刀击中了合作社主任的儿子的头,把他打哭了。
平时一仰脸躺下就入睡的新治,这天晚上上床后却兴奋得久久未能成眠。他从来没有生过病,这回他担心起自己是否生病了。
……这种奇妙的不安情绪,一直持续到今天早晨。眼下新治站在船头,眼前展现广大无际的海。只要一望见海,他平日那种熟悉的劳动的活力就在全身沸腾起来,心情自然而然地就会平静下来。发动机一震动,汽船也随之微微震动。凛冽的晨风,扑打在年轻人的脸颊上。
右边悬崖高处灯塔的光,早已熄灭。早春的褐色树林下,伊良湖海峡飞溅起的浪花,在清晨的迷蒙景色中,呈现一派白花花。“太平号”由师傅熟练地操纵着橹,乘风破浪地顺利穿过海峡潮水的旋涡。要是巨轮航行这海峡,必须通过总是掀起浪花的两处暗礁之间的一条狭窄的航道。航道水深一百四十米至一百八十多米,而暗礁上则只有二十三米至三十六米左右深。
由是,从这条航道标志的浮标周围,向太平洋方位深深投下了无数捕章鱼的陶罐。
歌岛年捕鱼量中八成是章鱼。11月开始的捕章鱼汛期,在起始于春分的捕乌贼汛期以前,已经接近尾声。伊势海天气寒冷,秋天章鱼群为了避寒,顺流游向太平洋的深处,所以捕章鱼的陶罐正等待着捕捉这些章鱼。也就是说,捕章鱼季节快结束了。
对干练的渔夫来说,熟悉岛屿的太平洋一侧的浅海海底全部地形的程度,就像熟悉自己的庭院一样。
“海底黑沉沉,简直像瞎子按摩一样呐。”渔夫经常这么说。
他们靠指南针辨别方向,仔细观察比较远方海角的群山,通过高低的较差,来弄清船儿的所在位置。弄清位置,就知道海底的地形。每条缆绳分别挂上上百个捕章鱼陶罐沉入海底,很规则地排成无数的行列。拴在缆绳上的一处处的许多浮标,随着潮涨潮退而摇动。要论捕鱼技术之老练,得数既是船主又是师傅的捕捞长了。
新治和另一年轻人龙二都认为,只要致力于适合自身的力气活儿就行。
捕捞长大山十吉的脸,活像被海风鞣熟的皮子。连皱纹的深处也被晒得黝黑,手上的疤,不知是渗透在皱纹里的污垢,还是打鱼的旧伤痕,如今已经分辨不出来了。他这个人难得一笑,平时很是冷静,虽然为了指挥捕鱼而扯大嗓门,可是不会因生怒而大声吼叫。
打鱼的时候,十吉基本上不离开掌橹场,用一只手调节发动机。到了海洋,许多原先看不见的渔船都麇集在这里,互致平安。十吉降低发动机的马力,一开进自己的渔场,就向新治示意,让他把传动皮带挂在发动机上,再绕在船舷的旋转轴上。船儿沿着挂上捕章鱼陶罐的缆绳缓缓行驶,这个旋转轴带动了船舷外的滑轮。青年们把挂着捕章鱼陶罐的缆绳拴在滑轮上,捯了上来。必须不停地捯,否则缆绳会滑回去。再说,要把吸足海水而变得沉重的缆绳拉上来,就需要加倍的人力了。
微弱的阳光笼锁在水平线上的云层里。两三只鱼鹰把长长的脖颈伸出水面游来游去。
朝歌岛望去,向南的断崖被群栖鱼鹰的粪便染成一片白花花。
风,格外地寒冷。由滑轮将缆绳卷上来的同时,新治望着湛蓝的海,从中感受到马上就应使自己出汗的劳动的活力涌了上来。滑车开始转动,湿漉漉的沉重的缆绳从海里被捯了上来。新治戴着胶手套的手,紧握住冰冷而坚硬的缆绳。捯上来的缆绳通过滑轮的时候,四处溅起了像冷雨般的水花。
接着,红赭色的章鱼陶罐从海面露了出来。龙二在等待着,倘使罐子是空的,他就不让空罐接触滑轮,迅速将蓄满罐里的水倒出来,然后靠缆绳把陶罐再放回海里。
新治叉开双脚,一只踩在船头,接连不断地把长长的缆绳捯上来,他心想:从海里会拉上什么来呢?他不停地捯着缆绳。新治胜利了。但是,实际上海也没有输。不断捯上来的都是空罐子,它们像是在嘲笑。
拉上来的相隔七至十米一个的章鱼罐已有二十多个,全都是空的。新治仍在捯着缆绳。龙二把空罐里的水倒了出来。十吉不动声色,手握住橹,默默地注视着年轻人的操作。
新治的脊背上渐渐渗出了汗珠。裸露在晨风中的额头上的汗珠在闪闪生光。脸颊火辣辣的。阳光好不容易透过云层,把年轻人跃动的淡淡的身影投射在脚下。
龙二把拽上来的罐子不是倾倒在海里,而是倾倒在船里。十吉停止了转动的滑车。
新治这才回头望了望章鱼罐。龙二用木棍连续捅了几下罐里,总是不见章鱼出来。他又用木棍搅动,章鱼才勉强从罐里滑了出来,蹲在船板上,就像人午睡正酣的时候不愿意被人唤醒一样。机械室前的大鱼槽的盖子弹开了,今天的次收获,一股脑儿地倾泻在槽底里,发出了低沉的声响。
整个上午,“太平号”几乎都在捕章鱼。仅仅捕获了五尾章鱼。风已停息,和煦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太平号”驶过伊良湖海峡,回到了伊势海,准备在这捕鱼禁区里偷偷垂钓。
所谓垂钓,就是一种捕鱼的方法,即把结实的一串串的鱼钩放在海里,船儿向前行驶,鱼钩就像铁耗子在海底耙来耙去。许多挂着钓钩的绳子被平行地系在缆绳上,缆绳水平地沉入海里。相隔一段时间再拉上来,四条鲬鱼和三条舌鳎龟从水面上蹦了上来。新治赤手把它们从鱼钩上拿了下来。鲬鱼露着白腹躺倒在沾满血迹的船板上。舌鳎鱼那两只被埋在皱纹里的小眼珠、那濡湿了的鱼身,都映照着蔚蓝的天空。
午餐时间到了。十吉将捕获的鲬鱼放在发动机部的盖子上,切成生鱼片,分成三份放在三人各自的铝饭盒盖上,浇上小瓶装的酱油。三人端起了在一角放上两三片萝卜咸菜的麦饭饭盒。渔船在微波中荡漾。
“宫田的照大爷把女儿叫回来了,你们知道吧?”十吉突然说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两个年轻人摇了摇头。十吉又说道:
“照大爷生了四女一男,他觉得女儿过多,三个出嫁,一个送给人家做养女了。幺女名叫初江,已经过继给志摩老崎地方的一个海女。独生子阿松去年突发心脏病,猝然死去,照大爷就成了鳏夫,他突然变得寂寞了。于是,他把初江唤回来,重新落了户口,还打算招个养老女婿呐。初江长得格外标致,小青年都想当他的入赘女婿,这是一桩了不起的事吧。你们怎么样?”
新治和龙二面面相觑地笑了起来。的确,两人都脸红了。只因为肌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看不见那股泛起的潮红罢了。
新治心中已将这个议论中的姑娘,同那个昨日在海滩上看见的姑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他也感到自己财力的缺乏,丧失了信心,昨日近在咫尺的姑娘,今日却变得远在天边了。宫田照吉是个财主,又是拥有山川运输公司出租用的一百八十五吨级的“歌岛号”机动机船和九十五吨级的“春风号”轮的船主,还是个闻名遐迩的爱申斥人的老家伙。他申斥人的时候,那头像狮子鬃毛般的白发就会竖起来。
新治考虑的问题是很切合实际的。他觉得自己才十八岁,考虑大人的事为时尚早。因为歌岛的环境与会受到许多刺激诱惑的城市少年的环境不同,岛上没有一家弹子房,没有一家酒吧间,甚至没有一个陪酒的女招待。再说,这年轻人朴素的幻想,就是将来自己拥有一艘机动帆船,同弟弟一起从事沿海运输业。
新治的四周是宽广的海,他却不曾向往不着边际的雄飞海外的梦。对于打鱼人来说,海就像农民在观念上之执着于自己所拥有的土地。海,是打鱼人的生活场所,它的无定形的白色波涛,就像田间的稻穗和麦子在容易感受到绿油油的软土上不断地摇曳着。
……尽管如此,那天作业将结束的时候,年轻人竟带着一种奇妙的感动,遥望着一艘从水平线上的晚霞前通过的白色货轮的影子。世界竟以迄今他连想也没想过的巨大的宽广,从遥远的天际逼将过来。这个未知的世界的印象,宛如远雷,从远处轰隆过来,尔后又消失了。
船头的甲板上,有一只小海星干瘪了。坐在船头上的年轻人,把视线从晚霞移开,轻轻地摇了摇他那用白厚毛巾缠着的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