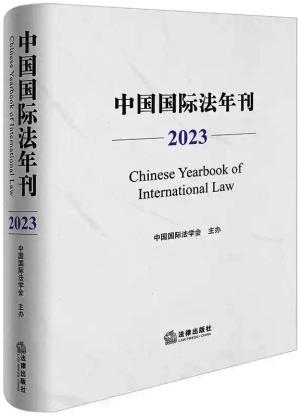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花外集斠箋
》
售價:NT$
704.0

《
有兽焉.8
》
售價:NT$
305.0

《
大学问·明清经济史讲稿
》
售價:NT$
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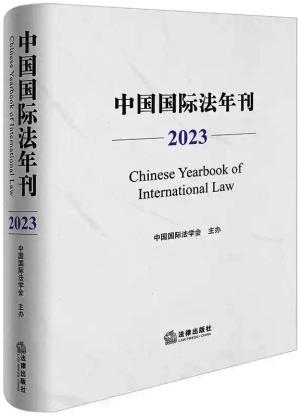
《
中国国际法年刊(2023)
》
售價:NT$
539.0

《
早点知道会幸福的那些事
》
售價:NT$
295.0

《
迈尔斯普通心理学
》
售價:NT$
760.0

《
古典的回響:溪客舊廬藏明清文人繪畫
》
售價:NT$
1990.0

《
掌故家的心事
》
售價:NT$
390.0
|
| 編輯推薦: |
用极度简洁的语言,抵达人类关系复杂、神秘的地带
花一辈子去做自己厌烦的事,比永远自私地追逐梦想、随心所欲,要勇敢得多。
|
| 內容簡介: |
《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所收入的七个故事,都发生在新斯科舍省布雷顿角那些严酷的风景中,有少年渴望摆脱家族在海岛世代挖煤的命运而在成年之际离家远行,有人到中年的大学教师回忆少年时他那心怀壮志但困居海岛打鱼为生的父亲,有散居各地的大家族成员在老祖母96岁生日之际齐聚老祖母寡居的海角,尘封往事也在个人心中泛起这些故事勾画了家庭内部紧密的纽带和难以逾越的鸿沟,以及人们面对命运时候那种一脉相承的脆弱和温柔。
书中的七篇故事既体现了人和自然世界粗粝而深情的交融,也含蓄而节制地勾勒了布雷顿角那些复杂、神秘而质朴的人心。它们被记忆和传说浸润,被海水和鲜血冲刷,又在人生一些微妙的时刻,抵达了艰难而令人喜悦的彼此谅解。
|
| 關於作者: |
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1936-2014),加拿大著名短篇小说家,因其一系列以新斯科舍省布雷顿角为背景的小说闻名,其作品已经被翻译成17种语言。著有短篇小说集《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当鸟儿带来太阳》和获得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其中,《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自1976年出版以来,已经成了加拿大文学的经典作品。
麦克劳德曾在加拿大温莎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多年,每年夏天都会回到布雷顿角写作。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小说既充满地域色彩,又传递审了深沉而普世的情感。
|
| 目錄:
|
1 秋
27 黑暗茫茫
67 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
99 回乡
125 灰白的金色馈赠
151 船
183 去乱岑角的路
227 跋/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媒体评论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出生地是加拿大,他的情感中心是布雷顿角,他是苏格兰人的后裔,但他的写作属于世界。
很难想出还有谁能写出具有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般魅力的小说。 爱丽丝门罗
和福克纳或契诃夫的作品一样,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短篇小说既是地域的,又是普世的,而且,我也认为它们是不朽的。 迈克尔翁达杰
在线试读我的朋友亨利范戴肯说父亲会这样是因为他是苏格兰人,这个民族在花草和家禽这些事上从来就不在行,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女人们干的活,男人动手是丢人的事。亨利的父亲种花弄草、养鸡养鸭都是好手。
我们正在局促的鸡棚里打转,忽然门砰地打开,我们眼见大卫几乎是被风雨吹打进来的。有个男人开着辆卡车,上面有头老牛,他说,他刚才进咱们家了。
我们进厨房的时候麦克雷就站在门口的那张桌子边上,父亲还是在窗子那里,虽然现在已经转过来背对着窗口了。看情势好像他们两个谁都没有开过口。
麦克雷这个牛贩子今年五十多了,矮小敦实,一张通红脸孔,嘴角叼着根雪茄。他的一双眼睛也很小,还布满血丝。他的裤脚塞在雨靴里,宽皮带是西部风格,棕色山羊外套下面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衣,领口没扣上,看得见他带些红色的胸毛。他手里有根短柄长鞭,一直在用来敲他雨靴的侧边。他刚刚在大风雨里走了一小段,所以衣服是湿的,因为厨房里的热量,这股刺鼻的湿气再混合了他雪茄的味道,让人觉得颇为难受。这种气味里闻得到不计其数惊恐的牲畜它们曾被关在他卡车的车厢里,也曾被他推来搡去还闻得到牛粪、汗臭和害怕。
听说你这儿有匹快不行了的老马,他的话绕过他的雪茄传出来,运气好的话,我还能用它来换点水貂饲料。我开的价是二十加元。
父亲一言不发,不过那双如同他身后大海一样灰暗的眼睛,让我想到曾经有一回,斯科特拖着的圆木撞上半掩盖着的障碍,疯狂地弹飞出去,猛烈的冲力正好压在父亲的双腿上,拖着他碾了一小段,直到撞在一个树墩上。那树墩几乎被撞得连根拔起,斯科特也被撞得差点一屁股坐下。父亲的双眼那时也灰暗,其中映射出的全是恐惧、痛楚和无声的讶异:惊讶的是自己如此苦厄的困境似乎又是如此的熟悉。
此刻的情形,很像他被我们所有人算计了,包括他的妻子、他的六个孩子和抽着雪茄的麦克雷。大海已经在这扇窗上留下不少伤痕,此刻它又被急风暴雨冲击着,而我们绕着父亲围成一圈,他靠着这扇窗,真的很像是被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了。他还是什么话都不说,虽然我知道,此刻他的思维正沿着所有可能供他辩驳的小径飞奔着,但所有的路线又一下被他自己否决,因为他明白在每条路的尽头,都有让他痛心的事实在等着他:拖延又有什么用?卡车已经开来了,以后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了;你自己就快走了;它再不会变回年轻了;价格不可能再提了;它可能这个冬天就死了,那我们就什么也拿不到;我们不是在给退休的老马开疗养院;我一个人在这里照顾六个孩子,本身就忙不过来;买饲料的钱该花在你孩子身上;对你来说,难道孩子还没有一匹马重要?你自己走了,把我们留在这儿照料它,不公平。我的朋友亨利范戴肯说父亲会这样是因为他是苏格兰人,这个民族在花草和家禽这些事上从来就不在行,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女人们干的活,男人动手是丢人的事。亨利的父亲种花弄草、养鸡养鸭都是好手。
我们正在局促的鸡棚里打转,忽然门砰地打开,我们眼见大卫几乎是被风雨吹打进来的。有个男人开着辆卡车,上面有头老牛,他说,他刚才进咱们家了。
我们进厨房的时候麦克雷就站在门口的那张桌子边上,父亲还是在窗子那里,虽然现在已经转过来背对着窗口了。看情势好像他们两个谁都没有开过口。
麦克雷这个牛贩子今年五十多了,矮小敦实,一张通红脸孔,嘴角叼着根雪茄。他的一双眼睛也很小,还布满血丝。他的裤脚塞在雨靴里,宽皮带是西部风格,棕色山羊外套下面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衣,领口没扣上,看得见他带些红色的胸毛。他手里有根短柄长鞭,一直在用来敲他雨靴的侧边。他刚刚在大风雨里走了一小段,所以衣服是湿的,因为厨房里的热量,这股刺鼻的湿气再混合了他雪茄的味道,让人觉得颇为难受。这种气味里闻得到不计其数惊恐的牲畜它们曾被关在他卡车的车厢里,也曾被他推来搡去还闻得到牛粪、汗臭和害怕。
听说你这儿有匹快不行了的老马,他的话绕过他的雪茄传出来,运气好的话,我还能用它来换点水貂饲料。我开的价是二十加元。
父亲一言不发,不过那双如同他身后大海一样灰暗的眼睛,让我想到曾经有一回,斯科特拖着的圆木撞上半掩盖着的障碍,疯狂地弹飞出去,猛烈的冲力正好压在父亲的双腿上,拖着他碾了一小段,直到撞在一个树墩上。那树墩几乎被撞得连根拔起,斯科特也被撞得差点一屁股坐下。父亲的双眼那时也灰暗,其中映射出的全是恐惧、痛楚和无声的讶异:惊讶的是自己如此苦厄的困境似乎又是如此的熟悉。
此刻的情形,很像他被我们所有人算计了,包括他的妻子、他的六个孩子和抽着雪茄的麦克雷。大海已经在这扇窗上留下不少伤痕,此刻它又被急风暴雨冲击着,而我们绕着父亲围成一圈,他靠着这扇窗,真的很像是被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了。他还是什么话都不说,虽然我知道,此刻他的思维正沿着所有可能供他辩驳的小径飞奔着,但所有的路线又一下被他自己否决,因为他明白在每条路的尽头,都有让他痛心的事实在等着他:拖延又有什么用?卡车已经开来了,以后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了;你自己就快走了;它再不会变回年轻了;价格不可能再提了;它可能这个冬天就死了,那我们就什么也拿不到;我们不是在给退休的老马开疗养院;我一个人在这里照顾六个孩子,本身就忙不过来;买饲料的钱该花在你孩子身上;对你来说,难道孩子还没有一匹马重要?你自己走了,把我们留在这儿照料它,不公平。
他点了点头,离开窗口,朝门口走去。你不会是要大卫说道,可母亲立马打断了他。闭嘴,她说,去,先把鸡喂好了。然后她好像管不住自己似的说:至少喂喂鸡还有点意义。几乎在父亲停下脚步之前,我就知道她已经在后悔添上最后那一句了。我知道她已经意识到自己伸手要抓的东西太多,于是连已经拥有的,恐怕都要全部丢掉了。就像被海水冲刷的那些几乎是垂直的悬崖,你一点点往上攀爬的时候,发蓝的指尖从这个缝隙抓到下一个裂口,突然你见到一根诱人的细枝,就忍不住去抓;就在你伸手的刹那,你心里清楚,很可能这根枝条所寄无物,那里既没有土壤或者植被作为它的根基,甚至很可能这根枝条只是被海浪抛掷起的废物。就在那一刹那,你已经绷紧自己的身体,准备好承受那不可避免的滑落,以及即将到来的疼痛和满身的淤青。不过对母亲来说,这次似乎躲过了这一劫。他只是停了一下,盯着她看了片刻,猛地打开门,迈入了呼啸的风中。大卫僵在那里。
我想他是去了关牲口的地方。母亲说,语气出乎意料的轻柔,还用眼神示意我,让我也跟去。等到麦克雷和我走出门口,父亲已经走了一半了。他没戴帽子,也没穿外套,整个人侧着走,像把斜斜插进风口的刀子。他的裤管被风撕扯着,紧紧贴着父亲的双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