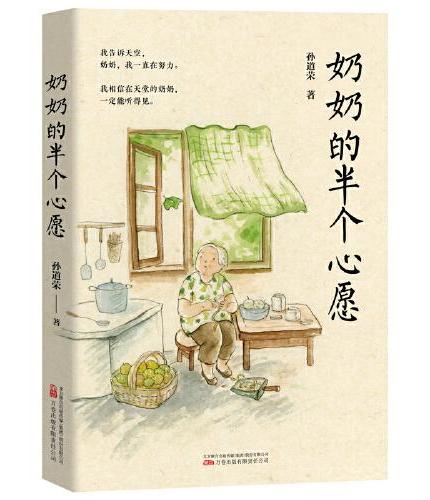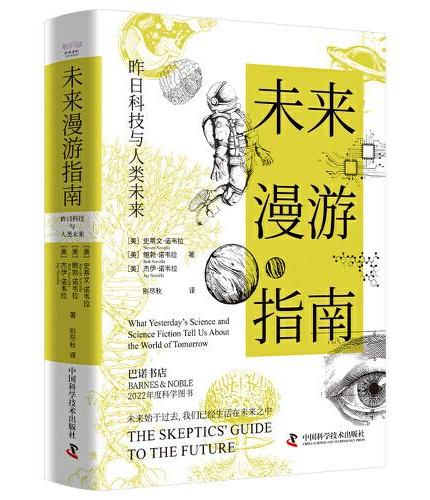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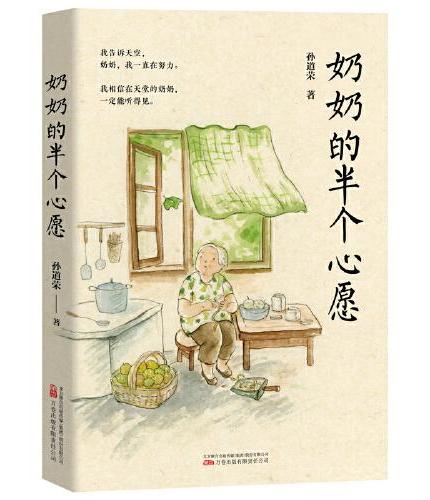
《
奶奶的半个心愿 “课本里的作家” 中考热点作家孙道荣2024年全新散文集
》
售價:NT$
190.0

《
天生坏种:罪犯与犯罪心理分析
》
售價:NT$
445.0

《
新能源材料
》
售價:NT$
290.0

《
传统文化有意思:古代发明了不起
》
售價:NT$
199.0

《
无法从容的人生:路遥传
》
售價:NT$
340.0

《
亚述: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的兴衰
》
售價:NT$
490.0

《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采煤机智能制造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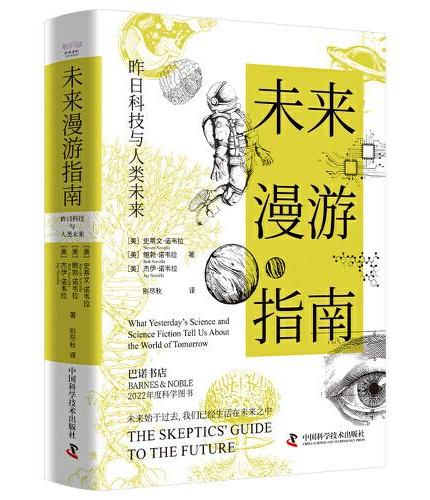
《
未来漫游指南:昨日科技与人类未来
》
售價:NT$
445.0
|
| 編輯推薦: |
哲学与诗的关系问题的复活
真正人类语言之圆舞
面向海德格尔与本雅明的隐秘对话
「思想只有承担诗的遗产,才能朝向散文的理念」
阿甘本美学三部曲(《语言与死亡》《诗节》《散文的理念》)之终章
几十个碎片式的分析,寓言、格言、谜语、短故事,以及各种人们如今不再使用的简单形式,阿甘本的批评实践就在这些离题的作品中展演,而这种离题乃是本雅明式批评必不可少的部分。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阿甘本的美学专著。通过对诗歌、散文、语言、政治、正义、爱与羞耻等主题的一系列碎片式分析,他进入了哲学与诗歌的区别这一主题。这些碎片式的论述没有形成贯穿全文的一致说法,但逻各斯的限制在此被打破,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区别不再明显。
阿甘本使用了各种文学手法,包括寓言、格言、谜语、短故事,以及各种我们如今不再使用的简单形式,在实践中演示出一种批评方式它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经验、一种觉醒,在这里,思想的问题成为诗的问题。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吉奥乔阿甘本 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曾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维罗纳大学、威尼斯高等建筑学院及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欧洲研究生院等多所学院和大学任教。他的研究领域广泛且影响深远,对文学理论、欧陆哲学、政治思想、宗教研究以及文学和艺术的融会贯通,使他成为我们时代最具挑战性的思想家之一。
主要著作包括《神圣人》《王国与荣耀》《例外状态》《奥斯维辛的残余》《空心人》《幼年与历史》《身体之用》《敞开》《语言与死亡》等。
译者简介
王立秋 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
| 目錄:
|
阈限
I
问题的理念
散文的理念
音顿的理念
召命的理念
独一者的理念
听写的理念
真理的理念
缪斯的理念
爱的理念
学习的理念
不可记忆者的理念
II
权力的理念
共产主义的理念
政治的理念
正义的理念
和平的理念
羞耻的理念
时代的理念
音乐的理念
幸福的理念
幼儿期的理念
普世审判的理念
III
思想的理念
名称的理念
谜的理念
沉默的理念
语言的理念(1)
语言的理念(2)
光的理念
表象的理念
荣耀的理念
死亡的理念
觉醒的理念
阈限
在卡夫卡的诠释者面前为他而辩
|
| 內容試閱:
|
*
《爱的理念》
与一个陌生人亲密地生活,不是为了把他拉得更近,也不是为了认识他,而毋宁说是为了使他保持遥远、陌生:不显露——如此地不显露,以至于他的名字就包含了他的全部。以及,即便不适,也只是日复一日地,做永远开放的场所,做不灭的光:而那一个存在,那个物,将一直在这里被暴露,也将一直被封闭在这里。
**
《羞耻的理念》
古人既无卑劣感的经验,亦无偶然感的经验(在我们看来,说到底,偶然夺走了人的不幸所有的伟大)。当然,对古人来说,欢乐,像(傲慢)一样可能在任何时刻,颠倒为它的反面,变成苦的幻灭;但确切来说,就在这个时刻,悲剧,通过它的英雄封锁卑劣的一切可能性的拒绝介入了。在他的命运面前,船难是悲剧的,而绝不是悲惨的;他的不幸和幸福都不会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卑鄙。同样真实的是,在喜剧中,悲剧展示出它荒谬的一面;不过,这个被众神和英雄抛弃的世界也不是一个卑劣的世界,相反,公正地说,这个世界是得体的:“在人真的是人的时候”,米南德的一个角色说,“他是多么地得体啊。”
在古人的世界里,人是在哲学中,而不是在喜剧中,遭遇到那种我们可以不强行引申地拿来和羞耻(那种让斯塔夫罗金的信仰瘫痪,或让我们觉得与神话的乱交,或卡夫卡的宫廷和城堡的神话般的污秽相似的羞耻)比较的感觉初和的踪迹的。(在古代世界,污秽永远不可能是神话的:百折不挠的赫拉克勒斯清洗了奥革阿斯的牛厩,使自然之力服从于他的意志。不过,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彻知我们的污秽,它在根源上总有一种神话学的残余。)奇怪的是,它(与羞耻相似的那种感觉)在巴门尼德的一段话中出现了,在那里,年轻的苏格拉底对伊利亚学派哲学家阐述他的理念理论。面对巴门尼德提出的这个问题——“头发、污物、泥巴和其他一切性质恶劣、令人不快的东西”的理念存不存在呢?——的时候,苏格拉底坦承,他觉得陷入了一阵眩晕:“我一想到这可以普世地延伸下去就感到痛苦不已。但一旦我心存这个想法,我就会立刻出于对因为堕入愚蠢的深渊而迷失的恐惧而逃避它……”但这只持续了片刻。“那是因为你还年轻,”巴门尼德回答说,“哲学还没有抓住你,我预言,有一天,它会的,那时你就不会再在任何这样的事物面前战栗了。”
在这里,重要的是,为思想(哪怕是片刻地)揭示卑劣带来的眩晕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说到底,是神学的)问题。上帝本身——天外的理念世界,巨匠造物主创造可感世界所依据的模型——呈现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如此熟悉的那个令人厌恶的面容,在它面前,异教之人移开了他的目光,并感受到傲慢,这个傲慢以如此伟力标志着古人的虔诚。上帝无需辩护:神是有理的,《理想国》中处女拉赫西斯的神谕就是这么说的。
不过,对现代人来说,神正论是必要的,但类似地,他也必然遭遇悲惨的那种失败。上帝指控自己,并可以说是在他自己的神学粪便上打滚,单是这个,就给了我们的不安其确定无疑的品质。现在,我们的理性脚下的深渊,不是必然性的深渊,而是恶的偶然性和平庸的深渊。我们不可能因为偶然而负罪或清白:我们只能感到尴尬或羞耻,就像我们在街上踩到香蕉皮那样。我们的上帝是一个面带羞耻的上帝。但就像一切战栗都透露出一种与恶心的对象的隐秘团结那样,羞耻,也是一种人与自己闻所未闻、令人害怕的接近的索引。卑劣感是人在面对自己时后的谦逊,就像偶然是那个隐藏(独属于人的原因对人的命运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的面具那样,现在,看起来,人的整个存在都是在偶然的符号下缓缓展开的。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只看到一个有罪的人,在一个变得疏远、遥远的上帝难以理解的权力面前的痛苦的总和,这是一种对卡夫卡作品的糟糕解读。相反,在这里,需要被拯救的,是上帝自己,而对卡夫卡的小说来说,我们可以想象的幸福结局,是克拉姆、伯爵、匿名者,和被不加区分地全部塞进满是灰尘的走廊,或弯腰走在逼人的天花板下的那个由法官、律师和守卫组成的神学群众得到救赎。
卡夫卡的天才之处在于,把上帝放进了柜子——使碗碟间和阁楼成了典范的神学场所。但他的伟大之处——只在罕见的情况下,他的伟大才在他的角色的姿势中闪现——则在于,在某个点上,他决定放弃神正论,并忘记关于罪与无辜、自由与命运的老问题,以达到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羞耻上的目的。
他面对的是这样一种人——世界范围的中产阶级——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经验,除了他们的羞耻,即人在内心深处对自我的认识的纯粹的、空的形式。对这种人来说,一种还可能的无辜将是,在冷漠中感到羞耻。害羞对古人来说并不是一种令人尴尬的感觉;相反,面对羞耻,他就像赫拉克勒斯在赫卡柏赤裸的乳房面前那样,恢复了他的勇敢和虔诚。卡夫卡力图教人使用这个留给他们的一个好东西:不是把自己从羞耻中解放出来,而是解放羞耻本身。这就是约瑟夫·K在他的整个审判期间努力要实现的,而在结尾他执拗地低头看行刑者的刀,是为了拯救他自己的羞耻,而不是他的无辜。“他的意思好像是,”我们在这个死亡的时刻读道,“他的羞耻会比他活得更久。”
只有通过这个任务,只有通过至少为人类拯救其羞耻,卡夫卡才恢复了某种类似于古代的极乐的东西。
***
《幼儿期的理念》
在墨西哥的淡水湖里生活着一种白化蝾螈,有一阵子,这个物种吸引了动物学家和研究动物演化的学者的注意。那些有机会在水族馆中观察过这种蝾螈的人,会为它的幼儿的、几近于胎儿的外表而感到震惊。它相对巨大的脑袋,没入了它的身体,它的皮肤是乳白色的,在口鼻上和持续活动的鳃周围隐约有灰色的和鲜艳的蓝色、粉色的花纹;它的细足前端是花瓣形的肉掌。
起初墨西哥钝口螈被分类为一个终生维持一些两栖动物的幼体阶段特有的典型特征(比如用鳃呼吸和水生环境)的独特物种。尽管有着幼体的外表,但它完全具有繁殖能力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了它是一个自主的物种。直到后来,一系列的实验才表明,在这个小蝾螈身上施用甲状腺激素,就能引发两栖动物的正常的变态。于是,它失去了它的鳃,并且,在发展肺呼吸的同时,它也结束了它的水生生活,并发展成虎纹钝口螈(Ambystoma tigrinum)的成年实例。这些环境可能诱使人们把墨西哥钝口螈分类为演化的退化的一个案例,分类为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的一次失败,这个失败使蝾螈放弃了它的存在的陆生部分,并无限地延长了它的幼体状态。但近来,恰恰是这种执拗的幼体主义(幼体性熟或幼态持续),提供了一把新的、理解人类演化的钥匙。
现在,人们认为,人不是从个体的成年体,而是从灵长类动物的幼体(就像墨西哥钝口螈那样,这个幼体早熟地获得了生殖能力)演化而来的。这将解释人那些形态学上的特征,从枕骨腔的位置到耳郭的形状,从无毛发的皮肤到手脚的结构,这些特征与成年的类人猿不一致,却符合类人猿胎儿的特征。在灵长类动物身上是暂时性的特征,在人身上变成了终的结果,这因此而以某种方式,在血与骨中,形成了一个永恒的孩童。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假设还支持一种新的、理解语言和体外传统的整个领域[后者比任何基因印记都更称得上是智人(homo sapiens)的特征,但直到现在,科学看起来都还在本质上缺乏理解它的能力]的进路。
让我们试着想象一个幼儿,和墨西哥钝口螈不一样,它不仅维持了它的幼体环境,保留了它不成熟的形式,而且,可以说,它还如此彻底地被抛给了它自己的幼儿状态,它的细胞的特化程度是如此之低而全能性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它为了坚持它的不成熟和无助,而拒绝一切特定的命运和一切确定的环境。动物不关心它们不被铭写在其生殖腺中的体细胞的可能性;与人们可能的想法相反,它们才一点儿也不关注这个必死的东西(体细胞是每个个体身上无论如何注定要死的东西)呢,它们只发展固定在基因代码中的那些无限可重复的可能性。它们只注意规律——只注意被写(在基因里)的东西。
另一方面,幼态持续的幼儿,则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况:他有能力注意未被写下的东西、任意的和不被编码的体细胞的可能性;在他的幼儿的全能性中,他会狂喜地被压倒,被抛出自己——不像其他生物那样被抛入一个特定的冒险或缓解,而是次,被抛入一个世界。他会真的聆听存在。他的声音依然不受一切基因的成规的束缚,并且他无物可说或表达,作为自成一类的动物,他可以像亚当一样,用他的语言命名万物。在命名中,人与幼儿期联系起来了,他永远与一种超越一切特定的命运和一切基因的召命的开放关联。
但这个开放,这个在存在中的呆若木鸡的停留,不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和他有关的事件。事实上,它甚至不是一个事件,某种可以在体内记录,并在基因的记忆中习得的东西;相反,它是某种必须保持外在的东西,是和他有关的“无”,和因为这样而只能被交给遗忘——也就是说,只能被交给一种体外的记忆和一个传统——的东西。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准确地想起“无”:在他身上发生或自我显现的“无”。但这个“无”,作为“无”,也先于一切在场和一切记忆。这就是为什么在传递任何知识或传统之前,人必然得先传递这个无思(svagatezza)本身、这个不定的开放本身——在这个无思、这个开放中,像具体的历史传统那样的东西才变得可能。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种看起来琐碎的论证来表达这点:在亲自传递某物之前,人必须首先传递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成年人不可能再去学习说话;次进入语言的是孩童,而不是成人,而尽管智人有四万年的历史,他属人的特征——习得语言——也依然与一种幼儿境况和一种外在性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谁,只要他相信特定的命运,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地说话。)
真正的灵性和文化不会忘记人的语言这个原初的、幼儿的召命;而那种为传递不朽的、编码的价值(在这样的价值中,幼体持续的开放,在一个特定的传统中,再次关闭了)而模仿自然的生殖腺的尝试,恰恰是堕落的文化的特征。事实上,如果说有什么把人的传统和基因代码的传统区分开的话,那么,区分二者的确切来说正是这个事实,即,人的传统想要拯救的,不只是可拯救的东西(物种的本质特征),还有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拯救的东西,那反而已经丢失的东西;或者这么说更好,那被当作一个特定的属性来占有,却恰恰因此而不可遗忘的东西,也就是说,存在,幼儿的体细胞的开放——只有世界,只有语言,才配得上它。理念和本质想拯救的是现象,那曾经存在的不可重复的东西;而符合逻各斯的目的的,不是保存物种,而是复活肉体。
在我们内部的某个地方,那个漫不经心的幼态持续的孩童,还在继续着他的王的游戏。正是他的游戏,给了我们时间,使那永不落幕的开放对我们保持微开的状态。而大地上各色的人和语言,都以各自的方式,为保存和抑制——在多大程度上保存,就在多大程度上推迟——而看守着那个开放。各种各样的民族和那许许多多的历史的语言都是虚假的召命,在它们的召唤下,人试图对他不可容忍的声音的缺失做出回应;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它们(人的这些尝试)是注定没有结果的,试图把握不可把握的东西,变成——这个永恒的孩童——大人的尝试。只有在那一天,当原初的幼儿的开放真正地、令人眩晕地如是地被把握的时候,当时间终于完成的时候,人才终有能力建构一种普世的、不再延迟的历史和语言,并停止他们在各种传统中的徘徊。这个人类对幼儿体细胞的真正回忆被称为思想——也就是,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