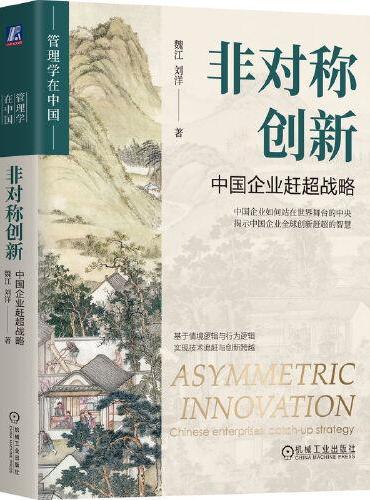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谁之罪?(汉译世界文学5)
》
售價:NT$
240.0

《
民国词社沤社研究
》
售價:NT$
640.0

《
帕纳索传来的消息(文艺复兴译丛)
》
售價:NT$
495.0

《
DK威士忌大百科
》
售價:NT$
1340.0

《
小白学编织
》
售價:NT$
299.0

《
Android游戏开发从入门到精通 第2版 王玉芹
》
售價:NT$
495.0

《
西班牙内战:秩序崩溃与激荡的世界格局:1936-1939
》
售價:NT$
9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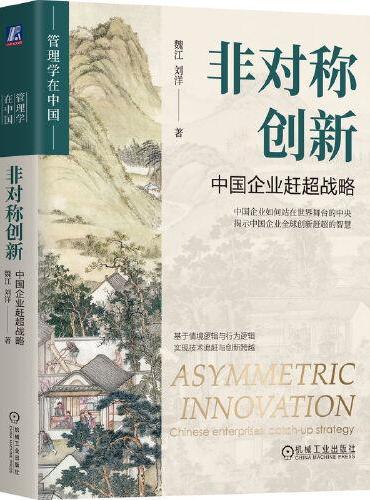
《
非对称创新:中国企业赶超战略 魏江 刘洋
》
售價:NT$
495.0
|
| 編輯推薦: |
王跃文 著《漫水》为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之一种。
一、该丛书是首部由当代著名评论家点评的涵括中国百年经典中篇小说、展示中国百年中篇小说创作实绩的大型文学丛书。
该丛书对五四以来中篇小说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读者可以通过本丛书确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中篇小说的阅读坐标。当代著名评论家何向阳、孟繁华、陈晓明、白烨、吴义勤对作品的文学价值以及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对文本进行了精彩点评,这对于读者欣赏把握这些经典作品起到了引导作用。
二、形式有突破。
丛书以作家分册,每册精选该作家*经典、读者认知度高的作品。除经典作品以外,另附文学化的作家小传及作家图片若干幅。所附内容既可以为文学研究者、文科学生提供必要的资料,对普通读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同样大有裨益。
三、所选作家有较大影响力。
作者出生于北京,而后求学生涯乃至之后的生活都在北京,北京的本土文化浸润着他的思想,也为他的京味语言的形成提供了养料,他也以自己戏谑幽默的京味语言、亦庄亦谐的叙述风格被誉为新一代顽主,拥趸甚众。
|
| 內容簡介: |
|
《漫水》是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中的一种,该项目已增补进入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小说讲述了以于公公、慧娘娘为代表的乡村人物的情感和人生经历,写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依存,也写出了乡村伦理在历史进程中遭遇的裂变。小说承接了自沈从文以来的湖南乡土小说的文脉,用醇厚生动的乡土语言,展示了乡村美好的人情人性,也表现出作者对乡村历史变迁的深刻洞察与审视。《漫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
| 關於作者: |
|
王跃文,当代作家,湖南溆浦人。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苍黄》等六部,中短篇小说若干,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从2001年10月起,专职写小说。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
| 目錄:
|
漫水
秋风庭院
我的堂兄
如何写好一个人?王跃文中篇小说的钥匙何向阳
|
| 內容試閱:
|
如何写好一个人?
王跃文中篇小说的钥匙
何向阳
如何写好一个人?这样一个问题,是几乎所有小说家都会在自己的小说中面对的问题。当然,就是那些不以人物塑造为目的的小说家,对于他们而言,也会或多或少迷惑于这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只有人能够写小说,只有人能够在现实以外的虚拟世界里创造自己。
那么,问题来了。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一,决定了文学的多样,小说家的多样。
王跃文的回答在他的小说里。从他两套笔墨一个是故乡里的人,一个是职场中的人,我们看到那个看似不一的答案最终却坚韧地纠缠在了一起。
读王跃文的中篇小说,与读其长篇所得的感受不太一样。中篇小说的结构与节奏,更紧更密,以至在阅读时会有密不透风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漫水》中尤为贴切。它不是丝丝入扣,相反它的叙述相对缓慢和跳跃,但因为细腻入微而有一种讲古的感觉,一种古雅,一种不计其他的一意孤行的意思,但这孤行,却又是左右逢源的,它毕竟是杂糅了种种人生经验同时也是种种人性经验的乡村叙事。所以这种阅读经验是与我们平常所获得的经验不一样的。如果真有北方叙事和南方叙事之分,这种写作就是典型的南方叙事,它是细细碎碎的,枝枝蔓蔓的,它像植物茂盛的森林,密不透风。
这可能就是《漫水》之漫,这种从生活本源的不断溢出,让我们的阅读有了一种徜徉之感,一种回归之感。南方叙事中的湖湘叙事,或者就是湘地叙事,尤其如此。比如,我们很难从韩少功的《爸爸爸》中找到一条明晰的线说它是写什么的,它什么都呈现给我们,而并不急于告知它要写的那个什么。还有,同是湖南作家的彭家煌,他的小说也是有两套笔法,一种以含蓄蕴藉的笔法写湖南乡土气息浓重的乡村生活,一种以嘲讽幽默的笔法写城市市民生活,当然,他最著名的还是前者,但是若要让一个评论家一言以蔽之地提炼出比如《陈四爹的牛》或《牧童的过失》等小说的主旨,也是艰难的,因为小说虽则不长,但枝蔓四溢,感性为王,根本是与中心思想主题精神这样的机械理性分析与单一价值判断相背离的。沿着这一条人文的路线,我们还可以看到沈从文,他的小说更是散文化得很,以至让人难以区分,倒不在笔法的散文化,而是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非人为的品格,就是让人与事、让生活本身、让原生态的人在场说话,而不是作家本人在那里喋喋不休。他的《边城》如此,《萧萧》如此,《长河》亦如此,当然,《牛》更是如此。
有了这样的眼光,我们回身再看《漫水》,便知王跃文的小说也是浸润在这样的一种人文文化中的。《漫水》中的余公公、慧娘娘,就很难用现成的人物模式套进去,他们更像是自然成长出来的,而不是作家主观创造的,作家在这里只是诚实地记录下来他们,而不是拔高他们或扭曲他们。这种诚实是怀有记忆的敬意的,是对乡村人的自然状态人的生态的一种虔敬和诚意。于此,这里的人之塑造,不是我们常见的这一个人,而是这一个人,人是重点,这一个并不突出。余公公、慧娘娘以及更多的乡亲所秉承的那一种生活伦理与自然法则是群性的,他们散漫在称为漫水的村子里,几十年、几百年都是这么过日子求生计,他们有着自己的一整套生存理念与生活沿袭以及情感联系,这种理念、沿袭与联系是已经现代化的我们难以严格秉承的,却如我们的祖规或家谱,不能为我们所忘记。小说也写了被现代化的余公公们的儿孙一代,当然那种叹惋,也可视作20世纪之初写下《边城》的沈从文的叹惋的延续。
那么,回到人的问题上。我以为王跃文所秉承的小说观是与现代化的小说观不一样的,后者是必有一个这一个来解说和阐释作家的理念。王跃文不然,他的特异性在于,他走的是一条反的路线,他从人物返回到人,他由主观塑造的人到自然法则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人。他对于人之个体的看法是不同的。他是前现代化的拥戴者。于此,《漫水》可视作是为一个称为漫水的村庄立传,在这个故乡之中,他小说中的人物很难一言以蔽之,余公公是什么样的人,一言难尽,慧娘娘又是什么样的人,也是一言难尽,因为他们都是人,而人是一言难尽的。我们只是看到感到这些人平平实实地、相亲相爱地生活着,虽在生活中有着各式样的小摩擦小纠葛,但在大节大义大的做人伦理上他们不输自然,经由他们传承和建立起的一整套长幼有序、互帮互助的生活秩序,人在其中,是有所敬畏和遵从的。所以,我说,它是一部前现代之作,丝毫没有反现代之意,也没有贬低之意。现在我们再看《边城》,谁能说那些生活在边城的人是反时代的人呢?谁能说记录下来他们并怀着礼赞和不舍之情的沈从文是反现代化的作家呢?恐怕不能狭义地理解现代化,那样的话则是机械的现代化,未必是人的现代化。而一个作家,是必须在物质的现代化进程中,思考人的现代化的。以之重读《漫水》,你会注意到王跃文小说中的散漫,也许是一种与村庄的节奏相叠合、相贴切的散漫。他的小说中,有将人物还原为人的倾向感。别的作家是综合杂糅各人而成就人物,而他则反着来,将你也许期待的人物打碎了还原成一个个的个体的人,真实的人。这种小说,也许只有南方叙事中有这样的人,也许多出自南方作家之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是自觉的,而是自然带出的。因而,之于这一个个的人的个体而言,典型一词在此无用,典型理论在此也面临失效之险。
那么,《我的堂兄》写的是一个人,通哥的这一个是不是最靠近一个典型呢?如果从人物来说,他的确是有一个成长史的人物,但比较《漫水》中人物的生存状态,这个人虽也是故乡环境中的人,却是在我(六坨)的观察下有着始终,有着我们称之为命运的长度。通哥是有才华和能力的,但真的是时运不济,加之所遇非人,他的能力与才华均被耽误和埋没,以致从向往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而屡屡遭他人篡改,到真的自暴自弃,以致到了最后还需我去监牢中接他出来。这样一个抛物线中的曾是非常生机鲜活的生命,被浪费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看法,作家的批判也是不动声色的,但是,较之他笔下之人的成长环境与性格养成,他的批判并不在通哥一方,而是在那些总是在通哥有可能改变命运时却来阻挠他改变命运的人,那些权力在手、肆意应用却不觉得是伤害他人的人,更何谈爱惜通哥的才分。作家对于这种反复出现,几乎是在每一层面都有这样一类人把持的现象,通过一个通哥揭示了出来。通哥,本来依他的才分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却最终也没能过上他起初想要的生活,以致成了一个有着阿Q相的人。在这一点,小说又突显出一种现代性的锋芒。
揭示权力对人的伤害,在《秋风庭院》中达到极致。陶凡是一个从官职上退下来的人。按说从官职上退下来,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自社会人到自然人的隐身和回归,加之陶凡本人又是一个爱好艺术而内心极为敏感的人,这种回归应该给了他巨大而难得的空间,去做自己以前想做而未来得及做的事。但回归谈何容易?经年的职场磨砺,使他对人事的敏感也极为发达,对于关系,对于后来者的态度与决策,他的信号系统并未随着退位而关闭,反而愈加敏感。动辄伤心、恼怒、愤慨而又消沉,令其无法安心,那艺术也一直对位于这样的不安,画面的讽喻与暗示,让我们看到由于艺术家本人的心态而使得他的艺术作品从来没有平静地回到自己。回到自己,是如此艰难,从这一个角色的自我退下来,回到本我,是如此不易。这是疾病的隐喻吗?陶凡,居然在桃树被砍光的山坡上有着自我被腰斩的感受,他所接受的信号,早已不再单纯,而一直是来自他者的所谓伤害,机心重重,防范不及,这不正是职场的机关重重导致的人心暧昧、人性脆弱的表现吗?官场后遗症是如此深重,以致这一个人在秋风之中再也感受不到来自人的温暖。身退而心乱,这一个人再也回不到了这一个人。王跃文的写作仍是声色不动,娓娓道来,但是这种对于人的关切,对于这一个的批判,对于真正的人的建设,对于人的异化的警觉,却是暗藏其中,绵里藏针。
如何写好一个人?关键在于人在现实中是什么样的?这个人,提供了什么样的存在?有什么样的存在,才可能有什么样的言说。言说一事,并非凭空而来,它或是记忆,或是现实,在我们于想象中造一个人出来之前,我们眼见的这一个人是避不开的。所以有先辈诗人说,如若想改变我们的语言,必先改变我们的生活。人物,也是如此。套用此句箴言,该是,如若要改变我们的人物,必先从改变人开始。然而,我们的人是否得到了改变呢?或者在另一些层面上,他(她)是否需要改变呢?这个问题纠缠下的作为作家的王跃文,一方面,他的关于人的理念是存放在余公公慧娘娘那里的,但是我们与作家一样在眼见着他们的消失,也许有一天他们只能存在于纸上,在现实社会中他们或将随着农业文明的逝去而只与我们相遇于文字中;另一方面,他的关于异化人的概念在陶凡那里,那是一个连自己的性格或者性情的故乡都回不去了的人,那是一个只有在角色中才能获得肉身的人。那么,人在哪里?什么慈爱地养育了这个人?又是什么无情地掠夺了这个人?得与失之间,或者还有一种,像通哥那样的,想成为社会人而不成,最终成为自然人而又不甘,只能成为在自暴自弃中麻醉自己的阿Q的翻版?不!如何写好一个人?如何塑造一个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文学的问题,他(她)的背后,隐含了太过沉重的社会学、人类学的概念,或者还不仅仅是概念,而就是人类的进化本身。
那么,这个命题,在经由也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雨果、卡夫卡等等作家提出来之后,王跃文再次将之提到我们眼前,仅就这一事实而言,这一命题,不只是一个作家、一个时代所要面临的难题。同时,这个写作的长链也显现出了这一命题的至关重要。是的,这个关于人与人物的命题,它在一切艺术之上,事关人的现实命运与未来发展。
2020年3月10日于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