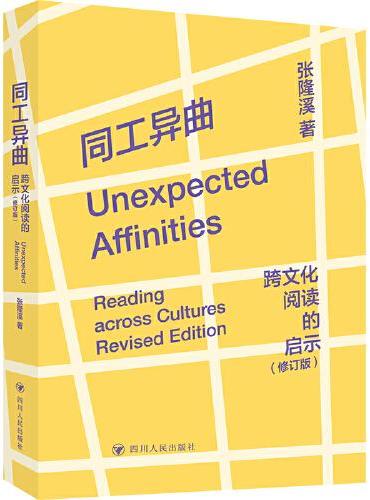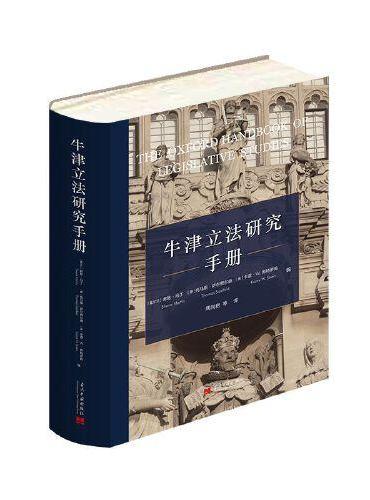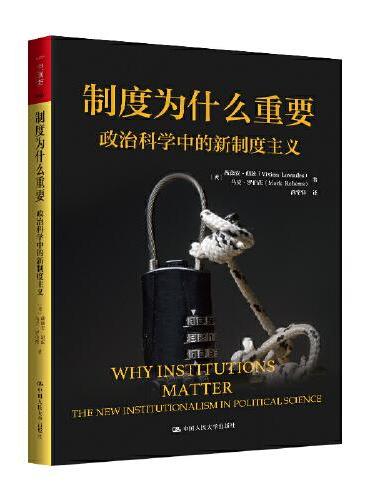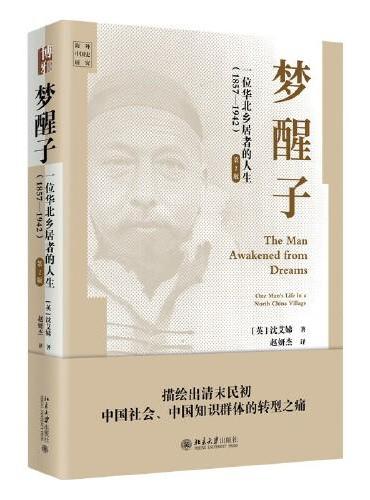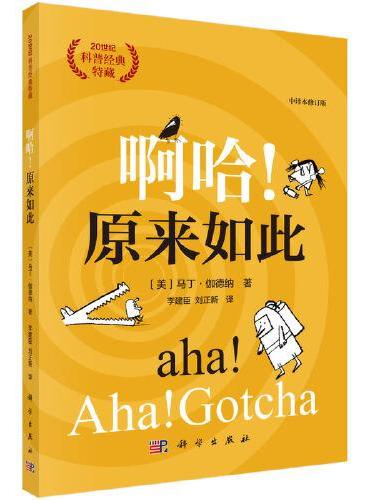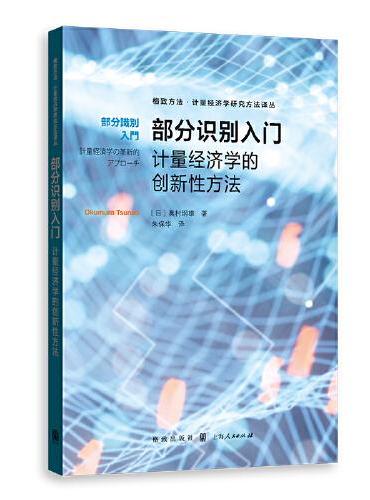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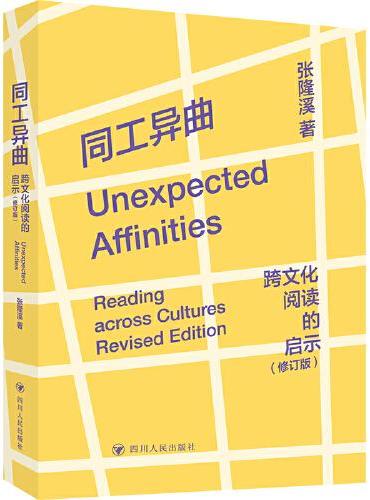
《
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修订版)(师承钱锺书先生,比较文学入门,体量小但内容丰,案例文笔皆精彩)
》
售價:NT$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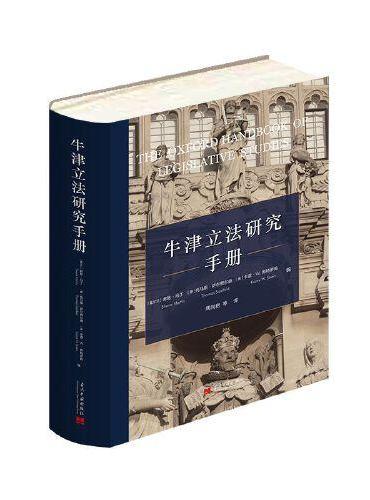
《
牛津立法研究手册
》
售價:NT$
16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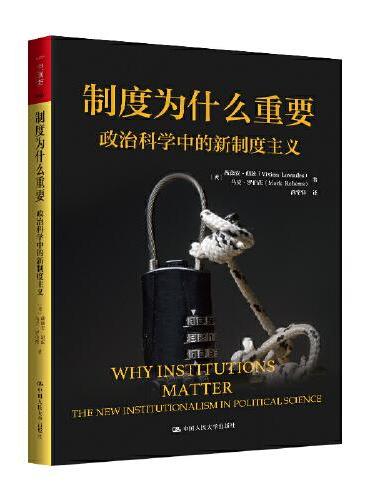
《
制度为什么重要: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人文社科悦读坊)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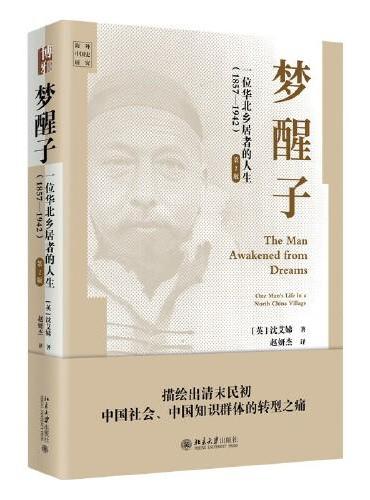
《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第2版)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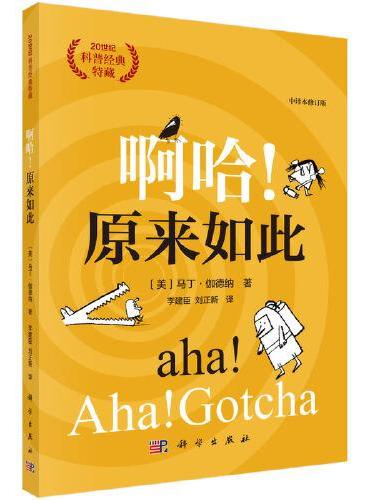
《
啊哈!原来如此(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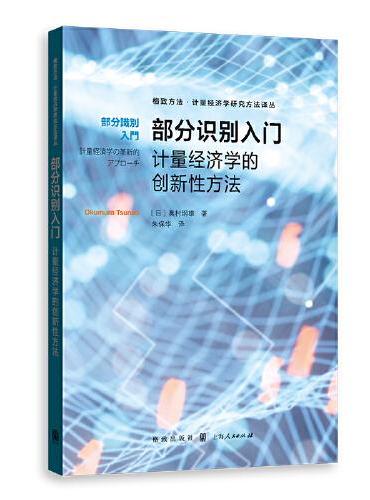
《
部分识别入门——计量经济学的创新性方法
》
售價:NT$
345.0

《
东野圭吾:变身(来一场真正的烧脑 如果移植了别人的脑子,那是否还是我自己)
》
售價:NT$
295.0

《
严复与福泽谕吉启蒙思想比较(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750.0
|
| 內容簡介: |
《大道与别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高山流水文丛之一种。
《大道与别径》是诗人郭建强的随笔集,收录了诸多充满哲理又醇厚隽永的文章。这些关于文学的阅读体验,特别是品评青海作家和诗人的文字,把读者带入了一个由广袤草原、高峻雪山、钴蓝天空,以及交融交织的多元文化组成的高原世界。在这个场域里,民族和世界之间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城市和乡村、草原之间的各种碰撞和反思,如同江河汇流,急浪翻涌,成为了本书的音效和背景;同时,展现了作者对文学艺术真趣的追求和生活之爱。
|
| 關於作者: |
郭建强,1971年出生于青海西宁。
著有诗集《穿过》《植物园之诗》《昆仑书》等。
获青海省第六届文学艺术创作奖,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人民文学》2015年度诗歌奖,2017年《文学港》储吉旺优秀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
|
| 目錄:
|
第一辑 诗人记
海子
昌耀
张枣
食指
异才
洛嘉才让
马丁
马钧
老虎、布莱克、多棱镜
胡安娜
巴列霍:痛苦深积在魂灵里
第二辑
既梦既醒读书记
轻盈地逸升
流水映倒影
得书记喜
失书记怅
读书,读书
买书,买书
搬书,搬书
关于书籍
眺望式的历史性乡愁
生物性世界图景中的说明和反讽
旅行是一种文学的动词
宿命的负债人
第三辑 为什么吟唱,为什么倾听
大睁双眼,沉入绿色之梦
杂草:人类生活的明证和隐喻
风吹城廛花木摇
一纸花笺邀入梦
波浪如同象群,披挂中国铸铁铠甲
《孤筏重洋》:行动之诗
在桑叶的脉网中穿行
人类智慧的地下布局
为什么吟唱,为什么倾听
一个镜中人,两本法国诗
近乎沉默
在巨流之源,饮《世界文学》
无休无止的搏斗
无能为力的审判
每一刻都重要
伊斯梅尔卡莱达来到我们身边
阅读勒克莱齐奥
在猜谜中品茗生命的滋味
《第七天》:哀歌和圣咏
向上的阶梯
用大半生来熬的一帖药
土地的不可估量的忧郁
伫岸听波 临水鉴心
第四辑:大道与别径
一个来自土星的牧人的漫游
我们的影子透露什么秘密
移民青海的本土叙事和人文追问
大道与别径
孤儿谜团尸语者
复活巴尔扎克的精神
鎏金镀银的温暖吟诵
两头血光的旅程
风吹肉身,沙磨骨桠
失根的人们
从文化的寓言到生命的感觉
沉浸在自然凝炼的脂膏里
|
| 內容試閱:
|
总序
五四新文学运动一百年来的历史证明:新文学之所以能够朝气蓬勃、所向披靡,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始终与青年的热烈情怀紧密连在一起,青年人的热情、纯洁、勇敢、爱憎分明以及想象力,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我说的文学创作资源,并非是指创作的材料或者生活经验,而是指一种主体性因素,诸如创作热情、主观意志、爱憎态度以及对人生不那么世故的认知方法。心灵不单纯的人很难创造出真正感动人的艺术作品。青年学生在清洁的校园里获得了人生的理想和勇往直前的战斗热情,才能在走出校园以后,置身于举世滔滔的浑浊社会仍然保持一个战士的敏感心态,敢于对污秽的生存环境进行不妥协的批判和抗争。文学说到底是人类精神纯洁性的象征,文学的理想是人类追求进步、战胜黑暗的无数人生理想中最明亮的一部分。校园、青春、诗歌、梦以及笑与泪都是新文学史构成的基石。
我这么说,并非认为文学可能在校园里呈现出最美好的样态,如果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校园可能是为文学创作主体性的成长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准备。在复旦大学百余年的历史中,有两个时期对文学史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北碚,大批青年诗人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个性鲜明的诗歌,绿原、曾卓、邹荻帆、冀汸形成了后来被称作七月诗派的核心力量;这个学校给予青年诗人们精神人格力量的凝聚与另外一个学校即西南联大对学生形成的现代诗歌风格的凝聚,构成了战时诗坛一对闪闪发光的双子星座。还有一个时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复旦大学中文系设立了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两个专业,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依然是以这两个专业方向来进行招生,吸引了一大批怀着文学梦想的青年才俊进入复旦。当时校园里不仅产生了对文学史留下深刻印痕的伤痕文学,而且在复旦诗社、校园话剧以及学生文学社团的活动中培养了一批文学积极分子,他们离开校园后,都走上了极不平凡的人生道路,无论是人海浮沉,还是漂泊他乡异国,他们对文学理想的追求与实践,始终发挥着持久的正能量。74级的校友梁晓声,77级的校友卢新华、张锐、张胜友(已故)、王兆军、胡平、李辉等等,都是一时之选,直到新世纪还在孜孜履行文学的责任。他们严肃的人生道路与文学道路,与他们的前辈七月诗派的受难精神,正好构成不同历史背景的文学呼应。
接下来就可以说到复旦作家班的创办和建设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复旦大学受教育部的委托,连续办了三届作家班。最初是从北京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接手了第一届作家班的学员,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高山流水文丛》策划书所说的,当时学员们见证了历史的伤痛,感受了时代的沧桑,是在痛苦和反思的主体精神驱使下,步入体制化的文学教育殿堂,传承五四文学的薪火。当时骆玉明、梁永安和我都是青年教师,永安是作家班的具体创办者,我和玉明只担任了若干课程,还有杨竟人等很多老师都为作家班上过课。其实我觉得上什么课不太重要,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初的讲课情况,学员们可能也忘了课堂所学的内容,但是师生之间某种若隐若现的精神联系始终存在着。永安、玉明他们与作家班学员的联系,可能比我要多一些;我在其间,只是为他们个别学员的创作写过一些推介文字。而学员们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也多次回报母校,给中文系学科建设以帮助。
三十年过去了。今年是第一届作家班入校三十周年(19892019)。为了纪念,作家班学员与中文系一起策划了这套《文丛》,向母校展示他们毕业以后的创作实绩。虽然有煌煌十六册大书,仍然只是他们全部创作的一小部分。因为时间关系,我来不及细读这些出版在即的精美作品,但望着堆在书桌上一叠叠厚厚的清样,心中的感动还是油然而生。三十年对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而言,不是一个短距离,他们用文字认真记录了自己的生命痕迹,脚印里渗透了浓浓的复旦精神。我想就此谈两点感动。
其一,三十年过去了,作家们几乎都踏踏实实地站在生活的前沿,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呼啸中,浮沉自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没有离开实在的中国社会生活,很多作家坚持在遥远的边远地区,有的在黑龙江、内蒙古和大西北写出了丰富的作品,有的活跃在广西、湖南等南方地区,他们的写作对当下文坛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即使出国在外的作家们,也没有为了生活而沉沦,不忘文学与梦想,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态度。他们有些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华文文学领域的优秀代表。老杜有诗: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这句话本来是指人生事业的亨达,而我想改其意而用之:我们所面对的复旦作家班高山流水般的文学成就,足以证明作家们的精神世界是何等的轻裘肥马,独特而饱满。
其二,三十年过去了,当代文学的生态也发生了沧桑之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已经从80年代的神坛上被请了下来,迅速走向边缘;紧接着新世纪的中国很快进入网络时代,各种新媒体文学应运而生,形式上更加靠拢通俗市场上的流行读物。这种文学的大趋势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不能不构成严重挑战,对于文学如何保持足够的精神力量,也是一个重大考验。然而这套《文丛》的创作,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依然坚持了严肃的生活态度和文学道路。我读了其中的几部作品,知音之感久久缠盘在心间。我想引用已故的作家班学员东荡子(吴波)的一段遗言,祭作我们共同的文学理想:
人类的文明保护着人类,使人类少受各种压迫和折磨,人类就要不断创造文明,维护并完整文明,健康人类精神,不断消除人类的黑暗,寻求达到自身的完整性。它要抵抗或要消除的是人类生存环境中可能有的各种不利因素它包括自然的、人为的身体和精神中纠缠的各种痛苦和灾难,他们都是人类的黑暗,人类必须与黑暗作斗争,这是人类文明的要求,也是人类精神的愿望。
我曾把这位天才诗人的文章念给一个朋友听,朋友听了以后发表感想,说这文章的意思有点重复,讲人类要消除黑暗,讲一遍就可以了,用不着反复来讲。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说,讲一遍怎么够?人类面对那么多的黑暗现象,老的黑暗还没有消除,新的黑暗又接踵而来,人类只有不停地提醒自己,反复地记住要消除黑暗,与黑暗力量做斗争,至少也不要与黑暗同流合污,尤其是来自人类自身的黑暗,稍不小心,人类就会迷失理性,陷入自身的黑暗与愚昧之中。东荡子因为看到黑暗现象太多了,他才要反反复复地强调;只有心底如此透明的诗人,才会不甘同流合污,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之所以要引用并且推荐东荡子的话,是因为我在这段话里嗅出了我们的前辈校友七月派诗人中高贵的精神脉搏,也感受到梁晓声等校友们始终坚持的文学创作态度,由此我似乎看到了高山流水的精神渊源,希望这种源流能够在曲折和反复中倔强、坚定地奔腾下去,作为复旦校园对当今文坛的一种特殊的贡献。
复旦大学作家班的精神还在校园里蔓延。从2009年起,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立了全国第一个MFA的专业硕士学位点。到今年也已经有整整十届了,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优秀写作人才。听说今年下半年,这个硕士点也要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我想说的是,作家们的年龄可以越来越轻,我们所置身的时代生活也可以越来越新,但是作为新文学的理想及其精神源流,作为弥漫在复旦校园中的文学精神,则是不会改变也不应该改变,它将一如既往地发出战士的呐喊,为消除人类的黑暗作出自己的贡献。
写到这里,我的这篇序文似乎也可以结束了。但是我的情绪还远远没有平息下来,我想再抄录一段东荡子的诗,作为我与亲爱的作家班学员的共勉:
如果人类,人类真的能够学习野地里的植物
守住贞操、道德和为人的品格,即便是守住
一生的孤独,犹如植物
在寂寞地生长、开花、舞蹈于风雨中
当它死去,也不离开它的根本
它的果实却被酿成美酒,得到很好的储存
它的芳香飘到了千里之外,永不散去
停留在一切美的中心
(引自《停留在一切美的中心》)
陈思和
2019年7月12日写于海上鱼焦了斋
序:权当一串串曲径分岔的脚注
己亥年惊蛰前两日,建强在微信里给我传来他已经编讫的一部书稿:《大道与别径》。浏览了一下目录,一多半文字早先读过,有的还在我们报纸的副刊上发表过。即便如此,我禁不住仍要为他榨取时间汁液、酣然锻造文字金蔷薇的韧力和拼力,拱手示敬,感佩再三。毕竟,对于一个曾经担纲综合性市民生活报的总编来说,日日如负泰山,时时如履薄冰、刻刻如临深渊,终竟而能呼吸匀称,气壮如牛,头不昏,眼不花,恐怕绕不过他对文学不可救药的沉溺。木心不是说过吗:文学是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
自救者郭建强在此之前,相继出版过《穿过》《植物园之诗》《昆仑书》三本诗集。藉此,他作为诗人的形象在当代汉语诗坛可谓头角峥嵘,他的名气也更其响亮地从原乡传播到远方。而《大道与别径》则迥异于先前的书写:它是一本文集涉及他对一些诗人的印象,读书、藏书、搬书的经历,对某些文学作品的赏析,对个别诗人、作家的品评。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四十年前写过一篇《诗人与散文》的文字(收录在坊间口碑甚佳的散文集《小于一》中)。布罗茨基如是表达了他对诗人写作散文的疑虑和慰藉:谁也不知道诗人转写散文给诗歌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即散文因此而大受裨益。他接着拿茨维塔耶娃为例,指出诗人由诗而文之后所获得的文本效应,乃是:把诗学思维的方法论重新植入散文文本中,使诗歌生长到散文中。郭建强的由诗而文,路数与茨维塔耶娃如出一辙,也是把诗歌的基因输入到散文的肌体,频繁地运用意象思维去谈艺衡文、知人论世,于娴习的诗人法器情感、意象、通感、比喻、象征、想象力、内在节奏、跳跃思维等等诗性的暗物质之外,又抖搂出理智、逻辑、判断、知识、灼见这些耀眼、明亮、尖锐的理性物质。郭建强似乎就此在理智与情感的跷跷板上,稍稍平衡了一下他的左脑和右脑,他的情智世界。
依我看,由诗而文,就是诗人的由内而外,由隐而显,就是诗人的一种自我显形。而诗歌骨子里就袅袅然冒着一股子隐身的气质;它总是在词语里滋生神秘,幻织迷雾,总是在舌尖下弹射巫辞、谶言和灵语,总是在用高超的迂回方式,发布着世俗世界里难言的智慧与洞见,还有真相。而诗人的转向为文,几近于把深海洋流里的游鱼,抛到陆地,间或明亮而短促地闪耀一下片片鳞甲的光芒,然后满身尘土地在地上翻腾、翕张鱼鳃,开张的鱼唇,仿佛叠印出蒙克那幅名画中桥上男人捂着耳朵呼叫的嘴形。
按照东西方文人约定俗成的文体等级,我把郭建强的诗歌视作正文,而把《大道与别径》这样的转型文字散文,统统视作对诗歌文体的一串串曲径分岔的脚注。
也就是说,诗歌是郭建强写作生涯和文学世界里的帝王,其余文字当是王之扈从(尽管他曾经也尝试写过若干短篇小说,仅从他的才情禀赋来看,他日的郭建强有无可能在小说这个包容性更强的文学体裁上,盯着诗歌,像刘邦那样轩昂一叹:彼可取而代之!,尚不可得而知)。
翻阅这本文集,郭建强最漂亮的文字当然是那些描画诗人、赏析诗作的篇什。诗人的灵与肉,使他但凡谈及与诗歌相关的话题,必会气爽神清,睛瞳放光,诸根互通,妙语纷披,发出一连串本色当行的声音。口说无凭,以例为证:
海子的天才在于,他能极准确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以近乎稚拙的手法,捕捉、定格光与影之间你进我退的残酷迷局,他的抒情含有一种来自血液和泪水的质地。(《海子》)
以肉身探触世间的那种疼痛和苦涩,像结晶的粗粒盐一样,凸显出昌耀最核心的诗歌主题:命运。(《昌耀》)
张枣早期诗歌中的微妙,到后来变得有些呛人,却仍然散发着奇怪的美感。我奇妙的肺朝向你的手,像孔雀开屏,乞求着赞美。(卡夫卡致菲丽丝》)张枣对于热情和绝望的书写,如此诡异,如此真切,如此美丽(《张枣》)
他也说话,低低的,有种过滤杂音的感觉;他就在咫尺之间遥遥劝酒,举杯致意,带着隐士间手谈的意味,有一种亲切的疏离的风度。我只觉得这夜饮也真也幻,梦残如花。(《洛嘉才让》)
诸如此类的文字,在书里俯拾即是,我想特别地说一声,郭建强这般如庖丁解牛般深中肯綮的文评,可不是什么文学研究生和文学博士们,包括许多学院派文学教授们能够轻易咳唾出来的文字。何以故?此乃诗人郭建强的郭氏秘制,一般人哪里能控得出这般精妙透辟的文辞!这样的文案,钱锺书的著述里早就反复下过截铁斩钉的断言:文人慧悟愈于学士穷研。
郭建强在这本书里自我披露了他的一种怪癖(一见怪癖一词,我的海马CA3区神经元就会串联到布罗茨基的一句名言: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郭诗人的这个怪癖,倒也跟什么抗恶挂不上钩,不过是以动物比拟友朋罢了,来路也不过是诗人屡试不爽的诗法,理论上我们把此法唤作隐喻、概念转换。我记起当代文评里几乎要空前绝后的动物喻论,当属于胡河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撰写的作家论,他以术数文化冠名蛇精格非灵龟苏童神猴余华。因其英年早逝,斯法也就半世而斩,回过头来瞻顾当下文坛,称为绝响也不为过。不过,倘若想要往久远里追怀,我倒觉得动物喻论大抵是原始思维里初民动物崇拜、互渗律、交感巫术之类神秘思维和集体无意识的孑遗。德国浪漫派代表诗人诺瓦利斯在《碎金集》里写下过这样的句子:每个人都是从一棵古老帝王树上萌生而出的,但是,仍然具有这一出身来源印记的人又有多少呢?诗人郭建强身上无疑带着这么一种古老的胎记,他浑然憨实地遥承着这一心绪和文脉,他拿动物喻人的好意思、妙意味,隐伏在书里,这里一句那里一段地散布着,野香着,我这里就不越权替明眼的读者代劳拾取了。我倒是想借机模仿一下他以动物喻人的方法,以便和癖主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这本文集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诗人郭建强给自己画的一幅嗜读自画像草稿。茨维塔耶娃说过:阅读是创作过程的共谋。一位诗人、一位作家谈论他的阅读,至少会让目光锐利的读者,见出他们心智的蜜源,见出他们与心仪的高人之间吮吸的蛛丝马迹。
关于他的阅读,我想用三个动物来设喻作譬。
一是饕餮,古代钟鼎彝器上的贪食者(杜预细解为贪财曰饕,贪食曰餮)。郭建强的阅读兴趣,范围除了各种文学书籍(尤其偏嗜诗歌),他还阅读耽读历史(尤其是地方史)、地理学、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植物学、神话、美术、考古、建筑等等庞杂的人文学科著述。只要是能勾起他食欲的,他都会大快朵颐一番。这本书里他随口点出的阅读书目,不过是他通吃海喝里的一鳞半爪和冰山之一角,姑且名之曰老餮食单之一,俟诸异日,当有之二、之三、之七之八的文字络绎以续。
二是蜜蜂。贺拉斯说过:吾辛苦为诗,正如蜜蜂之遍历河滨花丛,勤劬刺取佳卉(钱锺书译)。蜜蜂的勤快与忙碌,再配上《野蜂飞舞》这支钢琴名曲,才能仿佛于郭建强钻入书丛的醺然意态。没错,他必须得比喻为一只野蜂,才可与他禀赋里的野性子、野路子、阅读行迹的无定等个性匹配得丝丝入扣。就其致知造艺的路数来说,他不像大多数作家、诗人,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逐级而上,他非正规的科班出身,只是在青海铝厂充满有毒气体和粉尘弥漫的铝电解质车间,读完了他的赫拉巴尔式的社会大学。那时候,他和铝厂的一帮文青(我名之曰精神饥饿兽),被当时名重一时的文学期刊、抢手的文学书籍,煽动得火烧火燎。按捺不住青春期的情感骚动和迷茫,他们一个个都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拖着沉重的肉身,借助阅读轻快一下自我,然后磨砺词语,锻造诗行,把倾诉悄悄地写在日记本上,秘密地锁在抽屉里,隔一段时日拿出旧作晾晾,掸掸词语,蓬松蓬松文字的肌理,再学着皮鞋匠反复擦拭,以求过往的文字磨亮如新。出于对文学的神圣感和朴素得近乎庄重起来的虔敬,他们一面袖着习作,羞于示人,很少放开胆子投寄给那些神圣的文学期刊;他们一面又在志同道合的工友间半隐蔽半公开地负气争胜。小环境里的比试较劲,不知不觉间练就着他们写作的肌腱,提升着彼此的表达质量。及至后来(1991年间)郭建强在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进修了一年半(堪称他最美好的一段文学时光),算是从自修自证,走向了老师、同道面对面的高级别开示,从此悟力、创作力日益勇猛精进。
三是秃鹫。诗集《昆仑书》原先的书名不叫《昆仑书》,诗人自己的命名叫《秃鹫》,后来遵照出版社的建议,改成了现在的书名。诗人初衷里用秃鹫为书名,肯定有着他不苟同于世俗的价值趋向和审美考量,至少他把这种在很多人眼里视为不雅驯的动物,进行了一次诗学意义的加冕,赋予其若干高贵的价值和神妙的仪态,比如哲学家的冷静眼神,王者的漫步,比如懒懒地起身,比如飞行吞噬时光。在那首同名诗里,郭建强没有写到的一个地方,乃是秃鹫吞食骨头的习性。凭着超强的胃酸,秃鹫可以消融掉任何坚硬的骨头。我曾观看过一个视频,是一只秃鹫遇到比它的嘴最大的张合度还要大许多的整块骨头,它就把骨头叼到半空里,从高处把骨头丢到坚硬的岩石上,借助重力加速度去摔碎骨头。我想说的是,郭建强的一种阅读风格,太像秃鹫的吞咽了,他有时候未必去细嚼慢咽,而是迅速大块吞下,让胃去慢慢分解和消化。我以前阅读郭建强的诗歌,发现骨头一词是他诗歌里的一个高频词语,原先我只想到这与他对生命、对死亡的极度敏感有关,现在我似乎在秃鹫的意象联想中得到了新的感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