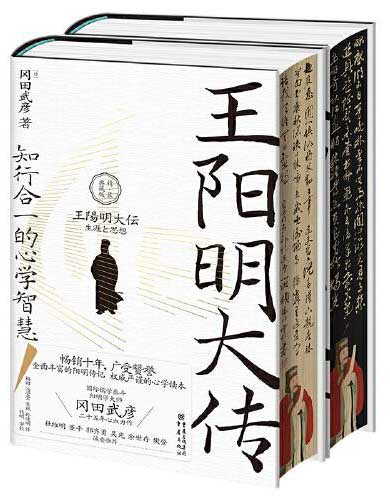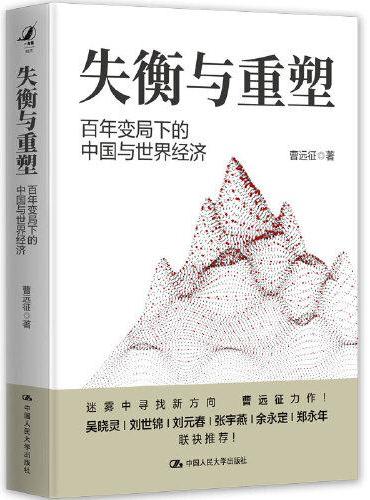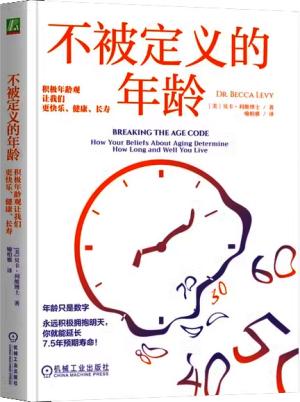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
》
售價:NT$
602.0

《
强者破局:资治通鉴成事之道
》
售價:NT$
367.0

《
鸣沙丛书·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
售價:NT$
551.0

《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兼论宗教哲学(英国观念论名著译丛)
》
售價:NT$
275.0

《
突破不可能:用特工思维提升领导力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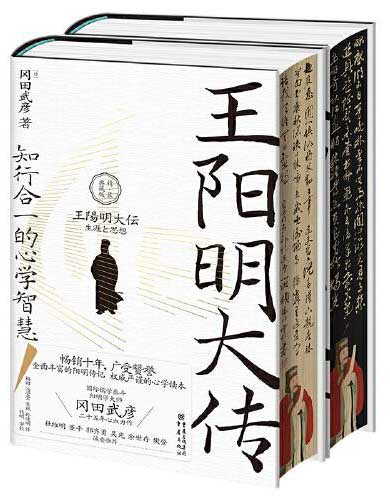
《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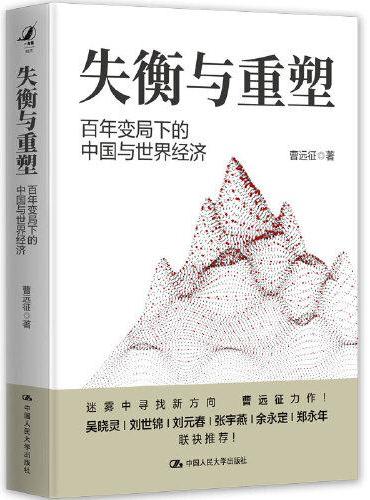
《
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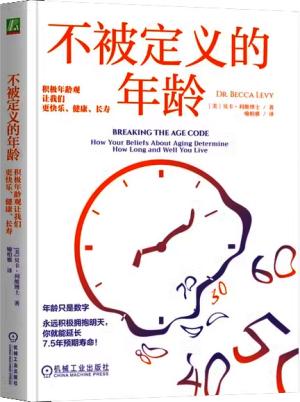
《
不被定义的年龄:积极年龄观让我们更快乐、健康、长寿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一部被改编为电影、话剧的双性人的回忆录
充满奇怪情色魅力的文字
倾听人类性历史中的失落声音
福柯的天才解读,唤醒平凡之外的命运,揭示文本的现实意义
|
| 內容簡介: |
|
1868年,位于巴黎贫民区的医学院街,一间简陋、肮脏的阁楼,一名男性自杀身亡,旁边放着一本自传的手稿。1897年,这本自传以《阿莱克西纳B的故事》为名,被一名法医学家编辑出版,人们这才发现了一位生活在黑暗之中的双性人的故事。这部双性人的自传以感情充沛的笔调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孩经受的折磨和动荡,以及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男性绝望的苦涩。1978年,在研究性史的过程中,福柯发现了这名声名狼藉者的生活。福柯把这部自传连同那些讨论真实性别所依据的医学和法律文件一同编辑出版,并附上一篇重要导读,阐释了双性人的身体如何成为话语权力管控的对象。福柯借助无确定性别的快感概念,回应了19世纪以来医学和司法要求确定真实性别的做法。
|
| 關於作者: |
|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他以其无比渊博的学识、才华横溢的文笔、惊世骇俗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现代主义、权力分析与社会理论、新文化史、刑罚史、身体史、性史、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以及文学与艺术批评等各种时代思潮。其主要作品有:《古典时代疯狂史》《词与物》《性经验史》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等。
|
| 內容試閱:
|
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真实的性别吗?现代西方社会以近乎顽固的坚定态度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现代西方社会令真实的性别这一问题遵循某种事物秩序,而在这一秩序中,人们可以自以为唯一重要的是身体的现实和快感的强度。尽管如此,长久以来,人们并没有这些需要。医学和法学承认双性人身份的历史就是佐证。人们用了很长时间要求双性人应该拥有唯一的、真实的性别。数世纪以来,又毫不费劲地认可他们有两个性别。那些造成恐惧、招致痛苦的残忍事件呢?事实上,情况要复杂得多。的确,无论在古代还是中世纪,都有不少死刑案例。但同样有与之截然不同的丰富的判例。中世纪,有关这方面的法规教会法和民法非常明确:那些两种性征这两种性征在不同人身上可能按不同比例分配并存的人被称为双性人。此情形下,由父亲或教父(因此,也是给孩子命名的人)在洗礼时决定其将被接受的性别。必要的话,建议选择两个性别中占上风的、最具力量、最强烈的那一个。但之后,进入成年阶段,到了要结婚的时候,双性人可自己自由决定是想要始终保留那个被赋予的性别,还是更倾向于另一个。只是必须的是:一经决定就不能再改了,要一直保持到死,违者以鸡奸罪论处。正是这些选择的改变,而不是人体构造上的性别混合,造成了绝大多数对双性人定罪的事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仍然保留着这些定罪的踪迹。[自十八世纪起],有关性征的生物学理论、涉及个人的法律条款、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形式一步步引导人们否定一个身体可以混合两种性别的观念,并因此限制不确定性别的个人进行自由选择。从那时起,每个人一个性别,唯一的性别。每个人都有最初的、深刻的、被限定的、决定性的性别身份;当另一种性征可能显现出来时,那只可能是偶然的、表象的,甚至仅仅是幻觉。就医学方面来看,这意味着面对双性人时,涉及的不再是承认出现两种并存或混合的性别,也不再是弄清楚两个中哪一个胜过另一个,而是破译隐藏在复杂表象下的真实性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医生要做的就是揭开迷惑人的身体构造,就是从可能已经具有相反性别形式的器官背后重新找到唯一的真实性别。对于那些擅长观察和诊断的人来说,性别的混合无非是对本性的掩盖:双性人都是伪双性人。至少这就是十八世纪时,通过一定数量的重要事件和激烈讨论而日趋获得证实的论点。从权利的角度来说,这显然意味着自由选择的消失。无论就法律而言还是就社会而言,都不再由个人决定他想要的性别,而是由专家来说本性为他选择了什么性别,并且因此社会应该要求他坚持这一性别。当人们必须求助于法律时(比如,某人被怀疑未按其真实的性别生活且不妥当地结了婚),它会为一种没有受到足够认可的本性建立或重建合法性。但如果本性可以通过随心所欲的改变或偶然发生的意外来欺骗观察者并在一定时间内掩盖真实的性别,那么人们也就可以怀疑那些个人为了能够像另一种性别那样利用自己的身体而隐藏对自己真实性别的深刻意识并利用某些人体构造上的怪事。简言之,本性的怪诞可以服务于放纵的习性。因此就有了对真实性别的医学诊断的道德关怀。我清楚地知道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医学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这种极度简单化中的某些东西。今天,即使曾经杂乱地囊括着人体构造上林林种种反常现象的领域被极大地缩小了,也不会再有人说所有双性人都是伪的。尽管困难重重,人们还是接受了一个人可以选择不在生理上属于他的那个性别。然而,认为人最终必须有一个真实的性别的观念远没有完全消除。无论生物学家对此持什么观点,至少在普遍的状态下,无论是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还是大众观点,都认为在性别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复杂、模糊而基本的关系。确实,对于那些违反法则的做法,人们宽容了一些。但他们还是认为其中一些做法是在藐视真相:被动的男人、男子气的女人、同性之间的爱情:人们或许愿意承认这并未对既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但他们同样足够相信这其中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东西。一种最传统哲学意义上的错误:一种不符合现实的做法;性别上的不规律或多或少被认为属于怪兽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想要摆脱认为这不是罪恶的观念如此困难,而想要摆脱认为这是得意的但无论如何是无用的,并且最好消除的发明的怀疑也没那么容易。请醒醒吧,年轻人,从你们虚假的享乐中醒来吧;褪去你们的伪装,记起你们有一个性别,一个真实的性别。此外,有人也认为恰恰在性别问题上必须探索个人最隐秘、最深层的真相;这样,才能最好地发现他是什么和什么定义了他;如果说数世纪间,人们认为必须隐藏与性别相关的东西是因为它们可耻,那么如今我们知道恰恰是性别本身隐藏了个体最秘密的部分:他那些幻想的构成、他的自我的根、他与真相的关系形式。性别的深处,真相。在这两种观点的交汇点上在涉及我们性别的问题上不能搞错,以及我们的性别隐藏了我们身上最真实的东西精神分析法强化了它的文化力量。它同时向我们保证了我们的性别那个真实的性别以及那暗藏在性别中的我们自己的全部真相。在真实性别的这段奇特历史中,阿莱克西纳巴尔班的回忆构成了一份档案。它不是唯一的,但足够罕见。十九世纪的医学和司法执意探询出真正性别身份的那些个体之一留下了这样一份日记,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份回忆录。在一个几乎完全由女性组成且非常虔诚的环境中被当作贫穷而值得称赞的小女孩抚养成人,埃尔屈利纳巴尔班周围人称她[ 本书中不同部分指代巴尔班时所用人称(她或他)依该部分作者观念而定,翻译时也均以原文为准。关于这些用法所暗含的作者意图,可参考《后记》的最后一部分。另需说明的是,在《后记》中,作者时而使用他,时而使用她,时而又两者并提,原文即是如此。译注]作阿莱克西纳最终被确定为真正的男性;被迫改变合法性别,经历司法程序和修改公民身份后,他无法适应新的身份,最终自杀。我真想说这是一个平庸的故事只有两三处让它有了点特别的强度。首先是日期。大约18601870年间,正好是性别方面的身份研究进展得如火如荼的时期之一:双性人的真实性别,还有对各种倒错的认识,它们的归类、特征构成等,简而言之,就是性反常方面的个人问题和类别问题。A. B.的最初检查报告于1860年以《身份问题》(Question didentit)为题刊登在一份医学杂志上。埃尔屈利纳-阿德拉伊德巴尔班,也叫阿莱克西纳巴尔班,或阿贝尔巴尔班,在他自己的文章里要么写作阿莱克西纳,要么卡米尔,是寻求身份认同的那些悲剧人物中的一位。这种既反应了当时寄宿生的写作方式,也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优雅、矫饰、爱用暗示,甚至有些过分铺排而且过时的文风,令叙述避开了所有获得认同的可能。后来医生向阿莱克西纳不确定的身体构造强加的那一有关真实性的残忍游戏,此前无人愿意在她曾经生活的女性圈子里玩,直到一次人人都在尽可能推迟、最终被两个男人一位神甫一位医生促成的发现。这具身体有些笨拙、不美,而且在与它一起生长的那些年轻姑娘中越来越显得反常,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却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而他似乎对所有人,更准确地说对所有女人,施展了某种魔力,蒙住了她们的双眼,把问题挡在了唇后。这种怪异的在场令那些在成人眼皮底下发生的接触、抚摸、亲吻具有了热量,这种热量受到所有人欢迎,而因为其中没有加入任何好奇心,人们的欢迎更是带着温情。故作天真的年轻女孩或自以为谨慎的年长教师都盲目得像是希腊神话里的人,对这个藏在寄宿学校里身材矮小的阿喀琉斯视而不见。这让我们觉得至少如果我们相信阿莱克西纳的叙述的话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激越、愉悦、悲伤、温存、柔情和苦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同伴的认同,尤其是密切联系之人的猜疑都不重要。[在操纵意识的艺术中,我们时常使用辨识力(discrtion)一词。这个特殊的词汇指向一种能力,即察觉差异,辨别情感,甚至在最细微的精神活动中,从看起来纯洁的表象下驱逐不洁,从心灵的激荡中分离出什么是来自上帝的、什么是被诱惑注入的。辨识力在于辨别(discriminer),如果可以的话,它会永远辨别下去;它应该充满好奇,因为它要挖掘意识的奥秘。但这个词同样旨在说明意识的操纵者还应能够把握分寸,能够知道在哪里停止,不能走得更远,能够对一定不能说的事情守口如瓶,能够让在光天化日下会变得危险的东西留在阴影里。可以说在这种属于修道院、寄宿学校、女性的和基督教的单性之爱的半明半暗的辨识体制中,阿莱克西纳可以活很久。而悲剧的是她进入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辨识体制中。管理、司法和医学的体制。在第一种体制下得到认可的细微变化和微妙差异在这里不再行得通。而我们在第一种体制下可以讳莫如深的东西,在第二种中则必须被暴露出来,必须被拿来分享。说实话,这已经不是辨别的问题了,而是分析。]从刚刚发现并建立新的身份起,阿莱克西纳就开始写她一生的回忆。她的真实的、确定的身份。但清楚的是,她并非在这一最终找到的或者说找回的性别视角下书写的。不是男人在讲述、在试着回忆当他还不是他自己时的感情和生活。阿莱克西纳写回忆录时,离自杀已不是很远;对她自己来说,她始终没有确定的性别;却被剥夺了她所体验到的与同她一起生活的、她爱着的并强烈渴望的人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所带来的快感。她追忆过去那种快乐的无身份的化外之地,矛盾的是,封闭、狭小、热烈的集体生活庇护了这种状态,在那些集体里,人们享受着只与唯一一种性别来往的既强制又禁忌的奇特幸福;[这让人们接受了甚至是他们的本质之本质的渐变、波动、明暗变化和色彩变化。由于分配和认同的严格要求,另一种性别不在那里,它会说:如果你不是你自己,不完全是,或不以同样的方式是,那么你就是我。推测还是错误都不重要;如果你留在那里,你就有罪。反省自己或者交出自己,然后成为我。我认为,阿莱克西纳既不想要这个也不想要那个。她不像一些觉得被自己的身体构造背叛或被一种不公正的身份束缚的人那样迫切渴望加入另一个性别。我想,她乐于在这个由唯一性别构成的世界、在这个承载了她的所有感情和全部爱意的世界成为别样的,却从不想加入另一个性别。既不是爱着女人的女人,也不是藏在女人中的男人。阿莱克西纳是对女性有着巨大渴望的无身份的主体;而同样是那些女性,没有什么能够迫使她们离开那个绝对女性的世界,对于她们的的女性特质来说,阿莱克西纳是有吸引力的,也确实吸引着她们。]大多数时候,那些讲述自己的性别变化的人都属于绝对的双性世界,身份认同上的不适被理解为想要进入另一边的渴望进入他们渴望拥有的或想要属于的性别的那一边。在这里,宗教生活和学校生活强烈的单一性别性显示出在所有与自己身体类似的人组成的圈子中迷失方向的无身份性发现并激起的温柔的快感。
当时,无论是阿莱克西纳的事件还是她的回忆录似乎都未能引起广泛关注。他通过塔尔迪欧的著作知道了阿莱克西纳的文章,这不足为奇:他是精神病学专家,并于1881年旅居法国。相比起医学,他更关注文学,但如果1882年返回德国后、在开始他的精神病医生职业生涯前他没有在某家图书馆找到《身份的法医学问题》一书,在法国时,他也应该看见过这本书。无确定性别的法国外省小姑娘与应该死在拜罗伊特避难所的疯狂的精神病学专家相遇,有什么好惊讶的呢。一方面是女子寄宿学校和天主教机构温热的氛围中涌动着的偷偷摸摸的无名的愉悦;另一方面是奇怪地将严格的实证主义与被迫害妄想症被威廉二世(Guillame II)迫害集于一身之人的反教权的狂热。一方面,秘密的特殊之爱在医生和法官的决定下变为不可能;另一方面,一位医生因为写了《爱的主教会议》被判一年监禁,这本书在那个时代必然被认为是最可耻的反宗教文本之一,他向瑞士寻求庇护,却因侵犯未成年人被驱逐。结果令人瞩目。帕尼萨保留了事件中个别重要的元素:阿莱克西纳B.的名字、医学检查的场面。他修改了医学报告,原因我不是很确定(可能是因为他手头没有塔尔迪欧的书,于是一面凭借阅读留下的记忆,一面使用他所能掌握的、情况有些相似的另一份报告)。他还颠覆了整个叙述。他改变了时代背景,改变了众多具体元素和整个氛围;尤其重要的是,他将主观的世界转变成客观的叙述。为整个文本营造出某种十八世纪的氛围:与狄德罗和《修女》(La Religieuse)气质相符。一所专为年轻贵族女孩服务的富裕的修道院;一位对侄女有着暧昧情感的好色女校长;修女之间的阴谋和竞争;富有怀疑精神的博学院长;容易轻信的堂区神父和抓着大叉子驱赶魔鬼的农民:其中写到的完全是一种易受影响的放纵、一场有些天真的不完全是纯洁的游戏,它与阿莱克西纳所在的严肃的外省教区相去甚远,也与《爱的主教会议》中巴洛克式的激情有很大距离。然而,帕尼萨在编造所有这些败坏风俗的风流韵事的场面时,特意在他的叙述中保留了一条宽阔的灰色地带:阿莱克西纳就在那里。修女、女教师、令人担忧同学、误入歧途的小天使,情妇、情人,森林中奔跑的野兽、温热的宿舍里悄悄潜入的魔鬼、腿上毛茸茸的怪兽、遭到驱赶的恶魔帕尼萨展现的只是她瞬间的形象,而别人正是通过这些形象看待她的。她,永远的男女孩、男女性,她是夜晚进入每个人的梦境、欲望和恐惧的那个东西,只此再非其他。帕尼萨只想把她塑造成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名字的灰色形象,在故事的最后消失,不留任何痕迹。他甚至不想用自杀将她留住,不想让她像阿贝尔巴尔班那样变成一具尸体,最终被那些好奇的医生赋予一个毫无意义的真实性别。我之所以把这两个文本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它们值得放在一起重新出版,首先是因为它们属于那个饱受双性人主题困扰的十九世纪末有点像受异装癖困扰的十八世纪那样。但同样是因为它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几乎没有一点丑闻性质的小小的外省传闻在传闻主角的记忆中、在牵涉其中的医生的认知里、在以自己的方式走向自己的疯狂的精神病学专家的想象里留下了怎样的轨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