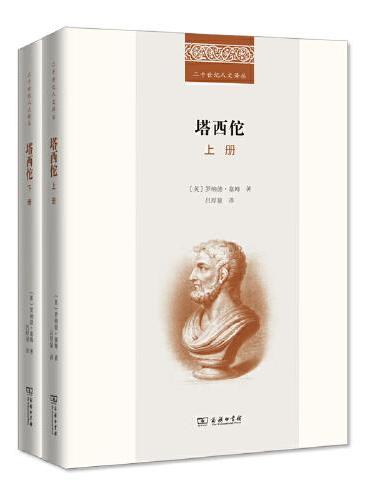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希腊人(伊恩·莫里斯文明史系列)
》
售價:NT$
845.0

《
世界巨变:严复的角色(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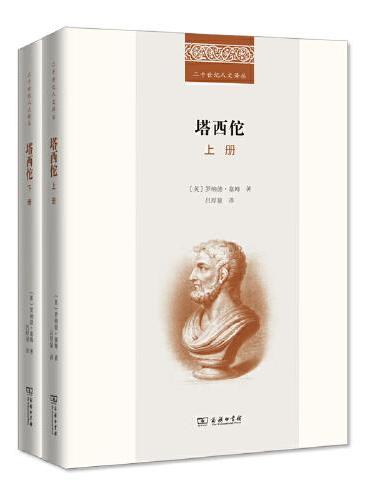
《
塔西佗(全二册)(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
售價:NT$
1800.0

《
宋初三先生集(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
售價:NT$
990.0

《
简帛时代与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上下册)(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1400.0

《
天生坏种:罪犯与犯罪心理分析
》
售價:NT$
445.0

《
新能源材料
》
售價:NT$
290.0

《
传统文化有意思:古代发明了不起
》
售價:NT$
199.0
|
| 編輯推薦: |
卡赞扎基斯是希腊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希腊人左巴》是他所有作品中广为流传的一部,被译为超过三十种文字,并搬上电影银幕,荣获三项奥斯卡大奖。
故事通过我和左巴的对话与思考,探索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这一永恒复杂的命题。两人的对话颇有古希腊对话录的风格,哲思色彩浓厚,发人深省。
卡赞扎基斯的这部作品影响了包括村上春树、李敖在内的许多知名作家。
|
| 內容簡介: |
我是一个读书人。我厌倦了长年以来闭塞死寂的书斋生涯,决定投身于真正的生活之中。在去克里特岛的途中,我结识了一个叫左巴的工人。这个老头已经六十余岁,曾经保家卫国上阵杀敌,也曾走街串巷兜售杂货,一生经历传奇丰富。他埋首工作时没日没夜,弹琴跳舞时不知停歇,不吝于赞叹世间美景,不惧于追逐欲望爱情。他虽已年逾花甲,却仍狂热地爱着生活中的一切,直至生命的终点。
在《希腊人左巴》中,相比踟蹰于理性和精神之中的主人公,左巴是激情与肉体的代表,两人的形象与相互交流体现着人类精神与肉体间既合且离的奇妙关系与激烈碰撞。卡赞扎基斯鼓励在灵与肉间徘徊不定的我们:要热爱生活,不怕死。
|
| 關於作者: |
|
尼科斯?卡赞扎基斯(Nkos Kazantzkis)20世纪希腊的重量级作家和诗人。他的作品体裁丰富,涵盖小说、散文、游记、戏剧和史诗,并曾将《神曲》《浮士德》等经典作品译为希腊语,为希腊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代表作品《基督的最后诱惑》《希腊人左巴》等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卡赞扎基斯曾九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卡赞扎基斯一生曾两次访问中国,与茅盾、郭沫若等作家有过交流,有希腊鲁迅的美誉。
|
| 內容試閱:
|
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比雷埃夫斯。我到码头去,打算搭船前往克里特岛。下着雨。一阵强劲的西罗科风猛烈地吹着,片片雪白的浪花一直绵亘到远处的小餐馆。那餐馆的玻璃门紧闭着,屋里弥漫着艾酒及体臭的气味。由于屋外的寒冽,人们的呼吸给窗子罩上了一层雾。五六个在那儿过夜的水手,紧裹着棕色的羊皮夹克,一边喝着咖啡或艾酒,一边凝视窗外朦胧的海。鱼儿在惊涛骇浪的冲击下已经潜到海底深处,它们将在那儿避难,直等到海面恢复宁静才会再度游上来。渔民们麕集在餐馆里,也在等待暴风过去,等待鱼儿回来追逐他们放下的诱饵。比目鱼、石鲈、鳐鱼都从它们夜的长征里归来了。天已破晓。玻璃门开了,一个船坞工人走进来,他个子矮壮,没戴帽,没穿鞋,浑身污泥,满脸风霜。“嗨!柯斯坦迪!”一个身穿蓝外套的老水手喊道,“近来做些什么事?”
柯斯坦迪啐了一口。“你想还会怎样?”他暴躁地回答,“早上——酒吧。晚上——我家。这就是我的生活。屁事也没有!”
于是,大伙儿笑了起来,有的则摇头咒骂。
“人生是场受不完的罪,”一个蓄髭的男子说,这是他从卡拉格兹戏里捡来的哲学,“不错,一场受不完的罪。去他妈的。”
一线微弱的绿光刺破了餐馆污秽的窗棂,照在人们的手、鼻子和额头上。然后,它又跃向柜台,照亮了酒瓶。电灯熄了半晌。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外头阴霾的天空。波涛的咆哮一阵阵地传来,餐馆里,水烟筒呼噜呼噜地响个不停。
老水手叹了一口气:“不知道列蒙尼船长怎样了?愿上帝保佑他!”他愠怒地瞪着海,咆哮道:“你这个摧毁了多少家庭的混蛋!”他咬着他那撮灰色的髭。
我坐在一个角落里,感到周身发冷,于是叫了第二杯艾酒。我想去睡一觉,可是却一直和睡魔苦斗着,同时也一直在抗拒着疲惫以及凌晨时分的孤寂。我凝视着朦胧的窗外。逐渐苏醒过来的港口再度喧嚣了起来,我听到船只的汽笛声和马车夫及水手们的吆喝声。而在我凝视的当儿,一张用海、天空以及离愁织成的无形之网把我的心紧紧地缠住了。
我的眼睛停留在一艘巨舶深色的船首上——整个船身依然隐没在黑暗里。天上下着雨,我看到无数的雨丝把天空和大地连接了起来。
我望着那黑船、阴影和雨,这时候一缕哀愁悄悄升起。旧事一起浮上心头。在这阴湿的空气中,雨使我忆起了我那位伟大的朋友来。那是在去年吗?或者,不是在此生此世?昨天吗?来这同一个码头向他告辞,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我还记得那个早晨也是下着雨,也是同样寒冷,我也还记得那相同的晨曦。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情也是同样沉重。
和一个伟大的朋友慢慢分开,这是何等痛苦啊!宁可一刀两断,而后将自己埋藏在孤独中。因为孤独最顺乎人之天性。然而,在那个落雨的清晨,我竟无法和我的朋友分开。(后来我领悟了其中的缘故,不过,哎,为时晚矣。)我和他一道登船,在他那间堆满行李的船舱里坐过。当他注意别的地方时,我曾仔细地打量了他很久,仿佛想把他的特征一样一样地抄录在我的心中似的:他那蓝绿色的、炯炯发光的眼睛,他那浑圆、年轻的脸庞,他那睿智、傲慢的表情,以及——最重要的——他那双高贵、指头修长的手。
当我在热切、仔细地看着他时,我一度被他发现。他转过身来,脸上现出一种用来掩饰感情的揶揄神情。他凝视着我,然后他明白了。为了冲淡这份离愁,他摆出一个嘲讽的笑容,问道:“要到什么时候?”
“你指什么?什么要到什么时候?”
“你还要舞文弄墨到什么时候呢?你为什么不和我一道去呢?在高加索那边,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同胞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让我们去拯救他们,”他笑了起来,仿佛在嘲讽自己那个高贵的计划,“或许,我们没有必要去拯救他们。你不是常这样对我说教:‘自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去拯救别人。’……那么,勇往直前吧,老夫子。你擅长说教,却为何不和我一道呢?”
我没有回答。我冥想着那块东方的圣地,诸神的老母亲,我倾听着被锁在岩石上的普罗米修斯的强烈抗议。我们的同胞也被锁在那岩石上,哀号着。我们的民族再度陷入险境。它正在向它的子孙高声乞援。我谛听着——毫无反应地——仿佛痛苦乃是一场梦,生命乃是一出感人的悲剧,在这场戏中只有粗人和傻子才会跑上舞台参加演出。
我的朋友不待我回答就起身了。船第三次鸣笛。他向我伸出他的手,然后再度以嘲笑来掩饰他的感情。
“Au revoir,书呆子!”
他的声音颤抖着。他知道,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是件丢脸的事。泪水、伤感的话、无意义的手势、普通的客套,这一切在他的眼中都是男儿不该有的脆弱。我们是这么喜欢彼此,却没有向对方说出一句热情的话来。我们像野兽般互相玩耍挠痒。他,一个聪明、爱嘲弄的文明人;我,一个野蛮人。他运用着自制力,并且在微笑间温和地将所有的感情表达出来。而我则突如其来地发出一阵不得体、野蛮的笑。
我也企图以严词厉色来伪装我的感情,可是我耻于这么做——不,不是耻于,而是不能。我紧握着他的手。我捉住它,不愿放手。他凝视着我,十分讶然。“你这么激动吗?”他说,极力想笑一下。
“是的。”我平静地答道。
“为什么?我们说什么了?我们不是好几年以前就已经同意这点了吗?那些你所喜爱的日本友人怎么说来着?不要动心!宁静,肃穆的宁静。脸孔是微笑着的、永不激动的面具,至于面具后面究竟如何,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
“是的,我们是说好了。”我答道,努力不让自己噜噜苏苏地说出一大堆话来,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控制我的声音。
船的锣响了,催促送行的人们离船。那时细雨迷蒙。空中充满了凄楚的声音:珍重再会、山盟海誓、无止无休的长吻,以及迫切的叮咛。母亲们奔向她们的子女,妻子们奔向她们的丈夫,朋友们奔向他们的朋友,仿佛他们将一去不回似的。仿佛这个生离令他们联想到死别。于是,突然间,在潮湿的空气中,锣声缥缈地从船首传到船尾,好像丧钟。
我的朋友将身子挨了过来。
“听好,”他低沉地说道,“你有没有什么预感?”
“有。”我再度回答道。
“你相信这种胡扯吗?”
“不。”我肯定地答道。
“哦?然后呢?”
根本就没有“哦”这种东西。我不相信它,可是我害怕。
我的朋友用左手轻轻摸着我的膝盖,他在失望时总是这样做。我要是催促他快做决定,他一定会反抗,会掩住耳朵并且拒绝;可最后他还是会接受,然后他会摸摸我的膝盖,仿佛在说:“好吧,看在我们交情的分儿上,我会照你的话去做……”
他的眼睛眨了两三下,然后再度注视着我。他知道我满怀忧伤,所以便迟迟不敢使出我们惯用的武器:大笑、微笑和嘲弄。
“好吧,”他说,“把你的手伸出来给我。不论什么时候,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个发现自己陷于致命的危险中……”
他突然打住,仿佛有点惭愧。像我们这种多年来一直嘲弄着形而上的“飞翔”,并且将素食者、唯灵论者、神智学者、灵的外质混成一团的人……
“怎么了?”我问道,一面猜测着。
“让我们把它当作一场游戏。”他突然说。他已经不再使用原先那种可怕的句子了。“不论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发现自己陷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就拼命去想另一个人,使对方能够立刻感应到……好吗?”他想笑,可是他的嘴唇一动也没动,仿佛冻结住了。
“好。”我说道。
我的朋友恐怕过分暴露他的感情,所以便紧接着说:
“不过,请听我说,我对于心电感应可是一点不信,还有那些……”
“放心,”我低声说道,“别去理会……”
“很好,那么,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同不同意?”
“同意。”
那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次对话了。我们默默无语,紧握着对方的手,我们的手指热情地缠在一起,然后突然松开。我头也不回地快步走开,仿佛我正在被人盯梢似的。我的心中升起了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动,想要对我的朋友投以最后的一瞥,但是我极力抑制着。“向前走!”我命令着自己,“不要回头!”
人的灵魂是沉重而笨拙的——陷在肉体的泥淖里。它的知觉更是鄙俚而粗俗。它不能清晰地预知任何事情,不能确切地预知任何事情。如果它能预知的话,这次的分别将会是何等不同啊。
天越来越亮了。这两个早晨难分彼此。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朋友可爱的容貌了。在港口的雨雾与空气中,他一动也不动,透着一丝落寞。餐厅的门开了,海在怒吼着,一个矮壮的水手走了进来,他两脚张开,长着下垂的髭。愉悦的声音响了起来:
“欢迎,列蒙尼船长!”
我隐遁到角落里,试图重新集中我的思想。然而我朋友的脸庞已经消融在雨中了。
天色更亮了。严肃而寡言的列蒙尼船长取出他的琥珀念珠,开始诵起经来。我极力强制自己不去看、不去听,而再将心神凝聚在那业已消散的影像上。当我的朋友骂我书呆子时,我是何等气愤,现在我多么希望再度生活在那个时刻中。接着我想起,我对自己所过生活的厌恶,全被这几句话一语道破。一个像我这样热爱生命的人怎么会在那些胡说八道的书堆及涂满黑字的纸张里陷溺了那么久呢!分手那天,我的朋友曾帮助我,使我看得清楚。我解脱了。既然现在我知道我的苦恼是什么,或许我能更轻易地克服它。它再也无法遁形了,它已经有名有形,我要和它战斗比较容易了。
他的表情必然一直在我的心中悄悄地活动着。我憎恨自己的身上被打上可怜人和书呆子的标签。我找寻一个借口,以放弃文墨生涯,投身于一种行动的生活。一个月前,我所期望的机会降临了,我租下一座在克里特岛海岸、面对着利比亚的废弃的褐煤矿,现在我要与单纯的工人和农人一同生活,远离书呆子那一类人。
我兴奋地准备启程,仿佛这次行程具有一种神秘的重要性。我已决定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在这以前,”我这样告诉自己,“你只看到影子,并且满足于此;现在我要引导你走向实体。”
我终于准备好了。启程前夕,当我翻找我的札记时,我偶然发现一篇尚未完成的手稿。我拿起它,注视着它,并且迟疑着。两年来,在我内心最深处,一种强烈的欲望——一颗种子一直在迅速地生长。我时时刻刻都可以感觉到,它在我的体内,摄取我的营养,日渐成熟。它生长着、蠕动着,开始踢着我身体的内壁要出来。我不再有勇气消灭它了,想做这样的精神流产,已经太迟了。
当我犹豫地拿着这份手稿,我眼前突然浮现出我朋友的笑容——一个由嘲弄和深情所组成的善意的嘲讽笑容。“我要带着它!”我说。我内心深处被刺痛了。“我要带着它,你不必笑了。”我小心翼翼地把手稿包起来,仿佛在包一个婴儿一样,然后一起带走。
列蒙尼船长低沉、粗哑的声音,声声入耳。我竖起耳朵倾听。他正谈到有关精灵的事:在狂风暴雨之中,他们攀上他的土耳其轻舟的桅杆,然后舔呀舔的。“他们身子柔软,通体黏糊糊的。”他说,“如果你抓他们一把,手就会着火。我捻了下髭须,结果我就像个魔鬼一样发出光来,亮了一整夜。后来,海水灌进我的小船,浸湿了我所载运的煤炭。当煤炭被水浸透时,小船也倾斜了,但是在那一刻,神眷顾了一切,他发出雷电,击穿了货舱口,煤炭漏了出来,掉进海里。小船减轻了负荷,船身便自动正了过来,我也得救了。就这么一回事!”
我从口袋里取出我的旅途良伴,一本袖珍本的、但丁所著的《神曲》。我点上烟斗,靠着墙壁,尽量使自己舒适。我犹疑了片刻,我究竟希望自己沉浸在哪一段诗中呢?沉浸在《地狱篇》燃烧的沥青中?或是《炼狱篇》使人净化的火焰中?或者直接进入人类希望的最高层次?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手拿着袖珍本的《神曲》,我在自由中感到欣喜。在这清晨时分,我所选择的诗篇,它的韵律节奏将会控制我一整天。
我俯身阅读,以便做出决定,我沉溺在这种热情的幻觉里,但是我并没有时间。突然,我的思路受到打扰,抬起头来,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好像有一对眼睛刺穿了我的天灵盖;我很快地回头,注视着玻璃门的方向。一种疯狂的希望闪过我的脑际:“我将再度和我的朋友见面了。”我准备看到奇迹,可是奇迹并未出现。一个陌生人,大约六十岁,很高很瘦,生着一双喜欢盯着人的眼睛,鼻子贴在玻璃上,注视着我。他腋下挟着一小包扁扁的东西。
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他那热切的目光。他的眼神带着嘲弄的味道,并且充满火焰。不管怎样,我对它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他似乎想要确定我就是他想要寻找的人——这个陌生人果决地用他的手臂把门推开,轻快而迅速地穿过桌子,走到我的面前。
“旅行?”他问,“去哪里?如果不介意我问一下的话。”
“我要去克里特岛。你为什么要问?”
“带我一道去,好吗?”
我仔细地打量着他。他的面颊凹陷,下巴结实,颧骨突出,灰发鬈曲,眼睛明亮,眼神锐利。
“为什么?我和你能做什么呢?”
他耸耸肩膀。
“为什么!为什么!”他轻蔑地大叫,“难道一个人做一件事前不能不问为什么吗?说做就做,只因为他这么做!怎么样!带我一起走吧!如果硬要说的话,就拿我当你的厨子吧!我会煮一些你听都没听过,想都没想过的汤……”
我笑了起来,他那副虚张声势的样子和尖锐的话使我觉得很开心。关于汤的话也很中听。我想,那也不赖,带着这么一个瘦骨嶙峋的家伙一道前往那偏僻而孤寂的海岸。汤以及故事……他看起来好像阅历广博,有点像水手辛巴达……我喜欢他。
“你在想什么?”他亲切地问我,摇着他那硕大的头,“你也带着一个天平,对不对?不管什么东西你都要称得精确,对不对?快点!朋友,下个决心吧!横下心来,做个决定吧!”
这个瘦癯的傻大个站在我的面前,跟他说话必须仰着头,这使我觉得很累。我合起我的但丁《神曲》。“请坐,”我对他说,“要不要来杯艾酒?”
“艾酒?”他蔑视地大叫道,“喂!侍者!来杯朗姆酒!”
他一口一口地啜饮他的朗姆酒,在嘴里含了很久,以品尝它的味道,然后才让它缓缓滑下去,温暖他的内脏。“一个肉欲主义者。”我想,“一个鉴赏家……”
“你从事什么工作?”我问。
“无所不做。用手、用脚或用脑——什么都做。如果我们择事而做,那么就会被限制了。”
“你最近的一份工作在哪里?”
“在一个矿坑。我是一个好矿工,对于金属我略知一二。我知道如何找寻矿脉,同时还会挖坑道,我进入矿坑并不害怕。我工作得不错,当工头,也没有什么不满的事情。但是魔鬼插手进来,上星期六晚上,只因为我想这么做,我突然发作起来,那天,老板在视察那个地方,我一把抓住他,揍了他一顿。”“但是为什么呢?他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
“对我吗?一点也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可怜的家伙,他甚至还请我们抽烟呢!”
“哦?”
“噢,你只是坐在那儿问问题!事实上,我只是突然间发作起来而已,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有没有听过磨坊主人妻子的故事?那么,你总不会期望从她的背上学习拼字吧!对不对?磨坊主人妻子的背,人的理智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读过不少关于人类理性的定义的书,这一个似乎是所有定义中最令我震惊的,而我喜欢它。我带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我的新伙伴。他满脸皱纹,饱尝风霜,像是被虫蛀过的木材。几年之后,另一张脸孔给了我同样的印象:那就是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
“你那个包里装的是什么?食物?衣服?或是工具?”
我的伙伴耸耸肩,笑了起来。
“你看起来是相当敏感的那种人。”他说,“冒昧了。”他用他结实而修长的手指抚摸着他的包袱。
“不,”他补充道,“这是一把桑图尔琴。”
“桑图尔琴?你会弹桑图尔琴吗?”
“当我手头紧的时候,我到各个酒店里去,弹桑图尔琴。我唱老希腊游击队员唱的、源自马其顿的调子。然后我拿着帽子绕一圈——就是这顶扁帽——它便装满了钱。”
“你叫什么名字?”
“亚历克西斯·左巴。有时候人家叫我面包师的勺子,因为我这么瘦长,同时我的头又扁平得像一个烧饼,此外我还被人叫做‘打发时间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沿街叫卖炒南瓜子。他们也叫我‘阿霉’,因为他们说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耍花招,什么事情都会变糟。我还有其他的绰号,但是这些绰号我暂时不用了……”
“你是怎么学会弹奏桑图尔琴的?”
“当时我二十岁。我在我们村庄——就在奥林波斯山的山脚下——的一次喜宴上第一次听到桑图尔琴。我屏息倾听,三天吃不下饭。‘你有什么不对劲吗?’我爸爸问我——愿他的灵魂安眠于九泉之下。‘我要去学桑图尔琴!’‘你自己不觉得可耻吗?你愿意做一个吉卜赛人吗?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成为一个乱弹乱唱的人?’‘我要去学桑图尔琴!’我为了结婚存了一点钱。那是一种小孩子的想法,但是那时我还没有成熟,我的血是热的。我想要结婚,可怜的白痴!我除了耗尽我所有的储蓄外,另外还花了许多钱,买了一架桑图尔琴——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把。我带着它离开我的家乡,前往塞萨洛尼基,并且紧跟着一个土耳其人,瑞特赛普·埃芬迪——他教每个人弹桑图尔琴。我拜倒在他的脚下。‘你想要干什么?’他说。‘我想学桑图尔琴!’‘没问题,但是你为什么拜倒在我的脚下?’‘因为我无法付钱给你!’‘你真的对桑图尔琴如此着迷,是不是?’‘是的。’‘好吧,我的孩子,你可以留下来,我不要你付钱!’我留在那里一年,跟他学琴。我想他现在也许已经去世了,愿神接纳他的遗骸!假如神让狗进入神的乐园,愿他也打开大门让瑞特赛普·埃芬迪进去。自从我学会弹奏桑图尔琴,我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当我沮丧或一文不名时,我弹奏桑图尔琴,它使我开心起来。当我在弹奏的时候,你可以对我说话,但是我一句也听不到,即使我听到了,我也没办法讲话。我试过了,没有用,我没有办法说话!”
“可是为什么呢,左巴?”
“啊!你不明白吗?一种强烈的感情,这就是原因所在!”
门开了。海的声音再度刺穿了咖啡馆。我们的手脚都很冰冷。我更进一步地缩到我的角落里,并且用外套紧紧裹住自己,我品尝着这一刻的极乐。
“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想,“我在这里很好,愿这一分钟持续好几年。”
我打量着面前这个奇特的人。他的目光集中在我的身上。这对眼睛圆而小,瞳孔颜色非常深,眼白上带着血丝。我觉得它们正贪婪地刺穿我、探索我。“哦!”我说,“继续说下去。”
左巴又耸耸他那瘦骨嶙峋的肩膀。
“不要再谈它了。”他说,“给我一根香烟好吗?”
我给了他一根。他从口袋里取出火石和灯芯来点烟。他满足地眯着眼睛。
“结婚了没有?”
“我是人,不是吗?”他愤怒地说,“是人就意味着眼瞎。我和走在我前面的人一头栽进一样的壕沟里。我结婚了。我走上了下坡路。我成了一家之主,我盖了一间屋子,我有了孩子——麻烦。但是感谢神,我还有桑图尔琴!”
“你靠着弹琴来忘却烦恼,是不是?”
“哎!我看得出来你不会弹奏任何乐器。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住在一间什么都要你操心的屋子里。妻子,儿女。我们要吃些什么?我们要如何赚钱买衣服?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妈的!不,要弹好桑图尔琴,你必须举止端庄,你必须心无旁骛。假如我妻子太多嘴,我怎么会有心情弹奏桑图尔琴呢?如果你的孩子肚子饿了哇哇叫,你弹弹看吧!弹奏桑图尔琴,必须抛开一切,你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左巴是我一直在找寻,却始终没有找到的人——一颗朝气蓬勃的心,一张贪吃的大嘴,一个尚未与大地割裂的、野性未驯的巨大灵魂。
艺术、爱、纯洁、热情,这些字的意义都从这个工人口中说出来,他用人类最简单的语言使我顿悟。
我打量着他那双既能握十字镐,又能弹桑图尔琴的手。他的手因工作而生茧、龟裂、变形,而且肌肉发达。他的双手非常温柔而小心地解开包袱,拿出一把被岁月摩擦得闪闪发亮的旧桑图尔琴。它有很多根弦,还饰有黄铜、象牙以及红色的丝穗。他那粗大的指头缓缓地、热情地抚摸着它全身,仿佛在抚摸一个女人,然后他又把琴包起来,仿佛在为心爱的人穿衣,生怕她着凉似的。
“这便是我的桑图尔琴!”他喃喃道,一面把包袱小心地放在椅子上。
这时水手们碰杯狂欢,并且爆出阵阵的笑声,熟练的老水手热情地在列蒙尼船长的背上拍了几下。
“你恐惧得要死,船长,你说对不对?天晓得你已经在圣尼古拉斯前面点过多少许愿蜡烛了!”
船长的两道浓眉皱在一起。
“不,我可以跟你发誓,当我看到死亡的天使站在我面前时,我并没有想到圣母,也没有想到圣尼古拉斯!我只是掉头驶向萨拉米斯,我想着我的太太,于是我叫道:‘啊!凯瑟琳娜,此刻我多么希望和你躺在床上!’”
水手们再度爆笑起来,列蒙尼船长也跟着大笑。
“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动物呢?”他说,“天使拿着剑在他的头顶上,可是他的心思却摆在那儿,在那里,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他妈的!”
他拍拍手,然后喊道:“敬大伙儿!”
左巴用他的大耳朵仔细听,他转过身,先注视着水手们,然后注视着我。
“‘那儿’是什么地方?”他问,“那些家伙在谈些什么呢?”
他突然懂了,并且吃了一惊。
“好极了,朋友!”他赞赏地喊道,“那些水手知道奥秘,大概是因为他们日日夜夜都在跟死亡搏斗。”
他在空中挥舞着他的大拳头。
“好了!”他说,“那是另一回事。让我们言归正传。我会留下来,还是走?做个决定吧!”
“左巴,”我说,并且必须勉强克制自己不投入他的怀抱中,“没有问题!你和我一起走,我在克里特岛有一座褐煤矿,你可以管理工人。晚上,我们可以仰卧在沙滩上——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妻子,没有儿女,也没有狗——我们将同吃同喝,那时你要弹奏桑图尔琴!”
“要是我心情好的话,你听到了吗?假如我心情不错,我将照你所吩咐的一切为你工作,在那儿,我是你的人,可是说到桑图尔琴,那就不同了。它是只野生的动物,它需要自由。假如我心情不错,我会弹奏,甚至还会唱歌,同时我也会跳赛贝奇科、哈萨皮克和潘特扎里三种舞——但是,我一开始就要坦白地告诉你,必须在我心情好的时候。让我们先把话说清楚一点,如果你逼我弹,那将会一塌糊涂。至于那些事,你必须了解,我是一个人。”
“一个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噢!自由!”
我叫了另一杯朗姆酒。
“来两杯,”左巴喊道,“你也来一杯,我们才可以举杯祝贺。艾酒和朗姆酒不很相称,你也要喝朗姆酒,这样,我们的感情才会长久。”
我们碰了一下我们的小酒杯。现在天已大亮了,船的号笛响着。脚夫把我的行李送到船上,对我打了个手势。
“愿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上船时我说,“我们走吧!”
“神和魔鬼!”左巴平静地补充道。
他弯下身,将桑图尔琴挟在腋下,打开门,率先走了出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