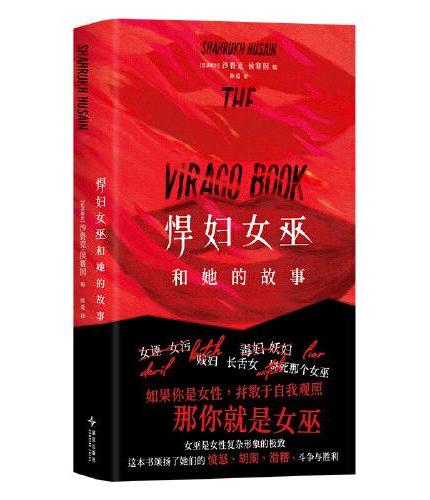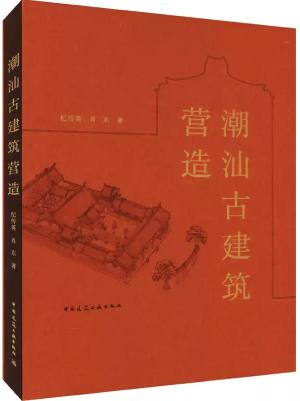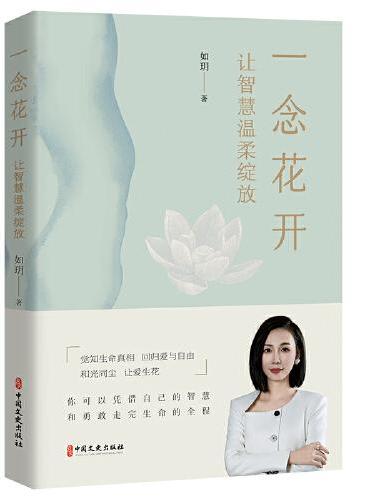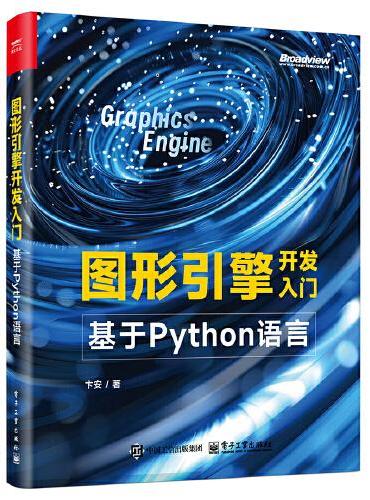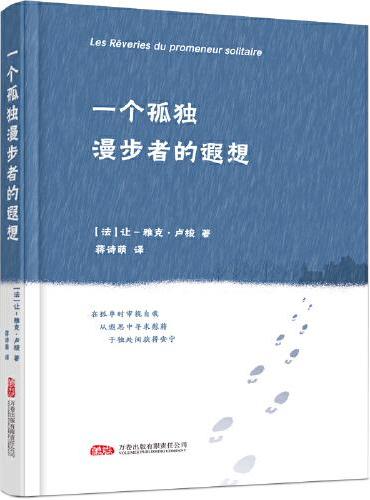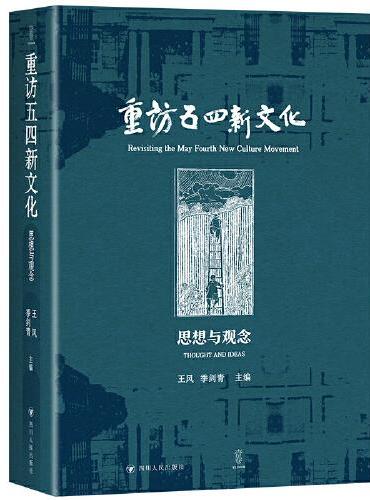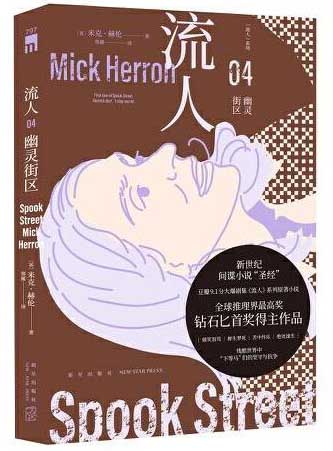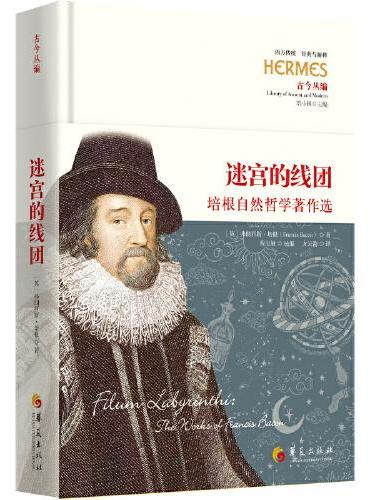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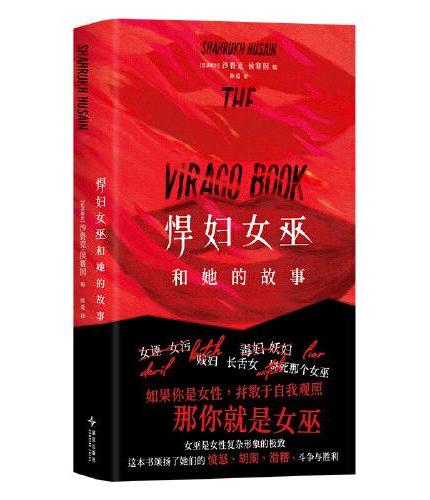
《
悍妇女巫和她的故事(第一本以女巫为主角的故事集!)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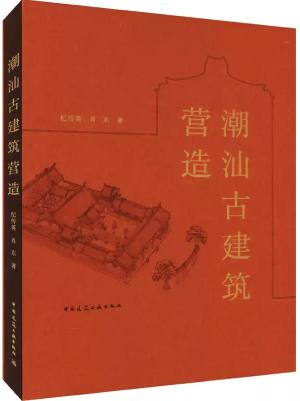
《
潮汕古建筑营造
》
售價:NT$
12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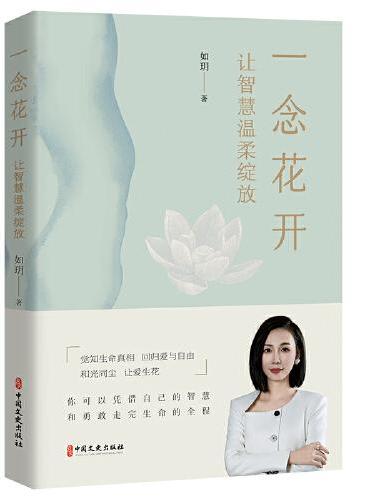
《
一念花开:让智慧温柔绽放
》
售價:NT$
2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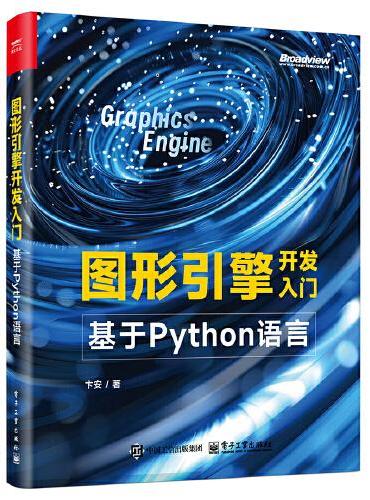
《
图形引擎开发入门:基于Python语言
》
售價:NT$
7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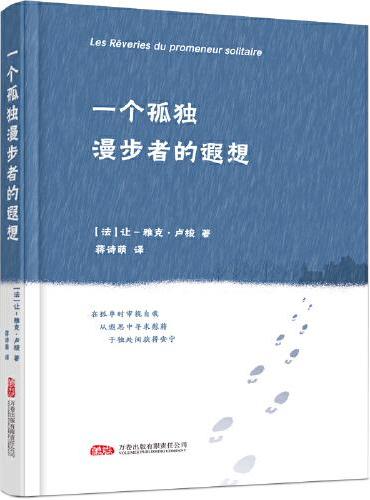
《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
售價:NT$
1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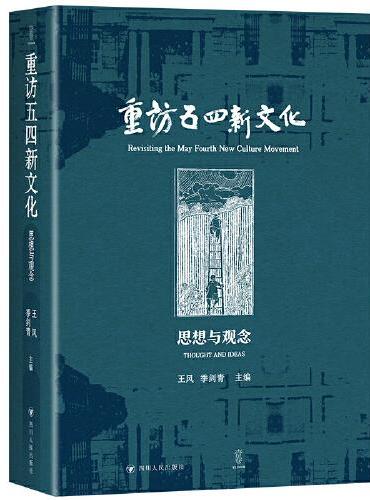
《
重访五四新文化:思想与观念(跟随杰出学者的脚步,走进五四思想的丰富世界)
》
售價:NT$
4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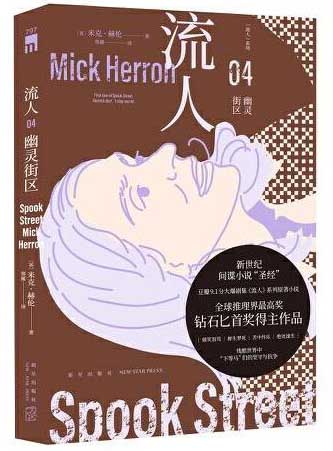
《
流人系列04:幽灵街区 午夜文库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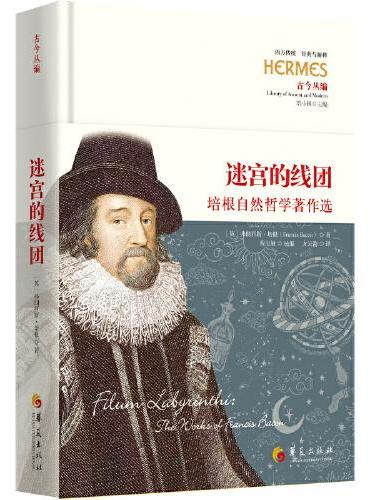
《
迷宫的线团:培根自然哲学著作选
》
售價:NT$
403.0
|
| 編輯推薦: |
★ 2017年美国现象级小说,大胆预言美国的第二次南北战争。
★ 从一鸣惊人到口碑爆棚,出版不到1年,全球36个版本,Goodreads、亚马逊好评近20000条。
★ 《纽约时报》年度瞩目好书,亚马逊年度选书,Goodreads年度票选好书;《华盛顿邮报》《卫报》《波士顿环球报》《娱乐周刊》《奥普拉杂志》年度畅销书;《出版人周刊》、《书单》星级评论推荐。
★ 普利策评论奖得主角谷美智子盛赞:震撼!就像科马克麦卡锡在《路》(The Road)中搭建的末日世界一部将战争报道和反乌托邦题材巧妙结合的佳作。
《纽约时报》:未来启示录也好,影射过去和现实的寓言也好,或者战争心理的研究材料也罢,无论你把它当作什么题材来读,《无人幸免》都是一本叫人深感不安的小说。
|
| 內容簡介: |
2074年,美国。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海水倒灌,城市内迁,人们抬头看见战斗机的情况像曾经遇见飞鸟一样稀松平常。这一年,历史重演,南北开战。此时,萨拉特6岁,父亲死后,他们举家逃离,从南到北,被迫落脚佩兴斯难民营。在这里,十年弹指一瞬,生死别离接踵而至:12岁,母亲死于屠杀,17岁,姐姐死于轰炸,哥哥下落不明,*后是她自己,与过去再见,为战争所用。
战争的创痛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它以相同的方式改变人,摧毁人,把人变得同样胆怯、愤怒,复仇心切,投入不可预料的未来
|
| 關於作者: |
奥马尔阿卡德Omar El Akkad
战地记者,小说家。1982年出生于埃及开罗,卡塔尔的多哈长大,16岁移居加拿大。大学毕业之后在《环球邮报》担任记者十年,报道过无数重大的国家新闻事件。现在,奥马尔和他的妻女一同生活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
|
| 內容試閱:
|
小时候,我喜欢搜集明信片。在孤儿院时,我把它们装进一只鞋盒,藏在床底下。后来,我搬进了来新安克雷奇 后的第一个家,在我那间摇摇欲坠的工具棚里有只旧油桶,我就把这只鞋盒存放在桶底。我大半辈子都在研究战争史,搜集这世界静谧而理想化的浮光掠影,帮我找到了某种平衡。
有时候,我也想把那只旧油桶扔掉算了,又怕别人譬如大学里的某个同事看见了,把它当作一种意气用事的政治表态,就像在曾属于红区的地方,住宅门前偶尔还会出现铜头蛇旗 和开膛破肚的肌肉车都不过是些苍白无力的反叛徽章,昭示着那段被摧毁、也摧毁一切的过去。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南方人出身。尽管我六岁就到了中立区,也从没与人谈起过此前的生活,但不排除我那帮同事中仍有人暗地里相信,我的血液中还残留着一丝反抗军的红色。
我最喜欢的明信片,出自21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那之后,这个世界就开始跟这个国家作对,而这个国家则开始跟自己作对。在明信片上,海岸边宽阔的沙滩尚未被高涨的海水吞噬;西南部的景致尚未化为灰烬;蓝天下的中西部平原依然辽远空旷,尚未挤满内迁运动中迁来的沿海流民。这些图景,记录了美国21世纪前叶的面貌:如日中天,繁荣兴盛,对危机浑然不觉。
我还记得自己买的第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一张安克雷奇老城的照片。画面上,城市海滨覆着皑皑新雪,海面上点缀着层层浮冰,山峦背后落日低垂。
六岁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阿拉斯加落日。当时,我,一个晒坏了的佐治亚男孩、一个难民,正站在走私船的甲板上。我还记得自己的睫毛上挂满了奇怪的白色碎屑,牙齿不由自主地打战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觉得冷。看到靠近山巅的天空中,高悬着一枚封冻的蛋黄,我还以为自己来到了人世的尽头,生息的尽头。
我们这代人,被称为不可思议的一代:都出生在2074年爆发、2095年结束的第二次美国内战期间。有人更进一步,把战后十年瘟疫期间出生的人也囊括了进来。长久以来,这个国家都有一个传统,总爱用几乎将一代人赶尽杀绝的动荡来为那些人命名,对我们这代人也不例外。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逃过了人弹的愤怒和鸟的蹂躏,又藏在塞满食物的地窖或避风窖里,躲过了横扫内陆的再统一瘟疫。我们为数不多,侥幸而已。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我们国家这场血腥的战争,为此我写过学术论文和杂志文章,还主导过不计其数的研讨会和工作会议。我研习过所有留存下来的文献,包括国会报告、口述历史,以及瘟疫幸存者令人心碎的证词。我还原了再统一日当天那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事件在反抗军所剩无几的旧部中,有一人潜入合众国首府,释放出一种病毒,将整个国家拖入了死亡的十年。据估计,战争期间的死亡人数达1100万,而战后死于瘟疫的人数则接近这个数字的十倍。
我收到的读者来信数不胜数,他们总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史实上与我纠缠例如某次自杀式爆炸是否真该算在反抗军头上,这场或那场屠杀是否确如南方宣传的那样恶劣,等等。我保留了成百上千封这样的信件,它们看似各抒己见,但实际上都秉持同一个论调:作为一个娇生惯养的新安克雷奇北方人、一个从未亲历过厮杀的中立区精英,我根本就不懂这场战争。
但我却知道战争中许多不为人知的事。都是她告诉我的。
我因知情而卷入其中。
如今,我已时日无多,于是,开始审视早年积攒的物什。
不久前,我找到了自己买的第一张明信片。上面那张照片的拍摄时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画面上的一切,除了山峦与大海,其他的都已不复存在。新安克雷奇原本是铺展在山脚下的一片郊区,建筑低矮,人口富足,这些年来,它向内陆迁移了不少。那个我当年作为一个晕头转向的战争遗孤登陆的港口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抬高和加固。过去码头上那些拴绳结的木桩,都换成了便于迅速移动和拆卸的组装平台。毕竟,猛烈的风暴说来就来。
有时候,我会沿着新安克雷奇的海滨漫步,一直走过码头和港口。如今,要是不租清道船的话,这就是我离自己最初登陆中立区的地点最近的位置了。我的医生说,经常散步对我有好处,在不引发病痛的前提下,我应该尽量多走走。我怀疑他对所有的临终病人都会说这句鸡肋的话,而这些人对有好处没坏处之类的说法早已麻木。
行将就木的感觉有些古怪。我一生都以为自己会死于非命,要么染上传入北方中立区的瘟疫,要么死于因红区再度掀起的叛乱,或者因这场叛乱而发生的手足相残。然而恰恰相反,我注定要以最平淡无奇的方式死去,死于大面积的细胞失灵。我曾读到过,患上一种病程适中的癌症,说实在的,要算一种体面的死法了患者既不必忍受长达数年的病痛,又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必要的安排、说完该说的话。
已经很多年没有下雪了,不过到了一月末,细碎的冰霜就会不时地爬上窗棂。每逢那样的日子,我总爱到海边去,看自己的气息凝结在空气中。那一刻,我感到心中了无牵挂,不再害怕。
我站在滨海板道边缘,望着海水,想着它带走的一切,还有它从我手中夺走的一切。有时,我会一连几小时盯着海面,直到夜色渐浓,直到我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时空,回到那个满目疮痍的红色国度我出生的地方。
这时,我就又见到了她,看着她从水面上升起。她依然是我记忆中模样,古铜色的身躯高大魁梧,背上布满了灰白的伤痕,每一道都意味着她经受的一次折磨、她遭遇的一次隐秘的暴行。她越升越高,宛如血肉筑就的磐石,在萨凡纳河洞开的肚腹中重生。
而我又变回了一个孩子,尚未与父母分离、尚未失去家园、尚未遭到背叛。
我又回家了,回到了河边,幸福快乐,依然爱她。
我的秘密,就是我依然爱她。
这个故事讲述的,不是战争,而是毁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