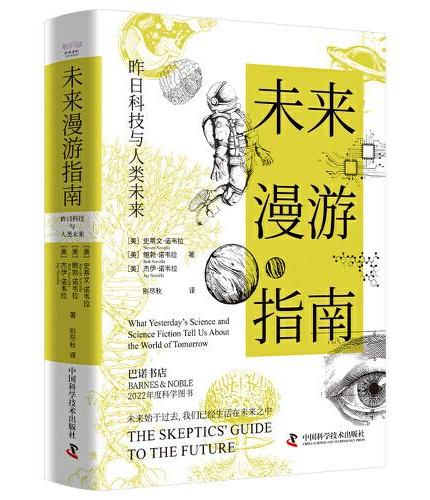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新能源材料
》
售價:NT$
290.0

《
传统文化有意思:古代发明了不起
》
售價:NT$
199.0

《
无法从容的人生:路遥传
》
售價:NT$
340.0

《
亚述: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的兴衰
》
售價:NT$
490.0

《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采煤机智能制造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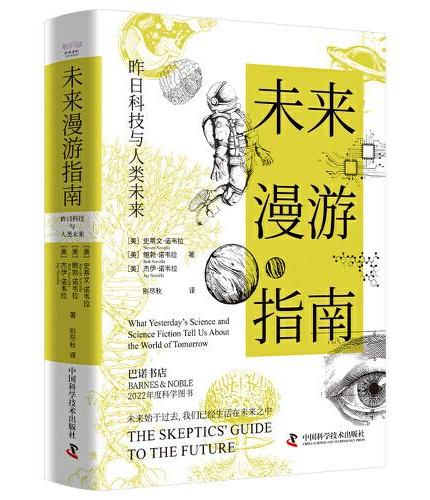
《
未来漫游指南:昨日科技与人类未来
》
售價:NT$
445.0

《
新民说·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上下册)
》
售價:NT$
790.0

《
我从何来:自我的心理学探问
》
售價:NT$
545.0
|
| 編輯推薦: |
三个人,三个女人,她们生长于田野,她们都梦想远方。
这三个女人属于过去时代,那个时代塑造了她们的命运;但她们又属于现在和未来,因为她们来自中国经验中*令人伤痛、*宿命意味的深处在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之间、在历史和生活之间,个人何以成立?她(他)的自由、她(他)的道德责任何以成立?
李敬泽,批评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从《玉米》中的玉米和玉秀两位姑娘身上,我也看到了我村上邻居姑娘的影子。每个农村姑娘都有一个嫁给自己梦寐以求男人和更好家庭的梦想,但大部分农村姑娘*后都梦想破灭读《玉米》,我有点读出《红楼梦》的感觉,如桃花般鲜艳的女性生命,从盛开到飘零,从干净如露到浸染如墨,最终如烟如土消融在凡俗的人间。
俞敏洪,企业家、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
|
| 內容簡介: |
玉米的人生分为两部分,结婚前和结婚后。
结婚前的玉米是傲气的,充满炙热能量的,哪怕和她写信的人远隔千里之外,人们也能感受到那些白纸黑字里汹涌澎湃的爱情。
结婚后的玉米是低微的,委曲求全的,她的身后拴着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她的姊妹,权力的欲望浸蚀人心,消耗飒爽。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源于那个稻草飘香的夜晚,玉米、玉秀、玉秧,王家庄里的三个姐妹的人生从这里发生了突变。
这是三个中国大地上*为普通的女人,她们忠于爱、失去爱、痛恨爱。
这是三个逃离他人目光审视的故事,她们挣扎、破灭、沉溺。
有多少时刻,我们向往一个没有窥探的世界?
有多少时刻,我们渴望一个没有束缚的自己?
|
| 關於作者: |
毕飞宇,1964年1月生于江苏兴化,现为南京大学教授。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文学讲稿《小说课》。
《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玉米》英文版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平原》获法国《世界报》文学奖,《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
| 目錄:
|
序(李敬泽)
第一部 玉米
第二部 玉秀
第三部 玉秧
后记一
后记二
|
| 內容試閱:
|
【序(李敬泽)】
2001年4月,毕飞宇发表了《玉米》。从那时起,在文学界,人们频繁地提起玉米:看玉米了吗?你觉得玉米怎么样?局外人听来,好像人人家里种着一片地,地里长着玉米。
十几年前,莫言写出了《红高粱》,因为这题目和这小说,高粱这种贫贱的作物焕发出神奇的光芒,从此,提起这个词,我们会想起刺目的血、妖冶的绿,想起丰饶而残忍的大地。
汉语之美、汉语之深厚和微妙,就在这一个一个的词,它被念出来,然后余音不绝,因为诗人和小说家们把层层叠叠的经验、梦想和激情写进了这个词里。
玉米也是贫贱的作物,在北方和南方,在平原和山地,玉米构成了乡土中国的基本景观,它太普通,太常见,提起玉米也许只会引出某种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忆:它曾是我们童年时代的主要食物。但毕飞宇把这个词给了一个女人,他让玉米有了身体,美好的、但伤痕累累的身体,他还写了玉秀和玉秧,那是将要成熟的玉米和正在成长的玉米,从此,在玉米这个词里、在玉米的汁液中就流动着三个女人的眼泪和血和星光般的梦。
《玉米》、《玉秀》、《玉秧》,毕飞宇是一篇一篇写的,我估计,他原本只是想写《玉米》,最后形成这样一本书可能并非他的初衷。但也许就在写《玉米》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玉秀和玉秧,这两个女孩子站在玉米身后,被光彩夺目的姐姐遮蔽着,毕飞宇察觉到她们身上存在着某种可能性小说中的人和生活中的人一样,每个足够活跃的灵魂都有一种冲动:要展开自己的故事,要从别人的故事里冲出去,开辟自己的天地。
小说家如同专制的家长或严谨的导演,他必须镇压和消除这种自由主义苗头,必须让人物各就其位。所以,在《玉米》中,毕飞宇没有向玉秀和玉秧让步。但是,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有一个决定性的特点,那就是他对人、对人的性格和命运有不可遏止的好奇,当他意识到那两个女孩在阴影中暗自酝酿着激情,跃跃欲动时,他终究无法拒绝她们,他必须提供机会让她们动,让生命自行其是。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它由三个相互联系的故事构成,由三个不同性格和命运的女人构成,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具有统一、强制、封闭性的结构意志的长篇小说,它更像是一次追逐:小说家被人的自由、人的魅力所引导,欲罢不能地追下去。
所以在这本名为《玉米》的书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人,令人难忘的人。姐姐玉米是宽阔的,她像鹰,她是王者,她属于白天,她的体内有浩浩荡荡的长风;而玉秀和玉秧属于夜晚,秘密的、暧昧的、交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夜晚,玉秀如妖精,闪烁、荡漾,这火红的狐狸在月光中灵俐地寻觅、奔逃;玉秧平庸,但正是这种平庸吸引了毕飞宇,他在玉秧充满体积感的迟钝、笨重中看出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觉。
三个人,三个女人,她们生长于田野,她们都梦想远方。但通向远方的路崎岖、艰险,三姐妹中玉秧走得最远,她的所到之处却是幽暗、逼仄的洞穴;在她们脚下和心中横亘着铁一般的生存极限,她们焦渴、破碎于干旱坚硬之地。
通过对极限的探测,毕飞宇广博地处理了诸如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所有这些主题如同血管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运行。对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上世纪70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
所以,这三个女人属于过去时代,那个时代塑造了她们的命运;但她们又属于现在和未来,因为她们来自中国经验中最令人伤痛、最具宿命意味的深处在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之间、在历史和生活之间,个人何以成立?她他的自由、她他的道德责任何以成立?我们从《玉米》中、从那激越的挣扎和惨烈的幻灭中看到了人的困难,看到人在重压下的可能,看到人的勇气、悲怆和尊严。
《玉米》的另一个可能的名字也许应该是《三姐妹》,这个和《玉米》一样朴素的名字让我想起契诃夫,想起他对俄罗斯大地上那三个女人的深情守望。
是的,守望,守和望,守着人、望着命运,这是作家的古老姿态,毕飞宇把这种姿态视为写作的根本意义所在
我想起2001年初,毕飞宇在电话里没完没了地对我谈起玉米,这个词和这个女人,他不可自拔地沉溺其中,他爱她,她将因此而荣耀
再往前二十年或三十年,在江苏北部的乡村,一个瘦的、黝黑的孩子,他注视着无边无际的田野,泪水涌上他惊喜的眼睛,我听到他说:玉米。
【后记】
一
一九九九年,我写完了《青衣》,在随后的十多个月里头,我几乎没有动笔。我一直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我不知道。这句话听上去有些可疑,但是,我的等待是真实而漫长的。一个有风有雨的下午,我一个人枯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百般无聊中,我打开了电视,臧天朔正在电视机里唱歌。他唱道:如果你想身体好,就要多吃老玉米。奇迹就在臧天朔的歌声中发生了,我苦苦等待的那个人突然出现了,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的名字叫玉米。我再也没有料到,一个乡村的女子会以摇滚的方式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开始骚动,但并不致命。
我爱玉米吗?我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怕她。我不止一次地设想过,如果玉米是我的母亲、妻子或女儿,这麼说吧,如果玉米是我的邻居或办公室的同事,我将如何和她一起度过漫长的岁月呢?这个虚空的假设让我心慌。我对玉米一定是礼貌的、客气的、得体的,但我绝对不会对玉米说,你围巾的顏色不大对、你该减肥了。我感觉到了我们在气质上的抵触。我尊重她,我们所有的人都尊重这位女同志,问题恰恰出在这裡。我们之间有一种潜在的战争,这场战争永远不会发生,然而,战争的预备消耗了我,我感受到了我自己的紧张,因為我感受到了玉米的紧张。
在〈玉米〉开始后不久,我就认识玉秀了。这让我多少松了一口气。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玉秀的那双手。玉秀的手真是太漂亮了,和她乡下姑娘的身分全不相符。我在许多画家和戏剧演员的身上看到过这双手。这双手洋溢着异样的气质,好动,时常会自言自语,有无限的表现力,内心的纵深与秘密全在指头上头了。我在〈玉秀〉裡头几乎没有涉及过玉秀的那双手,她的那双手太调皮了,正「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可是玉秀和我一起疏忽了,生活不只有被「蒙着」的眼睛,也还有一双手。当玉秀明白那双手是多麼地有力时,她已经倒下了。
玉秧是谁?这个问题依然缠绕着我。玉秧属于这样的一种人:我们天天见面,她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我相信她是简单的、平庸的。后来,玉秧这个人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有一天,我们在闲聊中提起了玉秧,或者说,有一天远方传来了关於玉秧的消息,所有的人都大吃了一惊──那是玉秧吗?是的,那偏偏是玉秧。这时候我们猛然发现,我们所有的人都被玉秧骗了。玉秧不是骗子,她并没有骗我们。但是,我们被她骗了。因為不可更改的生活环节──不是细节,是环节,我们被玉秧骗了。我们生活得过于粗疏、过于肤浅,我们与真相日复一日地擦肩而过。回头一瞥,再大吃一惊,成了生活赐予我们最后的补充。
对我来说,玉米、玉秀,还有玉秧,她们是血缘相关的三个独立的女子,同时,又是我的三个问题。我描绘她们,无非是企图「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亨利''米勒)。然而,我没有解决问题。这是我的目光至今都没有学会慈祥的根本缘由。我还想再一次引用亨利''米勒的话:「不要坐在那里祈祷这种事情的发生!只是坐着观察它的发生。」我想,我能做到的,也许只有坐着,睁着我的三角眼。
我没有想到臧天朔的一首歌能為我带来三位神祕的客人,因為她们,我度过了十五个月的美妙时光。我感谢臧天朔。
二
有一个问题我不能不有所提及,那就是这本书的叙述人称。
我坚持认為这本书采用的是「第二」人称。但是,这个「第二」人称却不是「第二人称」。简单地说,是「第一」与「第三」的平均值,换言之,是「我」与「他」的平均值。人称决定了叙述的语气、叙述的距离、叙述介入的程度,叙述隐含的判断、叙述所伴随的情感。这不是一句可有可无的话。我想强调的是,〈玉米〉、〈玉秀〉和〈玉秧〉当然都是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的,然而,第一人称,也就是说,「我」,一直在场,一天都没有离开。至少,在我的创作心态上,确实是这样。
关于人称,我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看法:第一人称多少有点神经质,撒娇、草率、边走边唱,见到风就是雨;第二人称锋芒毕露、凌厉,有些得寸进尺;第三人称则隔岸观火,有点没心没肺的样子。这些都是人称给叙述所带来的局限。事实上,叙述本身就是一次局限。我在乡村的时候遇到过许多冤屈的大妈:爱用第一人称的基本上都是抒情的天才、控诉的高手,一上来就把她们的冤屈变成了吼叫、眼泪和就地打滚;而爱用第二人称的泼妇居多,她们步步為营,一步一个脚印,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选择第三人称的差不多都是满脸皱纹的薛宝釵,她们手执纺线砣,心不在焉地说:「她呀,她这个人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当我回想起她们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艺术上的问题,或者说,人称上的问题,什麼样的叙述人称最能够深入人心?这就提醒我想起了另一位大妈。她不吼叫、不淌眼泪、不打滚、不挺手指头,只是站在大路旁,掀起她的上衣,她把她腹部的伤疤袒露在路人的面前,完全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在我看来她的惊人举动里有人称的分离,仿佛是有一个「我」在说「她」的事,或者说,有一个「她」在说「我」的事。我至今记得那位大妈裸露的腹部,可以说历历在目,比二十一世纪另类少女完美的肚脐眼更令我心潮涌动。这正是「第二」人称的力量。
三
我一直认為所有的艺术都存在一个「速度」的问题,即使是瞬间艺术绘画或者雕塑。小说裡的「速度」问题则尤為重要。小说是一个流程,有它的节奏,选择什麼样的速度对一部作品来说一点也马虎不得。小说的速度起码有两种,一,结构性的速度,事态自身「发展」的速度;第二,语言性的速度,也就是说,你叙述的速度。我发现许许多多的作品在语言的速度感上是不讲究的,读者就如同坐在一辆汽车上,驾驶员是一个冒失鬼,虽然他的绝对速度并不快,但他在忙,而你在慌。
中国作家里头叙述速度最快的也许是王蒙和莫言,他们是作家里的F1车手,是舒马赫或哈基宁。他们的语言风驰电掣,迅雷不及掩耳,所以他们的作品你最好是吃饱了再去看,否则你撑不住。而语言速度上最有控制力的则可能是王安忆和苏童,读他们的作品就好像在和他们拔河,一点一点地、一点一点地,你就被他拽过去了。读他们的作品,你永远是一个饿汉。
快和慢不存在好和坏,我只能说,快有快的魅力,慢有慢的气度。这本书我选择了什麼样的叙述速度呢?我把速度问题先放在了一边。这本书我力求让我的读者到「王家庄」去看一看,看清楚,把所有的角落都看清楚。这样一来,我只能让「马儿哎你慢点走」。我的叙述用的是骑驴看唱本的速度,或者,我乾脆用的就是步行的速度。这是很原始的。这样的速度傻巴拉叽。然而,对于一个一心要让游客「看清楚」的导游来说,我只能放弃「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四
我还想在这裡谈一谈所谓的「写法」。小说当然会有它的「写法」,〈玉米〉、〈玉秀〉和〈玉秧〉也有它的「写法」,这一点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这个该死的「写法」会让我们这些被称作「作家」的家伙们伤透脑筋。因為「写法」的差异,文学变得无比地热闹,有了「新」和「旧」的区别,乃至於,有了「新」和「旧」的对抗。其实,我更愿意把「新」和「旧」的区别和对抗放在一边,尊重和认同「写法」的变迁。「变迁」这个说法轻而易举地避开了一个无聊的逻辑,无聊的逻辑是这样下结论的:「新的就是好的,有生命力的;旧的就是坏的,快断气了。」
文学无语。但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时常会对着无聊的逻辑流露出含蓄的微笑。这种含蓄难免会带有讥讽的意味。阅读告诉我们,在更多的时候,文学总是在逼近了生活质地、逼近了生活祕密、逼近了生活理想的时候,绽放出开怀的笑声。如果我们勇敢,我们一定会在「变迁」面前沉著一些,而不会争新恐旧。争新恐旧是文学的性格之一,所以,总体上说,文学有点癲疯。
「写法」是折磨人的,在你做出选择的要紧关头,你不得不像一次脱胎换骨的探险。有时候,你在遥不可及的前沿;有时候,就在你最初出发的地方,在路口。
当一个人被折磨得伤了神的时候,他也许就不再犹豫,反而会加倍地坚定。比如说,刚开始,我曾经想把这本书写得洋气一些、现代一些。写著写著觉得不行,不是那麼回事。我就问我自己,到底什麼是「写法」?我对自己说:你觉得怎麼写「通」,什麼就是你的「写法」。文学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亲切起来的,最终成了朋友。我再也不会相信脱离了具体作品之外的、格式化的「写法」。「写法」还能是什麼?就是我愿意带上这样的表情和朋友说话。
五
在我写〈玉秧〉的时候,我曾经和一位朋友有过一次有意思的谈话。我们聊起了青春期,聊起了紧迫感。我说,我对青春期并没有特殊的怀念;我对我的朋友说,我对现有的年纪非常满意。朋友有些诧异,十分婉惜地望着我,对我说,飞宇,你老了,──你搞创作,為什麼不能保持二十岁的心态呢?老是很可怕的。
我问他,可怕吗?
我从来不认為时光的飞逝有什麼可怕。我对我的朋友说,如果我永远十八岁,那麼,我三十八岁的作品谁替我写?我六十八岁的作品又是谁替我写?我的「青春期书写」已经完成了,假如我的作品永远呈现的都是「二十岁的心态」,我会对我表示出最深切的失望。谢天谢地,我已经三十八岁了,我很满意我可以写出三十八岁的东西了。将来我六十八岁了,我还渴望我能够写出六十八岁的东西。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能够完整无缺地展示他的一生,我认為,那才是一个艺术家最大的幸运。
我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作為一个写作者,我没有任何的抱怨,相反,我感谢时光。时光会使我们一天又一天地老去,但时光同样会使我们一天一天地丰富起来、睿智起来。时光有她绝情的一面,然而谁也不能否认,时光也有她仁慈的一面。比方说,在我们的内心,时光总能留下一些东西。有时候,时光可以超越你的智商、气质、意志、趣味,使你变得像目光一样透明。我坚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天才,如果有,那一定和时光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繫,我们原本没有的东西,时光会有所选择地赋予我们。
我不敢说《玉米》这本书有多麼的出色,可是我可以负责地说,这本书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是写不出来的。尽管我二十岁的时候自视甚高,比现在还要自负。
【书摘】
相关的细节还是事后回忆起来的。王连方拿起了《红旗》杂志,开始回忆,后怕了。那是中午,他怎么突然起了这份心的?一点过渡都没有。女会计大他十多岁,长他一个辈分,该喊她婶子呢。女会计从地上爬起来,用搌布擦了擦自己,裤子提上来,系好,捋了捋头发,前前后后掸了掸,把搌布锁进了柜子,出去了。她的不动声色太没深没浅了。王连方怕的是出人命。一出人命他这个全公社最年轻的支书肯定当不成了。那天晚上王连方在村子里转到十一点钟,睁大了眼睛四处看,竖起了耳朵到处听。第二天他一大早就到大队部去了,把所有的屋梁都看了一遍,没有尸体挂在上面。还是不放心。大队部陆续来了一些人,到了九点多钟,女会计进门了,一进门客客气气的,眼皮并不红肿。王连方的心到了这个时候才算放下了,发了一圈香烟,开始了说笑。后来女会计走到了他的身边,递过一本账本,指头下面却压着一张纸条。小纸条说:你出来,我有话说给你。因为是写在纸上的,王连方听不出话里话外的语气,一点好歹都没有,刚刚放下来的心又一次提上去了,还咕咚咕咚的。王连方看着女会计出门,又隔着窗棂远远地看着女会计回家去了。王连方很不安。熬了十几分钟,很严肃地从抽屉里取出《红旗》,摊开来,拉长了脸用指头敲了几下桌面,示意人们学习,出去了。王连方一个人来到了女会计家。王连方作为男人的一生其实正是从走进女会计家的那一刻开始的。作为一个男人,他还嫩。女会计辅导着他,指引着他。王连方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好光景,他算什么结了婚的男人?这里头绪多了。王连方和女会计开始了斗争,这斗争是漫长的、艰苦卓绝的、你死我活的、危机四伏的,最后却又是起死回生的。王连方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女会计后来已经不能辅导了。她的脸色和声音都很惨。王连方听到了身体内部的坍塌声、撕裂声。
在斗争中,王连方最主要的收获是锻炼了胆量。他其实不需要害怕。怕什么呢?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嘛。就算她们不愿意,说到底也不会怎么样。女会计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批评过王连方,女会计说:不要一上来就拉女人的裤子,就好像人家真的不肯了。女会计晃动着王连方裆里的东西,看着它,批评它说,你呀,你是谁呀?就算不肯,打狗也要看主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呢。
长期和复杂的斗争不只是让王连方有了收获,还让王连方看到了意义。王连方到底不同于一般的人,是懂得意义和善于挖掘意义的。王连方不仅要做播种机,还要做宣传队,他要让村里的女人们知道,上床之后连自己都冒进,可见所有的新郎官都冒进了。他们不懂得斗争的深人性和持久性,不懂得所有的斗争都必须进行到底。要是没有王连方,那些婆娘这一辈子都要蒙在鼓里。
关于王连方的斗争历史,这里头还有一个外部因素不能不涉及。十几年来,王连方的老婆施桂芳一直在怀孕,她一怀孕王连方只能不了。施桂芳动不动就要站在一棵树的下面,一手扶着树干,一手捂着腹部,把她不知好歹的于呕声传遍了全村。施桂芳十几年都这样,王连方听都听烦了。施桂芳呕得很丑,她干呕的声音是那样的空洞,没有观点,没有立场,咋咋呼呼,肆无忌惮,每一次都那样,所以有了八股腔。这是王连方极其不喜欢的。她的任务是赶紧生下一个儿子,又生不出来。光喊不干,扯他娘的淡。王连方不喜欢听施桂芳的干呕,她一呕王连方就要批评她:又来作报告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