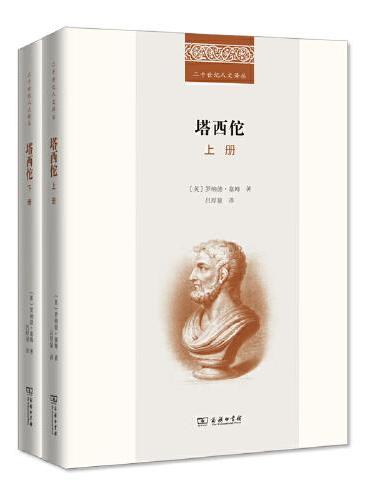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夺回大脑 如何靠自己走出强迫
》
售價:NT$
299.0

《
图解机械工程入门
》
售價:NT$
440.0

《
中文版SOLIDWORKS 2024机械设计从入门到精通(实战案例版)
》
售價:NT$
450.0

《
旷野人生:吉姆·罗杰斯的全球投资探险
》
售價:NT$
345.0

《
希腊人(伊恩·莫里斯文明史系列)
》
售價:NT$
845.0

《
世界巨变:严复的角色(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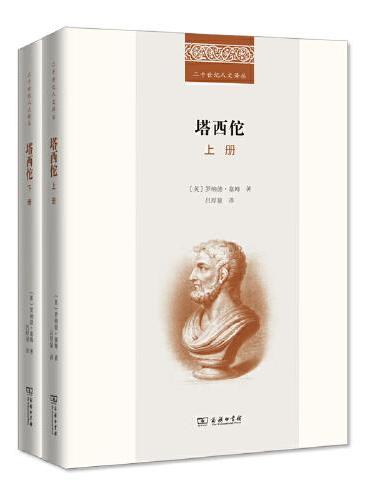
《
塔西佗(全二册)(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
售價:NT$
1800.0

《
宋初三先生集(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
售價:NT$
990.0
|
| 編輯推薦: |
|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故乡,在那个地方承载着我们童年的记忆、成长的印记。那些成长过程中的乐与痛、笑与泪,塑造了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成年人的完整人格。罗南的文字干净得如清冽的泉水。她对 “记忆”、对“亲情”、对“人性”的把握毫无疑问是非常到位的。她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破土而出的新生力量,勃勃生机,让人欣喜。
|
| 內容簡介: |
|
作者站在时间的窗口回溯过往,这个山逻街,或自己的家庭,曾经的琐琐碎碎,曾经的悲悲喜喜,扎实,不事张扬,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冯艺)作者以自己的出生地——山逻街为描写对象。这条丫字形的山逻街,对罗南而言是一个饱含情感,既沉甸又亲切,是逻楼养育了她的生命,那里有她祖辈的坟墓,有她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和那山那水,那风那情。这些牵动着她的精神世界,影响着她的人生。在罗南描写逻楼生活情景的散文里,掺杂着她对父母亲、兄长姐妹,以及乡邻们的生存状态的真情描写,缠绕着她对故乡的人们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
|
| 關於作者: |
|
罗南,广西凌云人,有小说、散文散发在《花城》、《作家》、《广西文学》、《民族文学》等刊物。著有长篇小说《泗水年华》(合著),散文集《穿过圩场》入选2015年度中国作协全国少数民族重点扶持作品项目。
|
| 目錄:
|
|
被脚印串起来的街道1 古一的锣声在一天傍晚又撕心裂肺地响了起来。 再次敲响锣声的古一已年近花甲。他的锣从街头响到街尾,节奏仍然是两声锣声和一声“朵梅”。这次全山逻街的人都听懂了,古一扯着嗓子喊的那声“朵梅”就是姨婆。药这种东西28 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祖母一眼就看到这棵树了,它蔓开的枝叶从四伯父的心里长出来,铺进祖母的眼睛里,铺得满屋子没有一丝空隙。祖母很不安,她深知那些盘根错节的枝蔓有多厉害,它们一旦扎进一个人的心底,便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可是,日子是一天三餐叠出来的,柴米油盐将会像最坚硬的石头,把儿子心里长出来的树砸得支离破碎,把儿子砸得支离破碎。娅番48 瘦长的丫字路,肥胖的丫字街,街头街尾家家户户全都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像一棵错节盘根的老树结出的果,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穿戴同样的服饰。我们知道彼此——谁家最难以启齿的丑事,或是谁身上某一道疤子的来历。这些裸露的生活痕迹让我们看着对方就像看着自己一样踏实。 多少时光的沉淀才堆积出一个山逻街?我不知道。在时间的皱褶里70 父亲却走了。一切猝不及防。我们与龙洞的联系蓦然断开,像两块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大陆板块,父亲一放手,我们就被强力推开,阻隔在时光之外。没有父亲,我们无从触摸先祖的气息。 龙洞彻底像一个谜,存放在某一处我们不知道的安静角落里。豁口89 父亲说,平时,你哥姐都不喜欢听我摆这些,你喜欢听,我就摆给你听。父亲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一个平素里不招家长疼爱的孩子,某一天终于做了一件令家长满意的事,迫不及待地向家长讨好邀功来了。 父亲的眼神让我疼痛。穿过圩场114 这些片段,零碎地储存在我的记忆里,在时间深处。我以为全然忘记时,蓦然窜出来,在另一个时空重复上演。我在梦里回到童年,又在梦外回到中年。妈妈的味道146 下雨天是全家人最忙的时候,母亲拿出大盆小盆大碗小碗,几乎所有能盛水的器皿都拿了出来,摆放在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雨水从腐蚀的茅草间滴下来,雨急时,滴漏处的雨水如柱,哗哗地往盆子里倾注,全家人各据一方,负责把盛满的水一盆一盆往门外泼;雨缓时,滴漏的雨水如断线的珠子,不时叭的一声,滴到盆里来……未嫁女150 姑妈去世的这些天里四哥一直没有掉眼泪。可看到照片和钱的刹那,他却流泪了。那一瞬间,他突然明白,原来自己欠姑妈的是一份绵绵长长的思念啊,而他寄回来的钱在姑妈那儿原来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四哥欠姑妈的永远没机会还了。奔向那地160 我等这鼓楼等了很多年。 这之前,它们待在不同的画面里,是一种神秘和安宁。它们层层叠叠飞翘的檐像载着一个远古的梦,这个梦长久地伫立在每一个侗寨,立成了岁月和符号。老枫树下的来弟们169 不时撞入我梦中的依然是那棵高耸入云霄的树,一棵老枫树。 老枫树生长在一个名叫大石板小学的校园里,那是一个山村小学校,在两乡交界处……水之上178 多少年里,百乐街的人一直在孜孜不倦谈论着那个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地理先生来到百乐,走过街道时,这位地理先生四肢着地,战战兢兢地往前爬行,人们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何不直立行走,地理先生回答说,百乐街下面是空的,他怕直立行走会塌陷下去。后记:朝着光的方向奔跑195 我看到时光落在我身上的样子,像一堵斑驳的墙,被侵蚀剥落。我站在时光这头,早早看进我的老年,孤独,唠叨,孱弱,健忘,而且脾气一定还会很坏。很多时候,我独自从街头的车水马龙穿过,某一个瞬间,便会看见小时候的自己,在每一段时光里奔跑。
|
| 內容試閱:
|
序罗南是一位生活在桂西北山区的作家,是一位虚心好学且有悟性的作家。近年来,她的散文频频在国内文学刊物上发表,看到她在写作上的日渐进步,曾作为罗南散文写作的指导老师,我为她高兴。如今,她要出版散文集,让我写个序,我应诺了。罗南的这本散文集,主要以自己的出生地——山逻街为关注对象。这个“瘦长的丫字路,肥胖的丫字街,街头街尾家家户户全都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像一棵错节盘根的老树结出的果,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穿戴同样的服饰。我们知道彼此——谁家最难以启齿的丑事,或是谁身上某一道疤子的来历。这些裸露的生活痕迹让我们看着对方就像看着自己一样踏实”的地方,是她所写的大部分。不一样的乡土,有不一样的故事。这个巴掌大的山逻街,对于罗南而言是一个饱含情感,既沉甸甸又亲切的词语,是山逻街乡土养育了她的生命,那里有她祖辈的坟墓,有她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和那山那水、那风那情。这些牵动着她的精神世界,影响着她的人生。因此,在散文里,她能通过细致的笔触,再现故乡土的山川风貌、人物景致、民俗民情等与乡土记忆、亲情记忆相关的事物。散文中叙述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我们对桂西北乡土的生存状态以及精神生活,有一定的真实的了解。真实是散文区别于小说的一种重要的内在特征。散文应该是在保持真实的基础上,富于情感的艺术呈现。可以说,在罗南描写山逻街生活情景的散文里,掺杂着她对父母亲、兄长姐妹,以及乡邻们的生存状态的真情描写,缠绕着她对故乡的人们挥之不去的悲悯情怀。作者站在时间的窗口回溯过往,这个山逻街,或自己的家庭,曾经的琐琐碎碎,曾经的悲悲喜喜,扎实,不事张扬,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比如,在《豁口》中,把母亲给予她的爱,用朴素的文字湿润地表述出来,使其在母爱的温暖中散发出感动。“每个节假日,她精心烹制我喜欢吃的食物,盼我归来,送我离去。母亲总是笑盈盈的,她站在车窗外,目送我一点点远离她的视线。我没有回头,我的眼睛盯着远方,却清晰地看进母亲的心底……”这样的文字表达,充满着丝丝缕缕的暖意。有过母亲呵护经历的读者,无不为此感动和共鸣。这种感动和共鸣应该源于作者灵魂深处的感恩和对生活的热爱,也让我们感到了平凡日子里家庭那爱意的涌动。一个散文作家,当他把心灵交给自己时,不说故事是否精彩,技巧是否娴熟,光是那些细节就能感动作者。比如:“父亲在屋里熬粥……火塘的三脚架上架着一大鼎罐水,父亲左手抓起一把玉米面,右手捏着一双比平常长出三四倍的竹筷子。玉米面从父亲左手缝飘飘洒洒缓慢落入鼎罐内,右手捏着的长竹筷欢快地沿着顺时针方向不停地均匀划圆圈。没干透的柴火嗞嗞地吐出白沫,冒出辛辣的烟火熏得父亲睁不开眼……竹筷划出的圆圈花朵一样在鼎罐内层层叠叠绽放。父亲熬了大半辈子粥,无须用眼,也知道左手右手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再如:“我们都假装看不到父亲的寂寞。父亲心里堆积有多少无人倾听的话呢?年轻时,他不能说,因为他忙着填饱八张幼小的嘴;年老时,他不能说,因为没有人肯坐下来听他说。从年轻到年老,父亲积攒的话早就葳蕤成参天大树,或是像书房里年久无人翻阅的书,积满厚厚的灰尘。”终于有一天,当作者因写作需要向父亲询问问题时,那时,“父亲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一个平素里不招家长疼爱的孩子,某一天终于做了一件令家长满意的事,迫不及待地向家长讨好邀功来了。父亲的眼神让我疼痛”。这样的叙述,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细节自笔端流出,使父亲的形象呼之欲出,读着这些文字,每每会情动于中。罗南在写作中,不论是写亲人还是写乡邻,都在叙述中注重细节的描写。比如,她写那个不知从何处嫁进山逻街叫娅番的汉族女人,第一次与作者说壮话的情形,“她的声音突然从山一样高的柴火下伸出来。娅番说,姨婆,吃饭了没?娅番的声音很犹豫,像是把一句话含在嘴里已经很长时间了,明明就在舌尖,却仍然不能确定要不要将它吐出来。娅番说的是壮话。她的壮话还没养熟,疙疙瘩瘩地长着刺,每一个声调都倔强地高高扬起,结束的时候,骤然落下,像一个硬物重重地砸在另一个硬物上”。由此看来,这些细节描述的灵动鲜活及其生活质地,需要生活的阅历,需要敏锐的观察,需要阔大的视野。一篇好的散文,有了好的细节和鲜活的表达,就有了成功的保证。从这本散文集中可以看出,作者还有一颗赤子之心,没有忘却背后的故乡,那里有她的来路,那里山明水秀,那里贫穷落后,那里淳朴善良,这些记忆在她心中最为深刻。比如《在时间皱褶里》、《娅番》、《药这种东西》等篇章,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山逻街的历史轮廓,时间的真相,古老的民风民情,眼里的景物,心中的情思,以及乡土有关的一切都在笔下渐次呈现。那里是她的祖先停留、驻足、安居、劳作的最后一站,是她的血脉和根系。她对乡土懂得了感恩,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无法割舍的牵挂。她沉浸在平凡的人和事中,在这些乡村日常生活中积聚着对自然、人生、世界的理解和感触,抒写那些曾经照耀过内心的亮光。这便是她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认知,也是她对于山逻街这个地方自身情感的由衷表达,时而轻松,时而忧伤而滞重。毫无疑问,我们与乡村有了疏离感。其实对于乡村的这种疏离感,是当下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现在,乡村在我们的眼前渐次变味,消解,逝去。这些年,那里除了老人和孩子,整个乡村空空荡荡,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有的甚至已把家安在了城里,我不知道这些年轻的一代,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否还有故乡。也许,他们当中一些人已成为没有故乡的一代,没有根的一代。悲叹之余,我又有了欣慰,这欣慰来自罗南笔下的文字,为我们保留了一份乡村中的记忆,同时,还会发现与之共生的关于悲悯、同情、叹息,关于回望,关于温暖的情怀,使我们与曾经疏离的世界紧密相联。写上这些感受,仅此感受而已。是为序。冯艺丙申夏写于京西八大处
被脚印串起来的街道遥远的哭唱姨婆蹲在黄皮果树下哭唱:命苦哟——命苦连天苦连地,苦瓜种在黄连地。苦命姑娘苦成婆,苦到地下苦堆泥。呜——呜!呜——呜!……姨婆的哭调,长声连绵,短声凄婉,这一长一短的哭唱声从沙沙摇响的黄皮果树下爬上我家窗棂,爬进已经入睡沉静下来的房间,爬进我们被睡意灌满的耳朵里。夜风过处,姨婆的哭唱调被撕扯成丝丝缕缕,时断时续,时强时弱,在黑魆魆的寂空里穿行。我从床上爬起来,踮起脚尖往窗外看——皎洁的月光下,姨婆正蜷着身子蹲在她家门后的黄皮果树下哭。姨婆边哭边唱,苍老的声音透着无尽的沧桑与凄凉。在悲伤哀婉的曲调中,我尚不解世事的幼小的心竟也无端被刺痛,眼里的泪不知不觉地滚了下来。姨婆把哭和唱结合在一起形成的这种悲凉曲调令当时年幼的我十分惊奇,我并不知道,在我祖辈父辈的年代里,我家乡桂西北凌云的每一个壮家女子都会这种唱法。在电视、网络还没有风行的年代里,山歌就像血液,在壮家人的躯体里四处奔流。一对男女从相识相恋到结成秦晋之好,大多因了山歌的牵引和成全。从出生到老死,山歌贯穿了壮家人的一生。对旧时的凌云壮家女子来说,不会哭唱就像不会种田织布一样,是一件不可思议和羞耻的事。山歌就是壮家人心中的喜怒哀乐。年迈的姨婆在流行歌曲日新月异,山歌渐渐匿迹的时候,依然固执地保持用山歌诉说内心的习惯。从故事里走出来的两个女人我和姨婆究竟是多少代前结下的亲戚,现在已经没人能理得清了。小镇年岁太古,从第一辈到我这辈之间不知历经多少沧海桑田。因此,在镇上,若要从先祖的那一代论起,牵七扯八,每一家都能沾上一点亲戚关系。小镇呈丫字形,丫字的一点一撇一竖笼统算是一条街。镇叫逻楼镇,街叫山逻街。丫字的一点是政府机关学校所在地,那里住的几乎全是外地人,丫字的一撇是街头,一竖是街尾,这一撇一竖住的全是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的山逻人。丫字交叉处有一棵三人合抱粗的大古榕。古榕的枝叶向四周蔓延,覆盖住整个路面,一直延伸覆盖到街对面的房顶,探进人家的院子里。古榕下是几块已经被屁股磨蹭得光溜顺滑了的大石头。傍晚时分,小孩子们在古榕下追逐嬉戏,大人们则坐在大石头上围成一圈闲聊。姨婆的故事就从这些闲聊里跑出来,流传到下一代去。姨婆家与我家只有几步之遥,小时候我对这个身材胖硕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很是畏惧。因为姨婆特能骂,不论大人还是小孩,谁不小心惹恼了她都有可能招来好长一段时间的骂。在山逻街,姨婆唯一的骂街对手是街头的婆大。按旧时的叫法,姨婆应该管婆大叫大姐。因为婆大和姨婆都是姨公的老婆,婆大是妻,姨婆是妾。在旧式家庭里,妾要称妻为大姐。当然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事了。新中国成立后,婆大与姨婆不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她们一个住街头,一个住街尾,如果不是田地的界线相连,她们几乎可以做到老死不相往来。可姨婆和婆大不但往来了,而且往来得很频繁,每隔三天五天就会惊天动地地往来那么一次。姨婆和婆大往来的方式很特别,那就是骂街。姨婆与婆大田地相连,姨婆的苕藤爬进婆大的地里或是婆大的瓜崽结到姨婆的田头,这些琐碎寻常的事都能招来姨婆或婆大骂街。山逻街不大,一丁点争吵声都会引来全街看热闹的人,更何况站到大街上唾沫四溅、指手画脚、指桑骂槐的人是姨婆和婆大。因此,有姨婆和婆大骂街的傍晚,山逻街连空气都氤氲着兴奋。首先入戏的一般是姨婆。白天,姨婆把地头的活儿做完了,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妥当了,吃罢晚饭,这才不慌不忙走出家门。她高高撸起两只袖子,露出两截白生生的胖手臂。走到马路中央,姨婆先是双手往腰上一叉,从嘴里狠狠啐出一口痰,紧接着,两只手掌猛地一拍,张嘴便开骂起来。姨婆嘴里骂骂咧咧,手掌拍得啪啪响,两只大脚丫蹬蹬蹬地往街头迈。她的骂声里只有事件没有人物,可每个人都能听出来她骂的是谁。姨婆走到婆大家门前,脚步便缓了下来,声音却高了上去,她没有停步,而是在婆大家门二十步开外不停徘徊。姨婆的话字字带刺,句句见血。在屋里听了半天的婆大终于忍不住走出家门,指着姨婆开始还击。姨婆见到婆大,立刻亢奋起来,她“哈”的一声怪笑,手掌拍得更响了。这时候姨婆最有杀伤力的那句话是“人不着急狗着急,我又不指你的名,既然不是你你着什么急?”婆大像被蜇了一下,跳了起来,她也把手掌拍得啪啪啪地响,冲着姨婆高声骂起来。两个女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从陈芝麻烂谷子翻起,一直翻到祖宗十八代。四周早就站满了人,他们边看边议论,姨婆和婆大的故事再次从纷纭的嘴里跑出来,流淌在山逻街的街头巷尾。围观的人饶有兴趣地看着,谁也不去劝架——只要两个女人不动手打起来,旁人是不会劝架的,其实,他们想劝也劝不了,清官还难判家务事呢,更何况是姨婆和婆大这对有着特殊历史和故事的老冤家?夜愈深,姨婆和婆大只是你啪啪地骂着走过来她啪啪地骂着走过去。两个女人虽然对骂了很多年却从未真正动过手,围观的人觉得没有劝解的必要,便打着哈欠一一散去了。姨婆和婆大少了观众,骂街的兴致便淡了下来,她们依然喊着骂着,声音却渐渐弱了下去,最后,一个往街头走,一个往街尾去,终于各自关上家门,带着惬意和满足爬上床睡去了。姨婆骂街更甚婆大是因为她比婆大多出了一份韧性。第二天,姨婆安排好坡上和家里的活儿,吃罢晚饭,又啪啪啪地拍着巴掌上街头找婆大。婆大毕竟比姨婆大二十多岁,她挨不住姨婆几次三番的纠缠,到最后,干脆紧闭家门不再出来,姨婆没了对手,也觉无趣,只好怏怏而归,一轮骂战方算结束。在姨婆和婆大骂街之前,山逻街最热闹的要算古一的锣声。古一年纪比我父亲大,可按辈分算我却管他叫哥。古一的家在街头。傍晚,古一从家里出来,他手里提着一面锣,每走几步就敲两声“咣——咣——”然后停下来扯着嗓子喊:“朵——梅——”从丫字的一撇敲着喊着走到一竖,又从一竖敲着喊着走到一撇,折回来,又从一撇敲着喊着走到一竖。古一来回敲喊着,就是不往丫字的那一点去。古一的锣只敲给土生土长的山逻街人听,古一的话也只喊给土生土长的山逻街人听,更重要的是,古一的敲喊是为了给住在街尾的姨婆听。街两旁探出许多小孩和大人的脸。古一目不斜视,专心敲打着手中的锣,扯着嗓子用力嘶喊着嘴里的话,街两旁的脸一张张往他身后移动,古一不看也知道,这些脸里没有姨婆。姨婆的家门静悄悄的,任由咣咣的锣声和嘶哑的“朵梅”一遍遍从门前来来回回经过。我把脸挤在那堆脸里看古一敲锣的时候,古一应该有六十岁了,他佝偻着身子踽踽而行,路两旁的灯光把他投在地上的影子拉得又瘦又长。古一迈一步,粘在他脚后跟的影子也跟着走一步。…………最后的锣声没有人能劝阻得了古一的锣声。每个人都说,傍晚敲锣的不是古一而是住在古一脑子里那个小人儿。对于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疯狂倒腾的小人儿,街人拿他没办法。街人说,就由着他敲去吧,敲累了总会回家睡觉的。古一的锣声顽固地从街头游到街尾,又从街尾游到街头,一声声绵长迟缓的锣声和一声声同样绵长迟缓的“朵梅”,像一对孤独的幽魂,孤零零地从街头出现又孤零零地在街头消失。古一高条条的身子弯成了一张弓,两只深陷下去的眼像两口被掘干的井,除了号喊那声“朵梅”时,井里还会泛起一些温润的东西,此外,便只剩下生硬的呆滞和憔悴。拥挤在古一身后,陪着他一起号喊“朵梅”的孩子一茬茬长大离开又一茬茬降生跟随。轮到我这一茬时却是最后一茬了,因为,等不及我们长大离开,古一连同他的锣声同时在山逻街上永远消失了。古一终生未娶,进入老年后就依靠政府和街坊四邻的救济过活。那夜,姨婆听着古一的锣声渐渐弱去,终于消失在街头。第二天一早,她就让儿子带着刚煮熟还热气腾腾的肉灌豆腐拿到街头给古一吃。姨婆的儿子站在古一的门前喊了几声,不见有人来开门。他推开门进去一看,古一静静地躺在床上。古一冷冰冰的,身体都硬了。古一死了。姨婆默默地蹲在古一身边,有条不紊地为古一擦身,换衣,入殓,做完这一切后,姨婆没多做停留,转身往家走去。古一入殓的棺材是姨婆的儿子为姨婆准备的寿棺。凌云的壮族人在过了五十岁之后,就由子女为自己准备好棺材,然后请风水先生帮选好葬地。古一无儿无女,自然没人为他准备棺材。姨婆要拿出自己的棺材给古一入殓,儿子不同意,儿子说:“古一的棺材不是有民政帮他出钱买吗?凭什么要妈妈出?”姨婆拿眼横了儿子很久,突然一巴掌打在儿子的脸上。姨婆从未动手打过儿子。已经身为人父的儿子捂着被打红的脸,怔在那里。姨婆还冲着儿子怒吼:“凭什么?啊?凭什么?就凭他那脑壳就是为了帮你们这几个饿痨鬼偷苞谷才被人打坏的!如果古一不帮你们偷集体的苞谷,他会挨批斗吗?如果他不挨斗挨打,他的脑壳会挨打坏吗?如果他脑壳不坏,好好的一个人,咋个会发癫吗!造孽哟——造孽哟——”姨婆自顾自地哭起来,儿子不敢再说话,乖乖地爬上阁楼,把放在那里的棺材取下来,抬到街头去。古一离世的夜是寂寞的。只有街尾的姨婆蹲在自家门后的五棵黄皮果树下哭唱:造孽哟——造孽哟——打错酸醋买错缸,打错主意嫁错郎,都怪媒婆油嘴猫,硬把山鸡配凤凰。呜——呜!呜——呜!姨婆的脾气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变坏的。她像一只张牙舞爪随时等候战斗的公鸡,每个走近她的人都可能会被她狠狠地啄上一口。古一和他的锣声一起消失后,山逻街平静了一段时间。当街人都渐渐习惯这种平静时,街头街尾却又热闹起来。说不清是姨婆先找上了婆大还是婆大先找上了姨婆,总之,某一天傍晚,山逻街人惊奇地发现,互不往来多年的姨婆和婆大同时出现在大街上,你啪啪地拍着巴掌骂过来,我啪啪地拍着巴掌骂过去。姨婆和婆大先是为了田间地头的琐琐碎碎吵,后来两人都做了豆腐生意后,又为了豆腐摊上的琐琐碎碎吵。所有的一切都淡去后如今的小镇,在原来丫字的一点一撇一竖上又旁伸斜逸出许许多多个小丫,大大小小的丫不断向四周延伸,撑大了这个古老偏远的小镇。 丫字的一点一撇一竖上到处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操着各种口音的人的身影出现在每条大街小巷中。枝杈错落的街街巷巷让年青一代的山逻街人再也分不出哪里才算是街头哪里才算是街尾。只有街心那棵大古榕仍然遒劲葱茏,蔓延的枝叶依然覆盖着路面,一直延伸覆盖到街对面的房顶,探进人家的院子里。婆大已经九十多岁了,瘪瘦枯小的身躯蜷缩得厉害,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到地面,她像秋天里最后一片还挂在树梢上瑟瑟抖动的叶子,轻轻呼出一口气都能把她从树上吹落下来。每个人都以为婆大一定会走在姨婆前面,没想到,先走的那个人却是姨婆。姨婆的死没有任何征兆,那天下午,七十多岁的姨婆还在厨房里帮儿子泡豆子——姨婆现在已经不做豆腐了,她把做豆腐的绝活传给儿子。儿子把姨婆的豆腐手艺发扬光大,在镇上开了一个豆腐加工厂。姨婆只在闲得无聊的时候帮儿子泡泡豆子,点点豆腐什么的。那天下午,姨婆一边泡豆子,一边絮絮叨叨地跟六岁的重孙虫虫说话。姨婆说:“虫虫,太婆做的豆腐好不好吃?”虫虫一边伏在小桌子上画画一边拉长声音奶声奶气地回答:“好——吃——”姨婆很高兴。又问:“虫虫知不知道是谁教太婆做豆腐的?”虫虫仍伏在桌上画画,头也不抬地又拉长声音奶声奶气地回答:“不——知——道——”姨婆说:“是你的大太婆呀,嗯嗯,就是那个特别爱骂街的白头发的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是太婆的大姐,你要叫她大太婆!大太婆现在骂不得街了,她老了,都差不多一百岁了。嗯嗯,就是她教太婆做豆腐的。她做的豆腐比太婆做的好吃多了,你那大太婆呀,整天凶巴巴的,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嗯嗯,和她做的豆腐一样软嫩嫩的豆腐心……”姨婆喋喋不休地说着说着,突然打了一个哈欠。她从凳子上站起来,说:“虫虫,太婆困得很,要上床眯一下下,告诉你公说不用喊太婆吃晚饭了哦。”姨婆这一眯就再也没有醒来。姨婆的丧礼举行到一半的时候,婆大摇着小脚颤颤巍巍地迈进来了。她人还没到,哭声先传了进来:背时婆你无良心,早早躲进苞谷林。要躲太阳讲给我,要躲老娘不是人!背时婆哎——你咋个叫不应了嘛!婆大走到灵柩旁,身子一歪,就势蹲在地上唱:你我本是同笼鸡,你叮我啄不稀奇,阴阳两分没处依,才知有缘要相惜。婆大唱着唱着,耳里依稀听到姨婆在叫她大姐。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婆大想起以前两人在一起持家时,姨婆一口一个大姐地叫她,可她却一口一个背时婆地叫姨婆。婆大还想起,姨婆为了不加重她的“罪”,宁愿和她一起成“地主婆”挨批斗也不愿站出来揭发她。婆大还想起两人一起挨批斗时,姨婆偷偷投过来的那种同病相怜的目光。就是姨婆的目光让婆大觉得,站在批斗台上的她并不孤独……当下心一颤,婆大对姨婆惯有的称呼脱口变成:妹妹哎——你咋个打个瞌睡就去了嘛!姨婆的儿子先是一愣,反应过来后连忙把婆大扶起来,婆大仍不停地哭唱:姐妹本是鸟同群,大限阴阳两相分。妹你阴间选好树,来日我俩还同林。妹妹哎——等我喔——等我下去同你磨嘴巴皮你就不闷了嘛!婆大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唱的声调也如姨婆般凄婉绵长。街人被婆大的哭唱彻底搞糊涂了,本以为婆大和姨婆的仇恨比天大。现在看到婆大悲悲切切地哭唱,倒真弄不清婆大与姨婆之间到底是恩还是怨了。难道说,大半个世纪的雪雨风霜,婆大和姨婆之间早就无所谓恩恩怨怨了?或是,婆大和姨婆正是用骂街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惺惺相惜相互取暖呢?恩怨恩怨,是恩亦是怨,是怨亦是恩啊!不管是恩是怨,婆大与姨婆的故事已经愈行愈远。前辈人的脚步刚刚从小镇走过,后辈人的脚步就如潮水般一浪浪涌来。镇依然叫逻楼镇,街依然叫山逻街。但镇已不是原来那个逻楼镇,街也不再是原来那条山逻街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