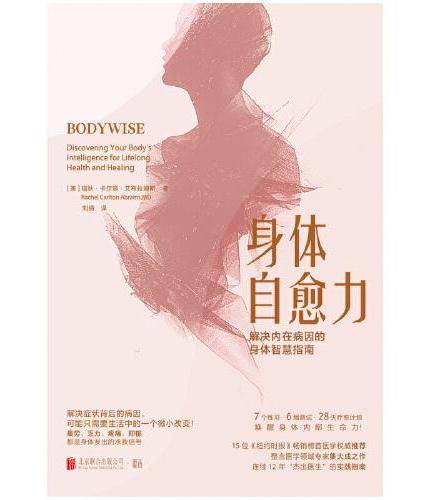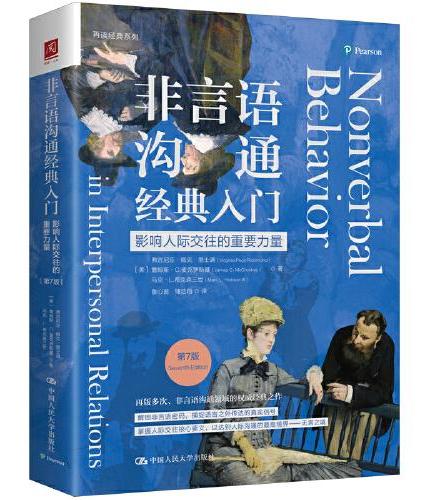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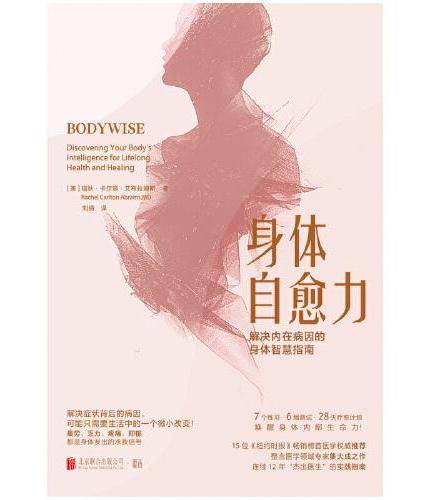
《
身体自愈力:解决内在病因的身体智慧指南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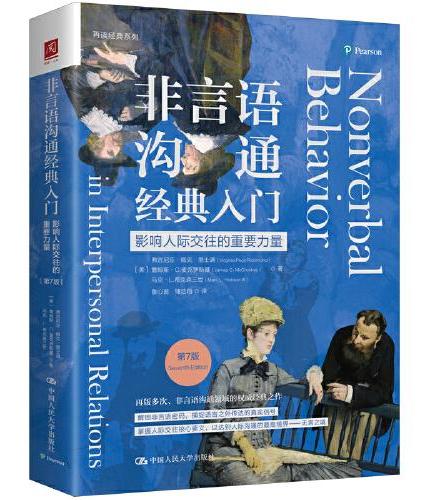
《
非言语沟通经典入门: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力量(第7版)
》
售價:NT$
560.0

《
山西寺观艺术壁画精编卷
》
售價:NT$
7650.0

《
中国摄影 中式摄影的独特魅力
》
售價:NT$
4998.0

《
山西寺观艺术彩塑精编卷
》
售價:NT$
7650.0

《
积极心理学
》
售價:NT$
254.0

《
自由,不是放纵
》
售價:NT$
250.0

《
甲骨文丛书·消逝的光明:欧洲国际史,1919—1933年(套装全2册)
》
售價:NT$
1265.0
|
| 編輯推薦: |
|
《屡次想起的人》中的每篇小说必有一点奇怪之处,沈大成喜欢构建超现实的社会,专写奇怪的人和只有一点点发生可能性的故事,然而在描绘超现实风景时,又异常珍视人之常情,让你在不可思议里读出日常生活的真实百态。打开每篇小说,便进入一个用有质感的想象力、美的文字,和理所当然的语气,构建起来的假世界,它绝不可能存在可又栩栩如绘,并真实地碰触心灵。
|
| 內容簡介: |
收录诡谲合理的15篇短篇小说,踏足真假两界,同时把玩恐怖、推理和想象,有时创建一个城邦,有时改造*,有时发明某种职业,有时捏造不存在的动物,有时重塑一套社会规则,在诡谲之中涌现合理的故事,又在合理之中惊人地转折。
《阁楼小说家》:小说家住进出版社阁楼,和社长、编辑朝夕相对,除非写出一部人生作品否则不会离开。《圆都》:赘肉和橘皮组织是一个恐怖组织,它攻击谁,谁就会发胖。而胖的人懂得一些瘦子不知道的事。《分裂前》:当你四十岁了,假如不想活下去,可以分裂成两个二十岁的别人
|
| 關於作者: |
|
沈大成,前前广告文案,前媒体人,现供职于出版社,任图书编辑及杂志编辑。生活在上海。曾为多家报刊杂志撰写专栏。合著《梦的14旅行》《不拆》。擅长以小说做这些事:打开脑洞,再缝合起来,装作没事;或者提出问题,看看清楚,但不解决它。
|
| 目錄:
|
〇一 阁楼小说家
〇二 义耳
〇三 擦玻璃的人
〇四 口袋人
〇五 理发师阿德
〇六 空房间
〇七 折叠国
〇八 大角星
〇九 待避
一〇 赏金猎人
一一 脱逃者
一二 分裂前
一三 分段人
一四 圆都
一五 关于玩抓娃娃机的年轻男子
令人恐惧的夜半孤魂
评《阁楼小说家》的小说家的小说(俞冰夏)
跋:假到这个程度是我喜欢的
|
| 內容試閱:
|
假到这种程度是我喜欢的
当在报纸上得到一个写专栏的机会,我一下就知道,我喜欢写超现实小故事。自那以后,十二年过去了,股票亏了两轮,工作换了两种,没有什么名气的我还在写那种故事。我好像不喜欢写很真的小说,非要写也会加一个怪梦、一段想象,把现实扭曲一会儿,否则我不舒服。我只喜欢写超现实小故事,以后也会一直喜欢的。
过去有很长时间,我经常使用一套方法。首先设想一个地方,它和我的世界基本一致,我不用多做什么,只稍微调整某个数值,顿时就破坏了数学题,使社会的方程式错乱。那个地方出现漏洞了,紧张了,失衡了。为重新回到平衡,那个地方的人必须行动起来,制订新的社会公约,找到新的相处方式,新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人们为此高兴和苦恼;而适应新状况的同时,一些经过千锤百炼的旧世界生存法则也得继续遵循,否则社会崩塌,人人受害。简单来说,设定一个地方,调整某个值,心中一半想着新秩序一半想着旧法则,就可以写出什么来了。这办法有效。假想一个地方每个表面都很滑;假想一个地方每当社会财富积累得够多,大家停止劳动坐吃山空,吃空后再度劳动;假想一个地方人人爱迟到;假想一个地方位于全世界最下游,人们靠从世界的大河中打捞顺流而下的废品生活照此想下去,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故事。但这方法太有效,培养出了我的懒惰,还有一个我控制不了的不良作用,它让故事生长出相似的样子来,因此现在减少使用了。
然而我喜欢重置某个数值的爱好没有变。因为我喜欢在稍稍离开常规的地方,试着创造出一个新的国家,一个似是而非的城市,再创造出一套适合它们的社会规则,最后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我想,要是我花一样多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有很多是公认艰巨的工作,有很多是对于别人简单但不适合我的工作,我是难以完成的,或者到完成时消耗比获得多。但想象是轻松的,它可以叫我在一块假的领域拥有权力,为了一再获得摆弄这种权力的乐趣,我也会再想想,再写写。只是从现在开始得找到更多方法,避免在一个枯燥乏味的假地方可怜地玩耍。
这里有十五个这样的小故事。除了它们,我还请我的朋友俞冰夏写了一篇假书评,评论对象是《阁楼小说家》里的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阁楼小说家》写了一个遁世者,一个把物质生活全部舍弃,把过去的自己献上创作祭坛的极端的小说家。我没有交代他如此奋不顾身地写作,到底写得好不好,但既然需要假书评,应该给俞冰夏设立标准,使她清楚小说家的水平,好调整蜜糖有多稠或刀锋有多利。参考什么好呢,想起我还在报社收稿子的时代,她写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的书评,就说:小说家是蹩脚的波拉尼奥。这句说完,还没等她开始写就已经很开心。因为现实中的波拉尼奥是我比不了的人物,但是,我可以假想我写出来的人某种程度上是他,并找人批评他的蹩脚变体,于是又一次感受到权力带来的乐趣。
俞冰夏写来的假书评不能再好了。她补完了小说家本人以及小说家的小说。关于小说家本人,她让我知道,他原先在社交派对或讲座对谈中,经常给人一种既热爱自己、又非常喜欢强调自己的努力,又精神清高的印象,也就是说,平均呈现作家们最常见的三种主要的样貌;等他躲进阁楼疏离圈子,五流文人见不到他了,就向他致以最高级别的尊敬,虽然他们嘴上不说尊敬,就像不会公开谈论自知的油滑柔韧。关于小说家写的小说,她又让我知道以下几点:一,小说有六百多页;二,主干情节是一个普通海员的情感历史;三,人物的对话被简化或者抽象化,同时又体量惊人,有三处长对话,竟然分别占用了58页、23页和74页,可惜写得不令她满意。我所没有写出来的,俞冰夏假模假样地写出来了,评论了,同时借着评论不存在的小说家,用她一贯有的根深蒂固的怀疑论者的论调嘲笑了一些真作家。
在她交稿的当晚,我们又见面了,先在破破烂烂的地方吞嚼了烤羊排,后来又去一个奇特的朋友家,她瘫坐在那朋友的一件既像沙发又像床的红色家具上,从一次性纸杯里喝酒时说出了她影射的几个真作家的名字但她不带坏的意思,我保证更没有,我们作为人,总得采用各种方式不时地谈论人家,否则干什么好呢。我们也这样谈论自己。我感觉整件事有点好玩,就想到,为了更开心,有时候一个人干假事,不如大家一起干。朋友们偶尔应该一起做一些亦真亦幻的事情,我这个拘谨的人,对此领悟得太晚了,现在领悟了似乎又不够力气做什么。
也不是所有假的我都喜欢。我讨厌漫无目的的假、不真挚的假,对单单追寻假没有兴趣。无论如何,我也不会仅仅写奇观化的东西。我向往写出奇怪境况中的亲切的人。假城中的理想的肖像应该具有这些特征:人们需要谋生,一般而言有工作,分配收入时精打细算;有正常的情感,可能偏爱某个家庭成员,对于和不同的人建立起新关系,心里总有点儿紧张;有主见,不依据主见行事,因为妥协更方便;常在新时代独个儿怀旧;最后,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观点是符合事实的,而事实是我捏造出来的。我尤其愿意让这些人保持某种为难的状态。他们的智力达到了既能够认清处境,也理解自己的程度,因此只要想,就想得出一些办法,但有办法也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所以谁也得不到完整的幸福。绝对不能太幸福,必须叫他们品尝遗憾,就像我们一样。遗憾的事会使人念念不忘,身上带有遗憾印章的人,是容易被屡次想起的人。
阁楼小说家
早在黄昏到来前,编辑们一个两个地下班了,手头的稿纸摞起来,啪嗒一声关掉绿色灯罩下的橘色灯光。办公室相继暗下去。连接办公室的走廊逐条撤空。保安在固定钟点出现,这里唯有文化,无惊无险,等他以散漫的态度巡过楼,一层留好一盏灯,天便全黑了。出版社所在的小建筑物里静静的。小说家这时从他的房间里走出来。
他出了阁楼往下走,走完一节黑色大理石楼梯,一转折,走另一节,来到下一层。他在无人的走廊上,在有着细腻雕花的天花板以及古典吊灯下,缓步溜达。数间紧闭房门的办公室,他经过了。到了走廊尽头,他停住。十四扇窄窗连成大半面墙,从这里,看到小马路上栽成行的梧桐树。春天到秋天,绿意渐浓又渐淡;冬天,只有枯枝干。绿叶成荫时,每逢刮大风,在窗里持续观看树叶摇动,容易头晕,仿佛身在一艘大船上,正行驶过梧桐树叶的海浪。此刻是冬天夜晚,风平浪静,他看了一会儿几乎和窗齐平的光光的树顶。他接着下楼梯,他把每一层楼游荡游荡,在每道走廊尽头,他都停步看风景。梧桐树的树顶。梧桐树的高枝。梧桐树的低枝。梧桐树低处的粗树干。他到了一楼,值班保安,就是刚刚巡楼的那一个,坐在胡桃木色的台子后面,他要在无聊的自由中枯坐到八九点,期间看看报纸,饮饮茶,最后做一次巡视,就窝到休息室里不出来了。
保安早就听着出版社里仅剩的脚步声,橐橐,橐橐,从头顶开始,回声响彻整栋楼。几十年前,保安还年轻,刚来工作,他必须从小说家的谈话中,过几年他可以从小说家的脸色上,现在他经验已丰,只要一听脚步声,就能猜出小说家今天写了几行字。他写得多时,因为满足而走路慢,他写得少时,因为背负的苦恼重而走路慢,他总之是走得慢,但保安懂得差别。今天他写得很不少。保安先是依据声音做判断,见到小说家本人迈下最末一级台阶时,他补充想,最近一直写得多,写得很顺利。保安是除老社长外最了解小说家的人,这个事实,他们三个人从始至终不知道。
两人简略地问好。小说家站在门里紧一紧旧大衣的领口,随后推门出去,走到出版社外面那条颇有吸引力的小马路上,他路过刚从高中低不同视角看过的梧桐树,他又以行人视角再次看了看树,反正小说家该从各种角度看待同一事物,并永远不应当生厌。他出门是要去吃晚饭。吃过饭,他将做一次长散步,然后回到出版社,回到阁楼上。
小说家定居在出版社。
很多很多年之前,小说家向出版社要下一间办公室。在拥有办公室之前,他曾经在这里出版过处女作,一本畅销书。在出版这本书之前,谁都不看好这本书,谁也都不看好他这个人,负责他的编辑不咸不淡地对付他,因为像他这种作者多得是,没理由对他特别期许。
但是这本书的命运好。它不温不火地销售了半年多,突然契合上一个社会话题而走红,库存一销而光,马上加印了又加印。小说家受邀上过几回访谈节目,给人谈不上好坏的极其飘忽的印象,不过这不重要,紧跟着,他的小说卖出电影版权,在三流电影导演的口中他的才华要比他本人承认的多。电影拍得平平,可又确实带动新一波销量,将小说家推上畅销书作者的榜单上游。小说家趁着余勇,出版第二本书,销量为畅销书的七分之一,不够好,也说得过去。他就是在写第三本书时,请求签下他的社长暂时提供他一小块写作的地方。社长不是拘泥条规的人,爱交朋友。小说家在那时具备当朋友的资格了,他们讨论过,在新书完成后,三本书要做成会引起关注、赢得奖项并卖得动的三部曲套装出售,尽管它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一个恰当的命名会掩饰问题。小说家并且创新地建议,房租可以和新书预订金相互抵销,社长同意了。
在出版社写作,一定是很好的。社长举出上一代八个名作家的名字,像他们。以前的作家都是出版社的好朋友,双方超越了金钱往来的关系,作家常和要好的编辑走动、交流,得到好的建议,写出好书。
是啊。小说家说。他不太想讲人际关系,主要诉说他的租房初衷,早晨九点来,晚上五点走,每天不受打扰,有规律地写作。我想试一试这样的生活。
社长赞同,那一定是很好的。写书没有别的法子,写一百个一百字才有一万字,写二十个一万字才有二十万字,成为一本书。与其说作家掏出了二十万字的天赋,不如说进行了二十万字有效的工作。作家需要好好工作。
小说家说,是这样。
社长带他走了几层楼。楼梯栏杆每隔一段装饰着弯弯曲曲的铜制的艺术化线条,抵到他们脚边。他们的皮鞋以四个步点轮流敲击黑色大理石,像两双手弹奏钢琴的黑键。他们走了一节楼梯,又走一节,再走几节。最后来到顶楼。这里不错。阁楼上的房间小,有个倾斜的顶,高处人能好好走路,最低的地方假如摆张书桌,人走近那儿离开那儿都要弯腰,坐在书桌跟前会坐得牢,能好好写。他由衷感谢,是工作的好地方。
当初梧桐树还不够高,要从阁楼连下两层楼,从那层楼的走廊窗前恰好平视树顶。从树顶再走下一层楼,到了观赏梧桐树高枝的最佳楼层,走廊最靠里是茶歇室,他以乔迁新居报答房东的心情,赠送出版社一台中档咖啡机,就摆在那里,用它替换掉了可怕的速溶咖啡。不同品质的咖啡豆,他也曾提供过很长一阵。每天下午,当写出点什么后,他下楼做一杯咖啡喝,物物交换似的吃茶歇室常备的小饼干。因为咖啡需求量大,出版社后来自购豆子,那不合他口味,他便不来喝咖啡,但仍来吃小饼干,还有彩色软糖。在楼梯上,在饼干和软糖附近,编辑们和他闲聊,双方都清楚一些话题不要谈:今天写了多少字?已经写了多少字?哪一天会写完?编辑们的共识:随便他,急也没有用,谈了会尴尬。他们不太诚恳但求客气,聊聊真实的天气和文坛的气象,便去各忙各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