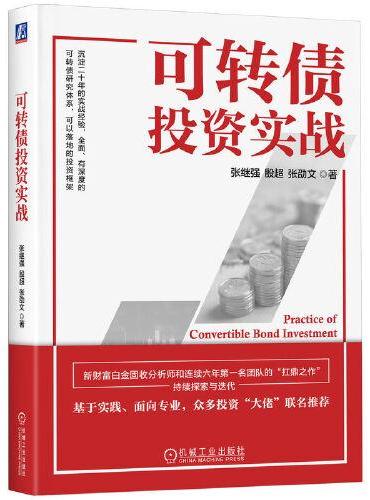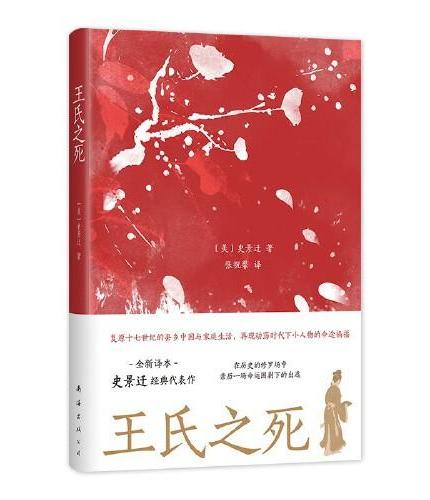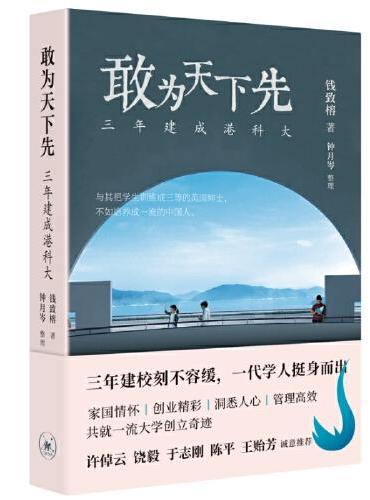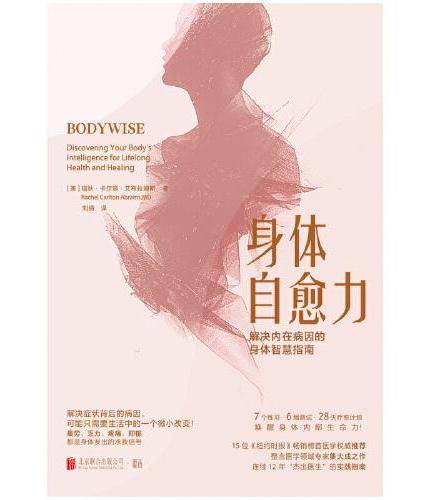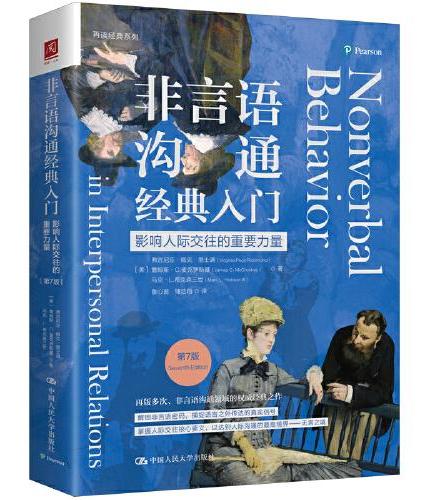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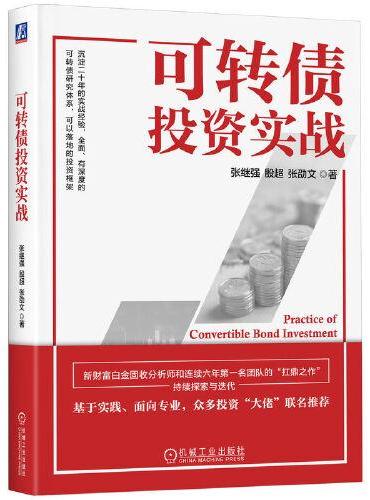
《
可转债投资实战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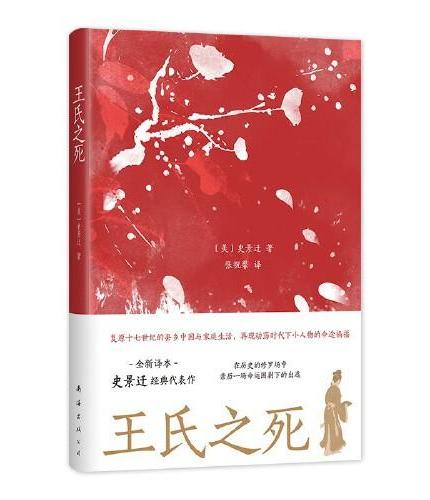
《
王氏之死(新版,史景迁成名作)
》
售價:NT$
2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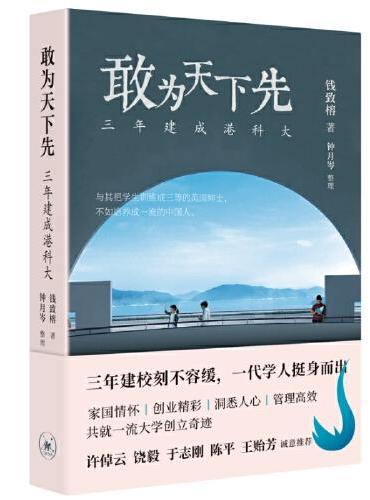
《
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
》
售價:NT$
352.0

《
直观的经营:哲学视野下的动态管理
》
售價:NT$
407.0

《
长高食谱 让孩子长高个的饮食方案 0-15周岁儿童调理脾胃食谱书籍宝宝辅食书 让孩子爱吃饭 6-9-12岁儿童营养健康食谱书大全 助力孩子身体棒胃口好长得高
》
售價:NT$
2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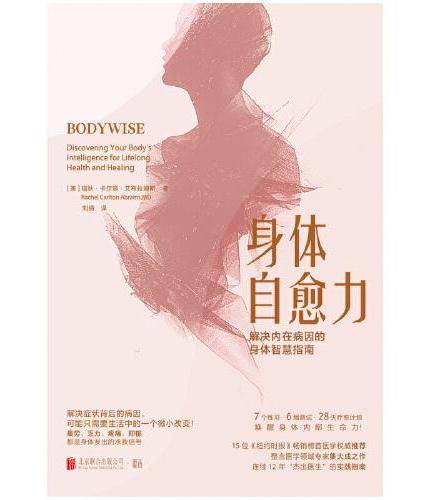
《
身体自愈力:解决内在病因的身体智慧指南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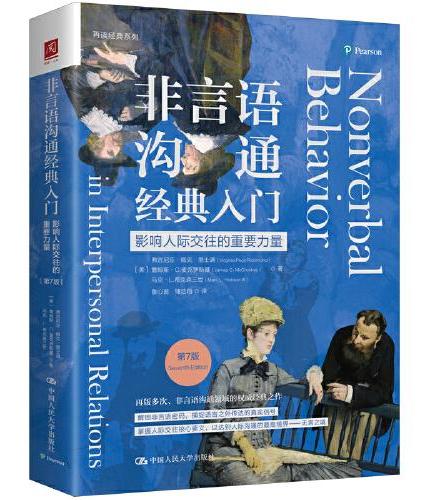
《
非言语沟通经典入门: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力量(第7版)
》
售價:NT$
560.0

《
山西寺观艺术壁画精编卷
》
售價:NT$
7650.0
|
| 編輯推薦: |
|
教育部新编人教版八年级(上)语文教科书自主阅读推荐。
|
| 內容簡介: |
|
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是迄今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悲惨的一页。作者当年赴唐山参与了抗震救灾活动,以其亲身经历和感受,全景式地真实记录了这场大地震和在大载重的人们,也留下了许多思考,使得这场灾难在更广阔的时空获得了更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注。本书也成为当代中国反映重大的自然灾害的*有影响的经典作品。
|
| 關於作者: |
|
原《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1998-2001)。2004年以来,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主任。他是资深传媒人,上世纪80年代是解放军报记者,中国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家之一;90年代是传媒领军人物,曾参与创办《三联生活周刊》、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策划。代表作品有《唐山大地震》(1986)、《海葬》(1989)、《大清留美幼童记》(2004,与胡劲草合作)、《旧闻记者》(2005)等。
|
| 目錄:
|
目 录
序
我和我的唐山(1986年版前言)
第一章 蒙难日七二八
3时42分53.8秒
大自然警告过
目击者言
濒死的拂晓
第二章 唐山广岛
红色救护车
陡河!陡河!
开滦!开滦!
目标──唐山
剧痛中的城
天上地下
抢夺生命
第三章 渴生者
3天: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
8天:小女孩王子兰
13天: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
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
第四章 在另一世界里
宾馆
看守所
精神病院
盲人居住区
40次列车
第五章 非常的8月
罪恶能的释放
推开瘟疫
方舟轶事
政治的1976
第六章 孤儿们
3000:不幸的幸存者
我和我的小拖拉机手
张家五姐弟
第七章 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饿死他们! 疼死他们 枪毙他们!
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
备忘录(一)
备忘录(二)
历史记着他们
我的结束语
附录
《唐山大地震》和那个十年
纪念我的蒋叔叔
|
| 內容試閱:
|
2008年,两位从汶川回来的记者,请我在一本蒙着尘土的旧杂志上签名。这是1986年3月号《解放军文艺》,整本刊登了《唐山大地震》。我谢谢他们找来这件出土文物。文物是戏言,出土倒不假。因为汶川,许多人想起遗忘已久的唐山。如今,汶川的记忆也已差不多被岁月掩埋了。不同年代的故事,一层层相叠。新的痛楚覆盖了旧的创伤,旧的悬疑又被新的追问覆盖。读者遇到此书,可能是在唐山地震40年后,也可以是在50年、60年后。书中的一切,包括叙述风格,可能与新的读者逐渐疏远。他们能否理解1976?他们怎样看1986?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1986年,《唐山大地震》发表。前者发生在文革末期,后者发表于80年代改革中期,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关键一年。自然灾害和社会演变有关联,但没有简单的因果律。将两者连在一起的,是人。唐山地震发生时,文革已近尾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全面专政的口号飘荡在废墟上。作为一名军中文学青年、上海文学杂志《朝霞》的工农兵编辑,我参加了抗震救灾。但那时我绝无可能写这样的《唐山大地震》。十年后,时移世易。还是那场灾难,但人们对灾难的态度,人们对人的态度开始改变。1976到1986,是浩劫后,在精神废墟上开始清理和重建的十年。我亲历了这种清理和重建,感受了它的艰难。我走进职业新闻队伍,走进报告文学队伍,告别虚矫,学习诚实面对现实和历史,包括重新搜集整理唐山地震资料,重新审视这场灾难。居于灾难核心的是什么?是人。是人性。是人的悲剧,而非被意识形态所需、所用的其他。这是常识。但常识的确立不容易。这本身是一个痛苦的历史过程。《唐山大地震》已成为史料。这本书记录了1976,也留下了1986的印记。1976年唐山人、乃至中国人的命运是一种真相;1986年一个中国记者的思考与写作状态,是另一种真相。因为这个原因,本书再版时除了订正事实错误,对1986年的文字(包括十年这样的时间概念)未做改动。1986年初版的《唐山大地震》,由我的老师、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怀中先生作序。他写道:钱钢是把《唐山大地震》作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毕业作品来写的。这当然不只是一份考卷,而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心理学家为我们整个星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一部关于蒙受了不可抵御的灾难的人的真实记录,也留下了他的许多思考和疑问。200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再版此书,我在序言里说:我没有看清前面的一切。对无数的悖论,我没有答案。但我相信,答案埋藏在20世纪最惨烈灾害的废墟里面,埋藏在我曾经目睹、曾经记录的历史里面。这仍然是我今天想要说的。
钱钢2016年4月15日写于香港大学
无疑,唐山是属于我的。如果说,十年前那个脚蹬翻毛皮鞋、肩背手压式喷雾器、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的23岁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生活已经把一片可歌可泣的土地交给了他,那么,今天当我再次奔赴唐山,并又一次挥别它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和我的唐山已经无法分开了。不久前,我和朋友们在新华书店看见了一本《世界历史上的今天》。出于什么呢?我立刻把它取下书架,几乎是下意识地,随手翻到了那一页。是的,那是一个注定要用黑色笔填写的日子──7月28日1794年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和圣朱斯特被处死1914年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此 开始1937年日本占领中国北平1973年法国在穆鲁罗瓦珊瑚礁进行第二次原子弹爆炸1976年中国唐山市发生大地震我又看到了我的唐山。我的灾难深重的唐山。我的伤痕累累的唐山。我的在大毁灭中九死一生的唐山。唐山大地震,它理所当然地要和世界历史、人类发展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同被人类所铭记。唐山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忌日。这些年,每当7月28日凌晨到来的时候,唐山街头就有一些人影在晃动着。悄寂无声中,亮起的是一小簇一小簇暗红的火苗。火光里映出的是一双双怆然的眼睛──老年人的,中年人的;也映出了他们手中一张张点燃着的纸钱:我儿收爱女收父母大人收晨曦中,淡黄色的纸钱化作的烟,由絮絮缕缕渐渐融合成一片,如白色的雾,浮动在新建的高层建筑之间。纸灰在雾中飘浮着,它们是孩子眼中一只只神奇的黑色蝴蝶,飞得很高,又缓缓飘落,落在路旁草丛中,落在伫立街头的老太太们的银色鬓角上。她们没有拍去它,她们的眼睛在痴痴地望着大地,不,是在望着地底下的那个世界;老人的嘴唇颤动着,在喃喃地诉说什么。我曾不止一次走过那些飘飞过纸灰的街心。我理解,在唐山,七二八地震的死难者们是没有坟场的;那些高楼下的十字路口,那些窄小的老巷,那些在地震后重新堆起的小山,甚至刚刚圈定的厂房新址,都是他们无碑的墓地。十年前,他们就是在这些地方,被房梁砸倒、被楼板压碎、被瓦砾和落土活活窒息的。十年后,废墟已不复存在,然而我认得出一切。我走着,从路边栽着拳头粗的小树的新修的干道,走向老树夹径的狭窄的老街。是一个无月的夜晚,我独自漫步在一条十年前曾去过的小路上,忽然发现,路灯下那一棵棵高大的老白杨,通体银白,闪着奇异的光。这些在大地震中,曾像浪中船桅一样剧烈摇荡过的老树,这些曾目睹过当年一幕幕惨状的老树,它们至今还在默默地、忠实地守护着什么呢?那一根根形状弯曲的枝条,使人想到它细密的根须。十年来,老树的根须一点一点地伸向死难者长眠着的大地深处,是在为地上和地下、生者与死者传递着什么音讯吗?唐山大地震,是迄今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中国地震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的震撼》一书,向全人类公布了这一惨绝人寰的事实:死亡:242769人重伤:164851人每当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的心便会一阵阵发紧。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8.2级大地震的情景是极为可怖的,强震引起的次生灾害──大火几乎焚毁了半个东京,死亡计10万人。1960年5月22日智利8.5级大地震,引起了横扫太平洋的海啸,巨浪直驱日本,将大渔船掀上陆地的房顶;这次地震的死亡者,总数近7000人。还有1964年3月28日美国阿拉斯加8.4级大地震,冰崩、山崩、海啸、泥喷,总共使178人丧生。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它们意味着: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是举世震惊的东京大地震的2.4倍,智利大地震的35倍,阿拉斯加大地震的1300多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字背后人的悲惨命运。人们尽可以用数十亿美元、数百亿美元来计算物质财产损失,可是又能用什么来计算人的损失呢?活生生的人是无价的。太难了,要想忘掉那一切是太难了。不久前我访问过一位唐山妇女。在她家,她给我端出水果和糖,出于礼貌,我请她也吃。她却连连摇手:不,不!她说,大地震后,我就没吃过一点甜的东西她告诉我,她是在废墟中压了两天两夜之后被救出来的,出来后吃的第一样东西,是满满一瓶葡萄糖水。从此,一切甜的东西都会使她产生强烈的条件反射。苹果、橘子、元宵、年糕,甚至孩子的朱古力,这一切都会唤起她十年前在废墟里渴得几乎要发疯的感觉。我不能沾甜的东西,我受不了!十年了,苦涩的滋味一直没有离开过她,一直没有经过地震的人,都像害过了一场病。另一位妇女对我说,我一到阴天,一到天黑,人就说不出的难受。胸口堵得慌,透不过气来,只想喘,只想往外跑她不止一次这样跑到屋外,哪怕屋外飘着雪花,刮着寒风,任丈夫怎样劝也劝不回来。她害怕!她是压在废墟中三天后才得救的,她至今还牢牢地记着那囚禁了她三天的漆黑的地狱是什么样子。平时只要天气变暗,当时那恐怖绝望的感觉又会回来,令她窒息。十年了,是什么无形的东西还在残忍地折磨着这羸弱的女人呢?你,一位中年教师,语调十分平静,平静之中又透着说不尽的酸楚:那些伤心的事多少年不去想它了,忘了,都忘了。真的忘了吗?当年,为了救出你的爱妻,你曾在废墟上扒了整整一天,是一场大火最终将你的希望断送。你告诉我,妻子是活活烧死在那片废墟中的,你当场晕了过去。怎能够忘记啊!那是一场可怕的火。采访中,曾有人捋起衣袖,指着臂膀上的疤痕对我说,大火烧化了亲人的尸体,这是滚烫的人油烫的痕迹还有你,老军人刘祜,我在你那冷清清的家里坐着,看着你竭力作出的轻松的笑,我真想哭。地震前的那天晚上,我出差在天津,夜里十来点钟还跟家里通了电话,是小女儿接的,她问:爸爸,我要的凉鞋你买好了没?我说:买好啦。她又问:是银灰色的吗?我说:是的!她问我好看不好看,还要我快快捎回去你说不下去,老泪顺着满脸的皱纹往下淌。十年了,你至今还珍藏着那双银灰色的小凉鞋,像是珍藏着女儿那颗爱美的活泼泼的心24万生灵仿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离去的。1200人中有400人遇难的陆军二五五医院,是我这次去唐山的住处。医院有一个小灵堂,保存着部分遇难者的骨灰盒。当我走进那间点着昏黄小灯的屋子时,我的胸腔立刻被塞紧了。所有骨灰盒上的照片,那一双双眼睛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一个扎小辫的女护士,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戴着一顶有檐帽,胸前还有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一切都带着那个年代的烙印,只有她那楚楚动人的笑容是超越时间的,以至于十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说她曾把什么照片送给自己的恋人,那一定就是这一张。有一个戴鸭舌帽的极可爱的大眼睛男孩,我简直不忍心正视他。他的骨灰盒上,放着一个小小的花圈,挽带上写着:韩冶安息。你的爸爸妈妈旁边还有一个小花圈,上面是同样的字迹:韩松安息。你的爸爸妈妈他的弟弟,一个更小也更讨人喜欢的男孩。失去了这样一对可爱的孩子,我很难想象他们的父母是在用什么来支撑自己的生命和感情。失去的是太多了。在小灵堂里,我不仅看到了一行行泪写的字,而且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些可怜的父母们凄婉而不绝的呼唤。在一个小女孩的骨灰盒上,有一包剥开锡纸的朱古力,朱古力都化了。可怜的孩子!也许生前她并没有尽情地吃过她所爱吃的东西,但一切都已不能再挽回。这就是大自然强加给人间的悲剧!灵堂里还有一个特制的大骨灰盒,由一大三小四只骨灰盒组成。这真是一组特殊的图案,它出自一位父亲的手,象征着人间失去了一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我无法想象,孩子们的父亲在亲手制作这只骨灰盒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孩子们都依偎在母亲的身边去了,独独扔下孤寂的他;究竟是死去的人更不幸,还是活着的人更不幸呢?灵堂外是一座小山。那是震后清理废墟时,用整个医院的断墙、残壁、碎砖、乱瓦堆成的。山上有石阶,有凉亭,有嬉戏的孩子是那些未经过灾难的震后出生的孩子。石缝间,偶尔伸出一截截锈蚀的金属,那是十年前折弯、拧断了的水管、暖气管;站在它们旁边,我仿佛置身于一片死寂的黑色的洋面上,倾听着极深极深的大地深处传来的种种属于人的微弱的信号。常常地,于寂静之中,我会突然听到自己的脚步又重新踏上昔日废墟上的声音,听到那些埋在地壳深处的24万活生生的灵魂的气息,他们诅咒、叫喊、哀求和呻吟;他们在生命被撕裂的那一刻,尚未来得及去思、去想、去躲、去避,就被活活地剥离开了那个光明的世界,成了这地心深处大自然牢狱的终生禁囚。我又想起了灵堂中那些无辜的天真的孩子,也许因为他们的存在,致使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痛苦地抽搐着。这就是我的唐山。十年前,当我一个未谙世事的青年,从平静的生活中一步跨到了堆满尸体的废墟上时,我只是感受了什么叫做灾难。尽管住在灾民的小棚子里,帮他们领救济衣、救济粮,排长长的队领一小桶水;尽管参加了护送数百名孤儿转移他乡我只是感觉到自己像在一夜间长大了,却还没有理解生活的底蕴。而这次重回唐山,我忽然觉得,自己懂得些什么了是的,与那24万蒙难者相比,与唐山目前依然存活着的人相比,我的确是来自另一世界的人。我仿佛第一次从灾难的角度观察我的民族、我的同胞、我的星球。这是残酷的,也是崭新的。如此惊人的灾变,如此惨重的浩劫,如此巨大的死亡和悲伤,我已经不能用正常的规范来进行思维。那些美丽得令人伤心的东西,那些亲切得令人肠断的东西,那些坚硬得令人发抖的东西,那些弱小得令人渴望挺身而出的东西,一切属于人的品质都俱全了。这就是我的唐山。1985年的春节,我是在唐山度过的。除夕那天一早,我就听见噼噼啪啪的爆竹声,过午,那声音更响,及至薄暮,满城的爆竹声已密得分不出点儿来,整个天空都被映得通红!我看见高楼上、大路口,那些年轻人正一个接一个地点燃挂鞭和烟花:闪花雷、菊花雷、银龙吐珠、五献花,听不见轻松的笑声,只是不停地放,放。我觉得那震耳欲聋的炸响声中,饱含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十年前访问过的那位在废墟中压了13天的卢桂兰大妈,邀我去她家包饺子。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爱女的孤独老人,似乎把我当成了唯一的亲人,她一口一个孩子,喊得叫人心痛。我要走了。拿起提包,忽然感到那么沉。原来老人在里面塞了半包玉田小枣!我提着沉甸甸的包,在唐山的街道上走着。满地是爆竹的碎纸,空气中飘着火药的甜香。我的心沉甸甸的。除夕的唐山,光明和黑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新建区灯火辉煌,而那些尚未推倒的防震棚里,只有暗暗的灯光。但那里有着真正的人间的气息,正如我这沉甸甸的包里装着的卢大妈那颗母亲的心。在文化路路口,我停住了脚步,我又看到了十年前看见过的那一株株老柳树。当年,树下是聚集尸体的地方。老柳树枝条仍然不动,仿佛在此起彼落的爆竹声中沉思着历史。我的眼睛发涩。人们对这些老柳树的理解,也许远不如它们对人的理解呵。24万人无疑是一个悲哀的整体,它们在十年前带走了完整的活力、情感,使得唐山至今在外貌和精神上仍有残缺感。一切似乎都逝去了,一切似乎又都遗留下来了。仿佛是不再痛苦的痛苦,仿佛是不再悲哀的悲哀。正是这一切,促使我用笔写出我的唐山。我要给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医学家、心理学家,不,不光是他们,还有人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留下关于一场大毁灭的真实记录,留下关于天灾中的人的真实记录,留下尚未有定评的历史事实,也留下我的思考和疑问。这就是我的心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