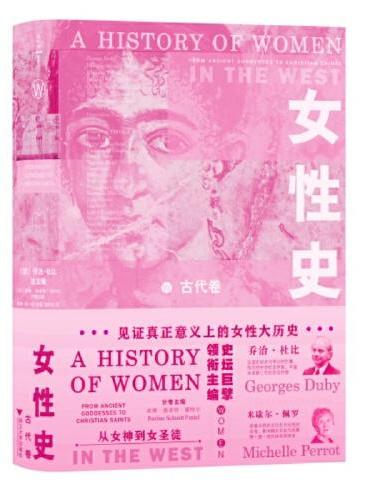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成吉思汗传:看历代帝王将相谋略 修炼安身成事之根本
》
售價:NT$
280.0

《
爱丁堡古罗马史-罗马城的起源和共和国的崛起
》
售價:NT$
349.0

《
人生解忧:佛学入门四十讲
》
售價:NT$
490.0

《
浪潮将至
》
售價:NT$
395.0

《
在虚无时代:与马克斯·韦伯共同思考
》
售價:NT$
260.0

《
日内交易与波段交易的资金风险管理
》
售價:NT$
390.0

《
自然信息图:一目了然的万物奇观
》
售價:NT$
6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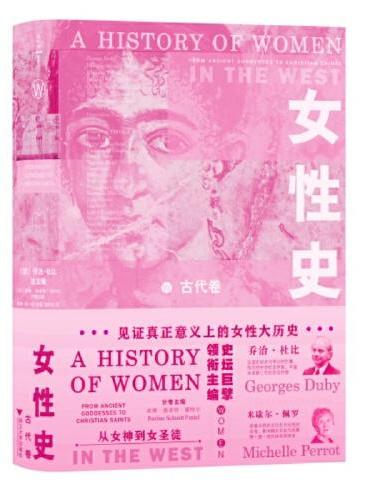
《
女性史:古代卷(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大历史)
》
售價:NT$
560.0
|
| 編輯推薦: |
《天赐》:关于祖父的故事,带你重回故乡那个回不去的地方。
《字戒》:当艺术与官场碰撞,当廉洁遭遇挑战,这仅是一场风花雪月的幻象?
《神医》:神医是实力派还是一个小人物的生存之道?真实又可叹。
《断指》:一个包子引发的血案城管来了,他怎么办?
《悯生》:地震之后的人间万象,撕裂隐秘的人性真相。
十九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记录一群小人物的生存秘史,总有一个故事触动你的悲欢。
冰心散文奖汪曾祺文学奖金奖老舍散文奖获得者凸凹历时十年创作修改,再现京西风土人情与人性之真。
小人物与官场、文学与艺术、体制内外的碰撞多元素的冲击,高潮迭起的讲述,触摸大时代的中芸芸众生的真实温度。
一部书写乡土中国隐秘真相、透视小人物们生存悲欢的呕心之作!
老舍文学奖获得者宁肯评价:凸凹呈现出的乡村与莫言、贾平凹、刘震云们笔下的乡村颇为不同,大的不同是凸凹的写作没那么多的文学观念,他延续的是中国化的中国乡村知识分子文脉。
|
| 內容簡介: |
《在场与及物》系著名作家凸凹的中短篇小说选。所收小说,曾在《十月》《当代》《大家》《花城》《长城》《中国作家》等核心文学期刊上发表,许多篇目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及中国作协创研部年度*小说选载,在文坛和读者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这些小说,描绘了北京京西的历史、风情、传奇,是京味文学的*收获。小说风格独具,人的欲望和土地上的生态浑然交融,既描摹世象,又揭示人性,耐人寻味、撼人心魄,与果戈理描写乌克兰风情的经典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有相同的品质。虽是地域的,却是民族的,是解读当下中国农村、农民,对国民性进行反思的形象读本。
小说的语言既有京西民间的幽默风趣,又有拉美小说的神秘荒诞,更有汪曾祺小说的妩媚品质,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
| 關於作者: |
凸凹,本名史长义,著名散文家、小说家、评论家。1963年4月17日生,北京房山佛子庄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联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房山区文联主席。
创作以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为主,已出版著作三十余部。著有长篇小说《慢慢呻吟》《大猫》《玉碎》《玄武》等八部。著有散文集《以经典的名义》《风声在耳》《无言的爱情》《夜之细声》《故乡永在》等三十部,出版和发表作品七百余万字,被评论界誉为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北京农村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作家。
近六十篇作品被收入各种文学年鉴、选本和大中学教材,作品获省级以上文学奖三十余项,其中,长篇小说《玄武》获北京市建国六十周年文艺评选长篇小说头奖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散文获冰心散文奖、第二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老舍散文奖、全国青年文学奖和十月文学奖。2010年被评为北京市德艺双馨文艺家,2013年被授予全国文联先进工作者称号。
|
| 目錄:
|
序一:在场与及物的乡村文学 宁肯
序二:北京乡土文学的扛鼎之作 邱华栋
本纪
天赐
悯生
无为
世象
温暖
端庄
断指
淘金
皮实
神医
字戒
欢悦
顺生
混沌
银音
心史
美满
同谋
小米
晌熟
落寞
后记:温暖的书写
|
| 內容試閱:
|
序一:在场与及物的乡村文学
宁肯
忘记是谁说的了,大意是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作家就要去读他的作品。这话不错,我在凸凹身上有深刻体会。与凸凹相识想来也有十年,十年间或出行,或开会,或饭局,可谓见面多多,聊天玩笑多多,自认是很好的朋友。但我也必需承认,我读凸凹的作品不多,印象较深的是他的一些散文。他的散文真诚、坦荡,笔端不时流露出别人往往倾向于隐藏的最真实的东西,因而富于震撼力。有几次这种震撼差一点让我打电话给他,说说我的阅读感受,但最终没有。我以为对朋友的欣赏最好珍藏起来,这样见面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但是我对凸凹的小说却一直有点隔,也不知为什么,过去也没怎么多想,好像是因为叙述方式,又好像是因为语言方式。小说不同于散文,散文是直接的艺术,比较容易让人接受,比较容易打动人,小说是间接的艺术,并且稍有不慎叙述便容易程式化,所以语言上或叙述方式上如果不是特别有一望而知的出新感,便不容易让我接受。这是一种相当苛刻的甚至固步自封的阅读习惯,此种阅读习惯不仅让我错过了凸凹,显然可能也让我错过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其实,只要克服一点点自我的阅读习惯,只要再往前跨一步,就会有惊喜的发现,并感到过去的自己是多么的一叶障目、固步自封,最近读凸凹的中短篇小说集《在场与及物》便有这样的感慨。
一册厚厚的中短篇小说,掩卷之后,觉得愧对凸凹,这么多年,这么独到的小说过去怎么就一直视而不见?虽说是金子迟早要发光,可埋没金子终归是一种罪过。我们常常感叹世间好的东西总是被埋没,我们却很少问问自己是否也在加剧这种埋没?甚至没埋自己身边的人?不能用存在主义人是无法沟通的他人即地狱这种形而上的观点开脱自己,应该认真反思自己。
在我看来凸凹的小说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语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二是叙述上开创了一种他独有的杂文随笔风格,三是在乡土文学中他几乎以一人的力量和个性传承了中国文化--一种在民间代代相传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文化。
凸凹自称特别崇尚两个人的语言,一是汪曾祺,一是孙犁。此二人最大的特点是中国气派:简至,意境,唯美,阴柔,而简至(主要是由简短的有节奏感的断句、语感、语气构成)在我看来则是首要的,没有简至,后面的三种审美都不能成立。简至甚至是中国文化中国特色的前提。凸凹在本书的后记中说:在中国当代文坛,汪曾祺老先生的文字,是镶嵌到我生命中去的,他的著作,是我的枕边书,每日耽读与揣摩,从无中辍,我把他当父执人物。可见凸凹受其影响之深。但事情的吊诡往往在于,我们崇尚的正是我们所缺的,所缺必导至学习揣摩,结果却往往是得了真髓,却并不似所学之人,成了另一种东西。在我看来,凸凹的语言除在简至上得了汪曾祺的真髓,其它都不像汪曾祺,也不像孙犁。凸凹的小说既不意境、也不唯美,更不阴柔,相反,在简至统摄之下,倒有一种阳刚之气,山野之气,俚俗之气,因为简至,这些本不文化的气息反倒有了一种神奇的文化味道。这种文化味道在中国鲜有,是凸凹所独有的,我认为是完全可以与汪曾祺、孙犁简至之下的意境、唯美、阴柔对话的。事实上在作品内容的广度与宽度以及复杂度上,凸凹比自认的师承还要更有力量,更浑厚,更贴近现实,用现在批评家时髦的话说:就是更及物。
试举一例:《天赐》一文中描述祖父特点:
他对女色无所用心,整天赶着一群羊往山上跑。累了,就躺在草地上,唱歌。那山歌的词句很不完整,词意也暧昧,他高一声低一声地唱,很任性,却不动情。
几句简至的话,简至的节奏,就把一个山野之人勾勒得异常清晰,与汪曾祺不同,与孙犁不同,却又有联系联系者,简至的味道也。
凸凹小说第二个特点是杂文随笔风格,这点也不同于汪孙二人,这使凸凹在小说的文体上有了一种可贵的拓展。关于这一点孙郁先生的论述已非常到位:凸凹的小说不饰铅华,有乡土的东西,也有学问的东西,九曲回肠,像诗,像随笔,像风情绘,又像戏剧,小说在他那儿成了很灵性、很自我的存在。最典型的是《悯生》,写了四种死,在一个短篇里写四种死本身已有随笔的行文方式,而每种死之后作者都要品评几句,比如写堂大伯的死,作者便作结说:生死契阔。这是鲁迅杂文里说的。堂大伯的父亲虽然跟鲁迅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是我的曾祖母――他的母亲,已把一些关于生死的信息通过血液传递给了他,他不仅学会了听天由命,而且还学会了给无奈找出让自己确信不疑的理由。这样在小说里把鲁迅抬出来议论的写法,完全是一种杂文随笔的风格,但它又是小说,因而让人耳目一新。
凸凹的第三个特点最为复杂,与前两者有关,与小说内容有关,更与凸凹没完全离开乡村有关,与他始终在场――在乡村的场中有关。当今中国文坛存在着强大的乡土文学,亦存在着强大的乡土作家群,如贾平凹、阎连科、莫言、刘震云、毕飞宇、余华,可以说数不胜数,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乡土,离开了本位,是离开乡土之后写乡土。他们呈现的早年的乡土或唯美、或抒情、或批判、或魔幻、或血腥、或荒诞,总之是回望式的加入了观念性的写作,是站在城市化的文学视角观照乡村,抒写乡村。凸凹无疑是乡土作家,但凸凹与上述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他始终没离开自己的乡土本位。
凸凹是京西农民的儿子,当过乡长,后来成为了作家,当了当地的文联主席,虽说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也住在小区楼房里,但无论感觉上还是切近的地理位置上,凸凹都没感到自己离开了乡村本位,始终觉得自己是农村人、是农民,他也经常把这话挂在嘴头上。批评家施战军曾把乡土文学与乡村文学做了区分,认为两者是不同的,前者通常是回望式的或观念性的写作,后者则是在场的写作。他认为师陀虽也写乡村,但不能划作乡土作家,因为师陀的乡村不是回望的、外视角的,而是原状的,是乡村本身所固有的,没有许多文学观念的观照。这样说来,凸凹的所谓乡土写作显然也应归为乡村写作。
确实,从作品的面貌来看,凸凹呈现出的乡村与莫言、贾平凹、刘震云们笔下的乡村颇为不同,而最大的不同是凸凹的写作没那么多的文学观念,他延续的是中国化的中国乡村知识分子文脉。他叙事状物的立场是乡村知识分子的立场,因此他的小说里没有观念意义上的魔幻、荒诞、残酷、暴力美学,有的是在场的乡村生活本身――其间流淌着源源流长的中国文化底蕴。换句话说,在凸凹的小说里几乎看不到西方小说的影响,甚至连点影子也没有,有的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乡村经验的写作。不仅如此,凸凹的小说也没有回望式的唯美与意境的影响,换句话说与他所崇尚的汪曾祺、孙犁也有质的区别。
凸凹是一个客观的乡村知识分子、乡村作家,而非乡土作家。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一是《神医》,一是《字戒》,它们都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性的标志:一是中医,一是书法,并在两个典型符号中寄予了个人命运的起伏,同时又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小说中有乡村文化、乡村政治,个人在文化中的命运际遇、善恶互现、夹缠曲折,异常深刻,异常本色,异常中国,异常文化,让我们看到千年文化一脉相承的东西。应该说传统中国文化与其说在乡村积淀着,不如说在乡村知识分子身上积淀着,古时候文化体现在乡坤身上,现代以后特别是经历文革之后,则薄弱了很多。而凸凹以文化之身坚守乡村现场则是一个特例,他写作,并始终在场,这使他不易受到西方浅显文学观念的影响,而可以完全基于乡村本位写作。
其实凸凹是读了大量西方经典文学的,功底异常深厚,但由于他是在场的,西方的影响总是被现场的生活经验以及所含的中国文化所纠正,并在他的作品中化为无形。《神医》表面上很难让人想到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因为完全是中国化的作品,但往深里想还是可以看到卡夫卡来自远方的照耀。《字戒》与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看起来毫不相干,但某种借助物的架构,在物中寓意人的一生与戏剧化的生活,不又是异曲同工吗?凸凹是非常狡猾的,他的视野当然不只是他的乡村,不只是中国,只是他把更大的视野在他的乡村中化为了无形。凸凹作品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们是在场的,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2010年10月10日初稿,2016年4月6日定稿
序二:北京乡土文学的扛鼎之作
读凸凹中短篇小说集《在场与及物》
邱华栋
前些年凸凹的长篇小说《玄武》出版之时,我曾情不自禁地说过,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凸凹是北京地域文学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符号性存在。《玄武》气势恢宏,纵横捭阖,接续了由鲁迅开创的中国乡土文学的大文脉,是一部史诗性作品。我的判断后来不断得到验证当代很多评论家几乎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解玺璋就认为《玄武》一反已有的政治划界、田园牧歌等固有样式,开创了一种深入土地内部,本真呈现人的生存的新的写作范式,具有划时代意义。白烨也把《玄武》和蒋子龙的《农民帝国》,一道列入了2008年度农村题材的代表性作品。陈晓明在《南方周末》中也称《玄武》有全新品质,值得关注。更让人惊喜的是,建国六十周年北京文艺评奖,《玄武》一路破关斩将,一举摘得了长篇小说的头奖,凸凹也勿庸置疑地获得了北京本土代表性作家的地位。
待我读到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在场与及物》,他的创作实力和勤奋更是让我感佩不已。
我一直以为,长篇小说的成功,基本上是取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靠题材取胜,也要靠结构艺术,形式和内容最好完美结合。而中短篇更是接近于刀锋一样的写作,大多要靠怎么写立身。怎么写,是文学技巧的运用,更是艺术品质的呈现。所以,我对他的《在场与及物》,在阅读上是更加用心的,而且还带着几分挑剔的目光。读过之后,对他的叙事技巧与能力我心悦诚服。在小说创作普遍推崇技术至上主义的风潮下,凸凹的《在场与及物》以足够的自信,进行了一种反其道而行的朴实叙事,描写小人物的常态生活,揭示出人性最本质的部分内心的温柔,足可以抵御外界的崚嶒与浇薄;精神的自守,足可以冲破物质的包围与挤压生活的美好,最根本的,是取决于人的精神驱动和人性之善。《在场与及物》从始至终充满了温暖、和谐的色调,让人从内心里生出欢悦,感到阴霾里仍有明媚的光。对于文学当下的处境来说,《在场与及物》更像是对崇高人性的一次次凭吊,它的理想主义色彩让人心绪激荡,因为它如此鲜明地映衬出文学与人间生活在现实中的隔膜,以及人们对于诗书之美的漠然。它也涤荡了当下小说的阴私之气,表现出了对世道人心抚慰和浸润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是当下小说中难得的一抹亮色。
小说集中的作品,整体淡雅,叙述从容,语言俊洁,其氛围、气韵、笔致以及语调都有汪曾褀之风,但与汪曾祺相比,作者不淡化环境、不回避现实,表现出在入世中出世的全新品格。因而就具有了时代的光泽和指归。可以说,《在场与及物》是对汪曾褀叙事传统的弘扬与拓展,具有独特的文本贡献。
进一步说来,凸凹的小说是土地上的生命叙事,能让读者找到自己的来路虽是讲荒山野土,蛮人陋事,却是人性生成和繁盛的地方。在阅读的同时,作品能够把读者带入共同生活的状态,因而建立起一种在无罪之罪中承担共同犯罪之责的文学伦理。
王国维认为,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悲剧又有三种之别
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固有故也
我看凸凹的小说呈现的就是这第三种悲剧。一切的悲情与怨事,都非由蛇蝎之人所造成的,也非盲目的命运使然,而是由乡土中的每一个人共同制造的他们都不是坏人,也根本没有制造悲剧的本意,他们只是本分地扮演着生活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每个人都有为何如此行事、如此处世的理由,每个人的理由也都符合社会确立的人情与伦理一切都是顺乎自然的发展,无可无不可,无是也无非,既无善恶之对立,也无因果之轮回;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状况下的无罪之罪,这些通常之人情,毫无预谋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
以中国的叙事传统,即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陈旧模式作比,凸凹提供了一个超越是非、善恶的道德评价,而进入到经验的内部、人性的深度的全新文本。他的文字,有很深的情理,然而却是家常的。正因为是家常的,便有了质朴而准确的价值趣味,即人性之真。
凸凹在长篇小说《玄武》的跋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每束阳光都有照耀的理由!这实际上是解读他作品的一把钥匙,他的写作追求,就是要用最柔软的方式,建立一种道德之上的道德、伦理之上的伦理。
凸凹也曾经跟我说过,一个写作者,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也不是生活的评判者,而是人间信息的记述者和传递者,要按照生活的逻辑写作,而不是把自己的理由强加给生活,也没有必要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态,能够准确地呈现人间的真相便是写作的意义了。
所以在凸凹的笔下,乡间人事,既原始又开放,即固守又旷达,既质朴又复杂,既高贵又卑贱,既宽容又褊狭,既正经又淫亵,既善良又恶毒总之,都体现着对生活的照拂与尊重,好像是让天道人心自己说话。
凸凹生活在京西,《在场与及物》中的小说,自然对京西的历史、风情、传奇多有描绘,因而也可以说是京味文学的最新收获。但小说风格独具,人的欲望和土地上的生态浑然交融,既描摹世象,又揭示人性,而且以悲悯的审视和批判为底色,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间的生存状态、情感样相和生活智慧,呈现出特有的文化眼光,与果戈里描写乌克兰风情的经典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有相同的品质。凸凹的作品超越了地域,是解读乡土中国,对国民性进行历史反思的形象读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凸凹作为北京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不辱使命,为北京文学争得了荣誉,也使自己具有了更加鲜明的符号价值。
2010年10月28日一稿,2016年4月8日修订
《神医》节选
范晚吾的父亲范续亭是个大胖子。不能走路,稍多走几步,就大汗淋漓,喉咙里像被塞上了什么东西,喘不上气来。他几乎是个废人。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人们集体在田里劳动,只有他窝在家里。农村人都厚道,从干部到一般群众,都不跟他计较横竖得让他活着吧。大家都悲悯他。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是瘦的,有贴骨肉的那种瘦,即:精干。他一直给地主当长工,卖重力气,吃小米焖饭、咸菜窝头、喝刚打上来的井水、睡榆木板拼成的床。他自然说不上媳妇,躺在长工棚里想女人,想得没出路的时候,就自己解决一回。然后衔着暧昧的恨意,昏昏沉沉地睡去。早晨醒来的时候,全身轻松,卖重力气时,也不以为苦,仅有的一点反抗意识也被汗水冲刷掉了。因为大汗之后,胃口好,吃得更香。
他觉得这就是命运,很好。
解放军从东北打到了淮海,到了后来,连京畿之地都能听到隐约的炮声。在一天晚上,地主突然把他叫进堂房,问他:你想不想要地?
我要地干吗?给你扛活就挺好。他说。
地主摇摇头,像长辈开导晚辈一样对他说:你不能这样疲沓,得有自己的日子。
他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的日子,木在那里。
地主接着问:你想不想当地主?
他觉得稀罕,反问道:我当地主干吗?
地主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废话,哪个长工不想当地主!
这一声锐响吓了他一跳,他求救一般望着对方。
你不能糊里糊涂地混了,得开窍了,地主说,你看,当了地主,就可以雇长工,就可以娶小老婆。
一听到女人,他嘿嘿地笑了起来,含混地说了一句:那就要地。
地主满意地点点头。念你帮我做了这么多年,也算是家里人了,我以赔本的地价卖给你一部分。
范续亭倾其当长工的所有积攒,还向其他长工借了一些血汗钱,置备下了自己的田产。地主的地减少了之后,用不了那么多长工,就让他挑一部分过去。他自然是挑了那些借钱给他的人,算是肉烂在锅里,兄弟主奴,福泽同享。
有了地之后,果然就有了身价,村里开油坊的梅老板把自己的小女儿梅香嫁给了他。梅香丑点,但结实,肥大的脚板,迈步时,能把地皮崴下一块来。长工们都是原来的兄弟,范续亭不好意思板起面孔吆喝,便把管理的差事交给了梅香。梅香会说粗话,可以跟长工们对骂,骂到将要吃亏的时候,她抬起脚来,再不听话,小心我踢你。长工知道她脚底的分量,多是笑着告饶。
那一年的年景不错,到了秋天,玉米饱满得呲牙咧嘴,由于身子重,稳稳地墩在地上,虽风声号啕,远远地望去,密匝匝的庄稼却纹丝不动。油坊老板在地垄上走了一遭,对女婿说:续亭,做就做大了,我油坊有些积蓄,你再多置备一些地。
再去找原来的东家,老地主竟二话没说,割了一半的地给他。结过账,地主有些伤感,叹口气,说:续亭,也就是你,我算是赔血本了。
范续亭抱一抱拳:得罪了。
自己有了粮囤,有了一囤一囤的粮食,范续亭的心境变了他给自己请了一个私塾先生,开始识文断字。他发现自己不笨,庄稼长得慢,可他的文化水儿却涨得快,临近麦收的时候,他居然能连蒙带猜地读县志了。
梅香的肚子也大了起来。
北平解放了,并且改称北京。不久来了土改工作队,评定成分。范续亭被划为地主,原来的东家,居然只定为富农。被斗争的时候,他排在东家前头。一个半辈子给人扛长活的雇农,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地主了?他冤啊!他薅住老东家的脖领,质问道:你老不死的是不是早就听到了风声?
老东家也不示弱,也反过来薅住他的脖领: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同样是在土里刨食的人,谁能预料到外边的变化?这就是命!
范续亭打了一声嗝,他被气淤住了。他瞪了瞪眼,眼前闪出一片碎花,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真是晦气。老东家叹了一口气,脱身而退。但往前走了几步,又觉得不妥,像拖死狗一样,连拉带扯把他弄回家去,对不知所措的梅香说:你好好地伺候他,这个人输不起。
老东家感到很委屈,二话不说,走了。
梅香赶紧给他掐人中。没掐两下,他猛地坐了起来,问梅香:老家伙呢?
走了。
我要告他。他没头没脸地说了这么一句。
有那些长工作证,他居然告赢了。老东家又被重新划成地主。道理很简单,虽然地亩少了,但剥削的历史是抹不掉的。连带的,老东家的姨小舅子(姨太太的弟弟)被降了职。老东家甩地的时候,他的姨小舅子就在队伍上,是淮安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自然是给他透过底的。
但范续亭自己的地主帽子也没有摘掉。虽然没有剥削的历史,土地的亩数在嘛。公家的政策不是泥巴,不能想怎么揉就揉。
范续亭气淤一次之后,坐下了病根,总是打嗝。平抑的办法就是吃东西,一来二去,把自己吃成了个大胖子。老东家却想得开,积极接受改造,无一丝怨气。铲粪、挑担、锄耪,都快六十岁的人了,干这些重体力活,还像个小伙子似的。看到他这个样子,队里人既不欺负他,也不歧视他,相反还有点敬重。他的身块变得像范续亭以前那么精干,而且两眼放光,白髯飘飘,有几分仙风道骨。
他在街上碰到范续亭,吃了一惊:范续亭,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范续亭抖了抖肩,还不都是你害的。
老东家笑了笑,说:谁让你是我的长工呢,不害你害谁?
你真不要脸!对老东家,范续亭一贯是恭敬的,恭敬得心里都起了皱褶,他今天终于可以俩直气壮地舒展一次了。
骂得好。老东家捋了捋胡须,说道,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你心眼小,没有心胸。
范续亭不甘地说:我就是弄不明白,怎么闹来闹去,跟你闹成一个阶级了。
这又有什么闹不明白的?自古咱们就是一个阶级。老东家说了一句玄奥的话。
范续亭更闹不明白了,忧伤地摇头。
老东家拍了拍他的肩,甭想那么多了:走,到我家里去,咱们闹两盅。
闹就闹。范续亭居然没有打愣,跟着老东家就走。
噫,这人一处在低处,就容易和解了。此时的范续亭对老东家竟连一点起码的仇恨都没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