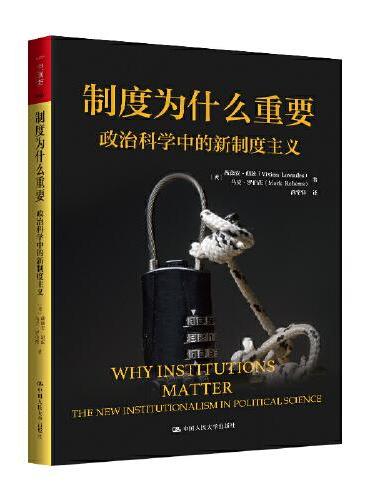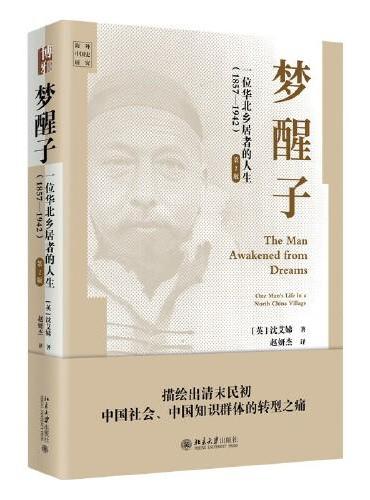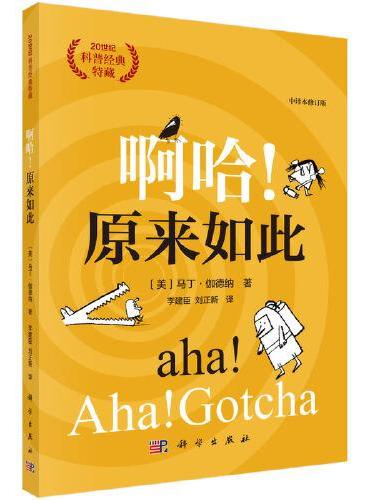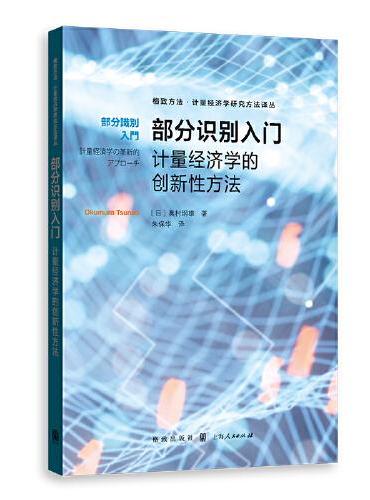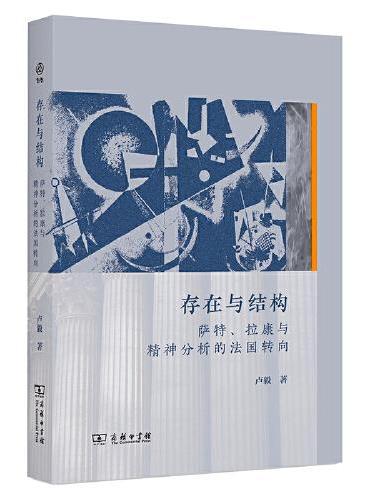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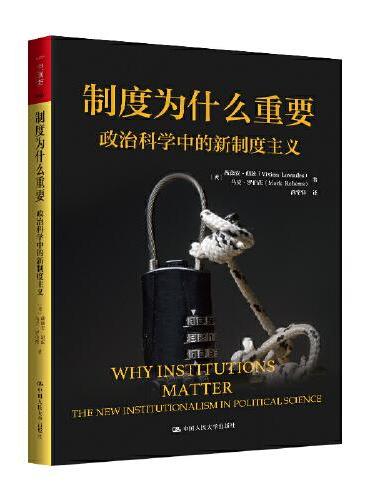
《
制度为什么重要: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人文社科悦读坊)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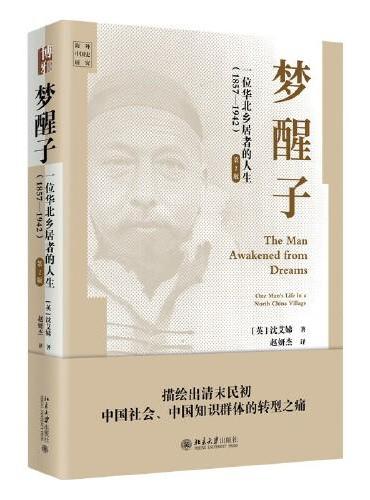
《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第2版)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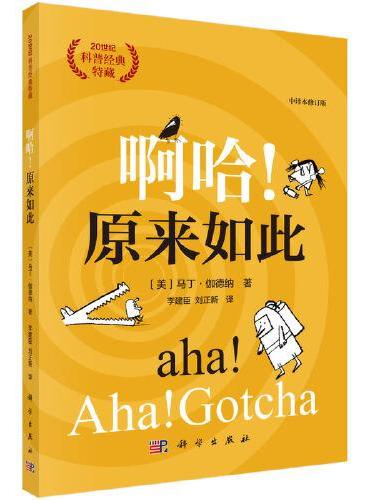
《
啊哈!原来如此(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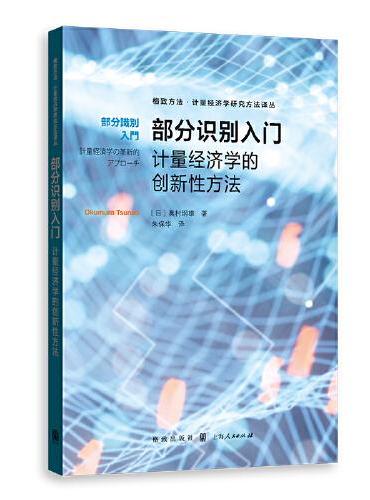
《
部分识别入门——计量经济学的创新性方法
》
售價:NT$
345.0

《
东野圭吾:变身(来一场真正的烧脑 如果移植了别人的脑子,那是否还是我自己)
》
售價:NT$
295.0

《
严复与福泽谕吉启蒙思想比较(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750.0

《
甘于平凡的勇气
》
售價:NT$
2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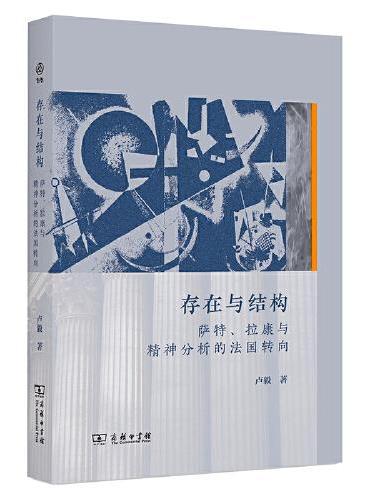
《
存在与结构:精神分析的法国转向——以拉康与萨特为中心
》
售價:NT$
240.0
|
| 編輯推薦: |
★
悬爱实力作家Sunness*之作,
法学科班的专业冷锐 悯世情怀 虐爱*,
被誉为中国版《白夜行》的口碑担当!
爱与诚,暗与光,秘密与反噬,自保与善良
穿越黑暗,触抚灵魂。
★
沿着迷雾的河流溯流而上,
他无数次停在她曾停驻的命运拐角
一步步接近真相,一点点蚀骨寒冷
爱,能否揭开*后的迷藏?
★
触不到的爱人,扑朔迷离的真相,泪点频发,读者直呼不敢看又忍不住一看再看的超级文本。
★
知名影视公司同步改编,重磅打造悬爱影视经典。
★
全书精修,新增番外,催泪家书,直击人心。
★
知名画手Lost7倾心绘制封面图,★
悬爱实力作家Sunness*之作,
法学科班的专业冷锐 悯世情怀 虐爱*,
被誉为中国版《白夜行》的口碑担当!
爱与诚,暗与光,秘密与反噬,自保与善良
穿越黑暗,触抚灵魂。
★
沿着迷雾的河流溯流而上,
他无数次停在她曾停驻的命运拐角
一步步接近真相,一点点蚀骨寒冷
爱,能否揭开*后的迷藏?
★
触不到的爱人,扑朔迷离的真相,泪点频发,读者直呼不敢看又忍不住一看再看的超级文本。
★
知名影视公司同
|
| 內容簡介: |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
成为更新的荒凉
狄金森
九年前,她怀着身孕神秘失踪,
留给他的*线索,
是一通打到他警局的十一秒的电话,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
成为更新的荒凉
狄金森
九年前,她怀着身孕神秘失踪,
留给他的*线索,
是一通打到他警局的十一秒的电话,
以及一句来不及说出口的牵念。
九年后,一通怪异的警告来电以及两张她的照片,
燃爆他积郁已久的思念。
随着警方的刑侦及他私下的打探,
大量令人吃惊的秘密与往事,席卷而来。
重重迷雾之中,
她的面容逐渐显现
曾经相濡以沫,
曾经一步之遥。
在善与恶的模糊边缘,
他能否理解她曾做过的每一个抉择?
在现实与记忆的短暂接壤,
他伸出手,
能否再度将她带回他身边
|
| 關於作者: |
从阳,常用笔名Sunness。
法学专业,爱好文字,对心理类疾病有深入的研究。
专注于言情类、悬疑类小说。
著有《时间暂停等到你》《风暴眼》等作品。
法学的严谨与感性思维的激烈碰撞,
成就读者眼中气味独特的她。
有人说,翻开她笔下的故事之前,从阳,常用笔名Sunness。
法学专业,爱好文字,对心理类疾病有深入的研究。
专注于言情类、悬疑类小说。
著有《时间暂停等到你》《风暴眼》等作品。
法学的严谨与感性思维的激烈碰撞,
成就读者眼中气味独特的她。
有人说,翻开她笔下的故事之前,
必须先深呼吸一口气。
原因,留待你慢慢探寻
|
| 目錄:
|
1 - 十年生死两茫茫 序
我忘记了欢笑,也忘记了叹息,
终生在猜测,没有谜底的谜语。
顾城
7 - 告别天堂 Chapter
1
我们只能一次次告别天堂,
一次次梦想着与地狱告别。
艾米丽狄金森
15 - 角落里的珍珠 Chapter 2
去吧,人世间的孩子,
到那溪水边和田野上去,
与精灵手牵着手,
这世上的哭声太多,你不懂。
威廉巴特勒叶芝
23 - 时间藏起记忆 Chapter
3
记忆就像滚滚浪潮,
撞上海湾里的礁石激出巨响。
记忆的巨响人们是听不到的。
木心
32 - 眼中的烛火 Chapter
4
亲爱的,贴靠近我;
自从你离去,
我荒凉的思想已寒透进骨头。
威廉巴勒特叶芝
40 - 一场无尽的道别 Chapter
5
在河畔的旷野,我的爱人与我伫立,
她柔白的手倚在我微倾的肩膀。
她要我简单生活,如河堰出韧草;
但我年少无知,而今满盈泪水。
威廉巴勒特叶芝
50 - 如果知更鸟来临 Chapter
6
一个波涛汹涌的自然,
在知更鸟眼中,
无穷无尽。
当内心的铁出现,
她死去,先于自己。
艾米丽狄金森
63 - 如果确定我们将相聚 Chapter
7
如果确定我们将相聚,
在你我生命终结之时,
我愿意把生命像果皮一样,
远远的抛弃。
艾米丽狄金森
72 - 无名的地方 Chapter
8
除了婴儿的啼哭,
我再不相信人话;
因为可怕的私欲,
已将真实扼杀。
顾城
91 - 黑暗不接受光 Chapter 9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圣经》
106 - 过去的已如尘烟 Chapter
10
云海浮沉,往日历历在目,
未来的似已惘然,
过去的已如尘烟。
生死乃一线之隔。
威廉巴勒特叶芝
116 - 跃下云端 Chapter
11
所谓深渊,
下去,也是前程万里;
所谓云端,
跃下,便也深渊万里。
木心
128 - 被埋葬的种子 Chapter 12
我相信,那一切都是种子。
只有经过埋葬,才有生机。
顾城
139 - 如果我未荒度一生 Chapter 13
如果我能让一颗心不再疼痛,
我就没有白活这一生。
艾米丽狄金森
153 - 孤夜里的星光 Chapter 14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圣经》
171 - 暗夜的回响 Chapter
15
我将要起航,因为我日日夜夜
都听到那水声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还是灰暗的人行道,
我都能在心灵深处听见这回响。
威廉巴勒特叶芝
189 - 多少门曾无风自开 Chapter
16
多少严闭的门,
无风而自开,
搏动的心,
都是带血的。
木心
204 - 我终要寻她而去 Chapter
17
原来鳟鱼变少女,
头插花朵,一路跑来,
又消失在天际,
久经浪迹,
千山万水走遍,
我终要寻她而去。
威廉巴勒特叶芝
220 - 但愿我是黑暗 Chapter 18
但愿我是黑暗,
我就可扑在光的怀里。
木心
239 - 生命和信仰的归宿 Chapter 19
大批大批的人类,
在寻找生命和信仰的归宿。
顾城
257 - 我没有时间憎恨 Chapter
20
我没有时间憎恨,因为
坟墓会将我阻止,
而生命并非如此简单
能使我敌意终止。
艾米丽狄金森
273 - 当漫长的黑夜刚过 Chapter
21
你无法扑灭一种火,
有一种能够发火之物,
能够自燃,无需人点,
当漫长的黑夜刚过。
艾米丽狄金森
285 - 这里都是深紫色的花 Chapter 22
我倒并不悲伤,
只是想放声大哭一场。
木心
310 - 刻在命运里的路 Chapter
23
他固执地走过许多路,
那些路,
早已刻在了他的命运里。
顾城
332 - 似粥温柔的人 Chapter
24
念予毕生流离红尘,
就找不到一个似粥温柔的人。
木心
360 -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Chapter
25
求你放我在心上如印记,
刻在臂上如戳记。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嫉恨如阴间之残忍。
《圣经》
376 - 于白昼之前 Chapter
26
但我仍要坚持,
向着纯美和永恒,
不论是幸福的死,
还是痛苦的生。
顾城
385 - 家书,勿念 番 外
|
| 內容試閱:
|
序 十年生死两茫茫
赵亦晨把车停在了十五栋楼底。
凌晨两点,小区内几乎所有的露天停车位都被占满。这两年业主没有剧增,私家车的数量却暴涨。他住六栋,通常只能把车停在十五栋,再步行绕过小区中心广场回家。
动手给车熄了火,这会儿赵亦晨却没想下车。
他太累了,后脑勺靠上车座头枕,合眼小憩。做刑警的头几年,跟同事轮流盯梢的时候,他们都习惯在车里休息。那时候信息网络不像如今这么发达,人们由于在车内过夜而窒息死亡的新闻报道还很少见。不过哪怕是近五年,在他们这些警察里,真正因为窒息死在车里的也屈指可数。他们更可能殉职、患癌、遇上车祸,或者从把人送进监狱变成被人送进监狱,最后死在曾经同僚的枪口下。
人的死法有很多种,不到那一刻,谁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怎么丧命。
有人敲响了车窗,赵亦晨从睡梦中惊醒。
最近半夜敲窗抢劫的案件增多,他本能地摸向腰间的枪,余光从后视镜里瞥见站在车窗外的是个女人,染黄的头发乱糟糟地绾在脑后,五官扁平的脸看上去毫无特色,大龄主妇的年纪,却在睡衣外头裹着嫩粉色的针织外套,在浓稠的夜色中尤其显眼。这个女人是他的姐姐,赵亦清。
赵亦晨拔出车钥匙打开车门,在钻出车子迎上湿凉夜风的同时捏了捏眉心,将身后的车门甩上:这么晚出来干什么?
这不一直看你没回来,怕你出事吗?两条胳膊环抱在胸前,赵亦清语带责备,办公室电话又打不通。
三年前赵亦晨当上刑警大队队长的时候,局里给他在新社区分配了一套房子。他没要,固执地住在这个旧居民小区里。赵亦清拿他没辙,又实在放心不下他一个人住,便在儿子上中学以后买下赵亦晨家楼上那套房子,一家子搬了过来,好相互照应。这些年赵亦晨办公室里接到的私人电话,也多是赵亦清打来的:过节回不回家吃饭?怎么凌晨都过了还不见回来?新案子棘手吗,危险吗?按时吃饭了吗,睡觉了吗?
这些本该是妻子或父母关心的,她一概揽下了。
赵亦晨又捏了捏眉心,和她一起穿过中心广场,走向六栋。其实他们可以抄小路回去,可那条小路光线暗,又是监控死角,赵亦晨从不让他们走小路。此刻他脑仁跳痛得厉害,但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一点烦躁的情绪,只说:紧急警力调度,也就剩两个接警的还在局里,估计是没听到。
我是看警车全都呜呜哇哇开出去了。赵亦清抬起一只手来在空中比画了一下,出什么事了?
警察的家属大多对警车鸣笛声敏感。即便隔个好几条街,他们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下意识地心头一紧。这算是一种本能,就像一个母亲听到孩子的哭声总会忍不住停下来四处张望,哪怕知道那不是自己的孩子。
赵亦清就是这种家属。她会在听到警车呼啸而过后开始焦虑。她是个普通的女人,这辈子害怕的事情有很多:父母在时,她怕自己被遗弃;儿子出生之后,她怕儿子会生病,怕一切能把她儿子从她身边夺走的人事物;弟弟当上刑警,她怕有天会有人打电话给她,让她去认领他的尸体。所幸现在父母走了,儿子还好好的;弟弟当上了刑警队长,命还好好的。她唯一需要克制的,就是她的担忧和焦虑。
赵亦晨知道她有这个毛病。这不怪她,他们的父母死得早,她从十几岁开始就要操心很多事,所以赵亦晨能体谅她,总是尽可能安抚她。
九龙村村民袭警。晚风扑向他的脸,他从兜里掏出打火机,给自己点了一根烟。
九龙村?就那个有好多人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村子?赵亦清裹紧了外套诧异道,怎么会袭警呢?
已经快到凌晨气温最低的时候,路灯昏黄的光线似乎都失去了温度,拉扯着他们并肩而行的影子,听路旁的芒果树在风中发出哀求似的呜咽声。
一个寻亲互助会,不知道从哪弄来消息,说他们当中一对父母被拐走的孩子就在九龙村。赵亦晨两指夹着香烟,一手插到裤兜里,缓缓吐了口烟圈,语气平静,难以分辨情绪,夫妻两个溜进村子偷走了孩子,跑出来的时候被村民发现,全村的人抄着棍子和刀追着他们打,正好碰上互助会的人来帮忙,两拨人就发生了械斗。那边的派出所出面调解不成,也被村民围攻,只好通知了区刑侦支队。支队鸣枪无效,又请求我们调动警力支援。
唉这些个村民也是,都几十年了,还跟群土匪流氓似的。赵亦清叹口气,她还记得从大约二十年前开始,就常有这类恶性事件发生,没想到一晃二十年,城市里的高楼砌起来了、乡村里的路修平整了,有些却从没跟着世界一块儿变过,你也去现场了?没受伤吧?
赵亦晨摇头:没事。
他们已经走到六栋三单元楼下。赵亦晨住三楼,赵亦清一家住四楼。他掏出钥匙站在自家门前开门,一回头,发现她还立在他后头,张张嘴好像有话想说,却欲言又止。
握住门把手拉开门,赵亦晨走进玄关,低下头脱鞋:上去吧,早点休息。明天还要送阿磊去学校。
原本就有些犹豫,这时再听他这么开口,赵亦清心里便打起了退堂鼓。
几秒钟之后,她吁了口气妥协:行,你也赶紧休息。说完便转身朝楼上走。可没走两步,她又停了下来,回过身看他。
亦晨,那个九龙村是不是珈瑛一提到那个名字,她就注意到赵亦晨拉住门把打算关门的动作顿了一顿,这让她条件反射地收了声,接着又换了个说法,小心翼翼问他,我的意思是,你还准备继续找珈瑛?
赵亦晨沉默地站在门边,右手搭在门把上,小半边身子还被笼罩在楼道的灯光里。她停在高出他几级台阶的地方,看不到他被眼睫挡住的眼睛。
大约过了十秒,他才平静地回答:已经习惯了。
是习惯自己一个人了,还是习惯一直找她了?赵亦清没忍心问出口,只能长叹一声。
你进去休息吧,她冲他摆了摆手,晚安。
赵亦晨抬头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楼道拐角。直到听到她开了门又关门的动静,他才合上门,反锁,扣好防盗栓,回身走进屋里。
阳台的落地窗紧合,外头还有不锈钢防盗门,用粗硬的锁拴住。厚重的窗帘挡住了外头街灯的光,屋子里一片漆黑。他没有开灯,径自走向客厅的沙发。他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十一年,闭着眼也能找到方向。
坐上沙发,他合上眼,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屋内很安静,可以听见壁钟秒针转动的声响。
许久,他睁开了眼。沙发缝隙里有个表壳磨损得厉害的MP3,常年插着耳机线,一圈又一圈地缠紧。他把它捞出来,解开耳机线,将耳机塞进耳朵里,拨开了开关。小小的长方形屏幕亮起,成了黑暗里唯一的光。
MP3里只有一个音乐文件,很短,只有十一秒。
他点开它,听到了那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
我想找我丈夫,他叫赵亦晨,是刑侦支队缉毒组的警察能不能帮我告诉他
是个女声。气喘吁吁,尾音发颤,戛然而止。
播放方式早已被设置成了单曲循环,于是短暂的杂音过后,他再次听到了她的声音。
我想找我丈夫,他叫赵亦晨,是刑侦支队缉毒组的警察能不能帮我告诉他
我想找我丈夫,他叫赵亦晨,是刑侦支队缉毒组的警察能不能帮我告诉他
我想找我丈夫,他叫赵亦晨,是刑侦支队缉毒组的警察能不能帮我告诉他
赵亦晨闭上眼,仰头将沉甸甸的后脑勺压向沙发的靠背。
他知道,现在是二零一五年十月六日,凌晨三点二十三分。
二○○六年十月五日,他的妻子胡珈瑛拨通了报警电话,通话却在进行到十一秒时忽然终止。胡珈瑛自此失踪。
那天赵亦晨还在毒枭眼皮子底下当卧底。这段录音是接警电话录音原件的拷贝文件,两天后,他的同事把它交给了他。
九年了,他已经将这段录音听了无数遍。他对她话语里的每一处停顿、每一次颤抖、每一个音节的长短都早已烂熟于心。但他依然找不到她。
他失去的不仅仅是胡珈瑛,他深爱的妻子。
谁都知道,在她失踪前,她已经怀孕六个月。
他也因此失去了他们的孩子。
CHAPTER
1
告别天堂
01
二○○三年,赵亦晨从派出所被调到区刑侦支队,师从当时的支队长吴政良。
赵亦晨参与侦破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一起特大团伙贩毒案。三十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唯一一名女嫌犯由赵亦晨和另一名警察负责审讯。
她坐在讯问室的凳子上,耷拉着脑袋,形容憔悴,身上穿的是女警给她临时找来的衣服,因为被捕时她正和团伙头目佘昌志一块儿赤条条地躺在床上。审讯持续了六个小时,她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个字,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脸色灰白,像是已经成了半个死人。
警方很快查明了她的身份:李君,二十五岁,本省人,籍贯在某个小村镇,曾经在X市一家洗脚店打工。如今那家洗脚店已经被查封,它是当地另一伙黑势力管理的色情行当之一。
隔着铁窗仔细瞧了她一眼,赵亦晨想,她可真不像二十五岁。瘦骨嶙峋,皮肤松弛,满脸烂疮,双眼呆滞无神,怕是长期吸毒造成的。
不想说佘昌志,就说你之前的事吧。赵亦晨换了个方式开口,一九九九年你还在一家洗脚店打工。记不记得那家洗脚店的名字?
李君还是不说话。
又过了两天,她浑身哆嗦地倒在地上,四肢痉挛,翻着白眼,几乎要晕厥过去。
赵亦晨和另外两个警察上去扶她的时候,她终于出声了。
给我给我一根烟她说。
李君十八岁那年高考,考进了X市一所名牌大学。
但她早几年就死了父母,一直借住在姑妈家。姑妈告诉她,没钱给她缴学费。
每晚李君都会梦到那所大学。想到将要失去这次机会,她就整日以泪洗面。一个月后,她独自来到城里,想要找份工作,半工半读挨过这四年。没想到刚到火车站,便被骗去拍了色情影片,导演就是那家洗脚店的老板。老板把她带进洗脚店,她成了洗脚妹,给客人按摩,从此再没有去过她梦里的那所大学。
结案以后,赵亦晨从菜市场买了条鱼回家。
他到家时是晚上十点,胡珈瑛已经洗了澡,正在客厅看电视。见他回来,她又跑去厨房给他做饭、蒸鱼。夏天晚上闷热,家里没有安空调,只有一台旧电扇咯吱咯吱地响。她把它摆在客厅,给他吹。
赵亦晨没待在客厅。他拎着电扇走到厨房门口,插好插头,将电扇对着她,好让她凉快凉快。然后他上前,从背后抱住她的腰。才忙活了一阵,她早已出了一身的汗,睡衣贴着汗津津的背,能用手抓出水来。
胡珈瑛拿手肘轻轻捅他:到厨房来干什么,这里热,你去客厅。
低低应了一声,赵亦晨把下巴搁到她肩窝里:再抱一会儿,等下我炒菜。
怎么今天突然腻歪起来了,也不嫌热。她被他下巴上的胡楂儿刮得痒痒,却也只是取笑他,没有躲开。
没事。他沉吟了几秒,你当年怎么来X市的?
讯问李君的时候,赵亦晨想起了胡珈瑛。她今年也是二十五岁,读大学前也没了父母。更凑巧的是,她是从李君梦里的那所大学毕业的。那四年她半工半读,过上了李君原本想过的日子。
手里择着菜,胡珈瑛心不在焉地道:还能怎么来。从乡下搭三轮车,出了镇子走到火车站,搭火车来的。
东站?
对。
那时候飞车党还在。
是啊。她话语间略有停顿,所以一出站就被抢了包。
赵亦晨揽紧了她。这事他从前没听她提起过。
钱都没了?
我只装了几块钱在包里,存折藏内衣里了,没被抢。她笑笑,终于拿沾了水的手拨了拨他的胳膊,示意他松点劲,出来前四处打听过,知道该怎么办。
这回答倒是意想不到的。赵亦晨愣了愣,而后微微低下头,轻笑一声。
笑什么?胡珈瑛转过头来看他。
笑你聪明。他抬手替她把垂在脸庞的头发绾到耳后。
那时候从农村进城的,有大半走了弯路。像李君那样最终锒铛入狱的也不在少数。但赵亦晨没有怀疑过胡珈瑛的话,他相信她聪明,运气好,所以他后来才有机会遇上她。
直到二○○六年,胡珈瑛失踪五天后,吴政良把赵亦晨单独叫到了办公室。
小赵,你知不知道你岳父岳母的名字?
胡义强,胡凤娟。都是胡家村的人。
吴政良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微微皱着眉头,搁在桌面上的右手握了一支铅笔,笔端一下一下点着桌沿,嗒嗒嗒嗒。
老刘带人去胡家村调查过了,半晌,他才重新开口,胡义强和胡凤娟夫妇确实有个女儿叫胡珈瑛,他们死后也把遗产都留给了她,供她去城里读书。但是胡珈瑛在学校的档案里登记的家庭成员不是胡义强和胡凤娟。她的户口是买来的,身份证也是买的。胡家村的人说,胡义强和胡凤娟结婚十几年,一直没有孩子。有一回他们夫妻俩去东北探亲,一年之后回来,就带着胡珈瑛。当时她已经十二三岁了。
赵亦晨沉默地站在办公桌前,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而吴政良抬起头,对上他的视线:她跟你说过她是生身父母过继给胡义强和胡凤娟的吗?
没有。他说。
我们又联系了东北那边的派出所,明确了一下这个事。但是胡义强在那边的亲戚也无儿无女,他们一家子恐怕都是有这个不育的基因。吴政良依旧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小赵,胡珈瑛很可能是胡义强夫妇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
赵亦晨立得笔直的身体终于细微地一动,他沉默了几秒,才动了动嘴唇。
她没跟我提过。
你说她大学是半工半读,她在哪里打工?
一家餐馆。她没告诉我餐馆的名字。
你们大二认识的,她当时经济状况怎么样?
不太好。
我听说她毕业之后就进了律所,跟王绍丰这个师傅学习。目光落回手中那支铅笔,吴政良不自觉减缓了用笔端轻敲桌面的频率,就像他的语气,不紧不慢,引他进入一个极有可能激怒眼前这个年轻人的逻辑,当时毕业生进律所很难,要找个师傅带更难,尤其是像王绍丰这种资深的老律师。
她说王律师觉得她有实力。赵亦晨语速平稳,却几乎是在他话音刚刚落下时就开了口。
吴政良知道,他已经猜到了自己要说什么。
那她说过她那三年给王绍丰倒贴学费的事没有?吴政良继续问道。
赵亦晨再次沉默下来,最后他说:没有。
放下手中的笔,吴政良抬起左手搁上桌,十指交叠。
小赵,我下面的问题可能有点难听,但是希望你能保持冷静。他望向赵亦晨的眼睛,缓慢地、不容置喙地问他,你和胡珈瑛是夫妻,你最清楚。在你之前,她还有没有过别的男人?
那天下着雨。十月的天气,在这座南方城市,依然没有带来半点凉意。
赵亦晨听得到此刻头顶吊扇呜呜转动的声音,意识却已经回到了二○○零年六月的那个晚上。那天白天,他和胡珈瑛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夜里他们挤在出租屋那张小小的床上,第一次睡在了一起。
她很疼,疼得一直在哭,但没有流血。赵亦晨知道她从前在农村干重活,没流血,很正常。因此他没有问她,只是把她搂进怀里,摸着她的背给她顺气,亲吻她的发顶。
胡珈瑛很少在他面前掉眼泪。那晚是她哭得最厉害的一次。
有那么一个瞬间赵亦晨甚至觉得,她哭并不是因为疼。
而他能做的只有给她一双坚实的臂膀,让她有个能够安睡的地方。
一直到现在,赵亦晨还会梦到胡珈瑛偎在他身边熟睡的模样。
他以为她回来了,他想问她这九年去了哪里。可是看到她睡得又沉又香,他没有叫醒她。梦里她还挺着大肚子,肚子里是他们俩的孩子。他撑起身子,替她翻了个身。他记得医生说过,孕妇不能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侧卧。
最终是电话铃声吵醒了他。
赵亦晨睁开眼,捏了捏眉心。屋子里依旧一片漆黑,一只耳机已经从他耳朵里滑下来,MP3仍在播放那段十一秒的录音,沙发尽头的电话吵个不停。他摘下剩下的那只耳机,侧过身捞起了电话。
喂?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毫无征兆的沉默让赵亦晨皱紧眉头,忽然彻底清醒。他拿出手机,解锁屏幕,看了眼时间。
凌晨四点二十分。
他眉心拧得更紧。
您找哪位?握着话筒,他再一次启唇出声。
这回电话那头的人只沉默了几秒,便开了腔。
你女儿在这里。是个男人的声音,经过了变声器的处理,沉闷、冰冷而又怪异,过来找她。不然她就会死。而后砰地挂断了电话。
02
一九八六年的冬天,八岁的胡珈瑛赤脚来到了X市。
那个时候她还不叫胡珈瑛,她的名字是许菡。许菡头一次到这个城市,便看到了满街的大学生。她想要过桥,却见桥上挤满了人,或站或坐,还举着竹竿挑的旗子和横幅,上头写着好些大字。傻傻站在桥头,她觉得脚底的桥都在跟着他们的脚步打战。
有人看到了她,在她脚边丢下两枚硬币,哐当哐当,吓得她拔腿跑开。
她身上只裹了件脏兮兮的单衣,裸露在外的皮肤上有一块块鲜红的疹子,乱糟糟的头发里尽是黑色的泥污和跳蚤,臭得像只从下水道里钻出来的老鼠。
但许菡知道,桥上那些人没把她当老鼠。他们把她当叫花子。
十天之后,南方的隆冬悄然而至。
骑楼老街底下的商铺挂起了年货,天不亮就开了张,铺主拿着竹帚扫去门前的灰尘,也扫去那些蜷缩在长廊里的乞丐。他们通常以天为被,以地为炉。偶尔在身子底下垫上两张报纸,睡在油墨的气味里,也死在油墨的气味里。
包子铺的老板娘抬了蒸笼出来,瞥见一个小小的人影缩在铺面边的墙角,身下的报纸被滑过地板的风刮得哗哗作响。她走出铺子仔细看了会儿,发现那是个女孩儿,一动不动抱着膝盖缩在那里,光着的脚丫长满了狰狞的冻疮。
喂,细路(小孩)?老板娘随手抄起擀面杖,小心弯腰拨了拨她,死咗啊(死了吗)?
那蓬头垢面的小姑娘还是没动,瘦小的身躯硬邦邦的,也不知是只剩了皮包骨头,还是早被冻僵了四肢。这时候老板走出来,伸长脖子瞅了瞅:乜事啊(什么事)?
唔知(不知道)又拿擀面杖拍拍那姑娘的胳膊,老板娘见她没有半点反应,迟疑着嘀咕,好似系死咗噢(好像是死了噢)
刚开张就碰上个死人,实在不吉利。
老板赶忙裹了袄子跑出去找人来抬尸体。而老板娘回身走进铺子洗干净了擀面杖,出来时已瞧不见那小乞丐硬邦邦的尸体,只有冰凉的报纸翻滚着朝长廊的尽头远去。
再抬头,便发现堆得比人高的蒸笼上少了笼包子。
许菡抱着那笼包子使劲往前跑。
滚烫的热气冒出笼屉,熏湿了她的衣襟,烫红了她的胸口。路边尖利的石子刺破乌紫色的冻疮,扎穿她的脚底,捅进她的脚心。她疼得脚趾都蜷缩起来,却不敢喊疼,更不敢停下脚步。
可她最终也没跑过第二个拐角。
老板带了人回来,刚好跟她迎面撞上。包子撒了一地,许菡闭上眼,只觉得星星点点的拳头砸下来,包子在滚,她也在滚。不同的是,包子不会叫,她会叫。直叫到喉咙嘶哑,再没了声音。
他们把她丢到了桥墩下的臭水沟边。入夜后,有什么滑溜溜的东西贴着她的脸爬过,她醒过来,才知道自己还活着。月色清冷,从她指间滑过去的是条泥土色的水蛇,她抬起眼皮,看到还有个被污水泡肿的人躺在她身边。
她想吐,胃里却空空荡荡,连一口酸水都吐不出来。
许久,她挪动手指,慢慢爬到了这个脸已经肿得看不清五官的人身边。
她在他的裤兜里摸到了一枚五毛钱的硬币。
桥西的夜市有家包子铺,铺子门口竖着块硬纸板,上头写着:肉包子五毛一两,一两两个。
许菡把五毛钱的硬币给老板娘,老板娘给了她两个包子。她用红肿哆嗦的手掰开白面皮,里头是白菜。
巷子口站着条大黑狗,一个劲地冲她吠。她跑,狗追着她跑。掰开的包子落下了馅儿,那团白菜掉在地上,大黑狗停下来,伸出鲜红的舌头把它舔进了嘴里。
最后许菡躲回桥墩底下,在黑暗中看着那具泡肿的尸体,发着抖,一面作呕,一面狼吞虎咽地啃着已经变冷的包子。包子是咸的,一半面皮,一半眼泪。
那是那年冬天最冷的一晚,许菡在熏天的臭气中睡去。
第二天黎明,她睁开了眼睛。
她找到一块锥子似的石头,爬上桥,摇摇晃晃,走向桥西静悄悄的市集。
等到天光微亮,早点铺子渐渐热闹起来。有人发现,裁缝铺养的那条大黑狗死在了巷子里。狗脖子不知被什么东西捅了个大窟窿,刺穿发紫的舌头,猩红的血一汩一汩往外冒。
老裁缝跑出来,扑在大黑狗跟前号啕大哭,如丧考妣。
到了中午,他给小孙子做了顿大餐。
小孙子吃着爷爷喂的肉,嗍干净手指头上的油问:爷爷,这是什么肉啊?
老裁缝给他擦嘴,笑眯眯地告诉他,是狗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