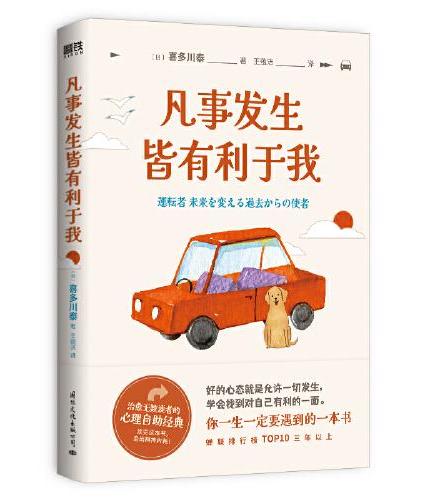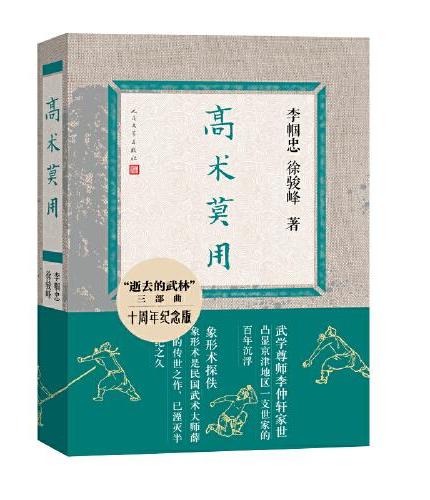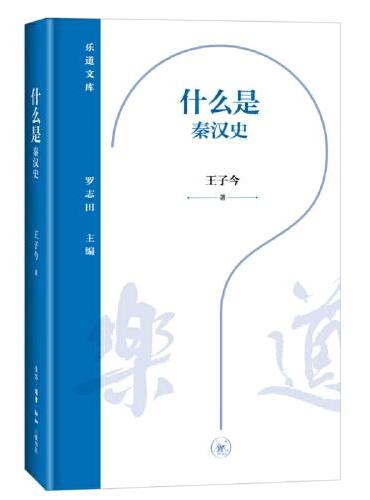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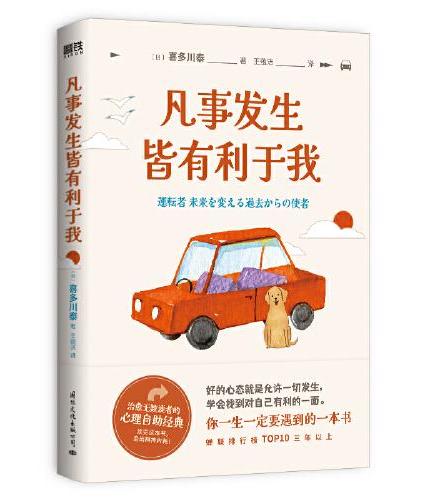
《
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这是一本读了之后会让人运气变好的书”治愈无数读者的心理自助经典)
》
售價:NT$
203.0

《
未来特工局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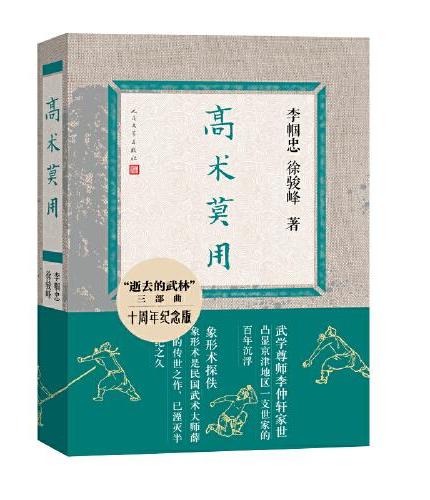
《
高术莫用(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续篇 薛颠传世之作 武学尊师李仲轩家世 凸显京津地区一支世家的百年沉浮)
》
售價:NT$
250.0

《
英国简史(刘金源教授作品)
》
售價:NT$
449.0

《
便宜货:廉价商品与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
》
售價:NT$
352.0

《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2024年新版)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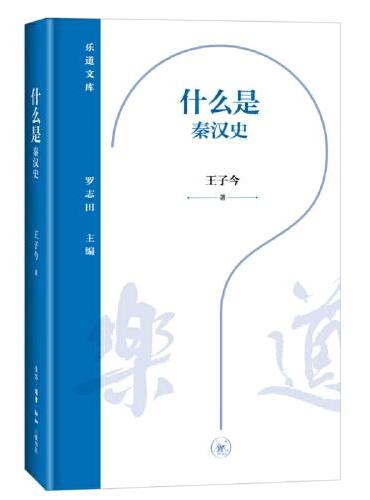
《
乐道文库·什么是秦汉史
》
售價:NT$
367.0

《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 自由、政治与人性
》
售價:NT$
500.0
|
| 編輯推薦: |
|
由当代诗人梁平主编,高质量、高稿酬、高颜值的诗歌刊物,立足成都,面向海内外,是成都诗意的城市文化符号,是华语诗坛的重要旗帜和标杆。
|
| 內容簡介: |
|
《草堂》诗刊以传承大唐风骨,繁荣当代诗歌为宗旨,立足成都,面向海内外,是成都诗意的城市文化符号,是华语诗坛的重要旗帜和标杆。设置有封面诗人、实力榜、非常现实、*青春、大雅堂、实验经纬、台湾青年诗人十二家、文本细读、子美逸风等主要栏目以及其他不定期栏目。
|
| 關於作者: |
|
梁平: 重庆人,现居成都。当代诗人,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200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拒绝温柔》《梁平诗选》《巴与蜀:两个二重奏》《近远近》波兰版等8部;长篇小说《朝天门》一部,评论集《深呼吸》等。作品被译介到美、英、法、德、日本、波兰、保加利亚、韩国、俄罗斯等国。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届中华图书特别奖、《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四川省文学奖、重庆市文学奖等奖项。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作家协会主席。曾任《红岩》杂志执行总编辑、《星星》诗刊执行主编、主编等,现任《青年作家》杂志、《草堂》诗刊主编。
|
| 目錄:
|
《草堂》目录
2017年5月总第9卷
[封面诗人] _4
张新泉 _ 大风吹我(组诗)张新泉 _ 雀,麻雀的雀
龚静染 _ 渔父、雏鸟和桃花的骨朵
张新泉诗歌印象
[实力榜] _14
朵 渔 _ 感谢每一个如愿醒来的早晨(组诗)
人 邻 _ 只是从命于大地已近黄昏(组诗)
倮伍拉且 _ 大凉山诗意生活录(组诗)
汗 漫 _ 散怀抱 组诗
阿 毛 _ 阳台外月亮在落下 组诗
王学芯 _ 被佛指触动的隐衷(组诗
[非常现实] _37
西 左 _ 人间物像
杨胜应 _ 把悲伤降低到大地(组诗)
杨泽西 _ 生死疲劳(组诗)
尹 马 _ 活 着(组诗)
朱绍章 _ 所有的城市都长着同一副面孔(三首)
孙思遥 _ 我要淳朴地活着(组诗)
[最青春] _51
秦三澍 _ 一把钥匙试图拧开不会终止的圆(组诗)
熊 曼 _ 清 白(组诗)
郁 颜 _ 苍茫人世才是一场苦役(组诗)
马小贵 _ 阿勒屯之歌
六 指 _ 怀抱鲜花的女人
左 右 _ 生活赞歌(组诗)
占 森 _ 雨滴模糊,风鸣渐烈(组诗)
卢 游 _ 恋人献完玫瑰就要离你远去(组诗)
[大雅堂] _68
何大草 _ 槐下读史(组诗)
何 苾 _ 九行诗(七首)
于贵锋 _ 小槐树林,或论梦(三首)
简 单 _ 霜冻于心(三首)
黄 海 _ 雨天路过电子正街(外一首)
宫白云 _ 各行其道(外一首)
曹 谁 _ 故 园(外一首)
施施然 _ 开罗时间 三首
李 炜 _ 1611 号信箱(外一首)
瞿 炜 _ 她在寂静里(外一首)
雷 文 _ 恩阳河(外一首)
风 言 _ 虚掩之门(三首)
陈小平 _ 故居(外一首)
高海平 _ 虞山下
[实验经纬] _84
茱 萸 _ 谐律与九枝灯(组诗)林典衣 _ 音调与形式的创格
小议茱萸的谐律与九枝灯系列
非 亚 _ 安 慰(三首)
大 雁 _ 非亚为诗:不一样的民间写作
[独白与对话] _91
百年新诗漫谈
霍俊明 _ 精英的水仙或大众手里的魔术袋
关于百年新诗的公众形象
[诗人故事] _96
傅 维 _ 昨夜里我见过一颗星星
回忆诗人张枣
[台湾青年诗人十二家] _102
张继琳 _ 未曾去过远方(组诗)
程一身 _ 近处的诗意
张继琳《未曾去过远方》简评
[子美逸风] _109
施议对 _ 施议对词选
周清印 _ 周清印诗词选
独孤食肉兽 _ 独孤食肉兽七绝
|
| 內容試閱:
|
草堂已经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符号。
这是因为安史之乱以后,诗人杜甫举家迁移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落户,一个伟大的诗人在这里,写下了不朽的二百四十余首诗。千百年来,杜甫草堂里的每一茎草都生长着诗意,这个诗意弥漫了成都,弥漫了四川,弥漫了中国。
成都从古至今产生了众多杰出的诗人,他们在各个时期留下的诗篇,成就了成都作为一个诗城的荣誉。然而,更能证明成都是一座诗城的,是诗歌对这座城市的影响,诗如水一样在这座城市漫延和滋润,已经潜移默化成这座城市的血脉和基因。
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发展,成都作出了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所不能比肩的重要贡献。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成都诗歌流派、诗歌运动以及优秀诗人层出不穷,无疑让这座城市成为了中国诗歌的重镇。吉狄马加、白航、孙静轩、流沙河、叶延滨、杨牧、张新泉、欧阳江河、翟永明、李亚伟、柏桦等一大批诗人,以自己卓越的创作和影响力跻身中国重量级的诗人,他们的诗被翻译成多个国家的文字,在国际诗坛频频亮相,成为成都乃至中国诗歌的标杆。进入新世纪以后,成都更年轻的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诗人已经在中国诗坛展示出一个强大的阵容,在中国诗坛的坐标上,各个年代都有成都代表诗人的名字,密集、耀眼,宛若一条延绵的星河。
2016年初春一个周末的晚上,成都市委主要领导黄新初同志约了诗人喝茶,茶喝至酽处,诗意就浓了。新初同志说:诗意成都,不是要每个成都市民都成为诗人,而是让成都市民在生活中能够享受诗意,做一个有诗意的人。新初谈到了杜甫草堂千诗碑林项目对于成都诗歌符号落地的意义和未来的影响,进而希望整合省、市诗人和诗歌资源,再做一个行走的诗歌符号,创办一个精品诗刊,立足成都,走出成都,办出全国的影响,让这个诗刊也成为诗意成都的一个重要标志。新初同志说,我们有杜甫草堂的品牌,这个诗刊就取名为《草堂》。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草堂》第一卷就这样应运而生。这是2016年的春天,中国诗歌已经繁花似锦,成都又为中国诗坛绽放了一朵芙蓉。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希望她的颜值不辜负这座城市,不辜负这个时代。正如马拉美所说:诗是为着一种已经完成的社会华丽的仪式和庄严的仪仗而创作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光荣才会有它应有的地位。
《草堂》有她特殊的地域。
《草堂》有她辽阔的胸怀。
《草堂》以自信与包容期待您的佳作。
《草堂》2017.5第9卷内容连载
《危 楼》
作者:张新泉
还有一群活物住在里面
一至三楼为乞丐
十楼以上猫鼠鸟杂居
自杀者说,从楼顶跳下去
可以直接升天
拆除方案已定
但工程车和民工一致要求
必须有警察持枪陪护
理由是,有人在墙角
看见白骨和绣花鞋
而酷似人声的猫叫
一声比一声悽惨
楼底是早年的火葬场
据说魂灵拱动时
楼会摇晃
《大风吹我》
作者:张新泉
从外到内
搜了N遍
无非是:
三块腹肌
两脚老茧
有旧爱,无新仇
刺于右臂的匕首
早已褪尽锋芒
老花眼里的平仄
正在煮碱熬盐
拜托
白发丛中
孵着
一窝鸟蛋
《埋》
作者:张新泉
一铲,又一铲泥巴,撒在棺盖上
润润地响。有时夹带着瓦砾
声音就沉些;有时夹带着叹息
时间就会拉长
你铲来的泥巴里,有金龟子、蛐蛐儿、花骨朵
每一铲都体贴,都称得上厚葬
后来,落土声止于一声炸雷
接踵而至是倾缸大雨
天地如一口巨棺,埋人的和被埋的
处境都变得一样
我脱下棺里的黑,加了一件衣裳
《雏 鸟》
作者:张新泉
母亲是从草丛里
把它捧起来的
它细碎的叫声
如同哭泣
如同呼救
树上没有窝
它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呢
一定会有鸟来找它
一定会有鸟来接它
所以,她不会走
她是母亲。她会一直
等下去,一直
即使脚趾生苔,头上长锈
《杨氏宗祠》
作者:张新泉
两根十米桅杆在门前提醒
没有五品以上官职,不得入内
所幸来访者都有高级职称
跨此门槛,应该是户对其门
进吧,一步迈至乾隆年间
看十二个院落里的幢幢人面
听大小天井平平仄仄的雨声
声嘶力竭叫苦的是园中灰蝉
劈哩啪啦拨算珠的是管账先生
切勿将小姐丫环喊成美女
入绣楼,请把手机调至静音
门槛普遍都高,抬腿时
小心长衫绕脚绊腿
门内神龛寂寂,栏杆沁凉
门外的楼市正在升温
《渔父、雏鸟和桃花的骨朵》
张新泉诗歌印象
龚静染
读过新泉先生过去诗作的人,一般都了解他的诗歌风格,他的诗歌就像被粗绳勒过的桩石,有着鲜明的印记,因为在那被磨出的纹理中有太多的伤痕是不能仿造的。新泉先生的人生非常坎坷,扛过包、打过铁、拉过船,这些底层的艰苦生活最终变成了他的诗行,浪抓不住我们涛声嚎叫着如兽群猛扑一匹滩有多重一条江有多重我们只有我们清楚(《拉滩》)。记得在1989年的一个小城里,那时正是诗歌运动高涨的时期,各种山头、旗帜林立,现代诗潮把人冲得天晕地转,我们热衷的是谈论庞德、艾略特和金斯伯格,好像不谈这些,便难以开口言诗。就在这时,我和几个热爱诗歌的年轻人读到了他的新作《渔父》,这是一首让人泪涌的诗作,显然它同那些热血飞扬的诗歌是不一样的。《渔父》是一首他怀念早年生活的诗作,讲的是一个渔夫把他从水中救起的经历:
记忆总在釜溪河下游
三十二年前,洪峰上那只打渔舟
把死鲫般的我捞起,掷于沙渚
又赠我以粗手重脚,鼻息悠悠
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
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
将那半生不死的弃于漩涡内
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
诗中有种沉甸甸的下沉感,或许你得抓着一把泥土才读得懂这样的诗。我们仿佛看到了激流下面的河床,宽阔、深厚,没有闪烁跳跃的浪花,也没有风和日丽的帆影,只有一望无际的卵石送走了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新泉先生,请告诉我,您挨过多少个浪头,呛过多少口江水,才能写出这样的诗?这是在浪涛之中拼尽全力的苦泅,却换来了甘美的诗歌。新泉先生的诗歌美学动力根植于个体生命的深处,激奋、粗犷、悲怆,那是在诗人的人生在受到严重阻碍之后却更加高扬生命本体的歌唱他,他说我的诗虽像手茧一般粗糙却蕴藏着亿万千卡闪光的热能(《班后》)。
进入八十年代后,西方现代诗学滚滚而来,诗人们好像兴奋地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诗歌引擎,但在时代的巨大轰鸣中,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失声,要么走调,直到被更大的噪声淹没。不过,在群声歌唱中我们听到了一个不同的嗓音,这一时期,新泉先生写出了《拉滩》《野码头》《残纤》《清明节,纤夫墓前》等好诗,正如《野码头》的名字一样,他的诗也有股子山野之气:野码头的捣衣棒很野野码头的渔歌很撩人野码头的烧酒不止六十度野码头的针线长过拉江拽河的纤绳。这首诗写的是一个流落在江口绰号叫野码头的女人,一个被人玷污又毁坏的女人,诗被悲剧般的命运笼罩着,其中的沧桑和苦涩,只有底层挣扎过的人才能体味,但她一朵凄苦的微笑是让人难忘的,能够永远留在岁月的深处。我常常想,诗歌就像他诗中的那些微弱、飘摇的桅灯,在人间发出不屈的光亮,这正是我对他诗歌最初的认识。
(注: 此文为节选)
《感谢每一个如愿醒来的早晨》
作者:朵 渔
失眠,整夜像骑着一个大海
温柔的波浪轻抚着下体
早晨醒来,阳光已穿透窗帘
感谢,又是美好的一天
我感觉体内的力量又回来了
像一个从沉船归来的船长
再一次搬过你的身体
光裸着,还是昨夜的模样
内衣堆放在橡木地板上
《风暴前》
作者:朵 渔
植物放弃了生长,星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灯光在夜里偶一闪亮,昆虫们屏住了呼吸
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但在这之前
将是长时间的静寂。
这是需要现身的时刻,也是墙头草表明立场的时刻
坏消息已数次发生,期待中的风暴却迟迟未到
置身于风暴前的山河,面对满大街的耻辱和荣耀
你要做出决定你选哪一个?
选择荣耀的人留在了街头,选择耻辱的回到家里
当我们终于懂得耻辱时,我们才触摸到人的形象
当荣耀留在街头时,荣耀不是增多了,而是
减少了所有的荣耀终归于那一个。
《五月的第一天》
作者:汗 漫
五月了,花朵和光线勤奋劳动。
我不劳而获,在菜市场闲逛
看美妇人痛快切肉像斩断情事和春愁。
小贩叫卖牵牛花、秋葵、番茄一类种子,
知我无田园、少体力,
就兜售风铃、扇子和草席。
抱一坛梅子酒回家,万物清和。
自我与人世之种种大局,尘埃落定。
宜微醺、午睡,像白居易
移榻于湖边树阴下,肥胖,翻禁书,
不作为,说家常话,自适
方能适应我阳台上只有一缸睡莲这一现实。
清洗空调过滤器和凉鞋是必要的
换纱窗是必要的
嘱咐亲人吃西瓜、败火、不思进取是必要的
给老汽车加冷却液是必要的
悖离导航仪进入草长莺飞的土路是必要的
月色里记着回家,是必要的。
五月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花香和光线都暗了。
倒春寒里积蓄的敌意也已消失。
镜中,老年斑像逐渐慈祥的星辰。
五月最后一天将紧邻儿童节,多么好。
我应该去池塘边与青蛙排练童声合唱
《她在哭》
作者:杨胜应
我们只看见她在哭
蹲在屋檐下,把悲伤降低到了
尘埃底部,就要接近大地了
这些流动的水,没有人能够看见
里面深藏着的清泉和盐
只知道她是附近工地的一个小工
没日没夜地搬运着砖头、水泥、砂浆
现在她还要搬运自己的男人
那个被失控的塔吊掉下来的重物
按回大地内部的老实人
她哭得那么伤心
因为她从来没有搬运过
这么远的路程
《低空篇》
作者:秦三澍
不会更高,是失去海拔的夜空,
是距离,从按门铃的指尖
压住深陷于食物的发烫的勺。
是让人担忧的餐具散出冷光,
把双份的病症,搅拌进数月后
咳喘着向我们举步的雪地里。
是勺子用金属的舌头卷起
碗底凉透的白粒,是一次外出
摇醒它:犹豫以至于昏睡的定音锤。
是脚,是离开的必然,让位于次要。
是天真的纤维,你显现它
只能求助于夜空替你掀开眼睑。
是你的手拧动另一种潮湿,
仿佛将要丢失的躁意
透过门缝,扶正屋内折断的香气。
《末 日》
作者:简 单
夜不深,但黑;灯不亮,
但有。我附着在一粒尘埃上,
一粒尘埃,便裂开了
人世的一道小缝。
血还没有停止,死亡,
还在大地上到处流动。我用绝望武装
我的每一寸肌肤。我用鞭子抽打
谎言弯曲的内脏。
幸福是这么的短暂,短暂得犹如它本身,
留下词义的饥荒。
我留不下我的青丝、眼泪和柔肠。
我施虐和受虐,在迷宫里,
抱残守缺,等待着大洪水,
再次降临。
《音调与形式的创格》
小议茱萸的谐律与九枝灯系列
林典衣
谐律系列和长诗《九枝灯》是茱萸近年来最为用心经营的两组作品:前者均是以谐音之法写就的短制,但较前人诗作更进一步,呈现为遍布机关的文本;后者则有恢弘的架构,按照作者的计划,它将由数十首看似相互独立、实则在宏观层面彼此勾连的诗作组合而成。放置在作者个人的写作进程中看,二者似乎具有某种承前启后的意味。茱萸早期诗歌的基本特质,诸如对古典文学的化用、对历史世界的沉浸,在其中皆有体现,并通过与社会现实、个人际遇乃至艺术思辨的有机交融获得了强劲的新生;与此同时,精妙的文体试验和形式创制,又为想象力的开展规划了新的路径与方向,这显然是诗艺自觉和诗学抱负的产物。
谐音对汉诗而言,几乎是一种宿命。即便考虑到声调之别,汉语的音节也相当有限,故而中文里多有同音的字词,这一度是困扰诸种汉字拉丁化方案的难点,但却为写作者们辟出一条幽径。借助谐音,拓展字词的语义容量;在语音的相似性中,发现事物的隐秘联结;通过听觉上的戏仿,制造反讽的效果;此类当代诗中常见的技法,也被广泛运用于谐律之中。茱萸在百余字的篇幅内安插、设置了十四到十八处谐音,诗作内部交错缠绕的电路所传输的巨大能量,与其玲珑、整饬的外观极不相称。随手拈出一句:抑郁突燃,如何扑救?异域的风情,舞断的腰身或无端之蕊?(《谐律:译李商隐北楼诗》)异域自是抑郁的缘由,突燃恐为徒然之举,谱就新曲纵能扑救羁泊之愁,也奈何不了花朵无端飘坠(《北楼》:花犹曾敛夕),如宫腰舞断(《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且问宫腰损几枝)。而谐律之为律诗,不惟在诗行的划一,更因其音乐性上的考究,如:有人离开,披起椅背上的单衣,你淡意转浓,又点了一杯热饮。(《谐律:路拿咖啡馆》)谐律虽无严明的格律,但错落的谐音词营造出的回环反复的音律之美,确是当代诗中普遍缺失的品质。
相比于兼顾音义的谐律,《九枝灯》的构思或许更费苦心。作为茱萸的友人,我有幸见证了它漫长的生成过程,也是其中多数作品最早的读者之一。《九枝灯》在结构上参照《周易》的卦象,每一组诗作对应于一爻,目前已经定稿的仅有初九与六五两部分,《夏街:雨中言》和《城堡:犬山行》等作都出自后者。尽管卦象尚未显明,因而也无从阐释它与各部分间的关系,但《九枝灯》中的每一首诗都可被视作自足的个体,它往往由与诗相关的经历引起,试图在作者与被书写的古今诗人之间建立一种更为私密的关系,并借助他们完成对生活与写作的重新审视,而诗前与作品互文的题辞和诗后说明背景的尾注则是理解诗之意旨的关键。初九以曹丕、阮籍、庾信、李商隐等古代诗人为主角,六五则将镜头切换回当下,上述几首诗分别记叙了与当代诗人罗伯特哈斯、竹内新、高桥睦郎等人的交游。考虑到六五在全诗中居于相对靠后的位置,做这般的推测或许不无道理:《九枝灯》里,作为自我之参照的他者或许存在一个由古至今、从中到西的转换过程,这实际同步于诗学视野的拓展和汉诗样态的流变。在此意义上,《九枝灯》的书写对象如作者所说的,是他对文学人物的私家遴选,换言之,他们无形之中构成了一部精心编排的个人化的诗歌史。
《昨夜里我见过一颗星星》
回忆诗人张枣
傅 维
1985年早春,北岛到重庆来了。他个儿瘦削,颀长,态度和气,言语不多,但并非沉默寡言,稍聊了一会儿,然后我们一行人直奔川外,张枣和柏桦在那里等候,谈话在略显拘谨的氛围中展开。寒暄一阵后,还是张枣率先打开了僵局,张枣对北岛说,我不太喜欢你诗中的英雄主义。北岛听着,好一会没有说话。听张枣把所有的看法说完了以后,北岛没有就张枣的话做出正面回答,而是十分遥远而平静地谈到了他妹妹的死,对北岛十分震动和悲伤,谈到他在白洋淀的写作,谈到北京整个地下诗坛与状况,最后说,我所以诗里有你们所指的英雄主义,那是我只能如此写。我当时感到,北岛虽然处在风暴的中心,但是没有风暴的喧嚣。
张枣柏桦等商量去重庆北温泉,找一个僻静地,大家再好好谈谈。当晚,全部人员都安排在北温泉有名的竹楼宾馆,说是西哈努克亲王住过的,宾馆建在悬崖边,悬崖下边就是嘉陵江上著名的温塘峡,冬日的江水清澈而舒缓,时而有汽轮拖着长长的驳船从峡谷中穿过,柔和的汽笛声仿佛来自很遥远的地方。淡雾从江面上轻轻掠过,江对岸是十分陡峭的高山,茂密的竹林看不到边际,时而有些大鸟发出清脆的叫声,一条石板铺就的路盘旋在山腰,赶场晚归的农民三三两两往家赶路,早炊人家的烟囱已经开始冒出炊烟。我们所处的北温泉则以温泉出名,流到江里的温泉水热气蒸腾,在寂静之中让人联想到温暖。一行人全部伏在栏杆上,长久都没有人出声,全部被眼前景色打动。
北温泉之夜,不像是先锋诗人聚会,倒像是朋友间的促膝谈心之夜,从那以后,张枣开始从更多的角度来理解和看待北岛那一代诗人的诗歌。在此之前,张枣更多阅读的是欧洲现代诗人的诗歌,对国内诗人的诗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诗则关注不多自北温泉之夜后,我发现他的阅读范围更广了。1988年,他从德国回到川外,见面跟我大谈闻一多的诗歌,最喜欢朗诵一句闻一多的清空里爆一声,咱的中国!但我同时发现,他涉猎越多,融汇进自己诗歌却更加谨慎,挑剔他以后越来越挑剔!
在重庆认识张枣到他去德国,接近两年时间。这段时间内,基本上隔天就见一次面,要么他到我学校来,要么我去川外。他来我这里,就拉着我先去学校后门菜市场上去搞荤菜,兴趣极其盎然,甚至还去学划鳝鱼开始他觉得很有趣,但是后来觉得太血腥了,先把鳝鱼在木盆边上敲晕,然后长钉子把鳝鱼头钉在木板上,然后锋利刀子从头一刀带下,就划到尾部了,他说,写诗要是都能这样一刀带下就好了。他笑眯眯的蹲在木盆边上,眼睛贼溜溜乱闪,我晓得他又在憋着什么坏主意了,他突然先嘎嘎笑起来,说,我们也把某某某(他极不喜欢的一个诗人)也这样剐了,你觉得如何?然后还以商量的非常温柔语气给我说,你觉得这个办法可好?我说,这下这个龟儿子没准还真把诗就写好了哟他接过话头,说,对头,对头,那些瓜宝诗人脑壳不晓得装的啥子,我真的想打开看看,拆了重新装过诗歌不是这样写的啥,不能啊,同志,诗真的不能这样写啊!他痛心疾首,跺着脚说。
相当神奇的是,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单位地址离川外约有20分钟的散步距离。这样从1985年夏天到1986年夏天,他离开川外去德国,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散步、谈诗、写诗。我和张枣经常去一个地方,一个是离我住处直线大约有20分钟散步距离的瓷器口老街,那时候尚未开发,陈旧但是很有古意,街上有几家老饭馆,做的老派川菜非常好吃,我们在那些临江吊脚楼小饭馆里,要几份菜比如油酥花生米、青椒皮蛋、卤牛肉、水煮肉片、回锅肉等,喝用土碗装的江津白干酒,一直说话到深夜二点,老板也不会发杂音,我们聊诗,说得又细又透,为一首诗一个韵脚的把握,可以说上好几个小时,不疾不徐,慢悠悠喝着,聊着,看江上的轮船拉着汽笛上下往来,江风吹着小酒馆满室清凉。
朋友处深了,就是兄弟,兄弟再往深处走,就是亲人。认识张枣的最初半年左右,张枣对我而言,亦师亦友。半年之后,直到最后就是兄弟了。1996年,距上次1988年张枣从德国回来见面已经快10年了。1996年,我在北京,张枣正好有机会回国,也正好在北京,一见面,就像昨天才见过一样,就说,哎呀弟弟,找个地方先睡一觉,几乎是话音一落,倒在床上,呼噜就睡过去了,鼾声之大,几乎可以掀翻房顶,瞅着床上那人,几乎都认不出来了,发胖,谢顶,鼾声如雷,哪里还是1988年那个美男子张枣。一直到天黑了,他才醒来,赧然不好意思,还红着脸说,兄弟,不好意思,还没有办法定下心来说话,我们还得一起去还要去赶个饭局,结果又是一顿曼卿轰饮,一直到深夜,就着酒劲说了一通话,醒来也全忘了。第二天,他又忙着要赶回长沙,将近10年后就这么见了一面,虽然仍然亲切,没有一点疏离之感,毕竟太短暂了。
(注: 此文为节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