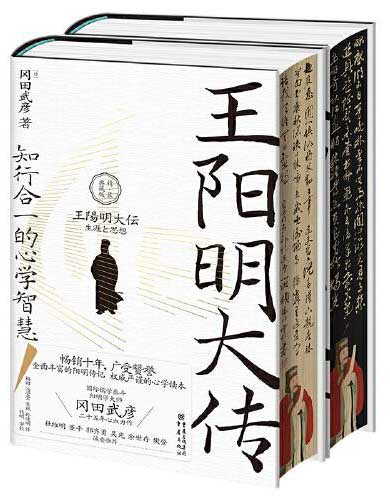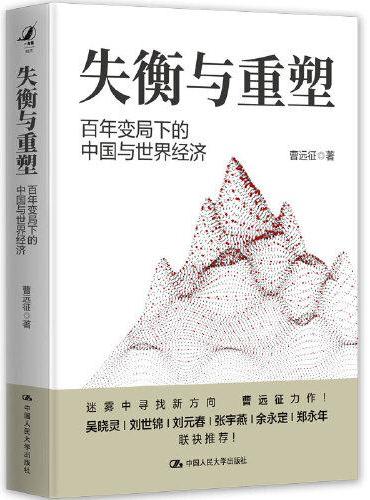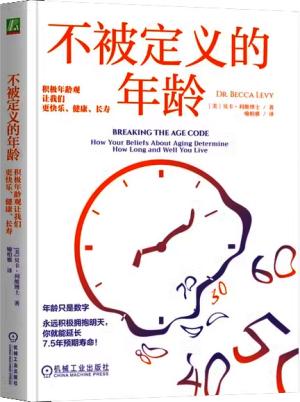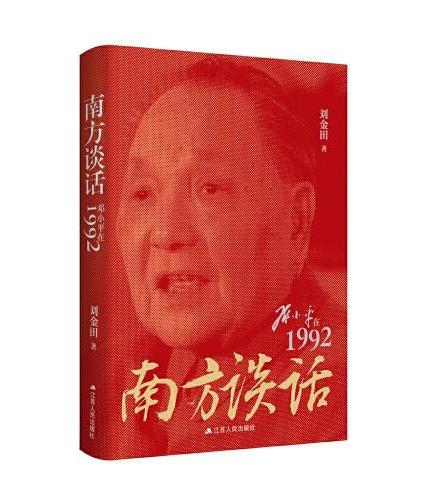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鸣沙丛书·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
售價:NT$
551.0

《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兼论宗教哲学(英国观念论名著译丛)
》
售價:NT$
275.0

《
突破不可能:用特工思维提升领导力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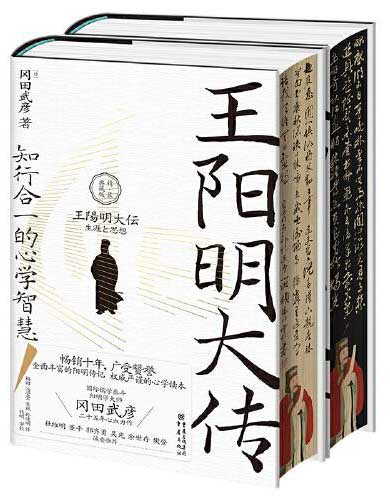
《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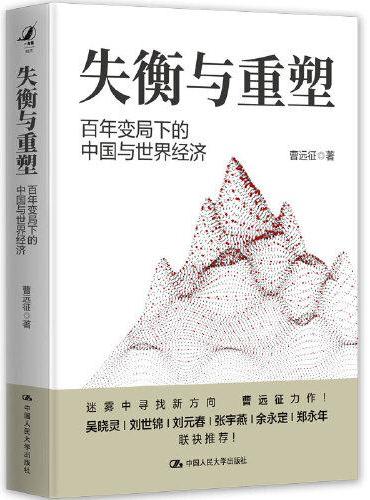
《
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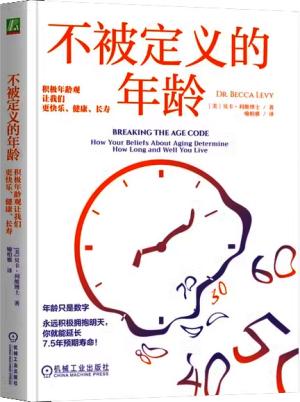
《
不被定义的年龄:积极年龄观让我们更快乐、健康、长寿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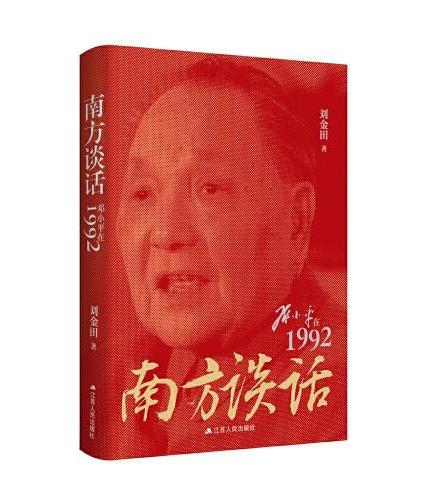
《
南方谈话:邓小平在1992
》
售價:NT$
367.0

《
纷纭万端 :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
售價:NT$
500.0
|
| 內容簡介: |
|
《炼狱天堂》是一本揭示韩美林个人成长的心灵史和特立独行的艺术史的书,也是一本关于两位艺术大家韩美林和冯骥才对生命、历史、现实和艺术的理解与碰撞。该书分为上卷和下卷,上卷是炼狱,下卷是天堂。炼狱是用口述的方式呈现出韩美林苦难又传奇的人生脉络,也是他的受难史;天堂是冯骥才在对谈中探究这些苦难的经历对韩美林心灵和艺术的影响,极为敏感又准确地建构出韩美林艺术世界的深层内涵,这是艺术的王国,也是美的旅程。
|
| 關於作者: |
|
冯骥才,祖籍浙江宁波,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作家、画家、文化学者。文学代表作有《珍珠鸟》《灵性》《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俗世奇人》《神鞭》《三寸金莲》《一百个人的十年》《无路可逃》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等多种文字。近十五年投身民间文化和传统村落抢救,相关理论、随笔及主编的大型文化档案颇丰。现于天津大学任教授。
|
| 內容試閱:
|
四、1967年4月7日
冯:我研究过你的各种材料,其实此前你所经历的一切,还只是一种序曲与前奏。你真正的苦难史应该是从文革开始的,对吧,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韩:1967年4月7日。
冯:记得这么清楚。
韩:如果轮到你,这辈子也不会忘。这个日子像刀戳在我心里。
冯:在你从杭州回来后不久吧。
韩:我是接到通知回来的,当时有预感,浑身充满一种不祥的敏感。我去杭州的时候,还特意跑了一趟上海看我的母亲。那时我嫂子在医院工作,我说我睡不好觉,找她要安眠药,要了几次,凑上几十片带在身上,准备遇到大难想寻死的时候用,这事后边再说。回来后,听说厂里不少有历史问题的人都挨斗了。连厂长戴岳也给揪出来了。几天后,我跟一个技术员去蔡家岗百货公司买东西。正走在路上,厂里一位运动里闹得挺欢的师傅骑车追来,说:韩美林,厂里有点事叫你回去。我边走手里还边用小刀刻着一个木头小人儿呢。我们就扭身返回去。那个师傅骑车一直跟着我,实际是盯着我,这时候我就感觉事情不妙了。
我还没到厂门口,差着八十米吧,就见好大一群人,总共有好几百人,像列队一样在门口等着我。我一来,都用眼瞪着我,我一看完了。
冯:请你讲得再细一些。
韩:我下意识把手里的木雕人和刻刀揣在兜里。一群人就拿着杠子上来,噼里啪啦一顿揍,再一踹我就跪下了,然后拿铁丝把胳膊和手拧上了,把我连踢带打弄进厂,到了办公楼的二楼上。刚到楼上,一个厂里出名厉害的,瘦高个子,斗鸡眼儿,守在楼梯口一个耳光把我从二楼扇到一楼,再拽上来,向右拐个弯儿,再左拐个弯儿,进了保卫科办公室,一脚又把我踹得跪在地上,一条杠子把我的腿和脚都压上了,叫我交代罪行。这时我一看,保卫科长、军代表、工宣队长都在,就知道今天大难临头了。
冯:你很怕吗?
韩:实话对你说,刚开始怕,后来不怕了。人到这时候了,怕也没用,也不知道怕了。我心想,我的言论该交代都交代了,也不是国民党特务,没干过亏心事。还交代什么呢?专政就专政吧,我就豁出去吧,我说我都交代了。身后一个小子,上来就踩压在我腿上的杠子,过去只知道日本鬼子对抓来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员踩杠子,这一踩我才知道踩杠子是什么滋味,浑身从下往上冒凉气,那种凉真是没法形容,而且疼得钻心,汗噼里啪啦下来了。这小子说:叫你嘴硬,给你再修理一下,然后用木棍往我脚面死死一戳再用劲一拧,死疼死疼,我脚骨头就碎了。
冯:怎么知道碎了?
韩:很久以后照相才知道,六根骨头碎成四十多块。我疼得大叫:我操你妈呀!再想叫想说,嘴不行了,已经充血,说不出来了。他们说:你跟三家村四条汉子什么关系,跟邓拓什么关系,你给他们画画,你跟他们勾着。这时我才知道北京中央工艺美院那边又把我一批新的材料转来了。原先认识田汉、夏衍、邓拓算什么问题,他们不都是大作家艺术家吗?谁知道文革一来他们是天天写在报上最大的敌人!我韩美林上辈子造多大孽,这辈子身上什么东西都能转化为反革命的证据!
冯:这是你的命运,可是只有我们这代才会有这样的命运。与三家村的邓拓和四条汉子的田汉拴在一起还好得了吗,你可真的是在劫难逃了。
韩:我当时想,我在劫难逃了,只有视死如归,横下心用我那破嘴只说一句:我没什么可交代的。那小子忽然从桌上的笔筒里唰地抽出一把水果刀,抓起我的手,在我靠近手腕肌腱的地方扎进去往外猛地一挑,咬着后槽牙说:我叫你画,叫你画!硬把我手上的筋挑了,血冒出来了。这一下,我没感觉疼,只想到我从此不能画了,什么理想、抱负、兴趣全完了,他毁了我!我朝他大骂:我操你妈!
我死命往上蹿,他们拿杠子压不住我的腿,就拿烟头烫我,把我胳膊用铁丝狠狠倒绑起来。你看看我的手吧,这是挑断筋的地方,这是烫的疤,都还留着。
冯:我不想叫你说下去了!你先别说了??
韩:我想说下去。我这人天生性格太硬。我从来不是软骨头,我什么也不怕的时候更硬。他打你,你愈怂,愈投降,他就愈欺侮你。有人说,就是因为你太硬,挨的揍受的罪才比别人厉害。这话也对。可是,我这性格不就是这么打出来的吗?
我接着往下说。他们打完我,就拉出去游街示众了。院子里边敲锣打鼓,集合队伍,喊口号,唱革命歌曲。还有一堆挨整的,头戴高帽子,都站在院子里。厂长书记也在里边,还有一个会计,上中学时集体参加过三青团,现在就是历史反革命了。这会计最后是被推到白灰里呛死的,我是亲眼看到的。
他们把压我腿上的杠子撤了,我已经站不起来了,两条腿感觉已经不是我的了。他们把我架下楼,游街就开始了。从厂子东门出去,绕一大圈,再从西门进厂。这时,满街都是游街的。街上的人往我们身上扔石块、石膏、泥巴、煤,还有人上来抽一嘴巴。满身都是扔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鼻子淌血,没有人样了。
我的腿已经木了,两只脚的骨头碎了,一双破皮鞋里全是血,脚肿起来,没法走了,我就把鞋脱掉提着。我也不知道自己这双脚这双腿怎么走了这么长的路。给我力量的不是人们对我的推推搡搡,而是走在我前边的两个老农民和两个孩子。
冯:你们厂的游街怎么会有农民和孩子?
韩:当时街上不少游街队伍,碰到一起就合到一起。这游街的农民和孩子都是从别的队伍合进来的,合进来就走在我们前边。两个农民一个是卖白菜的,一个是买白菜的,那时农民买卖自己的农产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碰巧抓到了就拉进游街的队伍里来。他俩手里各拿着一面锣,前边卖白菜的农民敲一下锣,说一句:我不该卖白菜,后边买白菜的农民敲一下锣,说一句:我不该买白菜。那两个孩子是土坝子小学的学生,学校叫学生到校外边拾废铁,有一定的数量要求,孩子拾不到,就去工厂偷,每人偷了一根铁棍,叫人抓住了,也推到游街队伍里来。游街时叫这两个孩子背着偷来的铁棍,铁棍有二十多斤重,走长了,快给压得趴下了,腰弯成一个钩,还硬往前一步步走,这两个孩子的形象给了我力量。他们走得了,为什么我走不了。我走过的地方,都有两只脚的血印子。
冯:我无法想象你当时的心情。
韩:可是这时奇迹出现了,就在这当口我的儿子突然出现了。
冯:儿子?你那小狗吗?它怎么会来了?
韩:是呵,它忽然从人群里蹿出来,扑到我身上,两个前爪子亲热地抓我,拉我衣服,从我裤裆下边钻过来,钻过去,用鼻子闻闻我的膝盖,我的腿,好像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好像它知道我受苦,浑身上下又是土,又是血。我当时已不成人样了,它是怎么认出来的呢?可是就在这时,押着我的那些人轰它,怎么轰也轰不走,还朝他们吼叫,他们火了,挥起杠子打下去,儿子惨叫,几杠子都打在它腰上,下手极重,我猜是打断了脊梁骨。它叫着挤出人群跑了;但是,它的出现给我增添了力量。
冯:什么力量?
韩:情感就是力量。人性也是力量。
冯:可惜这种人性在人身上不存在了,是狗体现出来的。你儿子的脊梁真的断了吗?
韩:我从此再没见过它。
冯:你知道巴金先生听了你这只狗的故事,被感动了,想起自己爱犬的遭遇,写下他那篇著名的散文《小狗包弟》?
韩:知道。
冯:你后来没有一点它的消息了吗?
韩:有,咱们后边再谈。
冯:此时此刻你的世界里肯定没有艺术了。
韩:你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有一部作品。
冯:怎么可能?什么作品?
韩:画。
冯:想象的吧。
韩:不,是画的,我告诉你。游街回来后,我们几个被斗的牛鬼蛇神坐在大礼堂前台阶上等着吃饭,饭后还要继续游街。这时,我的皮鞋不是一直提在手里吗?鞋壳里不是灌满了血吗?我忽然发现从鞋尖流出来的血淌在地上,那血的形状有点像个鸡头,我有了绘画的感觉,顺手用鞋尖蘸着血把这只鸡画了出来。
冯:这种时候你怎么可能还会去画画,而且是用血去画?能告诉我在那种情境里你从哪里产生的这种艺术行为?
韩:由着本性吧,因为我是画画的。
冯:现实那么残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韩:艺术对于我是听其自然的。
冯:这是什么姿态的鸡?
韩:站立着的,雄鸡,好像是这样吧!
冯:美好的形象吗?
韩:当然,它是我心里的,与这现实无关。
冯:它是美好的,但是用血画的。如果这只鸡还在,那一定是文革时期最伟大的作品。它的伟大不亚于毕加索的和平鸽。可是我们无从找到它了。
韩:就在我画这只血鸡时,过来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用柳条抽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叫我们喊他们爸爸,还踢我们。我们人都快给打烂了,哪里还受得住踢。
冯:那你们怎么办?
韩: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只是他们的恶作剧。再说这并不能怪他们,是那个社会告诉他们我们是坏人。我们只好叫他们爸爸,不停地叫他们爸爸。
冯:下午继续游街吗?
韩:是,一天下来我们走了十里路,我也不知道自己两条破腿怎么走了这么长的路。游完街,就被送到公安局的看守所。进了看守所,被看守上来踹一脚便跪下,朝我喝叫:现在宣布,拘留淮南瓷器厂反革命分子韩美林,你签字吧!我签完字,我们厂里的人就走了,我归公安局管了。警察把绑我的绳子铁丝解了,我的手脚和身上,不是紫的就是黑的,然后被两个警察押着走过院子,进到里边。
进看守所先要登记,然后解下皮带,身上的东西掏出来,工作证,一点钱,还有那木雕人,都交出来;刻刀在游街时掉了。没想到,我在这里被拘押多年,等到出来时,我那条皮带由于沾了不少血,还有汗水,沤湿发霉,全都烂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