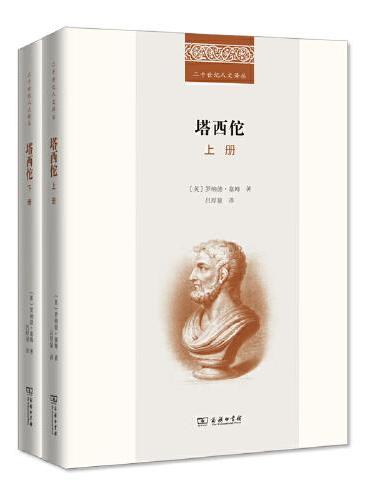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图解机械工程入门
》
售價:NT$
440.0

《
中文版SOLIDWORKS 2024机械设计从入门到精通(实战案例版)
》
售價:NT$
450.0

《
旷野人生:吉姆·罗杰斯的全球投资探险
》
售價:NT$
345.0

《
希腊人(伊恩·莫里斯文明史系列)
》
售價:NT$
845.0

《
世界巨变:严复的角色(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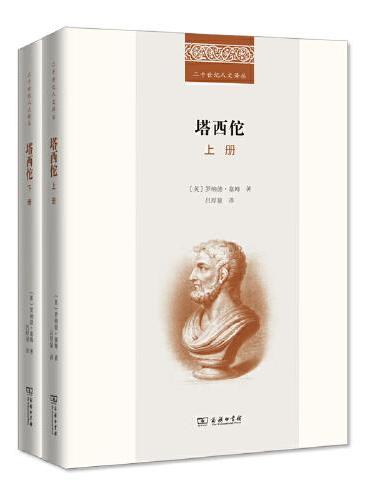
《
塔西佗(全二册)(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
售價:NT$
1800.0

《
宋初三先生集(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
售價:NT$
990.0

《
简帛时代与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上下册)(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1400.0
|
| 編輯推薦: |
相关图书推荐链接:
1.《小文艺口袋文库:不过是垃圾》
2.《小文艺口袋文库:正当防卫》
3.《小文艺口袋文库:夏朗的望远镜》
4.《小文艺口袋文库:北地爱情》
|
| 內容簡介: |
《二马路上的天使》中张起出狱以后的反常生活让他紧张不安、不知所措,他找不到什么有意义有趣的事情,只能用混乱的语言和行动来掩饰内心的不安全感。
《抒情时代》中的副教授袁枚、讲师张亮将精力和才情放在了勾心斗角、互相拆台、玩弄学生上,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在混乱的庸常生活中随波逐流李洱的小说以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为题材,透彻地写出了知识分子徒有知识,却处处显得无能和无力的生活状态。
|
| 關於作者: |
|
李洱,中国先锋文学之后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始终坚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短篇小说集《午后的诗学》《饶舌的哑巴》《破镜而出》等。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曾把德文版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一书送给中国总理*。该书被《普鲁士报》称为配得上它所获得的一切荣誉。
|
| 內容試閱:
|
二马路上的天使
二马路上的天使到了郑州,一下火车,我就给张起打了个电话,说我要在郑州呆几天,赶快给我准备住处。张起问: 是一个人住还是两个人住?我听出了他的话外音,说: 如果你硬要给我找个伴,让我享几天艳福,我也不会摆什么架子。张起立即笑了起来,说一切都包在他身上。他还连声夸我进步了,进步很快。
电话是在车站广场打的。电话亭的四周,蹲着许多滞留在郑州的民工,他们显得既焦虑又漠然。在他们的头顶上,悬挂着各种广告条幅的氢气球,像星斗一样飘浮着。我是一个烟鬼,所以我特别注意那些香烟广告。我注意到美国健牌香烟的英文书写是KENT,它在提醒人们吸烟有害健康。国产香烟的巨型广告上面,是炎黄二帝的头像。我一边打电话,一边透过玻璃瞧着广场。外面的景象,就像爆炸的瞬间突然凝结起来的样子,让人感到混乱和空寂。张起在追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模模糊糊听到电话里传来汽车刹车的声音,就问张起是否正在执行公务。张起说他确实正在路上,正在送老板回家。
他要我坐出租车到尔雅小区,在小区幼儿园的门口等他。幼儿园在哪儿?我问。他说你一进小区就知道了,哪里吵就往哪里去。现在我无法去接你,晚上我请你吃驴肉。
母校离车站不算远,坐一〇二路电车,用不了半个钟头,就可以到。也就是说我其实很快就可以见到正等着我的巴松。我从电话亭出来的时候,一〇二路电车刚好停在我身边。一帮人拎着大包小包往上面挤着,一个小孩夹在当中,被挤得哇哇乱哭。那其实是一辆空车,坐不满的,但人们还是担心失去自己的位置。我没有上去,而是站在一边,抽着烟,看着那辆车慢慢开走。
尔雅小区在郑州的东北部,是个新建的高级住宅区。出租车司机显然把我看成了有钱的住户,当我提醒他该找钱的时候,他用鼻孔哼了一声,才把钱递给我。
张起这小子混得不错啊。我想起几年前我到牢里探望他的情形。那时候他的头发全脱光了,就像个秃鹫。他可怜巴巴地要求我把吸剩的半包烟留下,同时敏捷地把一封信塞到我的手心。那是他写给马莲的一封信。在简短的交谈中,我得知他在牢里摇身一变,成了医生。医生?你的医术怎么样?我低声问着,生怕别人听见。他倒显得大大咧咧的,说: 我其实光管打针,反正人犯的屁股又不值钱,扎烂也就扎烂了。临分别的时候,他的脸色有点难看,眼角也有点湿润。他盯着我手中的信,沉默不语。我当然知道他的心事。后来,我把那封信交给了巴松,由巴松转给了马莲。
我一进小区,就悉心捕捉孩子们的叫声。因为是阴天,下午四点钟,天好像就快黑了。我在小区里转了好半天,也没有摸着幼儿园的门,因为我根本听不到孩子的声音。一个中年妇女在垃圾罐旁边给鸽子破膛,她动作很熟练,有点漫不经心的。手中的刀子几乎不费什么劲,就从肛门豁到了嗉子。我看了一会儿,问她幼儿园在哪儿,她没吭声,只是用手指了一下。
刚才在小区里转圈的时候,其实已经从幼儿园门口走过多次了,只是我并没有料到它就是。幼儿园的房子和四周的楼房,除了高度上的差异,其样式,墙壁上的卡通画,四周的草皮,都大同小异。那个小院子里没有什么孩子,倒是有几对打羽毛球的中年人。
张起很晚才回来。他把车倒进幼儿园的小院子里,然后做出拥抱的架势,朝我走过来。和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搂到一起,对我还是头一次。搂了一会儿,他松开我,说,老板请客,令他在一旁作陪,他不能不从。他问我是不是饿了,我说: 要不是在这里等你,几只鸽子就已经进肚了。他不解其意,微笑地望着我,似乎在等我作进一步的解释。我懒得解释,问他: 马莲现在还好吧?还行,他说。我又问他们是否领了营业执照(结婚证),他说领个鬼,还没有顾上呢。
张起将我领进了最靠边的一幢小楼,上到第五层。跟我上楼时想的不一样,房间虽然装修得不错,但完全说不上舒适。因为吊了顶,房顶显得很低,上面再装上几个枝型吊灯,就难免给人一种压抑之感。房间还很乱,大厅的柞木地板上堆放着一些玻璃和纸箱。有一只破纸箱就放在门口,一些像鸟一样的东西散落在地上,使得这里既像个仓库,又像个鸟窝,看来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住人了。
张起拾起一只鸟,说,好好看看,这是鹦鹉,刚生产出来的,跟真的一样会学舌。他这么一说,我就发现它确实像一只鹦鹉,几乎可以乱真。张起从皮带上取下钥匙,拧着鹦哥的肚脐。这里有个暗锁,他说。他从身上摸出一节电池,装到鹦鹉的肚子里。这是一只公鹦鹉,得找个母的跟它配对。他说着,就开始在那堆鹦鹉里刨,检查每只鹦鹉的屁股,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只母的,往它的肚子里也装了一节电池。他把鸟递给我,说: 为了这些鸟,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头发,又快掉光了。张起话音刚落,我的手心就震动了起来。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吓得差点把它甩出去。关上开关,然后再打开,张起说。我手忙脚乱地在它身上摸了一遍,也不知道是否摸着了地方,正担心的时候,张起说了一句: 我爱你。我还在纳闷,两只鹦鹉突然开口了,它们说的也是我爱你,此起彼伏,像卡通片中的人物的声音。
这样玩了一会儿,张起示意我把电池抠出来。好玩吧?张起问。接着他告诉我,这里面装有三种特制的芯片,是航天飞机上用的芯片,都是走私过来的,所以不能小看这些鸟。
是你造出来的?我问他。
主意是我出的,一个研制坦克的人帮助设计的。他说,这玩意现在已经在美国登陆,一开口就是地道的美式英语。
如果我不提醒他我还没有吃饭,他就光顾着说他的鸟了。我没有吃到驴肉。他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许诺,用方便面、鱼肉罐头和一罐可口可乐把我打发了。饭是在卧室吃的。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这套房子并不属于张起,因为这是女人的卧室。张起说用可乐将方便面冲下,吃得快还不掉渣。不掉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吃得太快了。我一边啃着,一边想着下一步可能有什么发生。那些摆放在梳妆台上的香水瓶、睫毛钳、防晒霜以及墙上贴着的好莱坞明星们搂抱的剧照,都预示着一种可能。我有点紧张,也有点为张起的盛情感动。
我想,下一步张起可能会借故走开,只留下我一个人,然后我将听到一个女人的敲门声。张起眼下正盘腿坐在地板上剔牙,牙床剔出了血也不知道。他有点神情恍惚。这是可以理解的,将一个女人(很可能还是他的情人)送给别人,谁都会犹豫,更何况我的这位朋友本来就不是很大方。
吃完之后,我用可乐漱了漱嘴,拍拍肚子站了起来,说: 我想洗个澡躺下来。张起不让,他说洗什么洗,见一次面不容易,咱们先聊聊嘛。巴松曾在电话中说,张起现在变得很怪,话多,见到熟人就走不动了,似乎担心别人把他看成哑巴。巴松还说,张起一静下来以为自己还身在牢门,所以他很想热闹,可是一吵闹,他就会有被审讯的感觉,所以他又渴望清静。看来巴松说的没错。可我现在实在没有心思跟他闲聊,我觉得还是先洗澡要紧。我说: 一身臭汗,影响谈兴,我得洗洗,是不是你这里不能洗?张起说,洗倒是能洗,就是得费点劲。他很不情愿地陪我走到客厅,指着一扇漆成白色的门,说: 进去吧,这里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
无法进去,因为装鹦鹉的那些纸箱堵在门口。我试着搬了一下,腰都快使断了,也没能将它挪开。张起也下手了,两个人累了一身汗,终于将它挪到了一边。张起说: 我也得洗一下,我们可以边洗边聊。
浴缸是粉红色的,上面落了一层灰。张起先用水冲了一下,然后,抓着缸沿上搭的一块毛巾,擦了起来。擦着擦着,他的手突然停了下来: 一只用过的避孕套从毛巾里跑了出来。我用脚趾挑了挑那东西,感觉到了它的柔软和上面细小的刺样的东西。你笑什么笑?张起问。我说: 你还挺负责任的。我把那个东西指给他看,他说: 你真是少见多怪,这种带刺的玩意,街上到处都是。这么说着,他自个儿先笑了起来,然后,他问我戴哪个型号的,我不好意思说大,也不好意思说小,就说戴的是中号。他说彼此彼此,他戴的也是三十三毫米的。他告诉我,马莲有时候也来这里住,这房间的钥匙,就是从马莲那里拿过来的。马莲用惯这个了,他说。他把套子放到了浴缸上方用来插花的篮子里。那里面有一枝经过风干处理,不会变型的玫瑰花。张起拿着它闻了闻,又把它放回了原处。
不会有什么人来了,我想。虽然我并不期望一定要在这天晚上享受到艳福,可意识到这一点,我还是有点失望。我还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因为我没有对不起乔云萍。
张起这会儿开始取笑我,他说他早就看出来我有点不对头,又是漱口,又是梳头,还嚷着要把自己洗干净。你是不是想着我已经把人给你预备好了?他说。我懒得分辩,只说了一句: 这不能完全怪我,是你把我的胃口吊起来的。他听了哈哈大笑,就像他妈的一只鸭子。
想搞女人还不容易?可以说差不多跟手淫一样容易,在这方面我有足够的发言权,张起说。他说,有那么一阵子,他急着要把积攒了一年的能量释放出来,而马莲又不能随叫随到,他就听从一个朋友的建议,去了几次舞厅。那里的女人果然非常容易上勾,容易得让人感到失去了起码的乐趣,因为它排斥过程和技术,让人难以适应。张起这种说法,我在别处也听到过,我总觉得有点言过其实,不足为信。张起一定捕捉到了我的这种心理,他一边往身上撩水,一边说: 当然这要看你去的是什么舞厅了。听我的话,你别去那种高档的舞厅,那地方的女人,漂亮是漂亮,珠光宝气的,但常常有脏病,花钱买病,不划算。你可以去中档舞厅,那里的女人大多是知识女性,她们往往是因为耐不住寂寞,出来放风的。和前一类比起来,她们更讲究曲径通幽,这就用得上了技术,就看你的功夫到家不到家了,只要你能把她引出来,上床的概率就十有八九了。他再一次强调,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发言权,讲的都是真理。
他讲的我不能说没有兴趣,但我更关注的是怎样打发这个漫漫长夜。我想,如果我现在在巴松那里的话,我大概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即便是在淋浴,张起也要叼着烟。他就有这种本事,浑身湿透,而嘴巴和烟却是干的。他提出要给我搓背,我担心他的烟灰烫伤我的屁股,就要求他把烟掐灭。他说: 掐灭干什么,我一边吸一边给你讲故事吧。他说他刚进去的时候,并不会吸烟,是慢慢学会的。这倒是真的,上大学的时候,在同寝室的六个同学中,只有他和巴松不抽烟,巴松比他还敏感,闻到烟味,嗓子眼就发痒。他说,进到里面之后,不会抽的,也慢慢地会抽了。他说里面并不禁烟,禁的是火,可禁烟和禁火实际上是一回事,没火你怎么抽?可人们还是变成了烟鬼,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呢。他说,为了搞到火种,人们差一点重新回到原始时代。探监者送来的火石,成了无价之宝。将牙刷把烧软,然后把火石按进去,是保留火种的经典方式。需要抽烟的时候,就拿牙刷把在平时收集到的坐便器的碎片上猛擦,让火星冒出来,那就跟猿人钻木取火似的。周围那些急猴们,看到火星,就赶紧把棉花团递过去,然后一帮人小心翼翼地把它吹燃。张起说,这种取火技术,他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有机会我给你表演一次,他说。
洗完澡,人显得很困乏,回到卧室我就躺下了。张起却毫无睡意,他还想接着聊。这时候电话响了,他走到梳妆台前接电话。我听见他说,厂里的事并不像外面说的那么严重。他们好像还抬了一会儿杠。我听出张起有点不高兴,抬高嗓门说了一句: 要是真飞不出去的话,你就让它飞回来好了。接着,他又给马莲打了一个电话,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通,并说,咱们当然得先通通气。他又说他现在和我呆在一起,老同学见一次面不容易,他明天不想上班了,要陪我好好玩玩。马莲说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听张起说: 先别挂,还有一件事我得说一下,你以后洗完澡,要把浴室弄干净。他们又说了一会儿,张起摇了摇我,说: 醒一醒,马莲问你和乔云萍好,她说她有空就过来陪你玩。我得拉上马莲,陪你好好玩玩,他说,不说别的,就说你去看我那一次,我就得记一辈子,我记得你还给了一包烟。还有谁去看过你?我问。他说还有巴松。还是老同学亲啊,我说,马莲也去过吧?他说: 她懂我,她知道男人不想让女人看见自己的软弱,所以没去。
过了十二点,我入睡就困难了,脑子既昏沉又兴奋,只好陪着他聊下去。后来还是谈到了巴松。我说明天我得见一下巴松,张起说: 见他干什么,走的时候给他打个招呼就行了,你跟他玩不到一块的。
我只好对他说,既然来了,还是见见为好。巴松遇到了一点麻烦,写信让我们帮帮他,我对张起说,其实他用不着找我,找你就行了,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能遇到什么麻烦?张起说,我怎么没有听说。
第二天,我和张起醒得都不算晚。因为没睡踏实,我的脑仁有点隐隐作痛,不得不下楼买了点清凉油。张起说他可以开车把我送到母校。他站在镜前刮胡子,用舌头挑着腮帮,让我看看是否刮干净了,还拉着衣领,问它够不够挺刮。他还特别注意他头上的那几根毛,把四周的尽量往当中捋,盖住当中的那片空地,然后喷上摩丝,使之定型。这叫地方支援中央,他说。
他给马莲打了一个电话,可没有打通。他还要再打,说把马莲叫过来,大家在一起聚一下。我说,不是说好了要去见巴松的吗?他说: 这也行,你可以先跟他聊聊,我呢,就不去了,不搅扰你们了。
上车之后,我感到有必要给他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见巴松。我说: 巴松迷上了一个女的,但不知道如何下手,想让我给他指点一下,他不知道真正的高手就坐在我旁边。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张起说,原来是这个。他还说: 其实你本人就是这方面的高手,当年,那么多人追乔云萍,只有你没有白忙乎。
他说的没错。乔云萍当时在我们年级,确实是第一支花,打她主意的人也确实不少。我和她结婚之后,她对此还常常津津乐道。我记得巴松曾问过我是用什么魔法把乔云萍娶到手的,我没有给他说那么多,只是对他说,这有点少儿不宜,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车到了我们母校门口,张起真的要走。他说他发过誓,一辈子不再进这个校院,即便它是个天堂。他的这种情绪,我是可以理解的。当初,母校的个别老师,为了保护自己,对张起干过一些落井下石的事。看来张起一直没有原谅他们。他对我说: 我不进去了,说吧,让我什么时候来接你。我没法把时间定下来,就说再联系吧。他朝我摆摆手,把车开走了。
天色还早,校院里人还不多。跟几年前相比,校院显得更加凌乱。新出现了一些楼,楼的式样非中非西、非古非今,显得不伦不类。还多了一些铁栅栏,就是带有矛尖的那种,它们将楼和空地都圈了起来。有不少人,主要是上了年纪的人,在栅栏内外练气功、慢跑或作操。我想巴松这会儿一定起来了。上大学的时候,他的外号就叫公鸡,每天都起得很早。他睡在我的上铺,他一醒来,别人就别想睡踏实了,因为他走路、洗脸、刷牙,声音都很响,能把人烦死。可大家都并不怎么恼他,对他还比较宽容。这是因为他对我们有用: 这只小公鸡,能将班上的女生引到我们寝室。女生们来找他,目的很明确,就是抄他的作业。她们不抄我们的作业,好像这有点丢人似的。抄巴松的似乎就不存在丢人的问题了,因为这并不能说明她们不会做,只能说明她们懒得做,才让男孩子替她们做的。
巴松引来的那些女生,后来纷纷成了我们的女友。我们寝室六个人,除了巴松,都从那些女生中挑到了自己的相好。譬如,我挑到了乔云萍,张起挑到了马莲。乔、马等人成了我们这些人的女友之后,并没有断绝和巴松的来往。有的女生还主动替巴松打毛衣,小气一点的,也给他织过手套。她们这样做,丝毫没有引起我们的醋意。毕业之后,巴松到上海上了研究生,然后他又回到了母校。在他给我的信中,我得知他现在给学生开了一门选修课,叫斯宾诺莎研究他担心我不知道斯宾诺莎是谁,就特意告诉我,这是个荷兰人,是梵高和古力特的同乡。斯宾诺莎的哲学就像郁金香一样沁人心脾,选修这门课的人出乎意料地多,在信中他这样写道。
摸到巴松住的教工宿舍楼,我看到楼前的水泥地上躺着许多人。他们都还没有睡醒。我想巴松说不定也在外面过夜,就挨个儿查看那些人。其中有一个人,我比较面熟。我想了想,想起他是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同学,在校期间就入了党,张油亮的苇席上,肚脐周围落着几只苍蝇。我走过去的时候,他突然翻了个身,吓了我一跳。那几只苍蝇比我镇定,它们并没有离开他,飞了一圈,又落到了他的屁眼儿周围。
没能在那里找到巴松,我就按图索骥上楼去找他。上到六楼(顶楼),一扇门正好半开着。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闲人免进。不知哪个闲人在免字上添了一点,使它变成了兔字。
我没敲门就进去了。巴松果然已经起床,他穿得整整齐齐的,正坐在一面大镜子前发呆。那是一面椭圆形的镜子,没有镜框,靠着墙放在桌子上。他通过镜子看到了我,但他并没有立即转过身来,而是盯着镜子看了一会儿,才慢慢地搓着手站起来。好玩得很,他站起来之后,还有点发愣,直到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才醒过来神,惊讶地抓住我放在他肩膀上的手。
你终于来了,他说。在那一刻,我的感觉好极了,觉得自己就像是巴松的救命恩人似的,这种感觉可不是你想有就能有的。当然,我同时也觉得有点可笑。巴松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还是那么瘦。当我们这些人都发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他还能保持原来的体型,真让人羡慕。当然,变化还是有的。他原来面相白净,现在却满脸是毛,胡子从鬓角一直长到下巴。他发现我在看他的胡子,就很不自然地摸着鬓角笑了起来。既然我是他请来的,我就有必要先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威。去把胡子刮掉,我对他说。
为什么?他问。少说那么多,我对他说,哪个女孩愿意让毛茸茸的嘴巴往自己脸上凑呢?你去照照镜子,看你像不像电视里的孙猴子,妖精们都喜欢唐僧,我还没听说有哪个妖精喜欢孙猴子呢。
真有那么严重吗?他问我。我只好装得正儿八经,说: 听我的没错,别因为这几撮毛坏了大事。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事实上,一直到我离开郑州的时候,他也没有把胡子刮掉。我事先也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在我要求他刮胡子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怎么向女孩子解释他的胡子: 你看,巴松的胡子多么像画框,画框就是界限,将他与庸常的生活分隔开了,就冲着他的胡子,我如果是个女的,就会嫁给他。我当然不指望这番话能把女孩说动。但见到女孩,总得开几句玩笑,活跃一下气氛吧?而巴松的胡子正是现成的由头,有了这样不伦不类的胡子,见到女孩就不会冷场了。
面对陷入单相思、热恋,或失恋中的人,你对他的尊重和安慰,就是克服厌倦情绪,听他津津有味或痛苦不堪地讲下去,不要随便插嘴,因为他其实并不需要你发表意见。他需要的只是你作出听的样子。
巴松提到那个名叫杜蓓的女孩子时,显得小心翼翼的,好像那是个易碎的器皿,稍有不慎,就会摔成一堆无用的碎片。她是巴松在二马路盯上的。上个学期刚开学的时候,巴松的扁桃体发炎化脓了,到二马路上的一家医院打针。一天下午,细雨霏霏(陈旧的诗意背景),他从医院出来,在那条混乱不堪的马路上推着车慢慢地走。刚进入秋天,天还不冷,可扁桃体化脓导致的高烧,还是让他感到了寒意。巴松青霉素过敏,他注射的是红霉素。红霉素刺激胃,使他直想呕吐。在巴松所描述的霏霏细雨中,他左手捂住胸脯,右手推着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破车,在马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就在这时候,他发现在他前面几米远的地方,冒出来一个女人。喜欢看女人,这是男人都有的爱好,巴松自然也不例外。他首先要看的是女人的光腿。巴松虽然没有详细地描述那双腿,但可以想象,那双腿即便算不上优秀,也不至于很丑陋。它们牵引着巴松,让他不由自主地跟着走。在给我的信中,巴松这样描述他初次见到杜蓓的感觉: 就像疲乏的农人在深夜的雪地里行走,突然看见了半埋在雪堆中的红色谷仓。不过在信中,他没有说那个女孩名叫杜蓓。
二马路向西,是郑州最繁华的商业区。它是郑州迈向现代化都市的标志(一些路牌上写着: 郑州的明天东方芝加哥)。几座大商厦以及商厦之间的天桥,围绕着一个小广场。广场中央有座塔叫二七塔,所以广场叫二七广场。二七塔是为纪念因罢工而死的烈士修建的,它是郑州市的象征,至少许多书上都是这么说的。巴松跟随那个女孩(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她名叫杜蓓)来到广场的时候,雨已经停了。阳光照耀着地上的水洼,使地面像个破碎的玻璃,反射着混乱的光线,有时使人睁不开眼睛。
巴松看到女孩在二七广场慢慢走着,就像一只悠闲的鸽子。在四周商厦的玻璃墙面的映衬下,巴松越看越觉得这个女孩和别人有点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她跟周围的环境好像既有关系又没有关系,这很怪,是吧?巴松说。她的衣料,雨伞(她把它收成短短的一截,像夹一本卷拢的杂志那样,把它夹在腋下)雨靴(红色的,靴筒很低,刚盖住脚脖子),头上的发夹,跟这个城市是有关系的;但是,她的身姿,步态,悠闲的气质,仿佛跟这个城市又没有什么关系。她就像个天使,巴松说,我觉得她就像个天使。
天使绕着二七塔的基座,在各种车辆之间穿行。巴松现在离她只有几步远。他甚至能看清她腿上的血管,像草茎一样发蓝。从二七塔顶垂挂下来的广告条幅,一直拖到地面。那是洋酒XO的广告。从未喝过洋酒的巴松,现在就站在那个条幅旁边。他现在感到头有点晕,就像是被广告上的洋酒灌醉了。就在这个时候,女孩绕着二七塔转了过来。那是一张略带忧郁的脸,忧郁使她的脸有一种沉静的韵味。
她也看见了他。让他惊奇的是,她似乎还认识他,在和他插肩而过的时候,她的眼神说明了这一点。
巴松越说越玄了。不过,下面这句话,却是很实际的。他说,当他醒过神来,想和她打个招呼的时候,她却突然没影了,这个时候,他只是觉得有点遗憾,还谈不上什么痛苦。他在广场上又停留了一小会儿,就骑车离开了广场。在返校的路上,他的胃又难受了起来。
我当然还会去留意别的女人的背影,但我没发现一个好的。说到这里,诚实的巴松害羞地搓着鬓角,笑了起来。
不妨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第二次相遇,巴松就不会有现在这种痛苦了,他会继续猫在屋里,老老实实地搞斯宾诺莎的神、人及其幸福论。问题是,命运要奇怪地安排他和天使杜蓓再次邂逅,而且时间还很短,就在第二天。
他还是去打点滴,打的还是红霉素。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把昨天的事给忘了。可他又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看到了天使光洁的腿,忧郁的脸。这次,他还发现天使很丰满,走路的时候,腰部扭动的幅度恰到好处。天使在同一个广告条幅下面,朝他微微颔首,然后,未等他作出反应,她就又在车流和杂乱的人群中消失了。
巴松相信,在同一时问,同一地点,与天使的相遇还会发生第三次。他已经想过,再见到她时,他一定鼓足勇气上前搭话,并向她说明,这种相遇只能出自神的安排。但是,第三天早上,他爬起来的时候,奇怪地感觉到自己的扁桃体不疼了。他用牙刷的把儿压住舌面,反复照镜子。扁桃体确实已经没有脓点。他马上想到这是天使在暗中起了作用,使那个小小的扁桃体在一夜之间恢复了原状。
斯宾诺莎比他现在还年轻的时候,曾经钻研过磨透镜的技艺。巴松相信现在照着他的喉咙的这面玻璃镜子与斯宾诺莎有关,而镜子里的那个无用的已经消去了脓斑的扁桃体与天使有关。通过磨透镜,斯宾诺莎有了某种异教徒的倾向,并且一辈子不结婚,而通过照镜子,我们的巴松成了二流时代的爱情的信徒。
扁桃体虽然已经还原,可是继续打针,巩固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问题是这天下午又有他的选修课,他不能不上。他相信,如果神让他见着她,那么他早晚还会见到她第三次的。
那堂课他讲得很出色。他讲的是斯宾诺莎有关爱的论述。巴松现在又把他那堂课的讲义从书堆里翻了出来,把他那天引用的斯宾诺莎的话给我念了一遍。爱的特点在于,我们从不想使自己从爱中解脱出来,如同从惊异或其他激情中解脱出来一样,这有下面两个理由: 一个是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另一个是我们不从爱中解脱出来是必要的。
在我眼中,巴松实在不能算是一个有激情的人,可他说,那堂课他讲得很有激情。我讲得从来没有这么好,他说。当然他也说出了他的遗憾: 缺课的人太多了,教室里的空位有一多半,而且还有不少学生一进教室,就埋头睡觉。
巴松讲得嘴唇都起皮了。喝杯水再讲,我对他说。他讲的时候,我可没少喝水,因为我早上没吃东西,巴松又想不起来给我弄点东西吃,我只好喝水。巴松看到暖水瓶被我喝空了,就说,他不需要喝水。我说,你得多喝水,否则你的扁桃体又要发炎了。巴松这才拎着水瓶,到下面的水房去打水。他走了之后,我像个耗子似的,赶快翻东西吃。在他的书架上,我找到了一盒熊仔饼干,几盒酒心巧克力(看来是给杜蓓准备的)。等他回来的时候,熊仔们已经被我吃去了一多半。
我替杜蓓吃了,我对他说。我让他看保质期,他一看就叫了起来,说: 怎么回事,刚买的怎么就过期了呢?他捏了一块尝尝,说,吃还是能吃的。
一坐下来,巴松就又接着讲开了。他说他后来又往二马路跑了几趟,可再也没有见到她。有一天,就跟做梦似的,他在学校的操场上看学生打排球,突然看到了她。她也在那里看球。他认准是她,就朝她走了过去。对他的走近,她显得有点吃惊,还想避开他。他站在她旁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想了想,他说: 我在二马路上见过你两次。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
这一局打得不好。她说。
她说的是球,可在他看来,她的话仿佛另有深意。这时候,球队开始换人,从球场上下来的一个女生,走到杜蓓跟前,接过杜蓓替她拿的外套,同时神秘地朝杜蓓笑笑,说: 你跟巴老师聊吧,我先走了。
这一天的下午,他在打开水的时候,又碰到了那个和杜蓓说话的女生。那个女生一见她,就跟他开玩笑,说: 巴老师,你跟杜蓓很能聊得来,是吧?
平时,学生们是不跟他开玩笑的,可今天,这个学生是个例外(我后来见到了这个学生)。直到这个时候,巴松才知道,他要找的那个天使名叫杜蓓,是四年级的学生,而且还选修了他的课(只是很少上课而已)。
巴松说,他平时不和学生打交道的,上课时也很少注意学生的脸,所以他不认识她并不奇怪。他的这个说法有点可疑,虽然我并不怀疑巴松的诚实。
巴松坦言,他以前最看不惯老师和学生谈恋爱,称之为胡搞。他经常看到有些女生和老师手拉手地在校院里走。在一次开会的时候,系领导还批评过一个教现代汉语的老师,说他把女生的肚子搞大,有点过分了。那个老师私下说,这不能全怨他,现在市面上卖的避孕套,质量不过关,他也没有办法。总不能让她去带避孕环吧?那个老师说。
巴松找到了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 我事先可不知道她是学生,现在我也没有把她看成学生,我是把她看成了天使。
后来,他多次在校院里遇到这个天使。让他难受的是,她每次见到他,都要躲,只有实在躲不开了,才会站在那里听他说上几句。鉴于二马路上的相遇是他们的共同经历,他当然每次都要从这里说起。可是,往往是他刚说出二马路三个字,她就显得很不耐烦,而且还满脸不高兴。问题是,她越是要躲避他,他就越是觉得自己爱的人非她莫属。巴松的考虑是这样的: 她的逃避,只能说明她很纯洁,值得我去爱。因此,虽然追不上她,他却并不气恼。相反,他的感觉还非常好,觉得自己过得充实。
但最近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杜蓓即将毕业了,也就是说,她即将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一想到她将在另外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和别人谈情说爱,他就感到她的未来一定充满痛苦;而一想到她可能会受苦,他的心就不得安宁。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 你怎么知道她会受苦呢?
这还用问!他说。
他不愿解释,他想做的是继续讲下去。他说,情况最近又有了变化,给我写的信发出之后,他得知杜蓓因成绩优异,已经列入直升研究生的人选。他说,这事年前就定了下来,可他刚刚得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