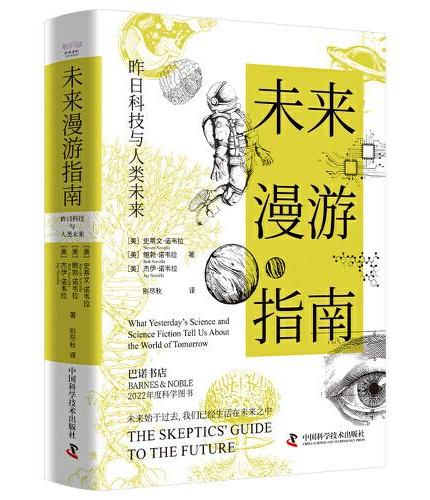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无法从容的人生:路遥传
》
售價:NT$
340.0

《
亚述: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的兴衰
》
售價:NT$
490.0

《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采煤机智能制造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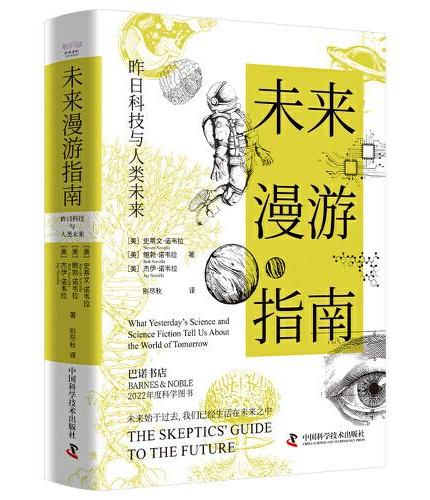
《
未来漫游指南:昨日科技与人类未来
》
售價:NT$
445.0

《
新民说·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上下册)
》
售價:NT$
790.0

《
我从何来:自我的心理学探问
》
售價:NT$
545.0

《
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
》
售價:NT$
390.0

《
送你一匹马(“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看三毛如何拒绝内耗,为自己而活)
》
售價:NT$
295.0
|
| 編輯推薦: |
|
对于中国人类学界来说,这是第一部有关香港社会的民族志研究。香港回归十多年来,大陆依然缺乏香港社会的民族志研究,缺乏对香港本土社会的具体了解和深入研究。因此大陆社会包括官方、民间和传媒,对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解,尤其是对香港以各种社会运动表现的社会景观存在误读。本书通过3年左右的田野调查,以民族志的形式展示了当代香港的公共政治过程,并讨论了西方政治理论如何在儒家文明和社会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具有香港特色的公共政治,并以内在的他者这一全新的视角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可以参照的对象,体现了人类学文化批评的自觉。
|
| 內容簡介: |
|
在中国人类学学界里,这是*部建立在长时间田野作业基础上的有关香港社会的著作。全书用权力的生成这一理论框架组织民族志材料的叙述,系统地阐述了无权者之权力的前提和原则,无权者之权力生长的机遇与限制,权力生长的社会戏剧、组织机制、网络机制和有效的行动机制和途径,以及其与无须暴力的国家权力形成的对抗性合作这一政治生态。
|
| 關於作者: |
|
夏循祥,男,湖北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1995),武汉大学社会学硕士(200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博士(2010),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哲学博士(与北京大学联合培养,2011)。现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医学人文教研室讲师,兼任中山大学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研究员等。主要研究兴趣为政治人类学、香港研究、城市研究等。
|
| 目錄:
|
导 言 理论的提出与研究资料的获取
第一节 文献回顾与概念框架
第二节 研究地点、方法及资料的获取
第三节 结构与安排
第一章 湾仔:百年旧区,香港之根
第一节 湾仔概况
第二节 湾仔小史
第三节 与海争地
第四节 时光隧道
第五节 湾仔生活
第六节 苏丝黄的世界
第七节 旧区街道
第八节 湾仔的中环化
第九节 保育战场
第二章 利东街:唐楼、街道与本土经济
第一节 唐楼
第二节 利东街
第三章 权力生长的机遇与限制
第一节 未民主化的政府与非政治化的社会
第二节 社会运动推动的政治
第三节 香港人:关注的旁观者
第四节 社会运动的机遇与限制
第四章 权力生长的社会戏剧
第一节 既有权力关系的破裂
第二节 当前权力关系的危机
第三节 权力体系的补救
第四节 权力关系的分歧
第五章 权力生长的组织机制
第一节 内部运行机制
第二节 组织者阿冼
第三节 无权者何为?
第六章 权力生长的网络机制
第一节 多元化义工
第二节 多层次网络
第七章 权力生长的行动机制
第一节 常规的行动
第二节 艺术的行动
第三节 建设性行动
第四节 公民教育行动
第八章 对抗性合作:两种权力,三个面向
第一节 当权者:有效行使权力
第二节 无权者:合法生长权力
第三节 对抗性合作
第九章 总结与探讨
参考文献
原博士论文后记:一条刚刚开始的路
出版后记:在痛苦中前行
|
| 內容試閱:
|
序言一 凝视世界的意志与学术行动
能叙事才好成事。是表述主体才可能是社会主体。
到海外去!
到民间去,曾经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生期所酝酿出来的口号。先有具备学术规范的社会调查,才有社会科学的出现。在少数人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一句凝结着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到民间去成为1919年之后的知识界的运动,在中国促成书斋学问之外的社会调查之风蓬勃兴起。社会科学诸学科此前在中国主要是课堂传授的西方书本知识,到民间去的调查之风呼唤着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逐渐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
今日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则萌发着另一种冲动,一种积聚了很久、压抑了很久的求知之志,这就是:到海外去!
曾经,在大家都不能出国的时期,我们在政治关怀上满怀豪情,而只是浪漫地放眼世界。今天,去海外旅行在中国已经大众化了,看世界的欲望已如春潮涌动。中国的知识界要做的是以规范的学术方式走进世界之后凝视世界!
关于社会调查,关于经验研究,到海外去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机会。社会调查的眼界有多宽,社会科学的格局才可能有多大。几辈知识分子在民间、在本土开展调查研究,奠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格局。我们今天到海外去,到异国他乡去认识世界,则是为了中国社会科学明天的新格局。
到海外做民族志
中国人出国,在镀金淘金挥金之外,新增加了一个目标,这就是扎在一个地方把它作为一种社会、一种文化来观察,然后写出有学理支撑的报告,名之曰海外民族志。虽然到目前只有10多个人怀抱着这个目标走出国门,但是它的学术和社会意义不同凡响。
海外民族志,是指一国的人类学学子到国外(境外)的具体社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而撰写的研究报告。这种实地调查应该符合人类学田野作业的规范,需要以参与观察为主,需要采用当地人的语言进行交流,并且需要持续至少一年的周期。
在西方人类学的正统和常识中,民族志就是基于异国田野作业的研究报告,海外是民族志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它们是没有海外民族志这个说法的。
人类学民族志的标杆是由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玛格丽特米德那批充满学术激情的青年才俊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著作所树立起来的。他们各自从伦敦,从纽约背起行囊,乘船出海,到大洋中的小岛和野蛮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完成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萨摩亚人的成年》等经典的民族志著作。他们是第一批靠民族志成为人类学家进而成为学术领袖的人物。他们的职业生涯成为人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做民族志,总要有充沛的激情让自己想得够远,走得够远。在拥有成千上万的人类学从业者的西方国家,即使后来在国内社会做民族志的人逐渐多起来,但是,到海外做民族志还是一直被尊为人类学人才培养的正途。
但是,对于中国的人类学共同体来说,民族志一直都是一种家乡研究,一种对于本乡本土、本族本国的调查报告,因此,海外从来都是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志所缺少的一个要素,所未曾企及的一个视野,所没有发育起来的一种性质,当然也是今天绝对需要的一种格局。
一般都说中国人类学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才有组织地把田野作业推进到海外,这项迟来的事业让我们终于可以跨越百年的遗憾。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具有人类学专业的国内高校正陆续把一个一个的学子送到海外开展规范的田野作业。
中国学人到海外做民族志的时代尽管迟来但已经大步走来!
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
一个共同体,在关于世界的叙事中所占的位置与它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是关联在一起的。民族志是共同体对共同体的表述地位、能力以及主体性明确程度的知识证明。
学术是用文字表达的抽象观念。文字是个人一段一段书写的,但是抽象观念不是在个人意义上能够成立的。学术是共同体的衍生物、伴随品。共同体造就学人,共同体产生知识兴趣、共鸣群体(读者),共同体传承学术成果。反过来,学术则催生新的共同体或促成共同体的新生。
具有集体意识的共同体必须是表述者,必须是能够言说自我、言说他人的表述者。民族志是关于共同体表述地位是否存在的证明,是共同体通过特定的表述得以构成或显现为主体的知识途径,是共同体的表述者身份的名片。
虽然民族志的主笔者是个人,虽然民族志的材料来自被访谈的个人,虽然一部一部的民族志都有各自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在集合起来的总体效用上,民族志承载着共同体对共同体的结构性关系。 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与非洲和拉美的关系,既是由西方所生产的器物所支撑的,由西方的武器所打出来的;也是由西方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叙事所建构的。这种结构性关系是难以改变的,但不是不能改变的。改变,只能由器物生产的实力和叙事的表述能力所构成的合力来促成。
在前现代,作为表述者的共同体是各自说话,并且主要是自说自话,偶尔才说及他人,对他人的表述和自我表述都难以直接影响他人社会,即使慢慢偶然传播到他人社会了,影响效果也总是以缓慢而曲折的方式发生。
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兴起,尤其是民族志的兴起,造成了一种知识后果,这就是群体作为自我与作为他者都被置于同一个表述所组成的社会景观之中,置于西方作为世界中心的这个社会结构之中。从视角来分析这种社会结构的知识关系,西方之所以处于世界的中心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观察者、表述者都是从西方往外看的。也就是说,从民族志来分析,作者都是西方学者或者学习西方的学者,而文本内容所叙述的都是非西方社会的事情;在共同体层次,西方是凝视者,非西方是被观察对象。知识的社会后果早就凸显出来:关于他人社会的叙事不仅在不断满足西方大众的猎奇之心,而且在知识和社会观念上不断强化我群与他群的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如果我群与他群的相互表述是不平等的,这种结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如果相互表述是极端不平等的,那么这种结构关系也是极端不平等的。民族志的作者在自己的社会中不过是一个普通学者,而在共同体的关系中却支撑着其共同体的优越地位。西方作为民族志叙事的主体,同时也成为普遍主义思维模型的创立者,普世价值的申说者、裁判者,世界议题的设置者。
不过,后现代的世界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一波来势汹汹的全球化,也是世界各个共同体、各个层次的共同体的力量和关系的再结构化机会。意识形态批判使西方中心主义得到深刻反省,新技术、新媒体与人口流动使关于他人的叙述不再能够作为一面之词而成立。更多的共同体能够在国际平台上成为关于世界的叙事者了,世界真正变得紧密了,于是,共同体的代表者对自我的表述与对他人的表述都会同时影响自我和他人在结构中的位置和关系。共同体在全球社会景观中的位置和关系是由代表者的表述和他们参与的表述的总和所塑造的。
中国学者是一个后来的参与群体。后来有遗憾,但是后来者必然有不一样的机会和优势。
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
西方人类学家打造了民族志的镜子,用它来审视非西方社会;我们从西方拿来民族志方法的镜子,我们几十年来只拿它观照自己。现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族志方法其实是一把多面镜,它可以观照我们,其实更方便观照我们之外的世界。
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是要靠关于社会的叙事来支撑的。支撑西方社会科学的是关于全球范围的社会叙事,而支撑中国社会科学的是限于中国内地的社会叙事。相比较而言,西方社会科学是以西方为中心看世界,而中国社会科学是以西方的学术眼光看中国。西方学者跑遍世界,当然也跑遍了中国各地,撰写了成千上万的民族志,建立了关于世界的叙事;中国学者也出国,当然主要是到西方国家,但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只是把西方当作一个大学,那里只是求学的知识殿堂,并不是他们做田野调查的地方。他们回国才做调查研究。
中国追求现代化100多年,几辈学者介绍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化国家的思想和理论,但是从来没有为国人提供特定的现代社会在社区层次的实际运作的经验知识。现代社会具体是怎样的?现代生活对于个人如何是可能的?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认真提过这种问题,中国的人类学也没有将其当作使命来回答过这种问题,当然就一直没有相应对象的民族志出现。
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科学也是以追求真理、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规律为自我期许的。但是,中国在近代以来主要是在政治、军事上纠缠在国际事务之中,在学术上因第一手经验研究的缺乏是处于国际之外的。我们也关心亚非拉人民,也声援发达国家的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正义事业,不过,这大多是在政治、道义上的努力。在知识产业上,中国的社会科学一直都是一种家庭作坊,是一种自产自销的格局:学者们在自己的社会中发掘经验材料,以国内的政府、同行、大众为诉求对象。一些学科也涉及国际世界,甚至以国际社会为论题,但是基本上都是站在(或藏在)中国社会之中对外人信息间接引用与想象的混合物。没有进入世界的田野作业,没有关于国际社会的民族志作为支撑,何来以现实世界为调查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
中国的社会科学,从关于中国、关注中国社会、关心中国发展的社会科学,到认知全球社会的科学,必须从最基本的海外民族志个案积累开始。中国学界的海外民族志将逐步建构中国对于世界的表述主体,中国将从民族志观察的对象转变为叙述世界的主体。在国际社会科学中,中国从单向地被注视,发展出对世界的注视,以此为基础,作为表征社会知识生产关系之核心的看就必须用注视-对视(也就是相视)的范畴来对待了。获得社会知识的单方面的审视总是被抱怨包含轻视、敌视,但是对视以及作为其产物的相互表述的民族志将在国际社会之间造成相视而笑的效果,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期盼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结果。
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与中国人口都在世界上占最大的比重。中国学人和中文加入关于世界的实地调查研究中来,世界社会科学无疑将因之大为改变。更多的参与者、更多的视角看世界,看彼此,被呈现的世界将会大不相同。
展望中国社会科学新格局
因为心中有春天,我们看见嫩芽会欢欣。
海外民族志是未来的人类学家出师的汇报演出。没有人指望其中有多少大师的代表作,但是它们无疑都是地区研究的一个区域的开拓性著作,更加确信的是,它们的作者是中国人类学乃至社会科学在国外社会大展经验研究的开路先锋,是为我们的共同体在知识世界开疆扩土的功臣。它们的作者从熟悉的家园到远方、到异国他乡去,拓展了中文世界的空间。它们从社会知识生产的源头而来,就像涓涓溪水从雪山而来,假以时日,配以地势,必将汇聚成知识的海洋。
我们年轻的人类学者已经走进世界,在泰国、蒙古、马来西亚、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巴西、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地,深入一个社区进行起码一年的参与式社会调查。他们会带动越来越多的学人参与,世界上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中国学界的关注点。他们陆陆续续地会完成自己的民族志成果,用中文书写当前世界各种社会的文化图像。他们的民族志个案今后可以组合成为对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研究,对于金砖四国的综合研究,对于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社会的比较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特别期盼对于非洲大陆、阿拉伯世界、太平洋众多岛国的研究,特别期盼对于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缅甸、越南的研究
海外民族志在中国的广泛开展,将改变中国社会科学单一的学科体制。中国社会科学按照学科划分为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分属不同学科的学人要开展合作,并没有学科体制的平台。民族志比较发达的那些知识共同体,如美国、日本,在学科分列的同时还有一个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体制。在学科与地区研究并行的体制中,大学教授分属不同学科的院系,但是相同的地区研究兴趣又把不同院系的教授连接起来。这个方向的发展是以关于国外社会的民族志为基础的,但不是人类学家单独能够操作的。我们刚刚开头的海外民族志事业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派生地区研究的机会却是靠整个学界才能够把握的。
海外民族志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领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在学术上也会更上一层楼。海外民族志除了在共同体层次上、在整体上对于社会科学具有重大意义之外,在技术层次、操作层次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也会是很实在的。从业者只在中国社会做调查与同时在海外社会做调查,代表着不同的眼界、不同的事实来源。更开阔的眼界对于议题的选择、对象的甄选、观念的形成都会更胜一筹。学术的精进总伴随着寻找更广泛的社会事实来源;由国际社会经验比较所支持的论说可能更加有力。
相对比较紧迫的是,海外民族志是疗治中国社会科学严重落后于时代的病症的一剂良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学者却只在本国的社会中做实地调查。中国把大量资源投在外语学习上,却没有几个人是计划学了语言去国外社会做调查研究的。中国的商品拥挤在世界各地,可是它们总是置身在陌生的社会被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挑剔,中国学界没有能够及时为它们创造各个方面都能够熟悉的知识环境。中国大众旅游的洪流已经从国内漫延到国外,在世界上浮光掠影的观光所形塑的世界观是极其偏颇而危险的。所有这一切都在期待中国社会科学的世界眼光。
凝视世界的欲望需要走出去的意志来展现。人类学者是共同体的眼珠子它们被用来看世界,看社会,看社会世界,看世界社会。有眼珠子就能够看,有心才能够凝视。人类学者也是知识群体的脚板子它们要走很远的路,走很多的路,走陌生的路,也就是走没有路的路。有了这样的人类学者群体,一个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才能走得够远,看得更远。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海外民族志项目负责人
序言二
20世纪70年代是城市研究(尤其是在社会学范畴)发生重大突破的时期。曾经作为城市研究主流理论框架的芝加哥学派,未能响应自60年代中期以来在欧美社会陆续出现的新兴社会现象,引起学界的反思与批评。尤为明显的是,当时欧美社会爆发各种新兴的社会运动,令之前很多社会观察家所预言的工业冲突的自行消亡,意识形态的终结统统未能兑现。对于当时城市的状况,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将关注点局限于人口的流动及其地理分布,又或者因城市小区的形成而忽略了社会矛盾和冲突。要进一步了解城市发展的形态,更不能将分析抽离于宏观的政治经济学。当中资本的支配作用和国家干预的内在矛盾,成为新的讨论和分析焦点。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学逐渐打破了芝加哥学派的垄断地位,而发展及推动新兴社会理论的中心,也由美国转移到欧洲。当年的新兴社会理论为城市研究注入了两大重要元素:一是对社会、城市结构中的社会经济矛盾的性质进行深入讨论。人口分布、城市结构的变化等均属于城市转变的表征和变动所带来的后果,而需要分析和揭示的,是在深层次产生着支配力量的经济社会动力资本累积的作用和国家机器在调解矛盾中的角色。例如市区重建便并非只是新旧更替,而是资本如何从中取利和政府怎样通过规划的方式来特别照顾资本的利益的一个过程。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要将城市发展嵌于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中。二是城市矛盾导致社会冲突,而这些新兴的城市社会运动不可简单地理解为工人运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是有其独特的要求和发展路径。经70年代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冲击之后,城市研究对城市生活、发展有了全新的了解。
在众多新的了解之中,权力是核心问题。夏循祥博士的《权力的生成:香港市区重建的民族志》正好针对这个重要的问题,是一本既有理论创新,同时又建立于扎实的田野工作之上的著作。他以香港利东街(亦称为喜帖街)为案例,深入小区,以民族志的方法来了解和呈现当中复杂的过程。这个案例在香港有其特殊意义:它不只是一个由下而上、扎根于小区的文化保育和争取权益的社会运动,也是一场揭示市区重建过程中不同利益、权力的互动的抗争。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当代城市发展的种种重要问题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支配力量、政府角色对资本利益的倾斜、市民在使用城市空间的权利等统统呈现在大众的眼前。城市发展所隐藏的矛盾,是这个个案的背景。
夏循祥博士的研究的更大贡献,在于对市民在参与社会动员后对整个局面所起的作用的分析。他的理论贡献是突显了权力的生成权力并不是静态的,因为若然如此,则一般无权无势的街坊、市民将无法争取改变,扭转形势。他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正好有助于认识整个市民参与的过程,并从过程中看见权力的生成,令一个本来可能是完全一面倒的形势,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夏循祥博士动态的分析,为城市社会运动和城市政治研究补上了重要的一笔。他对权力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在结构性矛盾与社会动员、行动之间找到中介,将两者串联起来,并透过分析过程的发展来了解原来的权力关系如何产生变化。
多年前初认识循祥的时候,他刚来香港读博士班。虽然才刚来不久,却有勇气踏足陌生的小区,进行观察、访谈,这令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我想,他在进行田野考察时,一定比其他本地学生更为困难。但很明显,他能将弱点(不熟悉香港)转化为强项(对区内发生的大小事情特别好奇,并会查根究底),成功地完成他的研究,并发表了这本甚有学术价值的专书。
吕大乐教授
香港教育大学副校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