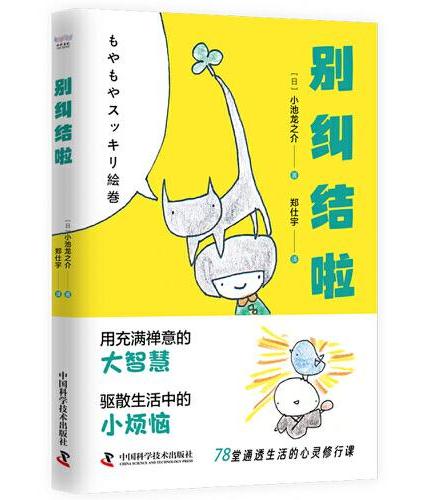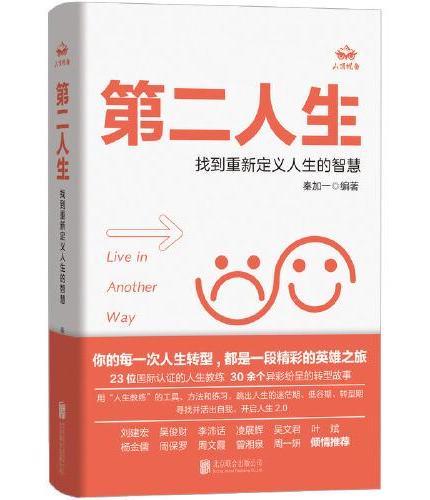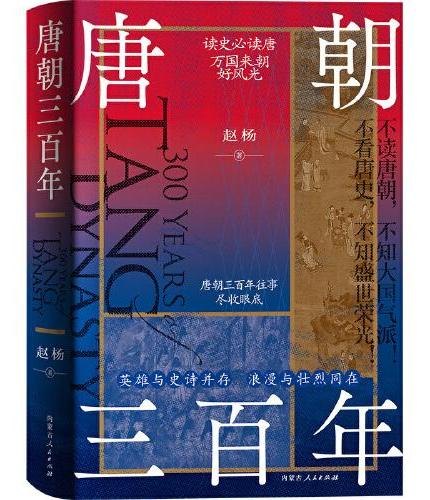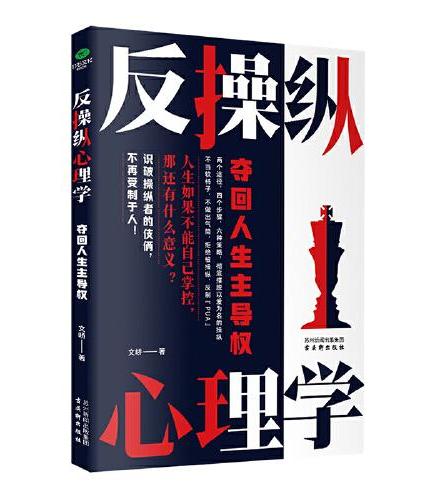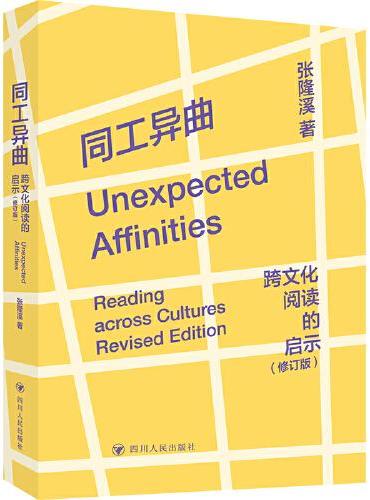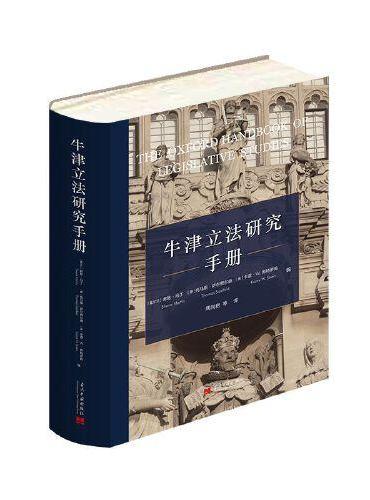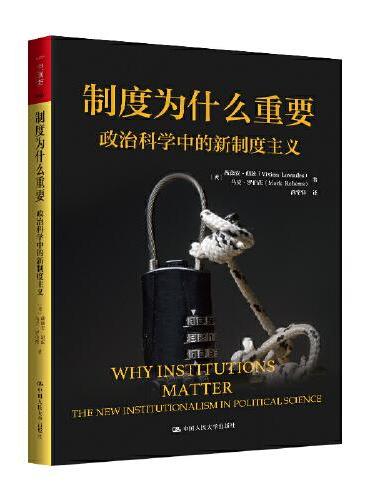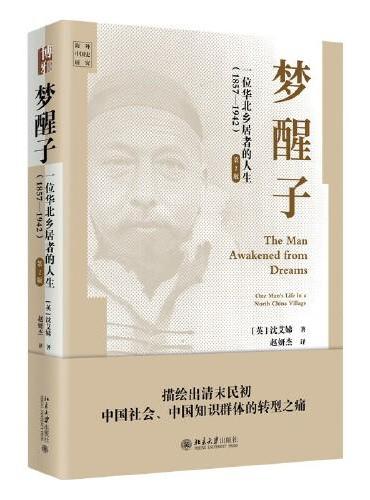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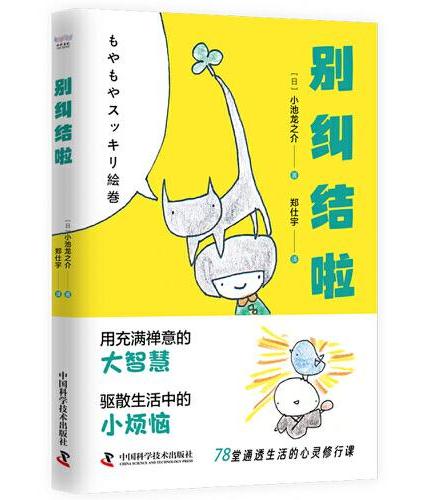
《
别纠结啦:不被情绪牵着走的通透生活指南(“当代一休”小池龙之介治愈新作!附赠精美书签!)
》
售價:NT$
2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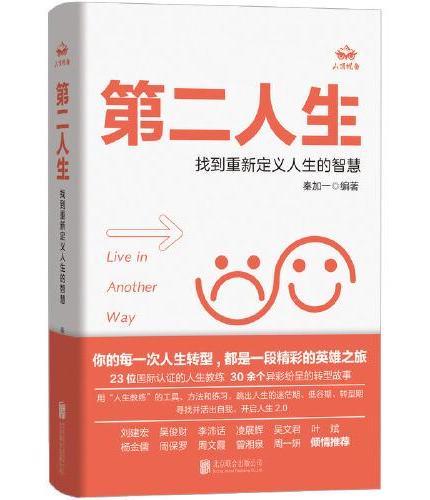
《
第二人生:找到重新定义人生的智慧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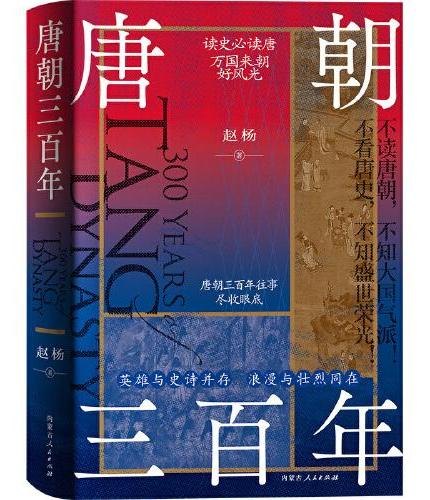
《
唐朝三百年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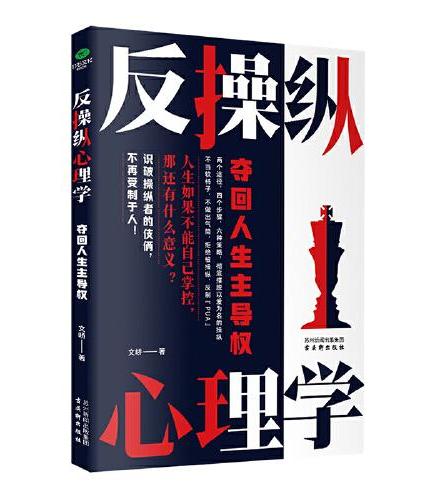
《
反操纵心理学:夺回人生主导权 拒绝被操纵
》
售價:NT$
2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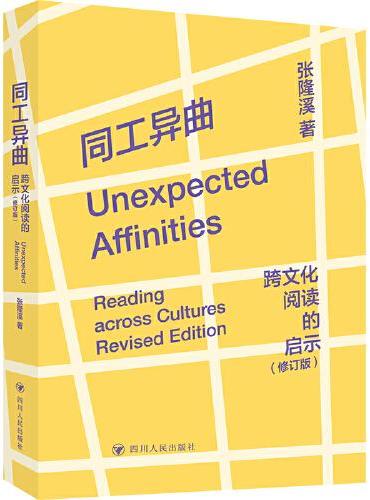
《
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修订版)(师承钱锺书先生,比较文学入门,体量小但内容丰,案例文笔皆精彩)
》
售價:NT$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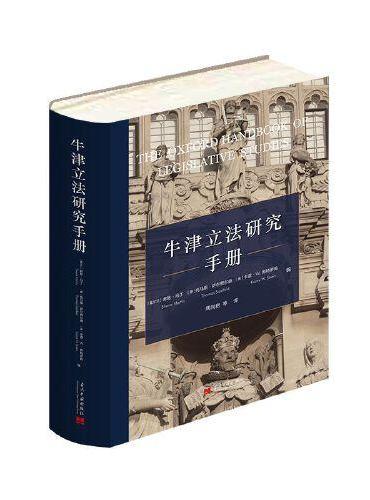
《
牛津立法研究手册
》
售價:NT$
16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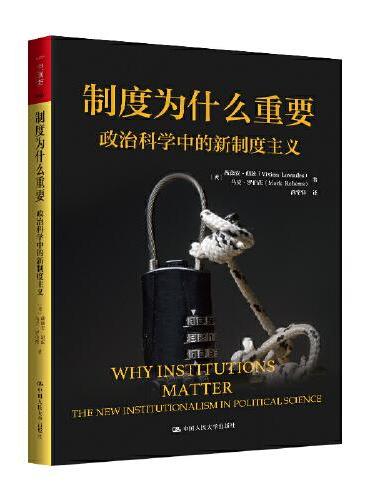
《
制度为什么重要: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人文社科悦读坊)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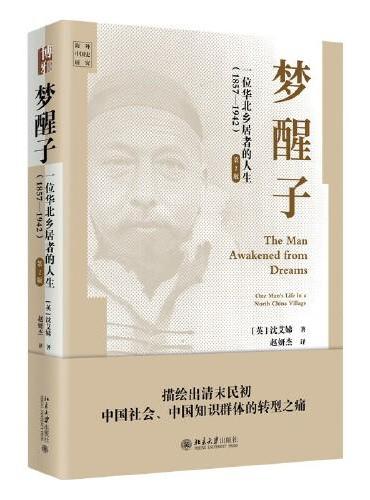
《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第2版)
》
售價:NT$
340.0
|
| 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主人公陶菊生就是作者自己。小说以1924年军阀混战时期河南西南山区为背景,通过被绑票的少年陶菊生的亲身经历,描写了李水沫为头目的一支杆子的传奇生活,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塑造了几个并非坏人的绿林人物。小说彰显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同时也为长篇巨著《李自成》作了思想与艺术准备。
小说译为法文后,姚雪垠被授予马赛纪念勋章。
|
| 關於作者: |
|
姚雪垠(19101999),河南邓州人。曾任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理事、创研部副部长,上海大夏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长夜》《春暖花开的时候》,中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戎马恋》等。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曾获茅盾文学奖。
|
| 內容試閱:
|
为重印《长夜》致读者的一封信
亲爱的读者:
如今我将三十多年前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长夜》送到你们面前,请你们在工作闲暇的时候读一读。请你们在欣赏之余,给予批评。我顺便将关于这部小说的若干问题,以及我的一些创作愿望在解放后未能实现的憾事,在这封长信中告诉你们,使你们更容易了解这部小说,同时也了解我在创作道路上的部分经历。我还要告诉你们《长夜》和《李自成》有密切关系,读《长夜》是打开《李自成》的创作问题的钥匙之一。因此,我将这封信作为《长夜》重印本的代序。
这部长篇小说写于抗日战争末期,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当时只印了两千本,没有引起读者注意,甚至不为人知。但个别读过这部小说的朋友给予一定的重视,告诉我它是一部有意义的作品,写出了别人不曾写过的题材,即民国年间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虽是中国农村的一个侧面,大概也反映了河南全省,也许还包括陕南、陕北、鄂西、皖西、皖北、鲁西、冀南等广大农村二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大同小异的普遍现实。
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虽然也有虚构,但是虚构的成分很少。小说的主人公陶菊生就是我自己。我是农历九月间生的,九月俗称菊月,所以我将主人公起名菊生。这故事发生在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到次年春天,大约一百天的时间。现在我将这一故事的历史背景告诉你们,也许对你们阅读这部小说是有帮助的。
一九二四年的夏天,我从教会办的旧制高等小学毕业后,(我没有读过初小)跟随一位姓杨的同学到了直鲁豫巡阅使、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驻节的洛阳。他的巡阅使署在洛阳西工。洛阳西工成了当时中国北方军阀、政客们纵横捭阖的活跃中心,也是吴佩孚的一个练兵中心。他亲自兼师长的嫡系精锐部队是陆军第三师,大部分驻扎西工。第三师附属有学兵营和幼年兵营。我怀着进幼年兵营当兵的目的到洛阳。我的大哥已于春天受到别人怂恿,进了学兵营当兵。他对于军队内部的黑暗已经有一定认识,坚决不许我当吴佩孚的幼年兵,请那位姓杨的同学将我送到信阳,进教会办的信义中学,插入初中二年级读书。学校设在信阳西门外,浉河北岸,面对贤隐山。
这年九月,酝酿数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吴佩孚离洛阳急速北上,由大总统曹锟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进驻秦皇岛,指挥直系各部队约二十万人向奉军进攻。双方都使出全力作战,战事胶着在山海关和九门口一线。原来也属于直系军阀阵营的冯玉祥,因受吴佩孚排斥,丢掉了河南督军的重要位置,挂一个陆军检阅使的空名义,驻兵南苑。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吴佩孚任命他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命他率部队进入热河,威胁奉军右翼。当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山海关一带鏖战正酣时,冯玉祥暗从热河回师,突然于十月二十三日进入北京,控制了北京各要地,拘押了曹锟,通电主张和平。吴佩孚前后受敌,被迫从大沽口乘船南逃。他将在山海关一带作战的直军交给张福来指挥,随即全线瓦解。吴佩孚从吴淞口入长江,到武汉上岸。他原来打算依靠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力量成立护法军政府,进行反攻,但这些军阀各为自己割据的地盘打算,离心离德。驻节武汉的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对他也是表面拥戴,实际抗拒。吴佩孚不得已急回洛阳,另谋集合兵力。但是反直势力不让他在洛阳有喘息机会,首先是国民二军胡景翼部由冀南攻入河南,接着是镇嵩军的憨玉昆部由潼关东进。吴佩孚不能在洛阳立脚,退驻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而他的部队在信阳车站外挖掘战壕,大有在信阳作战之势。
吴佩孚在鸡公山驻的时间不久,一筹莫展,只好通电下野,暂时到岳阳住下。胡景翼做了河南军务督办,自兼省长。小说结束时,已进入胡景翼做河南督办时代。到这年春天,为抢夺河南地盘,胡景翼和憨玉昆在豫西发生激战,被称为胡憨之战。结果憨玉昆战败。胡景翼不久病故,所以小说结尾处提到薛正礼一股杆子投奔一位将做信阳道尹的绅士家中,那位绅士姓刘,是国民党人。因为胡景翼死去,河南局势大变,姓刘的官梦并未实现。这最后一股杆子的下落,我不清楚。
由于信阳的局势混乱,学校提前放假,通知学生们迅速离校。我同我的二哥,还有另外两个学生,顺铁路往北,到了驻马店,然后往西,奔往邓县(今邓州市),在中途被土匪捉去。被捉去的地方可能属于泌阳县境,我当时也不清楚,只知距离姚亮镇不很远。关于我被捉去的经过和在杆子中的生活,小说中所写的都是真实情况。
土匪们对于如何处置这几位远方朋友不露出一丝口风,带他们顺一条荒僻的小路向东南走去。走着走着,他们渐渐地明白了他们已经成了票从语源上看,票就是钞票。土匪拉人的目的在换取钞票,故江湖上将被绑架勒赎的人叫做票。常常为说话时音节谐和起见,加上一个名词语尾,便成票子。有时为着同钞票区别起见,变成一个复合名词,便成肉票。在票的语根上加一个女性语头,便成花票。大股土匪中拘留票子的地方叫做票房,管理票房的头目叫做票房头。杀害肉票叫做撕票。,暂时也许不会死,但要过一段悲惨而可怕的日子,等候着家庭派人来讲价赎回。
一经猜破这命运的谜底,陶芹生立刻就想到他父母得到这消息后一定是束手无策,无钱来赎,而他和弟弟迟早免不掉一个一个地被土匪杀害。原来他们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上两代不管男女都吸食鸦片,而父亲是在童年时代就开始上瘾。六年以前,大约是初冬季节,像死水一样的平静的乡下发生了匪荒,把他们祖上遗留下来的住宅,连佃户居住的房子一起烧光;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到城内,六年来苦度着穷愁饥寒的日月。大哥小学未毕业就跑到洛阳当学兵,一则因为家庭没力量供他弟兄们同时读书,二则因为这正是丘八老爷横行霸道的时代,三则因为经过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的名字红得发紫。在河南这个封建落后的地方,很多出身于没落的地主之家的青年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又没有机会接触南方的革命思潮,多愿意到吴大帅的第三师投笔从戎。菊生小学毕业后,父亲也送他到洛阳去当幼年兵。先到洛阳当学兵的大哥已经看穿了第三师的黑幕,大哥竭力反对,托朋友将他送到信阳,进一个教会中学读书。芹生原是在湖北樊城读教会中学,因为要照料弟弟,这学期也转到信阳读书。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后,父母对于大哥不知流过了多少眼泪,如今又要为他们两个小兄弟哭泣。但家中的经济情形是那么不好,纵然父母把眼泪哭干又有什么用?想到了这些问题,就像有一把刀子割着芹生的心,眼圈儿禁不住红了起来。
芹生好几次向土匪们说明他同菊生确是亲兄弟,请求留下他,放他的弟弟回家报信,好让家人赶快来赎。菊生也要求留下自己,放哥哥回家报信。对于他们的请求,土匪们不是表示这事情需要看管家的怎么吩咐,便是表示不相信他们是亲兄弟。麻脸的土匪在他们两兄弟的脸上来回地打量几遍,露着黄牙笑起来,用非常肯定的口吻大声叫着说:哼,鬼儿子能相信你俩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虽然胡玉莹竭力替芹生和菊生证明,土匪们也决不相信。当芹生们恳求的次数太多时,车轴汉不耐烦地说:
好好儿走吧!你们对我们说的再多也是瞎子打灯笼,我们不能替管家的做主呵!
又过了一条小河和一个岗坡,土匪们带着这一群落难者走进了一座村庄。你们把他们交到票房,麻脸的土匪对他的同伴说,我自己去对管家的报告一声。于是他把步枪扛在肩头上,得意洋洋地唱着小调,向村子中心的一个大门走去,其余的土匪把票子带进了靠近的一个大门。
菊生们被带去的是一座相当舒适的地主住宅,进了过车大门向左转是三间对厅,票房就设在对厅里边。一进院子,车轴汉活泼得像一个大孩子,一面走一面叫骂,几个看票的都给他骂得笑嘻嘻地从票房里跳了出来。
瓤子九我操你祖宗!车轴汉望着一个白净面皮,手里拿着一根烟钎子的土匪骂着说,来了几个有油水的远方朋友,你鬼儿子尽躺在床上抽大烟,也不走出来迎接一下!
瓤子九快活地回骂他:妈的,有我的孝顺儿子到官条子官条子就是官路,大道。路与败露的露字同音,所以黑话称路为条子。上迎接他们,何必再惊动老子的驾?刘老义鳖儿子到哪里去啦?
老义到管家的那里去啦,我的乖乖。车轴汉用枪托照瓤子九的大腿上打了一下说:闪开,让远方朋友们进去歇歇腿,老子们也该去填瓤子啦犯和饭同音,犯字在土匪中认为是一个不吉利字,凡和犯同音的字都忌说。肚皮里边装有饭好像瓜皮里有瓤子,所以把饭叫瓤子,把吃饭叫做填瓤子。又引伸开去,姓范也改为姓瓤子,票房头瓤子九的本名就是范九。。
菊生们一进票房,首先映入眼睛的是靠左首的一群肉票。这一群共有十来个,有的在草上躺着,有的坐着,已经被折磨得不像人样。他们的憔悴的脸孔上盖满了灰垢,头发和胡子乱蓬蓬的,夹带着草叶和麦秸片,白色的虮子在乱发中结成疙瘩。他们的手都被背绑着,一根绳子把他们的胳膊串连一起,因此任成群的虱子在头上和身上咬,在衣服的外边爬,他们也只有忍受着毫无办法。他们拿黯淡无光的眼珠打量着新来的患难朋友,有的还用凄苦的微笑向新来者表示欢迎,但有的把眉头皱得更紧,脸孔上流露着严肃的表情,仿佛他们觉得这一群可爱的洋学生不该也落在土匪手里,特别那两位最小的学生深深地引起来他们的恻隐之心。
看票的对于这一群远方朋友的来到都非常高兴,替他们找凳子,拿香烟,真像招待自己的朋友一样亲切。票房头瓤子九忙着吩咐人去向老百姓派蒸馍和下面条给客人充饥。被派出的土匪刚走不久,他又派另一个土匪去催,并嘱咐要顶好的白面蒸馍。他虽然年纪在四十之谱,但为人很活泼,滑稽,爱同人开玩笑。在他下水蹚原来徒步涉水叫做蹚,是北方的一个口语。引伸开去,到社会上混人物也叫做蹚,如蹚光棍、蹚绅士、蹚土匪。混得好就算蹚得开,混得不好就算蹚不开。在这部小说中,土匪都自称为蹚将,这大概是那时代那一带地方流行的江湖话。之前,他有个绰号叫快活笼子,如今因为瓤子九这名字也很有意思,原先的绰号就不再被人叫起。躺下去吸完了斗门上的半个烟泡,瓤子九又立刻从床上跳下来,靠着柱子,向胸前叉起双手,笑嘻嘻地盘问新来的远方朋友。他有一双一般人所说的桃花眼,年岁没有腐蚀掉这双眼睛的风流神情。当菊生报告他是吴佩孚的幼年兵以后,瓤子九拍着屁股向前边跳一步,探着身子,睁大一双含笑的眼睛大声盘问:
你是幼年兵?你也到山海关去打仗了?
我们幼年兵在洛阳留守,菊生坦然说,没有开到前线去。
你会唱军歌不会?
当然会。
下过操么?慢步,正步,跑步,都练过?
都练过。
好,待一会儿填过了瓤子,我得考考你。军队的事情我不外行,你操不好我就教教你。瓤子九笑着说,端详着菊生的脸孔,晃着脑袋表示不相信。停一停,他轻轻地拍一拍菊生的头顶,又开着玩笑说:你这小家伙聪明胆大,到蹚将窝里来还要冒充军人呢!随即他快活地大笑起来,很有风味的稀胡子随着他的笑声跳动,增加了他的滑稽神情。
胡玉莹和那个中年小商人都为菊生的扯谎捏了一把汗。菊生虽然也知道说谎话终究不能够骗住土匪,但既然刚才在路上如此扯谎,如今也不好改口,将来的结果就只好暂不去管。他对于人生还没有多的经验。在他的眼睛里,瓤子九是一个有趣人物,瓤子九的部下也都不坏,单就大家对他们的亲切招待也可以看出在瓤子九的这个小团体中充满着江湖义气。在进到票房以后,芹生感到的是绝望的害怕和忧愁,而菊生所感到的害怕和忧愁都非常朦胧,甚至他对于这遭遇还起了一点好奇和新鲜之感。
瓤子九一面快活地笑着,跳到一个躺着的票子身上走几步,又踢一踢另一个已经割去了一只耳朵的票子的头,转过身来对新来的远方朋友说:再有几天他们不赎出去,就叫他们吃洋点心了。这一个惨无人道的小场面和这一句威胁性的话,使菊生起一身鸡皮疙瘩。中年商人低下头轻轻地叹息一声,胡玉莹和芹生都面如土色,而小学生张明才骇得像傻子一样。但菊生的不切实际的浪漫性格,和他从故乡的野蛮社会与旧小说上所获得的那一种英雄思想,使他依然竭力保持着脸上的微笑。他的神气是那么顽皮和满不在乎,使瓤子九和全票房的土匪们都把赞赏的眼光集中在他的脸上。
这个娃儿倒很沉住气。土匪们笑着说。
菊生一半是由于饿,一半是由于他对于新遭遇不像别人一样的害怕和发愁,这顿午饭他吃得特别多。瓤子九拍一拍他的头顶说:别作假啊作假就是客气,不过专指客人不肯尽量吃饱而言,不像客气一词可以随便使用。,待一会儿还要看你下操哩!菊生仰起脸来笑一笑,顽皮地回答说:当然不作假,吃饱啦不想家。吃毕饭,瓤子九真叫他先唱了两个军歌,然后又拔慢步。多亏那时的军国民教育,陶菊生能够圆满地度过了这个考试。
你家里一定有几十顷田,瓤子九躺下去烧着大烟说,凡是到老吴那里当学兵的都是有钱的主户主户就是地主家庭。。
既然家里有钱有地,又何必出外当兵?菊生强辩说。
你们这班有钱的少爷谁不想作官呀?只要喝过墨水子,到老吴那里干三年五载,肩膀头上就明煌煌的指军官的肩章。!
瓤子九把烟泡一会儿捏扁,一会儿滚圆,最后滚成光溜溜的圆锥形,安到斗门上,欠着身子向远方朋友举一举烟枪,连说了两个请字,随即他一点不肯误时地重新躺好,让斗门对准火头,贪馋地吸了起来。他吸得那么惬意,故意使吃吃声成一种活泼调子,而他的黄色稀胡子就随着迅速的节拍跳动。斗门上的烟泡吸光以后,他感到浑身舒服,松劲地抛下烟枪,闭着眼睛,大大地伸个懒腰,从鼻孔哼出来两股白气。过了片刻,他虎地睁开眼睛,从床上坐了起来,向远方朋友说:
你们快点各人给自己家里写一封信,我叫推车的替你们送到。信上就说务必在半个月以内派人来赎,半个月以内不赎就要撕票。俺们的管家的名叫李水沫,来人就到这一带打听李水沫的杆子成股的土匪叫杆子或捻子。。
可是我们是亲弟兄两个,芹生恳求说,请你替我们向管家的求个情,放我们一个回去。
老弟,你这不是故意叫我在管家的面前碰钉子么?瓤子九很和气地说:别说你俩的面貌不像亲兄弟,即令是亲兄弟,咱们这儿也没有白放人的规矩。咱们这儿拉票子就是兜票子。不管家里几口人,一齐兜来,隔些日子不赎就撕一个,或割一个耳朵送回去。你们瞧,那边就有两个票割去耳朵,过几天还要他们吃洋点心呢。
菊生说:家里接信后当然会派人来赎,不过我们家里太穷
看相貌你也不是没钱的孩子!瓤子九跳下床来,走到他的面前嘱咐说:你们在信上记清写一笔:来说票时要照规矩送小礼,每家的小礼是烟土十斤,盒子枪一打,金镏子一打。总之,越快越好,免得管家的生了气,话不好说。
为着票房中只有一张小方桌,这一群新来者就分开在两处写信。芹生和菊生被带到大门左边的书房去,其余的留在票房。芹生和弟弟面对面坐在靠窗的方桌旁边,桌上摆着笔砚和信纸。偏西的阳光凄凉地斜照在他们身上。窗外有一株半枯的老槐树,一只麻雀在树梢上瑟缩地啾啾鸣叫。槐树旁竖着一堆高粱秆,旁边是一个盖着磨石的红薯窖。西风吹着高粱的干叶儿刷刷作响。兄弟两个同时都想起来在故乡常常听到的票子生活,据说土匪把票子的眼睛用膏药贴住,耳朵用松香焊住,口腔用手帕或棉花塞实,手和脚用铁丝穿在一起,就这样投进红薯窖或高粱堆中,纵然军队打旁边经过也无法知道。芹生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提起笔还没有写出一个字,眼泪已经抢先落到纸上。菊生瞟了他二哥一眼,泪珠忽然涌出眼眶,但赶忙偷偷擦去,为的不愿叫看守的土匪瞧到。他忍着哽咽小声说:
信上不要写得太可怕,免得娘要哭坏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