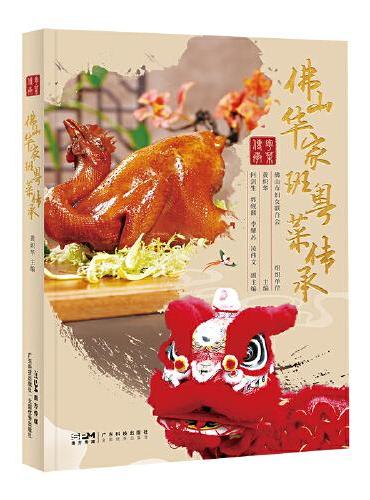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甲骨文丛书·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
》
售價:NT$
1367.0

《
欲望与家庭小说
》
售價:NT$
449.0

《
惜华年(全两册)
》
售價:NT$
320.0

《
甲骨文丛书·古代中国的军事文化
》
售價:NT$
454.0

《
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套装全4册):从未见过的王朝内争编著史
》
售價:NT$
1112.0

《
半导体纳米器件:物理、技术和应用
》
售價:NT$
806.0

《
创客精选项目设计与制作 第2版 刘笑笑 颜志勇 严国陶
》
售價:NT$
2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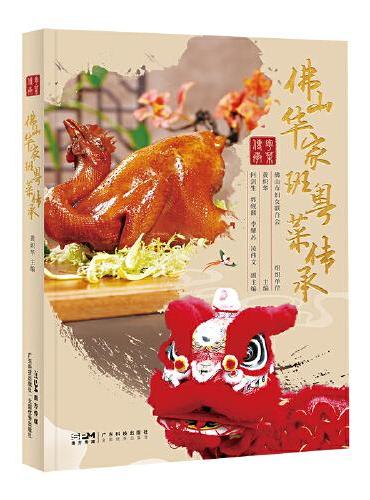
《
佛山华家班粤菜传承 华家班59位大厨 102道粤菜 图文并茂 菜式制作视频 粤菜故事技法 佛山传统文化 广东科技
》
售價:NT$
1010.0
|
| 編輯推薦: |
从这里走进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聆听乔伊斯与但丁对谈,徘徊于奈瓦尔的瓦卢瓦氤氲,重历三个世代的美国神话蜚声文坛的百科全书式作家埃科,召唤古今大师、历数文学公案、自白文字生涯。
★信手一捻,就是几百年的文学公案
★随口召唤,无数文学大师听命还魂
★十八堂贯古通今的文学课,集学者埃科思想之大成
★洋洋万言的创作自白书,坦陈小说家埃科诞生机缘
★从学者埃科的文学讲堂到小说家埃科的秘密后花园
★带你了解埃科的文学全景图,他的欢欣与焦虑、创作与迷信
★看埃科如何谈文学、品经典
|
| 內容簡介: |
作家如果无法对未来的读者说话,那么他必然是绝望的、不快乐的。
翁贝托埃科
《埃科谈文学》是翁贝托埃科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文学评论专著,收录了十八篇作家为各种场合而做的文学专题演讲和论文。
作为享誉世界的符号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埃科的博古通今在本书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从乔伊斯、博尔赫斯,一路谈到中世纪的但丁、拉伯雷,乃至更加久远的亚里士多德,以不同于一般文学评论家的跨领域视角,精辟地分析了诸多古今呼应的重要文学概念、文学名作反映的恒久人性追求以及文学内蕴的历史进程。全书文采飞扬、思路通达,展卷之间,有如亲临大师文学课。
尤其最后一篇《我如何写作》,更可以说是一部伟大长篇小说的生成指南。埃科的小说素以结构巧妙、高深难懂著称,每一出手都是重量级巨作,看埃科如何亲自讲述自己的创作过程以及概念形成的每个关键,无论是埃科迷、文学爱好者、研究者,还是有意投入写作的读者,都绝对不能错过!
|
| 關於作者: |
|
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1932-2016),欧洲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小说家、符号学家、美学家、史学家、哲学家。出生于意大利亚历山德里亚,博洛尼亚大学教授。著有大量小说和随笔作品,如《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布拉格公墓》和《密涅瓦火柴盒》等。
|
| 目錄:
|
前言
论文学的几项功能
阅读《天堂》
论《共产党宣言》的文体风格
瓦卢瓦之氤氲
王尔德:悖论与警句
作为bachelor的艺术家之形象
拉曼查和巴别之间
博尔赫斯以及我对影响的焦虑
论坎波雷西:血液、身体、生活
论符号体系
论文体风格
雨中的信号灯
形式中的缺陷
互文反讽以及阅读层次
《诗学》与我们
三个反美世代的美国神话
虚假的力量
我如何写作
|
| 內容試閱:
|
我如何写作
肇始阶段,久远以前
身为小说家,我的例子算是反常的。因为我在八岁到十五岁之间便开始写故事和小说,后来我停止了,等到快五十岁的时候才又恢复写作习惯。在这场成年人的傲慢爆发之前,我度过了三十个被认为是谦逊的年头。我说被认为是,这点我是需要解释一下的。让我们按部就班地来,也就是说,像我小说里的习惯一样,回到以往的时空。
当初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总是拿来一本笔记本并从第一页写起。作品的名称细想起来总有萨尔加里的味道,因为他的作品当时是我灵感的来源之一(其他的来源还有凡尔纳、布斯纳尔、雅科利欧,以及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一年的《海陆冒险及旅行画报》,最后这个是在地下室的大箱子里发现的)。所以我想出来的书名便是《拉布拉多的海盗》或《鬼船》。接着在书名页最下方我会写上出版商的名字玛戴纳出版社(Tipografia Matenna),Matenna是Matita(铅笔)和Penna(钢笔)这两个词的大胆混合。然后我就着手在每隔十页的地方放进一张插画,好比德拉瓦雷或是阿马多为萨尔加里的书所画的插画。
插画的选择决定了我接着要写的故事。刚开始的时候,第一章我可能只写几页,一般都用大写字母,而且绝不容许自己做任何改动,以便从出版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无懈可击。显而易见的是,往往才写了几页我便中途放弃了。因此在那个年代,我只是一些未完成的伟大小说的作者。
在这堆啼声初试的作品中(在一次搬家的过程中几乎都丢光了),我只留住一本有头有尾的作品,但是无法确定它的文类所属。那时有人送我一本很大的笔记本当礼物,页面印有淡淡的水平线,页边还有相当宽的紫色空白。这让我灵机一动写下《以日历之名》的书名(第一页标着一九四二年,然后下书第十一年,指的是法西斯政权的纪年,这是当时一般的习惯,也是规定要做的)。那是一个名唤匹林皮姆皮诺的魔法师的日记。他自诩为北冰洋一座岛屿的发现者、殖民者与改革者。那座岛屿名叫阿康恩,岛上的居民都崇拜一位名为日历的神祇。这位匹林皮姆皮诺每一天都会以极度卖弄又讲求精准的态度记录岛民的行为和(我今天会这样形容)他们的社会人类学结构。此外,这些文字当中还错落插入一些文学练习。比方有一则未来派短篇小说是这样写的:路易吉是个好人,所以在亲吻了野兔们的餐盘之后便上拉特兰那里去买现在完成时但在半路上他误闯山区死了。这是英雄行为和慈善举措最昭显的例子,所有的电线杆都为他哀悼。
除此之外,叙述者还描述(并且画下)他所统治的岛屿,岛上的森林、湖泊、海岸以及山区,巨细靡遗地解释他理想中的社会改革,他臣民的宗教仪式以及神话,介绍他的每个大臣,话题还旁及战争和瘟疫文本穿插着绘图,而且故事(并没有遵循任何体裁的规则)写写便成了百科全书。现在回头过来看我们就可发现孩童如何大胆地预告了大人的弱点。
到了最后,我实在不知道要再让国王和他的岛屿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第二十九页就做了结束:我将出发到远方旅行或许我甚至不会回来这里;这里我要做个小小的告白:
以前我宣称自己是魔法师。但那不是事实: 我只是匹林皮姆皮诺而已。请原谅我。
在这些实验之后,我决定自己应该朝滑稽的文体发展,而且也确实写出了一些。假设那个年代有复印机,那我应该早就让那些文字广为流传了;我向同班同学提议,要他们每个人给我足够抄写我一部作品的活页纸,另外还得再多付几张,算是折抵墨水费和抄写工,而我则答应回赠他们每人一本我那冒险故事的手抄本。我还煞有介事地和他们订了契约,心中压根无法体会手抄十本同样的作品是多么累人的事。最后,我只得把一沓沓活页纸还给同学,心中对于自己的失败感到羞愧,不是站在作者的立场,而是站在出版商的立场。
到了中学,我专门写一些叙事文章,因为在那阶段论说文(不能选择主题)已经被记叙文所取代(我们必须描述生活的片断,可有自己选择的成分)。我特别擅长幽默的小品文字。那时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沃德豪斯。至今我仍保有自己的杰作:
我描写自己如何在多次实验之后准备向邻居和亲戚展示一项技术上的奇迹,那就是,世界第一个摔不破的茶杯;我得意洋洋地让它跌落地面,结果当然摔成碎片。
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间我转而尝试史诗的写作,包括对《神曲》的滑稽模仿以及一系列对奥林匹斯山诸神的描写,呈现的是那个黑暗时代的风格,那是物资配给、灯火管制以及拉巴利亚蒂的歌曲正流行的年代。
在我高中的前两年,我写了一本名叫《欧忒耳珀克里皮的一生》(附有插图)的小说,而且那时我在文学上学习的榜样是乔万尼莫斯卡和焦万尼诺瓜雷斯基。到了最后那年,我便开始写一些较具严肃文学性的作品。我认为那个阶段的主要基调是邦滕佩利式的魔幻写实风格。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并且计划改写《音乐会》这部具有吸引人的叙事理念的作品。一位名叫马里奥托比亚的失败作曲家,他让世界上有名的灵媒聚在一起,并教他们以灵体的形式在舞台上再现昔日伟大的音乐家,并令这些音乐家演奏他自己的作品《士瓦本的康拉丁》。贝多芬担任指挥,李斯特弹奏钢琴,帕格尼尼拉小提琴等等。只有一位是当代的音乐家,那就是吹小号的路易斯罗伯逊。有一段描写相当精彩,那就是灵媒渐渐无法让他们创造出来的人物保持活生生的状态,最后,往日那些伟大的音乐家一个接着一个消融掉了,整个过程中乐器发出彼此不协调的哀泣,最后唯一例外的是罗伯逊那不受干扰、魔幻似的小号尖锐的乐音。
我应该让我忠实的读者(我可能会说总共二十四位,这样我就不至于和伟大的曼佐尼的二十五位读者打对台了,其实我是怀着谦逊的心情想胜过他的)自行去分辨,这两个插曲如何在四十年之后的《傅科摆》中重新被利用上。
此外,在这时期我也写了一些年轻宇宙的古老故事,主角是地球以及其他的星球,时间是银河系刚刚诞生的时候,星球彼此之间受到爱欲和嫉妒的牵扯: 在一个故事里面,金星和太阳相爱,费劲要脱离自己的轨道以便自我毁灭在她爱人那炽热发光的大体积内。那是我小小的、不自觉的宇宙奇趣故事。
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对诗开始感兴趣。我大量阅读艰涩难懂的诗作,不过我自己的品位比较偏向卡尔达雷利以及《拉隆达》杂志那些作者的古典主义风格。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对于诗的需要(以及同时发现肖邦的音乐)才引发我那柏拉图式的、说不出口的初恋,或者情况正好相反。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那种混合都是招致苦痛的,甚至是最温柔和最自恋的怀旧愁绪都无法令我在不感到完全彻底羞愧的情况下,去回味当时的努力。不过,从我那次的经验一定浮现出一种严厉的自我批评态度:
在几年之中,这种坚决不动摇的态度已促使我认清一个事实: 我写的诗和青春痘具有相同的、功能上的起源以及外貌。因此我决定(而这决心持续三十年之久)放弃所谓的创造性写作,而仅让自己局限在哲学的反思以及随笔的写作上面。
我如何写作
在这一点上我们便能明白,提出你写作前是否先做笔记,立刻就写首章还是末章,用钢笔、铅笔还是打字机、计算机来写等问题是多么没有用处。因为我们必须建构一个世界,日复一日,并且试过无数的时间结构,因为角色根据常识逻辑或者根据叙事成规(或者违反叙事成规)执行或者必须执行的动作必须符合限制的逻辑(牵涉到不断的再思考、删除以及重写),所以小说写作并没有统一的方式。
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我知道有些作家早上八点起床,在键盘上从八点半敲到十二点(每天至少写出一行),然后停止工作并且外出休闲直到晚上。但我则不一样。首先,当我写一本小说的时候,写作这项行为其实要到后来才会发生。我一开始都先阅读做笔记,替角色画出肖像,为小说中的地名画出地图,为动作定出时间次序。而且这些工作都用细马克笔或是计算机进行,至于选哪一种就看工作的时间和地点为何,或者我想记录的叙事理念或是细节是哪一种:
如果是在坐火车的时候生出灵感那就记在火车票背后,也可以写在笔记本或是资料卡上,可以用圆珠笔、录音带,如果必要的话蓝莓果汁也可以派上用场。
结果后续所发生的是: 我把记录的东西扔到一边,或者撕成一片一片,或者忘在不同的角落,所以我有一个又一个,里面塞满笔记本、不同颜色的大叠笔记、零散小纸片甚至是活页大页纸的盒子。这些性质如此不同的资料能帮助我记忆,因为我会想起曾在印有伦敦某家饭店头衔的信纸上信手写下哪个特别的笔记,或者某章的第一页是在我的书房里潦草写就,用的是标有淡蓝色线条的资料卡和万宝龙牌的笔,而接下去那章却在乡下住所写成,写在一张再生草稿纸的背面。
我完全没有特别的方法,也没有固定的写作时段、日子或者季节。但在写第二本和第三本小说的时候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身在何处,我都可以整理想法、写作笔记、打出草稿,但是当我一有机会能到乡下的住所待上至少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会在计算机上输入一整章的文字。当我离开的时候再把这些文字打印出来并加修改润饰,然后放进抽屉等待成熟,直到下次我再度回到乡下住所的时候。我最初那三本小说就是在自己乡下的住所里定稿的,每本小说的定稿工作大概耗去圣诞假期的二至三个星期。结果是我自己在心里维持一个迷信(而我应该是世界上最不迷信的人:例如走过梯子下面、满心欣喜欢迎从我面前经过的黑猫,还有,为了惩罚迷信的学生,我总爱把大学里的期末考定在礼拜五,如果是十三号那就更好了):除了极次要的更动外,完稿的时间必须定在一月五日以前,也就是我的生日以前。如果当年我无法在这天以前准备好,那我就等到下一年(到那时候,当我在十一月几乎准备好的时候便不计一切排除所有杂务,以期在一月初能定稿)。
在这点上,《波多里诺》又是个例外。起先,我也是一如往常,以同样的节奏到乡下的住所工作,可是大概写到一半的时候,在一九九九年圣诞假期的中间,我被卡住了。我那时想该不是千禧虫在作怪吧。那时我正写到巴尔巴洛萨之死,而且在那章里所发生的事会决定最后那几章的方向以及我描写前往祭司王约翰王国旅程的方式。我一连几个月都毫无进展,而且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跨越那障碍的方法。真的动弹不得,而且我暗中渴望动笔写作从一开始我就最兴致勃勃想完成的那几章,也就是和怪物(尤其是和伊帕吉雅)相遇的那些情节。我梦想能够从那些章节开始,可是除非解决了那令我烦心的问题,否则我是不愿意那样做的。
二〇〇年夏天我再度回到乡下,并在六月中旬绕过海角。我开始构思这本小说的时间是一九九五年,我花了五年时间才来到半途的位置,因此我告诉自己,还得再花上五年时间才能完成。
然而很明显的,在那五年当中,我也将心思全部放在构思这本小说的后半部上面,所以它在我的脑海里(或者心里或者胃囊里,谁知道)已经自动整理得有条不紊了。总而言之,在六月中旬和八月上旬中间,那本书几乎是一鼓作气地自动完成(然后就是耗时数月的检视以及重写,但在此之前,故事可以说已经完成)。在这点上,我许多原则中的一项也破灭了,因为迷信纵使再如何没有道理也算是原则的一种。我并不是在一月五日的那个时间点完成作品。
我想了几天,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接着,我的第一个孙子在八月八日诞生了。一切变得清晰自然;我的这第四本小说不是在我的生日那天而是在他的生日那天写好的。于是我将那本书献给他,而且心里觉得十分踏实。
计算机与写作
计算机影响我的写作究竟有多么深?从我的经验来看影响很大,但从成果的角度观察就无从知道它的分量了。
顺便一提: 许多采访我的人看到《傅科摆》里面谈到一部会创作诗歌以及连属情节的计算机,所以无论如何要我承认整本小说是由计算机里的程序负责写成的,是它发明了所有一切。我注意到,这些都是在新闻编辑部里工作的记者,那时都习惯在计算机上写文章,然后直接送去印刷,所以他们认为人类可以多么仰仗这部有求必应的机器。他们也知道,读他们所写东西的广大群众仍旧认为计算机具有无所不能的魔力,而我们知道,我们写作并不是要告诉读者真相,而是写出他们想看的东西。
后来我有些厌烦,就塞给他们其中一位如下的神奇公式:
首先,你需要一台计算机,这是一部会帮你思考的机器,何况对很多人而言,这可是天大的优点。你所需要的就是几行长度的程序,这连小孩都会。然后你把好几百部小说的内容喂进计算机,还有科学著作、《圣经》、《古兰经》以及好几册的电话簿(这对角色命名很有帮助)。比方,总共有十二万页的东西好了。接着,你又使用另外一个程序,利用随机方式,换句话说,你将所有文本混合起来,稍微调整一下,比方剔除所有字母a。因此你得到的会是一本奇特的作品。到了这个地步,你只需要敲下打印的指令,然后小说便自动印出。可是因为你去掉所有的字母a,所以得出的页数必然少于十二万页。然后你仔细将这些文字读上一遍,读上数遍之后,将最有意义的几段挑出来,将它们装上一部铰接式卡车送往焚化炉。接着你就坐到一棵树下,一手拿着炭笔,一手捧着一本高级的图画本,同时让你的思绪自由翱翔并且写下几行文字。比方:月亮高挂天上,树林沙沙作响。也许一开始出现的不会是一部小说,而是像日本俳句那样的东西;但又何妨,最重要的是开始迈出去的那一步。
没有哪个人有勇气宣扬我的秘方。可是有人说:我们感觉得出来,除了公墓里吹小号那一幕,其他都是在计算机上写出来的;那一幕是真正打动人心的,他一定重写过不知道多少次,而且一定是用笔写出来的。
说来有点不好意思,在这部小说里重叠了多少阶段的草稿,用的书写工具有圆珠笔、钢笔还有细字用马克笔,而且重写的次数也算不清楚,但是唯一在计算机上一气呵成,没有太多改动的正是吹小号的那一章。理由其实相当简单:
这段故事我时时放在心上,对自己对别人不知已经说过多少次,以至于仿佛已经写好似的。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再锦上添花了。
我将手放在键盘上,仿佛在琴键上弹奏一首自己熟悉得无以复加的曲子。如果在那幕场景中有种令人感动的成分,那是由于你自顾自弹奏就好,让你自己随着波涛涌动并记录它,该在那里的自然会在那里。
事实上,计算机的妙处在于它鼓励自然流露,你匆匆忙忙把任何浮上心头的东西一股脑输入进去,而且知道反正日后可以轻易改动它变化它。
计算机的使用实际上关系到修改的问题,因此也就是异文的问题。
《玫瑰的名字》最后几个定稿版本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所以我得修改、重新打字,有时候甚至还要剪剪贴贴,然后折腾半天才能交给打字人员。拿回来后,我必须再度修改,接着又是剪剪贴贴。使用打字机你只能将文本修改到某一程度。在自己重新打字、剪剪贴贴然后再送去请人重新打字的过程中,你很容易感到厌倦。你在校对的阶段进行最后一次更正然后才能送印。
使用计算机以后(《傅科摆》用Wordstar 2000来写,《昨日之岛》用Word 5,而《波多里诺》用的则是Winword),情况大大改观。你会禁不起一再修改文本的诱惑。你会先写一写,打印出来,然后再读一遍。接着你会东改西改,然后再根据你挑出错误或是想增删的地方用计算机顺一次。我通常会保留不同阶段的草稿。但是大家可不要以为一个对文本异文现象感到好奇的人可以借此重建你的写作过程。事实上,你在计算机上写作,打印出来,用手改动内容,然后又上计算机修正文本,可是当你如此做的时候你是在选择其他的异文,换句话说,你并不是亦步亦趋根据你手改的版本一字不差地重打一遍。研究异文的批评家将会在你用墨水修改过的最后版本和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新版本之间找到异文现象。总而言之,计算机的存在意味着异文的根本逻辑已经改变了。它们不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也不是你的最后选择。既然你知道自己的选择可以随时更改,你就会不断更改,而且经常会回到最初的选择。
我真的相信电子书写方式将会影响深远地改变异文的批评,同时心中对孔蒂尼精神怀着应有的尊敬。以前我一度研究曼佐尼《圣歌》的异文。在那个时代,更动一字一词可是无比重要的事。如今情况完全相反:
明天你可以拣选昨天丢弃不用的字,让它起死回生。还能算数的顶多只是最初的手写草稿以及最后打印的定稿中间的不同。其他阶段里的就是来来去去的一些东西,而且决定它们的是你血液中钾离子的浓度。
欣喜和悲伤
关于自己写小说的方法,我已经没有其他好说的了。硬要我说那么只能补充一点: 这些小说中的每一本都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我不懂为什么有人可以每年都写一本小说;这些作品也可以是令人赞叹的,而且我打从心底佩服,但是佩服归佩服,我可不艳羡他们。写作小说这事的美,并不是实时转播的美,而是延后传送的美。
每次我的小说快写到尾声的时候我就觉得苦恼,换句话说,根据作品的内部逻辑它要停止了,而我也得跟着停止;而且我注意到,如果我坚持继续下去可能只会弄糟作品而已。美妙之处(也就是真正的乐趣所在)在于六年、七年或八年当中(最好是永远)你能活在一个你一点一滴亲手建构起来的世界中,而且这世界已经专属于你。
小说写作的结束意味着悲伤的诞生。
这也是鞭策你再立刻开始写另外一本小说的唯一理由。但如果它不是已经好整以暇在那里等你,你就是着急地摩拳擦掌也没有用。
作家和读者
然而,我不愿意见到上面最后那些陈述自动触发一些劣等作家所共同持有的观点,那就是: 作家只为自己而写作。说出上面那句话的人你不要信任: 他们不但不诚实,而且是满口谎言的自恋狂。
唯一你会为自己写下的文字便是购物清单上面的文字。它能提醒你该买什么东西,但东西一旦买了就可以把它撕掉,因为它对其他人毫无用处。其他每一种你写出来的文字都是在对某些人讲某些事。
我经常扪心自问: 如果有人告诉我明天将有星际灾难,宇宙将要毁灭(也就是说,明天将不会有人读到今天我所写的文字),我是不是还会继续写作?
我的直觉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没有人读我写的东西,我为何要写?但经过考虑之后,我会改口说是,但那只是因为我舍不得放弃一个绝望中的希望: 在银河系的灾难中也许有哪个星球能够躲过浩劫,未来说不定有人可以解读出我文字里所蕴藏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在世界末日来临的前夕,写作仍然具有它的深刻涵义。
作家只为了读者而写作。凡是说自己只为自己写作的人倒也不必然就是扯谎。那只意味着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神论态度教人吃惊。即便从最严格的世俗观点来看亦复如是。
作家如果无法对未来的读者说话,那么他必然是绝望的、不快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