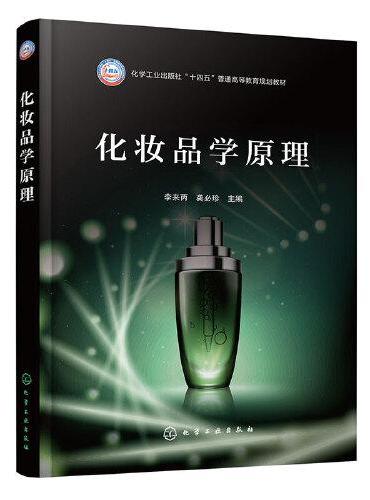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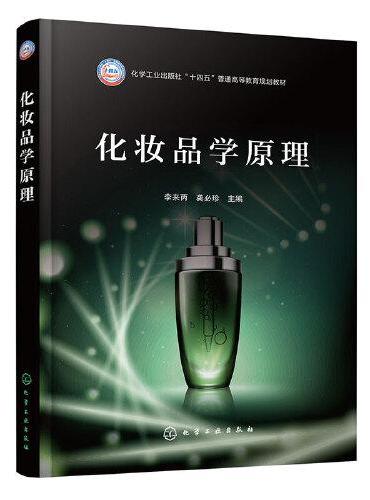
《
化妆品学原理
》
售價:NT$
254.0

《
万千教育学前·与幼儿一起解决问题:捕捉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教育契机
》
售價:NT$
214.0

《
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
》
售價:NT$
254.0

《
史铁生: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2)
》
售價:NT$
254.0

《
量子网络的构建与应用
》
售價:NT$
500.0

《
拍电影的热知识:126部影片里的创作技巧(全彩插图版)
》
售價:NT$
500.0

《
大唐名城:长安风华冠天下
》
售價:NT$
398.0

《
情绪传染(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
》
售價:NT$
403.0
|
| 編輯推薦: |
新散文领军人物祝勇首次发表的文化笔记
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得主,历史散文家祝勇多年文化笔记首次公开出版。
跨越时空藩篱,重回历史现场
跨越中国文化中两大争鸣革新的年代,回到国学经典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现场,回到经典作品与历史人物本身,方能理解这种变革背后的人文力量。将春秋与五四两相对照,别有妙处。
美文美图,艺术享受
精选第六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暨评奖插图类银奖得主、鲁迅美术学院李晨教授手绘插图22幅。
|
| 內容簡介: |
《国学与五四》一书系著名学者祝勇先生最新力作结集,共分两大部分。
上篇为《国学笔记》,以国学经典名篇《诗经》《礼记》《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老子》《庄子》《墨子》等为题,逐篇缜密解读,详细分析见。下篇为《五四笔记》,祝勇先生在充分肯定五四运动的正面价值及历史成就的同时,坐定下来,予以十足的耐力与细致、客观冷静地对这一丰厚历史文化遗产分析与反思,从而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
| 關於作者: |
|
祝勇,作家、学者、纪录片工作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历史研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全国青联第十届委员。已出版主要作品有:《旧宫殿》、《血朝廷》、《故宫的风花雪月》等,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多种选本。获第一、二届郭沫若散文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担任纪录片《辛亥》《历史的拐点》等总撰稿,先后荣获第21届中国电视星光奖,第25、26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纪录片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中国十佳纪录片奖,香港无线电视台台庆典礼最具欣赏价值大奖,与《舌尖上的中国》并列获得第18届中国纪录片年度特别作品奖。
|
| 目錄:
|
上编
国学笔记
《诗经》
《礼记》
《论语》
《孟子》
《中庸》
《大学》
《老子》
《庄子》
《墨子》
下编
五四笔记
题记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第十四节
|
| 內容試閱:
|
标榜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所欠缺的,恰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给中国这副满带着泥土气息的肠胃带来的西式大餐。它们确是那个落后黑暗的中国之急需亟需,而且,是一个有机体,相辅相成。民主的本质是平等,科学的本质是理性。所以,呼唤德先生、赛先生,亦即呼唤平等与理性。有了平等,才有宽容,思想才不会成为犯罪,科学也才会受到尊重,从而不再发生布鲁诺被焚火刑柱那样的惨剧。同样,只有具备了科学精神(理性),对话的渠道才能建立起来,也才能实现民主与平等。正如笔者曾经在《精神述说的一种可能》一文中写道的那样:中国文人最需要的,便是思辨辩理性,是站在道理上进行争辩的从容。理性是一切精神活动的基石。西方人文科学的发达,与其自然科学的发达是分不开的。西方许多思想和艺术大师,本身也是数学家、工程师。于是,周匝缜密的科学理性,自然而然地注入艺术情感之中,形成他们严谨的人文传统。知识的对象是物,在中国,科学理性的缺乏,使得精神意念失去了客观的保证,历史上许多美丽的思想都变得模棱两可,可以随意改变其精神指向,谁都可以拿它当王牌,而社会照旧黑暗。
穆勒说:如果除了一个人以外全人类都是一个意见,那么全人类没有什么理由不要他表示意见。正如这一个人如果有权的话,他也没有理由禁止所有的人表示意见一样。伏尔泰说: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我将誓死保护你有说话的权利。讲的都是这个问题。将此原则置放在五四时代的话语环境中,我们有理由要求倡导民主的五四精英在探讨的诸问题时能够遵循民主的原则。
而五四变革中的风云人物,许多似乎更专注于拓展自身的话语空间,并排挤他人(尤其是反对派)的话语空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几乎成了他们的标志性语句,而与其不如的句式则是他们最为习惯的一种标准句式,表现出一股不容分说的文化霸气。林贤治对此以赞赏的口吻写道: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激进分子,一元论者。连胡适,也都拼命走极端。 这种霸气的主要特点就是一语定性,直接导出结论,缺乏论证过程,更不给对手申辩的机会。就像轻率的法官,抓住疑犯就砍头,既不进行案情调查,也不进行庭审和辩论,一刀了事,何其快哉!杀错了怎么办?再抓一个便是。
这种极端、偏激、直截了当的话语定式的产生,自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合理性之一,便是新文化所面对的,是以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为背景的封建文化,对手是一匹行将瘦死的骆驼,虽然行将瘦死,但毕竟是骆驼,唯有虚张声势,才可能有所触动。有人说这是一场新旧思想的遭遇战,高手过招,这种新旧文化板块的大震荡应当是情节跌宕、险象环生,而在当时,新文化旗手却是蚂蚁缘槐,蚍蜉撼树,落入无人喝彩的窘境,根本谈不上什么遭遇,不得已,钱玄同他们才自扮红脸白脸,策划一场苦肉计,自己作践自己一番,以挑动对手的关注。林贤治先生称道这种极端、偏激的话语方式是弱势者的方法,被迫使用的方法,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也就是说,这种方法是出于战略和战术的双重需要。于是,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激进分子,一元论者。连胡适,也都拼命走极端。
对此,鲁迅开天窗的比喻,颇有代表性:你要开窗子,主人不肯;你说是连屋顶一起拆掉,主人就同意你开窗子了。陈独秀亦说: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
然而,这种以专制对付专制的做法,固然可图一时之快,达到一点短期效果,但从长远计,非但不能打倒封建,反而继承了封建话语方式的衣钵。我看不出五四一代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式,与他们反对的人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式有什么区别尽管具体观点上是截然对立的,但思想方法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国式的,封建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形成的一元、线性认知模式的现代翻版。非此即彼,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以立场画划线,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全没有探讨的耐心,全没有对不同观念的宽容和尊重,全没有对民主在本质意义上的理解,企图将思想权威化、垄断化。他们反对的并不是语言霸权,他们反对的是别人的语言霸权。就像哈耶克说的:思想一经权威化,人间就惨祸大作,黑暗就笼罩大地!在稍有实征态度(Positivistic attitude)的人看来,人类在这条旧路上走,何其残酷,何其愚昧,又何其浪费!
林贤治先生说:在许多时候,所谓宽容是虚假的,而冲突才是社会的生命之所在。 以此为五四精英辩护是无力的。宽容不是不冲突,不是缄口不言,而是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的冲突。没有这种冲突,又从哪里去考验和证实宽容精神?没有冲突的宽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宽容,如张东荪先生云:有势均力敌之对抗,然后始能有容。多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没有不同的声音在同一时空里的撞击,只依赖某种强力来获得统治地位,那样的文化建设,不能真正体现时代的进步,也是长久不了的。
显然,言论民主是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应该被容纳于五四精英们科学与民主的总纲领之内。当然,真正的宽容不是没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人的相对平等,在种族、文化、经济等方面出现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必然导致冲突。当时复杂的社会条件,使民主的倡导者们面临一个悖论,一种巨大的窘境:他们只希望从别人那里争取到民主的权利,却不打算把同样的权利施予他人。但是,要使中国走出以暴易暴,以一种霸权取代另一种霸权的怪圈,推行民主政治建设或早或晚都是必经之路。
即使站在五四知识分子自身的立场上,这种偏激和极端也是不明智的。一方面,它不利于在思想交锋中团结更多的同盟。如果一个文化族群想要最大限度地孤立自己,那么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采取这种话语方式。另一方面,这种极端主义的论说方式在学理上往往站不住脚,如钱玄同之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这种将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泼掉的做法,实在难以服人,这种勇气充其量是匹夫之勇,恰巧可以给对手提供攻击点和口实。
一九二五年,北京一些群众围攻和焚烧了《晨报》报馆。陈独秀当时支持了这一行动,认为它是理所应当的。而胡适则认为这种争自由的理念已走入死胡同。几日后,他深觉不能不表达自己的立场,于是给陈独秀写了这样一封信: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了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共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惟一唯一原则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在这封信中,胡适还举了一个发生在陈独秀身上的例子,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五四运动那一年,陈独秀被拘捕,居然有两名文学革命派的论敌、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参加了营救。胡适说:
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其实这个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在林贤治所说的冲突中,宽容是否必然虚假的问题。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个问题。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解决。一九一九年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之后,梁漱溟就指出:
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梁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问题。
所谓实质正义,就是当行为主体在认为其所做的都对的前提下,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显然,没有人能够无条件地拥有这种绝对的权利,因为行为主体自认的正确,未必是真正的正确,即使动机正确,也未必导致正确的结果。而程序正义,则做出秩序安排,为主体行为提供制度保证。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哪个更为可取?显然是后者。尽管程序正义并非一定导致正确的结果,比如一个发疯的民族完全可能通过程序来发起一场灾难,但是它发生错误的概率要远远小于实质正义。实质正义常常导致在正义的幌子下实行的暴政。就像邱吉尔对民主制度的评价:民主是个很坏的制度,但是其他制度都比它更糟,所以只能用它。
在当时历史和社会条件下,要求五四一代从容进行程序和制度建设,似乎有些苛求。各种危机使得他们饥不择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看到了制度的缺失所产生的后遗症。最初的欠账,在时间中已经滚动出巨额的利息。到一九六六年,无数法西斯主义暴行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施行的,实质正义成为他们革命行动的保护伞。
身体暴力是语言暴力的延伸。胡适批评的,不仅是身体暴力,也包括语言暴力。胡适在思想体系上并没有太大的贡献,他受到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
前面说过,这种语言暴力,是封建传统的现代翻版。儒家坚信价值唯一,放之四海皆准,一切价值都服从于这个统一价值。而自由主义者则坚持多元化观点,认为社会不可能建立在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和宇宙论基础上,应当在各种价值之上寻找公约性最大的因素,作为社会的共同基础。关于这个最大公约性,陈名先生概括为两点:第一是最底线的价值观念,比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无论什么派别可能在语义上有不同的诠释,但不会在语词上反对它,一个语词可以被公共使用,就包含了对这个语词的基本规定面上的公约性。例如,你可以说你理解的人权和我理解的人权不一样,但你不能说我根本就不要人权。第二方面是最大程度的公正,以一个相对公正的运作体系,来适应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人们所需要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如果没有这个相对公正,所有的社会运作都不能开展,所有不同的族群都不能共处,所有不同的团体都不能沟通对话,这个社会就解体了。相对的公正是一个社会在大多数民意取向上能够被认同的最重要的指标。
陈名认为他所说的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个社会就解体,其实未必解体,依靠强权和暴力可以得到维系。但这种维系并不可靠,解体随时可能发生,因而这种强制性的连接,也可以被称为解体。
在自由主义者眼中,达到陈名所说的最大的相对公正的途径,就是通过容忍、回避、搁置。尽管-胡适们在制度建设上没有成就,他们的声音立刻被激愤之声覆盖,但是他(们)对容忍的坚守,使人听到声嚣杂乱的五四合唱中,理性的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