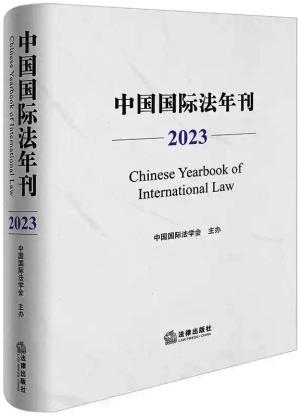不打不相识
关于胡适等自由知识人与三民主义在五四以后的关系,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仍有许多未增揭示的面相,特别是对双方关系的演变过程似乎还缺乏一种整体的了解。因而有必要对二者关系的由来、接近、冲突及磨合作一个长时段的鸟瞰。
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与三民主义者的最早接触应该是在他就读于中国公学时期。 1929 年,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中说:我那时只有十几岁,初进去时,只见许多没有辫子的中年、少年,后来才知道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有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姓名。如熊克武先生,不但和我同学,还和我同住过,我只知道他姓卢,大家都叫他老卢,竟不知道他姓熊。同学之中死于革命的,我所能记忆的有廖德璠,死于端方之手;饶可权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为黄花冈七十二人之一。熊克武、但懋辛皆参与广州之役。教员之中,宋耀如先生为孙中山先生最早同志之一;马君武、沈翔云、于右任、彭施涤诸先生皆是老革命党。中国公学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章炳麟先生出狱后即住在这里,戴天仇先生也曾住过,陈其美先生也时时往来这里。有时候,忽然班上少了一两个同学,后来才知道是干革命或暗杀去了。如任鸿隽忽然往日本学工业化学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去学制造炸弹去了;如但懋辛也忽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同汪精卫、黄复生到北京谋刺摄政王去了。所以当时的中国公学的确是一个革命大机关。
胡适这里提到的名字,大都是国民党的元老或后来的国民党要人。这段经历也许给胡适最大的影响就是见识了什么叫做革命。革命党人活动的秘密性和危险性,对于幼时就有小先生称号的文气十足的胡适,大概有一种天生的不相合。但是,他在革命大机关里却并没有走上革命之路,除了有革命党的爱护因素之外,显然还与他个人对革命党及其活动的观感有关。胡适回忆: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的多;我是做惯班长的人,到这里才感觉到我是个小孩子。不久,我已感得公学的英文、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那时候,中国教育界的科学程度太浅,中国公学至多不过可比现在的两级中学程度,然而有好几门功课都不能不请日本教员来教教员和年长的同学都把我们看作小弟弟,特别爱护我们,鼓励我们。我和这一班年事稍长、阅历较深的师友们往来,受他们的影响最大。我从小本来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现在天天和这班年长的人在一块,更觉得自己不是个小孩子了。
然而,在年龄上实是一个小孩子的眼里,公学的英文、数学都很浅,并感到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这说明胡适到中国公学以后很快就取得了一种心理上的优势和自信。他记得,有一次革命党从国外回来携带禁品出了事,由于他可以说几句英国话,还请他去海关上交涉。最能使他自感文才之突出的是,他这样一个小孩子竟做了《竞业旬报》的编辑,并且在学校里颇有少年诗人之名。作为一个小孩子却有这样的特遇,不能不令他感到年长的人也不过如此,这大概正是他和这班年长的人在一块,更觉得自己不是个小孩子的原因所在。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胡适又说受他们的影响最大,那么影响他最大的是什么呢? 显然不是学问上的,从其回忆及他后来的个人选择来看,也肯定不是革命精神上的。因此,影响他最大的应该是生活上的。这些人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有革命党的关系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圆。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幼年总是文绉绉的胡适,竟学堕落到这步田地,不能不说是革命党人对他的影响之大。这样一种影响,使他年长后对革命缺乏敬仰,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中国公学时期,革命党人给胡适的印象至少有这样三种:一生活放荡。二读书少,学识浅。 1926 年,丁文江曾向胡适谈及:至于国民党的那一套,我真正不敢佩服。我所检查到的信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主张,是学生应该少读书,多做事! 你想这般青年,就是握了政权,有多大的希望呢?对国民党的这样一种观念,在曾与国民党人胡混过的胡适头脑里,或许形成得更早。不过,少读书,多做事,此后的确成了中国青年人革命或者从政的秘诀。即使真正握了政权,在自由主义者眼里,也的确没有看到多大的希望,因而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三三民主义言论大而空。胡适曾说,在中国公学时期,要看东京出版的《民报》,是最方便的。暑假、年假中,许多同学把《民报》缝在枕头里带回内地去传阅。最方便一词说明读《民报》是胡适当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提示了他对《民报》有相当的了解。但是,后来他谈到报刊与时代的关系时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胡适对《民报》的这种看轻,不能不说与他早年对《民报》的读后感有关。虽然后来胡适被冯自由称为民国前革命报人,但他却经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国民党的无好感,乃至自觉地对它批评或谴责,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源于中国公学时期三民主义者给他的这些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