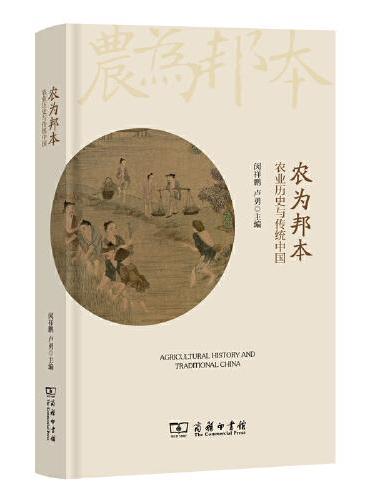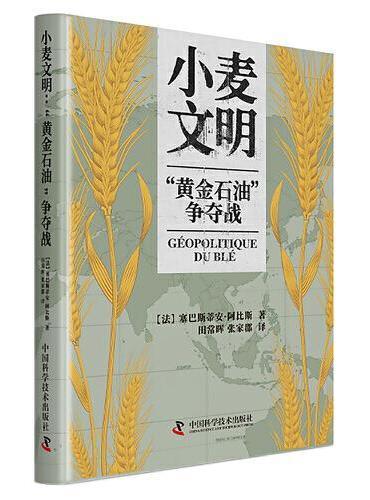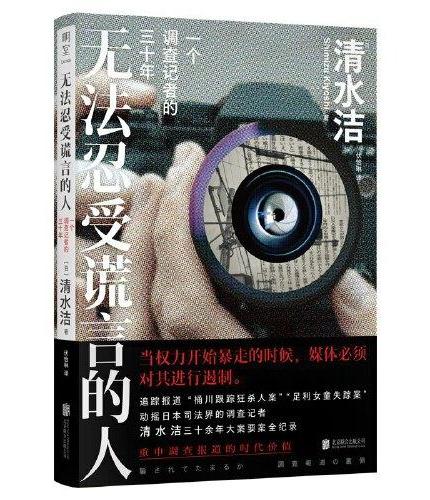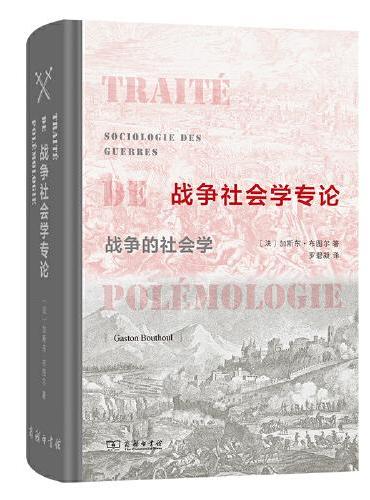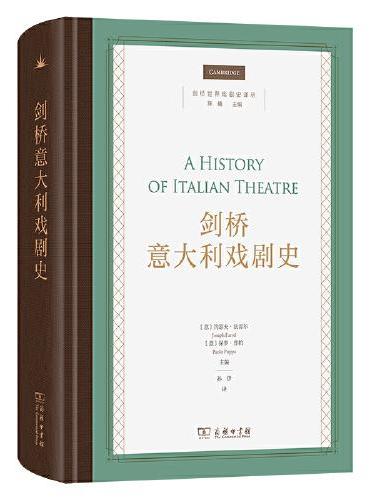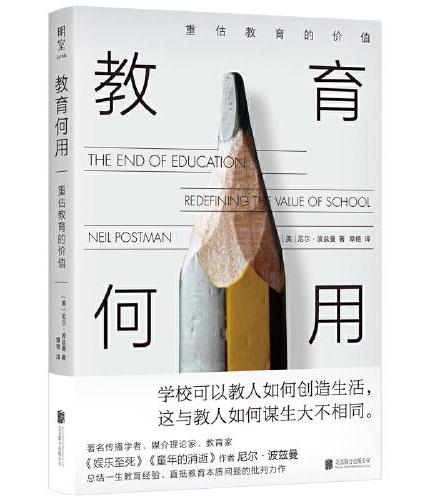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掌故家的心事
》
售價:NT$
3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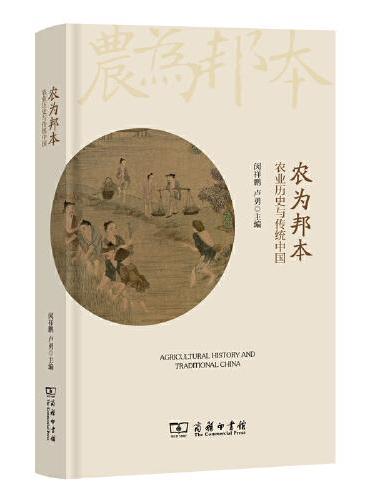
《
农为邦本——农业历史与传统中国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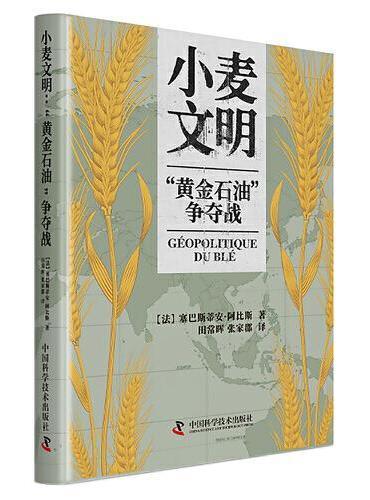
《
小麦文明:“黄金石油”争夺战
》
售價:NT$
445.0

《
悬壶杂记全集:老中医多年临证经验总结(套装3册) 中医医案诊疗思路和处方药应用
》
售價:NT$
6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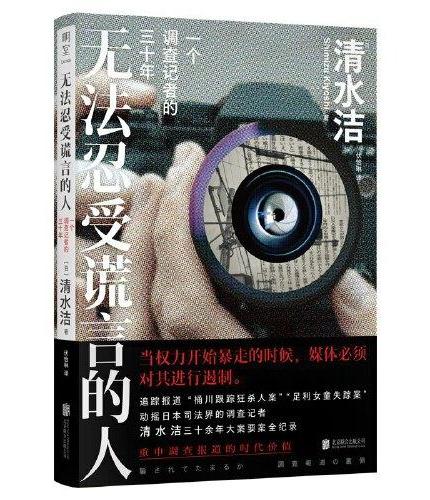
《
无法忍受谎言的人:一个调查记者的三十年
》
售價:NT$
2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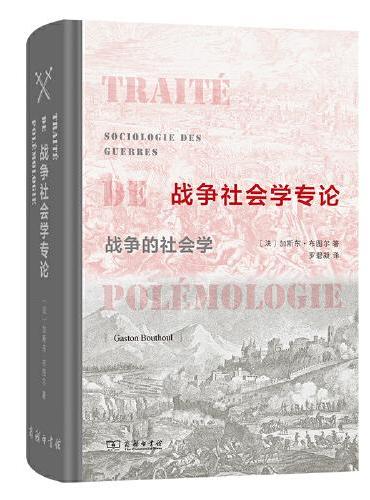
《
战争社会学专论
》
售價:NT$
5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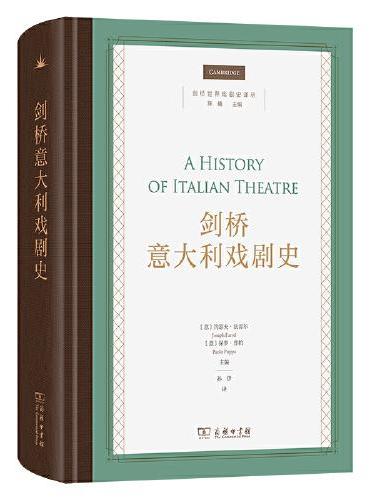
《
剑桥意大利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NT$
7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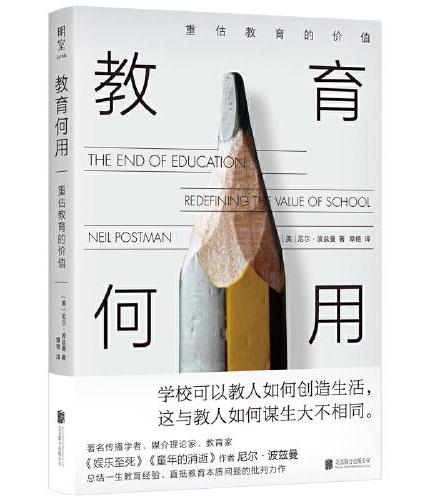
《
教育何用:重估教育的价值
》
售價:NT$
299.0
|
| 編輯推薦: |
《魔女卡丽》是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的成名作,1976年首次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成为电视史上的恐怖杰作。2013年《魔女卡丽》再度搬上银幕,由金伯莉皮尔斯导演,老戏骨朱丽安摩尔以及凭借《海扁王》、《雨果》而在好莱坞爆红的童星科洛-莫瑞兹主演,在北美再度掀起了一阵恐怖热潮,也让全世界读者又一次领略的斯蒂芬金的恐怖魅力。
《魔女卡丽》是斯蒂芬金众多长篇小说中篇幅较小的一部作品,情节惊悚恐怖,扣人心弦,加上电影的普及,小说在爱好恐怖小说的读者中知名度较高。
|
| 內容簡介: |
|
《魔女卡丽》系美国现代惊悚小说大师斯蒂芬金的早期作品,也是他的一部成名作,被称为恐怖小说之王第一部真正成功的佳作。1976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搬上银幕,成为电影史上划时代的杰作。小说描写女主人公凯丽的母亲是个信仰偏执狂,而他从小在母亲严格管制下长大,渐渐养成了孤僻自闭性格,与外界很少交往。有一天她被邀请参加高中年级组织的舞会,不料舞会上受到同学们的冷嘲热讽、恶意作弄。在极度痛苦下,凯丽奋起反击,把自己从小郁积在内心的愤恨一齐发泄到舞会上,将一个欢乐的舞会瞬间变成一个浴血葬场。
|
| 關於作者: |
|
斯蒂芬金,有史以来作品最多、读者最众、声名最大的作家之一。编过剧本,写过专栏,执过导筒,做过制片人,还客串过演员。作品总销量超过三亿五千万册,超过一百五十部影视作品改编自他的作品,由此创下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被《纽约时报》誉为现代惊悚小说大师,更是读者心目中的恐怖小说之王。六次荣获布莱姆斯托克奖,六次荣获国际恐怖文学协会奖,1996年获欧亨利奖。
|
| 內容試閱:
|
她只有实习驾照,她从冰箱旁边的挂板上取下妈妈的车钥匙,跑向车库。厨房里的钟正好指向11点。
她冲进汽车,第一次试着发动,接着强迫自己停顿了一下,又试了一次。这回发动机咔咔地响了,点着火了,她冒冒失失地让车子轰鸣着疾速驰出车库,车子的排障器叮当作响。她转了个弯,后轮把砂砾溅得劈啪作响。她妈妈的这辆1977年款的普利茅斯猛地转向上了公路,尾部摇晃着几乎要失控撞上山肩,让她胃里一阵恶心。只是在这一刻,她才发觉她的喉咙深处在呜咽,就像一只掉进了陷阱的动物。
开到6号公路与后张伯伦公路的交叉路口,她没有在停车标志前停留。火警响彻东部的夜空,那里是张伯伦与韦斯托弗的交界,从她身后的南部莫顿,也传来火警声。
学校发生爆炸的时候,她差不多已经到了山脚。
她双脚猛踩机动刹车,像个布娃娃似的摔到了方向盘上。轮胎在路面发出尖啸声。她摸索着总算打开了车门,手搭在眼睛上,挡住火光。
一团烈焰腾空而起,火光拖曳着震颤翻滚的屋顶钢板、木头和纸片。气味浓烈,有股油味。大街上像被打了闪光枪一样燃烧着。在那可怕的一瞬间,她看见尤恩中学整个体育馆毁于燃烧的废墟中。
过了一会儿,激烈的震动从她身后袭来。刹那间,路上的杂物带着一股暖风从她身边呼啸而过,这股风让她想起(地铁的味道)去年去波士顿的短暂旅行。比尔的家庭药店和凯利果行的窗户乒乒乓乓地向里倒去。
她跌倒了,大火把街道烧得如同地狱的正午。接下来的事情就这样慢慢地发生了,她的脑子却(死他们都死了吗卡丽为什么想到了卡丽)照着自己的速度镇定地飞转着。车辆朝火场疾驰而去,有人穿着浴袍、睡衣睡裤在奔跑。她看见一名男子从张伯伦镇警察局和法院联合大楼的前门走出来。他走得很慢。车辆动得也很慢。即便是那些在奔跑的人也是慢吞吞的。
她看见站在警察局台阶上的那个人用手环住嘴巴,在尖叫着什么;周遭尖厉的警笛声、火警声还有这恐怖的大火,让人听不真切,听上去仿佛是:
喂!不要哎,那傻瓜!
整条街都湿了。光亮在水面上起舞。光是从泰迪的阿莫科加油站射出来的。
喂,那个
接着,整个世界都爆炸了。
引自托马斯K奎兰对缅因州调查委员会所作的有关张伯伦镇5.27、5.28事件的宣誓证词(以下节选自《黑暗的舞会:怀特委员会的报告》一书,纽约印章书局1980年版):
问:奎兰先生,你是张伯伦镇的居民吗?
答:是的。
问:你的住址?
答:我在台球房的楼上有间屋子。那是我工作的地方。我拖地板,给桌子吸尘,管理机器就是弹球机,你们知道的。
问:5月27日晚上十点半你在哪里,奎兰先生?
答:呃实际上,我是在警察局的一个拘留室里。我每周四领薪水,瞧。我总是跑出去瞎混,输个精光。我一般去骑士酒吧,喝点舒立滋啤酒,玩点小牌。感觉就像脑子里在举行轮滑比赛。嘿,是幻觉吗?我曾经用一把椅子敲过一个家伙的脑袋
问:当你感觉这种情绪要爆发的时候就跑去警察局,这是你的习惯吗?
答:是的。大个子奥蒂斯,他是我朋友。
问:你是指这个县的治安官奥蒂斯道尔吗?
答:是的。他叫我只要不舒服随时都可以过去。舞会前一晚,我们一帮伙计在骑士酒吧的地下壁橱里玩梭哈扑克 ,我早就开始发觉滑头马塞尔杜拜在作弊。我早该料想得一清二楚了按照法国人的观点,要捉住一个滑头,就要看看他自己的牌我就走掉了。我已经喝了几杯啤酒,要知道,于是我握着手,朝警察局走去。普莱西在值内勤,把我关进了一号拘留室里。普莱西是个好小伙。我认识他妈妈,不过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
问:奎兰先生,你觉得我们可以谈谈27号晚上的事吗?晚上10点半?
答:有什么不可以呢?
问:我真诚地希望如此。请继续。
答:噢,普莱西在周五凌晨两点一刻左右把我关了起来,我立刻就脱衣服睡了。昏死过去了,你也许会说。下午四点醒来,吃了三粒消食片,又继续睡。我就有这个本事。我可以睡到宿醉彻底清醒。大个子奥蒂斯说我应该琢磨琢磨这是怎么做到的,去申请一下专利。他说我可以挽救世界上许多痛苦的人。
问:我想你肯定做得到,奎兰先生。那么你再一次醒来是什么时候?
答:差不多是周五夜里十点。我饿得要命,想去找点吃的。
问:他们就一直把你留在没上锁的单间里?
答:没错。我清醒的时候是个规矩人。实际上,有一次
问:就告诉委员会你离开牢房后发生了什么。
答:火警响起来了,这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我的魂都吓出来了。越战结束后,我就再也没有在夜里听到过警报声。于是我跑上楼,见鬼,办公室里一个人都没有。我对自己说,该死的运气真好,普莱西就等着瞧吧。一直以为总有人在值班的,万一有电话进来呢。于是我跑到窗口,朝外头张望。
问:从窗口能看见学校吗?
答:绝对能。学校在街道那一边,隔一个半街区。人们奔来跑去,叫喊着。我就是在那时看见卡丽怀特的。
问:你以前见过卡丽怀特吗?
答:没有。
问:那你怎么知道是她?
答:这很难解释。
问:你看清楚她了吗?
答:她站在路灯底下,就在梅恩大街和斯普林大街拐角处的消防栓那里。
问: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答:我想是的。消防栓的整个顶部朝三个方向迸裂开来。朝左,朝右,直冲天空。
问:这个嗯故障是几点发生的?
答:十一点差二十分左右。不会晚于这个点。
问:接着又发生了什么?
答:她往镇子中心走去。先生,她看上去可怕极了。从剩下的布料看,她穿着件礼服之类的衣裳,她站在消防栓那里,浑身湿透,浑身都是血。看上去她就像刚从一起车祸中爬出来似的。她居然在龇牙咧嘴地笑。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笑。它就像死神脸上的笑。她一直在看她的两只手,在衣服上不停地蹭着,试图把血迹擦掉,想着自己再也擦不掉,就打算血洗整个镇子,叫他们得到报应。真是个可怕的妞儿。
问:你怎么知道她在想什么呢?
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解释。
问:给你的宣誓证词提个醒,我希望你信守你的所见,奎兰先生。
答:好的。格拉斯广场拐角那儿也有个消防栓,那个也坏了。那个我看得更清楚。边上笨重的螺母全都拧不上了。我亲眼看见的。它炸了开来,跟另一个一样。她很开心。她正在对自己说,这样就能给他们冲个澡,就能高喊,对不起。接着救火车一辆辆开过,我看不到她了。又一辆救火车在学校附近停下,他们开始捣腾那些消防栓,却发现接不到水。伯顿长官冲他们抱怨着,就在这时,学校发生了爆炸。上帝啊。
问:你离开警察局里了吗?
答:是的。我想去找普莱西,向他报告那个疯狂的女人还有那些消防栓。我朝泰迪的阿莫科加油站瞥了一眼,这一瞥让我浑身的血液变得冰冷。六只气泵全不在钩子上。泰迪杜尚死于1968年,上帝保佑他,他儿子跟泰迪过去一样,每天晚上都会把那些气泵锁在上面。每只耶鲁挂锁都被锁搭砸碎了,荡在那里。喷嘴掉在柏油路面上,自动进油器在给每个气泵进油。汽油涌上人行道,又涌上了大街。圣母马利亚,见到那一幕,我的蛋都被扯疼了。接着,我看见这家伙点着一支烟在一路跑过去。
问:你做了什么?
答:冲他大喊。好像喊的是,嘿!小心香烟!嘿,停下,那是汽油!他根本没听见我。四周尽是火警声、镇子的鸣笛声还有来来往往的车辆,我并不觉得奇怪。我见他准备扔烟头了,于是连忙往屋子里逃。
问:接下去发生了什么?
答:接下去?啊哟,魔鬼来到了张伯伦镇呀
桶落下来的时候,她起先只是意识到哐当一声金属般的巨响刺破了音乐声,随即,她就被一种暖乎乎、湿嗒嗒的东西淹没了。她本能地闭上了眼睛。从她旁边传来一记咕哝声,在她那部分近来变得异常警醒的意识里,她微微感觉到了疼痛。
(汤米)
乐声哗的一下,七零八落地停了下来,之后还有几个声响像断了的弦一样在回荡,在这突如其来的茫然失措中,不等人们反应过来,她听见有人像宣读判决书一样清清楚楚地说道:
我的上帝啊,那是血。
过了一会儿,就像是硬要人接受这一事实,使这件事清清楚楚、明白无误,有人尖叫起来。
卡丽闭着眼睛坐在那里,感到那种阴森巨大的恐怖在脑海里升起。毕竟,妈妈还是对的。他们又一次欺骗了她,又一次愚弄了她,又一次把她变成了笑柄。这种令人讨厌的事情本来都是些老花头,但这次却不是;他们叫她坐在这里,坐在全校师生面前,再现浴室的场景只是这个声音说了句
(我的上帝啊那是血)
可怕得叫人不敢多想的什么东西。要是她睁开眼睛,而这一切是真的,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有人开始大笑,一个孤零零的、恐怖的、阴森的声音,她睁开了眼睛,睁开眼睛去看那是谁,这是真的,最后的梦魇,她被染红了,滴滴答答的,她们用私处的血让她湿透,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的思绪
(哦我被它淹没了)
被自己的嫌恶和羞耻染成了可怕的紫色。她闻得到自己,那是血腥味,可怕的、湿漉漉的铜臭味。在忽隐忽现、变幻不定的影像中,她仿佛看见鲜血沿着她光溜溜的大腿汹涌而下,听见它不停地滴落在浴室的地砖上,随着堵住它的催促声,她感觉到柔软的卫生巾蹭着她的皮肤,体味着恐怖的这种直截了当、令人作呕的苦痛。他们最终还是劈头盖脸地给她来了一下。
第二个声音也跟着第一个加入进来,接着是第三个女高音的咯咯声第四个,第五个,六个,十二个,他们全都,全都在大笑。维克穆尼在笑。她看得见他。他的脸完全僵住了,震惊不已,与此同时,却又在发笑。
她依然静静地坐着,任凭喧闹声如激浪一样冲击着她。他们依旧光鲜美丽,周遭依旧迷人梦幻,可她已经穿过边界,此刻,童话故事遭到了污浊和邪恶的嫉妒。在这个故事里,她会咬毒苹果,会遭到巨人的攻击,会被老虎吃掉。
他们又在笑话她了。
突然间,故事破碎了。她开始恐怖地意识到自己遭到了多大的欺骗,一个可怕而无声的呐喊
(他们在看着我)
试图迸发出来。她双手捂住脸,掩住它,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一心一意只想逃跑,离开亮光,让黑暗笼罩她、掩藏她。
可是,这就像是在糖蜜里奔跑。她背信弃义的脑子让时间放慢了速度,费力地爬行;仿佛上帝把整个场景从78转分调到了3313 转分。甚至连笑声也低沉下去,放慢成阴森森的低音噪声。
她双脚打着绊子,差点从舞台边缘摔下来。她重新站好,弯下腰,跳到了地上。折磨人的笑声越发响亮,就像岩石相互碰擦在一起。
她不想去看,但她还是看到了;光线太亮了,每一张脸她都看得见。他们的嘴,他们的牙,他们的眼睛。她还看见了面前自己那双血迹斑斑的手。
德雅尔丹小姐正向她跑来,脸上满是虚伪的怜悯。卡丽看得出在那张脸皮底下,真正的德雅尔丹小姐正带着令人作呕的、老处女的下流劲暗暗傻笑。德雅尔丹小姐张着嘴,她的声音恐怖、缓慢而低沉:
我来帮你,亲爱的。哦,我真遗
她向她猛击过去,
(发功)
德雅尔丹小姐飞了出去,一下子撞在舞台边的墙壁上,摔倒在地。
卡丽跑了。她在人群当中飞跑。她双手捂脸,但她还是可以透过指缝看见他们,他们很漂亮,沐浴在灯光下,裹着鲜艳的、天使般的袍子。亮闪闪的鞋子,光洁的面孔,美发厅做出来的精致发型,光彩夺目的裙子。他们朝后退去,好像她是瘟神,可他们一直在笑。接着,一只脚偷偷地伸了出来,
(哦是的接下去就是这个哦是的)
随后她跌倒了,她便开始爬行,沿着地板爬,被血污黏在一起的头发耷拉在脸上,她爬啊爬,就像被光线刺得睁不开眼的圣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接下来该有人踢她的屁股了。
但没有人这么干,她的步子又乱了。事物开始加速了。她穿过门,来到大厅,接着飞奔下两小时前她同汤米庄重走上来的这段台阶。
(汤米死了为把一个瘟神带到光亮之地付出了全部的代价全部的代价)
她向前一大步,笨拙地跃过了台阶,笑声依然像黑鸟扑打着翅膀一样围绕着她。
随后,是黑暗。
她飞奔过学校宽大的前草坪,两只轻便舞鞋都跑丢了,她光着脚在飞奔。新近修剪过的学校草坪像丝绒一样,微微结着露水,笑声甩在身后了。她开始有些平静下来。
接着,她的步子又乱了,她整个儿趴倒在旗杆边上。她静静地趴在那里,气喘吁吁的,她把炽热的脸埋进冰凉的草丛里。羞耻的泪水开始流淌下来,滚烫,厚重,就像月经初潮时一样。他们战胜了她,打败了她,一直以来就是如此。结束了。
现在,她得马上站起来,从偏僻的街道偷偷摸摸地回家,始终躲在阴暗处,以防有人过来找她,找到妈妈,承认自己错了
(!!不!!)
她内心的坚强她的内心非常强大猛地升腾起来,强有力地喊出了那个字。壁橱?无休止的、令人错乱的祈祷?宗教小册子、十字架,还有用来标记出她人生岁月余下的年、日、小时的黑森林布谷钟里的那只机械鸟?
突然间,就像她脑子里有台录像机开启了,她看见德雅尔丹小姐朝她跑来,看见她像个布娃娃似的摔了出去,她这样想着,甚至都不是有意的。
她翻了个身,扬着被弄脏了的脸,瞪大了眼睛看着星星。她忘了
(!!那种力量!!)
是时候教训他们一下了。是时候给他们露两手了。她歇斯底里地咯咯笑了起来。这是妈妈最喜欢说的话之一。
(妈妈回到家放下皮包眼镜闪着光好吧我猜今天我在商店里给那个埃尔特露了两手)
那儿有喷水系统。她可以让它开启,轻而易举地让它开启。她又咯咯地笑起来,起身,光着脚转身朝大厅的门那儿走去。开启喷水系统,关上所有的门。朝里看,让他们瞧见她在朝里看,她在注视,在大笑,而喷出的水毁了他们的礼服、他们的发型,冲走他们鞋子上的油光。她唯一遗憾的是那不是血。
大厅里空空荡荡。台阶上了一半,她停了下来,发功,她对着那些门全神贯注地发力,门一扇扇地啪啪全关上了,气压式闭门器也折断了。她听见有人在尖叫,那是音乐,甜蜜的灵魂之乐。
有那么一会儿没有什么动静,接着她发觉他们在推门,想把它们打开。这点压力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被困住了,
(困住了)
这个词欣喜若狂地在她脑子里回荡着。他们受制于她,受制于她的力量。力量!多么有力的一个词!
她走上余下几级台阶,朝里看,乔治道森撞在玻璃上,挣扎着,推挤着,他的脸都被挤得变形了。他身后还有别的人,这些人看上去就像水族馆里的鱼。
她向上扫了一眼,没错,是有喷水管,它们小小的喷嘴好似金属的雏菊。管子穿过绿色煤渣砖墙上的一个个小洞。里头有大量的水管,她记得。消防法,还是别的什么。
消防法。她脑子一闪,想起了
(蛇一样的黑黑的电线)
舞台上拉得到处都是的电线。它们被脚灯挡住了,从观众席上是看不见的,她刚才是小心翼翼地跨过它们坐到宝座上去的。汤米一直握着她的胳膊。
(火与水)
她想象自己伸起手臂,感觉到了管子,一路摸索过去。冰冷,充满了水。她嘴里觉出了铁的味道,又冷又湿的金属味,和花园浇水用的软管喷嘴里喝到的水一个味道。
发功。
一时半会没有发生什么。接着,人们开始离开门,向后退去,四下张望。她朝中间一扇门走去,透过小小的长方形玻璃朝里看。
体育馆里在下雨。
卡丽笑了。
她没有把它们全部打开,只是开了一些。她抬起头用眼睛看着喷水系统,发觉自己用意念来跟踪管道路线要来得更容易。她开始开启更多的喷嘴,越来越多。可是这还不够。他们还没有哭喊,所以这还不够。
(伤害他们去伤害他们)
有个家伙上了舞台站在汤米边上,夸张地做着手势,叫喊着什么。在她观察的当儿,他爬了下来,朝摇滚乐队的电子设备跑去。他抓着其中一个话筒架,钉住不动了。卡丽注视着,惊呆了,他的身体通过了几乎是静止的电流之舞。他的脚在水里捣腾着,头发尖尖地竖了起来,嘴抽搐着张开,就像鱼的嘴一样。他看起来很滑稽。她开始大笑。
(上帝啊接下来让他们全都变得滑稽)
刹那间,她闭上眼睛发功,把自己能够感觉到的力量一股脑儿发动起来。
一些灯爆掉了。一条带电的电线落到了一摊水里,某处闪过一道眩目的亮光。她脑子里砰的一下,就像断路器失灵了。刚才抓着话筒架的那个家伙摔倒在一台扬声器边上,炸出了紫色的火花,面对舞台的绉纸彩旗随即着了起来。
宝座正下方,有一条220伏的带电电线正在地上噼啪爆裂,边上,穿着绿色薄纱晚礼服的朗达西马德像木偶一样在疯狂地舞蹈着。她宽大的裙子一下子冒出火焰来,她向前摔了下去,身子还在抽搐着。
或许在那一刻,卡丽走到了悬崖边上。她倚在门上,心怦怦乱跳,但她的身体冷得就像冰块一样。她脸色发青,但两颊却出现了躁热的暗红色斑点。她的头剧烈地抽动着,她神志不清了。
她摇摇晃晃地离开了门,依旧让它们关着,这么做并不是有心或者计划好的。里面的大火越烧越亮,她悲切地想到,那个壁饰也许已经葬身火海了。
她瘫倒在最上面一级台阶上,把头垂到膝盖上,想让自己的呼吸慢下来。他们又在试图破门,但她轻易地就让它们紧闭着唯有那个是不费力的。她迷迷糊糊地意识到有几个人正从消防门逃离,让他们去好了。回头再收拾他们。她一个也不会放过。一个不漏。
她慢慢走下台阶,出了前门,依旧让体育馆的门紧闭着。这很容易。你要做的就是用意念看着它们。
镇上突然拉响了警报,吓得她尖叫起来,双手在脸上捂了
(警报正是火警)
一会儿。体育馆的门从她的意念之眼中消失了,有几个人眼看就要逃出来了。不,不。淘气。她重又把门啪啪地关上,还夹了谁的手指好象是戴尔诺伯特夹在门框里,夹断了一根。
她重又摇摇晃晃地穿过草坪,这个模样可怖的身影暴凸着眼珠朝梅恩大街走去。她的右边,就是镇子的商业中心百货商店,凯利果行,美容美发厅,加油站,消防站
(他们要扑灭我的大火)
但他们办不到。她开始咯咯笑起来,这是一种错乱的声音:得意洋洋,迷惘空虚,胜利的,又是恐怖的。她来到第一个消防栓前,试图把边上那个刷了油漆的耳状大螺帽给拧下来。
(哦嗬)
很重。重极了。这金属的玩意儿死紧,她拧不动。没关系。
她更用力地去拧,感觉松动了。接着是另一边。随后是顶上那个。而后她一下子把三个全拧下来了,她退后站着,眨眼工夫,它们全都卸了下来。水流朝两旁、朝上方喷涌而出,其中一个耳状螺母从她面前以不要命的速度飞出去五英尺远。那玩意儿落到了街上,又高高地反弹到空中,随后就不见了。水流在可靠的压力下呈十字形喷涌。
她笑着,摇晃着,每分钟心跳超过两百次,她开始朝格拉斯广场走去。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像麦克白夫人一样在裙子上擦着血手,没有意识到自己甚至在大笑的时候也在哭泣,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脑子里隐秘的一角正在为自己终极、彻底的毁灭而恸哭。
她想把这身血污带在身边,马上就要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了,直到遍地充满恶臭。
她在格拉斯广场打开了消防栓,接着朝泰迪的阿莫科加油站走去。这恰好是她去往的第一个加油站,但不是最后一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