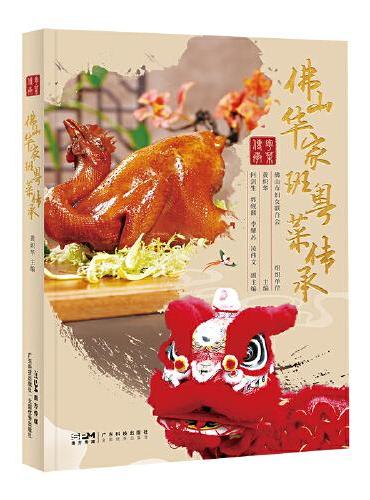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甲骨文丛书·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
》
售價:NT$
1367.0

《
欲望与家庭小说
》
售價:NT$
449.0

《
惜华年(全两册)
》
售價:NT$
320.0

《
甲骨文丛书·古代中国的军事文化
》
售價:NT$
454.0

《
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套装全4册):从未见过的王朝内争编著史
》
售價:NT$
1112.0

《
半导体纳米器件:物理、技术和应用
》
售價:NT$
806.0

《
创客精选项目设计与制作 第2版 刘笑笑 颜志勇 严国陶
》
售價:NT$
2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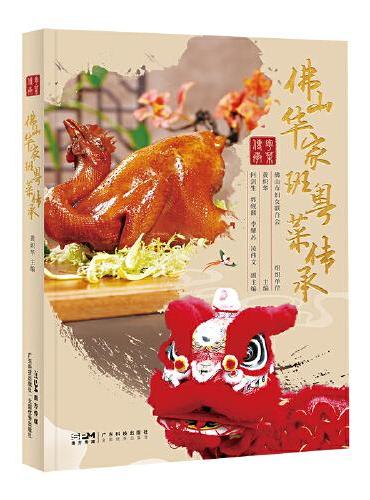
《
佛山华家班粤菜传承 华家班59位大厨 102道粤菜 图文并茂 菜式制作视频 粤菜故事技法 佛山传统文化 广东科技
》
售價:NT$
1010.0
|
| 編輯推薦: |
|
在当下浮躁之气弥漫的社会中,作者仍能保持一份沉静,透过纷繁看到本真,实属难得。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为广西20142015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散文类)之一。作品主要以描写小城中的人物、讲述小城中的故事为主,充满生活的气息,包含着浓浓的人情味。在作者笔下,小城并非水墨般优美清灵,但也不沧凉沉重,而像是一幅充满鲜活气息的生活画卷。
|
| 關於作者: |
梁志玲,广西作家协会会员,获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广西青年文学奖。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作品散见于《山花》《广西文学》《红豆》《民族文学》《散文选刊》《北京文学中篇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微凉的逃逸》。
??|?pn?N''?"olor:black''作品主要以描写小城中的人物、讲述小城中的故事为主,充满生活的气息,包含着浓浓的人情味。在作者笔下,小城并非水墨般优美清灵,但也不沧凉沉重,而像是一幅充满鲜活气息的生活画卷。
|
| 目錄:
|
第一章 微尘清扬
002出发与抵达
019阳光盛大
027稳住
第二章 浮世清音
042台上台下
049移植事件
059红与黑
064陌生人
070角落
075热闹的形式
079拆迁与窜改
第三章 城市清欢
084我是凡人,需要人间的忧伤
099岁月的秩序
104风景旧曾谙
109在缝隙中
113走过城西路
117尘在手中
123触角
129米的气息
133行走的吆喝
136指纹里的生命
第四章 苍苔清幽
142屐齿印苍苔
156茫然的空间
162孤独的壁垒
172角色
185突然静止
189灵魂之死
第五章 草木清宁
196如草木般清宁
203饱满的颜色
209我就是农民
212阡陌纵横录
219散淡的黄姚
222阳光的衍生物
225回乡记
230轻逸之美
236配角的逆袭山黄皮
第六章 碎片清逸
240尘世的豌豆
243算了吧
246有关吃的往事
249最后的稻草
252沉默的床
255突兀的盛开
258算盘噼啪
262老古董
265发呆
267转瞬之间
269占领
273后记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微尘清扬
出发与抵达
2006年3月11日,我正坐在前往南宁的列车上。列车员推着小车兜售东西,吆喝声抑扬顿挫饮料、啤酒、香烟、小吃、八宝粥,充满了鲜艳的饮食的气息,小车里五颜六色的东西是庸红俗绿的,喊到八宝粥时声音有点拖泥带水,含糊成了宝宝粥或是爸爸粥,那又怎么样,人的气息是挥之不去的。
我坐在列车上,列车的行驶是一种滑行于地球表面的机械运动,它使人发生移动,改变一个地方的人的数量,使人发生量变而已。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小弟告诉我说:外婆走了。我啊了一声,又安静了。周围的人并没有对我投以异样的目光。
到了南宁,换乘公共汽车,与小弟会合,再赶乘快班回到我生活的小城,再坐上三轮车。无论我乘坐什么样的车,它们唯一的区别是速度,共同的地方是它们在使人发生量变,我们坐在使人发生量变的车上去看望一个已经发生质变的人我的外婆,一个正在上路的生命,她永远无法再滑行于地球的表面,她将永远下潜,奔赴我们无法预知的无限的广漠的未知中。
外婆已经移到了地上的席子上,身上覆盖了略微泛黄的白布,这是一种土织布,俗称白扣布,那种接近天然的白色总是与孝和死亡有关,它的白不是绝对的。现代社会中的白布掺杂了太多的技术,比如增白粉,比如荧光粉,它们在与天然决绝,张扬着完美的白色。可是生命怎么可能是完美的呢?所以白扣布宽容地接纳了微微的黄色,它使一切有了一种别样的黯淡的温暖,它将缓慢地包容死亡此刻它正在包容我外婆冰冷的躯体,八十八岁的生命,也算是喜丧,黯淡的温暖。我的手臂上也缠了一根窄窄小小的白扣布。
白布的起伏不是很大,五岁的小表妹悄悄指了指,说:外婆的头在那个方向。我哦了一声,因为头与脚的起伏没有多大的区别,我对表妹稚气的解释表示理解,她只知道头与脚的方向而不知道什么是死亡。她问母亲:外婆怎么不睡在床上了?母亲说:睡在地上凉快一点。她又问:那盖那么多东西不更加热?母亲说:你出去玩吧,不要那么缠人没事不要进来。
我跪下来,焚香插到灰盆上,烧了一些纸钱给外婆上路用。她的脚前放置了两碗白米饭,筷子与匙羹也配放在那里,还有一盏煤油灯,有灯照着她吃饭,上路。她的躯体两旁各放置了一个小碟,是盛着生油点的灯。
我为外婆点上一支香烟插到灰盆上,是她生前常抽的青竹烟,虽然她不是很喜欢,但它便宜,一块钱一包。我母亲有记忆时就知道外婆喜欢抽烟。据说吃糖可以戒烟,吃九制陈皮可以戒烟,最后,烟还是照常抽,糖和九制陈皮也必不可少地照吃。另外因为喜欢在烟雾缭绕中回想往事,常犯偏头疼,外婆就吃上了退热散,最后她迷上了退热散配方中微量的咖啡因。烟、糖、九制陈皮、退热散,构成了她的零食结构。外婆有时会振振有词地说:我做姑娘时,在越南高平抽的可是上等的鸦片。我家里人可是跑马帮贩烟土的。这句话似真似假。
外婆的经典动作是:坐在床上,支着双膝,膝盖顶着下巴。床沿密密麻麻的黑点,是搁置烟头留下的烙印。她抽烟,叹息,然后揉揉太阳穴,说,头又疼了。有时就把风油精涂抹在太阳穴,或是就涂在烟头上。烟抽完了。头还疼,于是,她撕开一包退热散,伸出舌头,把粉末倒到舌面上,闭嘴含了一下,再喝上一大口水。药是苦的,口就苦,于是,剥开一粒糖含上。她吃的糖,经过几次变化,先是一毛钱一粒的硬糖,后是薄荷糖,最后确定为冰糖颗粒。
所有零食前前后后地登场,都只是因为异国记忆的存在。也许一开始是为了驱逐记忆,然而在与记忆较量时,强大的童年情景总是让各种充当驱逐工具的零食一一溃败,最后所有的零食褪变成外婆回忆往事的道具,甚至是一种情调。
外婆在没有星星的夜晚,躺在竹椅上,竹椅置放在天井中的苦楝树下。外婆穿着无领无袖的月白色上衣静静地、沉沉地融化在黑夜里。她脸的轮廓线条被黑夜施了催眠术睡了过去。这时,她冷亮不扩张的烟头凑向脸庞,借着亮唤醒了一些线条,半明半暗,再一微动,线条浮动,似乎那是一张一气呵成的脸。她夹烟的手搔了一下下下巴,仿佛不小心手指绊倒纷至沓来的记忆,慌忙抽身,把脸的线条抽拉成一条直线,幻成游蛇行于荒野中。烟灭了。只有烟雾扬眉吐气般喷了一空。想象着游蛇蹿向滴漏时间的空隙,于是卡在那里扭曲挣扎,时间停止了滴漏,一切可以这样顿住、空白。
我曾多次在我的小说中描写类似的镜头虽然我的小说并没有得以发表,只是有时候主人公会幻化成男性,很沧桑的男人,但是我所要表达的对生命的无奈是彻底的、黯淡的,它有着颓废的唯美。
童年的我有一段时间和外婆一起住在一条青石板砌成的小街上。年幼的我目光清澈,甚至不知道哭与流泪的区别。我守在她的身旁,不太敢像猫一样亲热地蹭她,只是懵懵懂懂地注视着她,注视着泪水从她闭上的眼睛流出来,我无法区分哭与流泪,见多了许多老人的风泪眼,就不能明辨其中代表的心境了。我静静地看着她的泪,同时滑出的泪,只因半侧脸,一边倾斜,另一边平直点,于是有一行泪领先行过,一路填了些皱褶,另一行泪中途开溜坠入耳边的发丛,濡湿润腻。我看着,似乎在丈量比画痛苦,似乎在奇怪痛苦是怎样具体到泪的形式上,带了一种不相关的诧异似乎又是安然。
当我写下这样的文字时,我知道它们充满了意境,是空灵的,但是可读性不强。我们的人生更多的是可读性不强的,也同样是与空灵无缘的。但是我的外婆在我删去一些意境后,她还是有故事的。
我来到右边的席子上跪下,开始漫长的守灵。我旁边是外婆的三个女儿母亲以及两个姨。
守灵是对生命最隆重的尊敬。所有琐碎的纠纷将在守灵夜里重释与升华。
三姨说:谁知道妈会走得那么快。夜里她说肚子疼,因为经常疼就给她吃了止痛药,安定后,开了核桃糊给她喝,还吃了一个香蕉,我还打了电话给二姨一声。
二姨说:半夜电话响时,我也是心神不宁的。前几个月妈胃出血时替她输了五百毫升的血,顺便全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她最关键的是腹动脉上有肿瘤。只能保守止痛,不能治疗了。她的日子不多了。可能夜里就是那个血瘤破裂了。
我父亲说:今天她还喝了大半碗米汤,还走出门口来张望了一下,过一个坎坎时还小跃了一下,真是胆大。
我母亲说:可能是回光返照了。
亲人们仔细检查着自己是否尽到了责任,在哪一个细节中可以挽留一个生命,哪怕是暂时的。在平时忽略的地方略略表示一下忏悔。
有亲戚说,你们忘了给外婆盖一张红布了。于是我们取下白布,我看见了外婆的遗容,她的肤色暗青,正在退隐的生命晦暗地发出气息。眼睛闭得很紧,嘴微张,舌尖顶了一枚硬币。她穿了一身黑衣,脚上套了一双白底圆口黑布鞋。两手放置于身体两边,各抓了一团饭。庞大的黑衣非常隆重地把她淹没了。肉体靠衣服显出大致的轮廓,最后一刻生命的被动与软弱被表现得不动声色。我有点悲哀,却没有面对死亡的恐惧。布重新盖上了。
外婆前段时间提出,拿那套衣服出来穿穿。母亲一时反应不过来,说:什么?哪一套?外婆说:心中有数的那一套。那套在大有号寿衣店里买的衣服最终给外婆过目了一下。她慢慢看着,抚摩着,没说什么。没人在时也许她试穿过,因为有一次,她淡淡地说:宽了,也得。一时让人反应不过来,一想又懂了。外婆非常喜欢针线活,凡新买的衣服必被她改一下才上身,也许这是唯一一套没被拆缝就上身了的衣服。
有一次,她和三姨讨论寿衣,她说:寿衣不要金属扣,容易硌身子,塑料扣也不好,火化会发出爆响,惊扰人的。我听着鼻子发酸,鼻涕水就下来了。
外婆对我说:你感冒了,就要早吃药。房间里的空气一时有点凝滞。
外婆自顾自地说,昨晚又梦见越南的姐姐,战争时被活埋的哥哥来看她了。凡是已经死去的人她都反反复复梦见了。吃早餐时,她经常和我描述昨天晚上又看见鬼了,鬼长得什么样,和她说了什么,穿什么衣服,又是怎样走路,她甚至还学着走了两步路。我埋头吃着东西,不敢吭声。外婆觉得很无聊,她对我沉默而又冷不丁的顶撞的性格的评价是:不吭声的狗咬死人。餐桌上只有外婆的声音在回荡,我抬头看见她,肤色青灰,两耳大而肥厚,这是一对预示着长寿的耳朵,可是再长寿的东西也有个尽头。我心头一阵发紧,我知道我再也不敢顶撞什么了。
我们默默无言地听着,毛骨悚然。这样的述说越来越多,我们也疲于呈现该有的表情,听了也就听了,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在缓慢地暗淡。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忙,我们也许都不是优秀的倾听者。而外婆也许在抓紧时间重复着自己的述说,她对我们不够积极的反应充满了愤慨,经常泪流满面。
而我们只能敷衍地说:你身体一好我们就帮你打听你的亲人,回去一趟。
有时候有朋友来看她,就逗她说:外婆教我两句越南话,我好去越南做生意。外婆就得意地说了,而且诲人不倦。然后又继续自己唠叨的故事,激动之余又放声大哭,搞得众人面面相觑。
母亲经常说:妈你少哭一点,你老哭,别人还以为我们在虐待你。你的身体已经是这样了,要保持好的心情。
外婆说:我就是忍不住。
外婆病了以后,我们决定让她和三姨住。然而她和我母亲一起住了几十年,感情太深了。外婆在三姨家住了一段时间后,老吵着回我家,而我母亲也老了,夜里实在陪不了床,二姨她上班又陪不了。我们反复劝说,在三姨家吧,她年轻照顾得了,工作也随意,迁就一下子女。
外婆有时想得通,有时想不通,想不通时整天吵着要户口本,说去找派出所安排住处,要找政府,要不然她就来到小城里最繁华的百货大楼,又是放声大哭。外婆的能说会道是非常著名的,也是非常煽情的,小城里的很多人都认识她。她需要围观带来的瞩目。
她要控诉的是:我没有家,到处都没有我的家,所有的人都在抛弃我。说得声泪俱下,不明真相的人纷纷红了眼圈,开始指责她儿女的不孝。
这个举动非常让人无可奈何。被影响声誉的做老师的二姨非常生气,她对外婆说:我们已经对你很好了,吃穿营养治病都有,你要户口本是吗?你有户口本吗?你是中国人吗?你不是,人家懒得理你。
外婆强词夺理地说:我什么也没说。
二姨情绪激动地说:某某师母说我怎么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公安局黄叔语重心长教育我对长辈要耐心,还有没影儿的事人家怎么老说呢?说我不像为人师表,气死我了!
二姨跪了一下,又上去为外婆上香,烧了一些纸钱。重新跪下时,我们闲聊了几句,清点了外婆的一些遗物。首先是一本蓝色的证书外国人暂住证。外婆没有户口本,只有这本东西。这文字的东西可以证明外婆的身份,它有着粗糙而又单薄的权威,苍白的权威无法为一个生命做盖棺论定,白纸黑字也许意味着证据,证据对于一个丰富的生命是言不及义的。
打开暂住证,内页已经泛黄了。姓名:陈海萍;出生年月:1919;籍贯:越南高平;暂住处:崇左县太平镇。
盖了崇左县公安局的公章,当然现在是崇左市了。非常简单的文字,技术最差的假证伪造者都可以仿制。这样的身份太不值钱了,所以高科技的制作没有必要落实到这样的东西上。
二姨叹息了一声,说:这个就不要陪葬了,留个纪念吧。
没有人知道外婆的真实姓名,陈接近越南姓的音,而外婆来来回回中国几次实在像一个传奇,它与几场战争有关,这样的漂泊像海萍一样,没有根基。于是一个叫罗荫枢的男人,为她取了名字,陈海萍,也许落笔时还微微叹了一口气。
那个男人是我的外公。一百多年前,广东梅县地区的罗姓两兄弟漂泊来到一个叫崇善县的地方,崇左县那时叫作崇善县。他们繁衍人口,经商生活。外公读过八年私塾,常为人写状纸,杂七杂八的活都干过,年龄大时,改行为人做道公。那时的外公瘦弱,体形颀长,有着中年人应该有的沉稳笃定,前后两个老婆的逝去,把他折腾得略略疲惫,留下的一个幼女正扶着大肚而又空荡荡的米缸学行步,女儿的口水把米缸的外壁弄得湿漉漉的,米缸的细小紧密的裂缝在口水的涂抹下显得异常清晰,仿佛是在水的滋润下茂盛蓬勃地生长出来,那是长不出树叶的枝丫,没有收获的疯长,令人恐慌。好在大男人何患无妻。这时有人把外婆介绍给了外公,那时的外婆虽然只是二十出头,却也经历了两个男人,满脸沧桑,两个人都在寻找黯淡的温暖。他们非常缓慢地相爱了,成了柴米油盐夫妻。外婆就这样做了外公的填房。
那个扶着米缸学步的幼女有了后妈,外婆是不是一个好的后妈谁也不清楚,印象中外婆是不大喜欢孩子的,她喜欢用烟头以及针线恐吓淘气的小孩。
再不听话我烫死你。再不听话我针就扎死你。
我不能心甘情愿地用慈祥两字形容外婆,她是乖张的精明的精力充沛的个性十足的。而慈祥这个词太温暾太具有奉献精神了。
1965年中国政府出兵越南援越抗美,青石板古镇来来往往大量的士兵,开赴前线的,从前线退下来的,在人流中一个士兵把当年扶米缸的幼女裹挟走了,他们来到了天津。在褪去军装的威猛后,他们面对的是琐碎与贫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饮食冲突,温婉与粗暴的尖锐冲突,这个女人回来了。然而古镇对她是陌生了,跟她有血缘关系的人也不在了父亲在1968年去世了,徘徊再徘徊,她又回到了北方,潦草嫁人,又潦草地死去了。似乎女人的家是在男人身上的,这似乎是女人的宿命。
五岁的小表妹又溜了进来,好奇而又惶恐。
我问:外婆喜欢你吗?
她说:不喜欢,她老用牙签戳我的手。
我问:你喜欢外婆吗?
她说:不喜欢,她骂我短命鬼。
我们对生命的爱憎是直白的,年幼的人更是不去深究其中的渊源。
我潦草地说:外婆病了,心情不好。
女人的家在哪里?这是个不好说的问题。是在男人身上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