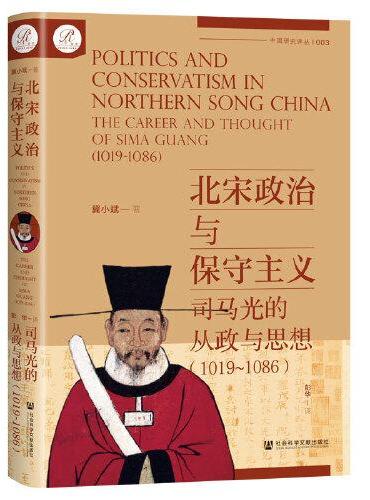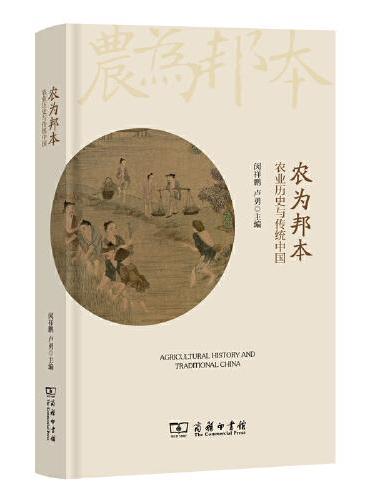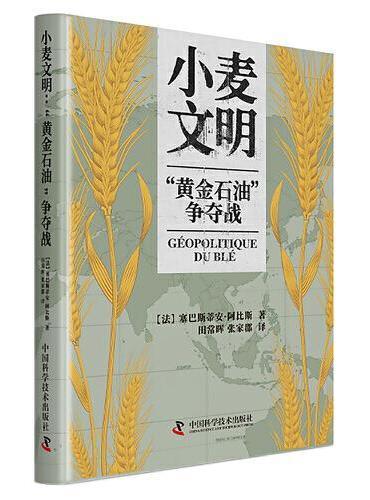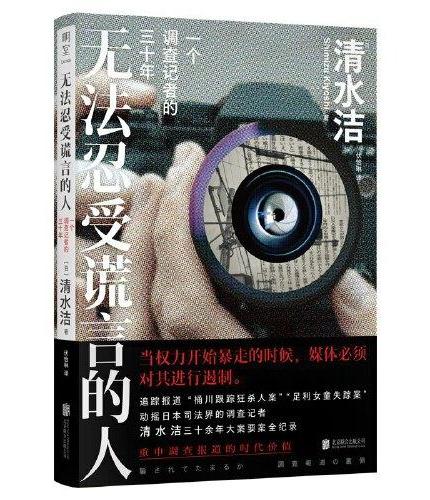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古典的回響:溪客舊廬藏明清文人繪畫
》
售價:NT$
1990.0

《
根源、制度和秩序:从老子到黄老学(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5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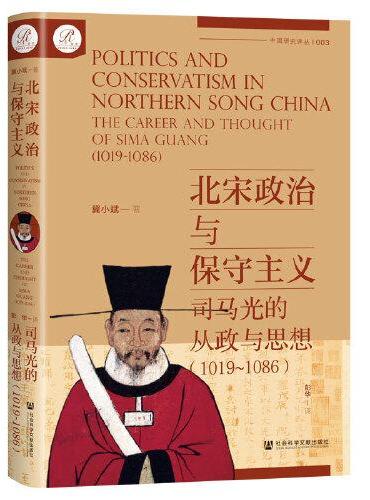
《
索恩丛书·北宋政治与保守主义:司马光的从政与思想(1019~1086)
》
售價:NT$
345.0

《
掌故家的心事
》
售價:NT$
3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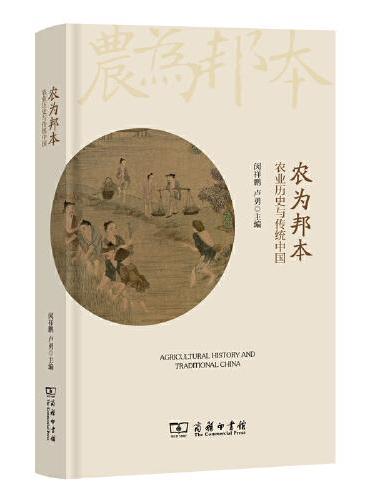
《
农为邦本——农业历史与传统中国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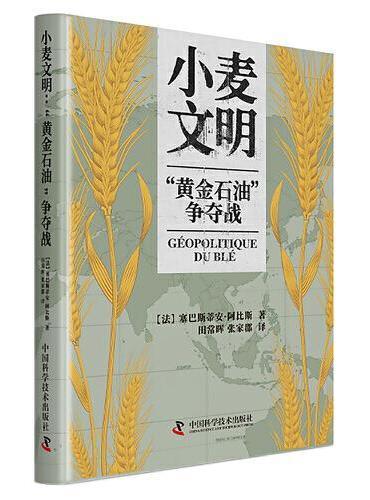
《
小麦文明:“黄金石油”争夺战
》
售價:NT$
445.0

《
悬壶杂记全集:老中医多年临证经验总结(套装3册) 中医医案诊疗思路和处方药应用
》
售價:NT$
6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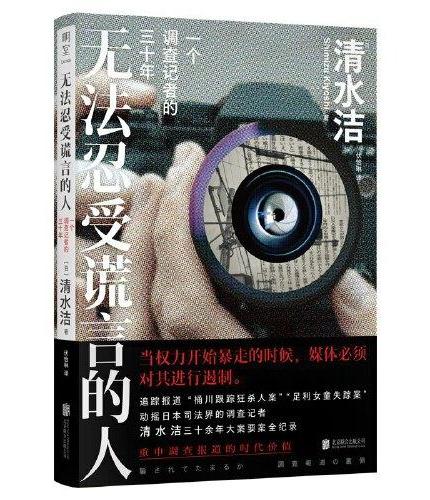
《
无法忍受谎言的人:一个调查记者的三十年
》
售價:NT$
290.0
|
| 編輯推薦: |
|
西蒙娜德波伏瓦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法国著名女作家,她和让-保尔萨特的一世情缘广为人知,但无论是萨特还是波伏瓦,都绝少在作品中两人之间紧张的个人关系。《情迷莫斯科》以两人的访苏之旅为材料,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并不总是能相互理解的一段私事,也清晰地反映出两人对当时苏联政体和国情的不同看法,使其成为见证前苏联的一个见证文本。
|
| 內容簡介: |
|
《情迷莫斯科》是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创作于1966-1967年间的中篇小说,1992年才在杂志上首次发表。小说讲述了妮科尔和安德烈所经历的婚姻和身份危机。这对夫妇是退休教师,他们去莫斯科旅行,见到了安德烈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作者让妮科尔和安德烈的视角快节奏地交替变换,书中的每个人物不时地局囿于彼此的误解、掩藏的失望和极度的怨恨之中。作者平行呈现男女主人公的视角,展现出他们的相似及不同之处:安德烈更关心政治,而妮科尔更关注感性世界。这篇小说参照了波伏瓦和萨特的访苏之旅,种种误会导致主人公政治上的失望,也生动而带有批评意义地见证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
|
| 關於作者: |
|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小说家,女权运动理论家和倡导者,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波伏瓦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29年和萨特同时获得哲学教师资格,并从此成为萨特的终身伴侣。1949年,波伏瓦出版《第二性》,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1954年出版小说《名士风流》,荣获龚古尔文学奖。此外,她还写过多部小说,如《女宾》《他人的血》《人皆有死》, 以及论文《建立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存在主义理论与各民族的智慧》《皮鲁斯与斯内阿斯》等,提出道德规范与存在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她一直被人们视为是第二萨特。
|
| 內容試閱:
|
她从书上抬起眼。所有这些关于无法交流的老生常谈,太无聊了!如果我们真想交流,好歹总是能做到的。就算不能和所有人交流,和两三个人总是可以的。邻座的安德烈正在读一本侦探小说。有些烦恼、遗憾、忧虑,她是不会告诉他的;他大概也有自己的小秘密。但是总体来说,他们还是相互了解对方的。 透过飞机舷窗,她向外看了一眼:黑压压的森林,绿油油的草地, 一望无际。多少次,他们一起乘着火车、飞机、轮船,各自手捧一本书,并肩穿越了世界的空间呢?他们经常还会在大海上、陆地上和天空中默默地并肩滑翔。这一刻承载着记忆的温馨、希望的喜悦。他们是三十岁还是六十岁呢?安德烈的头发早早就白了:以前,白发似乎代表着一种风雅,雪白的头发衬托出他深暗、纯清的脸色。现在,白发依然是一种风雅,但皮肤粗糙了,皱巴了,如同老旧的皮革。不过,他嘴巴和眼睛在微笑的时候,依然灿烂如昔。尽管相册上的他今非昔比,但他现在还是年轻时的老样子:在妮科尔眼里,他没有年龄。这也许是因为,他似乎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年龄。过去那么喜欢跑步、游泳、爬山、照镜子的他,如今坦然地背负着六十四岁的年龄。漫长的一生中,有微笑,有眼泪,有愤怒,有拥抱,有倾诉,有沉默,有冲动。有时,时间仿佛没有流逝。未来还在无限地延展。
谢谢。
妮科尔从篮子里拿出一块糖。空姐肥胖的体态和冷酷的目光,让她畏惧。三年前,餐馆和宾馆的女服务员,也让她有过同感。她们连假装的和蔼都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利意识太强,我们只能接受:在她们面前,我们总感觉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至少有嫌疑。
我们就要到了。她说。
看着越来越近的地面,她有点害怕。无限广阔的未来,可能在一分钟之内毁于一旦。她很了解心态的突然变化,怡然自得的安全感顿时会转为一阵阵的恐惧感: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安德烈得了肺癌每天两包烟,太多了,过多了!或者是飞机坠毁了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倒是不错:两人在一起,悄然离去。但别这么早,别是现在。飞机轮子突然触及跑道的那一刻,她心想:又躲过一劫。乘客们纷纷穿上大衣,收拾东西。大家原地等待。等待的时间很长。
你身上一股桦树的味道。安德烈说。
天气很凉爽,近乎寒冷: 空姐说的是16度。三个半小时的距离, 巴黎那么近,又那么远。今天上午,巴黎还散发着沥青和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味道,遭遇到入夏以来的第一次高温侵袭。菲利普 那么近,又那么远一辆大巴载着他们,穿过机场它比他们1963年来时大多了。他们来到一个蘑菇形的玻璃楼前,接受护照检查。玛莎在出口等他们。妮科尔又一次惊讶地发现,克莱尔 和安德烈两人迥然不同的相貌特征,在玛莎的脸上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她身材苗条,衣着高雅,唯有她的假发发型,体现出莫斯科女人的味道。
旅途顺利吗? 您好吗?你好吗?
她称呼她父亲你,称呼妮科尔您。这很正常,但还是怪怪的。
把包给我。
这也很正常。可是,一个男人为您提行李,因为您是女人;而一个女人为您提行李,那是因为她比您年轻,而您则感到自己老了。
把行李票给我,坐这儿吧。玛莎不由分说地命令道。妮科尔从命。她老了。在安德烈身边,她常常忘记这一点,但屡次受到的小小伤害,提醒她老了。年轻的美女,见到玛莎时她想起了这句话。她记得,三十岁时,当岳父针对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说出这句话时,她微笑了。现在,她也觉得大部分人都很年轻。可她老了。她很难接受这一点(她很少对安德烈隐瞒什么,但这一次,她没有告诉他自己悲愕交加的感受)。但这个年龄总归还是有好处的,她心想。退休听上去有点像被废弃的感觉。但是,想什么时候度假,就什么时候度假更确切地说是总在度假,还是很爽的。在酷热的教室里,同事们开始梦想出发度假的日子。而她已经出发了。她的目光搜寻着安德烈。他站在玛莎旁边,周围人群嘈杂。在巴黎,找安德烈的人太多了:西班牙政治犯,葡萄牙犯人,受迫害的以色列人,刚果、安哥拉、喀麦隆的造反者,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的游击队员还有一些人她忘了。他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随时准备为他们提供帮助。召集会议,起草宣言,组织集会,散发传单,组织代表团,所有的任务他一概接受。他是许多组织和委员会的成员。在这里,没有人找他。他们只认识玛莎。他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一起走走,看看:她喜欢和他一起发现新事物,期盼着长期被他们单调的幸福所凝固的时间,重新迸发出新的活力。她站了起来。她真想现在就走在大街上,走在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下。可她忘了,在这个国家,等待会是何等的漫长。
行李到了吗?
迟早总会到的。安德烈说。
三个半小时,他在想。莫斯科这么近,同时又那么遥远!就三个半小时的距离,为何却很少去看玛莎?(见她一面,困难重重,首先是旅费的问题)
三年的时间,很长。他说。你一定觉得我老了。
哪有啊。你没变。
你可是变得更美了。
他欣喜地看着她。他以为,不会再发生什么让他心动的事了,他已经认命了(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尽管他不动声色),可是突然,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厚的温情照亮了他的生活。他曾经对那个怯生生的小姑娘几乎不感兴趣她当时叫玛莉亚,克莱尔带着她从日本,从巴西,从莫斯科来到法国,和他见面,每次就待几个小时。她对他来说很陌生。战后,长成年轻女子的她,来到巴黎,向他介绍了自己的丈夫。但是,玛莎第二次(1960年)去巴黎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不太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强烈地依恋他,这让他很感动。妮科尔对他的爱热烈,专心,畅快;但他们之间太习惯对方,安德烈无法在她身上唤醒那种灿烂的喜悦。此刻,那种喜悦正在改变玛莎有点严肃的脸部表情。
行李到了没有?妮科尔问道。
迟早会到的。
着什么急呢?在这儿,他们的时间很富裕。在巴黎,时间的流逝让安德烈很苦恼,接二连三的约会应接不暇,尤其是自打他退休以后:他高估了时间的富裕。出于好奇,也因为无所事事,他揽了一大堆的事,无法脱身。现在,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可以解放自己;他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他很喜欢这种状态,喜欢过头了:他的大部分忧虑由此而生。
瞧,咱们的箱子。他说道。
他们把行李箱放到车里,玛莎开动汽车。和这里的所有人一样,她开得很慢。道路上散发着绿色植物清新的芳香,载着树木的船队在莫斯科河上漂游。安德烈感到一种激动之情涌上心头,缺少了它,生活对他来说将会索然无味:历险开始了,他既兴奋又害怕,这就是探险。成功、出人头地的事,他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如果不是他母亲独断专行,不遗余力让他继续求学,他完全会满足于父母的命运:当一名沐浴在普罗旺斯阳光下的小学教师)。他觉得,他存在的真谛和他的宿命,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像种子一样,隐隐糊糊地散落在大地上;要了解它们,就要考察养育它们的时代和地域;因此,他喜欢历史和旅游。当他研究折射在书本里的历史时,他很淡定,然而,一走近一个陌生的国度,他总是有种迷失感,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家完全超出了他对它的了解。他与这个国家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密切。他是在列宁崇拜的教育中长大的;他八十三岁的母亲,现在依然跟着共产党战斗;他没有加入她的阵营;但在经历了希望和失望的纠结之后,他仍然认为,苏联掌控着未来,也就是说,苏联掌控着这个时代和它自己的命运。然而,他感到,自己从来也没有即使是在斯大林主义盛行的黑暗年代对这个国家如此的不理解。此行会消除他的困惑吗?1963年,他们以游客的身份去了克里米亚、索契,那是一次走马观花式的旅行。这次,他会提出问题,让人给他读报,融入大众。汽车驶入高尔基街。行人,商店。在这里,他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吗?一想到答案是否定的,他就陷入恐慌。我真该更加认真地学习俄语了!他心想。这又是一件他打算要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他只学到阿西米教材的第六课。妮科尔称他是个老懒鬼,很有道理。读书,聊天,散步,这些事他总是乐此不疲。可讨厌的学习学单词或建卡片让他很反感。他真不该把这个世界太当回事。他太认真,又太轻率。这是我的矛盾所在。他乐滋滋地自语道。(这是一位意大利同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他很欣赏。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使他妻子饱受折磨)。其实,他自我感觉一点都不差。
火车站的绿色很惹眼:那是莫斯科的绿色。(如果你不喜欢它,你就不喜欢莫斯科。安德烈三年前曾这么说。)高尔基街。北京饭店。城里到处是雕饰繁复的高楼大厦,都借鉴了所谓的克里姆林宫建筑风格,与之相比,北京饭店就像一块渺小的塔式蛋糕。妮科尔什么都记得。她从车里一出来,就闻出了莫斯科的气味,一种比1963年更加强烈的汽油味儿,大概是因为汽车比以前多多了,尤其是大、小卡车。上次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吗? 她走进宾馆空荡荡的大厅时自问。(报摊上盖着一条浅灰色的布单;夸张的中式装潢的餐馆门前,有人在排队)。三年的时间飞逝而过,令人惶恐。她的生命中还有多少个三年?这里没有任何变化,除了过去非常低廉的外宾房价长了三倍,这一点玛莎已经告诉他们。四楼的女服务员给了他们一把房门钥匙。走过长长的楼道时,妮科尔感到,女服务员的目光一直盯着她的颈背。房间里有窗帘,这是运气:在这里,宾馆房间的窗玻璃常常是光秃秃的。(玛莎家也没有真正的窗帘,只有轻轻的薄纱。他们习惯了,她说;甚至,房间里一片漆黑反倒会影响她睡觉。)楼下的大路完工了;路上的汽车驶入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下的一个隧道。人行道上的人群身着夏装:正在散步的女人们穿着花裙子,露着胳膊和腿。现在是六月,她们认为天很热。
这些东西是给您的。妮科尔打开箱子,对玛莎说。
是些新出的小说、七星丛书,几张唱片。还有长袖羊毛开衫、长筒袜、短袖衫:玛莎喜欢打扮。她兴高采烈地摸着羊毛、丝绸,对比着颜色。妮科尔进了浴室。又是运气:两个水龙头和抽水马桶都运转正常。她换了裙子,补了一下妆。
裙子好漂亮!玛莎说。
我挺喜欢的。
五十岁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打扮不是太暗淡就是太鲜艳。现在,她知道可以穿什么,不可以穿什么。穿衣服不成问题。但也没乐趣了。过去,她和衣服之间那种亲密的、近乎温馨的关系不复存在了。她把套服挂在衣柜里:尽管穿了两年了,这套衣服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没有个性的物件,她从中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任何属性。玛莎正对着穿衣镜微笑,但不是冲着刚刚穿上的漂亮衬衫,而是因为她自己出乎意外的、迷人的变化。是的,我记得这家餐馆,妮科尔说。
我在普拉加餐馆定了座儿。玛莎说。
玛莎还记得这是妮科尔喜欢的餐馆:她这么体贴人,记忆力和我一样好,一样有条理。妮科尔理解安德烈对玛莎的喜爱。更何况,他一直都想要个女儿,他有点抱怨菲利普是个男孩儿。
玛莎在十分钟之内把他们送到普拉加餐馆。他们在衣帽间存放了大衣,这是规矩:这里禁止穿着或拿着大衣进入餐馆。他们在一个铺着石板、布满棕榈树和绿色植物的餐厅里入座;一幅淡紫色的风景画覆盖了整个一面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