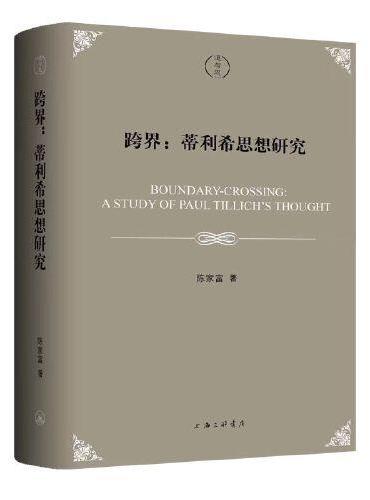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泉舆日志 幻想世界宝石生物图鉴
》
售價:NT$
611.0

《
养育女孩 : 官方升级版
》
售價:NT$
2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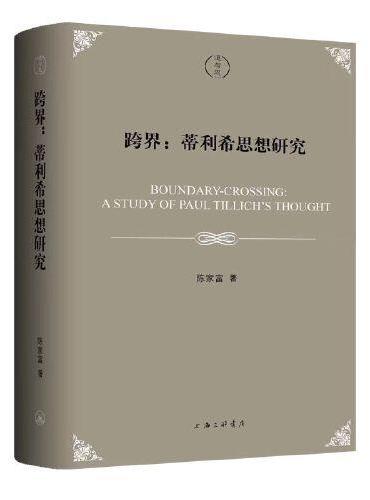
《
跨界:蒂利希思想研究
》
售價:NT$
500.0

《
千万别喝南瓜汤(遵守规则绘本)
》
售價:NT$
203.0

《
大模型启示录
》
售價:NT$
510.0

《
东法西渐: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法的记述与评价
》
售價:NT$
918.0

《
养育男孩:官方升级版
》
售價:NT$
230.0

《
小原流花道技法教程
》
售價:NT$
500.0
|
| 編輯推薦: |
|
商战风云诡谲X情场暗潮汹涌。这一生最幸运的是—— 以你之名,冠我之姓。
|
| 內容簡介: |
香港商人阮东廷为了照顾前女友何秋霜,与歌女陈恩静结婚,并事先明言,这是场有名无实的婚姻。可婚后阮家却接二连三地发生怪事:先是娱乐记者过分关注阮、陈二人的婚姻;再是阮家莫名出现的几个监控器;三是阮东廷任CEO的“阮氏酒店”出现了员工中毒案,阮东廷的妹妹阮初云被牵涉进去,可就在问题即将解决时,初云车祸身亡。
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正常的交通事故,可心思缜密的恩静却认为事故与何秋霜有关,并坚持查案。阮、陈二人的关系因这件事越来越紧张,最终恩静是否能揭开事故背后的秘密?阮氏夫妇是否能破镜重圆?“阮陈恩静”这四个字,是否能继续存在于世人眼前?
|
| 關於作者: |
吕亦涵
爱格签约作家。
闽南女子,大学经管专业教师。
平时教书,忙时读书,闲时写书。深爱勃拉姆斯与颠狂时期的舒曼,向往伊壁鸠鲁式的纯粹快乐,享受独舞的欢愉。
对爱情深信至固执,故常写爱情。
喜静亦喜闹,人生状态,常在沉默与喧哗之间,在冷静与热烈之间。
写作如同听交响曲,关键是,你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场盛大的欢愉或悲怆里。
新浪微博:@吕亦涵_Zoe
|
| 目錄:
|
楔子
第一曲 人生若只如初见
第二曲 似此星辰非昨夜
第三曲 历尽沧桑情不变
第四曲 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五曲 只是当时已惘然
第六曲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七曲 夜深忽梦少年事
第八曲 白头偕老共余生
番外 也无风雨也无晴——何秋霜
后记 关于爱,你想说一些什么?
|
| 內容試閱:
|
楔子
1992年,香港,维多利亚港。
维多利亚港的天永远暗得比鼓浪屿要迟,时至五时半,夕阳仍悬在海的那一方,不肯坠下。晚霞,
散漫地染了大半个世界。那样美至诡异的静,竟十万八千里地区别于海港这一方。
恩静眼望着那方诡异的静,置身处,却是一片喧哗——
“来来,阮生、阮太,再来一张……”
“太棒了!阮太真是上镜……”
此时的这二人,众人口中的“阮生”与“阮太”,正亲密地偎依在海港边上。他着黑色三件套,她
则是黑色小礼服配简约的钻石首饰;他高大冷峻,她纤瘦温文,远看近看,都是一对璧人。难怪全
港近半的名人都聚于此,娱记们的脖子和镜头也挤着要伸往这一处:“阮生、阮太,阮生、阮太…
…”
无数问题皆雷同,恩静在数不清的“阮生、阮太”中,渐渐被夕阳勾去了魂。
直到扣着她纤腰的手紧了紧,她才又回过神来。抬起脸转过头,就见她的阮生面色冷峻,原本就刚
毅的脸部线条此时更是锐气逼人。不必细想也知道,这就是他发怒的前兆,恩静连忙静心屏气,迎
向记者的提问——
“阮太太,对于今早的新闻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是啊阮太太,报纸一早就爆出阮先生昨晚在何小姐房里过夜,两人旧情复燃……”
“阮太太、阮太太……”
她的心一紧,没想到阮东廷黑脸的原因会是这个。周遭记者的提问猛于虎,某娱记甚至直接将话筒
伸过来:“阮太太,听说今天中午在何小姐的房间里,阮先生为了维护旧情人,甚至不惜和你翻脸
……”
“Shit!”这话一落音,阮东廷彻底黑了脸。记者们还要问,谁知他浓眉一皱,“让开!”
两个字不怒而威,众人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竟真的让出了一条道,半句“阮先生”都不敢再唤。
阮家大少在港媒眼里是出了名的坏脾气,可偏偏他含着金汤匙出生,在一群贵公子中又是难得的英
俊。剑桥毕业,回国后又在刚一接手的阮氏连锁酒店里掀起惊涛,如此具有偶像潜质的背景再加上
一张英俊的脸,即使记者不喜欢,读者也爱看哪!
故此话筒又不死心地伸向陈恩静:“阮太太、阮太太……”
谁知刚踏出这圈子的阮东廷又回过头:“恩静,过来。”
他伸出手,冷峻的面孔只对着她。
那样冷的脸对上她说不清是什么表情的清瘦面孔,大手朝向她,顿在空中。一群记者皆面面相觑—
—阮生这摆明了是不让阮太说话啊!而记者群中间的阮太太呢?没有多想,已朝着他走去。
他余怒未消,而她沉静如水,在镜头里,纤手再自然不过地交入那只大掌内。
在公众面前、在旁人面前、在报纸上、在杂志上,他永远牵着她的手,大掌贴置于她的腰间。所以
早一阵子,人人都说阮氏夫妇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是好姻缘,在贵公子群里简直难得一见。可唯
有她知道,那只手虽暖,但自始至终也未曾与她热络与亲密过。
他牵着她的手,一高大一纤瘦的两道身影不疾不徐地往夕阳处走去。
记者们纷纷叹气,可突然,行进中的阮太停下了脚步,回头,似有话要说。
记者们立即又迎上去,将话筒递向前方。
她的声音柔和,甚至还带着淡淡的笑意:“其实我本不想说的,因为觉得这是我阮家的私事。不过
既然各位关心,我也就不妨说清楚了。”她顿了一下,看着前方黑压压的一群人竟齐刷刷地拿出记
录笔,她流畅的港式粤语里,竟听不出一丝口音,“从昨晚到今天早上九点,我先生一直都待在家
里,希望各位不要再肆意诽谤他。我们不是演员也不是歌星,不需要将私生活都摊开摆到诸位的眼
皮子底下。如有下次,我不介意上律师楼采取防护措施。”
第一曲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止是记者?就连她的阮先生也有一瞬间的错愕。在他的印象里,恩静永远是个温文的女子,连话
也不曾大声说过。没想到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当着即将被送往全港各大电视台、报刊的镜头,
她会这么说。
不过错愕仅一瞬,待走到无人的停车库时,牵着她的那只手便松开了,阮东廷拿出手机。那时的手
机个头大,往耳朵上一贴,便挡住了他大半张脸。
只是声线里的冷冽却是如何也挡不住的:“把录像全部调出来,查查中午是不是有人跟踪太太去了
酒店。”
话刚说完,司机已经机灵地将车开了过来。他看也没看他的阮太太一眼,便上了车。恩静叹了口气
,绕到另一边,默默地开门坐进去。
车厢里一片压抑。
数不清这是第几次,他冷着脸坐在她身旁。
旁人都说阮先生面瘫,百年如一日摆着一张严肃的脸。可她就是知道,当他浓眉拧起,浑身散发着
“生人勿近”的厌恶气息时,这一刻的阮东廷是危险的。
而这样的危险,他已持续了整整一下午。
司机阿忠在前座说:“先生,刚刚老夫人吩咐我,让您和太太务必要回家吃晚饭。”阮东廷也不回
答,两眼只是盯着窗外飞速闪过的霓虹,徒留一个冷硬的轮廓印在她的眼中。
“阿忠说,妈咪让我们回家吃饭。”不忍看司机为难,恩静也开了口。
可阮东廷不买她的账,头也没转一下就发出命令:“阿忠,直接开去酒店。”
“可老夫人说……”
“阿忠,你停车。”柔柔淡淡的声音又从后座传来,这回是太太。
阿忠如获大赦,连忙选了个地方将车停下,人也机灵地下了车。
阮东廷却像是没看到这变化一样,依旧盯着窗外。恩静看着他冷硬的侧脸,沉默了片刻才开口:“
中午那件事,并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你的意思是秋霜骗我?”淡淡的嘲讽从男人嘴里说出来,这下子,他终于回过头,对上她的眼,
“我和秋霜认识了十五年,十五年来,她从没对我说过一句假话。”
“所以,就是我在撒谎了?”
他定定地看着她,这样好看的面孔,配上的却是那样冰冷的神色。
恩静垂下头,嘴边有自嘲的弧度淡淡勾起:“也是,再怎么错,也不会是她的错啊。”轻轻的话语
溢出,再抬起头时,她已换上一副平静温柔的神色。“妈咪估计很生气,你还是先回家吧。如果不
想见到我……”她顿了一下,努力维持着嘴角的温柔,“如果不想见到我,我先去商场买点东西,
再回去吧。”
她声音清清淡淡,温和无害得如同她的面目她的性子,如同嫁入阮家这几年来,平静如水的一千多
个时日。
直到,她出现。
七个小时前——
恩静挂断电话时,掌心已出了一层薄薄的汗。大哥一个月前向她要不到的那三十万,何秋霜竟然汇
给他了?
二十分钟还不到,她便出现在阮氏酒店里。三十八楼,12号房——恩静记得清清楚楚,这个房间在
阮东廷的安排下永远是空着的,只为迎接每年的那么几个月,娇客光临,蓬荜生辉。
敲门声轻轻响起。
“来啦!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哪?”娇俏的嗓音从房里传出来,门一打开,恩静只觉有无尽惊艳的光
从门缝里射出,那是何秋霜:皮肤白皙,身材高挑,五官深邃,再加上一头永远像是从美发沙龙刚
处理出来的长卷发。
门一打开,女子的欣喜便和着这艳光一同倾泻出来。只是在发现来人并不是阮东廷后,那笑意骤然
一敛:“怎么是你?阿东呢?”
话虽这么问,可秋霜看上去一点讶异也没有。
倒是恩静有些尴尬:“他不知道我过来。何小姐,我是想来问问你那三十万……”
话还没说完,已经被秋霜打断:“哦,给你哥的那些钱?”方才的欣喜已荡然无存,她边捋着泼墨
般的长卷发,边转身回房。
恩静也跟着走了进去:“何小姐,那些钱还是请你收回去吧……”
“哪有这种道理?送出去的钱就是泼出去的水,再说了,你这么帮我和阿东,我帮一帮你哥,也是
应该的嘛。”
她娇媚地笑着,明明是正常的道谢的话,可传到恩静耳朵里,那个“帮”字却似灌入了无限讽刺。
她看着秋霜慵懒地坐到贵妃椅上。是的,与这间房一样,房内所有的一切都是特别配置的。她记得
阮东廷跟下面的人吩咐过,秋霜喜欢软皮贵妃椅,秋霜爱喝炭焙的正山小种,秋霜要求房间里要有
香奈儿五号香水的气味——如今看来,员工们的办事效率还真是很高呢。
她在荡漾着香奈儿五号香水气味的房间里听着秋霜说:“恩静啊,我才真是要谢你呢。谢你这么识
相,替我和阿东掩护了那么久,却一点非分之想也没有。昨晚他在我这儿时就说过了呢。”说到这
里,她轻轻一笑,“在我这儿”等字眼被咬得暧昧而缠绵,“他说你始终谨记自己的出身,知道在
渡轮上唱戏的就算穿上了名牌,也只是个穿名牌的歌女,对他半点小女生的幻想也不敢有呢。”
恩静的面色微微白了白,却被何秋霜热络地握住手:“这么有自知之明,你说我该不该谢你?当年
阿东选你来替我们打掩护,可真是一点也没选错呢。”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却越来越清晰。
原来时隔那么久,当年她是怎么来的、她是为什么才跟他来香港的,她依旧坚定不移地记着——
“我知道你哥欠了一笔债,我知道你家里情况不好。”
“如果你需要,礼金多少都不是问题。”
“嫁给我,你会有更好的生活。”
“你的家人我也会打点好,生活费、房子、车,一样不少,一定会让他们满意的。”
“唯一不足的是,我已经有爱的人了,所以,我无法给你爱情。”
原来她自己也都记得,刻骨铭心地记得那一年厦门海边冰凉入骨的雨,一阵风吹过,她说:“阮先
生,我答应你。”
不是“阿东,我愿意”,而是“阮先生,我答应你”。
答应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恩静一家过上了好上不止几个档次的生活,他因此心安理得地带着她回香
港,让她成为阮太太。然后,他在这阮太太的掩护下,继续过他与秋霜的二人世界。
你看,她与他之间,说穿了,不过是场交易。
只因是场交易,所以从那年至今,无论在外界看来两人怎么举案齐眉怎么恩爱有加,在私底下,她
永远叫他“阮先生”——“你已经是我太太,以后家里怎么叫我,你也跟着叫吧。”那年新婚,他
这样说过。可永远对他言听计从的她只是笑笑,转头看向窗外盛开的紫罗兰:“阮先生你看,它们
开得真美。”
如此固执,不过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她与他之间,掀开表面看本质,亦不过是“阮先生”与“陈
小姐”的关系。
还能再妄想些什么呢?
何秋霜陡然变调的尖叫声拉回了她的思绪:“陈恩静,你不要太过分了!”
恩静一怔,还没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已经被何秋霜狠狠地甩开了手:“三十万我已经给过你了
,够仁至义尽了!现在你竟然还想狮子大开口?”
“什么意思……”
“怎么回事?”疑惑自恩静的喉间溢出时,门那边也传来了含怒的冷冽的声音。
一时间,恩静只觉得千年寒冰朝着她迎头砸下。
是阮东廷!那是阮东廷的声音!
电光石火只一瞬,她立刻就反应过来——难怪这女人会莫名其妙地勃然变色呢!难怪要说那段莫名
其妙的话呢!
彻骨的寒意瞬间窜过她的四肢百骸。
而何秋霜已朝着阮东廷扑过去:“阿东,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一定要告诉你!”
阮东廷没有推开她,只是在看到不应出现于这个房间的身影时,浓眉一皱:“你怎么过来了?”
“我……”
“当然是为了她哥!”恩静还没开口,何秋霜已经抢在了前头,“她哥做生意失败,之前她来找我
要钱时,我已经给过她三十万了,谁知今天……”
“你胡说什么?”恩静震惊地转过头,可对上的,是阮东廷已然皱起的眉头:“你哥的事?”
他看向恩静,满眼不赞许的神色:“我不是说过这件事不准再提了吗?”
“是啊,就因为你不准她提又不给她钱,她才会来找我嘛!”这女人的声音听上去可真是义愤填膺
,“那天说得可惨了,说自己当了这么多年有名无实的阮太太,全拜我这破烂病所赐,我心一软就
开支票给她了。可谁知她今天、今天竟然又来要钱,还一开口就是五百万!开什么玩笑,当我是印
钞厂啊?”
何秋霜声色俱厉,抓狂的表情看上去那么逼真。恩静站在这两人对面,一个义愤填膺地控诉着,一
个浓眉越拧越紧,那双永远冷峻的眼里仿佛夹杂着千年寒冰,射向她、射向她,寒意统统射向她,
似乎已不必再分青红与皂白。
恩静只觉得心一紧:“我没有……”
话音却被何秋霜的高分贝盖过:“还敢狡辩?阿东,你不知道她刚刚说的话有多难听!她甚至还威
胁我,说我要是不给她钱,就要把她当年嫁给你的原因公之于众,让你在媒体面前出丑!阿东……
”
“够了。”低沉的声音从男人的胸腔里震出,随便一听也知道那里头含了多少压抑的怒火。恩静只
觉得他眼里夹冰,话中冒火,冷与热复杂交融着对向她,“出去。”
“阮先生……”
“别让我说第二次。”
她僵直地站着。
对面的何秋霜正偷偷朝她愉快地眨眼睛,在阮东廷看不到的角度,就像看了一场有意思的戏:“走
吧妹妹,别再惹阿东生气了。”
恩静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房间的。
阮东廷还冷着脸站在那儿,秋霜已经像个好心的和事佬,半拉半推着恩静出了房间:“好啦,别再
惹阿东生气,你也知道他那性子……”直到走出房间一大段距离,快到电梯口了,她才笑吟吟地松
开手,“看到了吧?不管怎么样,阿东都是站在我这边的。”
那张娇艳浓烈的脸,笑得多么无邪。
恩静脸上已说不清是什么表情,她不可思议地看着何秋霜,若不是事情荒唐,她简直要佩服这女子
的演技:“为什么?”
这些年以来,阮太太的位置即使她坐着,可她、她、他皆知,这不过是个名存实亡的空壳——他爱
的是何秋霜,一直藏在心里的人也是何秋霜。地位已经如此稳定了,这女子到底为什么还要给她这
个毫不重要的角色一个下马威?
“为什么?你想知道吗?”何秋霜的声音低了下来。瞬间,对话从粤语转换成只有彼此熟悉的闽南
语。“从那天你不识相地到酒店给阿东送汤起我就觉得,很有必要帮你重新认清自己的位置。”她
轻轻一笑,口吻几乎是温和的,越发靠近她,“歌女陈恩静,因为被阮东廷和何秋霜看中,带回香
港打掩护,当了阮太太,穿了名牌,学了粤语,可她依旧只是个歌女!”
十个指甲深深地嵌入掌心,恩静的眼眶里似有什么东西要溢出。看清楚了,才发现那不是泪,而是
怒气。
她这个人,二十几年来都是一个软柿子,温温柔柔的,任人拿捏操纵。十几岁时被父母安排到渡轮
上唱南音,二十几岁时被阮东廷看中,来当了这个名不副实的阮太太。
以至于何秋霜所说的这些话,她无法反驳——她竟无法反驳一句!
恩静转过身,大步走向电梯。
很快却又被何秋霜拉住:“你以为这就够了吗?”
“放开我!”
“很快就能放开你。”何秋霜的表情森冷。说完这一句,她突然抓住恩静的手就往自己脸上掴来—
—是的,她拉着恩静的手,掴到自己的脸上!
她竟拉着恩静的手,掌掴她自己!
看上去是多么滑稽可笑的场面,可阴谋的味道也迅速窜入恩静的眼耳口鼻。很快,她就听到何秋霜
一边将自己的脸掴到通红一边大叫:“啊——你这个女人!阿东、阿东你快出来!”
等阮东廷赶出来,秋霜早已放开恩静的手:“快看看你的好太太,你看看!我不过是劝她两句,她
竟然动手打我!”晶莹的泪珠簌簌落下,点缀着她美丽的面孔。
恩静一开始还是错愕的,可是只一瞬间,那阴谋瞬间就明朗了——蓦地,她笑了。
那厢何秋霜还在声色俱厉地表演:“你这个女人,我告诉你,你哥那边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嘲讽在恩静的脸上越扩越大,越扩越大。
已经不想再看到这个演技绝伦的疯子,她只看向阮东廷:“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是她自己掌掴自己
……”
“你以为她是傻子吗?还是你以为我才是傻子?”阮东廷的脸上已结了一层厚厚的霜。
不必查也不必问,他已经相信了她。
是谁说过爱就是无条件地信任啊。呵,说得真好!何秋霜不是傻子,阮东廷也不是傻子,她陈恩静
才是傻子!傻得自投罗网来供这对相互信任的爱侣消遣娱乐,傻得竟还想在她何秋霜面前向他阮东
廷索要公平!
已经无须再多说什么,恩静转过身,静静地按下电梯的按钮。
显示屏上的红色数字跳动变化着,1、2、3……她在遥远的三十八楼,电梯迟钝而缓慢,终于升到三
十七楼时,她转过头来,平静地看向何秋霜:“你好像忘了,酒店里的每一层都有监控。”
何秋霜原本得意的脸一白。
恩静已走入电梯里。
十二月的风从车窗外冷冷地灌进来。很显然,他并没有去查监控,大抵是觉得没必要,于是至此,
他的表情仍冷冽如这十二月里的风。
“阮先生,你先回去吧。”这是她的声音。
他沉默了。
“妈咪等久了,估计会生气的。”她推开车门,纤瘦娇小的背,着黑色晚礼服,戴着配套的精致首
饰,融入夜色中。
“太太!太太!”阿忠在身后唤,见她不回应,又将头探入车内,“先生,太太她……”
“开车。”一个平缓没有起伏的声音响起,这是他的回应。
香港的夜璀璨得就像是永远也不必有天明。明明地处亚热带,可被灯光点亮的这座城,到了十二月
也还是冷。恩静脚踩三寸高跟鞋,极细的鞋跟踩在地上发出颤巍巍的声响,一下,两下……她漫无
目的地走了好久,终于,终于在路过的公园小石椅上,腿一软,瘫了下去。
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
“歌女陈恩静,因为被阮东廷和何秋霜看中,带回香港打掩护,当了阮太太,穿了名牌,学了粤语
,可她依旧只是个歌女!”这一个难堪的中午,何秋霜如此一字一句。
而她无法反驳。
自那天在厦门的海边,他说“我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而她回“阮先生,我答应你”,此后年岁
漫漫,她守着一个婚姻的空壳,人生再坏,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反驳。
路是自己选的,谁说过的,就是跪,你也要跪着走下去。
公园另一处,竟回应般地响起喧闹的管弦乐器声,多么讽刺!她静心凝神听了好久,才发觉更讽刺
的是,那方传来的悠悠唱声,竟是“一江秋,几番梦回”。
“一江秋,几番梦回,红豆暗抛,悲歌奏……”那是1987年的厦门,她曾在阮东廷身旁唱了一整夜
的南音。
恩静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晚上,月色冷冷地斜穿过别墅庭院——曾厝垵这边有户富人家的公子过
世了,招她来唱南音。满堂静寂的凄哀,越到深夜越是寂寥,只靠着她在一旁弹着琵琶唱着曲,哀
哀作为遗孀孤冷的背景。
直到夜很深很沉之时,别墅的大门终于被人推开,高挺的男子风尘仆仆赶到灵堂里。
那时弹琵琶的女子正好唱到了“一江秋,几番梦回”,而他置若罔闻,亦不顾她见到他时满眼欣喜
过后的呆滞,他只顾着拉着遗孀的手,冷峻却不容置疑:“秋霜,阿陈临终前我答应过他,一定会
找最好的医生,永远照顾你。”
弹琴女子的琵琶声断了一拍,却没有人在意。
弹琴女子呆呆地看着男人高挺的身姿,却没有人在意。
弹琴女子过了两三秒才重新操起乐器来,还是没有人在意。
夜深知琴重,只衬得遗孀的声音更加孤独:“你妈不会同意的,而且我也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你
怎么可能一直陪着我,陪到我死了再去考虑终身大事吗?”
琴声悠悠,凄哀如同背景,唱南音的女子也只是个背景,只用来衬托阮、何二人可歌可泣的爱情。
那晚她在灵堂,听着男客人与遗孀谈了大半生的旧事:八年前,共同自剑桥毕业回国时,她因查出
身患尿毒症,被阮妈妈逼着离开他、嫁给了他的好友;八年后,她丧偶病重,而她的尿毒症反复发
作,他却还是固执地想要挽回她。
那是1987年,落着雨的夜,整间灵堂里只有那对感人的男女和如背景般的唱着南音的女子。
可没有想到,也就是在那一夜,背景女子的命运却全然改变了——阮妈妈出现了。是的,就是她如
今的婆婆张秀玉——几乎就在东廷和秋霜聊完旧事没多久,她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灵堂里:“阿东
,这女人我是不会同意的,快跟我回去!”
可他怎么会愿意就这样回去?一回去就代表了什么,后来恩静也从张秀玉口中得知了:原来当时她
老人家已经在香港为阮东廷安排了好几场相亲。
只是,他怎么可能同意呢?
也就是在那一瞬,那双森冷的、精明的、锐利的眼盯上了她,盯上了一看就知家庭情况并不好的她
。
一分钟后,他朝着她走来,拉起她弹着琵琶的手:“妈,是她,我想娶的不是秋霜,是她。”
命运更迭,原来不过是一瞬。
不过是男主角的母亲不喜欢女主角,不过是他阮东廷和她何秋霜需要一个掩护,以偷天换日、暗度
陈仓,成全两人矢志不渝的爱情。
天亮时,这个还来不及认识便说要娶她的男子带着她到海边,走了好久,才开口:“不好意思,请
问小姐姓名?”
“耳东陈,恩静。”
“陈小姐,我有个不情之请,你可不可以嫁给我?”
是了,这就是求婚的全过程——她嫁给他,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他的不情之请。
绵绵细雨还在下着,冰冷得如同男子有礼而生疏的问话。可他的问话并不只是有礼,还有着他惯有
的不容置疑。他说:“陈小姐,我知道你家的情况不太好。”“如果你需要,礼金多少都不是问题
。”“你的家人我也会打点好。”……
那是1987年,他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她的场景。无数年岁后,当阮生忆起最初相识的场景,脑中浮现
的,总是那年女子听着他不像求婚的求婚词时,眼中慢慢生出的泪意。
而后,她垂下头,安安静静地等他说完,才接话:“我十四岁那年,曾幻想过一个浪漫的求婚仪式
,因为那时有人和我说,等我成年了,就来娶我。”
风马牛不相及的话让阮东廷愣了愣。
“后来呢?他来了吗?”
“没有,他没来。”
怎么还会来?那个在十四岁那年说过要来娶她的男子,那曾让她误以为是认真的男子,事情一过便
将她遗忘了,又怎么还会来呢?
后来再来的,已是八年之后现实中的人,在清晨冷冷的海边,对她说:“嫁给我,你会有更好的生
活。”
原来现实与记忆的差距如此之大,他再也不是十四岁那年在船上遇到的男子。
再也不是。
恩静的泪水突然滚出眼眶,止也止不住。她尴尬得忙用手揩去那些泪,可男子的手帕已经贴上她的
脸颊,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擦拭着那滚烫的液体。
半晌,低沉的嗓音才溢出喉:“别难过了,也许,他有什么重要的事。”
是啊,他还有更重要的事,他的人生里,始终都有更重要的事啊。
恩静的心一沉:“阮先生,我也有个不情之请。”
“说说看。”
“你能不能……抱一抱我?”
替她擦拭着眼泪的大手一僵。
他怎么会知道这一抱之于陈恩静的意义?
到底他早就已经忘了:关于他和她的初遇,怎么会是1987年、在阿陈过世的这一年?
1979年,她十四岁,头一回在豪华游轮上给人唱南音。而那晚,正是何秋霜与阿陈的婚礼。
是,何秋霜与阿陈。
爱人他嫁,新郎不是他。
而她,遇到了他。
即使后来大家都知道,何秋霜之所以会下嫁给阿陈,不过是查出自己患了尿毒症——听说那时的她
惊慌失措,只想着如何才能不连累深爱的他,想着想着,再加上阮妈妈的威逼,最终,她嫁给了别
人。
可彼时阮东廷并不知情。
在那场游轮喜宴上,觥筹交错间,乐声哀凄婉转,明明是南音一贯的曲调,却被满船不懂南音的宾
客批成了“丧乐”。而在她因这“丧乐”遭到一席乘客投诉时,他朝她招了招手:“到我房间唱吧
,小费双倍。”
众人眼中的暧昧如潮涌,何秋霜的眼里更像是能射出刀子,却阻止不了他将她带入房间。
只是进了房间后,他又不说话了,颀长的身躯只是伫立在窗口,一直沉默。
恩静站在他身后,无数次想开口,却又不忍打破这宁静。
许久后才听到他用生硬的普通话说:“马上要下雨了。”
话音甫落,甲板上就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
“你是厦门人?”他又问。
恩静轻声回答:“泉州人。”
“无妨,说的都是闽南话。”这下,颀长的身子终于转了过来,那张冷峻的脸直直地对向她,“听
说在你们闽南话里,‘美’和‘水’同音?”
不知为什么,恩静突然有点紧张,不过她还是点头:“是。”
“那‘你好美’怎么说?”
“是‘里雅水’。”
多奇怪的音啊!软软的,柔柔的,阮东廷学着她念了一遍,又念一遍,嘴角渐渐僵了起来:“没机
会说给她听了。”
那是她这一生第一次看到爱情的样子,罩在冷峻男子的身上。原来,连旁观者也会跟着心碎。
那一次,她在他的房里整整唱了一夜。他坐着,她站着,后来变成他和她都坐着。琴声悠悠,曲调
哀哀,有时一曲终了,他会问:“累了吗?休息一会儿吧。”于是两人便静静地坐着,坐到她觉得
奇怪,又开口:“继续吗,先生?”
“继续吧。”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了又停,下了又停。
她拨动琴弦,调起嗓子,凄婉的歌声绕着男子冷峻的脸。伴着雨,她悠悠地唱起:“悲欢离合总无
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天明时再出阮东廷的房间,旁人看她的眼色已经不同。那群狐朋狗友一见阮东廷便围了上来,口吻
暧昧:“昨晚还尽兴吗?”
不怀好意的口气让恩静又惊慌又尴尬,还好阮东廷懒得理,扭头就要吩咐她离开时,眼睛一移,却
又瞥到一抹越走越近的红色身影。
一时间他换了表情,大手突然伸过来握住恩静的手,薄唇移到她的耳边:“他们问我尽不尽兴呢,
你说我尽不尽兴?”
原来这样冷峻的人,在某种时候,面部表情也能变得这么邪气。
恩静被握住的皮肤一整块灼烫了起来,可刚要挣扎,又被阮东廷更紧地握住。
直到那抹红款款走到两人身边,略带鄙夷地说:“阿东,你这是饥不择食吗?”
恩静挣扎的手一僵。
可阮东廷只是冷冷地勾了下唇,深幽如海水的眼看似定在了恩静身上:“饥不择食?呵,这样漂亮
的孩子,陈太太却用饥不择食来形容,是不是太过分了?”
何秋霜的脸几乎气到变形,完全没有别人家太太的自知:“阮东廷,你这是在报复我吗?”
阮东廷却像是听到了笑话:“陈太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人皆有之?呵,要真那么喜欢,你把她娶回去啊!”
“好啊。”这话一落音,所有人都愣住了。看着恩静像是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阮东廷又调柔嗓音
,“可惜太小了,这样吧,等你成年了,我就来娶你。”
没有人会信这种话的,富家子弟和卖唱女?呵!
可那时她十四岁,自知卑微却仍对这世界存有幻想。恩静睁大眼,瞪着这张不应存在于她的世界的
好看的脸,口吻是那么小心:“真的吗?”
握住她的那只手一僵,可很快,又传来他淡定的嗓音:“真的。”
可后来呢?
后来,游轮抵岸,欢闹散场,那个说要回来娶她的人,一转身便将承诺抛到了海水里——
“等你成年了,我就来娶你。”
“真的吗?”
“真的。”
阮先生你看,你一笑我记了那么多天,你一句话我记了那么多年。
那是1979年,厦门海上落雨的夜。
即使最终的最终,你真的前来,将我娶走,也未曾发觉这场命运的更迭。
(未完待续)
精彩看点,烧脑悬爱:
1、爱情中穿插悬疑成分,且疑点随着剧情层层深入、不断改变。
2、无狗血的“所有男配都爱女主“或”所有女配都爱男主“的情节,男女主的感情由极度虐心发展成为极度娇宠,感情强烈。
3、融入商战、中国传统音乐南音元素,富有文化底蕴。
4、两对男女的爱情充满了甜蜜温馨感,使得悬疑的剧情依然充满了爱情的感觉。
5、男一、男二之间“一朝为兄弟,则一世为兄弟”的感情令人感动。男二、女二的爱情故事有趣诙谐。
角色设定,个性鲜明:
阮东廷:时而冷峻,时而邪魅,典型的腹黑男,永远胸有成竹却不动声色。不爱时严峻冷漠,爱时极度娇宠。对何秋霜,他是同情;对恩静,他是宠爱和保护。
在恩静将南音引入“阮氏”、惹得媒体一片流言诽语时,他说:“既然是我的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我担得起。”在恩静因恨何秋霜而差点犯错时,他说:“你来我阮家时就是清白坦荡的女子,所以我要你这一生,都这么清白坦荡。”
连楷夫:香港花花公子第一人。风流倜傥、拥有一双桃花眼。一开始为了帮阮妈促进男女主角的感情,表现出对恩静的觊觎,其实与阮东廷是很铁的哥们,并在查案过程中出了大力。 对恩静的好友Marvy一见钟情。
陈恩静:细心、聪慧、冷静。唱南音出身,虽因此屡屡被何秋霜嘲笑,却对南音有着深厚的感情。外表温柔,内心坚强,该狠戾时亦表现出女强人般的狠戾。后来成为香港商界的风云人物,将“不入流”且渐渐衰落的泉州南音引入香港上流社会,后致力于两岸的文化交流。
Marvy:介于女神与女神经病之间,恩静的好朋友。主业大小姐,副业私家侦探。表面高冷傲娇,其实有一副热心肠。口直心快,何秋霜经常被她损得全无颜面。因恩静而与花花公子连楷夫相识,高冷女遇上风流男,俨然一对欢喜冤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