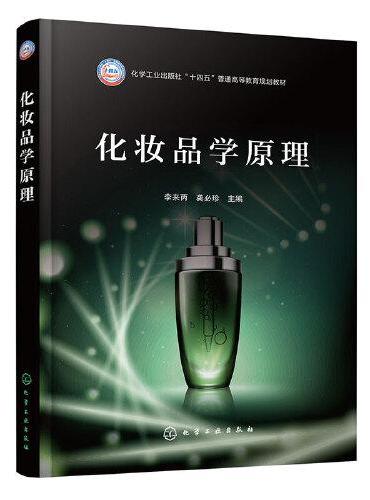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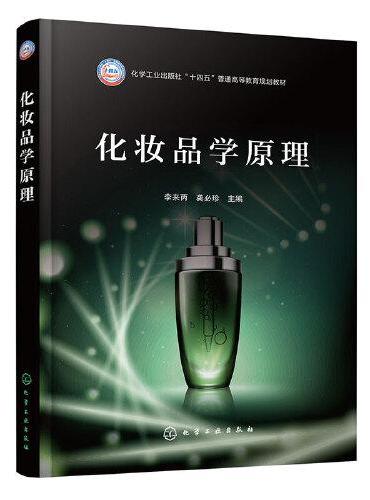
《
化妆品学原理
》
售價:NT$
254.0

《
万千教育学前·与幼儿一起解决问题:捕捉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教育契机
》
售價:NT$
214.0

《
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
》
售價:NT$
254.0

《
史铁生: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2)
》
售價:NT$
254.0

《
量子网络的构建与应用
》
售價:NT$
500.0

《
拍电影的热知识:126部影片里的创作技巧(全彩插图版)
》
售價:NT$
500.0

《
大唐名城:长安风华冠天下
》
售價:NT$
398.0

《
情绪传染(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
》
售價:NT$
403.0
|
| 編輯推薦: |
|
骆驼草,属落叶灌木。身躯并不高大,但根系发达,扎根极深,不怕风沙,不怕干旱,即使一年不下雨也不会枯死。在恶劣的环境中,骆驼草与大自然抗争,顽强地生长,以它不屈的意志滞止了风沙的流动。这正是我们这些病残作家自强不息的真实写照。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更是伤残人作家中的杰出人物,他们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如同顽强生长在茫茫沙漠中的骆驼草,彰显着生命的壮丽。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为《骆驼草丛书》之一。选录的四篇小说均节选自作者的四部长篇小说。《胡青云·郭玉川·钱晋生》,通过三个普通青年投身抗战洪流,反映出晋北人民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大无畏精神。《郑爱蓉·刘喜喜》,这是一个一夜之间变为下岗女工的厂长助理与一个刑满出狱后被聘为“保镖”的“流氓犯”的故事。《金瑞·小龙女·金宝蛋》,反映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残疾与健全、自强与堕落的挣扎与抗争。《方立伟和梁丽》,当农民企业家投身于全新的市场经济平台时,他们的道义、良知和情感将受到怎样的拷问?作者以其犀利的笔触和流畅的语言,为读者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芸芸众生的百态。
|
| 關於作者: |
|
曹利军,笔名寒黎,祖籍河北高阳,20世纪60年代末随父亲所在部队迁居山西忻州,8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500多万字。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曹利军中短篇小说选》(百花文艺出版社)、《曹利军作品精选》(华夏出版社),长篇散文《山·河·关》(三晋出版社),长篇小说《血祭忻口》(合著)(北岳文艺出版社)、《红尘手》(作家出版社)、《金太阳》(作家出版社)、《步天图》(作家出版社),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合著)(中央电视台)。曾获全国“德敏学习成才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协第五、第六届全委会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首届签约作家,《五台山》文学月刊主编。
|
| 目錄:
|
目 录
长篇小说节选
胡青云·郭玉川·钱晋生
1
郑爱蓉·刘喜喜 63
金瑞·小龙女·金宝蛋
163
方立伟和梁丽 250
|
| 內容試閱:
|
胡青云·郭玉川·钱晋生
1
胡青云手挽着一个青布小包袱,拐过街口,朝家里走去。胡家的宅院坐落在忻州顺城街,虽谈不上如何豪华,却也是青砖门楼、琉璃照壁,月亮门隔着前后两进大院,前院有花池,后院有苗圃。胡文庆老爷虽然有点钱,但他自知在忻州,自己的财力与郜、王、张、石、连、陈诸家大户相差甚远,量体裁衣,有这样一处宅子已经很不错了。
胡文庆老爷有一儿一女,一妻一妾,钱够花觉够睡。他这人不贪不占,不嫖不赌,日子过得四平八稳。倘若日本人不来,忻州不起战火,那么胡文庆老爷的日子还会四平八稳地过下去。
晋北一开战,忻州就像一口烧滚的油锅,而胡文庆老爷和二太太月娥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再也坐不住了。尤其是二太太月娥,成天价在胡老爷面前唠叨不休。胡老爷便找了一辆顺道去南怀化村的大车,要接他大老婆和女儿青云来,然后全家人到晋南去躲躲战祸。
这天上午,胡老爷有事要出门去,听到门环叩得啪啪响,开门一看,正是女儿青云,忙问道:
“你娘哩?”
“家里呗。”青云撅着嘴,一脸的不高兴,跨进门径自朝后院走。后院的西厢房是她的屋,她身上装着门上的钥匙。青云一年不来,西厢房的门就一年不开。
“青云,你来哩?你娘哩?”二太太月娥从正屋迎出来,满脸堆着笑。
“家里呗。”还是那句硬邦邦的话,说完后掏出钥匙开了门,自管自走了进去。
胡老爷见女儿来了,又从屁股后头跟回来,见女儿如此待月娥,就改了主意,折回正屋。他知道月娥脾气好,但还是象征性地责怪了女儿一句:
“这娃娃,随她娘,倔!”
这阵子不断有队伍打忻州街上往北开,风声也一天比一天紧。月娥的意思是赶紧锁门走人。月娥娘家是运城的,爹娘虽然不在世了,但还有个亲哥哥,这回可派上了用场。说实话,这年头躲灾避祸没个落脚的地方还真不行。
胡老爷起先对这事举棋不定,大老婆和青云还在乡下,绝不能撇下她娘儿俩不管。月娥催他:你叫她娘儿俩一齐走呀,都是一家人嘛!
于是有人赶着大车顺道来了南怀化,说老爷和二太太请青云母女进城,打算举家到晋南逃反。青云娘不走,她这人的脾气就像胡老爷说的,倔!早年她跟胡文庆老爷成亲的时候,胡老爷还是城内北大街一家绸布庄刚熬出徒的小伙计。后来胡老爷成了老爷,想纳妾,征求青云娘的意见。青云娘说:“能行!”可在胡老爷纳妾后又请青云母女搬到城里一起住,青云娘却咋也不肯,说在这老宅子上住惯了,街坊邻居处得好,进城孤闷。也不知是不是心里话。胡文庆老爷只好依着她,不过倒是常常回村去探望她们母女。
青云娘不走的道理有四:其一,她走了屋门就得上锁,这老宅子和屋里的东西谁来照料?还不叫人偷光了?其二,日本人到中国来,自然是想进城了,跑到这穷乡下干什么?其三,即使日本人来了,又能把她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婆子咋样?其四,就因为人上岁数了,哪还能经得住大老远的折腾,身子骨还不散了架?
青云娘不走,却非要青云走不可。她觉得兵荒马乱的留个十七八的大闺女在家,也实实叫人放心不下,而她也自知就凭自己这个土埋了半截子的人是保护不了青云的。万一青云有个三长两短她就是死也合不上眼了。
开始青云死活不肯走。她说娘要走俺就走,娘要不走俺就不走。娘说你得走,万一日本人要打这儿路过呢?谁知道这些外国兵匪是些甚东西?会干出些甚事来?青云说娘要这么说俺就更不能走了。娘开始劝,继而骂,最后便十分伤心地哭了。娘一哭青云就傻眼了,她很少见娘哭过。
走的时候青云给娘躹了个躬。这一躬躹得有些不大对头。多年来她与娘相依为命,娘疼她爱她自然也把她娇惯得不成样子,她在娘面前胡搅蛮缠向来连句正经话都没有。
青云坐在大车上,已经出村了,娘还在后头跟着。娘的三寸小脚踩在布满深深车辙的黄土道上,身子显得更加摇摇晃晃。青云发现娘的斜襟袄上有一疙瘩扣儿开着,便又一次跳下车来,给娘扣上。青云忽然觉得娘老了,娘刚刚哭过的脸更显得皮肉松弛。娘的白发也多了,根根银丝在早晨的太阳光下闪闪烁烁。青云不知自己走后娘的日子该怎么过,心里一酸,就给娘正儿八经地躹了一躬。
2
临走的那天青云早早就去敲邻院玉川哥家的大门。“谁呀?”玉川的嫂子在屋里间。青云说:“嫂子,俺是青云,想找玉川哥说句话。”
玉川边系扣子边从门里出来,两眼迷迷糊糊,好像还未完全从梦里醒来:“这一大早的叫俺,干啥?是不是想请俺进城看戏?”
“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青云生气了。
“好好,你说罢,俺听着。”
“这里快要打仗了,娘叫俺跟爹到晋南逃反去,这一走也不知啥时候能回来,麻烦你好生照顾俺娘,她一人在家俺说啥也不放心。”
玉川听青云这么一说,也变得严肃了,一本正经地说:
“青云你放心走吧,有俺在,保管伺候得你娘周周到到,等你回来,连一根头发丝儿都少不了。还有你家那头老母猪打今儿就由俺喂。你看咋着?”
“行!玉川哥,那俺就谢谢你了。”
“甚话,小小一块儿长大的。再说,婶婶待俺再好也不能了,照顾她老人家也是该的。”
青云是南怀化一带有名的标致姑娘,小伙子见了标致姑娘没有不喜欢的。玉川家与青云家紧邻。青云家无男丁,原来家里雇着个老长工,干些重体力活儿。老长工老得干不动了,回了家。已经生得膀阔腰圆的玉川在长工走了的那天早上跳进青云家院子,从屋檐下拿起扁担勾起大桶,到村口的大井上挑水,以后天天如此。青云娘儿俩的吃水就由玉川包了。青云娘也取消了再雇长工的打算。
大约过了半年的光景,有天早上,玉川将水倒进瓮里,正要走,被青云娘叫住了。返身进屋,从里面拿出几块大洋,要往玉川手里塞。
玉川一下子脸红了:“婶婶,俺给你家担水可不是为了挣工钱,反正俺家的水也是俺担,多担两担又累不煞人,多年的老邻居了,这不是给俺难看么?”
有一天青云跟玉川扯闲话,青云问:“玉川哥,你说你天天给俺家担水,到底图了啥?”
玉川说:“不图啥,就为见你一面。”
青云说:“那你不是吃了亏?”
玉川说:“吃啥亏,咱村人谁有俺这福气,能天天见你一面?实话告你,见你一面饭都吃得香着哩!你说到底谁占了便宜?”
青云说:“狗掀门帘儿,你也就是嘴好使。”
其实玉川远远不止见青云一面。他与青云家隔着一道土墙,墙那面是青云家的猪圈,墙这面是玉川家的柴垛。喂猪的活儿自然是由青云来干。因此,每天中午或晚上,只要听见墙那面的猪哼哼,玉川就迫不及待地跑出去,蹬上柴垛,跟青云搭话:
“嗬,这猪可是又见长,俺说的没错吧,连猪见了你都吃得香。看俺家那猪,就是天天见俺这张丑八怪嘴脸,才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
青云笑着说:“那你以后甭在墙头上露脸,免得连累俺家猪。”
玉川给青云家挑了两年水,村里自然有许多闲话,有一回他挑着水在街上走,道边的几个后生笑着问:“玉川,这一担又是给你老丈母娘挑的?”玉川立刻变了脸,抡起扁担就跟人家打起来。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见了血,玉川的脑门儿上鼓起一个大血包,鼻子也破了。
玉川的哥嫂觉得兄弟到了娶媳妇的年龄,便四处托人说媒,还请算卦的测八字,看命里婚姻动不动。玉川额头上鼓起大包的那天早上,哥哥玉山说:“兄弟,哥跟你掏掏心窝子。别看青云跟咱是邻居,你瞅瞅人家城里带花园的大宅子,再瞅瞅人家北大街、东大街上的大货铺,你的花花心准能收回去。”
嫂子正给玉川揉脑门上的大包。玉川龇牙咧嘴地说:“哥,你这可是把你兄弟看得扁了,俺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么?俺给人家担水,就是因为她家没男人,邻里街坊互相照料着有啥不对?再说,俺这水肯定白担不了。你不是老哭穷么?等俺娶媳妇的时候,婶子肯定会送你大大一笔钱,你信不信?”
玉川嘴上说对青云不存非分之想,要真不想那才怪哩!心里想想又不犯法。就在青云临进城的前三天,玉川听到邻院的猪哼哼,就急忙扒上墙头:
“青云,婶子在不在?”
“不在,咋啦?”
“告诉你,俺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啥来?”
“梦见娶媳妇哩,你没瞧见那场面,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花轿进了门,啧啧,你猜猜新媳妇是谁?”
“谁?”
“还有谁?你呗!”
“怪不得人家说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儿,敢情真有你这号人。”
“醒了以后俺又想,费那事干啥?把这堵墙往倒一推不就得了?”
“那你今晚再梦一回。真的,前天俺也做了个梦,没好意思跟你说。”
“梦见啥啦?”
“俺梦见你找了个讨饭的婆姨,脸黑黢黢的,到处都是皱纹儿。”
当着青云的面儿,玉川什么玩笑话都敢说,青云从来不恼。青云在村里是个很持重的姑娘,见了后生们从不多看一眼,唯独玉川例外,她也跟玉川哥开玩笑,往往把他噎得一愣一愣的。
关系处得这么好,可玉川还是搞不清青云到底爱不爱他。他这人耍笑惯了,没个正形儿,自然也猜不透青云的真实想法。有时觉得青云好像有那么点儿意思,有时又觉得青云只把他当好邻居、亲哥哥。说媒的人不断上他家来,玉川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娶媳妇的事看来是拖不久了。他决定改天正正经经地问问青云,虽说自己对这事不存非分之想,但问问也无妨,大不了和现在一样,又不会少块肉,买卖不成仁义在,他还要接着担水。
可是,就在玉川刚刚下定决心的时候,青云要随她爹到晋南了,临走还把娘托付给他。这事只能等青云以后回来再说了。他一想,正好能在这段日子里亲近亲近婶婶,说不定还真有戏呢!
3
青云娘没来,青云就把气撒在爹和姨娘月娥身上。青云骨子里对姨娘有一种仇视态度,不管爹和姨娘如何迁就于她都消除不了。胡文庆老爷是很疼青云的,再加上老觉得对不住青云母女,就越发看重她。胡老爷每次回村都要给青云带礼物,或是花布、头巾、辫绳、盒粉,或是瓦酥、蛋糕、冰糖、瓜子,每次都说是姨娘送的。青云也知道这是爹的,回回照收不误,心说谁叫你是俺爹。爹的东西不要白不要,收了心里照样还是恨恨的。她从不肯进城去,有时被逼不过,就去住一两天,姨娘总是笑脸相迎,问寒问暖,还亲自陪她看大戏,或者到茶馆听书。青云也不领情,她觉得姨娘这人有点假惺惺的。
这次青云来了以后,除了吃饭,就一个人在屋里待着。下午姨娘来了,进门见青云在炕上躺着,就小心翼翼地说;
“青云,姨娘想跟你说说话儿。”
青云只好从炕上坐起来:“说罢。”
“青云,你跟姨娘实话实说,是不是你娘不待见俺,才不肯来?”
“俺娘可没这么说,她可从来没说过你的不是。”青云说的是实情,不过,娘嘴上不说,谁也不能担保心里不这么想。
月娥叹了一口气说:“青云,姨娘跟你说心里话,俺也是穷人家长大的女儿,当初嫁给老爷的时候,俺就想好了,过门后要好好服侍老爷,服侍姐姐,俺咋也没想到姐姐说啥也不肯一起住。这几年俺和老爷在城里,却把你娘儿俩留在乡下,你以为俺心里好受么?俺心里愧得慌哩,欠了姐姐这么多也不知啥时候才能还。
“这世道你也看见了,都乱成啥了?前天日本人的飞机撂炸弹,在城东口炸死两个人,有人说太原也有日本人的飞机,俺前些时琢磨,咱全家一起到晋南俺哥家躲躲,俺也有机会好好服侍姐姐,让她也知道俺是个啥样儿人。可姐姐就是不来。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把姐姐一个人留在家里,俺就是走了,心也在这儿悬着。俺打算亲自回村去请她,她要不走,俺就在乡下陪她,要死咱一家就死在一块儿……”
月娥说着说着,哭了。
姨娘的一席话说到了青云心里,也把青云深深打动了。她下了炕,亲自倒了一杯水,送到姨娘跟前。姨娘接过杯子,又捉住青云的手,还是一个劲儿地哭。
青云消除了对姨娘的仇恨,自然也就原谅了爹,又知道爹和姨娘要到乡下去接娘,一家人一起走,心情就开朗了,活泼的天性也就显露出来。
青云心情好了就常到街外面走走。这阵子街上到处都是人,街边巷口小摊前,三五一伙儿七八一群,议论的全是眼下的战事,有说日本人厉害的,有说中央军厉害的,也有说红军厉害的,说红军个个都是神兵,飞檐走壁,打起枪来百发百中。街上人多了生意也火,生意火了就分外热闹,青云到现在自然觉不出打仗有什么不好。
第二天,青云见好多人都朝文庙的方向拥。她以为有啥好看的,一去才知,原来文庙的大操场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操场中间是部队士兵们扛着枪排成整齐的方阵队伍,队伍中有穿黄衣服的,有穿灰衣服的,有戴钢盔的,有戴布帽的。青云也分不清哪是中央军,哪是晋绥军。周围拥着老百姓,有人手中拿着小旗,有人手里扬着传单,青云活了十八岁从没见过今天这么多人,兴奋得脸都红了。
文庙大操场的最前边搭起一个大戏台,戏台很高,上边飘着五色彩带,台上坐着一排人,有穿军服戴大盖儿帽的,有穿中山装的,也有穿长袍马褂的。周围的老百姓指指点点,说部队的司令官、忻县县长、商会会长、中学和小学的校长都在。青云一个也不认得,上边的人开始轮着讲话,讲完了还有军队代表、学生代表、工商界的代表讲。
青云在文庙大操场站了足足两个时辰,她认真地听着每一位代表的讲话,有的代表含着热泪讲述,说外国人曾经怎样侮辱中国人,大红鼻子怎样殴打中国人,外国人的大门上挂着牌子,把中国人比做狗。一直讲到现在,她才知道“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的关头,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千千万万的同胞正在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会场上不时有人挥着小旗高呼口号:
“打倒日本!收复河山!”
“誓死不做亡国奴!”
“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辱!”
周围的人都跟着喊,青云便也跟着喊。她的眼里闪动着泪光,浑身热血沸腾。
中午回了家,青云在饭桌上把自己听到的跟爹和姨娘复述了一遍。搁下饭碗,又到文庙大操场去了,这几日不断有队伍开来,天天都有大会。
下午的会场更是激动人心,有个教师讲日本人侵犯东北犯下的罪行,好多人都哭了,青云自然也哭了。散会后,县长宣布成立“抗日决死队”。好多青壮年都当场报了名,大戏台上摆着一捆捆的长枪,青年人一报名,就能领到一支枪。会场上的气氛空前高涨。青云只恨自己是个女的,要不然她也会报名,到前线打日本去。
4
火车一开,小诸葛孔三捅捅身边坐着的郭二东,俩人便哈哈大笑,大伙儿便瞅瞅钱晋生,都哄堂大笑起来。
从石家庄出发的火车刚一启动,郭二东就说:“你们仔细听着,火车一过娘子关,声音就变成了‘老西!喝醋喝醋喝醋……’大伙就跟着乱笑一通,原以为郭二东胡说八道,没想到进了山西后,小火车开得慢,时不时还得爬坡,呼哧劲儿就大。见郭二东笑,一琢磨还真是这么回事,便再也忍俊不禁。再看看钱晋生那张脸,更笑得不可收拾。这当然不包括大鼻子刘杰柱,他是班长,大小是个领兵的,这种场合不起哄。
钱晋生靠着车帮半仰着,这是一节拉货的闷罐车,没座位,刚进来时黑咕隆咚的。一尺见方的小窗子在钱晋生对面,有整块的阳光从他的脸上移过,把他那张瘦脸映得愈发苍白。
钱晋生是一班唯一的一名山西兵,所以人们讽刺老西儿就把目光往他脸上移。法不责众,钱晋生心里干气就是没治,那张脸就变得古古怪怪,说不上是什么表情。
后来大家说笑够了就枕着膝盖打盹儿,小诸葛孔三手里又捧着那本没头没尾旧得发黄的破书,挺专心地看。由于光线太暗,他的脸几乎贴在书上。车厢里很宁静,有了火车单调的咣叽声就更显得宁静。
这时候钱晋生的脑子里又生出了开小差儿的念头。他认为自己刚才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足以说明他在大家心目中没什么地位,得不到尊重。既然他得不到尊重就不可能提班长,提不了班长就谈不上提排长,提不了官还当个什么兵,干脆当逃兵算了。
车厢里很闷,充满了浓厚的尿臊味和汗臭味,一股又一股直往鼻腔冲,越没事干越觉得冲。钱晋生站起来到对面去,踮着脚尖儿扒着小窗朝外看,视野里出现了一道道黄土沟地带,是那种沉沉浊浊的黄。有高低错落零零星星的庄稼地,也被一层厚密的黄土尘埃覆盖着,看不出一点儿生气。
这让钱晋生感到亲切。冀中大平原再辽阔再明朗也不是他的家。他喜欢站在这黄土崖头上朝远处瞭,瞭一瞭心里才真正觉得宽敞。
多年前他在村口的崖头上瞎瞭的时候,就瞭见了钱二疤。钱二疤用一根棍子挑着蓝布包裹,低着头在那条弯弯曲曲的土道上走着,步子迈得挺大,一看就像出远门的样子。
钱晋生急匆匆地跑下崖,紧走几步撵上钱二疤。
“二疤哥,你上哪去?”
“……”
“二疤哥,你说啥?”
“……”
“你到底说啥,没听见。”
“俺说×你娘!这回听见了吧。”
钱晋生愣住了,站下身子目送着钱二疤远去。那是一个干旱的夏季,太阳很毒,钱二疤的一双大脚板将道上尘土溅得飞飞扬扬,很快就看不见他的背影了。
本来这算不了什么,实实在在不算什么,只是因了某种独特的原因,钱二疤出村时大脚板扬起的尘土就一直在钱晋生的脑子里浮着,抹也抹不掉。
那天钱晋生回村后才明白钱二疤为什么要骂娘:钱二疤当了绿头乌龟。
“啥叫绿头乌龟?”他问村里人。
“就是他老婆养了汉。”
“啥叫养汉?”
“快滚吧,回家问你娘去。”
那时钱晋生十四五岁,真不明白。不过事情的经过倒是听得很清楚。那天前晌钱二疤正在地里干活儿,有几个人大老远气喘火燎地跑过来:
“二疤哥,俺疤嫂正跟男人睡觉哩!”
“放你娘屁。”二疤说,接着干他的活儿。
二疤嫂是村里有名的俊媳妇,女人长得标致就容易让男人动心思。见天有人跟二疤耍笑,说把疤嫂借俺用一夜。二疤以为又是闹着玩。
“二疤哥,真的,钱财主家的二心进了你家门,门都顶死了,俺们跳进院隔窗缝儿瞭见的。”
二疤撅起屁股往家跑。翻过土墙跳进院,将两扇门打得叭叭响。好半天老婆才开门,头发蓬乱,扣子还系错一个。二疤一个箭步冲进屋去,掀开被子,二心没顾上系裤子,两个屁股蛋子还露着。二疤抡起拳头就是一顿好打。二心跑了以后,二疤又揪住老婆头发拖倒在地,嘴里骂着婆娘,拳脚结结实实地往女人身上招呼,外面聚了半院人看热闹,也没人进来拉。
正当二疤打得十分兴致的时候,二心带着自家两三个护院家丁冲进来。这一回又是家丁将二疤拖倒在地,两个压着二疤的头和脚,一个握着湿荆条拧成的短鞭,冲着二疤的屁股狠狠揍了三五十下,打得二疤屎尿流了一裤裆。家丁说:“好臭。”这才走了。
钱二疤这件轰动了全村的事对钱晋生起到了开发智力的积极作用,使他初懂了男女之情。钱晋生开始注意彩花,并且生出了抱抱彩花亲亲彩花的想法。
彩花小时候裤子老是提不起来,前胸和两袖有大块亮亮的鼻涕痂,动不动就哭。村东头的男娃娃们老是欺负她。那时候钱晋生活得挺好,私塾的周先生看他聪明,免费让他听课。他在下学的路口老是见彩花哭,还见男娃娃们朝她脱裤子,朝她掷土坷垃。他每次见了都呵斥那些男娃娃,有一回还跑上去将一个领头的踢了两脚。
彩花长大后也许还记得小时候的事。见了他总要问:“晋生哥吃啦?”挺热情,倒是他变得唯唯诺诺,不那么爽快。
钱晋生开始注意彩花后就变着法子接近彩花。起先他掏了两只小家雀儿给彩花送去。彩花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两手捧着小家雀儿惊喜地看。小家雀儿身上还没长全毛,嫩黄嘴岔儿,张着大嘴唧唧叫。彩花家里没男孩,她是头一回捧住家雀儿,就张罗着在盒子里垫上棉花和碎布条儿,又忙着喂水喂米,丢了孩子的大家雀儿不知咋就知道了,在彩花家门前的枣树上喳喳喳可着劲地叫。
“怪可怜的。”彩花说,就把小家雀儿放到院子里。大家雀儿围着小家雀儿团团转,喳喳直叫就是没办法。后来彩花把盒子摆在窗台上,大家雀儿就飞来飞去喂食,彩花在窗台上撒满了高粱和小米。后来小家雀儿飞走了大家雀儿还是天天来,常常落在彩花肩膀上或手心里,村里都好奇,真日怪,家雀儿还能喂熟哩!
那时候钱晋生总是借口看小家雀儿去看彩花,小家雀儿飞走了他又到河里捞了几条鱼。彩花放在家里的水瓮里养着,他又借着看鱼去看彩花。总之他有的是办法。
钱晋生在小窗口扒累了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将车底板上的稻草往起拢了拢,重新坐下。他又闻到了尿臊味儿和汗臭味儿,又听到了火车咣叽咣叽的声音,又想起了“老西喝醋喝醋”,从而也又一次坚定了逃跑的念头。
钱晋生究竟当了几回逃兵他自己也没细数,反正是当一回逃一回。刚开始他心存侥幸,觉得有一天兴许能碰上钱二疤。后来世面见大了,他才知道中国敢情大得很,光部队就有上百万,找二疤就如同大海捞针。他当兵唯一的念头就是想提官,觉得没啥前途就逃,然后长途跋涉随便找支队伍再当。他逃跑没有一回叫抓住过。他有个诀窍,不论兵是叫人家抓的还是自己去的,都要表一番决心,说部队上有吃有喝有穿,他大老远出来就为当兵。所有的人都会对他放松警惕,别人不会想到一个兵瘾如此之大的人会逃。这些年他究竟参加过哪些队伍?说不来。
不过钱晋生这些年的兵算没白当。身体练得挺结实,手榴弹投得远,枪法也练得极准。他读过两年私塾,算有文化,说不定哪天就等来了升官的机会。
5
有一年钱二疤回家来了。村里人大呼小叫,南街北巷到处都是急促的脚步声。据说是钱二疤带了整连的兵将钱财主家的大院围了个水泄不通。钱晋生赶到钱财主家大院时兵已经撤了。据说是奔了村东口。
村东口有棵老槐树,究竟有多老谁也说不清。逢了村里有什么大事,长老们就在这棵树下召集人。这是一个即将日落的傍晚,西山顶上的太阳把天上的云彩照得火似的红。二疤婆姨、二心还有二心的爹娘兄嫂十几口人都被五花大绑捆着,在树前跪了一长溜,当年殴打钱二疤的三个家丁跪在最前面,周围站满了整排的端着长枪的士兵。
钱二疤骑着一匹雪白的高头大马,戴着大盖儿帽穿着新军服,衣扣儿、皮带、长靴到处都熠熠放光,人也显得威武多了。
“把这对狗男女给老子吊起来!”
钱二疤一声令下,过去四个士兵,将长绳往树杈上一甩,哧溜一声便将二心和二疤婆姨吊到半空中。钱二疤用手里的马鞭指着那三个家丁:
“当年你等狗仗人势,心狠手辣,老天长眼,老子今儿个报答你们来了。来呀,给我乱棍打死!”
士兵们不知从谁家拿来两柄镢头,大头朝前,一顿横敲猛砸,只听一阵哭爹喊妈的惨叫,不消一刻,三个家丁便被打得筋断骨折,脑浆迸裂。
钱二疤又用马鞭指着钱二心:
“钱二心你个狗娘养的,当年你给老子戴绿帽子,老子今儿就给你戴顶红帽子,给我狠狠打!”
这一回士兵拿上来的是一条长鞭,伸到水桶里蘸湿了,也不知这东西是什么做的,一鞭抽下来就将钱二心的衣襟拽下了一大块,跟着鞭梢儿就全部集中在钱二心的头顶上。钱二心一边尖声惨叫,一边喊:
“二疤哥,二疤爷爷,你饶了俺吧,俺再也不敢了。”
“老子好好的日子叫你搅黄了,我饶你天不饶!”二疤恶狠狠地说。
鞭子把二心的头发连头皮都扯了下来,二心的脑袋说啥也看不成脑袋了,变成了血红的肉葫芦。胆子小的人们扭过头去不敢再看。二心也早被打得昏死过去。兵们又将一桶水用力泼在二心头上,二心头上的血水淋得满地都是。
钱二疤从马上下来,朝前走了两步,又指着自己的婆姨破口大骂:
“你这个臭婆姨,老子哪点儿对不住你,天生的婊子,你还有什么话说。”
二疤婆姨在树上吊着时间长了,满脸都是汗,强撑着说:
“当家的,你走了俺也思前想后琢磨过,都怨俺初时心意不定,叫他软磨硬缠绊住了,可惜人不能活第二回,俺后悔也晚了。当家的随你怎么处置,俺都没说的。”
钱二疤听了这话火气就不像刚才大了,放慢了语气说:
“这还叫个人话,凭你这几句话,免了你皮肉之苦。来呀,执行!”
当兵的扛过一挺机枪,架在地上,“突突突……”一阵猛射,把二疤婆姨和二心浑身打得跟马蜂窝似的。二心娘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昏死过去了。二心爹也吓得打开了摆子,就像二疤当年似的屎尿流了一裤裆。他一边叩头一边颤声说:
“看在俺一把年纪的分上,饶了俺吧,饶了俺的家人吧!”
钱二疤又朝前走了两步,十分宽容地说:
“你身为人父,虽有养子不教之过,可也罪不至死,给你个小小的惩戒也就算了。”说罢朝围观的众人一抱拳:“各位父老,今后有什么事用得着钱某,打个招呼,我一定尽力而为。”
钱晋生一眼不眨地看着钱二疤回村演出的这场复仇剧,直到钱二疤翻身上马带着队伍扬长而去。此后的一段时间特别是他当兵以后,每当回顾这一幕时他都感到无比激动。
钱晋生第一次抱彩花亲彩花就是在这之后不久。有一天他跑去找彩花,说他掏到一窝小松鼠。
“在哪儿,快叫俺看看!”彩花果然一脸惊喜的样子,急不可待地瞧着他。
“林西头树林里,有好几只呢!”
于是他就领着彩花进了小树林,东看看西找找,越走林子越深。
“在哪儿?”
“就在这儿。”
彩花蹲下身,凑近一个树根的洞猫了腰,钱晋生看看前后无人,便扑上去从后面拦腰抱住彩花。彩花的身子抖了一下,在回过头来的时候他就结结实实亲了彩花嘴一下。
彩花恼了,挣脱他的胳膊,扭头就走。
“彩花,彩花。”他跟在彩花身后,不住地唤。
“别叫俺,以后你再不要来,你不是个好东西。”
“谁说俺不是个好东西?”
“你就不是个东西,你干坏事就不是个好东西。”
晚上回了家钱晋生在炕上翻折了一夜,眼都没合。彩花身上的那种撩人的香味儿使他意乱,彩花怒气冲冲的话语又让他心烦。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便跑去找继哥,继哥是他无话不说的朋友。继哥听完后说,怨你,都怨你。
“干偷鸡摸狗的事人家能不骂你灰人?回去叫你爹备上礼提亲去!”继哥最后说。
晌午吃饭的时候钱晋生就把这事吞吞吐吐地跟爹说了。
“什么,叫俺去跟彩花爹提亲?”爹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
“嗯爹。”
“呸!”爹将一口唾沫包括一些饭食的残渣吐到地上。
“你把你自个儿当成啥人了?你以为你是财东家少爷?你瞅瞅咱家,破衣烂柜,有一件囫囵东西没有?你再瞅瞅咱吃的这饭,连人家彩花家的狗食都不如。人家那么俊的闺女,多少达官贵人都眼巴巴瞅着哩!就凭你,睡着梦梦就得了!俺见了人家彩花爹还得绕道走哩!”
人穷了火气反而大,爹的这一通连珠炮似的数落挖得钱晋生骨头根子都疼,把他刚刚鼓起来的一点希望泄得一干二净。
这之后钱晋生又过了一段十分痛苦而又孤独的日子,直到他有一天打麦场跟前路过。那时天马上就要黑了,他看见彩花和一个男人从麦垛后边转出来。彩花在前,那个男人在后。他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彩花低头走路的样子就跟那次从树林里走出来时一模一样,不过不如那一回走得快。那个男人在后边紧跟着,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
钱晋生看得清清楚楚,那个男人是钱三冬。
此后钱晋生便十分坚定地认为钱三冬霸占了他的老婆。他对钱三冬和彩花在麦垛后面的情景做了至少几十种设想,每次都有万箭穿心的感觉。于是他便想起了钱二疤在那个干旱的夏季出走的情景。他觉得钱二疤的两只大脚拍在黄尘土道上十分气派,充满了天地间的一种豪壮之气。他决定去找二疤哥,有朝一日也能骑着高头大马回来,把钱三冬吊在树上用机枪打成马蜂窝。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那个情景。不过他可没把彩花算在内,彩花毕竟是个女孩子,很可能会哭,到时候他就会把彩花抱在怀里,给她擦眼泪,然后娶她做婆姨。
钱晋生同样用棍子挑了包袱,沿着当年钱二疤出村的路朝村外走。这个夏季同样显得十分干燥,不过并没有一个半大男孩儿从光秃的崖头朝他跑来……
6
本来胡文庆老爷打算带着青云跟月娥一起回南怀化接青云娘的。最初月娥表示要一个人去,说啥也要将姐姐说动。可胡文庆老爷知道自己大老婆的脾气,这人一旦绷住哪根筋,恐怕是九头牛也拉不转。再说,青云娘对月娥并不一定有好感,她又怕月娥一个人去了,非但劝不了青云娘,反而热脸贴个凉屁股,碰上一鼻子灰,逃反不成,倒弄得一家人都不痛快。他想有他和青云就好说话,再不行就是抬也要把她抬来。
事情一加上胡文庆老爷,就变得复杂起来了。这几天胡老爷的身子说啥也腾不干净,自己要走了,这忻州还不知守住守不住,哪个店该关,哪个店不该关,留哪位人守摊子合适,哪些货可以让出去,哪些货可以转运走,哪些货留下,还有百十家“相与”(即有业务关系的商户彼此也该清算一下,货货相抵,多退少补。杂七杂八的事等了结了,十来天也就过去了。
说起来也是胡文庆老爷有些大意。本来他是打算马上就走的,可人在忻州城里,就有了一种“当局者迷”的味道。忻州街上接连不断有军队过,整师整团地往上开。胡文庆老爷心想,咱有这么多队伍,哪能一下子就输了?心里踏实了,事情就办得稍嫌琐碎。
这天下午胡文庆老爷和女儿青云来到斜对面卫立煌指挥所,对守门的卫兵说:“麻烦你通传卫将军一声,就说住在街对面的商民胡文庆特来拜访。”
卫兵走了不大一会儿,回来说:
“进去吧,卫总指挥等您呢!”
卫立煌在屋外的台阶下站着,见了胡文庆,十分热情地抱拳行了个百姓礼,又一眼看到了身后跟着的青云:
“欢迎,欢迎!噢,这位小姐原来是令千金……”
“正是小女,青云,见过卫将军。”
“晚辈青云见过卫将军,卫将军辛苦了!”青云上前给卫将军行了个礼。
“胡先生真好福气呀,有这么个聪明伶俐的女儿。”
“乡下孩子,不懂事。”胡文庆老爷十分谦逊地说,又与卫立煌礼让一番,才进了屋。
胡文庆老爷和青云对卫立煌来说都不算生人了。卫立煌的指挥部刚刚搬到顺城街这座宅院的时候,战局未开,忙虽忙但却是另一种忙法。他在街口门前总能遇上青云或胡文庆。他虽然不认识他们可人家都认识他,见了都先招呼,道一声辛苦。他从胡文庆的穿着打扮上,便看出这不是位普通人。有一天他在胡文庆向他招呼的时候就站住闲聊了几句,知道他姓胡,就在斜对面住着,在忻州也算是稍有名气的富商。
胡文庆老爷受到卫立煌的热情接待,立时感觉还真有点过意不去。他坐在椅子上,咳嗽了一声,说:
“卫将军身负党国重任,日理万机,我看还是开门见山地说。说起来惭愧,我打算明天启程,携家去运城了。你们为了国家冲锋陷阵,而我等却苟且偷生,相比之下,实在令人汗颜。”
卫立煌马上摆摆手,笑着说:
“胡先生言重了。我在多种场合说过,希望乡亲父老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我们军人的职责最终还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兄弟姐妹嘛!”
胡文庆老爷笑笑:“我老了,不中用了,今天带了一份薄礼,也算我这个平头百姓对抗日尽的一点心力。”
青云将手里的一个包裹放在桌案上,打开,里面是红纸裹着的大洋,五十块一棒,一共十棒。
“本来我已随商会给咱军队捐了一点钱,这两天一想,国破何以有家,还想再尽一份心。这点钱,还有门外的几箱货物,恳请卫将军笑纳。”
卫立煌朝门外一看,几个小伙计和士兵正从大车上往下卸货,箱口上贴着红纸封条,也不知是什么东西,足足有十几大箱。
卫立煌深受感动,再次抱了抱拳:
“我代表前线将士谢谢先生了。真想不到,忻州的父老乡亲抗日热情这么高,这么有觉悟。”
“按理我应该把东西送到商会去的。也怪我腿懒,图省事,就近送来了。卫将军心系国家安危,为这点小事打搅您,真觉得过意不去。”胡文庆老爷起身告辞,在屋门口,胡文庆老爷拦住卫立煌,说啥也不让卫将军送了。
出了指挥部的大门,青云说:“爹,俺还想上街转转,到文庙看看,那儿可红火呢!”
胡文庆老爷说:“快回家吧,收拾收拾明天还动身呢,这两天可把你转疯了,日本人的飞机说来就来,到处扔炸弹,爹怕你出事。”
青云说:“爹,瞧您说的,日本人的炸弹哪有那么准,正好能扔到您闺女头上?您放心吧,俺一会儿就回,啊?”
“这孩子。”胡文庆老爷背着手,自管自回家去了。
青云在街口买了一支棍棍儿糖,含在嘴里,又称了几斤核桃,用刚才包钱的那个包袱皮包了,挎在胳膊上朝文庙的方向走。她这些核桃是准备送给上前线打仗的士兵的。青云看到每次动员大会开完后,队伍朝北走,道两边的乡亲们都手里提着篮子什么的,里面有盛着红枣的,有盛鸡蛋的,也有盛苹果梨的,用手抓着往士兵们口袋里塞,那场面特别感动人。尤其是看见有些老太太,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穿成那样了还舍得从家往外拿东西。她也应该这么做。
青云赶到文庙大操场上的时候,大会正进行到了高潮,人们举着拳头或小旗呼口号,每喊一句,操场上就有无数的胳膊伸起来,就像生出一大片茂密的林子。她挤进人堆儿里,引颈翘首朝前观望,想看看下一个由谁来讲话,她特别爱听台上的人讲话,他们说的都是她这辈子从未听到过的新鲜事。
就在这时,天空又响起了嗡嗡的怪叫,眨眼间,三架日本飞机出现在顶空,好像天空被什么东西撕裂了,声音尖厉刺耳。戏台上的扬着胳膊张大嘴喊着什么,声音被刺耳的飞机声音压住了,根本听不见。操场中的军队开始蠕动,周围的老百姓四散奔逃。有炸弹在什么地方爆炸,轰轰轰轰的声音分外沉重。青云被挟裹在人群里,左突右撞,身不由己,她的一只鞋子被人踩掉了,肘上挎着的包袱也散了,她在炸弹爆炸的间隙里还清晰地听到自己包袱里的核桃啪啪落地的坚硬的声响。
此时,青云感到,她自身所处的正是一个灾难的漩涡。
然而当时,她根本不知道,这个灾难的漩涡并不在她置身的文庙大操场,而是在自己家里。
对于青云来说,日本人可真够毒的,日本飞机的炸弹扔得可真够准的,那颗炸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胡家二进院正房第二间的屋顶上,将房顶炸塌了。
而且,她爹、她姨娘,还有她那个没学会说话的弟弟,偏偏就在这间屋子里。
爹、姨娘,还有小弟弟的尸身停在当院里,头上蒙了被子,青云伏在爹的身上放声痛哭。指挥部的士兵们正在清理瓦砾下的东西,卫立煌将军也在,胡老爷店铺里的黄掌柜、王掌柜也在。黄掌柜见青云哭得死去活来,就上去扶起她。青云偎在黄掌柜怀里,依然痛哭不止。
卫立煌将军默默地伫立着,刚刚才把五百块大洋交到他手里的胡文庆,不到一盏茶的工夫就离开了人世。他无法表达自己沉痛的心情,也找不出适当的话来安慰青云。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在青云要掀开被子看一眼爹的时候,才去劝道:
“青云,别看了,都不成样子了,你看了会害怕的。”
青云的手提着被角,抬起头看着卫将军,说:
“他成啥样都是俺爹,俺不怕!”
7
南怀化位于四十里金山北端的一道深沟里,北面云中河,东距公路七八里。当初,包括青云娘在内的许多村民都认为,这个掩藏在沟谷中的偏僻村庄肯定是个逃避战祸的安全所在,大多数人对玉川哥哥玉山等人逃跑置之一笑。外面一些村子的人没有远方亲友的,也都来到这里投亲靠友。因此南怀化反倒比平时多出了许多人。老百姓们哪里知道,因为从这条沟往上冲是占领忻口中央地区高地的最理想的途径,南怀化就成了一处兵家必争之地。
直到战火蔓延到了村边,村人们才幡然猛醒。
这天上午,玉川将青云家的大门推开一条缝儿,伸进手来,摘下了扣在门环上的链钩。他直奔正房,将门敲得啪啪乱响:
“婶子,在屋里做啥哩?快逃哇!没听见村北打得正紧么?”
此刻青云娘还在被窝里躺着。青云娘有早起的习惯,平日里早就起来屋里屋外地忙乎开了。青云娘人虽老了可耳朵不聋,村北的枪声噼里啪啦打得爆玉米颗子一般,“砍呀杀呀”的叫喊声一阵紧似一阵,还有大炮声,亦是不歇不住地响,将窗棂都震得嗡嗡乱颤,顶幔上簌簌地直往下掉土,即使聋子都得叫再震聋一回,别说青云娘了。
即使青云娘起来也无事可做,仗都打成这样儿了,心提在喉咙口上,哪还有心思干家务。倒不如索性在被窝里躺着,用被蒙住头,外面的响动声还小一些。因此玉川敲门时青云娘最初没听见。
门开了,玉川见青云娘头发蓬乱,一脸倦容,眼角处还趴着两颗不大不小的眼屎,就跺着脚,十分惶急地说:
“好俺的婶子哩,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睡觉,快逃哇!俺在外面看见北边有溃兵下来了,再不逃就晚啦!”
“逃?往哪儿逃?”青云娘的表情木木的。
“出了村再说呀,哪儿也比待在家里强。”
“俺一个土埋了半截子的人,日本人又能把俺咋样,莫非他们还要把中国人都杀光?要逃你快逃,别为俺连累了你。”
玉川又攥了攥拳,跺了跺脚:
“婶子您这叫啥话,咱们可是紧邻,俺生在穷家,打小就受您家的接济……不说啦,来,俺背您!”
俩人正在屋里纠缠着,街上就有纷沓的脚步声响起,接着又听到了战马的嘶叫,后来就有人大声喊:
“老乡快藏起来呀!前边顶不住啦!”
用玉川的话说,青云娘真格就像跟上鬼了,命里就逃不脱。青云娘没走两三步,就在台阶上摔了跤。青云娘坐在台阶下,将一只小脚揽在怀里,两手握着,龇牙咧嘴地喊:
“哎哟哟!哎哟哟!”
“看看,俺说背您吧您不让,摔着了不是?来,抓住俺的手。”玉川又伏下身来,掉头望着青云娘。
“不行啦,俺的脚脖子崴啦,你快走哇,哎哟哟!”
“那哪能哩!青云走时把您交代给俺了,她日后回来叫俺咋向她交代。”玉川一着急,也就把实话说出了。
这时候,街外的枪声噼噼啪啪地响得更紧,让人辨不清究竟是哪个方向,整个村子都让密集的枪声覆盖了。玉川紧跑几步,拉开大门朝外一望,又马上掩紧门,踅了回来,面如土灰:
“好啦,这下可放心啦!日本人已经进村啦。”
玉川将青云娘扶回屋里,上了炕。俩人便再也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青云娘一边揉着小脚,一边说:
“你咋说日本人来了?大门外不还在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