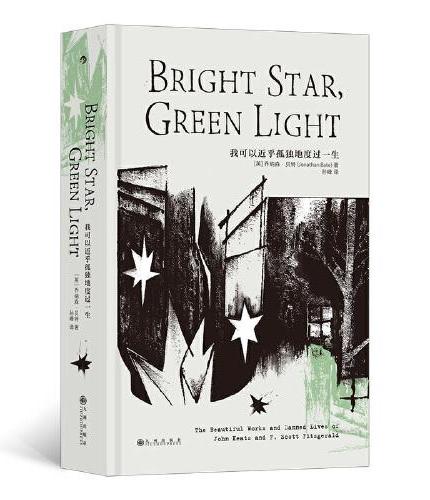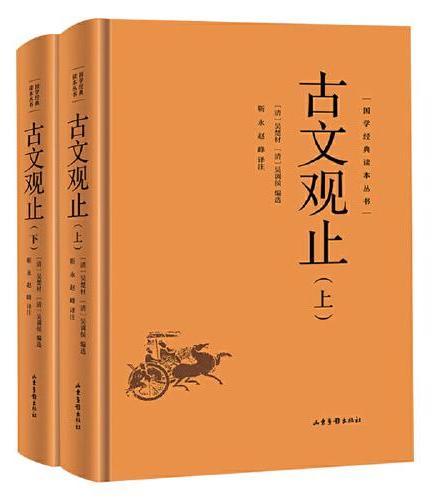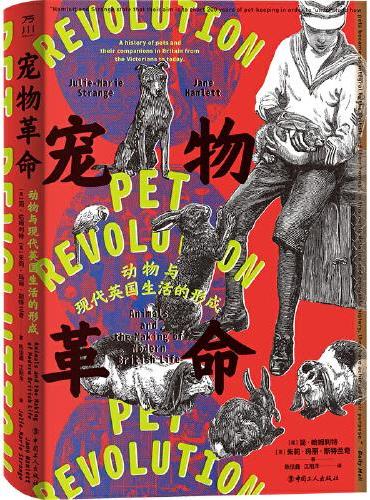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量价关系——透视股票涨跌脉络
》
售價:NT$
340.0
![创伤与记忆:身体体验疗法如何重塑创伤记忆 [美]彼得·莱文](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46645.jpg)
《
创伤与记忆:身体体验疗法如何重塑创伤记忆 [美]彼得·莱文
》
售價:NT$
295.0

《
复原力
》
售價:NT$
345.0

《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演变(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9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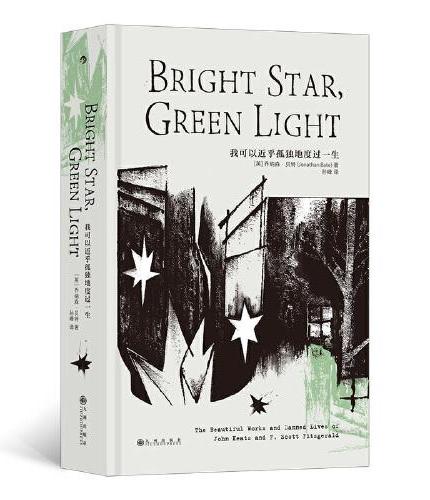
《
我可以近乎孤独地度过一生
》
售價:NT$
440.0

《
二十四节气生活美学
》
售價:NT$
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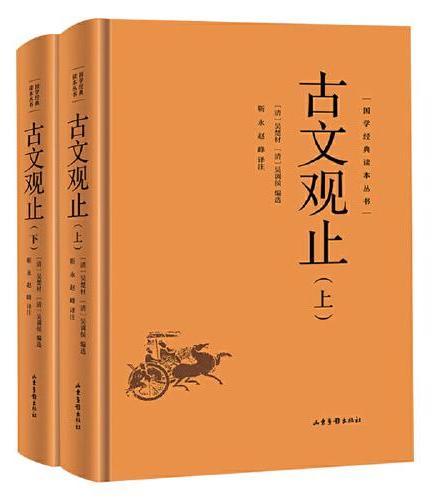
《
古文观止(上+下)(2册)高中生初中生阅读 国学经典丛书原文+注释+译文古诗词大全集名家精译青少年启蒙经典读本无障碍阅读精装中国古代著名文学书籍国学经典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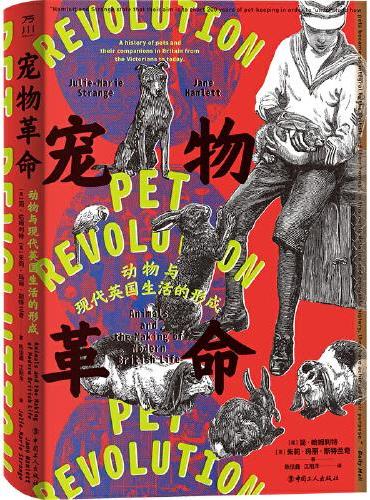
《
宠物革命:动物与现代英国生活的形成
》
售價:NT$
360.0
|
| 編輯推薦: |
1.这是一部让人读后心情无法平复的作品,真实残酷而又无能为力,时时只想无声的呐喊。在生存的面前对于亲情、对于爱情都成为一种残忍痛到骨髓的苦难,生命只能撕成令人厌恶的碎片无奈的继续生存。
2.《碎片儿》对人类生存、生命的探索,仿佛把人的灵魂放到时代的手术台上一刀一刀地解剖,这就难免看到残忍、流血、挣扎!但正因为勇于解剖才更知人类世界爱与善念的珍贵!人类自身的伦理道德至关重要。
|
| 內容簡介: |
|
歌德说:“在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时,看到的是宛若一个破碎物件的许多碎片……”一个不向现实妥协的女人,将自己少女时代被扭曲的灵魂,强为人妻时被玷污的情感撕成碎片,向世人撒开……带血的记忆,把一个女人的苦难、倔强、自尊、奋进、敏感、野性、泼辣写到了极致!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励志范本和超越自我的生命体验。
|
| 關於作者: |
陈亚珍,女,1959年生,山西昔阳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副主席、晋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二级编剧。
著有长篇小说《碎片儿》《神灯》《十七条皱纹》《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长篇纪实文学《陈荣桂与陈永贵》《谁在守约》、散文集《玫瑰:撒下一地殷红》、电视剧本《苦情》《路情》及中短篇小说若干。其中,《碎片儿》《神灯》分获北方地区优秀图书一、二等奖。《十七条皱纹》由作家出版社、台湾秀咸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版发行,并获第二届赵树理文学奖。《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获2012年中国小说学会上榜图书,2013年被全国图书推荐委员会推荐为200本好图书之一,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晋中市第三届优秀长篇小说奖。散文入选多种选本,其中《我想对你说》入选《2004年我最喜爱的散文100篇》和《致爱人》。《苦情》《路情》分获第六、第八届华北地区电视剧三等奖,《唢呐魂》获全国第一届音乐电视剧“灵芝奖”二等奖,《地委书记》(合作)、《土岭纪事》(合作)等均获省市级奖项。
|
| 目錄:
|
引言01
上卷
第一部消失在黄昏13
第二部哭泣的山梁52
第三部淌血的心灵121
下卷
第一部叩响命运之门186
第二部灵与肉的厮杀222
第三部沉重的翅膀267
|
| 內容試閱:
|
第一部消失在黄昏
一
女人,苦难的象征!这是千古遗传。
从我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就带着深深的悲剧意识来到了人间。
人都说,结婚要选良辰吉日,我却说,一个人诞生才最该择个吉日良辰,而我没选,父母也欠责任感,于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我出生在钢铁世界,这年月有人极精辟地总结了三个字叫“大跃进”。
据说父亲当时是沪平城的县长,母亲是服装厂的车间主任。一对夫妻,两个党员。在那个时代,群众“小跃”,党员就得“大跃”;群众“大跃”,党员就得“特跃”。“跃”来“跃”去,“跃”得不食人间烟火了,连普通父母的感情都给“跃”没了。
就在这“感情枯竭”的时刻,我不知怎么就鬼鬼祟祟地“跃”进母亲的肚子里和她同“跃”。据母亲口述,怀我的时候九个月不能吃饭,吃一点吐两点,吐不出饭来就吐血,这就极严重地影响着大跃进。父亲于是烦乱、焦躁,大发雷霆,且极“刻毒”地要母亲去流产,想让那个不识时务的小家伙以光的速度,“跃”罢这一生。
然而,我自岿然不动。我想,这能怪我吗?你们一夜合欢将我造就,要我堕地没那便宜事!
母亲大概也做了自我批评,因自己一时不慎让一个生命灭绝是不公平的,于是擅自将我隐藏在肚里,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在大跃进里顽强地“跃”。
然而,终于有一天我不能不检举母亲了。我不甘于在阴暗的肚子里隐姓埋名,日日受屈,于是便抗拒一切嫌弃因素死皮赖脸地挤进了这个世界。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母亲正准备一天的劳作,却突然感到肚子不对劲儿了。撕心裂肺的疼痛使她滚作一团,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一声接一声地呻吟冲出院外,凄厉可怖。三岁的姐姐瞪着恐惧的眼睛盯着母亲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孔,哇地哭了。
母亲攥着姐姐冰凉的小手断断续续地说:“快,去政府……让叔给你爸打电话……回来……”
姐姐挣脱母亲的手躲在一边,死也听不懂母亲的话。
母亲曾经是怎样的美艳绝伦,庄重典雅而有韵味。母亲眉目清秀,双瞳剪水,淡雅中透着高贵。母亲从来是非常的沉静,任何意外的事都不会破坏她的仪态。可此时的母亲,丑陋不堪,面目憔悴苍白,睁大无神的眼睛蓬松着乱发呼叫着、呐喊着,向尚未明事的姐姐发号施令。可姐姐不依,姐姐不允许她的母亲如此的面目狰狞,她不想看到母亲扭曲变形的五官,她要她以前的母亲。
她不明白是谁把她的母亲搞成这个样子。她贴着墙抽泣着。
巨大的阵痛使母亲陷入昏迷,在沉沦中挣扎。她的脑海里一片火海。她看到父亲矫健的身影漫山遍野地奔跑着,指挥着千军万马大炼钢铁,那一个个炉膛燃烧着,如同夜晚的一簇簇篝火。父亲戴着褪色的草帽,满脸灰渣出入在其间。父亲的英雄气概倾倒了多少人,多少双目光在仰望着他。母亲笑了。她要的就是这种气概,她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品格。牺牲是光荣的!创造生命的欢乐是他们共同的,而分娩时的痛苦只能由母亲一个人来承受,但母亲面对苦难微笑着,这个看上去凄美绝艳的美妇人毫无怨言,坚强无比。
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母亲从昏冥中醒来,扶着炕沿站起来,挺着硕大的肚子,艰难地拉开门,拖着尚未走稳的姐姐朝人类诞生的地方蹒跚而去。
母亲躺在产床上无数次被我折磨得窒息。不甘寂寞的我,曾经急不可耐地想闯出来见见世面,可产床前没有助产士,白色的产房一片冷清,没有人迎接我。没有人昭示生命诞生的伟大与庄严,只有姐姐在一旁无可奈何地哭泣,言明我是不受欢迎的角色。
我站在母亲温湿的子宫口,放声疾呼——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然而,就在母亲爬上产床的那一刻,炼钢场上下来一个重伤员,助产士被人喊了去。本来就不大的医院,全民总动员抢救伤员,这是头等大事,任何看病者都必须暂停诊断,何况是一个产妇?
我知道母亲不会为自己去抢夺大夫,她会忍耐着,无期限地等待,只要她的生命还许可!这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格。
可我不能等待,无论这世界发生了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挡不住一个顽强生命的诞生。
我——庄严诞生了!
就在母亲拼此一生的呼叫中,从产房外慌慌地跑进来一个大夫,奇丑无比,舞弄着他全部的能量和医术,诱惑着我从母亲的子宫口哗然而出。他的围裙上溅出一朵火红的木棉花样,为他珍惜生命做了个永恒的标记。
很对不起,面对火红的大跃进母亲却不能“跃”了。父亲也受到干扰,于是,一张钢铁般冷酷的脸出现在母亲面前。母亲面对这种冷酷极温和地笑了,然后说道:“还是生了好,昨晚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天上的月牙儿掉在咱家的门槛下,门外盛开了一片桃花,很鲜艳。那月牙儿叽里咕噜地在桃花下滚动,她就生了……”
父亲重重地回说:“那是迷信。”转身到襁褓室里抱出我来说:“奶妈已经问好,还是及早奶出去吧!省得有了感情又……”
妈妈,可惜我当时不会说话,假如我会说就一定要问问,难道在那个时代出生的孩子就不该跟父母建立感情了?难道人也该变成钢铁吗?然而不管该建不该建,反正不能建!我不知道容没容得母亲看我一眼,就被父亲残忍地交给一个农妇乳养。天晓得,与我生命休戚相关的居然有三位母亲。如此看来,我一脱娘胎就面临着复杂的感情世界,而我认识的第一个母亲,便是这个农妇,我管她叫奶妈。
二
奶妈个子不高,“解放脚”。她的整个面目像庙里的菩萨,奶妈很实在也很善良。
可我却是少有的自私刻毒。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换一个环境并不曾感到陌生,换一个女人的怀抱也没什么痛苦可言。我想,我来这个世界就是要大“跃”一番的。许是因了分秒必争的胎教之缘,造就了我的不安分?那时候我没有别的本事,唯一的本事就是吃!
奶妈说我食量很大,大得无法无天。当时吃的是地道的大锅饭,一村人合用一口锅,名曰集体食堂,说这叫共产主义。一孔破旧的窑洞前排了长长的一串队伍,大人叫、小孩哭,乱成一片,有人为饭稠饭稀打破脑袋,哭爹叫娘,骂大街,都围绕一个“饿”字!
奶妈属于那种息事宁人的善良人。无论饭稠饭稀,她打一份回来吃,我就要“敲诈”她两份饭的奶水。后来奶爹就不得不受点委屈。可奶妈不忍,每顿饭都要推来让去,最后推出一个原则,不为你也不为我,挣别人的钱就要为别人负责。
我正中下怀,你有责可负,我就不尽天理人情地只管吃。吃着吃着先是奶爹委屈,后来是奶哥奶姐委屈。委屈来委屈去,委屈得全家都顺理成章地瘦了下来,只我一人满不在乎地胖了起来。
到了一九六〇年,天灾人祸,大家谁都不能再委屈下去了,谁也想为自己宝贵的生命向残酷的灾害进行一次顽强的抗争。于是,树根、树皮,野菜、野果,谁逮着谁就使足劲儿往肚子里塞,竟也奇迹般地胖起来,且胖得发光、发亮,胖得萎靡不振。据说那是浮肿。
就在这饥寒交迫的年月里,我却扬扬自得地活着。别人吃的是榆叶、榆皮,我吮吸的却是精细甘甜的乳汁。尽管奶妈使足劲儿给我流奶,但我终于还是瘦了下来。
母亲说我当时已瘦得鬼似的。这话尖刻且形象。
三
那年,母亲和五岁的姐姐来看我。
奶妈院里长了一棵很粗很大的倒栽柳,树荫下趴着一个孩子,头大,身瘦,脑门上一片片的黑痂,额头上横着二条浅浅的沟壑,肮脏的小脸,黑炭似的小手,两孔稀溜溜的鼻涕像两条惆怅忧郁的小河,通过嘴边,汇入嘴里,两只小而亮的眼睛机警地扫来扫去,四处寻觅,伺机找到可以充饥的东西。一只瘦鸡脱毛露皮,咕咕着,悠闲自在地在院中散步,徘徊来,徘徊去,低着头慢步而行,行至我身边,两腿一撇,拉出一泡大冒热气、尖尖朝上的鸡屎来。我即刻爬过去,直勾勾地盯着黑中带白、具有空前绝后诱惑力的“宝点”,流着口水,一把抓在手里,正欲品尝,姐姐尖叫一声把我吓了一跳。
姐姐惊慌失措地扯扯母亲的衣角,神色像见了驴上树:“妈,快看,她吃鸡屎。呸!真脏。”
母亲心头一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掴扇掉我手中的“佳肴”。我哇地哭了,透过泪光我愤怒地盯着夺我“佳肴”的“凶手”,以示微弱的反抗。
母亲无奈,从包里掏出一块“无粮点心”给我吃。我顿时止住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母亲和姐姐对视一眼望着我笑。这完全是人的本能,并非是母亲对女儿的爱。因为母亲已看不出这个鬼似的孩子就是我,就是从她高贵的躯体里分割出来的钢铁般的小生命——沈跃小姐。
烈日当空,骄阳似火。
奶妈打着一捆榆叶,弯腰曲背地走进院里,黑云似的头发上点缀了几片绿叶,反使憨厚朴实的面孔上平添了几分活跃。一件破旧的有襟布衫连挂在身上,肆无忌惮地敞着怀,那袒露出的两条扎了口的“小布袋”,却显得垂头丧气。
我惊喜贪婪依稀模糊地唤着娘,嘴里冒着水泡泡,小手一奓一奓地朝奶妈扑去……
奶妈见院里有客,急忙卸下重负,拍拍身上的土,歉然地朝母亲一笑,并不会说一句客气话。她从树荫下抱起鬼似的我,干柴似的手刺啦啦地在我鼻子上拧把鼻涕在大襟上蹭蹭,然后说:“妈妈来看宝宝啦,妈妈来看宝宝啦。他婶,快屋里坐。”
奶妈说一句,母亲心里重重地挨一锤,挨够了,也惊得目瞪口呆了:“啥?这是我们家二丫?你怎么把孩子放在院里满地乱滚,让她乱抓乱吃,连鸡屎都吃进了肚里!”
奶妈脸唰地变白了,讪讪地,神态局促不安,就伸长脖子喊:“惠明——惠明哎——死鬼跑哪儿去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随着喊声,惠明脆生生地应声从茅厕里慌慌张张提着裤子跑出来,一见院里有人便怯生生地低下头。
奶妈三步并作两步扯过惠明,冲脑袋啪地一掴:“叫你看孩,你死哪儿去了?”
惠明受了无端的呵斥并不敢哭出声来,眼里噙着泪:“娘,我屙不下来。”
“屙铁哩呀尿钢哩?”啪啪又是几巴掌。
惠明哇地哭了:“娘,比铁还硬,不信你去看。”
那时候屙“铁”屙“钢”并不稀罕。奶妈并不做理论,却是以此掩饰着自己的失职。
母亲却尴尬了,急忙拽过惠明:“算啦算啦,她也还是个孩子呢。”
是啊,惠明只有七岁,是奶妈最小的女儿,可她因我而受气并不稀罕。
比如我吃奶的时候,小嘴叼着奶妈的右奶,小手摸着奶妈的左奶。小姐姐多是依偎在奶妈左奶下,咂着小嘴,舌尖舔着嘴,仅此而已也颇香甜的。我常常是叼着乳头得意忘形,小脚不断地朝小姐姐的脸乱蹬乱踹,小姐姐并不生气。奶妈轻轻地拍着我的脚吟道:
小捣蛋,小捣蛋,
吃奶睡觉都不安。
我被拍得咯咯直笑,便顾不得吃奶,白色的乳汁怪可惜地汩汩外流。小姐姐手疾眼快伸过嘴来“抢救”,却被奶妈一把揪过乳头塞进我的嘴里,并虚张声势:“有人抢吃奶喽,有人抢吃奶喽。”
我一勾头叼住奶头,小脚三踹两踹把小姐姐踹开。
p style="
|
|




![创伤与记忆:身体体验疗法如何重塑创伤记忆 [美]彼得·莱文](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4664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