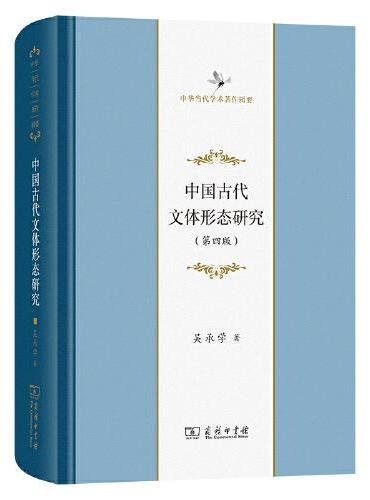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纷纭万端 :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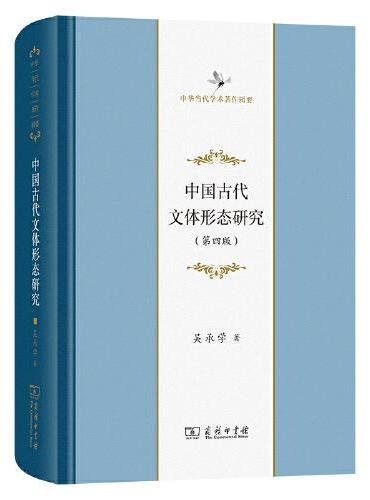
《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四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
售價:NT$
765.0

《
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大学问
》
售價:NT$
454.0

《
甲骨文丛书·波斯的中古时代(1040-1797年)
》
售價:NT$
403.0

《
以爱为名的支配
》
售價:NT$
286.0

《
台风天(大吴作品,每一种生活都有被看见的意义)
》
售價:NT$
245.0

《
打好你手里的牌(斯多葛主义+现代认知疗法,提升当代人的心理韧性!)
》
售價:NT$
301.0

《
新时代硬道理 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
》
售價:NT$
352.0
|
| 編輯推薦: |
|
肖斯塔科维奇是历***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今年是其逝世40周年的年份,作家出版社重新推出本书,以示纪念。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肖斯塔科维奇口述,由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
肖斯塔科维奇是世界范围内知名的音乐家,他的“肖五”“肖七”等名作早已享誉全球,他本人也成为了符号化的传奇。但是,其个人经历却并不为世人所熟知。在肖氏晚年,他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做了细致的梳理与回忆。而这本书的出版,改变了无数的指挥家与乐团对其作品演奏的方式。
在书中,他的回忆以灰色调为主:权力的阴影下造成的不可逆转的人格扭曲、面对人性的抉择时失去的珍贵友谊、忠于人格却最终被迫害的悲惨人祸——这些沉重的往事几乎占据了回忆录的大部分篇幅。书中也写到了人性的良善——如其和索列尔金斯基、格拉祖诺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真挚友谊。肖氏对朋友们的回忆饱含深情、非常真挚。书中还涉及不少前苏联重要人物:政治、音乐、文学等方面的大人物一一登场亮相。本书文风节制、准确、细致、平和。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带领读者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去再次认识这位知名音乐家——在特殊年代里,为了像人一样活着,他付出的努力与饱受的煎熬。
2015年8月9日肖氏逝世40周年,出版此书以示纪念。
|
| 關於作者: |
所罗门·伏尔科夫(SolomonVolkov1944-)
俄裔美国作家。1944年生于中亚细亚列宁纳巴德,1967年毕业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国家音乐学院。他主要研究俄罗斯和苏联音乐的历史和美学,以及音乐感觉和音乐演奏的心理学。
伏尔科夫于1976年到美国,进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工作。曾在《纽约时报》《新共和》《美国音乐》《音乐季刊》以及美国和欧洲其他多种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述音乐的文章。
伏尔科夫的主要著作有《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与约瑟夫·布罗茨基谈话录——二十世纪诗歌之旅》《圣彼得堡:一部文化史》等。
|
| 目錄:
|
原版本封面介绍1
序所罗门·伏尔科夫1
引言所罗门·伏尔科夫1
见证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25
主要作品以及生平职称和获奖表297
|
| 內容試閱:
|
引言
所罗门·伏尔科夫
他安卧在棺中,脸上带着微笑。我多次见过他笑;有时是放声的大笑,他经常讥讽地嘿然一笑或者低声轻笑。但是我不记得有过像这样的笑容:超脱、安宁、平静、满足,似乎他又回到了童年。似乎他已经逃脱了一切。
他喜欢讲到有关他所崇拜的文学巨子尼古拉·果戈里的一个故事:他怎么样显而易见地从坟墓里逃逸了。当坟墓挖开时(30年代在列宁格勒),果戈里的棺材是空的。当然,后来事情澄清了;果戈里的遗骸找到了并且安葬在他的归宿处。但是这种想法一在死后躲藏起来——本身却极为令人神往。
他逃脱了,官方的讣告已无从影响他了。在1975年8月9日他去世以后,刊登在苏联所有报纸上的官方讣告说:“我们时代的伟大作曲家,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列宁勋章与苏联国家奖章获得者季米特里·季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逝世了,享年六十九岁。共产党的忠诚儿子,杰出的社会和国家活动家,人民艺术家肖斯塔科维奇为苏联音乐的发展献出了他的一生,坚持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想……”
如是等等,一板一眼的官样文章。讣告下面第一个署名的是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下按字母顺序排列着秘密警察头子、国防部长……(列在这一长串名单的末尾的是一个真正的小人物:亚戈德金,莫斯科主管宣传的头头。此人之所以被人记得,只因为1974年9月他曾用推土机铲除了一次离经叛道的文艺作品的户外展览。)
8月14日,在官方的葬礼上,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高级长官们群集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灵床边。他们中间许多人多年以来是以罗织他的罪状为业的。肖斯塔科维奇的一位亲密的音乐家朋友脸色苍白地朝我说:“乌鸦聚会了。”
肖斯塔科维奇早就预见到这一场了;他甚至为一首描写另一个时代的俄罗斯天才普希金的“体面的”葬礼的诗谱写了音乐:“如此殊荣,使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无地立足……右边左边,只见宪兵的胸膛和恶相,粗大的手垂在两侧……”
现在,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多一次古怪的场面,多一次矛盾,他已不会再介意了。肖斯塔科维奇是在矛盾之中诞生的。1906年9月25日,他在俄罗斯帝国的首都、1905年革命余震未消的彼得堡出世了。这座城市后来在10年中两次改名——1914年更名为彼得格勒,1924年更名为列宁格勒。在这里,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只是时或隐蔽一些而已。
俄罗斯的诗人和作家早已为彼得堡塑造了一个邪恶的形象——一个“虚伪者”的城市,充满堕落生活的场所。彼得大帝不惜牺牲无数生命,强迫人们在沼泽地带建立了这个城市,它是暴君狂妄设想的产物,是专制君主的疯狂梦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认为“这个腐烂的、可厌恶的城市会随雾而升起,像烟一般消失”。
这个彼得堡是肖斯塔科维奇许多作品的源泉、基础和背景。在这里举行首演的也有他的7首交响乐、2部歌剧、3部舞剧以及他的大部分四重奏。(他们说肖斯塔科维奇想埋葬在列宁格勒,但他们把他埋葬在莫斯科。)肖斯塔科维奇承认彼得堡是他自己的城市,这就注定了他在心理上的两重性。
另一个矛盾来自他的遗传,这就是他的波兰血统与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穆索尔斯基一样)始终力求在他的艺术中探讨俄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遗传和历史相遇了。作曲家的曾祖父彼得·肖斯塔科维奇在青年时代是一位兽医,参加了孤注一掷企图向俄国争取波兰的独立的1838年起义。在起义被残酷镇压而华沙沦陷之后,彼得和成千上万其他起义者一起被流放到俄国的蛮荒——先到彼尔姆,后来到了叶卡捷琳堡。
尽管这个家庭已经俄罗斯化了,但是,“外国血液”的搀和无疑仍然起了作用。1927年,在肖斯塔科维奇去华沙参加肖邦比赛之前,别人也使他想起了血统问题,因为当时政府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让“那个波兰佬”前去。
肖斯塔科维奇的祖父鲍列斯拉夫参加了另一次波兰起义的准备工作(在1863年)。这次起义也被俄军击溃了。鲍列斯拉夫·肖斯塔科维奇与革命团体“土地和自由”(最激进的社会主义团体之一)关系密切。他被送到了西伯利亚。在那个年代,“波兰”这个名称在俄国几乎是“叛乱”和“煽动者”的同义词。
19世纪60年代在俄国流行的激进主义显然是唯物主义的。艺术被视为闲人的消遣而被摈斥。当时有一句流行的口号:“一双靴子比莎士比亚更有价值。”这种态度持续着。作曲家的父亲季米特里·鲍列斯拉夫维奇·肖斯塔科维奇没有卷入政治,他和著名化学家季米特里·门捷列夫一起工作,在彼得堡当一个工程师,颇有成就,生活顺遂。他娶了钢琴家索菲亚·瓦西里耶夫娜·科柯林娜。这个家庭对音乐有真诚的爱好,不再藐视莫扎特和贝多芬了,然而他们的基本观念仍然认为艺术必须是有用的。
小肖斯塔科维奇——米佳——9岁开始学钢琴,学得比较晚了。他的第一个老师是他的母亲。她在看到他进步很快之后就为他另找一位钢琴教师。家里人最爱提到下面这段对话:“我给你带来一个聪明极了的学生!”
“所有的母亲的孩子无一不是……”
两年之内,他弹完了巴赫《十二平均律》中的全部前奏曲和赋格。显然,他的天赋过于常人。
他在普通学校的各门课程上的成绩也优秀。不论做什么,他总是力求做得最出色。他几乎在学钢琴的同时开始作曲,态度认真;在他最早的作品中有钢琴曲《悼念革命牺牲者葬礼进行曲》。这是一个11岁的孩子对1917年二月革命的感受。这次革命推翻了尼古拉二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从国外回来,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受到群众的欢迎,年幼的米佳也在欢迎的人群之中。
同年,十月革命使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不久,爆发了国内战争。这时已不再是首都的彼得格勒(列宁把政府迁到莫斯科)逐渐空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家庭仍然忠于新政权,没有像许多其他知识分子那样离开这个城市。当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货币几乎已失去价值,粮食成了无价之宝。工厂倒闭了,交通停顿了。诗人奥西普·曼杰尔施塔姆写道:“彼得堡在光荣的贫困中奄奄一息。”
1919年,在这种乱纷纷的时候,肖斯塔科维奇进了当时仍享有国内最高音乐学府声誉的彼得格勒音乐学院。那年他13岁。学校房屋里没有取暖设备。在开得成课的时候,教授和学生们都裹着大衣,戴着帽子和手套。肖斯塔科维奇是最有坚持力的学生。假若他的钢琴老师、著名的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没有到学院来,米佳就自己到他家里去。
家庭境况越来越差了。1922年初,父亲由于营养不良,患肺炎不治去世,遗下索菲亚·瓦西里耶夫娜和3个孩子:米佳16岁,长女玛丽亚19岁,小女儿卓娅13岁。他们没有任何维生之计。卖了钢琴,但房租还是没有付。两个大孩子去工作了。米佳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电影院里弹钢琴为默片配乐。历史学家喜欢说这种卖艺生涯对肖斯塔科维奇是“有益的”,但是作曲家回想起这段日子就觉得厌恶。而且,他病了,医生诊断是肺结核。这疾病把他折磨了将近10年。
换了别人也许已被这种遭遇压垮了,但是肖斯塔科维奇没有。他倔强、坚韧。他从小就相信自己的天赋,虽然他把这个信念藏在自己心里。对他来说,功课才是最重要的。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他也要当高材生。
我们所看到的肖斯塔科维奇最早的画像(由俄罗斯杰出的画家鲍里斯·库斯托季耶夫用炭笔和红粉画的作品)表现了这种顽强和内心的专注。这幅画像还表现了另一种品质。画上,肖斯塔科维奇的凝视就像他年轻时的一个朋友的诗意描绘:“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那是你的眼睛。”库斯托季耶夫称肖斯塔科维奇为弗洛勒斯人。但是,肖斯塔科维奇虽然年轻,却感到这种比拟太浪漫主义了。勤奋就是一切。他从童年时代就相信这一点,而且一生都依靠它。在肖斯塔科维奇的成熟时期,一个学生向他诉苦说找不到主题写他的交响乐第二乐章。肖斯塔科维奇告诉他说:“你不该寻找主题;你应该写第二乐章。”直到1972年,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仍然强调音乐技巧的重要性。
得天独厚的青年肖斯塔科维奇在作曲上似乎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学派的音乐传统的忠实追随者。虽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已于1908年逝世,音乐学院的主要位置仍然由他的助手和学生在担任。肖斯塔科维奇的作曲教师是里姆斯基的女婿马克西米利安·斯坦因伯格。肖斯塔科维奇在音乐上初露头角就证实了他与“彼得堡学派”的血缘关系。作为毕业作品,他写一首交响乐,时年19。同一年(1925),这首交响乐由一个著名乐队在列宁格勒音乐厅演出,指挥是第一流的。这首交响乐立即引起了轰动;人人都喜欢这部作品,它令人激动,感情丰富,配器是巧妙的,同时又符合传统并容易理解。这首交响乐很快就出了名。1927年,它在柏林首次演出,指挥是布鲁诺·沃尔特;1928年列昂波尔德·斯托高夫斯基和奥托·克伦帕勒都指挥了它的演奏;1931年,《第一交响乐》成了阿图罗·托斯卡尼尼的保留节目。它几乎到处引起热情。肖斯塔科维奇被誉为新一代中出类拔萃的音乐家之一。
然而,在这凯旋的时刻,肖斯塔科维奇避开了成为一个因袭他人的作曲家的道路。他决心不当果戈里《死魂灵》中的“八面玲珑的妇人”〔鲁迅译作“通体漂亮的太太”——编注〕。他烧掉了许多手稿,包括一部以普希金的一首长诗为题材的歌剧和一部取材于安徒生童话的舞剧。他认为这些是粗制滥造的作品。他担心,假若他使用学院式的技巧,恐怕会永远失去他“自己”。
尽管音乐学院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但是,20世纪20年代是“左派”艺术君临新的俄国文化生活的时期。原因很多。主要原因之一是,先锋派准备与苏维埃政权合作。(传统文化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不是离开了俄国,就是正在对新政权怠工或者在等待事情过去。)有一个时期,似乎是左派人物在给文化政策定调子。他们得到了机会实现一些大胆的计划。
外界的影响助长了这种趋势。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生活比较安定一些了,新音乐立即从西方进来了,人们起劲地学习并演奏这些音乐。在20年代中期,列宁格勒几乎每星期都有一场有趣的首演:兴德密特、克任内克〔奥地利作曲家,生于1900年〕、“六人团”的以及“外国的”俄国人——普罗科菲耶夫和斯特拉文斯基。兴德密特和巴尔托克等著名的先锋派作曲家来到列宁格勒并演奏了他们的作品。这些新音乐使肖斯塔科维奇感到兴奋。
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来访的著名音乐家们在听到种种关于这个新的进步国家如何慷慨地支持新艺术的故事后肃然起敬。其实,没有任何奇迹。事实很快就证明,国家的艺术赞助人只愿支持有宣传意义的作品。肖斯塔科维奇接到一项重要任务:为革命十周年纪念写一首交响乐。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献给十月革命》(他给这首作品起的名字)附有合唱,歌词是共青团诗人亚历山大·别兹缅斯基的慷慨激昂的诗句。这首交响乐(以及少数其他作品)标志了肖斯塔科维奇向现代主义技巧的转变。总谱里有一个声部指定用工厂的汽笛演奏(虽然作曲家注明可以用圆号、小号和长号的齐奏代替)。
当时,肖斯塔科维奇另外还写了几首指派给他写的大作品。这些全都受到报刊的普遍好评。音乐主管部门的有影响人物支持这位有才能的青年作曲家。他们显然准备给他补个官方作曲家的空缺。
但是肖斯塔科维奇并不急于填补这个空缺,虽然他非常想得到成功和承认——以及不虑温饱。20年代后期,真正的艺术家们与苏维埃政府间的蜜月过去了。权力终于使出了它一贯的、必然的行径:它要求屈从。要想得到青睐和任用,要想平静地生活,就必须套上国家的笼套听任驱策。有一段时间,年轻有为的艺术家肖斯塔科维奇曲承新保护人的意旨,但随着他在创作上越成熟,苏维埃官僚幼稚的要求就越使他难以忍受了。
肖斯塔科维奇怎么办呢?他不能,也不想公开顶撞当权者,但是他很清楚,完全的屈从有扼杀自己创造力的危险。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肖斯塔科维奇成了第二个佯作颠狂、假托神命的“颠僧”式的伟大作曲家(穆索尔斯基〔1839—1881,俄国作曲家〕是第一个)。
“颠僧”(yurodivy)是俄国的一种宗教现象,即使是谨慎的苏联学者也称之为一种民族特征。在任何其他语言中,没有任何字眼能够确切地表达俄文юродцвый这个词的意义以及它的许多历史和文化的含意。
颠僧能看到和听到别人一无所知的事物。但是他故意用貌似荒唐的方式委婉地向世人说明他的见识。他装傻,实际上坚持不懈地揭露邪恶与不义。颠僧是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解放论者。他在公开场合扮演的角色是打破众人视为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藐视习俗。但是,他为自己规定了严格的戒律、规则和禁忌。
颠僧的起源要追溯到15世纪甚至更早,直到18世纪才成为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整个这一段时期内,颠僧可以揭露不义而保持相对的安全。当权者承认颠僧的批评权利和保持放诞行为的权力——在一定限度之内。他们的影响极大。他们的令人摸不清头脑的预言,农民听,沙皇也听。颠僧通常是天生的,但也可以“为了基督”而自愿加入其行列。一些受过高深教育的人成了颠僧,把这作为一种聪明的批评和抗议形式。
肖斯塔科维奇不是唯一的“新颠僧”。在他的文艺界同人中间,采取这种处世方式的并不乏其人。列宁格勒的年轻的达达派组织了奥伯里乌小组,行为与颠僧相似。有名的讽刺家米哈伊尔·左琴科戴上了一副颠僧的面具再也不脱,他对肖斯塔科维奇的行为和表现影响很深。
对这些现代颠僧说来,世界已成废墟,建立一个新社会的企图显然已经失败——至少暂时是这样。他们是光秃秃的地球上的赤裸裸的人。过去的崇高的价值标准已经被扫入尘埃。他们感到,新的理想只能“从反面”来肯定,必须用嘲笑、讽刺和装傻为烟幕来传达。
这些作家选择平淡、粗糙和故意晦涩的语言来表达最深刻的思想,但是这些语言的涵义并不简单,而是带有双重的、甚至三重的言外之意。在他们的作品中,插科打诨、玩世不恭的市井俚语屡见不鲜。玩笑话成了寓言,儿歌成了对“世态”的可怕的评判。
不用说,肖斯塔科维奇及其友人的装疯卖傻不可能像他们的先驱那么始终如一。过去的颠僧永远抛撇了文化和社会,而“新颠僧”的退身是为了存身。他们企图用从反文化武库中借来的手段复兴传统文化,虽然故意带上些宣道说教的味道,却与宗教无关。
肖斯塔科维奇极其重视自己与穆索尔斯基的这种关系。关于穆索尔斯基,音乐学家阿萨菲耶夫这样写道:他“从某种内心的矛盾逃入了半说教、半颠僧状态的领域”。肖斯塔科维奇曾在音乐上以穆索尔斯基的继承者自居,到了这时,他在作为人的意义上也与他联结在一起,不时扮演“白痴”(甚至穆索尔斯基最亲密的朋友也这样称呼他)的角色。
既然踏上了颠僧的道路,肖斯塔科维奇也就对他自己所说的一切卸脱了责任:任何语言都已失去它表面上的意义,即使是最高的颂辞、最美的辞藻。关于人所熟悉的真理的宣讲却原来是嘲弄:嘲弄往往反而包含着可悲的真理。他的音乐作品也是如此。这位作曲家故意写了一首“没有结尾诗节”的清唱剧,为的是促使听众从这首初听之下似乎并无意义的声乐作品中去寻觅它的真意。
当然,他下这一决心并非突然;这是经过了许多犹豫和矛盾的结果。肖斯塔科维奇日常的举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局的反应——就如从前俄国真正的颠僧“为了基督”的所作所为一样。当局有时宽容些,有时苛刻。自卫是肖斯塔科维奇和他朋友们的行为的一大支配因素。他们要生存,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颠僧的面具帮了他们的忙。应该指出,不仅肖斯塔科维奇以颠僧自居,而且他近旁的人们也是这样看他。俄国音乐界提到他时常常用颠僧称他。
肖斯塔科维奇在他一生中不时回到这种继承了对受压迫人民的关怀的颠僧的角色上来,只是形式随着这位作曲家的身心由幼稚到成熟、凋萎而有所不同。在他年轻时,这种角色使他远离文艺界执牛耳的“左派”人物如梅耶霍尔德、马雅可夫斯基和爱森斯泰因。普希金有一首《为堕落者乞怜》的名诗。肖斯塔科维奇在1927年后可以说也同普希金一样同情堕落者;这是这位颠僧式作曲家的两部歌剧中的重要主题——一部是《鼻子》,取材于果戈里的故事(完成于1928年),一部是《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取材于列斯科夫的故事(完成于1932年)。
在果戈里的这篇故事中,角色都是假面人,但是肖斯塔科维奇把他们写成了“人”。即使是从他的主人科瓦廖夫市长脸上跑下来穿着军装在彼得堡街上闲逛的那只“鼻子”,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处理中也具有现实的特征。作曲家对只有一般性的群众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很感兴趣;他仔细地探索群众心理的规律。我们关心被狂怒的城镇居民逼死的“鼻子”,也关心“没有鼻子”的科瓦廖夫。
肖斯塔科维奇只是把这个故事的情节作为跳板,用一位同果戈里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风格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棱镜来折射事件及人物。
在《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这部歌剧后来在第二版改名为《卡捷琳娜·伊兹麦洛娃》)中,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对耀武扬威、无处不在的警察权力的描绘。像在《鼻子》一剧中一样,肖斯塔科维奇安排他的角色与警察机器迎面相撞。
两部歌剧都用刑事案件来反衬他的人物“在耶稣受难像前的纪念默祷”。他使本已粗鄙的显得更粗鄙,用强烈、刺目的对比使色彩更为浓重。
在《麦克白夫人》中,卡捷琳娜·伊兹麦洛娃为爱情而杀了人,然而肖斯塔科维奇赦免了她的罪。按他的解释,卡捷琳娜杀死的那些毫无心肝、仗势欺人的人才是真正的罪犯,而卡捷琳娜是他们的受害者。这部歌剧的结尾十分重要。劳动营那一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中某些章节的直接的音乐再现。肖斯塔科维奇认为,这些囚犯是“可怜的亡命之徒”,同时也是法官。卡捷琳娜受良心的责备,她的吟唱和众犯人的合唱几乎融合在一起;就是说,个别性溶入了一般性,罪恶溶入了伦理。这种赎罪和净化的概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本概念;在《麦克白夫人》中,对这种概念几乎是以大起大落的戏剧手法直言不讳地表达的。肖斯塔科维奇并不隐藏他的说教意图。
从《鼻子》到《麦克白夫人》,肖斯塔科维奇所走过的路程是从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到一个遐迩闻名的作曲家之间的路程。《麦克白夫人》是现代作品中取得巨大的——也是无与伦比的——成功的杰作。1934年在列宁格勒首演后,它在5个月内演出了36场;在莫斯科,仅仅两个戏剧季节就演出了94场。斯德哥尔摩、布拉格、伦敦、苏黎世和哥本哈根都几乎立即上演了这部歌剧;托斯卡尼尼把其中的片断列入了他的保留节目。在美国的首演由阿图罗津斯基指挥,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弗吉尔·汤姆生在《现代音乐》上发表的文章(1935年)题为《大都会剧院的社会主义》。
人们赞美肖斯塔科维奇为天才。
接踵而来的是灾难。斯大林到剧院看了《麦克白夫人》,离开时一腔怒火。1936年1月28日一篇置人于死地的社论《混乱而非音乐》在党报《真理报》上出现,事实上是由斯大林口授的。“听者从歌剧一开始就被接连不断的故意安排得粗俗、混乱的音响惊住了。片断的旋律和刚萌芽的乐句被撞击声、挤压声和嘶叫声淹没,刚逃逸出来又再次被淹没。这种音乐令人无法卒听,要记住它是不可能的。”
当时正是全国一片恐怖的时期。清洗的规模极大。国内正在出现一个新的国度——“古拉格群岛”。在这种时候,斯大林对肖斯塔科维奇的警告——“这是故弄玄虚,这样下去结果可能很糟”一是明显的、直接的威胁。一星期后,《真理报》上又出现了第二篇社论,这次是申斥肖斯塔科维奇为大剧院上演的一部舞剧谱写的音乐。作曲家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认定他要被逮捕了。朋友们对他保持了距离。像当时许多人一样,他收拾好了一只小提箱,准备着。他们通常是在夜里抓人的。肖斯塔科维奇夜不成眠。他躺在黑暗中,听着、等待着。
这个时期的报纸上充满了要求处死“恐怖分子、间谍和阴谋家”的信件和文章。几乎每一个想生存下去的人都在这上面签名;但是,无论风险多大,肖斯塔科维奇都不愿意在这种信上签名。
斯大林私下对肖斯塔科维奇作了一个永远有效的决定:不逮捕肖斯塔科维奇,尽管他与被斯大林无情地毁灭的像梅耶霍尔德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这样一些“人民之敌”很接近。在俄国的文化历史中,斯大林与肖斯塔科维奇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是有其深远的传统的:沙皇与颠僧之间,以及沙皇与为了生存而扮演颠僧角色的诗人之间的爱憎交错的“对话”具有一种可悲的激烈色彩。
斯大林一挥手就能创造或毁灭整个文化运动,个人的声名更不在话下了。《真理报》的文章是对肖斯塔科维奇和他的同志展开一场阴险的攻击的开端。使用的形容词是“形式主义”,这个词从美学词汇转入了政治词汇。
在苏维埃的文学艺术史上,哪怕只是小有名声的人也没有一个没有被打上过“形式主义者”的烙印。这完全是武断的指责。许多遭到这种指责的人死去了。在《混乱》一文出现后,肖斯塔科维奇处于绝望之中,几乎绝望到要自杀。他经常等待着被捕,内心抑郁。差不多有40年,直到他逝世,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个人质,一个被判了罪的人。这种恐惧有时强些,有时淡些,但从来没有消失过。整个国家成了一所无路可逃的大监狱。
(肖斯塔科维奇对西方的敌意和不信任有许多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当时西方是尽量地不去注意古拉格。肖斯塔科维奇从来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建立过友好的联系,只有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也许是例外。他把《第十四交响乐》题献给布里顿并非偶然——这首交响乐是为女高音、男低音及室内乐队写的,其中的主角在被投入监狱时筋疲力尽地喊道:“墓穴在我的头顶上,对所有人来说我已经死亡。”)
考虑到自己有被捕的危险,肖斯塔科维奇把他在1936年完成的《第四交响乐》公开演奏的事情搁了下来。他怕重新试探命运过了25年才首次公演。在这些年里,作曲家耐心地听任报纸报道说他把这首交响乐束之高阁是因为他对它不满意;他甚至鼓励这种瞎说。当这首交响乐最后又排练时,他连一个音符也没改。指挥建议作一些删节,他断然拒绝。“让他们去啃,”肖斯塔科维奇说,“让他们去啃。”《第四交响乐》取得惊人的成功,正如其他长期禁锢后的作品重又复活时一样。他的音乐经受了时间的考验。。1932年,经过热烈的追求,作曲家与尼娜·瓦尔莎结婚了。尼娜年轻美丽、富有活力,是有才能的物理学家。1936年他们的女儿嘉丽亚出世了,1938年又生下了儿子马克西姆。从此,肖斯塔科维奇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他的家庭负责了。
处境越来越危险。凡是独裁者,无一不想建立一部机器来处理“他们的”艺术,但是斯大林所建立的乃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最有效的机器。苏联创作界人物对他无比顺从,为他的不断更改的宣传目的效劳。斯大林加强并完善了“创作协会”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工作的权利(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存在的权利)只给予那些得到官方承认和赞许的人。作家、作曲家、艺术家等等的协会作为官僚组织从1932年开始纷纷成立,成了等级区别严明、责任检查严格以及不断交叉控制的官僚组织。每个组织,除了无数非正式的告密分子外,都有一个“保卫部门”,即秘密警察。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今天。如果企图蔑视自己所属的协会,那不会有好下场: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镇压随时都能临头。谁服从,谁就受到奖励。在这个上足了油的、运转顺利的机器后面,站着斯大林这个人物,他的无处不在往往给事物涂上一层怪诞的、悲喜剧的色彩。
肖斯塔科维奇和斯大林的关系是他的生活和工作中的决定性因素。在一个统治者对他的子民掌握着绝对的生杀大权的国家里,斯大林对肖斯塔科维奇备加折磨和公开侮辱;然而,几乎同时,他又奖给他最高的称号和荣誉。看来似乎荒谬,然而事实上,荣誉和屈辱都给这位作曲家带来了无人可及的声名。
1937年11月21日可以认为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命运的分界线。列宁格勒的音乐厅里挤满了人:苏联社会的精华——音乐家、作家、演员、画家和所有各方面的名人——聚集在这里出席失宠的作曲家的《第五交响乐》的首演。他们等待着这部作品出事惹祸,猜测着作曲家会有什么遭遇,交换着流言蜚语,说着俏皮话。在恐怖环境里社交生活毕竟还是存在。
当奏完最后一个音符时,全场沸腾(后来肖斯塔科维奇的重要作品在苏联首演时也几乎全都是同样情况)。许多人流下了眼泪。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体现着一位诚实而有思想的艺术家,在巨大的道义压力下面,对决定性的选择作出了奋斗。这首交响乐充满着神经质的搏动;作曲家热狂似地在寻求走出迷宫的门户,结果,在终曲中,像一位苏维埃作曲家所形容的,他发现自己是在“思想的煤气室”里。
“这不是音乐;这是高电压的神经电流,”一位深为《第五交响乐》所感动的听众说。这首交响乐至今仍然是肖斯塔科维奇最受称颂的作品。它显示了肖斯塔科维奇在为他的一代人说话。有数十年之久,他成了一个象征。在西方,他的名字不论对左派或右派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在音乐史上大概没有第二位作曲家被放在如此富于政治性的地位上。
肖斯塔科维奇恢复了交响乐的垂死的流派;对他来说,这是表达他的思想感情的理想形式。在《第五交响乐》中,他终于从新的西方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和主要是古斯塔夫·马勒——的影响中脱颖而出了,创造他自己的、无人模仿得了的独特风格。
肖斯塔科维奇音乐的最大特色是它的紧张的、探索的旋律。主题通常在交响乐的整个过程中成长,形成新的“分支”(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油画的完整性的源泉,它往往篇幅巨大,而且几乎总是变化很多)。
肖斯塔科维奇音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丰富的、立体的、多变的节奏。他有时把节奏作为独立的表达手段,在交响乐中大段地自成段落(如《第七交响乐》——即“列宁格勒”交响乐——中著名的“进行曲”插曲)。
肖斯塔科维奇认为配器非常重要。他能立即想象到由乐队演奏时的音乐,落笔就写成总谱,而不是像许多作曲家那样先写简化的钢琴谱。他把各种乐器的音色视同不同的人,因此也喜欢把它们人格化(如《第十一交响乐》第一章乐的“冥界”中的黎明前的长笛声)。在他的管弦乐作品中,独奏乐器的独白常常像演说者的演讲,有时候则与内心的自白相结合。
在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中还有许多内容唤起对戏剧和电影的联想。这毫无可以责备之处,虽然许多评论家似乎仍然这么想。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当年在他们的“纯”交响音乐中曾经描绘了启蒙运动的一些形象,柴可夫斯基和布拉姆斯也各以自己的方式把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和戏剧改编为音乐。肖斯塔科维奇参加了20世纪音乐神话的创造。他的风格,借用索列尔金斯基描写马勒的话来说,是卓别林真实地再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
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是崇高的感情、奇异的方式、深刻的抒情与朴素的叙述的结合。
听者几乎都能理解音乐中的“情节”,即使他没有多少音乐修养和经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