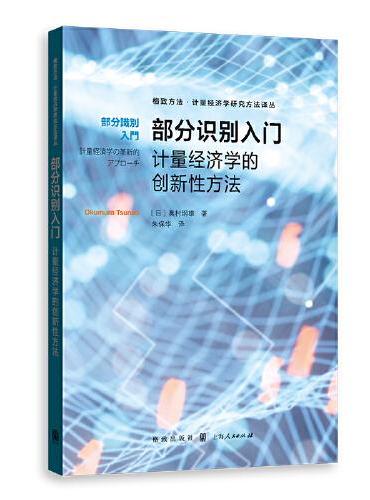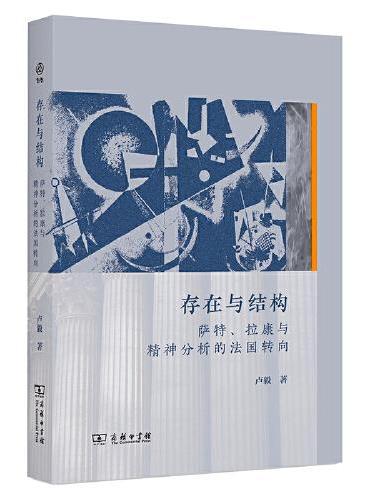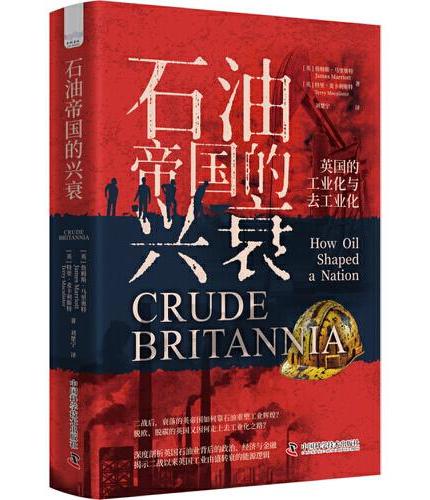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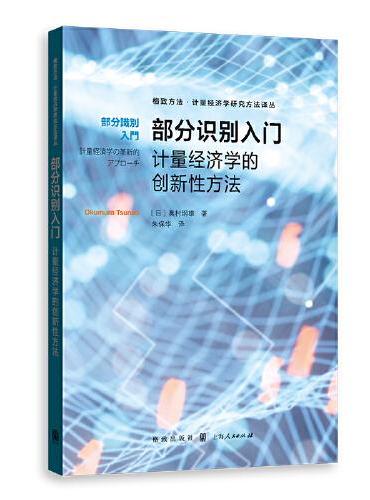
《
部分识别入门——计量经济学的创新性方法
》
售價:NT$
345.0

《
东野圭吾:变身(来一场真正的烧脑 如果移植了别人的脑子,那是否还是我自己)
》
售價:NT$
295.0

《
严复与福泽谕吉启蒙思想比较(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750.0

《
甘于平凡的勇气
》
售價:NT$
2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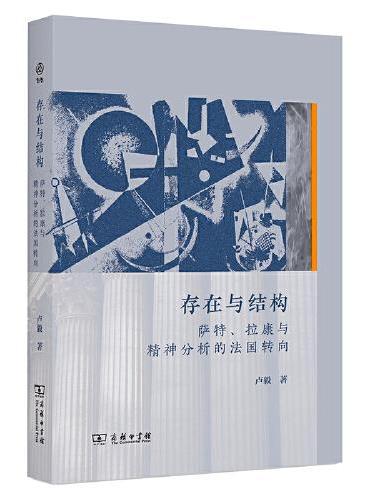
《
存在与结构:精神分析的法国转向——以拉康与萨特为中心
》
售價:NT$
240.0

《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与多模态技术应用实践指南
》
售價:NT$
4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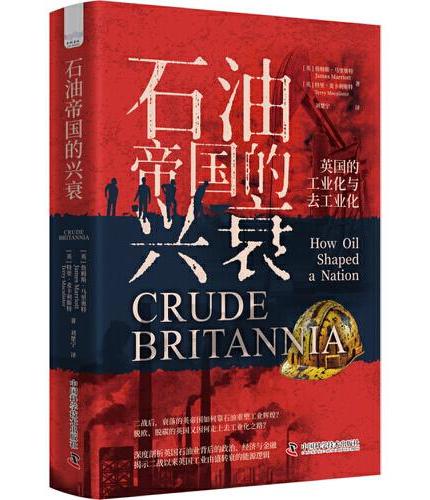
《
石油帝国的兴衰:英国的工业化与去工业化
》
售價:NT$
445.0

《
古典的回響:溪客舊廬藏明清文人繪畫
》
售價:NT$
1990.0
|
| 編輯推薦: |
庐隐,
一个民国女作家,
一个一生都在热烈追求爱情而又屡屡为情所虐的女人,
一个坚持用心灵写作力图超越自我的个性女作家。
邵洵美说:
“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
陆晶清说:
“庐隐既是一个受时代虐待的女性,她又是一个叛逆时代的女性。”
庐隐自己说:
“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
“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
|
| 內容簡介: |
庐隐(1899—193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著名女作家,民国时期与冰心、林徽因齐名的“福州三大才女”之一。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和艺术风格,庐隐曾在当时文坛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她短暂的35年人生、15年写作生涯中,创作了包括长、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剧本等题材丰富、数量可观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奠定了庐隐在民国文坛上的地位,使她成为五四时期杰出的女性文学先驱者和开拓者。
本书第一次采用编年的方法,即大体上按作品创作或发表的先后顺序编辑,收入迄今所能找到的庐隐全部著作,包括其他选集未收录的作品及新近发现的数十篇佚文等。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全集,能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庐隐作为我国现代著名女作家的心路历程,了解她的文学创作成就,以助于重估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
| 關於作者: |
|
王国栋,1936年生,福州人。在高等院校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近四十载,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长期致力于钩稽福建籍现代作家的生平资料,细致解读作家作品,对庐隐、梁遇春和林徽因三位著名闽籍作家的生平事迹考索和文学作品的钩沉掇补用力尤多,诸多发见均为学界前所未发,为重新估量和评价闽籍现代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多有助益。主要研究成果有:《庐隐生平著作简编》《庐隐年表》《关于郁达夫在闽任职情况和时间的考证》《庐隐集外诗文掇补》《庐隐的最后时光》等。
|
| 目錄:
|
卷一
1920—1923年
卷二
1924—1928年
卷三
1929—1930年
卷四
1931—1932年
卷五
1933年
卷六
1934—1935年
分卷目录
第一卷
1920年
“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
小重阳登陶然亭记
金陵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思想革新底原因
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
1921年
劳心者和劳力者
海洋里底一出惨剧
一个著作家
近世戏剧的新倾向
小说的小经验
一封信
一个病人
红玫瑰
创作的我见
月夜里箫声
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
两个小学生
“作甚么?”
砍柴的女儿
王阿大之死
哀音
迷路的羊
安眠的儿
秋风秋雨
心弦之音
影
一件小事
雪
月下
黄英
灵魂可以卖吗
祝《晨报》第三周的纪念
思潮
1922年
一个女教员
一个月夜里的印象
邮差
傍晚的来客
一个快乐的村庄
余泪
灵魂的伤痕
悠悠的心
碧涛之滨
东游得来的礼物(外一篇)
华严泷下
海边上的谈话
月下的回忆
最后的光荣
月下
或人的悲哀
1923年
彷徨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
扶桑印影
最后的命运
丽石的日记
月色与诗人
中国小说史略
她的来信
秋菊
流星
寂寞
秋别
海滨故人
淡雾
新的遮拦
将我的苦恼埋葬
……
|
| 內容試閱:
|
庐隐自传|思想的转变
在我所述的过去生活中,也许可以看出我思想的大概来。但我觉得这十年中,我思想上有几个显然的转变期,很有关系于我的作品,所以想把它详细说:
从童年到中学时代这一节时间,虽然不短,而我的思想还没有确定的形式,姑置不论,到了大学时代——也就是我从事于创作的时代,因此就从我表现于作品上的思想来说吧。
我第一期作品《海滨故人》一书所取材的方面有关于恋爱的,有关于工厂生活的,也有关于教育方面的,但是其中除了一两篇如《海滨故人》等是真的由我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东西,其余多半由于间接听来,或者空想出来的。在这本册子里,充满了哀感,然而是一种薄浅的哀感,——也可以说是想像的哀感,为了人生不免要死,盛会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残,圆月不免要缺,——这些无计奈何的自然现象的缺陷,于是我便以悲哀空虚,估价了人间,同时,又因为我正读叔本华的哲学,对于他的“人世一苦海也”这句话服膺甚深,所以这时候悲哀便成了我思想的骨子,无论什么东西,到了我这灰色的眼睛里,便都要染上悲哀的色调了。在这时候,我的努力,是打破人们的迷梦,揭开欢乐的假面具,每一个人的一声叹息,一颗眼泪,都是我灵魂上的安慰,——但是我自私了,我自己对世界这里[样]认定,我也想拖着别人往这条路上走,我并不想法来解决这悲哀,也不愿意指示人们以新路,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
这种思想,支配我最久,第二本的小说《灵海潮汐》,和第三本小说的《曼丽》,都未能出这个范围。不过在实际的生活上,我比从前复杂了,同时我接连着遭遇人间最不幸的死别:第一是母亲的死,在儿时我虽然不被母亲所爱,但是以后几年,为了我的努力,母亲渐渐的对我慈和;同时呢,我是个感情重于理智的人,所以对于母亲仍然有着极深的眷恋,——而且她的死是太出乎我意料之外,那时候正是年假,我放学回家,在家里住了七天,接到北平的朋友的快信,要我即刻北去,一来参观她们的婚礼,其次呢另有要事介绍我去担任,必须当面接洽,我当时把信给母亲看过,母亲脸上露着不忍离别的热情,和声说道:“差五六天就到新年了,你一去不是不能在家过年了吗?”我听了这话,又看了母亲那慈和的面容,我就想不走吧,但那时候究竟是少年,血气方刚,觉得动比静好,〈因〉此最后还是决定去了。
我走时,是早上八点钟,那时节母亲不曾起来,只坐在床上招呼我吃东西,并嘱咐我路上小心,她含着微笑,望着我走出家门,我心里不期然的发酸,眼泪滴了下来——我从来离家没有掉过眼泪,而这是第一次。
唉,谁知道这一次的别离,是我们母女间的永别。我到北平两个星期,忽然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是“母病重速归!”这一吓我如失去了魂魄,当夜就动身南下,那晓得到家时,母亲已经死了两天,棺盖已紧紧的盖上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晓得母亲死后一年多,郭君也一病不起,这仿佛在那尚未结痂的疮痛上,又刺了一刀。这时节我对于人生才真的了解了悲哀,所以在这个时期我的作品上,是渲染着更深的感伤——这是由伤感的哲学为基础,而加上事实的伤感,所组成的更深的伤感。
我被困在这种伤感中,整整几年,我只向灭亡的路上奔,我不想找新的出路。后来我又回到北平,认识了几个新朋友,是由石评梅介绍的,——评梅那时也正过着悲伤的生活,所以她很体贴我,帮助我,我俩同在一个中学教书,稍有闲暇就一同出去散步谈心,有时两人跑到陶然亭,对着累累荒坟,放声痛哭,有时尽量的吃酒,吃得人事不知,有时呢,绝早起来,跑到中央公园的最高峰上,酣歌狂舞,我们是一对疯子。就在那个时期,我获得浪漫女作家的头衔,好在我道不孤,我因有评梅和我同情,对于这种生活仍能继续下去,——那顾得别人的冷讽热嘲,在这个时期我写了《醉后》等短篇文章。
不久评梅得了脑膜炎的急症,从她病起,直到她死,我不曾离开她,后来她搬到协和医院去,我也是天天去看她,在她临终的那一夜正是阴历八月十六,我接到协和医院的电话,连忙坐汽车赶到那里,她正在作最后的挣扎,我看她喘气,我看她哽咽,最后我看她咽气,唉,又是一个心伤!从评梅死后,我不但是一个没有家可归的飘泊人儿,同时也是一个无伴的长途旅行者,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着慢性的自杀。
可是天心还不以为足,评梅死后两三月,我又接到我大哥哥去世的消息,他遗下了几个幼小的侄儿侄女,和一个刚刚三十岁的寡嫂。唉!人非木石,这接连不断的割宰,我如何受得了?我病了,在病中我想了许多,我觉得我悲哀的哲学,和悲哀的生活已经到最高潮,这时节我若不能死,我不论对于生活上和作品上,都有转变方向的必要,——因为我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在我病好以后,我结束了我第一个时期的思想。
到了我作《归雁》的时候,我的思想已在转变中,我深深的感到,我不能再服服贴贴的被困于悲哀中,虽然世界是有缺陷,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纵然这只是等于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梦想,但我只要有了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上便有了光明,有了力。所以在《归雁》中,我有着热烈的呼喊,有着热烈的追求,只可恨那时节,我脑子里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礼教的藩篱,可是我内心却燃烧着这种的渴望,因为这两念的不调协,我受尽了痛苦,最后我是被旧势力所战胜,“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从新去飘泊了”。
我的《归雁》虽是以这样无结果而结果了,而我在这时期,认识了唯建——他是一个勇敢的,澈底的新时代的人物,在他的脑子里没有封建思想的流毒,也没有可顾忌的事情,他有着热烈的纯情,有着热烈的想像,他是一往直前的奔他生命的途程,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为他的灵光,一扫而空,在这个时期,我们出版了《云鸥情书集》——这是一本真实的情书,其中没有一篇,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当我们写这些信时,也正是我们真正的剖白自己的时候,在那里可以看出,我已不固执着悲哀了,我要从新建造我的生命;我要换过方向生活,有了这种决心,所以什么礼教,什么社会的讥弹,都从我手里打得粉碎了。我们洒然的离开北平,宣告了以真情为基础的结合,翱翔于蓬莱仙境,从此以后,我的笔调也跟着改变。虽然在西湖时我还写了一篇充满哀情的《象牙戒指》——那并不是我的理想,只不过忠实的替我的朋友评梅不幸的生命写照,留个永久的纪念罢了。
在这个大转变之后,我居然跳出悲哀的苦海。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换句话说,我的眼光转了方向,我不单以个人的安危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围的人了。最近我所写的《女人的心》,我大胆的叫出打破藩篱的口号,我大胆的反对旧势力,我更大胆的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
但这些还不够,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作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沈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
归纳上面的事实看来,这十余年来,我的思想可分三个时期:——
一,悲哀时期——在这时期产生了《海滨故人》,《灵海潮汐》,《曼丽》。
二,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归雁》,《云鸥情书集》。
三,开拓时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女人的心》和短篇《情妇日记》等。
以上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里,已确定了我的人生观;到第二个时期,我的人生观,由极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转变;到了第三个时期,就是我已另开拓出一条新路来了,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难道一个人的人生观,根本上也会改变吗?——也许有的人是如此的,不过我却不是这样。我不满意这个现实的人间,我伤感,一起头我就这样,其中所不同的,是从前只觉得伤感,而不想来解决这伤感;所以第二步,我还是不满意人间的一切,我还是伤感,可是同时我也想解决这个伤感;第三步呢,不满意于人间和伤感也更深进一层,但我却有了对付这伤感,和不满意于人间的方法,我现在不愿意多说伤感,并不是我根本不伤感,只因我的伤感已到不可说的地步,这情形正好以辛弃疾的《丑奴儿》辞来形容之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辞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文摘二
第四卷|补袜子
一天下午,空气特殊的沉闷,满天堆叠着雨云,房里的光线十分黯淡,这也许正是使人发脾气的原因吧!路侠从学校教课回来,嘴里衔住一枝小茄利克,洒然的斜倚在沙发上,当然她满脸都表现着懒散的神情,这更触怒他——子韵的满腔不高兴,路侠对于他的发牢骚,常认为是一种心理变态,最初一两次路侠看得颇严重,仿佛这是一种可怕的暴风雨,平坦的前途,也许就要受影响,有时竟伤心的落下泪来,但是每次在路侠心灰意懒的时候,子韵的脾气便不发了,他必含着温和的微笑道:“路侠!我们讲和罢!”于是一天的云雾都消散在路侠一声长叹里了。
今天子韵因为要洗澡,打开衣橱,找袜子,一双咖啡色的线袜,头里破了一个口子,女仆忘记替他缝,他把破袜子一摔摔到床上,冷笑了一声道:“这真奇怪,从来袜子破了不晓得补,这算什么家庭,我还不如去住旅馆呢!”
“这有什么奇怪呢!袜子破了叫娘姨补补就是了,生什么气!”路侠满不在意的说。这更使他不爽快,额上涨起几条青紫的筋来,面颊发着红,不住的冷笑,这不免激起路侠满肚皮的不平来,她冷然的说道:“你冷笑什么,我看你这个人,真正是有点神经病,心理作用太大了,想到风就是风,想到雨便是雨,像这芝麻点大的事也值得气得这个样子?”
“不管怎么样,你对于管家太不行了,不用说我的衣服你料理不清楚,就是你自己也是有了这件缺了那件,其实每年并不少作衣裳,结果还是弄得没有衣服穿!”
他气愤愤的叨唠着,路侠陡然站起,把吸残的烟头丢在痰盂里,含怒的说道:“我本来不配作好太太……其实呢,你也太会替自己想了,因此就忘记了别人。你为了一双破袜子没有补就像是拿到把柄了,一股劲的向我发脾气,我老实说说罢,别人的太太没有替老爷补袜子也许是太麻糊[马虎]不管闲事了,至于我呢,每天和你一样的在外面教书作事,下午回来对于这些琐碎的事情真没精神问了。你自己为什么不会吩咐娘姨一声……。假使你以为我没有替你补袜子就不够好太太的资格,那我就只好退位让贤了。”
“当然我不能怪你,……不过我觉得补袜子的太太也很需要的呢!譬如炒炒小菜呀,管管仆人呀,家里弄得清清爽爽多少舒服呢!……”
“我也知道你的话是很有理的,不过天下事很难两全,你要是要我送你两双新袜子到好办,如果要我替你补袜子那就办不到了。别说我一天到晚都忙着在外面工作,就是有些工夫与其补那破袜子,我还不如写写文章呢。”
“当然,当然,”子韵的口锋忽然柔和了许多,想来离讲和的程度不远了。可是路侠的脾气还不曾发够,她故意的激他道:“我想你还是赶紧到纱厂里去找个好太太吧,她不但会补袜子而且还会织袜子咧。同时当然也会烧小菜,领小孩子,色色出人头地——但只一件她可未必能经济独立。同时也不见得能陪你这神秘的诗人清谈罢!”
“噗哧”一声子韵转过头去笑了,“不闹,不闹,我们下去品茗吧!”
“口哀!老爷的花头真多,几时又学会了品茗,我简直不渴则已渴了就是牛饮,没有这么多讲究。什么龙井雨前……不过是些嫩树叶子泡出一股苦涩味儿的水来罢了,有什么可品的呢!”
“那里,你不知道,好茶确有妙品……你真感觉不灵!”
“当然!如果感觉灵,至少就能直觉到你的袜子什么时候破就连忙替补好了,免得你发牢骚了!”
路侠说着不禁也笑了,他们间补袜子的公案,就在这笑影里消除了,不过在喝着清浰[冽]的龙井茶时,子韵仍旧很郑重的说道:“补袜子的太太,和能经济独立的太太不可得兼,也算是一个妇女问题呢……!”
“不错,是一个妇女问题。”路侠捧着一杯茶懒懒的回答着,热茶的蒸汽在他们之间罩了一层烟雾,但刹那间便又消除尽净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2年10月26日《申江日报》副刊《海潮》第6号,后收入《东京小品》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