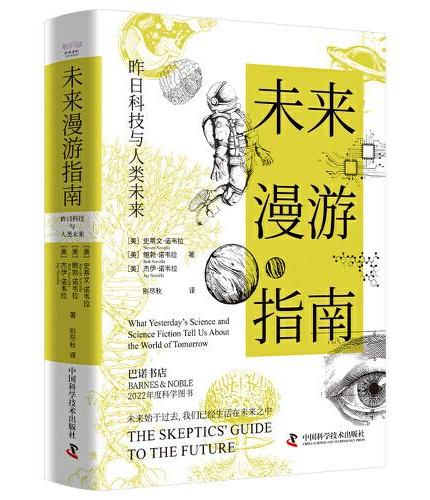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新能源材料
》
售價:NT$
290.0

《
传统文化有意思:古代发明了不起
》
售價:NT$
199.0

《
无法从容的人生:路遥传
》
售價:NT$
340.0

《
亚述: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的兴衰
》
售價:NT$
490.0

《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采煤机智能制造
》
售價:NT$
4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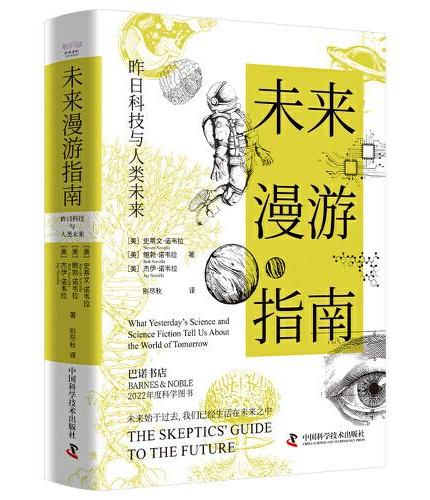
《
未来漫游指南:昨日科技与人类未来
》
售價:NT$
445.0

《
新民说·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上下册)
》
售價:NT$
790.0

《
我从何来:自我的心理学探问
》
售價:NT$
545.0
|
| 編輯推薦: |
1、取材广泛,记录真实,数百位亲历者讲述鲜为人知的兵团往事;
2、立场客观,视角多维,大规模多层次资料还原历史本来面貌;
3、内涵丰富,语言生动,是一段在国家使命下秣马厉兵的国防历史,也是一首在时代潮流中跌宕起伏的青春之歌。
|
| 內容簡介: |
《生命中的兵团》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由非兵团亲历者完成的有关兵团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分为上下两卷,共有300多张图片,120多万字。书中附赠作者自制的推介光盘。
作者用近两年的时间采访黑龙江兵团历史的亲历者,在身份上涵盖各种人员层次,并查阅和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在口述和文史两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作者以客观审视的态度,把对人性的解读作为落笔重点,讲述了那一代知识青年在北大荒的种种生活经历。他们来到北大荒,到建设北大荒,把热血的青春留在了黑土地,离开后对北大荒也抱有深切的怀念。
|
| 關於作者: |
|
朱维毅,德国工学博士。1952年10月出生,北京“老三届”初中生,“文革”期间曾两次从城市赴山西榆次插队,前后历时6年。1975年在农村被推荐上大学,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工科学习,毕业后分配山西太原工作,1980年考取硕士研究生重返北京,1983年毕业后在北京以工程师身份从事科研工作,1988年赴联邦德国留学,4年后在柏林工大获博士学位,其后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工—商—文”的职业三级跳,逐步将自身的主业回归到自幼喜爱的文学创作,曾发表过《留学德意志》、《寻访“二战”德国兵》、《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等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
| 目錄:
|
上 卷
引 言历史走到“六一八”
第一章将士三千赴边陲
“三军”老将
从“三八线”到黑龙江
军中“学生兵”
第二章专列指向北大荒
“我们只要出身好的!”
走向边疆和未来
扒车奇缘
美术之梦
从越南到兵团的“志愿军”
第三章不打不成交
该出手时就出手
小架天天有,大架三六九
以城分阵营,拳脚论高低
善不为官,慈不掌兵
第四章北疆布阵
老兵出马
统帅现役部队之梦
“北方乙种师”的使命
中美对话与兵团同行
第五章不穿军服的士兵
我们是值班连
兵发二抚路
二流兵力守一线
第六章江上出击
渔船斗炮艇
冲进珍宝岛的硝烟
八岔岛上的枪声
第七章军人的新使命
不消除派性怎么打仗?
兵团的当家人
新战场上的新挑战
众说纷纭话兵团
第八章“小六九”的成人礼
“简直就像从幼儿园跑出来的”
想说爱你不容易
“小上海”之恋
“老油条”的纯真年代
幸运的成才者
第九章“老三届”质量
淘气兵
理想与现实之间
有兵团这碗酒垫底
有情有为大老张
“老上海”告御状
第十章少帅建三江
军人就是要拿强敌开刀
在抚远荒原摆它一个师
务实的“王大吹”
擦边球和自选动作
留痕于历史和人心
下 卷
第十一章黑土地的脊梁
“英雄解甲永不放下枪”
万道涓溪汇铁流
没有血缘的亲人
好连长
第十二章知青官
女儿当自强
我的连队我的兵
从兵团开始的长跑
第十三章艺术的星空
宣传队里的武林人
濮存昕:兵团给我承受力
笑面人生一姜昆
从美院附中进“兵团美院”
小画家的心路
白毛女宣传队
第十四章左右之间
有一种包袱叫“出身”
“黑龙会参谋长”
父女两代人的北大荒
逝去的美丽
兵团蒙难记
两代人的选择
自投落网的“黑后台”
第十五章名誉与情欲
“这根弦我们绷得很紧”
记忆中的阴影
枪声的警示
倾听历史的回音
第十六章青春的墓碑
她们永远与大江相守
火光就是命令!
难忘“11?7”
第十七章潮落
条条道路通城市
换个地方再姓“农”
举国围观的“黄刘之争”
第十八章找回岁月
体制内外
生活困境的进出
最后的掏粪工
边疆的知青校长
留在心中的故乡
我们这一代
后 记生命中的兵团
|
| 內容試閱:
|
后记——生命中的兵团
北大荒的故事像一部历史大剧,一批批演员在剧中出场、表演、造型、谢幕。兵团的故事是其中的一幕,九转回肠,高潮迭起,在播放几十年后仍令人回味无穷。几十年来,书写这一幕故事的人不可胜数,我是其中的一个后来者,也是为数不多的兵团历史的局外人之一。
人之社会属性,决定于社会与人的交互作用。说到社会留给我本人的最深刻影响,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的知青经历,所以我要写这本书。
知识青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群体的终身称谓。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主要在于和它相关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给上千万参与者及其家庭的命运都留下了深刻印记,因此,即使一代知青消失在历史长河之后,这个群体仍将拥有这个年轻的称号。它成了一个难以抹去的国家记忆。
我有过两次上山下乡的经历,两次都因为在城市找不到求学或就业之路而选择了去农村插队,都没有任何人指派或动员,都是自作主张取出户口偷偷离家出走,去的都是一个地方——山西省榆次县。我的两次知青经历共有六年,第一次插队历时四年零四个月,第二次插队历时一年零八个月。
上山下乡带给我的,不仅是吃苦的能力和对社会底层的了解,还包括对困难与挫折的承受力,这些收获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也决定了我的思想特征。在作家的创作中,印象至深的自身经历往往会影响选题思考,所以我要写知青。
二十多年前,当我开始尝试写作时,我就知道自己迟早会在知青这个题材上落笔,是小说、剧本,还是纪实文学?我心里没数,但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做这件事,这不仅是因为上山下乡的经历带给了我太多的东西,还因为它影响了至少三代中国人乃至这个国家的命运走向。说三代人的命运,是因为除知青自身之外,他们的父辈和子女的命运亦与上山下乡相连;说
到国家的命运,是因为返城后的知青们曾履行过涵盖中国社会所有层面的岗位职能。
从最终留在农村的知青,到返回城市的知青;从扫马路、开出租车和摆地摊的身处社会底层的知青,到对国家的技术、教育、文化、商业、行政、安全负有重责的那些位居社会核心位置的知青;从对上山下乡运动持完全批评态度的知青,到把上山下乡经历视为一生中最宝贵财富的知青……无论他们在身份、命运和历史态度上如何千差万别,这个群体都在影响着中国的现实和未来。这个群体是值得作家落笔的。
2011 年末,我开始筹划写一本有关知青的纪实文学。
由“文革”开启的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年,人数上涉及1700 万人,地域上涉及全国各地,形式上涉及插队、返乡、去五七干校和国营农林牧场,我应该选择哪一段时间、哪一个地区、哪一个群体?
写一本关于知青的书,和我写关于“二战”德国老兵的纪实文学《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不一样。德国老兵是一个曾经影响了世界,却又很少被世界关注的一个特殊历史群体,讲述他们的故事,很容易让受众感到耳目一新。而记录上山下乡历史的书籍在中国已经多得不可胜数,如果没有独特的写作思路,落笔于这个领域就如同在大海中增添一滴新水,有无皆可。
我是学工科出身的人,长期的科研训练赋予了我一种写作习惯,那就是按照科学创新的基本要求来对待文学的创新。做一篇科学论文,前提是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的基础,接着就要调研和选题,包括总览学科现状、发现创新空缺、了解资料来源、落实研究手段。搬到文学创作领域,这就意味着要阅读大量同类作品,找到足够的素材,并对自己的写作实力能否确
保创新做出一个客观的估计。
为此,我阅读了一大批关于知青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其中虽不乏精锐之作,但存在的两大问题也很明显:
第一是题目常常喊得太大,动辄冠以“中国”二字,翻开一看,不是对在某一地区下乡的知青群体记载,就是以不充分的资料来概括全国的知青;
第二是作者本人的观点和立场在作品中介入得太多太深。对事情应该怎么看,作者全告诉了你!这样就难免要折损作品的客观性,一来排斥了和作者价值观不同的读者群体,二来也挤掉了后人的评价空间。
我决定写一本主要由历史亲历者去回忆、去倾诉的书。我可以加入一些相关信息和个人分析,至于对历史的思考和评价,我觉得还是要交给现在和以后的读者。
那么,在写作对象上我应该选择谁呢?
首先我想到的是自己最熟悉的山西榆次县的插队知青,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我否定了,因为这个群体的交互性和集体感几乎不存在。
到榆次插队的知青在落户时间上有很大的跨度,从稍早落户到杜家山的北京知青,到1968 年末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被送来的北大附中和北京123 中学的知青,再到在1970年代从太原榆次等城市下放来的小知青,前后时间跨距至少十年,其间人来人去,就像一场“下乡流水席”。
从落户的地点上看,在榆次插队的知青在榆次县境内的地理分布很广。我们这些“老插”被送进了与太谷县、和顺县相邻的榆次边缘区的大山里,而后来的小知青则基本都被安排到了平原或丘陵地区的人民公社。如果把榆次县安置知青的工作比喻为撒玉米籽,其结局不是长成一片玉米地,而是东一棵西一棵的玉米单株,相互之间很少有关联。
榆次县的插队知青都以村为单位结成集体户,不同村落之间的知青很少有来往。这些知青户少则三五人,多则二三十人,一旦走出自己的村子,就很难再找到朋友。我第二次插队所在的榆次县东赵公社大发大队,和附近的东赵大队只有两三里路之隔。这两个村子的知青之间的唯一一次交往,就是打过一次篮球赛,场上气氛十分对立,几次犯规出现后,双方队员的脖子就像斗鸡一样涨红了。同在一个公社这一点,并不足以把我们融合为一个集体。我们一样在“战天斗地”,却无法产生互为战友的感觉。
在对特定历史题材的纪实写作中,作品形式的选择,和对象的特点存在着密切关联。在我看来,对插队知青只适合写个体故事,而不适合于群体纪实,因为群体需要较强的人员同质性和共处稳定性。倘若大而化之,把不同的人群硬往一起归拢,令人震撼的最多只会是书的标题,一旦读者翻开书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大板砖拍过来事小,浪费了纸张事儿大,毕竟纸是用木头做的,那是宝贵的资源。
有鉴于此,我自觉不但无力涉猎一个省份的“插队知青命运纪实”的写作,就是写自己比较熟悉的榆次县知青之命运也无法胜任,因为我实在难以将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都相当错乱的众多自生自灭型的知青点,在文学上做一个整体性归纳。
我热爱写作,同时又对写作充满敬畏之心。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不仅要面对历史亲历者,还要面对试图通过作品来触摸历史的后来者。它只要发表,就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于是我想到了“兵团”。
在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中,“兵团”几乎成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专用简称,
以至于今天只要提及在“文革”中成立的其他生产建设兵团,人们都需要在这个称谓之前特别加注地名,以区别于黑龙江兵团。新疆兵团虽然比黑龙江兵团成立得更早并延续至今,但由于它基本上没有受到“文革”期间城市中学应届毕业生移民潮的波及,在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中所占有的地位也就很难和黑龙江兵团相提并论。
要写准写活一个历史群体,需要作家本身置身于这个群体之中,获得对方在当下和在历史中的时代和生活感受。
我本身和兵团知青属于同代人,并且在四十多年前就和这个群体有过接触。兵团人出发前的统一置装,是我对这个群体最早的印象,而他们有建制、有工资、有武装、有探亲假、有统一的号令和管理、有参与机械化大农业生产的机会这些特点,也让我对兵团和插队知青在下乡环境上的不同有所体验。
当年每逢春节,中国各个城市里总会汇集起回家探亲的各路知青,那是我最早观察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之间的差异的机会。
这些人都有工资,探亲期间带着全国粮票揣着现金,花起钱来手脚挺大,聚在一起时缺点儿什么吃喝时,马上就有人起身去买,这让我们这些辛苦一年下来除了挣出口粮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现金收入的插队之辈羡慕不已。
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军队的色彩。我们这些插队的人在称呼农村干部时从来不提职务,张口就是“二货”“秋生”“狗子”什么的,而这些人一说到兵团的干部就是“连长”“股长”“团长”“参谋长”……他们还经常会提到武器保养、战备值班这些军队用语。但他们又不大像军人,多数人穿件厚实的黄色大衣,当时的说法叫作“狗屎黄”假军大衣,上面或多或少都会有几个被烟头烫出来的小孔洞。他们说话的调子也有些变味,把“做”说成了“整”,把“干啥”说成了“干哈”,气质上带有几分东北农村汉子的粗放和野性。但只要探亲假期限一到,他们立马就在北京消失。据说兵团纪律严明,不允许超假一天,和我们这些想在城市赖多久就赖多久的插队知青大不相同。
在我第二次到山西榆次插队时,我开始和一群从兵团转来插队的知青一起生活和劳动了。他们带来了兵团各师基层连队的信息,显示出在兵团形成的和插队知青迥然有别的行为特征,他们具有更多的服从意识和对艰苦生活的承受力,集体认同感也更多一些。在和他们的相处中,我对北大荒有了更多的感觉,成了一个能远距离观察兵团6 个师的局外人。
在“文革”结束后的后知青时代,我看过很多有关知青题材的电视剧、小说和报告文学,我发现其中最有影响力和震撼力的作品基本都是关于黑龙江兵团的。这一点进一步促成了我探讨兵团历史和荒友之间关系的愿望。
黑龙江兵团在地域、人数和生产规模上的尺度之大,为榆次县农村远不能及,但我却感到对兵团故事的归纳会更容易一些。它是一个半军事化单位,体量虽大,但有共同使命,有行政中枢,有建制层级,有统一管理。这些条件既有利于在时空两方面梳理出它的分布和发展,也有利于发现兵团人物之间的命运联系。写兵团知青和写插队知青的差异,就如同写战争年代中的一个野战军的作战史和一个省的游击史的差异,前者的历史主线显然更为明晰。
着眼于大历史,黑龙江兵团在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也具有举足重轻的地位。它汇集了“文革”时期全国最大的一个知青群体,履行了一段在全国各兵团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屯垦戍边任务,演绎了一场充满悲欢离合的知青命运大剧,在全国各大知青群体中也涌现出了最多的精英级社会人才。同时,兵团在建设边疆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两方面所发挥出的历史作用,使它成了中华大粮仓北大荒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一个历史环节。
基于这些原因,在迄今为止的知青文学领域里,黑龙江兵团一直是最受社会关注的一个写作重点。再次对它进行历史挖掘,创新的挑战性不言而喻。要写出一个既与众不同,又真实可信的兵团,我感觉需要做到几个“独特”:
独特的视角——站在兵团亲历者的立场之外去审视兵团;
独特的立场——站在传统或时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之外去解读兵团;
独特的方法——把挖掘历史资料和收集口述史两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
独特的比较——从插队知青的观感出发来发现兵团知青的经历特色;
独特的目标——通过对典型内容中的典型人物和故事的展现,浓缩出一幅黑龙江兵团的历史概貌。
这一系列的“独特”能否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权威的评判者是读者,我要做的只是尽己所能。
我原本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查询历史资料,用半年时间整理素材并完成写作。但真到动手做的时候,我才发现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兵团历时八年,多数知青在北大荒生活十年。要写好他们的故事,调查中要涉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除了要收集兵团知青的口述史以外,我还要了解国家的上山下乡部署、组建兵团的背景和过程、各地动员和输送知青的情况、中苏关系的发展变迁、沈阳军区的戍边部署、黑龙江国营农场在“文革”中的变动、现役军人和农场干部职工的北大荒经历……其中每一方面的素材都足以撑起一本大书。
写作投入如果不足,就很难浓缩历史;但写作胃口如果过大,又有可能写成一部兵团百科全书或大事记,最终因可读性的降低而使作品失去活力。
初步的调研让我看清了自己面临的三大挑战:
第一,能否确保在采访调研上做足够的投入;
第二,收集到的素材是否具有足够的质量和代表性;
第三,对庞大的信息量是否具有足够的驾驭能力。
迎接第三个挑战的能力是无法在短时间里提高的,我只能倾力回答前两个问题。我用了两年时间进行采访和资料查询,在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杭州、宁波这些城市之间往返穿梭,并三赴北大荒走访农场,还专程去过唐山、丹东、成都等地。让我倍感幸运的是,我的计划和努力得到了一大批兵团人的认同。在寻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很多兵团知青、现役军人和黑龙江农垦人帮我构建起了一条又一条采访链。他们帮助我联系,陪同我采访,和我一起就重要事件的时间、过程、数据、人名等相关信息反复进行核对。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很多兵团人成了可以深谈,可以喝酒,可以交心的同龄好友或忘年之交。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次次被感动,一次次被震撼,也一次次陷入深思。消失近四十年的兵团,在我心中渐渐活了起来,站了起来,动了起来,让我再一次感到从事历史的调查和写作是一件何等充满快感的事情。对我而言,它已经不是工作,不是任务,而是和历史的一种对话。
这种对话不仅使我兴趣盎然,也让我的生活更充实,眼界更开阔,对人性有了更多的感知,透析事物的思想力也得到了一定提升。一般而言,人过六旬后朋友只会逐渐减少,而我在写这本书时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同代朋友,这难道不是对我的一种特殊回报吗?
时间在不知不觉之间消逝,和出版社约好的成书日期几度延迟。我觉得不能继续拖下去了。
过程固然重要,但结果终归是无法回避的。于是我开始盘点素材,确定作品结构,动手写这本书……
在全书收笔之际,三年时间过去了。我感到一种难言的失落,就像必须要和一个朝夕相处三年的好朋友作最终的道别。
无论兵团在亲历者心中的地位如何,它是所有兵团知青、职工和现役军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无论我和它的距离多远,它都进入了我的生命之中,这不仅因为我投入了大量精力去感受它,还因为我在这种投入中倾注了一个知青作家的历史情感。我知道以我这样的写作模式注定不可能高产,但我相信,当一个作家在写作中注入情感时,这本书就会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我把这本书的名字定为《生命中的兵团》。
我希望读者能通过阅读这本书中感受到某种历史温度,并由此引出一些对社会演进和人之本性的思考。果真如此,就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要向所有接受过我采访的人致敬,还要向三年来为我介绍采访对象并提供珍藏资料的朋友表示由衷的谢意。
|
|